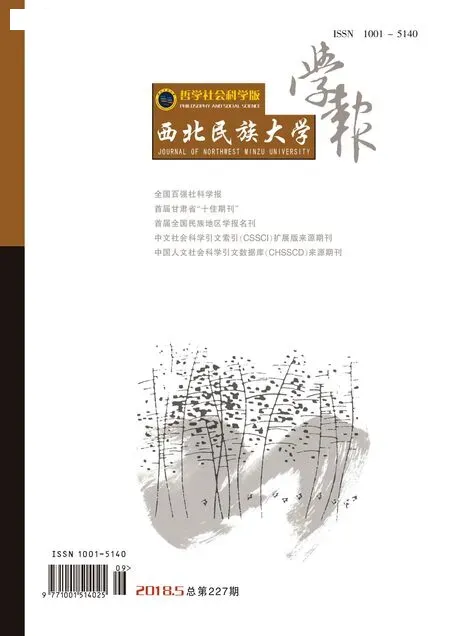试论中古目录类佛典及其序跋
赵纪彬
(河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河南 新乡 453007)
中古*在本文,“中古”指的是始于建安元年(196年),止于北宋(960年)的建立,横跨764年。被视为我国佛教的繁盛期,随着佛教的深入发展,佛典的数量日益增加对佛典的查阅造成一定不便,为之编制目录成为需要,目录类佛典由此产生。目录类佛典是产生于中古时期的一种新类型佛典,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佛典的类型,改变了之前佛典类型的单一,在我国佛典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意义。中古目录类佛典的形成,为其序跋记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目录类佛典序跋记形成于中古时期,是序跋记题写在中古目录类佛典领域的延伸,体现出中古佛典序跋记题写范围的扩展。中古佛典序跋记在延及目录类佛典领域之时,亦为目录所影响,致使自身带有目录的意味。整体观之,中古目录类佛典序跋记包括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与目录化的佛典序跋记,二者有异有同。与其他中古佛典序跋记相比较而言,目录类佛典序跋记在形式、内容、功能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特色,它理应有所发展,然而此类佛典序跋记呈现出薄弱情形,产生时间晚、数量偏少、参与者屈指可数,尤其是具有目录作用的佛典序跋记在隋唐时期并未得以延续,其发展状态由多种因素所致。
一、佛典目录的流变
何谓目录,著名文献学者王欣夫先生认为“目”指的是“书中的篇目”,而“录”则是“合篇目和叙的总称”,将二者合为一者则始于刘向。刘向在整理典籍时“爰著目录,略序洪烈”[1]。其实目录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它萌芽于先秦时期,今人余锡嘉先生认为“《诗》《书》之序,即其萌芽”[2],《诗》《书》之序可能为孔子所作,其中包含了目录的元素。尽管目录萌芽于先秦时期,然而它的发展极为缓慢,至刘向时始定型,并且开始应用于典籍的整理活动并且趋于完善,其中以刘歆的《七略》最具代表性。刘歆的《七略》在撮取刘向《别录》的基础上而成,并对所存典籍进行分类,形成“七略”,也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并对其中每一“略”予以详细述之,如诗赋略著录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类作品。刘歆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目录文献,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在其基础上编纂而成。
经过刘向、刘歆父子之手,我国目录学的体制基本形成,然而延及佛典领域则经历了漫长过程。佛典目录的形成具有渐进性,并非一次性定型。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认为佛典目录雏形于安清与支谦,“佛教目录之兴,盖伴译经以俱来。观乎后竺法护、释真谛之译经有录,则始创佛录者,其安清、支谦之伦”[3]237。安世高、支谦来华的时间相对较早,在我国翻译与整理了大量佛典,这就为佛典目录雏形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四十五与三十六之数亦非寡少,其必有一纸账单以为备查之用,实系事势所趋,不得不然者;而此账单纵极简陋,亦目录之雏形也”[3]238。安清、支谦有一些以备查用的“佛典账单”,这些“佛典账单”可被视为我国早期佛典目录的雏形,为佛典目录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安清是安息国之人,在汉桓帝之初来华,历时二十余载,翻译三十余部佛典。支谦是天竺人,在汉献帝时(190年—220年)来华,在华的活动期间,共翻译与整理了《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49部佛典。若以此论之,我国佛典目录始雏形于安世高所完成三十余部佛典翻译时的公元168年,这就与刘向、刘歆父子完成典籍整理与编目的公元前6年相隔了174年,较之我国其他典籍的目录,它的形成时间相对较晚。我国佛典目录雏形是在早期来华域外僧人的推动下才得以确立,域内人士所编纂的首个佛典目录可能是朱士行的《汉录》,它编纂于朱士行从雍州西行求法(260年)之前,比安世高所完成佛典翻译的时间晚了近百年。
从严格意义而论,尽管安世高、支谦手中以备查用的“佛典账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佛典目录,仍然为佛典目录的编纂提供了借鉴,如朱士行的《汉录》、竺法护所撰的《众经录》等。较之安世高、支谦的“佛典账单”,朱士行的《汉录》、竺法护的《众经录》均有一定提高。之后的支敏度编撰有《经论都录》《经论别录》。经过长期的目录编纂经验积累之后,降至道安法师,我国佛典目录正式形成,其《综理众经目录》被视为我国佛典目录的鼻祖。《综理众经目录》编纂于东晋宁康二年(374年),收录了东汉至晋孝武帝时(372年)的汉译佛教典籍及其注经之作,凡六百三十九部八百八十六卷,该书分为经论录、古异经录、失译经录、凉土失译经录、关中失译经录、疑经录等部分。尽管道安法师的《综理众经目录》已经佚失,然而它在中国佛典目录史上具有一定价值,为后之佛典目录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则是在它的基础上编纂而成。
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可能是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炼子认为该书“原为十卷,当撰于齐代”[4]10,该书并非一次性完成,在释僧祐入梁之后随着资料的丰富而不断得以补充,“直至次年僧祐去世以前,皆在不断增补之中”[4]11。释僧祐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年),他在去世的前一年即梁武帝天监十六年(517年)仍然在完善《出三藏记集》。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包括四个部分,凡十五卷,依次为撰缘记(卷一)、铨名录(卷二至卷五)、总经序(卷六至卷十一)、述列传(卷十二至卷十五),它保存了大量佛典文献及僧众事迹,在我国佛典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我国佛典目录形成脉络的梳理可知,它伴随着佛典数量的增加而逐步形成,萌芽于安清、支谦等手中以备查用的“佛典账单”,与我国最早的目录萌芽——《诗》《书》之序则相隔久远,至道安法师于宁康二年(374年)完成《综理众经目录》的编纂而正式形成,不过此时距我国目录体制形成的公元前6年已经相隔380余年,与我国其他典籍的目录相比较而言,佛典目录的形成时间相对较晚。整体观之,我国佛典目录的发展较为缓慢,从公元168年的萌芽到公元374年的正式形成,历时二百余载,由最早佛典目录文献的正式形成到现存佛典目录文献的编纂又间隔了二百余载,因此从佛典目录的萌芽到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历时四百余载。
二、中古目录类佛典的形成
尽管目录被引入我国佛典领域的时间相对较晚,佛典目录的发展相对缓慢,在中古的数百年间仍然产生一定量的目录类佛典,如表1所示:
表1中古目录类佛典列表[注]本表格选取自姚名达先生所编制的“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中国目录学史》,第231页-236页)。

由表1可知,一是目录类佛典在中古时期有所发展。在中古时期,共有50人参与了目录类佛典的编纂活动,形成60篇目录类佛典。目录类佛典的编纂活动在中古时期一直得以延续,在各个历史阶段均有参与者及相关作品产生,因此目录体制在中古佛典领域逐步确立,其价值逐渐得到认可。
二是通过对中古目录类佛典名称的梳理可知,它们多冠以“某某录”、而“某某目录”者仅有16篇,其中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9篇,隋唐时期7篇,因此目录的称谓在中古佛典序跋记领域尚未盛行,与其他典籍的目录相比则略显滞后,因为“目录的名称自晋以后都通用”[5]。
三是中古目录类佛典的编纂者多为僧众,在50位的编纂者中,其中11人身份不详,在39位可知身份的编纂者中,除王俭、王彦威、李廓、刘勰、阮孝绪5人之外,其余34人均为僧众,约占此时目录类佛典编纂者的68%,与中古佛事活动的构成主体相一致。
四是中古目录类佛典编纂者的平均编纂量偏低,50人共编纂了60篇,平均每人一篇多点,这一现象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除释道流与竺道祖编纂有4篇,支敏度编纂有2篇之外,其余每人均编纂了1篇。降至隋唐时期,编纂者单产量偏少的状况有所改变,14人共编纂了21篇,平均每人一篇半,其中以释智升所编纂的4篇为最多,编纂2篇者有4人,编纂2篇及2篇以上者共5人,约占隋唐目录类佛典编纂者总人数的36%,这一比重较之汉末魏晋南北朝有明显的上升。中古目录类佛典编纂者的编纂量之所以偏低,可能由下述因素所致。首先,中古目录类佛典的属性所致,中古目录类佛典需要以一定数量的佛典文献为基础,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在此过程中需要搜集、校勘、辨伪各类佛典文献,若佛典文献散佚则增加了编纂工作的难度,因此中古目录类佛典的编纂是一个系统庞大且有一定难度的工作,较之其他目录类典籍的编纂则更耗时费力,编纂者的平均编纂量偏低乃自然之事。其次,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环境所致,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对当时目录类佛典的编纂活动有一定制约,如佛典文献的散佚、编纂社会环境的不安定无形中增加了编纂的难度,导致其编纂量的过少。降至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稳定,这一状况有所改变,然而由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类佛典文献的编纂量过少,造成了中古目录类佛典编纂者的编纂量在整体上偏低。最后,中古目录类佛典文献对其编纂者素质要求过高所致,较之其他典籍的编辑,目录类佛典对其编纂者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因为佛典多来自域外,是域外文化的载体,由域外语言书写,这就对其编纂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而他们素质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无疑制约了中古目录类佛典的编纂,致使它的编纂量偏少。
三、中古目录类佛典序跋记的双重性
在中古时期形成60部目录类佛典,这就为目录类佛典序跋记的题写奠定了一定基础。在中古时期,序跋记趋于成熟,其影响力有所扩大、价值为世人所认可,由此促使序跋记延伸至中古目录类佛典领域,目录类佛典序跋记应运而生。事物之间的影响往往是双向的,序跋记在延伸至中古目录类佛典领域并产生目录类序跋记的过程中,也为目录所影响,致使中古佛典序跋记带有目录的意味。中古目录类佛典序跋记包括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与具有目录意味的佛典序跋记,其中后者的题写对象——佛典不一定具有目录属性,而它的序跋记可能具有目录的意味。
中古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由前文所述可知,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文献可能是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并且该佛典写有序文。《出三藏记集序》的内容较为丰富,囊括了《出三藏记集》的编纂起因及其体例构成等,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我国佛典目录文献序文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现标志着序跋记的题写正式延及中古佛典目录文献领域,彰显出中古佛典序跋记题写领域的延伸,其意义值得肯定。自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之后,伴随着佛典目录文献的编纂,佛典目录文献序跋不断形成,如表2所示。
表2中古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分布表

由表2可知,在中古时期有7人参与了佛典目录文献序文的题写活动,形成9篇作品,在整体上较为薄弱,尤其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唯有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序》一篇。今人傅秀莲认为《出三藏记集序》的撰写于“当在建武五年之前”[6],齐建武五年为公元498年,而《出三藏记集序》可能作于释僧祐去世之前与《出三藏记集》初稿形成之后,即齐建武五年(498年)至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年)之间,具体时间则不详。
试看隋唐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的作写时间。其中《大隋众经目录》编纂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由于其编纂者释法经的生卒年不详,因此《大隋众经目录序》书写时间的上限是隋开皇十四年(594年),下限则无法断定。《历代三宝纪》编纂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年),由于该佛典的编纂者费长房的生卒年不详,因此《开皇三宝录总目序》作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年)之后,具体时间则不详。《大唐内典录》编纂于唐麟德元年(664年),同时该佛典的编纂者释道宣生于公元596年,卒于公元667年,而《大唐内典录序》《大唐内典录后记》只能写于《大唐内典录》之后与释道宣去世之前,也即公元664年至公元667年之间。《续大唐内典录》由释智升所编纂,具体编纂时间则不详,《续大唐内典录序》则由释道宣题写,现存各类大藏经多标为“麟德元年于西明寺起首移总持寺释氏撰毕”,该佛典序文可能题写于唐麟德元年(664年)。释智升在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完成了《开元释教录》的编纂,由于《开元释教录序》只能题写于《开元释教录》成书之后,因此《开元释教录序》题写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之后,具体时间则不详,因为其题写者释智升的生卒年不详。《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由佛授记寺70名高僧在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编纂而成,《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序》只能撰写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成书之后,因此释明佺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序》写于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之后,具体时间则不详。《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编纂于唐麟德元年(664年),“麟德元年,奉敕编次经论,撰成《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7]。《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只能写于《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形成之后,因此《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题写于麟德元年(664年)之后,由于《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的书写者释静泰的卒年不详,因此导致无法界定其所形成的时间下限。在隋唐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的写作时间上,可能以释法经的《大隋众经目录序》及费长房的《开皇三宝录总目序》为最早。
由上述可知,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序》至少作于齐建武五年(498年)至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年)之间,释法经的《大隋众经目录序》、费长房的《开皇三宝录总目序》的写作时间至少与之分别相隔了76年及79年,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由汉末魏晋南北朝向隋唐时期发展的过程中曾一度间断。总而言之,中古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在数量上整体偏少,参与者屈指可数,相对于其他典籍的文献序跋而言,它在多个层面上呈现出薄弱态势。然而中古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的形成具有一定意义,在一定层面上暗示出中古佛典序跋记题写范围的延伸,并且这种延伸具有一定延续性及持续性。尽管中古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的发展态势在整体上呈现出薄弱情形,然而这种薄弱态势具有阶段性差异,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较而言,隋唐佛典目录文献序跋记在数量上、题写者等方面均有所提升,写作时间相对集中,其中4篇集中写于唐麟德元年(664年)之后,其余4篇的写作时间也相隔不久,因此它“弱”中有“强”,呈现出强化之势。
目录化的中古佛典序跋记。序跋记在引入中古目录类佛典文献领域并产生与之相关序跋记之时,自身也为目录所浸染。目录的体制与形式可能为中古相关佛典序跋记的题写者所借鉴,由此致使中古佛典序跋记融入目录的元素,然而其题写对象——佛典本身可能不具备目录文献的性质。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的“杂录序”,所收录的11篇佛典序跋具有目录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中古佛典序跋记目录化的倾向,如表3所示:
此类佛典序跋记具有固定模式,先阐释与佛典相关的内容,“每披圣文以凝感,望遐踪以翘心。遂搜访古今,撰《萨婆多记》。其先传同异,则并录以广闻;后贤未绝,则制传以补阙。总其新旧九十余人”[4]466,交代了《萨婆多记》的成书起因、章法与叙事策略、内容。“每服佩思寻,惧有坠失,遂集其旧闻,为《义记》十卷”[4]496,交代了《十诵律义记》的成书原委及其卷帙情况,相关事例不再一一举之。随后罗列了相关佛典构成篇目的目录,限于其中的复杂性于此不予列举之。由上述可知,释僧祐始将目录元素引入中古佛典序跋记,他在围绕书写对象题写序跋记时,罗列了其构成篇目的目录,致使中古佛典序跋记带上目录的意味,此乃中古佛典序跋记形式的新变,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意义。然而具有目录意味的佛典序跋记在隋唐时期并未出现,它是汉末魏晋南北佛典序跋记所特有的形式。
表3中古佛典序跋记目录化一览

序跋记由于题写范围的扩大而延伸至中古目录类佛典领域,在此过程中亦为目录影响,从而带有目录的意味,二者形成互动,由此产生双重意义,一方面扩大了中古佛典序跋记的题写范围,致使序跋记的题写延伸至中古目录类佛典领域。另一方面导致中古佛典序跋记含有目录的元素,丰富了此类佛典序跋记的形式。
综上所述可知,目录萌芽于《诗》《书》之序而定型于刘向、刘歆父子之手,随着佛教的发展与佛典数量的增加而延伸至佛典领域,佛典目录由此逐步形成。纵观我国佛典目录的发展脉络可知,它发萌芽于安世高、支谦等手中以备查用的“佛典账单”,至道安法师的《综理众经目录》正式形成,由于该佛典尚未保存,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是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古目录类佛典为与之相关的序跋记提供了题写对象,目录类佛典序跋记随之形成,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序》可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类佛典序文,该佛典序文的产生在一定层面上映射出佛典序跋记题写领域在中古时期的延伸。序跋记在延伸至中古目录类佛典文献领域的过程中,又受到目录的影响,致使自身融入目录的元素,由此丰富了中古佛典序跋记的形式。在中古目录类佛典序跋记的发展过程中,释僧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把序跋记的题写延伸至中古目录类佛典领域,题写了中古首篇佛典目录文献序文——《出三藏记集序》,而且首次将目录的元素引入中古佛典序跋记领域,在写作的过程中加以借鉴,由此导致某些中古佛典序跋记带有目录的意味,然而此类佛典序跋记在隋唐时期并未得以延续,因此中古目录类佛典序跋记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残缺,相关要素并未得以完整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