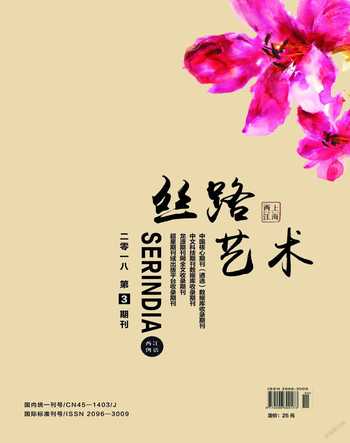范百禄与元祐年间的党争
王瑜君
一、元祐年间的政治氛围及其趋势
(一)元祐年间的政治走向
朋党之争历代有之,宋代也不例外。宋代的党争萌芽于宋太宗时期,在宋仁宗景祐、庆历年间,由庆历新政而引发庆历党议,将党争推向高潮。至元祐年间,因宋神宗推行的熙丰变法不能挽救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再次引发新的党争。哲宗九岁登基,由高太后垂帘听政,大量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成员。宋神宗在推行王安石变法之时,遭到慈圣、宣仁两位太后的反对。高太后对新法持反对态度的,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其执政期间的政治态度。元丰八年六月,“以吕公着、司马光推荐的人选为基础,高后大量提拔熙丰时期对新法持异议的官员,以组成一个新的官僚体系……占据了台谏、吏、户部长官等要职。”[1]最高统治阶层对人事的安排也表明他们为废除新法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此举明显是加深了新旧党人之间的矛盾。旧党上台的初期,便着手罢废新法,同时还排斥“新党”成员。因此,哲宗年幼是无法左右政局的,而高太后是一位常年深居后宫的女主,在此之前是不能干预政治的。她在垂帘听政期间要受到赵宋王朝祖宗家法的制约,其从政的经验和眼界是不如宰执大臣的,尽管掌握了最终的决策权,但在政事的处理上十分依赖宰执,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元祐年间的政治局面并不掌握在最高统治者的手中,而是由担任重要职务的旧党成员所左右,政治氛围也由这些人所营造,保守倾向在朝堂上处于优势地位。
(二)学术思想与元祐党争
蜀学在元祐年间盛极一时,范百禄也是蜀学的著名学者之一,治学方面以儒家思想为主。他提倡儒家尊亲爱民的道德观念,反对酷刑劳民的施政理念,并多次劝谏君主广开言路。在元祐年间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朔学、蜀学、洛学之间的學术争鸣和学术活动也受到政治氛围的影响。蜀学虽在当时各个学派的争鸣中占据优势地位,但也受到朝堂上朋党相争的影响。然而,北宋士大夫拥有的集文人、学士、官僚于一身的复杂性,致使蜀党、苏门、蜀学彼此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蜀学虽是宋学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个分支,但其思想对蜀党成员意识形态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凝聚蜀党成员的重要支柱。蜀党从政治的角度看,是党争的产物。而蜀学从学术活动的角度看,是当时学派争鸣的产物,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也是朋党相争的结果。蜀学的成员日益壮大,日后也逐渐成为党争中的一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三者的关系:作为北宋党争的产物——蜀党,苏氏蜀学是其立党思想,而苏门则是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2]
二、范百禄涉及党争的具体事例
(一)参与差役法的论争
差役法自唐朝开始实行,宋承唐制,里正、户长、散从官等差役由民户轮充。至太平兴国五年,制定差役法。宋神宗时期推行王安石变法,将差役法改为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由官府雇人服差役,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依据自身的贫富等级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的钱。从免役法的影响来看,其弊大于利。它的弊端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免役法的政策超越了当时的现实,推行上面临巨大的阻力;二是免役法与青苗法、市易法等一样,具有明显的敛财性质,加重了民众的负担。[3]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提出恢复差役法,这与免役法在当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有关的。此时,朝堂之上旧党成员已占据重要职位,政治局面掌控在他们的手中,且旧党内部尚未明显的分化为洛、蜀、朔三党。旧党的党魁是司马光,他明确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方面,旧党成员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始议复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司马光曰:“熙宁初,百禄为咸平县,役法之行,罢开封府衙前数百人,而民甚悦。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剥。为法之害。今第减出钱之数以宽民可也。”光不从。……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且谓:“乡民被徭役,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赇遗人,既以重法绳之将见当黥衣赭充塞道路矣。”
免役法实施初期受到了百姓欢迎,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官吏的盘剥,弊端突显。范百禄提出“减差钱之数以宽民力”作为解决的方法,表明他不同意完全废除免役法。但司马光并不采纳他的意见,坚持废除免役法。在免役的废罢方面,范百禄与司马光的意见不一致,二人甚至产生了争执。元祐初年,新旧党主要围绕新法罢废展开争论,范百禄也参与其中,他虽是旧党的成员,但他的政见是偏向支持免役法的,同时他也承认免役法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官吏盘剥百姓的弊端。这也符合当时“保守派中不少人或从新法的实际成效考虑,或从政府财政及国防、治安需要出发,不同意完全废罢新法”[4]的倾向。因此,新法的“废罢”过程相当漫长,既有来自新党的攻击,也有保守派内部政见的分化。
(二)封还李定词头事件
范百禄在担任中书舍人期间,与苏轼参与了3次封还词头的事件,其中一件涉及到新党的成员李定。李定曾是政坛上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人物,“在王安石被罢免之后的元丰年间,李定在朝中任御史中丞,对三舍法进行整顿。这之前的熙宁二年末,他已是王安石的门下,又明确表示支持新法,因而被王安石任用为《三司岁计》及《南郊式》的编纂官。”[5]宋代,中书舍人封还词头的发展与封驳司封驳职权的衰落相呼应,中书舍人以封还词头的形式逐渐取代了封驳司旧有的封驳职能。元祐年间的政治局面,使中书舍人的封驳职能成为党争中的一道工具。而高太后垂帘听政之初,便设立看详诉理所,其目的是为反对变法受到打击的官吏昭雪平反。同时起用大量旧党成员,如司马光、吕公着等,而罢黜蔡确、章惇、吕惠卿等新党成员。此时朝中的政治局面是偏向于旧党,政治风向也被旧党所掌控。元祐元年五月甲戌,苏轼、范百禄上奏:
“李定备位待从,终不言母为谁氏,……落龙图阁直学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许于扬州居住。臣等看详李定所犯,……朝廷勘会得实,而使无母不孝之人,犹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教,为害不浅。兼勘会定乞侍养时,父年八十九岁,于礼自不当从政。……考之礼法,须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词。”[6]
根据规定,只有中书舍人之间意见统一的时候,才能确实保证封还词头职能的行使。其次,即使中书舍人意见一致,当舍人不肯草词之时,即便于制不合,会招致非议,仍可以用熟状行下,绕过舍人草词的程序。[7]上述材料表明,苏轼、范百禄二人的处理意见一致,不撰写李定的词头。但之后的有关的材料仅见于“五月十八日,定初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扬州居住。”可见,对李定的处置是绕过了舍人草词的程序。但当时新旧党之间激烈的斗争并不会因此停止,苏轼、范百禄认为定刑太轻,要求严厉责罚李定。元祐元年六月甲寅,左司谏王岩叟言“李定不持生母仇氏服,乞行窜殛。诏定责授朝请大夫、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滁州居住。”在旧党人士的攻击之下,朝廷还是对李定的处理稍作修改,责授为朝请大夫、少府少监,将扬州改为滁州居住。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旧党主导政局占据优势地位,李定等新党成员已处于被旧党攻击的地步。李定是变法派的坚定支持者,而苏轼、范百禄则是旧党的成员,对李定词头的撰写与否则是两党之间的一场较量。李定本人的行为又存在诸多不合礼制之处,这更有利于旧党对其进行打击。
熙宁年间,李定曾被御史台陈荐揭发他不为生母服丧,此时正值新党在宋神宗支持下推行新法,而有关此事的讨论也只是导致李定未被授予御史一职,并没有对李定做出更深层次的处罚。至元祐年间,旧党上台执政,仍抓住熙宁年间的事情对李定穷追猛打,从道德的角度继续追责,并不是依据已经出台的法律规定对其惩处。而且李定事件的疏漏之处是范百禄等人的奏章并未提到李定从政期间有何奸邪之事,他们不撰写词头的原因是李定的行为有违孝道。由于元祐年间的政治氛围是旧党成员共同致力于打击新党,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决定了对新党成员的打击是不断寻找借口。因此,从法制层面看,对李定的处罚与规定不符,缺乏李定从政期间的不法之事。但从道德角度看,李定不赡养年迈的父亲,则是大逆不道。从党争的大背景看,对李定的打击和贬斥则是排斥新党计划中的一部分,采取何种政治手段并不是很重要,成功排斥新党成员才是最终的目的。此时,范百禄是旧党成员中打击新党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同时也充当了党争中的一把利刃。
(三)范百禄引荐川人与党争
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这为隐藏己久的各派冲突提供了一个契机,朔、蜀、洛党争致使旧党内部开始的瓦解。在对新党成员的打击力度上,旧党内部产生了分歧。洛党对此持反对态度,蜀党二苏则主张将新党一网打尽。二苏对新党的态度,也使他们在哲宗亲政后的政治命运伴随着旧党的失利发生了扭转,蜀党也逐渐走向衰落。元祐八年三月,范百禄上奏说:“台官言苏颂稽留贾易知苏州诏旨,累起罢免。劾章所指虽不及臣,臣实何苟逃罪戾?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职。”范百禄所说是实情,但从禁中所出的诏令是允许他继续任职。该年的三月至九月期间,朝中的政治风向已开始向宋哲宗亲政倾斜。九月,高太后去世,这也意味着旧党丧失了坚定的支撑者,为新党的重新上台提供了机遇。蜀党因其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常被洛、朔党攻击,蜀党的很多成员也随之从中央调离。而监察御史黄庆基对范百禄的攻击,则为范百禄的离职加上了致命的一击。
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宰臣苏颂近以稽留制书、援引亲党、除授不当罢政。……今来苏颂既罢,所有中书侍郎范百禄实预职事,岂可不任其责?……则其罪有二:一则朋比宰相,欺罔朝廷,不守典法,是不忠也;一则内怀险诈,恣颂所为,阴图倾夺,是不正也。”侍御史杨畏言:“窃惟稽滞制书虽出于苏颂之意,而中书侍郎范百禄既同职事,实亦瘝官。”监察御史来之邵言:“中书侍郎范百禄既同职事,无所建明,亦不能逃连坐之责。”[8]
范百禄受到攻击均来自台谏官,而此时的台谏已朝着病态的方向发展。他们对范百禄的攻击也有合理之处,苏颂稽留文书之事,范百禄作为中书侍郎是不能脱去干系的,但黄庆基对他所定的二罪则过于偏激。杨畏在党争之中,其态度摇摆不定,偏向于朝堂中占优势的一方。来之邵善于揣测时局,并无专一的政治态度。因此,他们对范百禄的攻击缺乏真凭实据,仅靠言辞予以攻击。
台谏官又以范百禄多次引荐川人参与政事或担任要职为由继续弹劾。“按百禄自执政以来,援引吕陶为起居舍人,……皆川人也。……以宋炤知凤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首先吕陶担任起居舍人与范百禄并无直接的关系。通过查阅史料,对吕陶所担任的官职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元祐四年六月,苏辙推荐吕陶担任谏官。八月,贾易上奏弹劾苏辙、苏轼和吕陶等人结为朋党。元祐六年,吕陶改任为右司郎中,元祐七年(1092年),又任起居舍人。在梳理史料过程中发现,吕陶由谏官至担任起居舍人的过程中,未见到范百禄推荐的史料,而且由谏官改任起居舍人与之前贾易的弹劾有关,与范百禄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不能证明吕陶担任起居舍人是范百禄所引荐。御史虽可风闻言事,但此事明显缺乏有力的证据。有关宋炤的资料更是缺乏,扈充也仅在其他文献中见到于元祐六年举升清要,并未提到是何人荐举。因此,仅就吕陶来看,黄庆基所言不实,不足以证明范百禄在从政期间大肆引荐川人。
黄庆基甚至罗列了范百禄的五宗罪,这其中多是借川人势盛之名打击范百禄,而且弹劾的对象被扩大到蜀党。“近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朋比欺罔,很愎自任,援引党与,……前日陛下罢黜刘挚、王巖叟、朱光庭……而后洛党稍衰。然而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百禄之亲戚朋游,皆在权要,……今因罪状明白,早赐罢黜。”黄庆基弹劾范百禄是以其援引朋党之名,以及专擅权力之罪弹劾,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证明范百禄的这些罪行,同时还言明洛党衰落之后,蜀党趁势壮大。黄庆基的奏章中还提及范百禄的亲戚朋友多人担任显要职务,这也都是由于范百禄的引荐,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并不属实的事件,成为了黄庆基弹劾范百禄的资本。
黄庆基因冯如晦的案件再次上奏弹劾范百禄,但该案件并不属实。“冯如晦为户部郎中,坐前任夔州路转运使日按发公事不当,御史台究治未结绝间,百禄以其同乡,遽除馆职,差知梓州。……违朝廷之法,徇乡里之私,其罪三也。”[9]《苏辙集》记载,“监察御史董敦逸上言‘近为川人太盛及‘差遣不公等,因言冯如晦缘翟庠推勘公事,枉陷徒配杖刑人数不少,系圣旨下御史臺取勘,更不候事了,便除如晦馆职,知梓州。”冯如晦被授予馆职并不是因为范百禄和他是同乡,而是案件未了结之前,圣旨下至御史台所致。御史中丞李之纯及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亦言:“二人诬陷忠良,朝廷容贷……得意任私,敢肆狂诬。”这二人是指董敦逸和黄庆基,他们多次所言不实,已是常态。因此,黄庆基对范百禄的构陷也是查无实证。从上述材料中,我们也可看到当时蜀党势力过大易招来各方的攻击,政治局面也随之受到影响。范百禄因受苏颂案件的牵连而被台谏官弹劾,从职责上来看,他确有失职之罪,但以援引朋党为名的弹劾是不属实的。
此时朝中的政治局势是蜀党被各方所攻击,蜀党成员也不断从中央被调出,旧党内部严重分化,新党积极准备上台执政。因此,以朋党之名作为弹劾的罪状也逐渐成为党争中的常态,即便没有朋党,也不能避免自身被构陷为朋党的罪名。而范百禄被贬,也是其步入党争中的必然结果,他最终以同省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徙河阳、河南。
元祐党争是北宋政坛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承接了来自熙丰党争的消极影响,并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元祐元年,高太后垂帘听政,对政务的处理十分依赖于当政的宰执。而她对司马光等旧党成员的重用,使得朝中的政治局势朝着有利于旧党的方向转变。但在废罢新法的问题上,旧党成员内部意见不一,也在对是否过度打击新党成员上产生了矛盾。范百禄与司马光就差役法的废罢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在打击新党成员方面较为积极。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内部的问题就暴露出来,蜀、洛、朔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新党趁势发展,政治局势也逐渐发生转变,最终蜀党被排挤,范百禄也不可避免的沦为被攻击的对象。台谏的恶性发展,更加速了他个人的政治生涯的终结。
注释:
[1]张云筝:《论宣仁圣烈高太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年06期,第85页。
[2]李真真:《蜀党的立党及成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05期,第39页。
[3]方宝璋:《再论宋代免役法的利弊》,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2012年05期,第66页。
[4]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6页。
[5](日)近藤一成:《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1页。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是日,第9178页。
[7]宋靖:《唐宋中书舍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87页。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2,元祐八年三月乙酉,第11466页。
[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2,元祐八年三月乙酉,第11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