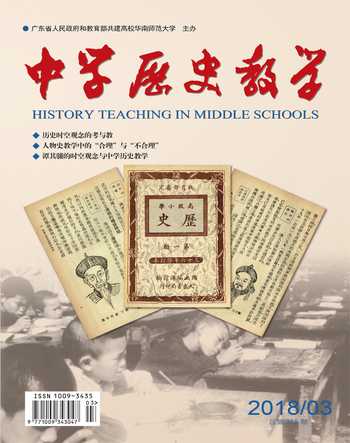以图证史应给予合理的解释
刘忠奎
以图证史是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法之一。在2016年出版的北师大版七年级上册历史教材中,有一副图片“桀驾人车”。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通过展示此图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来得出夏桀腐朽荒淫和残暴的结论,力图使学生对夏桀的暴政有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教材中对于此图片没有任何必要的说明和解释,由本图片出发可以印证夏桀的残暴吗?此图片背后又隐含着哪些重要的信息呢?
无论是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亦或是旧版初中历史教科书,在编写“夏朝的建立”一节时,基本上均在选用此图。这幅图片是一幅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石刻画石像的拓片,是画石像中十副描绘中国古代帝王像之一。该画石像中除榜题“夏桀”可辨明人物身份外,无其他文字记载。在选用此图片作为教材插图时,各版本教材对图片的命名说法不一。一般称为“骑在两个妇人身上的夏桀”,也有的称为“以人当坐骑的夏桀”或“桀把人当做坐骑”,唯有2016年出版的北师大版七年级上册历史教材称此图为“桀驾人车”,并作脚注“画像描绘夏桀骑在跪伏地面的两妇人肩上,如乘‘人车。”[1]从表面意思来看,“桀驾人车”与“骑在两个妇人身上的夏桀”大意相类,但显然“桀驾人车”更富有深意。那么什么叫做“桀驾人车”呢?“桀驾人车”一词出自于《后汉书》卷83《井丹传》,信阳侯阴就约井丹赴宴,当阴就宴席中起身时,左右进辇,于是井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2]井丹用夏桀的例子对当时的外戚专权进行了有力的讥讽。当然,这种讥讽仅是一种借喻。北师大版七年级上册历史教材对此图命名显然源自于这个典故。
尽管后人对夏桀暴行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夸大,但夏桀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暴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在位期间,“筑倾宫、毁容台”[3],作琼室、立玉门,极尽荒淫之能,司马迁称其:“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4]以致于百姓咒骂“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5]祈为上苍,“降灾于夏,以彰厥罪。”[6]为着力突出夏桀的暴政,2016年出版的北师大版七年级上册历史教材选用了“桀驾人车”作为实物史料来进行补充印证。但相对于夏桀的大兴土木、长年征战以致民生困苦而言,“桀驾人车”从表面意思来看,在印证夏桀的暴虐无道上是很牵强的。“桀驾人车”图片的主体是夏桀骑在两个妇人身上,关于图中两个妇人的身份,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字记载,不可考。但由其服饰和装束出发,极有可能是姬妾或宫女。她们被绳索缚在一起,双膝跪伏,面目痛楚,作为夏桀的坐骑。夏桀则跨在以两妇人充作的人车上,肩上负着武器。夏桀身躯硕大,两个妇人瘦小纤弱。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凭借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和权势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夏桀作为夏朝最大的奴隶主,做出驾人车的荒唐事是很正常的。但这仅可以证实在夏朝妇人的社会地位卑微,是奴隶主肆意把玩的工具。
那么,在这幅东汉时期的画石像中,夏桀真的仅是把人充当驾车的工具吗?从北师大版七年级上册历史教材对此图片命名的引据出发,该图片描绘的很可能是夏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刑罚——耻辱刑。什么是耻辱刑呢?用现代语去解释,耻辱刑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惩罚,“以公开侮辱犯罪人的名誉和人格为内容的刑罚方法”[7]。就我国来说,耻辱刑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尧、舜时期,那时的象刑就是最早到耻辱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8]。关于象刑究竟是什么历代论者说法不一,目前尚未达成一致。但一种最有说服力并为大多数论者所认可的观点认为,象刑是“通过对犯罪人加以特异的衣冠服饰来象征刑罚”[9]。象刑是一种象征性、虚拟化的刑罚,服饰的不同代表着犯罪人所受的刑罚不同。到了夏朝时期,耻辱刑已广泛流行。耻辱刑或单独使用,或与肉刑搭配使用,以起到对人民的精神震慑来达到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显然,耻辱刑在夏朝时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刑罚。
已故的于省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专家,他对很多甲骨文字都曾进行过有力的考释。他认为,甲骨文中,“尼作 形或 形,均像一人坐于另一个人的脊背之上。”[10]这便是甲骨文所载属于身体蹂躏性质的耻辱刑。于省吾先生进一步认为,这幅来自于东汉时期夏桀的画石像,描述的正是《后汉书·井丹传》所说的“桀驾人车”,反映的是这种存在于夏朝时期的耻辱刑。由图片中夏桀肩上负有武器来看,夏桀不仅在对两个妇人执行耻辱刑,极有可能也在执行肉刑。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对人的折磨相比较来看,肉体的痛楚是短暂的,而精神的痛苦却将伴随人一生。这种坐他人之背,耻他人之心,蹂躏他人之身的耻辱刑,受刑者会饱受内心耻辱之苦,反映了夏桀时期阶级压迫的残暴,也反映出夏桀时期刑罚的残酷。“夏刑三千条”[11],在数量不菲的刑罚中,耻辱刑是其必要组成部分之一。
图片是一种可视的历史符号,是形象化的讯息,也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在一定意义上,它具有比文字语言更容易的辨识功能,表达的内容也更直观丰富,可以立体地起到以图证史、图文互证的双向效用。瑞士文化史学家布克哈特把图片称作“往昔人类精神发展诸阶段之见证”[12]。美国图论学者哈拉里也强调,“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13]。在课堂上运用以图证史的方式,更具直观性,可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有助于教化的推动。或许“桀驾人车”反映的是否为一种耻辱刑仍需进一步考证,但于省吾先生的观点为我们的教学打开了另一扇窗。在教学中,我们不妨采鉴于省吾先生考释的结果,将“桀驾人车”图片从夏朝一种残酷刑罚的角度进行剖析,这样夏桀统治的残暴便会跃然纸上,“桀驾人车”图片即成为反映夏桀时期刑罚残酷的鲜活的史料。这种解释不仅适合教学需要,也更为学生所认可和接受。
【注释】
朱汉国主编:《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范晔:《后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99页。
方诗铭,王修龄校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司马迁:《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孔丘著,何怀远等主编:《尚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第35页。
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八《汤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页。
孙膺杰,吴振兴主编:《刑事法学大辞典》,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11页。
李昉编纂,任明等校点:《太平御览 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3页。
杨鸿雁:《中国古代耻辱刑考略》,《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页。
康有为著,宋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86页。
曹意强:《可见之不可见性——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新美術》2004年第2期。
(美)F·哈拉里:《图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