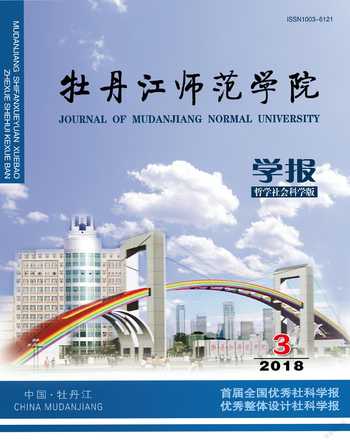《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李寅生 胡艳菊
[摘 要]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世情章回小说,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也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有关《金瓶梅词话》中女性生活的描写,研究者多根据其在生活中的种种表现,集中分析这些女性形象。由法国作家波伏娃的《第二性》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观点切入,对《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加以观照,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所表现出的种种意识和行为并非自愿,而是社会及男性的天然优势使然,是时代和社会影响下的产物。
[关键词] 女性主义;《金瓶梅词话》;第二性
[中图分类号]I242.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18)03-0060-06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世情章回小说,是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在《金瓶梅词话》中,作者兰陵笑笑生运用大量笔墨描写女性生活。在作者笔下,女性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每天围绕一个男人争风吃醋,依附于男人而生存。在古代中国社会,男尊女卑以及以夫为天的思想一直束缚着女性,这在《金瓶梅词话》中表现尤为明显。读者从小说中看不到属于女性的曙光,只得见她们在“以男为尊”的社会里慢慢沉沦,至终变得麻木不仁。而法国女作家波伏娃是女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代表作《第二性》是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使广大女性认清自身处境,努力摆脱“他者”地位,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1]3。表面来看,《金瓶梅词话》所描写的女性与《第二性》认清自身处境,寻求自身解放的女性毫无关联,其实不然。波伏瓦的《第二性》在帮助女性认清自身处境的过程中,分析了女性为何一直处在“他者”地位,即丧失了作为和男性一样存在的独立个体的主体性而依附于男性存在[1]232;分析了为何女人放弃获得自由的权利,甘愿活在男人为其建造的家庭牢笼里,而不去追求自由,也不寻求实现其价值。《金瓶梅词话》中关于女性生活的描写就是这样。几个女子的唯一工作就是为了家里唯一的男主争风吃醋,每天挖空心思讨西门庆的欢心。有了孩子的女人,中心由丈夫转到儿子,没有孩子的女人则想方设法要怀上儿子来巩固在家中的地位。如果《红楼梦》是一部描写女儿国的悲剧,《金瓶梅》更是如此。海明威说过,“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们看”。《红楼梦》中那些美丽女子的悲剧结局往往能够激发人们身上的悲伤因子。而《金瓶梅词话》恰恰相反,其中的女子身上有太多的世俗味,甚至那些女子的举止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金瓶梅词话》中的潘金莲在久等西门庆不来后,无故把气都撒在迎儿身上,其行为令人咬牙切齿。这些情节在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有很多。所以,《金瓶梅词话》中女子的悲剧结局不但没有使读者产生共鸣,反倒让读者无不拍手称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描写女性悲剧的作品,从《金瓶梅词话》这部小说可以略窥明末时期女子作为男人附属物的卑下生活,她们的女性气质,她们的处境,以及她们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2]。以下将针对这些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女性气质
在传统观念上,所谓的“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来赋予的。对此,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做了解释:“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她不仅应当修饰打扮,做好准备,而且应当抑制她的自然本性以长辈所教授的做作的典雅和娇柔取而代之。”[1]241“女性气质”是陶铁柱先生在翻译《第二性》中得出的一个特殊词语。但这种所谓的“女性气质”不论在中国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存在的。比如,中国古代要求女子以夫为天,遵从“三纲五常”,多数妻子第一次见到丈夫也是在洞房时掀开喜帕的一瞬间,而“一夫多妻”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婚姻状态,无论是女子还是男子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的不平等,甚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种关系是理所应当的[3]。女子從小就被教导和熏陶要温良、贤德、大度,一旦违背就会被冠上善妒的罪名,甚至成为女子被休弃的理由。而《金瓶梅词话》中最符合这种“女性气质”的莫过于吴月娘。吴月娘作为西门庆的大老婆,不仅在事业上帮助西门庆,而且家中事无不料理得井井有条。吴月娘出身于官宦之家,她的身上具有官家小姐的气质,因此能够帮助西门庆处理官场上的各样关系。作为西门庆的正妻,她在众多妻妾中很有威望,家中的聚会以及聚会的各样礼制她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同时,她也是一个“贤妻”,无论西门庆纳多少房小妾,有多少情人,她都表现得不介意,甚至成为调节西门庆妻妾之间矛盾的中间人。官家小姐气质使她做不到像潘金莲那样明目张胆地争宠,因为,作为传统的大家闺秀,她要温顺、含蓄,所以在与西门庆冷战期间,她一面放不下官家小姐的架子,甚至在丫鬟都劝她去找西门庆,她仍不肯向西门庆低头;而另一面,晚上她却在后院摆下祭台祈求西门庆的妾早点怀上子嗣[4]。而这一幕恰好被西门庆撞见,看到一心一意为他着想的妻子,西门庆心里十分感动,也正因此两人关系得以修复。如果没有后面潘金莲与庞春梅的对话,读者一定会认为吴月娘是典型的“贤妻”。其实不然,她没有忘记她是依附与西门庆而存在,在这个家里,西门庆才是主人,失去西门庆的宠爱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为自己地位受到威胁的恐惧感迫使她主动消除危机。由上可以推断,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提出的“女性气质”在中国古代女性中也是存在的,吴月娘身上所体现这种“女性气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广大女子的一个“缩影”。
二、女人的处境——“他者”
波伏瓦从处境方面对女性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进行了阐述,并提出“女性是他者”[1]231的重要概念。何谓“他者”?一般人很容易将“他者”与“他人”的涵义混淆,甚至将二者等同。“他者”的概念是由“他人”发展而来的。简单地说,“他人”是相对于他物而言,而“他者”则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由此,波伏瓦给出定义:“他者是指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之下,处于客体地位以及失去了主体人格并且被异化的人。”[1]232波伏瓦提出“他者”问题时,在她的《第二性》中第五部“处境”中明确表示:之所以女性是作为“他者”的身份存在,是要表明“女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按照男人的需求来规划自身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自我和他者、主体与客体、依附与被依附、本质与非本质的关系。相对与男人而言,女人是他者、客体,要依附于男人而存在,其命运就是尊敬和服从男人,而男人始终是主动性、超越性的存在。”[5]
(一)“他者”与客体
波伏瓦说:“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欲望以及男性后面的价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她们仍然是支配地位。由此可见,女人在看待自己和做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在男人面前,她成了一个客体。”[1]238由此反观《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对内,他作为家庭唯一的男性,主导着家中的一切;对外,他凭借生药铺发家致富,由商到官一步步往上爬,靠钱财与统治阶级攀上关系。他依靠钱财任意将女子的自尊踩在脚下,特别是那些唱曲的女子在应伯爵和西门庆等人面前更是毫无尊严,在前一刻还是西门庆的情人,而后一刻就变成了干女儿。更有甚者,在这种不顾伦理道德、身份颠倒的情况下,里面的男女双方居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由此也可以看出,《金瓶梅》中的男人一直处于主体地位,而里面的女人只能沦为客体。
(二)“他者”与内在性
内在性是指女性被封闭在狭小的空间,被动接受自身处境,思想停滞,无所事事而又无所作为的一种生存状态。[1]673中国古代,女子的成长环境就是养在深闺。深闺禁锢了女子的身体,也禁锢了她们的心灵,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所受的教育是三从四德,如何对待夫家、夫君。《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家的后院每天都在上演争风吃醋的戏码。本文认为,并非她们想围绕西门庆转,实际上除了为这个后院唯一的男人争风吃醋外,她们已经找不到任何事情可做。正因为有这件事可做,她们才会在生活中找到些许刺激。换句话说,是争风吃醋这件事情的本身来证明她们存在于这个世界,进一步讲,争风吃醋这件事让她们找到了存在的价值感,让她们意识到她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三)他者与被动性
女人作为“他者”缺乏主体性,显示出被动性的特性。波伏瓦在《第二性》的“生物学依据”[1]3这一章中,针对女性为何具有被动性的特征指出,两性应该是不同的,一个是主动的,另一个是被动的,被动性是属于雌性的。在性这一方面,女性是被动的,她成为男人的猎物、财产,任凭男人占有和剥削。许多学者认为,《金瓶梅词话》最大的败笔就是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笔者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性描写有其深厚的思想背景,这部小说成书于明代末期,当时的思想家,如李贽等人开始强调人正常的欲望[6]。而《金瓶梅词话》中的性描写不过是对这种思想的一个回应,也是以此来对封建社会的控诉。而且,正是其中过分的性描写才使得这部小说一直有争议,而争议才会使得人们对它的持续关注,并进一步研究,发现其中更多的价值,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奇书”。《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在性方面的确是被动的,任凭男人占有和剥削。她们在性行为上,都以符合西门庆的恶趣味为主。如,李瓶儿嫁给西门庆,带来了很多嫁妆,却因为她曾经嫁给西门庆的老对头蒋竹山而在新婚之夜将其毒打。在她生下哥儿时,将留在西门庆身上的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也使得西门庆有些不满,因而不顾李瓶儿刚生下孩子并且还在经期就强行和她行欢,成为李瓶儿病情加剧的原因之一。作者用大量笔墨写这一幕,实际上是揭露西门庆是杀害李瓶儿的凶手。不仅仅是李瓶儿,潘金莲、奶妈如意儿等也无不在情事上迎合西门庆的恶趣味。
此外,通过对历史和生存环境等方面的考察也可以看到,整个社会也使她们处于被动的地位。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男人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男人凭借外在优势成为家中主力,从而掌握了话语权[7]。在生存环境上,中国古代女子未出嫁时生存环境是闺房,出嫁后则变成夫家,女子试图打破这种状态基本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当家庭和私有财产无可争议地成为社会基础时,女性完全是被异化,成为男人的财产;同时,社会也几乎不会对女性加以保护[7]。对此,《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们都受到摧残,忍受言语攻击和作为商品而被送出去的凄惨命运。
三、对恋爱女人的批判
波伏瓦在《第二性》的第二卷《辨解》中对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自身生存之辩的三种女人进行了批判,这三种女人分别是——自恋的女人、恋爱中的女人和虔信的女人。本文认为,自恋中的女人和虔信的女人在《金瓶梅词话》中并不明显,因此,论述重点放在恋爱女人上。传统印象中,《金瓶梅词话》这部著作表面看都在描写世间的丑恶,无美可言,特别爱情一词用在《金瓶梅词话》中就是侮辱这个词。但本文认为,里面是有爱情成分的,只是爱情的成分也许不那么纯洁,不过影子在其中。如,《金瓶梅词话》中介绍潘金莲美貌时,“长成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尤细由弯”[8]10。然而,从一开始的张大户到“三寸矮冬瓜”的武大,没一个在外貌上是和她相配的,由此不难理解潘金莲心里会有不甘。所以,当她第一次看到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时,立刻产生了钦慕之心。而当她勾引小叔子失败后就把目标瞄准了西门庆。她第一次看到“手里摇着洒金叫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貌的西门庆时”[8]23,见惯了年过半百的张大户以及随后的武大,突然看到潘安貌的西门庆,可想对潘金莲的视觉冲击有多大。在此可以想象,武松一出场就是打虎英雄的形象,而西门庆一出场就是翩翩公子的形象,这些都会极大满足女子心理上对男性的预期。由此也可以推想,潘金莲开始对武松和西门庆都是有爱情的,只不过这些爱情多出于情感和生理方面,而且是在萌芽状态。再看李瓶儿对西门庆的爱情。《金瓶梅词话》产生于明末,明末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西门庆是以一个新兴商人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的,因而他的形象颇讨人喜爱。孟玉楼、李瓶儿无不是看中了他新兴商人的形象而不顾一切,带着丰富嫁妆嫁给西门庆的。小说描写西门庆和李瓶儿认识之初,她本是花子虚的妻子,花子虚在外嫖妓,整天午夜不归家(第十三回)[8]138,她劝告无效,为此“气了一身病痛”(十三回)[8]139。但是,她仍希望花子虚回心转意,并哀求花子虚的朋友,即西门庆劝花子虚改变行为。西门庆假装同情,来博得她的好感,于此同时却唆使朋友常把花子虚留在妓院,方便他勾引李瓶儿。最后,西门庆的诡计得逞,李瓶儿不但嫁给他,并为他生下哥儿。李瓶儿对西门庆的爱情源于对花子虚的失望,而在她最无助時,另一个男人出现并陪伴在她身边,安慰她、帮助她,这样的情形下,一般的女子都会对这样男性产生好感,并发生爱情。潘金莲、李瓶儿都想要通过爱情来摆脱困境,她们以为搭上西门庆就可以财富爱情兼得,以为摆脱了囚禁她们的围城,却没想到进入另一个更大的囚笼。
四、女性意识的觉醒
明代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对正常人欲加以肯定,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对自我和爱情的意识也开始萌生。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以及与女性这种自我意识觉醒不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有先天的不足,后天畸形的特点。《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为读者塑造了几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其中也暗含了萌生的女性意识。本文认为,《金瓶梅词话》中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语言、身体的欲望和行为。
语言是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工具,男权社会就是通过语言的潜移默化地建构性,将女性禁锢在男性设定在性别角度内,所以女性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解构男权的语言体系[9]。大多研究者都是通过《金瓶梅词话》中的语言来看待明末时期山东地区的方言及其语言文化,但从语言角度凸显女性意识这一主题却少有提及。中国古代女子想突破自我时,好像总有一条无形的界限,时刻警示她们不要越雷池一步,言语举止中都要透着卑微才合规范。中国古代女子处处以男子为尊,与男性谈话时都带着敬意,就是指出男子错误也要经过多方斟酌。但是,《金瓶梅词话》中的语言不一样,尽管放在古典文学标准下,这些语言都太过于粗俗,然而细品之下却另有趣味。可以说,《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语言处处透露出个性的鲜明与解放,富含活泼、辛辣意味。如小说的第十四回中,李瓶儿对花子虚骂道:“你成日放着正经事不理,在外边眠卧柳,不着家,只当被人算计,弄成圈套,拿在牢里,使将来对我说,教我寻人情。奴是个女妇人家,大门边上也没有走,能走不能飞,晓得什么?认得何人?哪里等人?浑身是铁,打得多少钉儿?替你到处求爹爹,告那奶奶。”[8]154从中可以领略李瓶儿面对花子虚时恨铁不成钢的愤怒。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李瓶儿对花子虚张口就骂的话,与以往唯唯诺诺的女子不同,此处李瓶儿给我们看到的是她自我意识的显露[10]。再如,宋惠莲得知来旺儿遭到西门庆陷害,就当面斥责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8]301不难看出,她的语言也带有那种自我意识觉醒后,面对自己所做的事的悔恨和对西门庆的愤怒。
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失去自我,首先从失去自我的欲望的感觉开始的,她们的觉醒也就要从身体的觉醒开始。[9]《金瓶梅词话》中女性的自我觉醒就是从身体开始的。她们发现了自己身体的价值,力图通过肉体欲望的狂热追求和满足实现其身体价值,而肉体的欲望归根到底就是性。性描写一直是中国文学的禁区,而这也是长期以来《金瓶梅词话》为人所诟病之处。但《金瓶梅词话》不仅写出了男性欲望的强烈,也写出了女性欲望的强烈,最典型莫过于潘金莲、李瓶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勇气。潘金莲可以说是一个“性饥渴者”[10]。年过半百的张大户、“矮冬瓜”武大不能满足于她的性欲望,所以她把目标投向了武松,却遭到武松拒绝。而后,她又把目标锁定西门庆,而西门庆恰恰在情事上能够满足她,所以她萌生了与西门庆做长久夫妻的念头儿,而这也是因西门庆“风月久惯,情事高强”。在和西门庆成亲后,她的这种欲望不但没减反而越来越强。这样的需求在李瓶儿的身上表现得也很充分。她对西门庆的评价则是:“莫说他(蒋竹山),就是花子虚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时,奴家也不恁般贪你了,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得走,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8]218所以她气死花子虚,抛弃蒋竹山,抛弃正妻身份来给西门庆做妾。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看,懂得自己想要什么,才会不遗余力,尽管她们的追求的方式可圈可点,但从中也看到她们的心已经从麻木中苏醒,并开始付诸行动。
或许要问,当这种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是不是该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在《金瓶梅词语》中,女性的确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表现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比如,宋惠莲发现来旺儿遭到西门庆陷害,就当面斥责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杀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了!还看出殡的” (二十六回)[8]301西门庆想要跟她和好,派人百般劝她,她却坚决不肯就范,最终自杀。或许这也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美丽的外貌,轻浮淫荡的生活背后,灵魂深处也暗含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描述过他作品中的人物:“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低下的罪恶,而且还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这句话似乎也可用来形容《金瓶梅词话》中的宋惠莲。她不但敢于指责西门庆,在面对自己企盼已久成为西门庆第八妾时,她严词拒绝了。再如,当西门庆死了,吴月娘并没有像其他小妾一样改嫁,而是帮助西门庆撑起这个家。在明末时期,“从一而终”“为夫守寡”等规条已不能再约束女子,而吴月娘的这种行为也可解释成女人是可以不需要依附男人才能生存的。又如,第八十回“吴月娘大闹碧霞宫”,吴月娘夜宿寺庙,殷天锡破窗而入向月娘求欢,她奋力反抗,用行动维护了自己的清白。很多研究者认为,吴月娘是因其西门府正妻身份而较少参与妻妾间的争风吃醋,而《金瓶梅词话》就是通过吴月娘这个近乎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后院女人一步步的沉沦,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第一部“极摹人情时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情小说,借用法国作家波伏瓦《第二性》中有关“女性是他者”的观点,站在新的角度,运用西方观点考察,让读者可以看《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生活的另一个层面,即女性在社会上处于附属地位并不是自愿,而是社会以及男性的天然优势使然,而《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所表现出的种种意识和行为也可以说是时代和社会影响下的产物。
[参考文献]
[1][法]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2]杨静亚.浅论《金瓶梅》中市井女性的独特生活面貌[J].时代文学,2010(2):223-224.
[3]陈顾远.中国婚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4]曾锦标,刘小英.《金瓶梅》中女性形象的矛盾性表达探窥[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38-41.
[5]王妹.对波伏娃《第二性》中女人“他者”处境的源性探讨[D].延安大学,2013.
[6]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姜家君,傅小凡.《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与女性的生存困境[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4(2):92-97.
[8]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陶慕宁,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张岸冰.女权主义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0]王引萍.试析《金瓶梅》中女性形象的塑造[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4):91-94.
[11]肖祥.“他者”与西方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0-04-01.
[12]徐晗.波伏娃《第二性》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評的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2016.
[13]张翠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D].郑州大学,2002.
[14]陈肖利.波伏娃《第二性》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启蒙[J].中华女子学院,2009(6):48-52.
[责任编辑]李献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