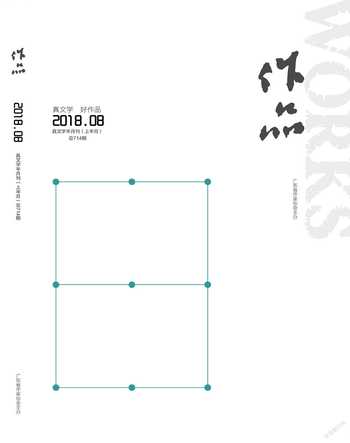狗命
1
狗房里都是来历不明的实验品,它们没有身份,没有血统,也没有未来。破门而入的斑驳光影里,灰尘悬浮在空中飞舞。骚动,不安。牢笼子里补丁一样的花色身影,比肩站立着,显得有些拥挤。臊臭味滚滚袭来,我遇到了比落魄更加触目惊心的场景。每一点外界传来的窸窣声响,都扯动着它们敏感的神经,喉头接连发出警告的震颤。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似乎连它们的生命也开始倾斜,这些犬类变得比人类更加多疑,无论是温顺如舌的轻舔,或是冰冷如牙的撕裂,不管是隐藏在黑暗角落里的,那些奴性的,还是狼性的,都成了无济于事的特性。别无他法,我必须选择和其中一条狗来对峙。我想就是它了,被命运选中的那一个,短毛枯黄,看似如枯草一样易燃。我们四目相对。它的肚子里仿佛有一垛柴火在呼吸,我从声声犬吠中窥到了熊熊火焰,烧灼了空气。烟尘在头顶旋转,久久不愿散去。
用一支长铁钳扼住它的咽喉,稳稳将它制伏在大地,再用尼龙绳紧紧缠绕和捆绑死结。狗嘴,前腿,后腿。它剧烈地喘息,回头打量了自己的肚皮,圆圆的眼睛温润如水。我们是穿白衣的杀手,试图给它一场没有尽头的安眠。可离奇的是,这条狗的肚皮竟然容纳了双倍的麻醉剂,才开始变得昏昏欲睡。待它呼吸变得平稳而有节律,我和同伴用钢管架起这条狗,穿过闹市一样的人群。从狗房到实验中心的旅途中,恐惧在弥散,这条狗竟然不知羞耻地小便失禁。深黄色的液体沿着走廊不断淋漓,沾湿了我的裤脚和鞋袜。我惹了一身无可奈何的臊臭味儿,就像被留下了某种气味的记号。我有些懊恼,可我耻于因为一条狗而愤怒。
我们让它毫无防备的,如同野兽示好般的姿态,充分暴露柔软的肚皮,剃毛和用冷水冲洗。明明是最锋利的刀片,不知不觉间就变得迟钝,可心急时又无意在皮肤上划出了微小的伤口,从细细的红线里,缓慢地渗出来某种麻木的情感。那不是鲜血——因为那里面没有迟疑也没有疼痛,仅此而已。准备工作结束,狗在磐石一样的手术台上被固定,即将用作外科实验。这场景让我想到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英雄即将遭受轮回般的苦难。这是一场伟大而光荣的牺牲。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说辞罢了。我们身着墨绿森林的手术衣,戴上帽子和口罩。用刷子洗手,用酒精浸泡双臂。涂抹滑石粉,穿戴橡胶手套。我们要保证无菌操作,每一个步骤,都仪式般一丝不苟。我似乎看到了自己一只手的善,一只手的恶,在互搏纠缠。
主刀、第一助手、第二助手、器械护士、巡回护士,角色分配完毕,我们蓄势待发。所谓实践出真知,这是我们四个时辰之内要完成的手术:股静脉切开置管、破腹探查、阑尾切除、胃造瘘、胃穿孔单纯缝合、小肠切除及断端吻合。我不知道这样一条狗是怎样被饲养或捕获的,它来自村庄,来自偷盗,或者来自专门饲养,这些都未可知,但内脏结构与人类的雷同,让狗成了最理想的实验材料。而人类的介入是如此唐突,我们从来不会征求一条狗的意见。
这是一条健壮的母狗,可是我们在它的腹腔中虚设了无数个假想敌。刀锋凛冽而细腻,尖锐处如针般刺入。我们要给它的身体打开一条小小的通道,皮肉就像是柔软的衣服般,被一层一层剥离。暖的气息从腹腔涌出,一如春花绽放,瞬间露出来的花蕊,在风中摇曳生姿,细密的汁液凝集渗透。主刀者专注的神情,一如花蜜般的香甜。我们正抵达生命最深处的律动。探寻,解析,割离,缝合。而这条狗的奇怪之处也开始逐渐显露。它的内脏似乎与其他犬类不同,所处方位总是略有偏差,这令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实验课临近尾声,才有人指着一颗“果实”惊讶地问道:“这是狗的膀胱吗?”它看起來似乎有些过于肿胀。一时间想到病变、增生或者肿瘤,如是的恶果闪耀在自己的刀尖下,我的心中突然生出一些亢奋。带教老师同样疑惑,他开始仔细分辨,神情却愈发凝重,之后他无奈又笃定地回答:“它怀孕了。”空气里似有水银弥散,令人感到窒息。原来它是一位正在怀胎的母亲,这一切似乎都能够解释清楚了。是子宫吸收了部分麻醉剂,也挤压了其他内脏器官发生偏移。子宫里竟然藏着几只已然成型的小家伙!有人提议,把小狗剖出来,兴许还能存活下来。老师断然拒绝,说不可能活下来的。他申述自己不是一名产科医生,所以只能简单粗暴地剖开子宫,如果只是为了展示几条幼小的尸体,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天是我为这位母亲做了最后的缝合和处死。我要为它关上一扇小门,同时打开另外一扇大门。或许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工作。但对于我而言,这是我所能给它的最后的尊重和告别。我就这样掌握了生杀大权,其实处死动物更加折磨我的内心。空气被慢慢推入静脉,那些平常的气体蓦然在血液里沸腾爆炸,引起栓塞,我看到了生命在颤抖和抽搐。于是我只能安慰自己,死亡对于它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痊愈。我求你了,请快一点,再快一点。
关灯,散场,瞬间的门庭冷落。门口的垃圾桶撑开一个巨大的黑色胶袋,用来收集动物尸体。这些狗终于进入了永恒的睡眠。透过柔软的毛发,温度像是一条河流,正在缓缓诠释着一场生和死的交融。当然,在自然界里,死亡有时候也意味着新鲜的肉食。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拒绝血肉是艰难的。有人提议,让我偷出去一条狗烹食,神不知鬼不觉,可以温补身体。可一想到我身上还残留着狗的尿液,想到它会不会有一天寻着气味找到我,我就有些寝食难安。我拒绝了他,我迫不及待要和这团血肉脱离联系。
我们都是屠夫。屠夫总是对刀下的牲口说,下辈子,我们换个身份,换个位置,我做你,你来杀我。我们甚至还要把肉食加工成模糊的性状,肉卷、香肠或是肉酱,看起来是那么美味诱人。这或许就是人类的优雅和虚伪。夜幕里,我看到了鬼鬼祟祟的影子,他是孤独的夜游者。他小心地捆绑了胶袋,拖拽离开。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很沉很重,他的咳嗽声就像瘟疫蔓延,催促着亡魂赶紧回家。一台小货车把狗肉运送到了小餐馆的后门。厨房里,屠夫顺着声嚣望去,灯光闪烁间,隐隐约约有衬衫、工服、校服和赤膊。那里觥筹交错,夜夜笙歌。
2
她家门前有狗,拉帮结伙的,见到生人就一起吼。母亲本能地在狗吠声中退了两步。
这本来应该是楼房一层住户的后院,通常人家用来栽种花草或堆放杂物,如今却被改装成了低矮简易的小屋,有门有窗,五脏俱全。暑气逐渐消散的暮色里,我透过敞开的木门看见了各式老家具,它们险些要把房间的肚皮胀破。不同深浅的赭石色,散发出古旧的气息,所有的摆件都仿佛随时会因为细小的震动散架破碎。屋子的房顶是用石棉瓦搭的,浅蓝色,波浪形。我对石棉瓦是有些恐惧的,那里面藏有碎而尖锐的玻璃丝,亮晶晶的却像刺猬,触摸后的手掌又扎又痒,只是这种瓦片似乎已经很少使用。此时的屋顶上还卧着几只慵懒的花猫,彰显出高高在上的优雅。它们大大小小的都是同样的花色,我想应该源自同一个家族。
女人众星捧月一样,在几条狗的簇拥中走出门。她始终弯腰的姿态瞬间让屋子又矮了一截。“你还记得我吗?原来我们住同一条街。你小时候很厉害,还打过我。”这是温婉的母亲一次别开生面的问候。女人明显有些迟疑,只是听了母亲的名字后才恍然点点头,有了一些灵光乍现的点滴印象。“我那时候是有些厉害,可现在唬不了人的。”女人这般说道,又有些难为情地笑了一下。我这才仔细打量了这个从黑暗中走出的女人,她身材高挑,黑且瘦,瓜子脸,高颧骨,淡眉毛,衣着随意而宽松,虽与母亲同龄却看似年长许多。
几条狗放下警惕,开始在屋外打闹撒欢,时而围着女人的脚踝打转,然后被女人一脚踢开。母亲怕狗,像站在一个无形的圈里不敢随意走动。屋里还留有一条大白狗,正从床底探出身子来,眼巴巴向外望。门外有匆匆的行人、葳蕤的植物和活泼的空气,不断撩拨着它的心弦。起初它还有些犹豫不决,迈开几步作为试探。它见女人并未斥责阻拦,才又小心翼翼地跨出门槛。女人发觉时只是回瞪了它一眼,目光像棍子一样戳下来,它就连忙退却两步。女人松了一口气,说道:“出来吧。”它才不再小心谨慎,脱缰的野马一样往外跑。
“它前天咬死一只猫崽儿,被我狠狠揍了一顿,这几天都窝在床底不敢出门。”女人和母亲如是埋怨道。其实女人不是目击者,当时的情景是她根据多方证人推测出来的:一只猫崽儿不小心从屋顶滑落,却攀不回屋顶。大白狗见到了有些焦急,就用嘴衔住。它趴在墙上,想把猫崽送回屋顶,可是它的个子不够高,一时情急咬伤了它。鲜血顺着牙缝流入喉头,眼瞅着猫崽的气息越来越弱,不久就一命呜呼。“不知深浅的东西”,这是女人对大白狗的控告。我却以为,是女人太过苛责,简直要把狗养成精怪。
而这里的狗大多是残缺的存在,是在人类为杀而杀的快感中,挣扎而活下来的。它们残缺的部分成为一些人的快感,有可能是一只眼睛、一条后腿或者是一条尾巴。这样的狗,挂着短命的标签,疑心重,胆子小,害怕与人接触,又依靠少数人的怜悯苟延残喘。曾经在街上,我见到成群的流浪狗,其中有些聪明者还学会了推举首领,像人一样沿街乞讨。一条狗走进店铺,其他狗在门口蹲坐等待。而肢体残缺的狗,它们的名字还是狗。可是我发觉,有时候人类真的不如狗。
起初,女人并没有打算把家当作流浪狗收容所。可这些狗来了以后就再没有离开。一只两只不打紧,剩饭剩菜就可以满足需求。同情心泛滥的时候,她也不断奉劝过自己,可捡回来的狗还是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屋子里会毛发凌乱、气味发臭。或许夏天的时候还能圈养在院子里,可眼瞅着树叶黄了,秋风起了,她只能赶在下雪前把院子改造成了狗窝。然后不久,她竟然也搬进了狗窝,同这群动物杂居在一起。她说自家男人从没埋怨过这些食客,虽未爱过,却也从未嫌弃。他陪她啃馒头,吃咸菜,拣市场收摊时最便宜的蔬菜,却从未辜负了这些狗。说话时,我见到男人的身影正在厨房里忙碌。一只锅里煮着的食物,是狗的,也有人的。女人指着一条懒洋洋盘在身边的黄狗说:“它做母亲了,平日里还要加餐。等再过些日子生产了,还要吃鸡蛋喝红糖水的。狗也要坐月子,不然没有奶。这次再生下来的崽子,养不起了,还是要送人的。”她有些愤懑,一方面要额外增加支出,另一方面还说它不知羞耻,弄不清怀了谁家的野种。“可谁又没做过母亲。”女人又说道。
不知不觉,这些狗就成了女人的命。她的儿子留在大城市里生活和漂泊,逢年过节却有些不愿回乡。儿子不喜欢这些侵占了他家领地的狗,甚至还侵占了他母亲的生命。女人庆幸说还好,邻居们都是善的人,猫叫狗吠的也并不多言语。如若花猫掉落在隔壁的院子里,邻居还会帮忙拾掇回来。孩子们放学了,也喜欢偶尔逗弄一下小狗。稔熟了的,这些狗也不会伤人。我发觉,女人的思维变得很简单,却也很有效。她就这样开始以周遭之人对动物的态度,直接给他们贴上了善与恶的标签。
听女人讲述,她的母亲因病瘫痪,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床和轮椅上度过的。老人怨恨床和轮椅,怨恨自己的腿。女人每天都要去给孤寡的母亲送饭。可老人总是以为活着时,残疾截断了她的自由,她是在用余生所有的时间期待死亡的降临。直到有一天,甚至连女人都想不明白,她的母亲是以怎样的方法,诱骗了一条流浪狗爬上三楼。老人给狗以食物,甚至为它清洗身体。老人突然间活了过来。从此一条狗开始死心塌地在她膝下陪伴。但她的邻居恨死了这条狗,狗吠声是邻居挥之不去的梦魇。邻居会砸着老人的门大声地诅咒:“你和狗怎么不去死!”
女人和母亲的谈话说到这里,饭菜也已经出锅。我看见了男人穿着棉白背心,弯着腰走出房间。他看见我们的时候点头笑了笑,擦着额头的汗不说话,有些腼腆和木讷。女人准备去喂狗了。她还要收拾食盒去探望她的母亲。她的心已经飞走,我们也该离开了。我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人怎么可以容不下一条狗,今天我要和他们拼命去。”
点评 阿微木依萝
《狗命》是作家端木赐的散文。我与作者并不陌生,细算起来已有六年交情,我们见过两次面,平日的话题多半围绕文学。他从前当医生,后來是京城某报记者。他是个外表阳光内心细腻而忧郁的人。他说当记者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经历,让将来有一天可以开启从前经历的一切。作为文学创作者,多关注生活事件融入其中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狗命》这篇文字取材的肯定是他从医期间的事情,另外的一篇大致也来自那个时期。
关于狗的文字身边有好几个人写过,我自己也写过,但是像端木赐这样写得如此生动令人不安的,目前还没有见着。他是心思细腻的人,在我们相识之初,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女生。他的文字气息温润,又忧郁,情绪绵延,但是又包含了手术刀似的利落干脆,在某些段落上,你甚至看到他窘迫的、孤独的又不能不如此去做的纠结样子。他有写字的人必备的特质,我说不好具体,但从文字的气息来看,他很适合写字。
《狗命》由两个不同故事的章节组合,我读第一章最有感触。尤其当他写到与同伴一起将狗抬走的画面,让人看到那个可怜的男生,他有些羞惭地走在大街上,抬着那只活体动物通向实验室,它作为实验品或许吓坏了吧,居然在走廊里撒了一泡尿,尿液沾湿他的裤脚和鞋袜。在我自己的看法上,我觉得写散文就是在绳子上打结。而端木赐在这段文字的描述上,就是用非常漂亮的手法打了个结。这泡狗尿撒得好,撒得正是时候,不论在现实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恰好需要这样一泡狗尿。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结,端木赐抓住了。老天爷给每个写作者都留了机会,如果感官足够敏锐心思足够细腻,恰好在当时情景下情感也很充沛的话,类似的结会在写作的途中出现,它本身来自现实而什么时候恰好在什么语境中出现,这就是个人的造化了——看你如何开头,如何调用情感、搭配词句,如何省略和凸显,都是考究天赋加功力的过程。很多人不一定抓得住这泡狗尿,抓住了也未必能写出该有的味道。端木赐很聪明并且克制地使用自己的情緒。在调用文字的能力上,他的感官敏锐,有时出于天意有时出于自身能力,他的句子的韵味令人着迷。虽然我们也能看出一些他遗漏的闪光处,但是沙子握在手里,难免要漏掉一些。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品被解剖,关于这里的描述端木赐非常冷静。这是让人佩服的底气。我们通过他的感官,融入当时的情景:一条躺在手术台上的狗,它是一位怀孕不久的母亲,人们并不知道它怀孕了。它们母子作为实验品,共同承担了所有的麻药和最后的死亡。我们通过文字的情绪,看到这个无辜而又参与了选择实验品、抬走实验品、身上沾了实验品尿液的少年,他心中的撞击。
说起来这样的题材算不上陌生,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但是端木赐写得很好。我读这篇文字受到的冲击也很大。一个一个的结,他打得漂亮,将读者的心扎得很紧。
《狗命》第二章,写的一位收养了许多流浪狗的女性。他很稳地讲述了这个女性的故事。她爱狗,她丈夫也不反对,还帮助她一起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狗,只有她远在大城市漂泊生活的儿子不太愿意,逢年过节不太愿意回家。儿子觉得这些狗侵占了他的家,也侵占了他母亲的生命。然而这些都不能影响女人继续照顾狗。她为何要收留那么多流浪狗,恐怕只有最后一句话能说清:人怎么可以容不下一条狗。在这个章节中,有一段描述是这样写的:“听女人讲述,她的母亲因病瘫痪,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床和轮椅上度过的。老人怨恨床和轮椅,怨恨自己的腿。女人每天都要去给孤寡的母亲送饭。可老人总是以为活着时,残疾截断了她的自由,她是在用余生所有的时间期待死亡的降临。直到有一天,甚至连女人都想不明白,她的母亲是以怎样的方法,诱骗了一条流浪狗爬上三楼。老人给狗以食物,甚至为它清洗身体。老人突然间活了过来。”这段话写得通透,写出了人同样孤苦的心灵。
最后部分是《斌叔、厨子和我》。要是没有记错,端木赐从前跟我闲聊时提过这个人。他说曾经有个认识的人,每天锻炼肌肉就是为了将来有个姿色不错很有钱的富婆包养他。在这篇文章中,这个人写得更清楚,更活,更让人通过文字一眼看到本人。端木赐把这两个人物都写活了。无论散文还是小说,写人物很关键。
斌叔爱赌钱,是个健身教练,性格略内向。厨子很风趣,也就是先前说的那位拥有远大理想、要找个有姿色的富婆包养他的那个人。
我对厨子的印象特别深,而端木赐也很聪明地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全部展示。厨子说的一些话简直可以称作名言。端木赐是这样写厨子的:“厨子是广西人,颧骨高,眼窝深,多体毛。关于体毛,这是厨子自己掀开衣服给我们看的,阴毛到胸毛连成一片,这也是他引以为豪的。或许,毛发真的和性欲有关,而厨子从来不以欲望为耻。厨子说过,他的乡邻里,很多男人来深圳打工,以卖身为生。陪酒,嬉戏,上床。满足女人的欲望。女人可以卖,男人为什么不可以?大抵就是练就了花言巧语,舍得糟蹋身体忍上三五年,就是立地成佛。说这话的时候,厨子神采奕奕。”正是这样的细节描写,让这篇散文有了提升。让人看后想到生活中许多个与厨子一样的人。我从前也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跟端木赐遇见的这位厨子差不多,他曾经也说过类似的话。
端木赐是个难得的作者,年轻,抓得住文字的气息。我相信他继续写下去,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来。
责编:周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