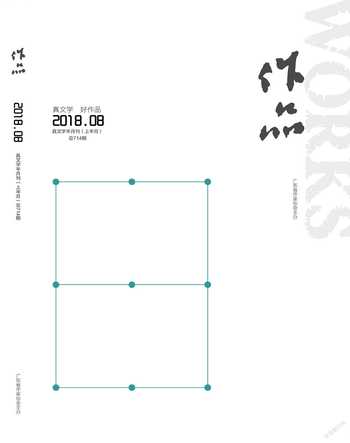风中流浪的一只猫
连亭
奶奶说,那个疯女人的家就在水田边。
她的疯,与一场火有关。那时她还小,不过几岁,正挨着冬天的火炉午睡。几根甘蔗叶被风吹落在火炉上,被炭火引燃喷发出妖娆的火舌,火顺着叶子爬到柴火堆,迅速蔓延成猛烈的火势。那时,屋内定是浓烟滚滚,而女孩昏迷在屋中。门窗都关着,散不开的烟气,慢慢从窗缝、门缝、屋瓦渗出,盘旋成一阵阵黑雾。人们回忆起来都说,远远看去,那屋子好似有瘟神降临。女孩被破门而入的人救出已昏迷多时,原本天真可爱的人儿,醒来后头脑却不灵光了,村里从此又多了一个傻姑娘。这傻,或许如医生所说是长期缺氧导致,或许如村民所说是瘟神附体。
疯女人十六岁时,嫁给村里的老光棍阿来。说是嫁,其实并未领证,而是请父老乡亲摆上几桌酒席,就算过门。阿来是个本分的农民,娶疯女人时已经四十三岁了。结婚前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自从病后,更为阿来的婚事忧心,终于在临死前托亲戚给阿来讨了个媳妇。虽说是个疯女人吧,但总归是个媳妇,老太太放心地闭眼了。
阿来的母亲,也是个可怜的女人,活着时受了许多苦,死后终于可以安心,为阿来说媒的人和来喝喜酒的乡亲,都觉得自己出了力,积了德。没有人问起那个消失了的男人,连母子俩都没提起。那个男人对阿来母亲造成的伤害,似乎已经和她没有关系了,将死的人总是乐于原谅的人,她闭眼时甚至都没想起过那个男人,心心念念只盼望阿来能娶妻生子。那个男人当年抛下她和阿来,跑到城里再也不回来,对孤儿寡母死活不过问,想起他老母亲会难过吧。她必定是难过的,所以她不愿提起他。
阿来的母亲死了,刚参加过阿来喜宴的乡亲,又聚集在他家参加丧礼。人们全都愿意为老人的死赴会。而她活着时的艰辛,却少有人过问。可见,人活着时,是孤单的,死了,才在众人的泪水中被全部接纳。一个人,只要是活着,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困难,却无人问津,这真是人的悲哀。
鞭炮声后,她的棺材被抬到山上去埋掉,她死的时候围绕在身边短暂爆发的泪水,像一场雨一样下过就消失了。也是,泪水从零散的田地里汇集而来,自然又要回到田地去,村民们为了庄稼不停地忙活,又怎能长久地沉溺于自己并不擅长驾驭的情感。他们清楚,不能为了什么人和事去耽搁一株庄稼的生长。
老母亲希望阿来能有个孩子,阿来自然是放在眼里记在心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更何况是临终嘱托。养家、生孩子,就要花钱,可是阿来没有积蓄,只好去打工挣钱。阿来四十多岁了,不能像年轻人去到广东进工厂,所以挣不到许多钱。他只在离家一百公里以内的林场或者工地找活干,时不时地还能回家看看疯女人。
疯女人生得一副好身材,双腿修长,臀部丰满,从背后看去,是个漂亮的人兒。从正面看,就十分骇人,右脸上没有一处完整的肉,颊上覆盖一块巴掌大的疤,疤的周边是粉红色的新肌,是大火烧伤的痕迹。要是在暮色中或者晨曦里猛然碰见疯女人,还以为见鬼。你可以想见,为什么村里的女人们哄小孩时,总会说“再不听话,村那头的女鬼就把你捉了去”。小时候每当母亲这么对我说,我就立马吓得缄口不言,把哭声吞回肚子里去。
村民们白天不常在村里看见疯女人,她总是早上天没亮或者晚上天黑了才从家里出来,在村子里、田地上幽灵般飘飘荡荡。那时,胆小的孩子总是躲在家里,生怕出门遇见她。每当我傍晚在河边赶鸭子时,最恐惧的是遇见疯女人,因此我总是反抗着母亲,不愿独自去河边,可母亲太忙了,需要我给她分担家务。
当我看见在暮霭中有一团粉红色(她总穿粉色衣衫)在飘移时,我就躲进河边的芦苇丛中。晚风吹得芦苇沙沙响,水声听起来也特别凉。晚霞落到岸边的一块粗石上,一只鸟从山的背面飞来,喝了几口水,然后久久地立在石头上,落日隐去才飞走。黑鸟每天都往返一次,就像我几乎每天都要在芦苇丛中经受恐惧。我不知道疯女人为什么每天都要来河边,也许水是照见她苦难的一面镜子,也许是水流能给孤寂的乡村带来浩大的鲜活。我害怕她朝我走来,因而我总是蜷缩成一团,提心吊胆地窥伺她,躲避她。否则,她莽莽撞撞地朝我走来,被一根草绊倒摔在我身上,或者她那不长眼的脚踩在我的脑门上,我就要像她一样一辈子顶着一块巨大的伤疤过日子。
疯女人一次也没有踩到我,可经常踩到我的鸭子。鸭子被她惊得四处逃散,我也只能躲在芦苇丛中,敢怒不敢言。我常常担心鸭子会在慌乱中不知去向,那样我就得像《地球上的王家庄》里的男孩一样,四处寻找我的鸭子,并且有可能因此而一去不归。
疯女人似乎迷恋上我的鸭子,她扯断一根芦苇,扬在手里,“嘘嘘嘘”地冲着我的鸭子叫唤。她走过的地方,扬起纷纷扬扬的芦花,白花花地在暮色中飘散。
我趴在“沙沙”的下雨似的芦苇声下面,既怒又怕。落日渐渐西沉,天空中的火烧云蔓延到芦花上,漾起一片晕红。我远远地看着我的鸭子被一朵粉红色的云团赶来赶去,直到溜下河滩。坏了,要是鸭子在河里一直不肯上来,我可就遭殃了。
果然,鸭子欢腾起来,扑腾着翅膀奔向河流。长河落日圆,暮色中旷野逐渐安静,而我的鸭子却开始了不合时宜的亢奋。它们有的在河面上浮来浮去,优雅得像女王一般;有的卧在河岸的草丛里,那安详的神态让人怀疑多毛的腹部底下藏着椭圆形的鸭蛋;有的站在水边慢条斯理地梳理自己的羽毛,好像它们是要准备参加一场舞会的公主。疯女人就在河边站住,眯起眼睛如看孩子似的看着我这群白色的鸭子,手里还兴奋地扬着芦苇秆。
她一会儿用秆子拍打河面扬起四散的水花,一会儿嘴里“哦哦”地对着鸭子呼唤。鸭子朝着她的呼唤游过来,她又击打水面把鸭子赶到河中心。直到夕阳沉到山背后,她才开始厌烦这个游戏,丢下芦苇秆和鸭子,离开河岸朝另一个方向走。黑鸟也在此刻从石头上飞起,掠过河面,向山那边而去。
我从芦苇丛中站起来,感到如释重负。我气急败坏地呼唤我的鸭子,幸好它们都一只一只地爬上岸,一颠一颠地朝我跑来,跟着我慢慢走回村子。此刻落日已经西沉,夜色从眼睛深入到心里。
疯女人和鸭子的“游戏”持续一年多,以至于我身心俱疲,以至于我恨得一次都没有祝福过她,甚至诅咒她。
疯女人不来找鸭子时,她在干什么呢?关于这一部分的信息,都来源于村民的传说,而我从没想过要亲自去了解。
村里的妇人说她在自家天井挖了一个水坑,后来那里冒出一眼泉水。她家本来就在水田边,能挖出泉水并不稀奇,稀奇的是疯女人总是脱得赤条条地在泉水里洗澡,或者说玩水。她一定以为自己是只鸭子,否则怎么会老是脱光了泡在水中呢?听说她像鸭子一般,时常把双手张开成翅膀状,一会儿扑棱扑棱地扇动“羽翅”抖落水珠,一会儿不停地拍打水面做滑行的嬉戏。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她想洗澡了就洗,想玩水了就玩。有的人白天去她家,就撞见她白花花地浮在水里,乍一看还以为是美人鱼。
一定有人爬上阿来家墙根的树偷看疯女人洗澡,不然何以他们描绘起来如此细致呢?
夏天的月亮把夜晚照得发白,夜风散去余热,破屋子不再像白天那么寒碜,只见那女人一丝不挂地坐在水池边,身体被月光浸润得莹白。她的长发披散开,手拿着瓢子轻轻地舀水淋在长发上,不时还能听见她发出娇嗔痴傻的笑声。光线昏暗使人看不清她的脸,却给她浑身罩上一种纯洁的玉色。修长姣好的轮廓浮现在月色中,真真是好看,尤其是那对乳房,虽看得不真切,却好比两颗娇艳欲滴的葡萄。小伙子们说完,发出享受般的轻笑。
那时我十岁,实在无法忍受这种传闻,既鄙夷那些轻薄的青年,也鄙夷胡乱洗澡的人。
我没细想过疯女人的一切异常行为和“神经异常”有关,或者与一场火有关。我太小了,以至于都不会理解人,也不会同情人。
在奶奶口中,疯女人挺可怜的。
阿来外出了,疯女人要一个人在家操持家务。她那错乱的神经常常让她把粥煮成了饭,把饭煮成了粥。菜呢,更是做得一塌糊涂,有时烂得如猪食,有时还未去生。阿来驻留在工地不归,疯女人一个人在家打理田地,拔草时常常把秧苗当成草拔了,给田放水时总是放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别人笑她、骂她,她也分不清楚。总之,似乎总是添乱的多,活干得像样的少,还得阿来回家时补救。
奶奶就常常叹着气说:“这两口子日子可真够艰难的。”
最难的还是生孩子。
阿来经常外出务工,也没耽误疯女人怀孕。可听奶奶说,她从没顺利生下过任何一个孩子。有时她在河边洗衣服或者在地头干活,身子下面就流出一摊血,染红河水,染红泥土,也染红每一双目睹悲剧的眼睛。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流出那么多血,匍匐在地上哇哇地大哭。我赶鸭子路过她身边时,生怕那些血弄脏鸭子的白羽毛,总是试图远远地绕开。
好心的女人送她去乡村医院,并让自己的男人想办法通知或在工地或在林场的阿来赶快回家。每次阿来紧赶慢赶地回来,孩子已经流掉了。阿来问她疼不疼,疯女人哭着说疼。现在回想,她必定是感到疼的。疯了的人也会感到疼,这是上天的公平,也是上天的残忍。
疯女人第五次怀孕的时候,阿来为了确保母子平安,不再外出务工,相反,他还耐心地告诉疯女人逐渐大起来的肚子里是什么。是孩子,是生下来会哭会笑,会跑会跳,会长大成人的孩子。
奶奶说,那时的阿来可会疼女人了。他伺候疯女人吃喝,还耐心地教疯女人给胎儿唱歌:“孩儿啊,你快快长大啊,你是爸妈的好孩子啊。孩儿啊,你像山上的小鹿儿啊,快乐又美丽啊——”
住在山脚的神婆却说阿来不会有孩子,甚至不该娶疯女人。这话无凭无据,且十分扫兴,甚至显得恶毒,跟诅咒没什么区别,让人怀疑这个神婆和阿来或者阿来的老母有仇。
可是神婆能掐会算,擅长念咒,甚至到了差神使鬼的地步,她的话又说得头头是道,让人忍不住心里犯嘀咕。
神婆形容枯瘦,塌鼻梁,尖嘴巴,脸色青紫,双眼睫毛稀稀落落,眼神锋利骇人。她每次见到疯女人都会说,疯女人是死过一遭的人,身上有鬼气,谁娶了她是要倒霉的,是要断子绝孙的。疯女人脸上的伤疤使她看上去本来就人模鬼样的,经神婆这么一说,越发显得鬼气十足了。
疯女人生得漂亮,早被鬼王看上,鬼王招了她去,她不愿意,拼了命地回到人间,这就得罪了鬼王,强留在人间是要倒霉的,那块疤就是鬼王在她身上做的标记。神婆一本正经地讲这种话,多数人不信,有些守旧的老人却信,这样的老人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不断,真是让人生气。话传到阿来耳朵里,起初不在意,日子长了心里慢慢地就不踏实了。
作为一个想要孩子的男人,阿来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意思,去向神婆求取破解之法。神婆眯着眼睛若有所思地说:“破解之法,有是有,但要费些功夫。”说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阿来。彼时的我正站在奶奶身边,奶奶素来对神婆有些敬畏,听到说有破解之法,很为阿来高兴,我却对他们这些大人的事感到迷惑不解。
神婆说应当立即举办一个仪式(当然神婆举办仪式需要很多钱),以斩断疯女人与神鬼世界的联系。她会被绑在一棵樹下,用烟火和艾叶熏上一天。疯女人以前流产上医院,阿来已经为她花去了很多钱,已经没什么余钱了,有时候疯女人看病的费用还是工头提前给阿来支付工钱才补给上,如今听得神婆要许多钱,阿来犹豫了一下,可为了孩子,阿来决定一试。
有些年轻人就劝阿来,神婆和巫医们总是故作惊人之词,要是这些人说什么都当真,那还要医生和科学干什么?这老巫婆装神弄鬼罢了,不过是夸张的骗取钱财的把戏,不必当真,安心照顾你女人去。
阿来不放心啊,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后生仔们懂什么,还是听村里的长辈的话。于是阿来不顾经济拮据,请神婆为疯女人举办驱魔仪式,任凭年轻人们取笑他,他也不动摇。
我目睹了那个仪式。疯女人被绑在树干上,惊恐地大喊大叫,身子却被绳子牢牢绑着不能挣扎。阿来痛苦而又怜悯地看着他,最后跑过去守在她身边,陪着她一起经历烟熏火燎,疯女人这才安静下来,眼中满是困惑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可当烟火越来越大时,兴许是儿时火灾的记忆太深刻,疯女人又惊恐地大喊大叫起来,阿来没有办法,只好往她嘴里塞上一团布堵上。她只能睁圆眼睛愤怒而又绝望地看着阿来。
這期间,神婆不为所动地进行她的驱魔仪式。她一手摇铃,一手拿着被点燃的艾叶把,头发披散,面目狰狞,嘴巴振振有词,神神叨叨,咒语迭出,身体剧烈摇晃,仿佛神灵附体。突然,她从一次最猛烈的摇晃中静止下来,眼珠睁圆,表情恐怖,一动不动地呆立了一分钟。神婆再次摇晃起来时,动作有所改变,她一边转圈一边撩拨火堆,每转一圈就往火堆和疯女人吐一泡口水,如是再三。
这样的仪式耗时耗力,不光是神婆和被烟熏的疯女人及阿来会觉得体力不支,就连我们这些观看的人,到了中午就忍不住肚子饿,于是纷纷回家吃饭,神婆和疯女人、阿来却从早上坚持到了日落。吃了饭又去玩耍的我,没有目睹仪式的结束,只看到阿来抱着已经晕过去的疯女人在暮光中蹒跚地走回了家。
奇怪的是,疯女人那次果真不再流产,几个月后顺利地生下一个女婴。本来村里人对神婆将信将疑,这下全都把她当成了神仙。孩子满月后,阿来又准备礼金去答谢神婆,并让神婆给孩子取了个名字。神婆说不能用疯女人的奶喂养孩子,阿来每天都到养羊的那一家要些羊奶喂丫头。
孩子一天天地长着,疯女人的疯病却更厉害了。只要阿来不注意,她就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往外跑,边跑边疯疯癫癫地哭哭笑笑。
有一天夜里疯女人跑出去,阿来没来得及拦住她。阿来以为那次和以往没什么不同,疯女人闹够了会自己回家的,所以为了照顾女婴,阿来没有及时出去找,等到天亮再去,却再也找不到了。
阿来去请问神婆,神婆说她也没有办法,可能再也找不到了,毕竟是和鬼王有牵扯的人。阿来心里不甘,几经寻找无果后,也只好作罢。毕竟他怎么敢奢望有老婆呢,能有个孩子就该知足了,多年以后每当听村里人说起此事,阿来就神情空洞而又满含感激地说。
疯女人失踪之后,村里发生了许多怪事。有些人晚上睡觉,总能听见窗外或者树下传来似哭非哭、似笑非笑、似猫叫非猫叫的声音,那声音一会儿被风声掩盖,一会儿又冲破风声刺入耳朵。害怕的孩子就问母亲:“那是什么声音?”母亲们有的说是猫叫,有的说是狸叫,有的说是貉叫。
关于猫或者狸或者貉的传闻,经母亲们的口传遍整个村庄,后来又传到山那边的人家。此后有人在夜里上山打猎也听见了叫声,甚至有的猎人说他们打到的山鸡和狐狸在夜里也会发出那种叫声。
关于叫声或者有关叫声的消息,有时从山上传来,有时从山那边的村庄传来,有时从河边传来,有时从对岸的人家传来,有时从树梢和瓦屋顶传来……
女婴在阿来的悉心照料下渐渐长大,渐渐地会说会笑、会跑会跳了。有一天夜里,她也被那种叫声吵醒。她抓着我的裙摆诉说那个夜晚时,眼角还带着泪花。
她说,那夜她躺在被窝里,突然被屋外的动静吵醒,就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那声音一会儿在墙根,一会儿在院门,一会儿又在池塘边,一会儿又在树下……
她掀开被窝爬起来,把窗户打开一道缝隙察看外面的动静。窗外,大地罩着皎洁的月光,风温柔地抚弄树梢,她把头探出窗户,四下张望,突然吓坏一般尖叫起来。
她说她看到一个鬼魅般的影子闪进了树林。
阿来被女儿的尖叫声吵醒,慌忙过来询问。女儿不清不楚地说完情况,他就拿起手电筒去屋外察看。手电筒四下扫射,却只看见一只猫蹲在墙头上,对着月亮凄厉地叫着,此外什么也没有发现。
记忆中,女孩似乎吓坏了,神色苍白,日渐憔悴,让人哀怜。第二天,我陪她去河边洗衣服时,她指着沙地上的一些痕迹对我说,除了一个鬼魅般的影子,她清晨早起时还在池塘边的泥沙地上,看见一行凌乱的似人非人的脚印。而我们都记得,前一天傍晚沙地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痕迹,却在那个鬼影来过之后,泥沙地有了脚印。
不久之后的冬天,山那边的村庄在山庙里发现一个冻死的女乞丐。那个村庄的好心人把女乞丐埋葬了,故事传出好几里,传到我们村时面目已经模糊。有人说,女乞丐的面庞虽然脏兮兮的,可是脸上依稀可见一块硕大的疤痕。
那个女乞丐或许是疯女人,或许不是。不管是不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我忽然想起阿来早已离去的老母亲,似乎捕捉到世界暗藏的一点隐秘关联。在这些纵横交错的网线中,我搜寻出当年在老人的葬礼上领悟到的话:这个世界对她造成的伤害,似乎已经和她没有关系了(只是这个她,如今变成疯女人,或者别人),过去的事都是被原谅的事,也是被遗忘的事。
只有夜风中流浪的一只猫,或许仍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当它找到一块避风的石头,安静地躺进石头的影子里,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梦就席卷上它的疲倦。偶尔醒来,眯着眼睛看见圆圆的月亮,流浪的日子就结束了。石头的阴影多么静谧……
点评/草白
《风中流浪的一只猫》是篇写人散文,写一个疯女人的故事。有些场景颇有意味,比如傍晚时我在河边赶鸭子,与疯女人的相遇,以及后者几近癫狂的表现,就很有画面感。随后,在情节的有序推进中,逐步展示了疯女人的悲惨命运。最后疯女人的忽然消失,处理得有些仓促,没有进一步展现人物在现实层面的悲剧意义,反而是减弱了之前树立起的人物形象。如何完成对一个疯人的书写,我觉得与其费大量笔墨去书写其“不正常”,不如着眼于其在某些时候的“正常”举止。疯癫如果成为常态,人物的可塑性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散文中的人物书写,与小说还是有不同之处的。散文更侧重的或许是有作者参与其中的对人物的重新记忆、发现和再认识,因为散文里的自我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确切地去写一个固定的人或物,而是去想象它,从而在文本里能够重新讲述它。
这篇写人的散文,文字娴熟流畅,叙述转折也自然,有些细节场景描写颇富温情,比如驱魔仪式上疯女人丈夫的举止,但总体而言叙述还不够节制,笔墨常有游离。另外,取题为《风中流浪的一只猫》也很值得商榷,它几乎没有起到表现主旨或者与主旨相关的用意。
责编:周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