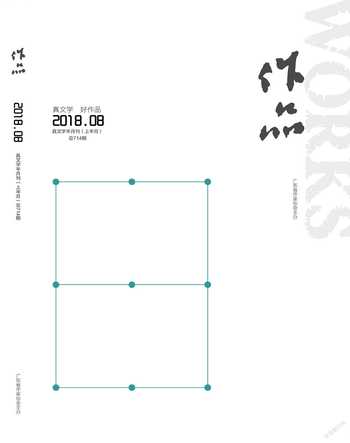曾经大雪封门(散文)
贺颖
1
北京的十一月,秋尚在,天地万物醇酽如金,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城池之一。走到哪儿,都仿若置身画帷之间,锦绣,魅惑,炫艳,庄严。
于众多色彩之内,明黄色,这源自华夏文明最为正宗的皇室象征色,则有如深秋北京的色彩之灵,以银杏为先,杨树次之,更有无数数不出名号的蒹葭草木,均以纯粹的明黄暗合这座古老悠远的皇城。
据说明黄是唯一与太阳最为接近的颜色,远古更有“黄道吉日”之说,而所谓“日月循黄道”,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十一月的北京彰显得更为恣意浩荡,匠心独具的了。仰头目之所及,俯首行之所至,明黄仿佛成了深秋草木的铭志,璀璨迫人而生死不改。
风中摇落的,雨丝裹挟的,初雪渲染的,总之无处不明黄,盖地铺天,不谋而合。
最为销魂的当为银杏莫属了。从风雪漫天的北方转至北京生活以后,才认真熟悉了银杏,这种北方以北并不常见的树种,隽永,清雅,以至是标致。一直觉得银杏的叶子从绿到黄只是一夜间,后来偶然发现,它们原也是有着渐变的过程,从最初镶着丝丝缕缕的金边开始,到全然整株树毫无杂色的太阳般的炫艳明黄,正常的年份差不多要两周的时间。在深秋,这时间其实并不短暂,而之所以会认定一夜之间,实在是那一树树炽烈炫目的色泽,太过美得触目惊心,以至全然掩映了之前并不短暂的过程。
站在树下,总疑惑,仿佛它们始终就是这样一个只为秋天而来的物种,仿佛刚刚才自大地深处缓缓升起,自时间深处诞育而来,仿佛周身尚弥散初生生命的腥甜、异香,仿佛太阳自黎明中倏然腾向山峦,不由人不炫惑,每每诧异,而这诧异,大多就会弥漫似真如幻的整个秋天。
而今年秋天,北京提前下雪了,且是一场罕见的大雪。秋天的雪于今天的北京而言算得上并不多見。如蝶的雪片自黄昏开始渐渐密集起来,从小到大,从从容容几乎下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的午后仍没有停下的征兆,灰白的天空低低垂下来,看久了越发不真实,目之所及难抑惊诧,不由身随心动,恍如已然悠游于天地间的一片鸿蒙。
关于雪,就最爱宋代张元的锦瑟诗句:“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奇谲魔幻的想象,动人心魄。而今年的这场秋雪,无疑是对宋人张元最神异的呼应了。
据说刚进十一月就下起这样的雪,在近年的北京几乎从没有过。已近傍晚,依旧雪大如蝶天地间纷飞。人们或凭窗仰望,或出去房间外立于雪中,更有小孩子早就耐不住了,在雪中打闹嬉玩。不用说那些拍客,早已在雪中不知流连了多久。
雪虽大如斯,而事实上毕竟是秋天,温度尚未很低,大部分雪落在身上落在树上落在地面,渐渐就化掉了。只余下一些落在高高的建筑上、树梢上以及京郊稍凉地方的雪,就化得慢些,就渐渐有了景致,被惊呼的拍客们收进了镜头,发布于网络,于是一整天无处不人声唏嘘,“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
如此想来那当年北平城必定是多雪的吧,以至这雪已然成了北平城一向以来最为人所认同的表征。
细细思之,也或者其实人们对雪的种种印记,不仅仅关乎地域,更与时间有关也说不定。比如这十一月初的浩然落雪,即使在北方以北的小村,也似乎已多年未见。毫无怀疑,这场气势夺人的漫天秋雪,倘使是落在此刻辽河边的小村庄,也会令村人沸腾。因为至少差不多十几年了,或者更久,未曾在深秋就得见一场像模像样的雪了,无怪乎人们街头巷尾地于雪中忘返流连。
而事实上说到时间,于远年的十一月而言,太多地方早已是彻头彻尾的冬天了,哪怕是北平城,更加不用说遥远的北方以北,我出生的那个辰时,以及那个冬辽河北岸,被如烟大雪覆埋的寂寂小村。
2
母亲在世时,常常看着我,喃喃疑惑我会长成这样大。
将近一米六的母亲,在女性身高里已不低,而我并不知道,初一之前,始终排在全班身高最低的自己,永远站在女生队伍最前面的那个小丫蛋,因而一度是母亲心里的难言隐忧。看着同龄的孩子一个个在长高,而顽劣的自己除了日渐增长的食量,身高体重依旧被远远落在后面,母亲常常焦虑不已。懵懂的我却浑然不觉。
当我在某个夏天,像棵冒冒失失的庄稼青苗,如梦方醒般地倏然超过了母亲的头顶,母亲惊诧后的喜悦,喜悦后长长地呼了口气,欣慰之情长久弥漫于脸上。就越发说得多,常常说,而我知道她要说什么。
每次看见母亲喜悦闪亮的眼神儿,我就挨着她坐下,她就摸我的头发,摸我的脸,让我再站起来,看看到底长了多高,然后点头,我就再坐下。必定她就开始说起那些年月,那个早晨,那个辰时出生的属狗的小孩儿,那些大雪,大雪中的冷,那些酷寒中一个母亲对一个乳香四溢的小生命未来成长的深沉忧虑。
自己记忆中早些年代的雪,真正像模像样,雪一度是北方冬天的魂魄,是天地间亘古而在不绝如缕的寂寂交响。雨夹雪,小雪,中雪,大雪,大到暴雪,暴风雪,从十月末到来年五月,将近小半年的时间,人们在各种雪的仪式中穿行整个冬天,以至北方特有的早春酷寒中,偶尔仍有毫无征兆飞撒而至的春雪。
母亲说我生在辰时,是属狗的孩子里最好命的,因为忠诚守夜的狗狗警惕了一夜,当黎明的旭日初初升起的辰时,狗狗们安心卸任饱吃暖睡,看吧最享福的时候到了。
母亲常常不觉间说起这些,显然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深爱之语。晚熟的自己,少年时尚懵懂不化,时而就野蛮顽劣如男孩子,全不似姐姐的早慧与静美,更不及妹妹的内敛与心思,却唯对母亲此说欢喜上心,虽不解其间深意种种,却执拗地相信着,每听这些吉祥的话,就雀跃着奔出家门,欢喜于乡野小路田间地头,那些自己最爱的乡下浆液饱满的野果,亦因而格外凛冽甘美。
可见人类对命运吉祥福美的期许与渴念,自幼年开始竟已莫名被启蒙,多么地深远。成年以后,每每母亲再说起,与其说我仍然在相信,或者说是心魂愿意相信更为准确。一则我也成了母亲,我知晓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祝福与祈愿,有多顽固多深邃,而这祝福与祈愿本身,已经神奇地成为孩子好命的一部分了,这该是某种觉醒的庄严,是每个经历过心魂阵痛的母亲,甚至经历过生死抗争的母亲,与上苍的某种契约,事实上正是这样与生俱来的祝福与祈愿,冥冥中引着自己的孩子,走向传说中的好命。
也果然就被母亲的好命之说引着,自己的成长之路始终有贵人相伴,好运总相随,甚至这顽劣懵懂与晚熟,也似乎成为生命中某种神秘的蕴意,只为经年之后,成全一个平凡生命对万物有灵的世间万事异样深情地认知。
于自己而言,这世间最神秘之一当属我的母亲,她的异人之处在自己心中,已然就是神异的,不可解的。
读过邱特切夫的一句话:早在那神话般的年代,我就已经认识了她。这话几乎就在说母亲,我的母亲,我也许真的并非出生时才认识她,也许她果然来自遥远的那些神话般的年代。
从小到大,顽劣成性的自己算得上胆大,却有命中天敌。生来就不能吃药,任何种类的都一样,被迫吃进口中,全然不可能咽下,就仿佛喉咙是封闭的,吃几次就会吐出几次,忍住不吐等药片在口中被水溶化,释放出如今想来依然身心战栗的酸涩浓苦,无奈依旧会吐出来。尝试碾成药粉,则更加恐怖万分,往往尚未入喉就被那些古怪可怕的味道呛得大咳不已,每每以痛哭流涕而作罢。
以至后来每有感冒发烧之类,总将药片趁母亲不备,藏在某处,而奇就奇在,却无论藏在怎样诡秘的地方,无一例外均会被母亲一一寻到,仿佛她背后就还长着眼睛,以至后来渐渐唤起了我童心深处的强烈好奇。我太奇怪了,也曾缠着母亲问过,而母亲总爱昵地掐掐我的脸,微微笑着不说话。后来母亲则以开水代替了退烧药,说来也神奇,退烧降温竟然极为有效。而这萦绕童年的秘密,直至今天仍是个谜。
常常感恩上苍恩典,从小到大赐予自己的健康,印象中除了偶尔感冒,用母亲的话说,几乎是一眨眼就长大了。幸好是这样,因为自己除了不能吃药,生来竟也不能打针。如果每次吃药让自己身心战栗恐惧至极,而打针则就是毁滅,全然就不要这命了一般,连挣扎都不会,乖乖就直接昏迷。上天成全平安无恙,连小毛病也不曾生过几回。
记忆中唯有少年时一次任性淋了雨,重感冒,不能吃药不能打针,便久不见好。看着工作忙碌家务繁杂、对自己心疼又无奈却不忍苛责一句的母亲,我第一次生出大人般的庄严愧疚,决意拼尽全力去打上一次退烧针,早些为母亲解忧。我晕晕地向附近一间诊所走去,一路为自己加油打气。可刚刚走到那条通往诊所的小巷,远远看见那间诊室的外墙,脑子里便映现了那个身穿半新白大褂、高声大气的女人,那些隔着玻璃同样轰然而至的消毒水的味道,仿佛刹那就冲进了鼻腔,我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仿佛在消散,最后的影像是一个骑着自行车越来越远的路人的背影,而后就没用地软软倒在了小巷的墙边。
睁开眼时我已经躺在诊所的小床上,母亲正切切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拉着我的手,但什么也没问。我感觉到自己周身尚未消散的冷汗,潮潮的凉凉的,唯有手心里是母亲熟悉的炽暖。女大夫见我醒了,依旧高声大气地说,丫头,你妈可真神了,我也刚从那经过,咋没留意你在那儿,随后你妈就带你进来了,前后不过几分钟。后来我问母亲,她说记挂我的高烧,回到家却没看见我,就出来找,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直接就走到了那条小巷。
我就在心里依旧惊奇。而说起来,母亲的奇处算得上数不胜数,或者说母亲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譬如从一个怀着孩子的女人身形之上,母亲能够看出婴儿的性别,毫厘不差,包括我们姐妹几个均已应验无差。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母亲居然知道小孩子出生的时间,是说具体哪一天,比所谓的预产期还要精准。
那一年我成了准妈妈。医院检查的表格上,写着预产期,医生嘱咐说,这只是大概的日期,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仅作参考。
必然仅作参考,生小孩子那么复杂微妙的事,怎么可能有具体日期?
日子一天天过去,表格上的日期也过去了好些时日,全家人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母亲来了,淡然从容地安慰大家。母亲看看我,看看那张表格上参考的日期,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具体的时间,是在半个月后,说得轻松而确凿。
我第一次对母亲半信半疑。
新生命的到来,这种复杂的事情毕竟不可能任由人的意愿,而因为身体上的个体差异,更加存在难以捉摸的无数可能,因此可以想见几乎没有理由如此确认的。但我没说出自己的疑虑,也许是母亲一直以来的神奇在自己心中的惯性依旧强烈,也或许自己不忍反驳母亲。
其他人自然也是觉得母亲在说笑。母亲并未辩解太多,依旧轻松而确凿,在离开时格外叮嘱我,一切正常,不用有任何担忧,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不用提前去医院,因为医院的环境并不适合,只须在家里安心等待半个月即可。家人们送走了母亲,坚持带我去医院进行了常规检查,医生的结论与母亲如出一辙,一切正常,就是时辰未到。接下来等待的日子里,家人们偶尔还说起母亲的确凿预测日期,依旧当作笑谈。只有我在半信半疑中,隐隐感受着某种神秘的期待。
事实是半个月后,就在母亲确认那个日期的前一天夜里,我如期开始了分娩前的阵痛,在母亲预测的那一天早上,我来到医院的产科病房。十二小时之后,在母亲指定的日子里,我的孩子准时平安降生,比预产期刚好迟了半个月。
这件事经年以来在家人们中间几乎成了公案,甚至也包括自己。尽管母亲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已经是足够神奇的,但这一次的震撼仍旧令自己至今惊叹,依旧无解。后来也问过母亲,母亲的答案是当年我弟出生的时候,就是迟了半个月。而母亲已然看出了我怀着的是男孩,更加在预产期毫无反应,便由此确认我必定会与母亲一样,将延后半个月。我曾经把这个理由说与家人们听,大家都觉得仿佛有些道理,却深觉母亲料事之神异难解,每每说起总惊叹不已。
孩子出生时体重并不重,不过感谢命运,孩子应该像我,身体一直很健康,眨眼就到了三四岁。可一直非常懂事健康的孩子,不知为何开始夜里哭闹,白天里一切正常,晚上就哭闹只说肚子疼。做了所有相关的检查,没有任何问题,却仍然白天欢天喜地,一到夜里就哭闹。
一夜夜被孩子的哭声惊醒,一次次半夜里带着孩子去医院,急诊,背着上楼下楼,心急如焚。可每次折腾了大半天,一在诊室的床上躺下,孩子就不哭了,不疼了,啥事都没有了。回家,睡上一会儿,再次重复。
百思不解,太不明白了,这么小的孩子,没有理由故意捣乱。可事实就是这样在莫名重复。看着孩子哭闹的样子,自己已然心疼心碎,无助慌乱。
几个上了年纪的亲戚听说了,开始出主意了。这是些不言自明的秘密,我懂,但不甘。难不成真要去乡村里请人来瞧吗?家人们也开始考虑了。我却下意识地抗拒,不是抗拒世界的神秘无解,而是内心深处不愿相信这样的事实,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带上孩子回了母亲家,难过地向母亲说着情况。没料到还没等自己说完,母亲说没事,看你脸色不好,一定是晚上照顾孩子累的,你在家好好睡一觉吧,然后抱着孩子云淡风轻地出去了。我一觉醒来,母亲带着孩子回来了,拿来一小包药片,嘱咐我刚刚已经给孩子吃了一次,回家后按时给孩子吃,吃完若孩子仍然夜里哭闹再回来找她。
看着母亲平静笃定的笑意,我惊奇欣喜得简直是晕头转向地回了家,当晚就给孩子再次吃了小小的药片。
那天晚上,我紧张得根本没有睡意,一方面对母亲的期待,期待神迹的再次降临,帮孩子渡过难关;另一方面更加是满满的好奇,好奇母亲笃定的笑意。
而再次几乎令自己不敢相信的是,连日来对夜晚都心生恐惧的孩子,这一夜竟果然就沉沉香美地睡到了天亮。我惊讶得简直快要大叫了,更加好奇不已,大早上就给母亲打了电话,急急地问母亲,到底是什么灵丹妙药啊?简直神了啊,看了多少次医生都没用呢,母亲静静听我大呼小叫地说完,然后笑着说,驱虫药。
我恍然,心一下羞愧地想起,可不是呢,孩子出生以来身体一直很好,自己也似忘记了,真真没给孩子按规定吃过驱虫药。而母亲听了我说的症状,猜之十有八九是小孩子肚里闹蛔虫,白天孩子活动,它是不动的,而夜晚孩子睡觉,它要觅食,孩子自然就肚子疼,而一去医院折腾,它就又不动了,孩子就又不疼了,回家了,一睡觉,就又出来,仅此而已。
粉碎效力的驱虫药,只吃了两次,孩子就全然生龙活虎一如往常了。
我的惊异却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母亲说这有何神奇的,不过是生活的小经验而已吧。但我心里想的是,自己身边有那么多与母亲同时代的人,却因何不曾有一个人知道呢?包括每次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时遇到的医生们,竟从未有一人想到。
后来一次我曾依葫芦画瓢,用同样的方法帮过一个朋友的孩子。朋友与我一样,大清早打来电话,电话里大呼小叫,大声连连感谢称奇,赞不绝口,同样惊异不已,随连连问我何时练就半神之体,云云。
我忽哑然,未及张口,有泪直冲眼眶,猝然而落。那时母亲离开我们已多年。悄悄挂断朋友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为朋友孩子恢复如常慰藉,为母亲的神异功德之延续慰藉。
3
假使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特定的精神属性,那么晚熟一定就是自己的标识了。甚至是在年龄意义上的成年之后,精神上的某些发育似乎仍显滞后,比如对新生事物的无感,等等。刚买回电脑的时候,曾建过一个电子邮箱,一次偶然在一个系统自动的电子邮件中,看见一个测试,大意是通过完成一些艰难的步骤,成功者将获取自己命运中一个秘密。
自己一向对网络各种杂乱游戏避而远之,况且更猜得到过程必定艰难烦琐而并无意义可言,但这一次有了例外,那个结果处将获取“命运的秘密”的神秘力量,意外地引发了我的兴致,于是开始一项项地完成既定的任务,深思熟虑,谨小慎微,竟一路来到了标注胜出的宫殿。
屏幕中的宫殿那么美,水晶般的淡紫色光泽熠熠而在,璀璨奇幻。右下角记录着参与测试的人数,将近三千人,而成功的还不到七十人。
我以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之一的身份点开了一个指定的按键,里面霎时弹出一阵美妙的七彩光晕,之后,现出一行紫色金边的粗体文字,竟是我最爱的隶书体,只有五个字:你有三条命。
三条命,我看后陡然一惊,看着那紫金相映的五个字愣愣失神,以至对这游戏的测试忽生神异的敬畏,因为我想起母亲曾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你有三条命。
在早年,北方鄉村家家都在院子的大门口打眼水井,平时就到井里提水到屋里的水缸中饮用。灰绿色的粗陶制的水缸大多高大深阔,是为一次能多盛些水。
水缸里的水多被父亲装得满满盈盈,是为小孩子们伸手就能取来喝。
我两岁多时,一次父亲连日加班,早出晚归,极度疲惫中浑然忘记了水缸中的水正越来越少。父亲上班走了,孩子们还在睡觉,早起的母亲趁着太阳没出来的清凉,在自家的园子里忙着收拾各种菜苗。
忽然她不知为何,箭一样冲回屋子,而就在进屋的刹那,在外间屋的水缸里,看见两只朝上的小脚丫,一只光着脚,一只穿着小布鞋。母亲倏然提着两只脚丫儿,将孩子一下就提了起来。
是我。我早上睡醒了,去喝水,水少,我握着搪瓷缸的把手一下下舀着,够不着,就把瘦小的身体趴在缸沿上,向底下的水面伸去。把不住缸沿的小手,头重脚轻的身体,两岁多的我大头向下,掉进水缸里了。
母亲将我拎出水缸的时候,我应该还没有任何被水呛到的感觉。母亲说,当时我还在笑。
我家的院落很大,从菜园到屋里,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米,母亲是如何听见那么微弱的落水声?几乎不可能。而即便听到,又怎能确认那微小至极的声音,在冗杂的乡下晨光里,会是孩子失手落进水缸里这么小概率的声音?就算听到了,冲到屋里最快也要十几秒,而母亲应该就在我掉进水里的同时冲到了屋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事实就是如此。
母亲将我拎出水缸,我真的还在笑,因为未被呛到水,反而仿佛成了好玩的游戏。母亲说水缸中的水应该没过了我细细的小脖子,也就是说,倒立的时候我的头部全然浸在水下,就是说,倒立在水中被水浸过头部的两岁多的那个小孩儿,那姿势,将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挣扎,只要刹那的几分钟,就将全然在世上消失了。
而母亲则在生死之交的须臾之间将我从命运的谷底拎了出来。
水从我的头顶流下,身上的衣服很快就湿了,散乱的头发贴在耳朵上,还在滴着水,一副可怜至极的样子,母亲倏然泪奔。而我还在笑,为母亲擦眼泪。母亲急忙问话,我应答如常,我的耳朵居然没进去一点水。母亲长呼一口气,但内疚后怕似乎使母亲因此受到了惊吓,据说躺了好些天才好起来。
自此家里的水缸換成了小一号的,而且里面的水永远满满的,永远在缸面上波光荡漾,满得流到外面来。母亲后来反复说起,我当时如何眨巴着刚刚睁开的眼睛,看着她笑的样子,愧疚心酸、欣慰又惊心。
后来我懂了,那个自水中被母亲拎起的自己,已仿佛一番神秘的再生。母亲第二次诞育了我,再次给了我一个来自水中的生命。
而母亲还给了我第三条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宽宽窄窄的路大多都是土路,漫长的冬天,不止的飞雪,常常几个月都不会化掉,厚厚地就积在地上。当来年春天来临,地下水及冻土层开始解冻,大量的积雪在路面之上,在太阳下慢慢融化,雪水再慢慢渗入土层,尘土飞扬的乡路就这样被上下夹攻一层层软化。若恰有负重的车经过,常常就会压破一些不结实的路面,一些泥浆就会涌出。更有甚者,车轮就会陷进泥坑之间,在乡下,谓之“翻浆”。
春天来了,母亲怀抱妹妹,三四岁的我跟在后面,嘴里吃着零食在路上走。
一辆马车果然陷进了刚刚开春翻浆的土路泥坑之中,路过的车辆和乡亲就都来帮忙,于是就有了喊号子似的热闹场景。远近的人情不自禁被鼎沸的人声吸引,纷纷望了过去。
母亲在看,对面过来一辆马车,赶车的人也在看,我猜小小的我应该也在看。没有人知道,马车离我们越来越近,要命的危险就在眼前了。
直到旁边一个人惊恐地大叫了起来:孩子裹进马车里了!赶车的人才醒过神来,手忙脚乱地停住马车,却已经晚了,小孩子已经完全在马车底下了。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车夫傻掉了一般,几个路人也全然懵掉了。而母亲刹那将妹妹扔在路边的草甸上,就从车底拉出了我,速度之快,躲过车轮马蹄之不可思议,令人惊诧,目瞪口呆。以至后来她自己也完全不能准确回忆起当时的动作。
马车夫彻底吓坏了,包括几个目睹的路人,大家都以为小孩子必定要受伤不轻,十几个马蹄,两个粗大的车轮,任何一个碰在三四岁的小孩子身上,小胳膊小腿的怕也不敢设想。
而我再次毫发无伤。
除了衣服上粘了点土,我就如同在路上跌了一下那么简单。是的,母亲在十几只钉着铁掌的马蹄,在两个宽大的车轮下,再次毫发无伤地救出了我。母亲说,她把依然瘦小的我紧紧抱在怀里哭了,而我依然在笑嘻嘻,非但没有任何伤,甚至都没受到一点惊吓,因为母亲的速度之快太神奇了,以至我都还完全来不及感觉到恐惧,就已经被母亲再一次从灾难的边缘拉了回来。
马车夫坐在路边发抖,连车也赶不了了。母亲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赶紧抱着妹妹拉着我回了家。
这两次生死攸关的过命经历,自然都是后来母亲讲起的,并在她的有生之年,讲过多次。每次就都如同第一次讲起,认真,深情。我也一样,每次都仿佛第一次听到,久久无语而百感交集。
一次大年初几,我该有二十岁的样子了,我和母亲在家里包饺子,母亲又讲了起来。这次讲完,母亲停下手,抬头看看我,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算上你出生,你有三条命。
三条命。
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怎样神异的祝福,怎样信仰般的炽爱灼灼。
想起惠特曼说的:“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地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是的,母亲,天下的母亲,当她自女孩儿一经成为母亲,她其实就成了赤子,而后成为每个孩子的神明,在世界的一切境遇面前,没有犹疑与含混,唯有笃定与坚韧,以及一颗通灵之心。
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十一月初的北方小村,已然是彻头彻尾的冬天了,早已不知下了几场雪,天地茫茫然无际无边,那个黎明,如一大雪封门。
那座简单的里外间平房里,正透着殷殷的热气,偶尔从哪个缝隙渗出去,在大雪的酷寒中,形成一缕玄美的白雾,如真似幻。小屋里比平日多烧了柴火,热热的炕头,满锅的热水。年轻俊朗的父亲从窗子跳到外面,铲开封在门口的雪,打开了被冰水封住了门轴的外间木门,再铲开院子里的雪,才打开了院门口吱呀呀的大门。
村里的接生婆来了。父亲屋里屋外忙活着,接生婆熟练地指挥着咬紧牙关的母亲。
太阳初升的辰时,我来了。我在母亲的阵痛中呱呱坠地。
母亲说刚出生的我细弱得像只小猫,哭声却还对付,仿佛隐喻着未来岁月的顽劣与荒蛮。这应该就是我的第一条命。我被裹进软软的襁褓,放在用柴火烧得热乎乎的炕上,像后来许多年一样,紧紧挨在疲惫而欣慰的母亲身边。
窗外大雪漫天,厚厚的积雪早已齐齐漫过外墙的窗台,接生婆和母亲说了一些话,就沿着父亲早起在雪中开出的仅一人宽的雪路,摇摇摆摆地回了。
雪继续下,天冷,不是那一天那一年,是那些年月,都那么冷。母亲说,有多冷呢,就是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基本整个白天不敢打开裹着的布包,因为温度太低,哪怕换个尿布的时间,就可能冻到一个婴儿。只等晚上门窗关紧,窗帘厚厚地挡住窗缝,炕头烧得烫人,热气不散了,才敢打开,换下那个裹了一天的布包。
记得少年时听母亲第一次说起这些的时候,自己惊呼着跳起来,讶然地看着母亲,随即就拉着母亲的胳膊,不依不饶地耍赖,说自己多可怜,竟是被尿布包裹着长大的呢。母亲就笑着拉回我坐下,摸着头发摸着脸摸着胳膊,说小婴儿的尿水是宝物,金贵着呢,若是男孩儿还是治病的灵药了,即便是女孩儿,也有营养的,看看,看看,你不是就长得这么大了,这么好。
每说到这儿,母亲都会认真再看着我,好像我真的长得如她所言的那么好。
我知道母亲要说的是什么,我是她的尿娃娃,那么一小小的尿娃娃,咋能长这样大,还这样好。天下母亲是多么稀罕自己的孩子呢,母亲也一样,甚至格外。于是就每次这样说,每次夸奖我长得这样好。
其实自小我就知道,自己在四个孩子中是最平庸的,眼睛不如妹妹大,睫毛不如弟弟长,皮肤不似姐姐白,姐弟三人如一择优遗传了父母,唯自己完成了缺点遗传,而更加有性情顽劣,等等。于是就曾无赖地埋怨母亲,为啥兄弟姐妹都继承着父母的优点,而凭啥他们只将自己的缺点都给了自己一个人,母亲依然笑着,依然说我长得如何稀罕人儿,并每次不厌其烦历数她口中我的各种好。
其实我心里最晓得母亲的安慰,所以我就不爱照镜子,一照就委屈得很,想起来也就胡乱又缠着问母亲,大多是老话,凭啥这么对自己,为啥自己眼睛不似母亲大,皮肤不随父亲白,凭啥全家就我一个人眼睛小小脸蛋不亮。稍大一些了,一次因为一个邻居婶婶的玩笑,说这孩子怎么长得就一点儿不像这家的呢,我就愤愤跑回了家,甚至还悲伤地疑虑自己也许是捡来的孩子也说不定,并为此认真地郁郁寡欢。
每次各种闹,母亲就每次都细细给我数着,我二宝眼睛多黑呵,像个闪闪发光的葡萄粒,腿多长呵,像电影里的人,脚丫多好看,不大也不小,歌唱得多好听呵,一学就会,小脑袋瓜多聪明呵,什么也都懂。每次母亲就这样极有耐性地说着,说着说着我就不闹了,就缠在母亲怀里憨憨笑了,忘了眼睛没有母亲大,皮肤没有父亲白。就只知道自己是母亲最稀罕的娃儿了。那种舒展的无边的温暖安心,那样刻骨而无际无边,并这样的安心,神奇地渐渐化作成年后内心深处的自信,化作内在心灵力量的无尽之源。
尘土飞扬的成长之路上,必定会经历过五味杂陈的心灵历程,却独独在任何时刻,都不曾缺失内在的自信之本,也正是这样的精神之根,令自己一路走到今天。无疑这是一个母亲赋予孩子最伟大的宝藏,是使得一个孩子在毕生成长的路上无数次满血复活的法宝。而母亲以自己对孩子最质朴的真爱,完成了这样如一神异的预置,于我,何止是仅仅的三条命,而是如母亲执拗的祝福一般,足够炽暖的安心,足够长久的幸运,丰沛而辽阔。
5
11月7日,世上平常的一天,1107,一组平凡复平凡的数字,就像许许多多的日子一样,像无限众多的数字一样。
但它曾有过不凡的时刻,甚至有过贵重的光荣与梦想,有过太阳初升的绚艳,有过星月沐照的辉光,而这一切,唯有母亲在的那些时候。
从那个大雪封门的辰时开始,到差二十四天六十岁的母亲离开世间,这组数字一直有着分外的温度,就像母亲的手,永远厚重暖热,无论多么冷多么冷的天,被母亲握在掌心,就如同婴儿回到母亲的心口窝一样妥帖温暖。
直到那个拂晓,我坐在医院的病床边,与昏迷的母亲度过最后一个夜晚。
初夏的黎明来临,天微微露出淡白的晨曦,昏迷的母亲越来越安详。而握着母亲的手,我知道母亲已然在回返的路上了。
母亲把命运与魂魄中最后的一缕温热,经由掌心交给了我,而后渐行渐远。天光微明,母亲终于从我的掌心收回最后一缕心魂。
天空睡去,大地冰凉。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清醒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可是在睡梦中人们却离开这个共同的世界,各自走进自己的世界。我知道此后,永远睡去的母亲,已然恒久地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而我在这个曾经与母亲生活的共同的世界,将踏遍人间每个角落,也再不会见到母亲了,这个赋予我生命与命运的人。
母亲生于农历七月初七,这是个从古至今弥漫着仙气的日子,因而我确信母亲的一生有着独属的神秘与仙异,而母亲倏然离开的时候,我们正在悄悄筹划着为母亲祝寿。
母亲倏尔倒下,只住了几天医院,未遭受任何痛楚,亦未留任何话语,就仿佛睡去一般。那一天,离母亲六十岁生日差二十四天。
无以复加的内疚,在母亲离世后的时间里,仿佛漫天的潮水一日比一日更汹涌地覆埋着自己的心神,终于令自己绝望了。无以救赎。
是为人子却未能尽孝的锥心刺骨的巨大痛楚。无以救赎。
直到许久后在一本书中依稀看到一句话,大意是说自古人生六十为一甲子,一甲子方为一轮回,也就是说,在人间时日未满一甲子的人,均非凡俗之类。
蓦然一惊。而后渐渐懂了,这就对了。是的,母亲绝非俗世凡人,母亲怎么能是泛泛之人?否则何以给孩子三条命,何以常常通晓凡俗之人无可解的谜题,何以于一甲子轮回前不言而别。
我的母亲必是仙界某位仙官,身怀秘密使命,下得凡尘几许年岁,如今期满复差去了。我确信母亲回返了自在光明的天界,就像我确信母亲说我长得好,确信母亲给了我三条命。
母亲回返了天界。1107,这于自己而言曾经荣光闪耀的一天,这组在母亲口中暖暖的数字,亦再次回归了平凡,悄然隐于浩瀚时空,隐于无限众多的数字之内,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也失去了出处,甚至失去了身心魂魄赖以活命的佐证。被命运从此唤作孤儿,不承认也得承认,这不是修辞,是认领。
在乡下,人们说“儿的生日,娘的苦日”,成年后的人所谓生日,就是孝敬曾经为自己受难的母亲。因为这一天,是母亲与命运与上苍达成某种秘密契约,才换得孩子平安健康来到这世上。而后,她是你的命运,你的菩萨,你的护法神。她让你成为在世上闪光的孩子,因为她看你的每一次,都在你的命运镌刻进最深沉壮美的祝福,像金子。
如今母亲离开了。
美国电影《兔子洞》中,一个痛失孩子的绝望哀恸的母亲,曾经在影片结尾时坚强地这样说:
“这一切,只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悲伤的版本,但我们还有其他的版本,在那儿,我们过得顺心如意——我喜欢这个想法,真不错——在某个地方,我们仍在欢度年华。”
欢度年华。我也喜欢这样的说法,或者说不是仅仅喜欢,而是毫无疑虑地深信,就是如此。
而且我要把这句话说给另外版本中的母亲,我同样相信她必能听见这些话,同样喜欢而深信,并正在感受到这些别样的时刻。
刚刚读过木心的一篇文章《哥伦比亚的倒影》,是將一些零散的时间与事物梦幻般弥合于一起,呈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倒影中。纷繁散碎却意味隽永如斯,掩卷而久久回味。
而世间一切果然不正是如此嘛,那些看似如水般流过生命的琐细的时光,只要人的灵魂还在找寻,生命还在铭怀,也许真的就都会在命运的湖水中有着真实的倒影,比如那些另外的版本,那些人们在欢度的年华,比如赋予我无限性命的神异的母亲,我命运深处,曾经的大雪封门。
多年后的北京,一场大雪,令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或者就如同艾略特所说:“我们所有的探寻的终点,将是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说得好,回到出发的地方,应该就是回到那个辰时,回到那一组数字被命运恩典的那场封门大雪。我在窗前看着并不真实的漫天大雪,偶然发现了今天的玄幻之处,竟然如同回到了原点,因为2015年11月7日,与多年前的11月7日一样,竟然也是周六,也是立冬的前一天,竟然仿若另一种时光神异的倒影,不由一阵温暖而惊心,而窗外同样亦如多年前一般,天地鸿蒙,大雪纷飞。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