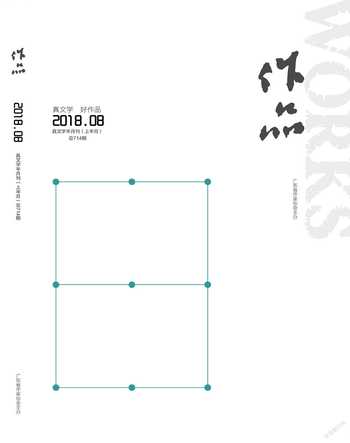走在东莞的街道上(散文)
一
我常想地球的神奇,它有海洋,有陆地,给我们最好的栖息空间。平时,它以安静的姿态听从人的安排,无论是绿树参天,还是高楼林立,它从不抱怨,只是沉默地接纳一切。偶尔,它报以地震、以海啸、以飙风,回应人类对它无止境的索取。
古人吃山拜山,饮水敬水,对喂饱其肚腹的五谷、禽畜致以最感恩的祭拜。如今,人和土地的关系则是以经济为基础。“土地如奥德赛的女奴一样,只是一笔被任意役使和处置的财富。”很多次走在东莞人群熙攘的街道,看着周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楼群,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苇岸在《土地道德》中的这句话。高楼大厦,在土地上制造更多阴影的同时,也阻碍了一些低处的人们获得阳光的可能。
但是,这并不妨碍五湖四海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垦、建设,通过勤劳的双手获取生存的资本。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奇迹,由此而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移民,他们同时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同一个地方,在这里工作、生活、扎根。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盛大景观。为此,我在我的诗歌中做过忠实的记录:
那一具具移动的肉体
他们有喧嚣的嘴唇
他們的肉体中有铁钉和裂缝
心中有同样的乡愁,眼眶里
有同样酸涩的泪水,他们
是一粒粒漂来的谷子或麦粒,从泥土中抽身
在城市里遍尝冷暖,被时光和命运蹂躏
渐渐变成一块坚硬的水泥
置身冰冷的场景
他们是决堤的涌流,是群飞的候鸟
是流失的故土的一部分
带着山谷晦暗的深渊
背负盛满眺望和叹息的村庄
追寻红色的浆果,出没在高楼的阴影之中
——《马路上到处是熙攘的人流 》 (选自诗集《别处》 ,漓江出版社, 2013年)
那么多的人,不同身份的人,混杂着挤在一起,让我想起了所在的城市和我的村庄,想起了狄更斯的《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二
当我再一次走上这里的街头,主山市场、莞樟大道、天骄百货……透过熙攘的人群,拥挤的气味、光、声音,我看见了曾经的自己,瘦弱的身体,穿着蓝色的工衣,在一排排轰隆的机器之间和流水线上穿梭,仔细检查手中的产品,用卡尺测量它的尺寸,签下一个个合格样板、不合格样板,与装配、喷油等部门交涉返工或者退货,在各种检测报表上飞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当我回忆起这些时,那一年的时光仿佛被擦亮,在空气中晃荡。十二年,足以使一个人的青春消耗殆尽,十二年之后,当我再一次从这里恍如迷宫的街道中辗转过来,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正是万达广场开业的那天。
广场上、楼梯上、走廊中、店铺里,到处都挤满了人,拥挤熙攘的人流,从一间店铺,涌向另一间店铺。孩子被大人们牵着手或自己蹦跳、奔跑。更小一点的被抱在手中,或放在小小的手推车里,稚嫩的眼睛望着这一切,眼神里充满了新奇。洁净明亮的地板,不停升降的电梯运送着兴致勃勃的人群。一楼空地上,罗马战神、巴洛克女皇、假面女王和天鹅公主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俄罗斯、巴西的火辣热情桑巴舞团,节奏明快、热情奔放的非洲手鼓,以及充满浓浓异域风情的肚皮舞和草裙舞,点燃了人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也点燃了身边的空气。身边走过的每个人脸上都笑意盈然,仿佛在庆祝某个重大的节日。
坚硬的墙壁,围成一座欢乐的城堡,仿佛一块巨大的磁石,将周围方圆几里的人们全都吸附到了这里,以至于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之前那么沉寂的一个地方,这些人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在人潮中让人感觉到自己极度渺小,仿佛就要被这喧嚣、巨大的声浪给吞噬掉。
这样的情景让我忆起小时候只有在节假日才有的欢乐心情,现在我们将这样的欢乐献给一栋建筑物的崛起、开业。
这座新生的城堡,繁华、欢乐的代名词。
从万达广场,到文华酒店,在明亮的玻璃窗户下站定,深深呼吸了一口空气。这风,仿佛也有了现代化的气息。
现代化,这三个字真是让人又爱又恨,欲罢不能。一边跟随人流在明亮的楼道、店铺里走着,一边啧啧赞叹现代建筑的美观,设计精巧。我想起了2012年,我再次来到这里,只见之前耸立的工厂已然不见,只剩一片偌大的平地,红色的土壤被一垛低矮的围墙围住,长满齐腰的野草,偶尔几个红色或黑色的塑料袋被弃其中,显出一派荒凉之色。我曾几次在这里抄小路去世博广场,从这片土地中穿过,仿佛在穿越一片荒凉的坟场……
十二年前,我也是在这里,从工厂的机房走向食堂、走向大门出口,仿佛已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
建筑物在围墙之内以看不见的速度悄悄向上生长,不需要其他营养。供它生长的只是建筑工人的汗水、石灰、砖瓦、钢筋、水泥。记得我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明亮、高大的建筑总使我感觉到生存的坚硬、冰冷,给我心理上的胆怯和荒凉。走在它的下面,我们被尘土裹挟着,机械地上班下班,在人群中迷茫,或者低下头,保护起自己一份小小的心情。十几年里,身边的建筑群不断生长,这座城市也风起云涌,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传统的农业小镇,变成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制造业名城。
曾经,在生命中的一段里程中,我无比抗拒这些建筑,过分开发的土地、矗立起来的越来越多的高楼,因为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一面是大量买不起楼房而只能租住在低矮潮湿的出租屋的人群,一面是大量开发的楼盘和空荡荡的楼房。那时,我还没有能够将这些因果理解通透的足够心智,只能在诗歌中徒劳地做着苍白无力的记录:
傍晚走过建筑工地,看见
夕阳的余光中,一排裸露的钢筋
矗立着,仿佛土地里生长出的
一条条毒刺,伸向茫茫苍穹
这是我所写的一首诗歌《废墟》中的一段。其实在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每天都从这片建筑工地旁经过,上班下班。虽然围着高高的围墙,但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象里面的劳作情景,看着围墙外壁的效果图,臆想着大楼建成之后的景象。同时,也会想起玛雅和楼兰的传说,想起底特律的废墟。我在想:什么时候,这一片繁华是否也会像这些城市一样,最终只变成一片废墟?于是,在结尾,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现在,零落的砖瓦和石块在夕阳中安静极了
面对未来成为废墟的命运
它们潜伏着
有比我更为长久的忍耐之心
——《废墟》节选 (选自诗集《别处》 ,漓江出版社, 2013年)
在我犹疑的生活中,庞大的建筑物不断向着太阳生长,终于,揭开了它的帷幕:形状各异的装饰性标志点缀在宽阔的广场、喷泉、花坛、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一切,让人感觉现实而又梦幻。高高矗立的文华酒楼比我想象的更加宏伟。墨蓝色的玻璃使整栋大楼更添神秘和奢华,点缀着一方蓝天,使天空也变得辉煌而美丽。我天生对美毫无抵抗力,看到这情景,我忘记了曾经的这些忧患。
但是,谁还会记得,高大、辉煌的文华酒楼坐落的地方,以前,是一个电子厂,一个三来一补企业,近千名生产工人,铁棚房里有日夜轰鸣的机器,加工车间里有一条条通宵不眠的流水线。工厂内的员工们穿着千篇一律的工作服,走在南方低矮的灌木丛间,走在围着围墙的厂区内,那也曾是记忆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现在,人们从酒店旁、马路上走过。他们之中,还有谁,有着与我同样的记忆?
三
十二年前,站在同一个地方,我深呼了一口气,望着对面的工厂。
其时,我只是一个来到这里的打工者,刚应聘上益安厂的品质主管。在立着文华酒楼招牌不远的地方,十二年前,立在那里的是朱红色瓷砖上镶嵌的一行金色大字:益安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虽然这家工厂在几年前已经搬迁走了,但在网络上,百度“东莞益安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的名称,仍然可以找到相关资料:主要经营生产CD唱机、扩音机。注册时间:1993年,法定代表人:梁华济。企业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主山工业区。
高大的机房里,一排排体型巨大的注塑机,发出一阵阵嘎嗒的声响,模具在体型粗陋的机器中一张一合,不时吐出造型精细的各种塑胶件。每一台机器都会安排一两个工人看管,半自动机器还需要工人拉开门,从模具中取出塑胶件。全自动机器一个工人则可以看几台,只须观看机器是否正常运转即可。除了看机器、拿产品,一些产品从模具中掉出来时,身上还带着成型时留下的披锋。工人们得用披锋刀把这些披锋仔细地削去。这个简单又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我就亲眼见过一位工人,因为开关门取塑胶件时分神了,手指被模具夹住骨折;我也曾见过被模具夹断的手指,只能做切除手术;还有的工人,因为削披锋时不小心,手指被披锋刀削到了,瞬间鲜血淋淋。这种工伤在塑胶厂常常发生。
机房里可以走动的有加料工、机修工和品检人员。加料工得常常观察机台上的生产原料是否用完,得在它还没用完之前把生产用的塑胶原料倒进机器的料斗。机修工得巡视机台,如果机器不能正常运作,得马上检修,不能耽误生产。品检人员得在规定时间内巡查机台,检查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在轰隆的机器声中,每一个人,就像机器上的零件一样,有序地运转。
在机器轰隆的机房里巡查机台、检查产品质量,给QA、QC(工厂品质管理人员简称,QC为品质控制人员,QA为品质保证人员)签合格、不合格样板,签他们所做的質量报表,偶尔与制造部的人因为产品质量问题争论,带着一群工人去返工。这就是当时我全部的工作。
有一天,当我巡到一个机台时,发现一位女工,坐在机器旁一边削披锋一边压低了声音伤心地哭泣。那低低的啜泣声中,能听出隐藏了许多心事和悲苦,在轰鸣的机器声中显得那么无助和悲凉。旁边机台的员工都关切地看着她,没有说话。这位女工我熟悉,四十多岁,来工厂做普工已有十几年,四川人,话不多,但生活极其俭朴,工作也非常认真。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泣。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那天她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家贫路远,为了节省回家的路费,将微薄工资中更多的钱寄回老家,她已经有十二年没有回过家了,孩子慢慢长大,记忆中并没有她这个妈妈,并且在电话中拒绝喊她“妈妈”,她为此伤心而泣。
了解这一情由后,我回到办公室呆坐了很久。其实,我知道,她的哭泣又何止这些?贫困的生活、远离家乡的牵挂、独自一人在异乡的孤苦无依……这些精神上的重负,都是压抑在每一个人心中的痛。
她低低啜泣的声音,这十几年中,我时时想起,那哭声中无法压抑的绝望和悲凉让人心碎。时过几年之后,我重新开始了写作,我写了大量关于漂泊、思乡的诗歌。没有人知道,在我那些诗行之后,总是漂着一个女人压低了嗓音无奈而又悲凉的啜泣声:
我们,现代的普罗米修斯
幻想在风雨飘摇的异乡盗取火种
回去点燃乡村年复一年沉寂的原野
身后翘首以待的心灵啊
希望,烛泪铸成的花朵
贴近你,我的双颊淋漓尽湿
——选自《蓝紫十四行诗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年)
因为工作职位的便利,家乡、村子里面便有一些人过来找我,以求让我在所在的工厂,给他们也谋上一个工作。我先后介绍过一些村子里的老乡进厂,之前熟悉的不熟悉的,进了异乡的工厂,便都成了亲戚一般,常常会有来往。
记忆中,邻村有一对夫妻,我介绍他们进了这家工厂。2003年,那时工厂还提供男女宿舍、饭堂。但他们选择租住在主山市场后面的一间狭小的屋子,早上穿过主山市场到工厂上班的时候,顺便捎上一些蔬菜,中午没时间做饭时,他们在工厂饭堂午餐,两个人只打一份饭菜凑合着吃,晚上则自己回到出租房里做。那时候,物价尚未飞涨,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才一千五六百元。但我听同村的另一个老乡讲,他们为了多存一点钱回家盖房子,一个月只给自己一百元的生活费,平时在主山市场挑最便宜的蔬菜买,将领到的工资全部寄回老家,工作几年之后他们离厂回家,便将家中破旧的老房子翻了新,盖了一栋明亮的大瓦房。另一位老乡与我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神里闪过的羡慕之情让人难忘。其实我知道,这位老乡的生活也是极其拮据,所得工资也全部寄回老家。她的心愿也是回家将破旧的住房翻新,盖一栋明亮的新瓦房。
有一次,周日休息,我路过主山市场,顺便去他们租住的出租房里看看,同时拉拉家常。过去的时候,正是午餐时间,简陋的桌子上只有一个青菜,青菜里难得地有了几块肉,丈夫舍不得吃,夹进了妻子的碗里,妻子心痛丈夫,又将肉夹回丈夫的碗里……我看到了他们推让的这一幕,虽然清贫但充满了温馨,但那一刻我的心中却满是酸楚。
这一幕,让我多年之后想起来,仍然感慨。在这里,他们租住最阴暗最便宜的房子,吃着市场里最便宜的菜,他们的工作虽然劳累,生活虽然清贫,但这种相濡以沫的亲情与恩爱,让人感觉多么温暖。
这样的情景,你们现在听我叙述,与我当时亲历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东莞,外来人群成百上千万,他们有的做一线员工,有的做中层或高层管理,有的有了自己的小公司做老板但仍在漂泊的,还有台籍、港籍或外籍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范围,但在他们中间,我时常会看到无形的墙壁,他们在同一个世界生活,但生活感受、精神世界、所思所想都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后来我开始写诗,我的脑海里常会浮现这两幕情景,我感觉到他们哭泣的脸、满带着爱的笑容的脸不时在我的诗行中出没。我明白了,其实,他们的哭泣就是我的哭泣,他们的清贫就是我的清贫,他们的温馨也是我的温馨。
现在,富丽堂皇的文华酒楼里,还有谁会记得这片土地上曾经机器轰隆的工厂?还有谁会记得制造车间那一条条通宵难眠的流水线?还有谁会记得这片土地上曾收留过一个女人因为生活拮据而发出的无奈的哭声?也有他们相依相伴、相濡以沫的温情?
四
时间,往后又推了几年,在一家餐馆里,我们围坐一桌,听同事小张讲述他小时候的故事:“小时候,爸爸常带我去主山市场那一带,提着鸟枪打鸟……”他说,在益安电子厂建成之前,这片土地还是一座小山头,山上树木葱茏,鸟儿翻飞。
小张是东莞本地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有着这片土地上人的典型性格:憨厚、正直、善良,言行之间又不失灵气。关于这片土地,他有着比我更深远的记忆。
对于这片土地,我只是一个后来者,只能根据这些零星的叙述,根据有限的资料以及这几年混迹东莞的经历,做出自己的联想。一次,我去东莞展览馆观看东莞老照片展,二百幅照片,记录着这个农业小镇原初的模样:水田、阡陌、沟渠、老屋和衣着朴素的人们。如今,照片中的这些地方,已经变成了酒楼、工厂和繁华的街道,以及散发着恶臭的下水道。
我们只是被时代裹挟的洪流,洪流过处,土地也会改变它原来的模样。
后来,我在网上查阅到这样的资料:
东莞历史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新石器时代,其境内东江沿岸已有原始人群聚居。公元前20世纪的夏代,东莞属南交趾。春秋战国时,东莞属“百粤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东莞属南海郡番禺县地。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公元222-228年中,分增城立东官郡。进入晋代,废东官郡,东莞分属番禺、增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东莞立县,名为宝安。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改名为东莞……
枯燥的文字介绍,它略去了这片土地上风起云涌的历史。我想起了1998年刚来这里的情景:到处是在建的工厂,工地上不断向上生长的高楼,马路上呼啸而过的车辆,留下回旋的黑色尾气;偶尔碰见挑着担子的本地女人,她们皮肤黝黑、身材瘦小,显得精干而利落,不论天晴还是下雨,都戴着斗笠,边缘围着一块黑布,随着头部晃动,脸在晃荡的黑布后面若隐若现,岁月刻画出来的皱纹里淌着汗水,她们挑着大大的笨重的担子,却能健步如飞;本地的男人们也不再务农躬耕,而是骑着一辆辆摩托车,在汽车站、在街道口等待着,搭载刚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群,他们用不熟悉的话语招呼:克宾朵,靓女?摩托车在他们的胯下发出不安分的轰鸣……
我想起几千年来,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俯仰躬耕之间,是对天空和大地的礼拜……什么时候起,这里“朴素的酒旗变成了诱人的霓虹,细碎的石子路变成了车辆飞驰的柏油路,一片片荒芜之地竖起了摩天高楼……”我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将二十多岁最好的年纪,撒落给了这里的五金厂、塑胶厂、电子厂…… 在不同车间、办公室里,挥霍仅有的青春,与来到这片土地的人们一起,背着简单的行囊向城市奔跑,失去了土地的荫护。为在这座城市有一方自己的遮风避雨之所,我们历尽艰辛,费尽全部的积蓄,也只能如蜗牛般,背负着重重的壳行走。
我也想起了我的家乡,在湘西南连绵起伏的山峦丘陵之中,房舍坐落于参差的树荫之间,周围阡陌相连。春天,连绵的绿色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秋天,金黄的稻田把大地打扮得像黄金的宫廷。鸟儿的啾啾声在林间起伏,偶尔传来邻村的犬吠。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瓦屋顶上开始飘出缕缕炊烟,放牛的孩子相互嬉笑、打闹。这记忆中的一幕一幕,曾是我生命的根源,是生活的全部价值与意义的承载,也曾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那里,土地是我的每一寸肌肤,走在绿色的田埂上,内心便感觉安宁、平静。在屋后面的小竹林里,曾印下我们童年的脚印,回荡着无忧无虑的笑声;在屋前的小河里,我们捕鱼摸虾,河水清澈,从未浑浊、干涸,浇灌着两岸的稻田;我们吃自己种的青菜、自己养的鸡鸭,唇齿之间是来自土地的滋养和芳香。天空清亮透明,在我们的字典里没有出现过“霾”这个词。什么时候,我们跟随时代的浪潮走了出来,生活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之中,季节的变换渐渐消失,人们慢慢变得脆弱而精致。而曾经水土肥沃的家乡,却因为大量的人群出走,渐渐变得荒芜、破败。
几十年过去,许多人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有了诗人贾岛“客舍并州数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的类似感觉。也有一些人,虽然身处这片土地,却时时在回望自己的故乡。我也写下过这样的诗歌:
朝南的方向,有未曾说出的
有默默守候与等待的
亲人居住的地方
总想回去的地方,叫故鄉
那一片沉默的土地和树林
只适合孤单地怀想
那片春花、秋月
眺望的时候,湘中
就端坐在一枚小小的枫叶之上
……
——《有一个方向是用来眺望的》 (选自诗集《别处》 ,漓江出版社 ,2013年)
时至今日,我怀揣着乡愁,仍在这片土地上谋求生存,但已经鲜少再看到挑着竹箩戴着斗笠的本地妇女了,拉客的摩托车司机也换成外地人,租房也慢慢变成外地的二手房东。以前能看到的她们,辛劳和沧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名贵护肤品和美容院护理过的脸,散发着舒适和慵懒的气息。在这片土地上,我终于清楚地看到了命运,看到了彼此的差异和不同。我们没有土地,我们所依赖的,只有从超市购回的粮食、水,暗淡的理想、生存的欲望以及绵绵的岁月,我们只有心灵的空间,储存属于自己的温暖、警觉和敬畏,储存忧伤、无助和高贵的信仰。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
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拍摄手法非常高明:从一个屋子里的生活场景,镜头推远,至窗户、至这条街道、至这座城市……随着镜头一步步推远,城市变成地球上的一个小点,最后,地球也变成一个小点,似一位尘埃,飘浮在浩渺的宇宙之中。有时,在我的脑海里,我也用这种方法,想象着自己在高楼林立的城市的一个小房间里,在庞大的地球上,在更庞大的宇宙里,微小到不存在。人类,地球上的蚁群,在这片土地上繁洐生息、战争、搏杀,如流水般奔流不息。而我这一生的轨迹,似乎就是一只流萤,在地球这庞大的地图上低飞,最终,消失在尘土里。
无论想象多么遥远,回过神来,我还得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地生存。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行走,从喧闹的菜市场里买回必需的食物,在嘈杂的生活中,使卑微渺小的心灵变得足够强大,足够抵御生活给予的种种重压和苦难,以便在这片土地上走完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