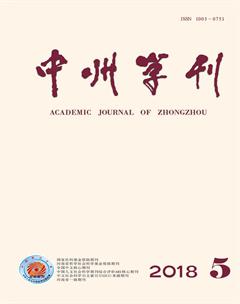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面向探讨
徐建宇 纪晓岚
摘 要:在当前关于城市社区治理微观基础的探讨中,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围绕政府权力、社会资源介入等外向力进行分析,却较少关注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然而,城市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激发社区内生的治理力量,盘活社区内在的各种关系,以社区自治推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具体表现为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它能够在社区自组织的形成和行动中将其组织成员的身份、关系和能力嵌入日常生活、集体行动和社区舆论等具体的治理实践层面,并推动城市社区实现可持续的良性治理。
关键词:内生力;日常生活;集体行动;社区舆论
中图分类号:C91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5-0074-06
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作用,实现“社区人治理社区事”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目标。在外向力指向的社会资源和政府支持有限的前提下,城市社区治理需要更多地依靠社区自身蕴含的内生力,即通过社区自组织有效整合、释放社区内在力量,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转向。目前,学界围绕城市社区治理内生力面向的深入研究还不充分,如何在社区管理活动中激发社区内生的治理力量,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社区自治的本质:治理的内生力面向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区建设在取得阶段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治理难题,比如社区组织发育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以及社区性公共活动缺乏吸引力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对城市社区治理内生力进行探讨的目的和价值正是为了应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上述困境。
在关于城市社区治理内生力问题的现有研究中,目前主要存在三种分析框架:第一种分析框架强调社区要以政府为主导,并在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外向力量的结合中强化社区自身的自治基础,整合内部治理力量。第二种分析框架主张在社区治理的微观层面加快推进社区“去行政化”“去代理化”转型,同时培育社区群众力量,使其成为社区治理力量的重要补充。第三种分析框架则倡导要从社区的社会资本、社区共同体精神和社区文化等方面激活社区内部能量,以此形成社区新动力来推动社区治理。三种分析框架都是从“元治理”和“多元共治”这两条主线对社区治理的内生力进行考察,并尝试通过明确政社关系来厘清不同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行动边界。但是,上述三种主张有着共同的不足,即不信任“社区自主自治”的可能性,均未摆脱国家—社会研究范式的局限。最近,有学者主张用社区“微治理”来盘活治理内生力以创新社区自治模式。①一些西方学者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要将社区治理的过程置于社区实践的结构框架内以突破过往研究的限制。②这种认识在本质上都是希望通过强化社区自治来达成行动共识以弥合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各种张力,最终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但是,对社区自治实践发生的本质——社区治理的内生力面向,学界仍缺乏专门的具体研究。
事实上,随着城市社区单位制的逐步瓦解,同一社区居民不再拥有共同的组织身份,这种转变在一段时间内削弱了社区居民的内在向心力和身份认同感,许多城市社区面临“组织衰败”的危机。当城市社区的居民对所居住的社区缺乏情感归属与认同时,就需要大量的活动类、公益慈善类、维权类、居民自治类社区社会组织将处于原子化的社区居民进行组织化联结,以期在社区组织再构中形成一种“微治理”机制③,并以此实现城市社区自主性治理。而这种以社区自治为旨趣的“微治理”何以可能,其重要的支撑基础就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因此,本研究从城市社区生活出发,结合上海梅陇三村“绿主妇议事会”(以下简称“绿主妇”)这一社区自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经验来诠释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并在研究中以社区自组织为轴,围绕日常生活、集体行动和社区舆论集中讨论社区治理内生力的现实面向,以期具体回答社区自组织如何通过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实现社区良性治理这一问题。
二、内生力的日常生活面向:从繁到简的转换
社区日常生活面向是社区治理内生力的现实基础。当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力量使日常生活与城市社区诸要素在开放性的耦合中变得愈加繁杂和不确定时,尤其是当日常生活构成社区治理的全部内容时,社区中自发产生的旨在解决社区日常生活复杂性的内生性力量开始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起点和行动支撑。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时,社区内生力的现实面向倾向于采取组织性行动降低这种复杂性,并在化繁为简中追求将社区日常生活内化为共同体意义上直接、自觉和能动的生活关系。
1.共同行动策略:行动简化与身份激活
城市社区基于住房空间特征和日常生活联系形成了一种“居住共同体”以应对社区生活的各种问题,而这种“居住共同体”成为社区内生力面向日常生活的分析单位和主体性基础。但是,城市社区碎片化的现实使得社区居民在复杂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更难以形成集体认同感,这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因此,聚焦和形塑涉及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内容的共同行动是简化社区复杂性问题的切入点。现实中,共同行动的基础往往是社区居民自发围绕日常生活问题(尤其是影响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倒逼式问题)而形成的一致性行动意向。比如,因居民与物业公司存在矛盾,梅陇三村小区一度垃圾遍地,居民日常生活因此受到极大影响,垃圾问题很快演变成社区公共问题,这倒逼社区居民不得不寻求解决办法。但是,社区生活垃圾问题的背后是一条繁杂的问题链,即居民与业委会、居民与物业公司以及居民与居委会之间长久积累的各种矛盾和不信任。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社区居民要借助自身的共同行动简化不同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率先打破社区问题停滞不决的僵局。實践证明,由社区居民中的积极分子自发成立的“绿主妇”,积极号召全体居民开展一系列垃圾减量活动,并因此成了梅陇三村从“垃圾村”变成“花园社区”的关键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居民尤其是其中的积极分子,采取的共同行动激发了居民自我动员的潜在性意愿,凝聚了社区居民内在的主动性力量,并由此盘活了社区治理的内生力。
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微观的人的态度的改变无论好坏,都一定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④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变革不会一蹴而就,但随着社区居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干预,居民微行动的持续性积累已经在自行地影响着社区治理的关系和社区生活的局面,而且一种充满变革意义的深远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形成。在此,我们还需要看到,共同的身份是共同行动的前提和基础。社区自组织赋予参与的居民以共同的组织身份,并以此凝结共识,进而重新激活社区居民之间原本陌生、松散的内生性社会关系,其目的就是要以自身身份、态度的转变以及面向日常生活细节的切实行动将居民潜在的关系和意愿转化为一致性行动。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社区居民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培育和锻炼,进而带来社区整体生活状态的改变,最终社区实现从封闭单一的居住空间向开放多样的邻里空间的转变。
2.组织功能拓展:问题介入与价值整合
“绿主妇”的实践表明依靠组织来挽救社区认同危机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尝试。以社区内生力为基础的自组织具有自身独特的组织功能,即通过自组织的各种活动,实现社区自我治理能力的培育、行动力量的凝聚以及治理目标和相关主体权责边界的明确,同时在赋予参与者以共同身份的过程中强化社区的价值认同。居民自发成立的社区组织蕴含一种天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组织共同目标的引导下能最大限度地缩小不同居民因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异带来的不平等。这样的组织特性是社区自组织能吸收不同成员以及进行组织功能拓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社区内生力得以不断释放的重要动力。其中,每个社区自组织都是以支持其行动的某一群体为基础来盘活社区内生力的,这是问题介入者的力量来源。介入者不断参与社区问题解决的过程同时也是社区治理内生力得以整合和统筹的过程。因此,社区问题介入者的角色确立是社区自组织实现功能定位的重要基础。“绿主妇”的特殊性在于其组织成员以女性居民为主,当其将社区自治工作的突破口放在女性居民上时,其所秉承“一个主妇牵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楼道,一个楼道辐射整个小区”的行动理念就迸发出强大的内生性能量。正是这一口号激发了“绿主妇”成员的集体认同感,鼓舞着社区女性居民积极介入社区事务,并将居民的主观感受和自我价值判断融入自组织的行动理念,最终在社区形成某种价值共同体。
在社区日常生活中作为治理主体的居民与作为治理客体的居民往往是相对意义的存在,两者角色常随社区事务的变化而转换。在最有限的环境里,最微小的个体行动也蕴涵着潜在的无限性,因为有时某个人的一个行动甚至一句话,都足以改变局面。⑤由社区普通居民组成的“绿主妇”通过积极参与居民代表会议、小区事务联席会、妇女代表会等自治性会议的一系列行动将其组织功能嵌入对社区所有居民共同生活问题的关注中,并以自组织的微行动来影响居民的态度和行为,由此实现社区自治行动价值链的整合。而正是社区自组织对社区所有居民共同生活问题的持续性关注有力消解了社区日常生活中居民关系碎片化和矛盾对立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成为问题介入者的社区意见领袖和精英分子对居民个体态度的转变和行为的选择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在解决社区公共问题时表现得更为直观。以社区自组织为轴来激活治理内生力不仅体现了超越主客二元治理思维的理念优势,也体现了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互构的新型社区治理关系。
三、内生力的集体行动面向:公共性与私性的平衡
城市社区公共生活是城市居民在社区居住空间内集聚的重要方式,但相互隔离的城市住宅模式以及社区自身对空间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增加了居民之间联系的困难程度。因此,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借助社区居民集体行动来打破社区因居住空间隔离造成的公共生活困境。鉴于此,在探讨城市社区内生力的集体行动面向时需要首先澄清三点事实:一是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是基于社区居民私性的居住空间而存在的,因此城市社区中的集体行动天然地面临着公共性与私性之间的张力;二是各种具体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固有存在是城市社区治理内生力的关系基础,其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社区集体行动在公共性与私性之间的摇摆;三是美好社区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社区公共性秩序的良性运行,这有赖于居民的集体行动力及其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
1.公共性与私性的联结要点:责任、回应和情感
通常情况下,城市社区内生力是社区潜在的能量,其迸发往往缘于居民对社区生活问题的集体性焦虑,尤其当社区治理难题久悬不解时,这种集体性焦虑会在社区中广泛弥漫,并迫使社区居民开始反思自己对社区的责任以及寻找自我(私性)和社区(公共性)之间的联结点。由此,社区居民发生從围观到参与的转变,并开始倾向于以集体行动来回应社区问题,这也是弥合社区公共性与私性之间张力的重要契机。在持续的回应中,社区集体行动强化了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对社区的责任感,情感上的沟通、理解和信任开始联结起原本并不熟悉的个体,居民之间的认知及其对社区的认同开始形成。当责任、回应和情感统一于社区公共生活时,居民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就会打破社区生活中公共性与私性的隔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指向社区治理难题时,源于社区内生力的集体行动能够潜移默化地强化居民的自组织性,激发居民作为组织成员的身份感,提升社区生活的公共性,弱化居民个体行动的私性,从而使社区生活处于公共性与私性的均衡状态。例如,在面对小区“停车难”问题时,同为社区居民的“绿主妇”成员虽然非常明白解决“停车难”问题的难处,但因“绿主妇”的组织身份,她们愿意担负起解决问题的责任。于是,“绿主妇”把回应这件涉及社区公共生活的难事当成自己的事情,并通过组织性的集体行动介入这一社区难题解决的全过程。不同于公共权力的强制性,社区自组织在集体行动中往往将情感的共鸣演绎成对他人的影响力,用“老邻居”“热心阿姨”等身份将居民纳入“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网中。这一“情感治理”的结果是将社区的公共生活与居民的私人生活自然地纳入社区的共同社会空间中,为社区公共生活的营造奠定了群众基础。
2.集体行动的持续条件:工作项目化运作与群己互构公共空间
城市社区治理实现“自治共享”的关键是要将居民有序组织起来,要从过去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转向以居民生活需求和优势发挥为导向的自我组织动员。这一转向意味着社区内生力指向的集体行动要保持动员上的可持续性,就要以社区公共性为基础对居民个体私性进行有效激励。其中,社区工作项目化运作是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激励形式。社区要形成这种性质的激励就要在社区公共性范畴内构建公共空间,并开展具有项目化特征和公众吸引力的活动以聚集分散的社区内生力,以此保持集体行动的可持续性和社区自组织性的延续。同时,集体行动的持续要注重“互动共享性”,即参与者要能在集体行动的面向中共享某种文化、规范、思维和兴趣等,并在自主性行动中自觉地开辟自我和群体互构的公共空间,由此强化社区集体性价值认同。另外,当社区内生力具化为社区自组织性时,集体行动的现实面向构建起以“信任—激励—声望”为核心的组织行动链,这表明居民参与社区集体行动是以信任和激励为前提条件的,是以提升自身声望为归依的主动性参与,其参与程度主要取决于参与者对公共性和私性的态度、对他人的信任、激励本身的吸引力以及他人对个体自身行为的影响等。实践层面,社区自组织集体行动保持可持续性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鼓励居民参与工作的项目化运作,让个体通过实践参与改变自身态度。以社区环保项目运作为例,“绿主妇”利用环保达人评选和积分制来有效激励居民参与,并通过开辟一平方米菜园和酵素坊等固定公共空间来组织居民开展环保集体行动,将环保阵地打造成能消解社区公共性与私性张力的公共空间;二是在群己互构公共空间的过程中主张居民的主体性地位和独立性。社区自组织借助自身组织平台,在主动与社区党员骨干、业委会成员、楼组长和社区志愿者等其他社区内生性自治力量的共商共议中提升居民的自我价值、主人翁意识和自主行动力,从而强化其参与社区自治的主动性。社区工作项目化运作增强了居民的集体行动力,使其从纯粹的情感联结转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营造。群己互构公共空间的营造过程也是自治互助性社区文化的培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公共性与私性在他人与自我、集体与个人、社区与社会的互动中得以弥合,社区居民的情感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得到提升。
3.集体行动的框架整合:关键群体的过程—结构演绎
类似“绿主妇”的社区自组织从成立到具体运作通常需要依靠社区中积极分子、精英的行动力量才能构筑社区自治的基层社会网络,并由此成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群体。关键群体能够在其他人不愿加入的情况下坚持开展动员活动,而且愿意付出必要的社会成本。在集体行动过程中,以动员居民参与为主要内容的行动框架成为社区关键群体以行动过程介入居民私人生活的结构性基础。框架源于个体之间共享的经历,就框架整合来说,框架与更大尺度的价值(信仰)系统的关系以及框架与参与者的关联性在其中较为关键:构建越强的关联性,就越能放大框架的动员效能。⑥作为关键群体的社区自组织能利用共同的生活经历等社区内生性元素将社区居民的利益、责任和情感联结于同一社会空间中,从而形成一种关联性,并借此凝聚社区参与者之间的行动联系,强化社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统一性,同时将动员性行动置于社区认知觉醒、社区行动强化和社区叙事记忆的过程—结构框架内。
围绕过程—结构的行动框架,社区自组织主要通过组织意义上的诱致性集体行动来整合社区治理的内生力。第一步是社区认知觉醒。为了提高集体动员的水平,集体行动要着眼于改变人们的问题意识。具体来讲,就是要以社区公共生活在居民私性中的投射为行动切入口,以此帮助居民形成社区问题意识。以社区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为例,“绿主妇”不仅向居民倡导绿色生活理念,还利用智能终端“零废弃回收卡”对每户家庭投送的塑料垃圾回收量进行记录、跟踪和管理,以此唤醒居民对该项问题的认知。第二步是社区行动强化,即在认知觉醒的基础上,社区自组织倾向于利用一系列行动来强化行动框架,主要是在开展集体行动中结合居民的生活需求和自身优势,通过制度化手段使居民的自主性行为嵌入集体行动中,形成社区居民之间互动的关系网络和行动传递机制。第三步是社区叙事记忆,即引导居民将自身参与的行为活动转化为行动的叙事记忆,这是自组织强化集体行动和社区生活中所蕴含的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社区自组织会利用自媒体、社区联谊和社区评选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记忆的持续性,目的就是通过营造“美好回忆”来强化居民的集体行动意识。
四、内生力的社区舆论面向:共在与共生的构建
社区舆论可理解为社区相当数量居民对某一问题公开表达的基本趋于一致的看法和意见,是居民对某一问题所持态度的集中体现。调研发现,社区舆论能够成为影响社区治理过程和成效的重要内生力,它既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又是形塑社区治理中不同主体内在结构关系的一股力量。通过社区居民的话语表达和舆论的发生机制,社区舆论能够激发社区治理的內生力,引导解决问题的行动面向。因此,与社区舆论共在的社区自组织,既需借助社区舆论来了解居民关注的社区议题,又需留意围绕某一具体议题所形成的社区舆论。
1.社区居民的话语表达:三种逻辑的生成和社区生活叙事
社区舆论的主体是社区居民,但其异质性、原子化的特点使社区舆论的生成面临无序化的困境,这就需要将社区居民的话语表达纳入组织性的集体行动中,唯有如此,才能激发舆论的动员能力。当个体被纳入特定组织时,组织成员的身份有利于扩展人际交往范围,增强集体动员的感召力。既存的关系纽带和群体亲和力是居民有效参与社区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同样,在社区舆论形成过程中,社区居民的话语表达只有与集体行动共在才可能形成公众意志,其中居民的话语表达主要围绕“什么情境”“什么人”“做什么”三种逻辑展开。因社区自组织的成立缘于对社区治理问题的回应,所以其在回应过程中倾向于借助社区舆论的力量来影响居民的行动意愿,同时这也成为其营造社区舆论的行动情境。许多社区自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和家庭主妇,这一群体同时也是社区日常生活中形塑社区舆论的主要力量。从社区信息传播主体的角度来看,他们是社区舆论的风向标,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传播各种信息。社区自组织“做什么”的话语表达内容就是要陈述、描绘和展示自身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图景。这是支撑和形塑社区公共舆论的行动基础,也是社区自组织激发社区内生力的行动面向。
生活叙事是社区舆论的内核,也是社区内生力在生活层面的重要内容。因社区生活叙事主要是社区居民围绕本社区日常生活细节进行的舆论营造,所以其结果是居民能在共同的生活叙事中形成和强化“自己人和自己社区”的认知和共同体信念。生活叙事能够充分利用社区舆论将社区居民和社区事件置于同一讨论话题中,这不仅能有效地将社区舆论与居民需求进行适时匹配和对接,还能构建社区舆论与居民需求彼此共在的互惠共生关系。尤其是社区自组织成员可以借助生活叙事来鉴别和扩展受众需求,并形成对社区某项待解问题的导向性话语,这对于社区信息传播和问题解决都有重要意义。
2.社区舆论的发生机制:话题策动、舆论导向与共识达成
任何问题都可能成为舆论话题,舆论话题是影响社区舆论的重要力量。围绕社区治理,社区舆论有着自身特有的发生机制。这一发生机制以社区治理的内生力为驱动,是构建社区价值认同的行动依据。也就是说,社区舆论本身能为社区自组织的行动提供一种正当性的论述,反过来,社区自组织能为社区舆论的形塑和传播提供相应的行动支撑,两者形成一种实践机制层面的共在与共生关系。通过由话题策动、舆论引导、共识达成等环节形成的舆论发生机制,社区自组织能够逐渐成为社区的民意代表,促成社区集体认同的形成。话题策动源于社区自组织对社区事务的关注;舆论引导可理解为一种舆论层面的集体动员,其侧重于用生活叙事和意见表达来策动社区居民参与共同行动,促使居民在共同行动中达成价值共识。社区舆论作为社区民意可理解为社区精神层面的内生力,对于推进当前社区生活的“共同体化”具有特殊作用。
这里,以话题策动、舆论导向和共识达成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舆论发生机制暗合了社区舆论中行动、组织与话语的三元整合,其所关注的是社区内不同要素如何利用社区内生力来整合社区舆论资源的问题。其中,行动是指自我动员和社区自组织的组织性行动,强调如何动员居民参与社区议题讨论,形成共同的行动意向和愿景;组织指的是当社区内生力具化为社区自组织时,如何通过社区自组织的话题策动和舆论导向强化居民的自我组织性和参与性,影响社区居民的行动选择和个体行为;话语指向社区舆论的表达内容和技术,尤其是社区舆论话语的选择和建构过程,以及在舆论表达中通过激活社区内生力来构建社区话语—行动实践系统的技术。伴随着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和集体行动,社区自组织利用三元整合将社区舆论从片段化转向秩序化、专题化和方向化,并由此构建自身与社区舆论的共在共生关系。这既有利于拓展社区治理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维度,又有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共享感和认同感。
五、余论
社区治理内生力的核心是社区居民自组织的培育,这是由内而外实现社区良性治理的关键,也是理解城市社区生活共同体何以可能的主线。日常生活、集体行动和社区舆论是社区治理内生力的三个现实面向,三者之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存在着共同的发生逻辑和内在的联结关系。另外,城市社区治理内生力的萌发离不开两个基础性条件:一是,随着城市住宅产权改革,城市社区居民开始注重自己在居住空间方面的话语表达和生活价值追求,这是城市社区内生力面向的行动基础;二是,目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集体行动无序化、治理主体缺失和资源整合低效等多方面困境,这些困境反过来又成为社区内生力的行动指向。正如本文所述,从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层面去探寻新的社区治理模式,能消解、转化社区治理中的一系列矛盾,尤其是充分发挥社区自组织的组织优势和功能,能有效减轻基层政府和居委会的治理压力,减少社区治理的成本和代价。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结合“绿主妇”组织运作的经验来探讨城市社区治理内生力的现实面向并不意味着社区治理内生力的其他方面(如内生力的运作机制、逻辑等)不重要,恰恰相反,要深刻理解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并不断优化治理路径仍需要对社区治理的内生力进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①参见宁华宗:《微治理:社区“开放空间”治理的实践与反思》,《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12期;陈福平:《厦门社区“微治理”》,《决策》2015年第6期;黎昕等:《社區微治理:社区创新治理的重要载体》,《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9期;谢正富:《治理孵化器:社会工作视角下“微治理”实现机制探索》,《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尹浩:《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多维赋权机制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②See Box R. C. Citizen Governance: Leading American Community into the 21st Century,Sage Publications Inc,1997, pp.12-26.
③See Hur M.H. Empowermen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xploring a Typology of the Process and Components across Discipline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006, Vol.34, No.5, pp.523-540.
④[匈]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7页。
⑤[德]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⑥See D.A.Snow, R.D.Benfo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1988, No.1, pp.197-219.
责任编辑:翊 明
Abstract: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microcosmic basi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ers tend to analyze the external forces of government power and social resource intervention, but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forc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However, the key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urban communities is to stimulate the community′s endogenous governance forces, to invigorate the various relationships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promote community governance by community autonomy. In reality, the internal forc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embodied in the self-organizing ability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t can embed the identity, relationship and ability of its members into the concrete practice level of daily life,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mmunity public opinion in the formation and action of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good 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ies.
Key words:endogenous force; daily life; collective action; community opi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