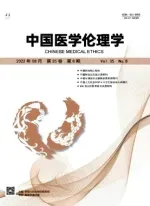道德创伤后应激障碍诊疗的探讨*
程 祺,常运立
(1 解放军第102医院全军精神医学中心,江苏 常州 213003, worldli5968@sina.com ;2 海军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433)
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对异乎寻常的威胁性、灾难性事件的延迟的、持久的反应。PTSD的核心症状有三组,即闯入性再体验症状、回避和麻木类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有些患者还可表现出不良的应对行为,如:滥用成瘾物质、攻击性行为、自伤或自杀行为等。同时抑郁症状也是很多PTSD患者常见的伴随症状。PTSD是一种常见的重性精神障碍,各国的总体发病率差异不大,美国社区样本中终生患病率为7%~12%[1]。而由于PTSD症状丰富、病程反复迁延,严重影响患者社会功能影响,导致精神残疾比例极高,不少患者因无法忍受其痛苦而自杀。PTSD是少数病因相对明确的心理障碍之一,且具有独特的临床特征(如反复的创伤性体验),是理想的疾病研究模型。故考察其病因及发病机制,能够对高危人群进行防护,提高心理危机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在总结了大量对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后提出,心理创伤源自内在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期待与集体或个人行为的冲突,战争经历导致PTSD不仅源于对生命的威胁还因为道德信念和社会期望被否定[2]。而近年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退伍老兵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道德创伤”的概念。道德创伤是反道德行为对个人道德良知造成的创伤,创伤源多是战争中具有违背道德信念的创伤事件,包括战争中的暴行、受命杀戮或目睹杀戮、无力保护遇难者等。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 (Veterans Administration,VA)在《道德创伤和退伍军人的道德修复》(2009)中将道德创伤定义为“参与、未能阻止、残忍目睹和闻听违反根深蒂固的道德信仰和期望的行为造成的伤害”[3]。Nash WP等通过对道德创伤性事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两个潜在因子并将其命名为感知犯罪和感知背叛[4]。
道德创伤性事件是罹患PTSD的危险因素还是独立致病因素?伴有道德创伤的PTSD是否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症状和远期预后,是否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法?本文将从以上这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1 PTSD诊断标准中创伤性事件的界定
诊断PTSD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患者近期经历了创伤性事件,而创伤性事件的界定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一般认为,PTSD的应激源强度往往异常剧烈,甚至是灾难性质,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10, ICD-10) 举出了若干这类事件的例子,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如战争、严重事故、目睹他人惨死、身受酷刑、恐怖活动受害者、被强奸等。几乎所有经历这类事件的人都会感到巨大的痛苦。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5, DSM-5) 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中关于经历创伤性事件的“标准A”是患者直接经历或目睹他人接触于实际的或者被威胁的死亡、严重的创伤或性暴力;获悉亲密的家庭成员或亲密的朋友身上发生了创伤事件,创伤事件必须是暴力或事故;反复经历或极端接触于创伤事件的令人作呕的细节(例如,急救员收集人体遗骸;警察反复接触虐待儿童的细节)[5]。
既往研究结论一致认为,威胁到生命的创伤事件(如战争或严重自然灾害的经历)对于平民以及军人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显著的预测力。然而大量的研究表明,更多具有PTSD症状的患者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并未达到严重伤害或死亡威胁的程度。平民罹患PTSD的创伤性事件包括遭受亲人的非暴力死亡、慢性疾病、离婚、被捕、诉讼或者被欺压等社会事件,与军人罹患PTSD相关的创伤性事件包括遭受暴力事件、丧失亲友、恶劣的环境等,这些并不包含在ICD-10和DSM-5的诊断标准关于创伤性事件的界定之中。
针对创伤性事件界定中存在的争议,Weathers FW等提出需要考虑对达不到诊断标准的创伤事件进行定义的必要性,解释为什么相对低强度的刺激事件也会引起PTSD[6]。Nash WP等认为罹患PTSD并不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威胁安全或者生命的事件,而是因为他们所遭受的内在信念和价值观的冲突和损害[4]。综上,当创伤性事件包含“道德创伤”时,即使创伤性事件的强度未达到严重伤害或死亡威胁的程度,也可能引发PTSD,即“道德创伤”对心理健康的损害,增加了个体罹患PTSD的危险。
平民遭遇的道德创伤事件可能包括遭受恐怖袭击、绑架、暴力犯罪行为,也包括较低刺激强度的离婚、诉讼或者被欺压等社会事件。在战场上,可能导致军人道德创伤的事件则包括:①背叛个人道德伦理信念的行为(背叛者包括领导、战友、平民或自我);②施加给他人的过度暴力行为;③致平民死亡或伤害的行为;④群体暴力行为。在所有的创伤事件中,参与暴力性杀戮,无疑是最直接、最危险的引发PTSD的因素[7]。
2 道德创伤对PTSD发生的影响
创伤性事件是PTSD诊断的必要条件,但不是PTSD发生的充分条件,虽然大多数人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最终只有部分人成为PTSD患者。许多变量影响到PTSD的发生,相关危险因素有:存在精神障碍的家族史与既往史、童年期曾遭受心理创伤、人格异常或神经症病史、创伤事件前后有其他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家庭经济条件差和躯体健康状态欠佳等[1,8]。以上危险因素可降低个体对应激源的防御力,延长疾病自然病程。
PTSD的早期研究主要以退伍军人、战俘及集中营的幸存者等为对象,后逐渐在各种人为和自然灾害的受害者中展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美国退伍军人中所报道的PTSD患病率多在30%~70%的范围内,少数报道患病率在90%以上[9-11]。在包含中国的数项地震受灾群体中的调查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在7%~20%左右[12-13]。可见,同样在创伤性事件的强度达到严重伤害或死亡威胁的程度时,大量包含遭受道德创伤的战争经历比可能随机遭遇的自然灾害,导致个体罹患PTSD的危险要高数倍,提示道德创伤可能有独特的引发相关症状的机制。
道德创伤的发生始于打破了有关公平正义、善恶判定、生命价值等伦理规则的行为。道德创伤事件作用于由个体道德信仰、文化传统等共同塑造的道德直觉,并基于此作用于士兵的道德推理,由此创伤事件内化成一种道德事件。进而道德事件或是道德事件所引发的二次体验的强度与道德情感的道德韧性相互作用,决定道德事件是走向自我宽恕或是道德创伤。自我宽恕意味着一条恢复调和之道,但如果受创者不能自我原谅,未能调和严重的道德冲突,并一再自我谴责,进而产生退缩、自伤、攻击等行为、认知和情感症状,受创者将陷入一个道德创伤愈来愈严重的恶性循环[14]。简言之,个体对杀戮、暴行的负罪感,引发羞愧、罪恶的内心体验,无法达成自我宽恕时则会产生逃避、自杀等行为和PTSD的认知及情感症状。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道德创伤中违背道德信仰的行为产生的内心冲突,导致与个体内在形象不一致的自我不和谐状态。如何协调自我不和谐的冲突是缓解创伤的关键,如果个体不能用现存的自我及相关模式完全同化和适应这一事件,他们将不断经受内疚、羞愧和焦虑情绪的折磨。由于频繁的侵入体验,不能融合将导致挥之不去的心理痛苦,且逃避行为也阻挠着协调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伴随道德创伤的PTSD,频繁唤醒的负性情绪是与“内疚”相关的情感,而不是“恐惧”相关的情感,与一般的PTSD不同。近期的神经影像学研究也表明,道德冲突时与认知、情感相关脑区环路的活化,前额叶—杏仁核的联系增强,可能反映了认知和情感反复的冲突与强化[15]。与既往研究发现的PTSD患者的前额叶控制功能减弱,导致杏仁核与对恐惧性反应的过度增强,形成概念化的条件反射,导致症状持续存在不同。
综上,道德创伤引发更多的认知和情感的冲突,导致个体难以协调自我不和谐的冲突,频繁唤醒与“内疚”相关的负性情绪,引发回避或攻击性的应对行为,与单纯的心理创伤性事件具有不同的引发PTSD相关症状的机制。
3 道德创伤对PTSD症状及预后的影响
依据目前的诊断标准,PTSD的主要临床症状包括:闯入性再体验、警觉性增高和回避。闯入性再体验指患者在清醒或梦境状态下,反复发生的闯入性地出现以错觉、幻觉构成的创伤性事件的重新体验,同时表现出当时的各种情绪反应。创伤性体验的反复重现是PTSD最常见和最具特征性的症状。警觉性增高表现为过度警觉、惊跳反应增强,易激惹及焦虑情绪。回避症状指患者对与创伤有关的场景、话题等采取持续回避的态度,甚至出现对相关内容的选择性遗忘。抑郁症状也是很多PTSD患者常见的伴随症状,可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悲观消极、与外界隔离等。
伴随道德创伤的PTSD即包含上述症状群,又有其显著的特征。众多对美军越战退伍老兵的临床研究发现,“对独自存活或求生行为感到罪恶(特别是后者)”是有战争经历的PTSD患者的常见症状。Nash WP对2009-2010年间参加阿富汗战争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研究发现,PTSD患者内疚的情绪多于恐惧,导致内疚最常见的原因是杀戮和未能救助战友[4]。另一项对幸存者的研究发现,独自存活者比失去爱人有更为严重的内疚症状,甚至会持续数十年。总结几项伴随道德创伤的PTSD的研究,发现突出的症状包括:① 社交障碍,如孤僻、回避亲人或具有攻击性;② 缺乏信任感,对组织和领导不信任、对照料者不信任;③ 价值感缺乏,精神颓废、信仰迷失;④悲观厌世,寻求自杀,相信宿命论;⑤精神药物和酒精依赖[2-4]。
可见,个人价值观崩塌和抑郁症状是此类病症的突出症状。与道德冲突相关的内疚情绪,更多的抑郁反应和不良的应对行为,包括物质依赖、自伤或自杀、伤害他人等,显著多于普通的PTSD患者。虽然“为独自生存感到罪恶”等症状也出现于自然灾害所致的PTSD患者,但因为很少存在因背叛个人道德信念的行为引发的剧烈道德冲突,症状闪回时伴随的内疚情绪较轻,精神上的痛苦程度相对较低。
不同于难以察觉的个人内心价值观念垮塌和道德情感冲突,PTSD患者的自杀和伤害他人等外显行为极易引发社会关注,频繁见于媒体报道。特别是有战争经历的现役军人和退伍老兵的高自杀率引发了大批学者的对道德创伤的巨大危害的关注和思考。VA的一项研究表明,2004-2012 年,平均每年约有1000位老兵自杀死亡,占到全美自杀总人数的20%[16]。罹患PTSD的战场老兵成为美国、英国等国军队及退伍军人医院精神科就诊的主要人群,军人自杀预防计划也成为美国、以色列等国军方卫生部门投入最多的项目。
综上所述,伴随道德创伤的PTSD患者,症状更丰富,突出表现为与道德冲突相关的内疚情绪,更多的抑郁反应和不良的应对行为,症状持续时间更长,预后更差,导致自杀的风险更高,对战争频发的国家和军队医疗资源的消耗巨大。
4 道德创伤对PTSD治疗的影响
对于PTSD的常规治疗包括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可用于PTSD的各个时间,目标是控制情绪和行为症状,本文不做详细讨论。心理治疗则是同时对症状和病因治疗,早期主要采用危机干预的原则和技术,提供心理支持,表达和宣泄相关情感,可改善预后;后期治疗中最常用且循证医学证据最多的是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CBT),而眼动脱敏和再加工、催眠治疗、精神分析治疗等也被报道有一定疗效[1]。针对PTSD的CBT治疗的核心是暴露疗法。采用复述、想象或游戏等方式让患者反复暴露在能够引发其创伤记忆并确保安全的情景中,使用放松方法控制情绪,将导致患者创伤记忆所引发的恐惧和痛苦下降,个体获得掌控感后通过引入新的信息改变原有的创伤记忆获得治愈。
而面对伴随道德创伤的PTSD患者,各种传统的心理疗法均未获得较好疗效,不少学者从心理治疗的原理上进行了分析。Litz BT指出,常规的认知疗法不能为道德创伤提供有效的治疗策略[3]。如果军人在充足的非增强性暴露下,能够获得认知重建的机会(或重获社会资源),他们的悲痛将会自然痊愈;而在道德创伤情况下,因患者无法在认知层面接受违背道德信念的行为,是缺乏重建的内置因素的,校正破坏性人际或社会关系的核心信念是非常困难的。如不采取辅助方式,而仅重复暴露于道德冲突经历之中,可能会引发医源性的再次创伤体验,尤其是对于那些有显著羞愧情绪体验者。换言之,如没有相应的归因与评估策略,缺乏除暴露治疗以外形成矫正和增进宽恕的经验,重复粗放地暴露于道德创伤的记忆之中,将会适得其反且产生潜在伤害。
VA认可并推行了 Litz BT基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老兵PTSD治疗的临床经验提出的适应性暴露(Adaptive Disclosure,AD)干预计划[3]。这是一种改良型的CBT治疗,主要步骤如下:①建立强大的工作同盟和充分信任的治疗关系;② 对道德创伤及其影响的教育,共同制定协作干预计划;③基于暴露疗法(情感聚焦式披露)处置道德创伤事件建立积极认知;④紧接着,以关键自我和其他形式对创伤经历造成的个体影响进行一次谨慎的、指令性和格式化的检测;⑤与仁慈的道德权威(如父母、教师、神职人员等)进行一次关于发生了什么、对患者当前和未来有何影响的想象对话,或与感觉不能救赎的战友进行一次关于自我做了什么(未做什么),以及对其当前和未来计划的想象对话;⑥促进修复和自我宽恕;⑦重建各种社会关系;⑧进一步评估目标与效果。
正念法通过在治疗师指导下进行正念冥想、接纳痛苦达到自我愈疗的效果,也广泛应用于治疗伴有道德创伤的PTSD患者的临床实践。具体包括正念减压法、接受与承诺疗法、正念认知疗法等[17]。以上治疗方法理论上能够缓解道德创伤后的自我不和谐的冲突,通过引入新的认知和感受元素完成自我与创伤事件的同化和和解,起到治愈的效果,但是还需要更多实证性研究结果的支持。此外,支持性团队也是实现康复的重要力量,积极利用社会支持资源,重建各种社会关系有利于促进道德创伤的康复,预防自杀和其他不良应对行为。
总之,道德创伤作为PTSD的致病因素有其特殊的致病原理,伴有道德创伤的PTSD,症状更丰富,预后更差,导致自杀的风险更高,治疗更加复杂。但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此类道德创伤几乎一定伴随心理创伤,对其进行回顾性对照研究其实是以道德、心理复合创伤与单纯心理创伤的区别进行对比,无法完全避免归因谬误,部分结论难以实证。因此,对于道德创伤对PTSD的影响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为此类疾病的防治提供更多的临床思路。
[1] Chris R. Brewin, Marylène Cloitre, Philip Hyland, et al. A review of current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CD-11 proposals for diagnosing PTSD and complex PTSD[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7, 58:1-15.
[2] Friedman, M J. Post-Vietnam syndrome: Recognition and management[J]. Psychosomatics, 1981,22:931-943.
[3] Litz B T,Stein N,Delaney E,et al. Moral injury and moral repair in war veterans: A preliminary model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y[J].Clinical Psychology eview,2009,29:695-706.
[4] Nash W P,Carper T L M, Mills M A,et al.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Moral Injury Events Scale[J]. Military Medicine,2013,178(6):646-652.
[5]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M].5版.张道龙,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69-173.
[6] Weathers FW, Keane TM. The criterion a problem revisited: controversies and challenges in defining and measuring psychological trauma[J]. J Trauma Stress,2007, 20(2): 107-121.
[7] Shay J. Moral injury[J].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2014,31(2):182-191.
[8] Dawne Vogt, Christopher R Erbes, Melissa A Polusn. Role of social context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7(14):138-142.
[9] Noelle B. Smith, Jack Tsai, Robert H. Pietrzak, et al. Differential predictive value of PTSD symptom clusters for mental health care among Iraq and Afghanistan veterans following PTSD diagnosis[J].Psychiatry Research, 2017,256:32-39.
[10] Joseph M. Currier, Jason M. Holland, Kent Drescher, et al. Initial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Moral Injury Questionnaire-Military Version[J]. Clin Psychol Psychother,2015,22: 54-63.
[11] Julia A. DiGangi, Stephanie Gorka, Kaveh Afshar,et al. Differential impact of post-deployment stress and PTSD on neural reactivity to emotional stimuli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veterans[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7, 96:9-14.
[12] Judite Blanc, Guitele J. Rahill, Stéphanie Laconi,et al. Religious Beliefs, PTSD, Depression and Resilience in Survivors of the 2010 Haiti Earthquake[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6,190(15):697-703.
[13] Wang HL, Jin H, Nunnink SE,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risk factors in military first responders 6 months after Wen 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J].Journal of Affecfive Disorders,201l,130(8):213-219.
[14] 杨放,常运立. 道德创伤:军事医学伦理新概念[J]. 医学与哲学, 2015,36 (11A) : 9-12.
[15] Wi Hoon Jung, Kristin Prehn, Zhuo Fang, et al.Moral competence and brain connectivity: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J]. NeuroImage, 2016, 141(1):408-415.
[16] Brock R N, Lettini G. Soul Repair: Recovering from Moral Injury after War [M].Boston: Beacon Press, 2012:Ⅻ.
[17] Ariel J Lang. Mindfulness in PTSD treatment[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7(14): 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