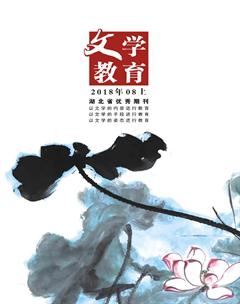阿图尔·施尼茨勒作品中的“卡萨诺瓦”人物形象对比
内容摘要:卡萨诺瓦是欧洲18世纪著名的“风流浪子”,他的自传《我的一生》给欧洲作家们留下了大量的创作空间,其印象派的生活方式受到当时维也纳现代派作家的推崇,阿图尔·施尼茨勒作为维也纳现代派中的杰出代表,在一战末期创作了两部风格迥异的“卡萨诺瓦”作品:中篇小说《卡萨诺瓦归乡记》和幽默剧《姐妹们或卡萨诺瓦在斯帕》,两部作品都围绕同一个人物,呈现其不同阶段的人生状态,以及行为方式的相应变化。本文将对施尼茨勒创作的这两个卡萨诺瓦进行比较,尝试通过分析他们的异同,探究作者对于印象派生活方式产生两种截然不同态度的原因。
关键词:施尼茨勒 卡萨诺瓦 维也纳现代派 印象主义
一.创作背景
1.真实的卡萨诺瓦
贾科莫·乔瓦尼·卡萨诺瓦是18世纪意大利的传奇人物,他的自传《我的一生》描述了他精彩的冒险经历,其中要数他与众多女性的交往尤为引人瞩目,这部作品的传世成就了卡萨诺瓦的冒险家之名,更使“卡萨诺瓦”一词,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名字,而成为了一个专属名词,这个词的注脚多为“爱情冒险家(Liebesabenteuer)”或“引诱者(Verführer)”。
由于卡萨诺瓦的自传涉及敏感人物,他在世时并未出版,直到1821年方才问世,由于内容太过离奇,围绕其真实性的争论一直存在。19世纪中叶,更有学者开始考证卡萨诺瓦自传的可信度,涉及他的生平故事的大量资源与素材纷纷被发掘,其文学价值也逐渐被作家们发现,自1833年起,卡萨诺瓦的形象便开始不断出现在文学和戏剧舞台上。
2.卡萨诺瓦与唐璜
在欧洲,卡萨诺瓦常与唐璜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四处周游,并有不计其数的伴侣,但他们在文学舞台上又呈现不同的形象:首先唐璜是一个虚构人物,来自传说,没有史实证明此人真实存在过,唐璜他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往往遭到被玩弄女性的怨恨,是个猎艳高手、采花大盗,形象负面;而卡萨诺瓦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对女性彬彬有礼,懂得如何取悦她们。尽管他和唐璜一样,也不会和这些女性长相厮守,但大都能保持友好的关系,甚至有的女性在卡萨诺瓦离去数年之后,仍对他念念不忘。在中文语境中,似乎没有和他对应的人物,很多文章中仅简单地将其称为“花花公子”,其实这并不能准确地诠释他的形象,因为卡萨诺瓦身上并未背负过多的道德审判,他的形象不是完全负面和被否定的,称他为“风流浪子”或许更为贴切。因此卡萨诺瓦虽和唐璜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并不能相互代替。
3.卡萨诺瓦与维也纳现代派
在德语文学领域,“‘卡萨诺瓦文學再创作”始于1899年。此时卡萨诺瓦的自传广受欢迎,被大量阅读与研究,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世纪60年代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匈牙利贵族达成协议,组建二元君主制奥匈帝国,此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这一时段被史蒂芬.茨威格称为“安全的黄金时代”。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催生了奥地利文化在1890年后的20年里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在多个文化领域颇有建树,涵盖文学、心理学、建筑、绘画、音乐等诸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化多元而没有统一的主题,且创作量巨大,很难被定义和描述,于是统称为“维也纳现代派”。不过在这一片繁华的背后,哈布斯堡王朝走向衰弱是显见的事实,整个维也纳都充斥着“世纪末的悲观气氛”,人们在极度绝望中追求暂时的欢愉。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还通过物理研究,提出一种哲学理论,即摒弃传统科学中的对于内部与外部世界都具有固定的规则这一原则,马赫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世界是人们感觉的总和。没有绝对永恒的物体,组成物体的各种要素仅存在于人的感觉中,所以都是变化不定的。(韩,自我-心灵-梦幻——论维也纳现代派的审美现代性 69)他强调,只有当下和当下的体验才是真实的,“自我”依赖于眼前的体验而存在。于是根据这种思想,衍生出了印象派生活方式,即应该及时享受当下的时光,不要考虑过去和未来,因为所有一切在下一秒就可能消失。(Lehnen 95)这为人们的“末世狂欢”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此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维也纳现代派文学,也承接这一观点,虽然该流派作家在创作风格上各有千秋,但都围绕自我、心灵和梦幻的主题,而且他们共同的认知是:世界上的事物无一不处在不可阻挡的消失和变化的过程中;永恒的运动、永恒的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现实是飘忽不定的、瞬息万变的,因此艺术创作的意义不再重视再现客观事物,而是把外在的生活引入到内在的精神中去,表现人在一个又一个瞬间的主观感受。(韩,赫尔曼.巴尔:维也纳现代派的奠基人 54-55)于是某一主题被大量不同的作品反复采用,或者某个主题反复由某个人物呈现,只是其行为在不同作品中会有所不同,正是这种创作主观性的体现,而冒险家的故事又完美地呈现了印象派的生活方式,自然成为了当时广受欢迎的创作主题。卡萨诺瓦作为有名的冒险家,作家们纷纷创作以他为主角的作品,卡萨诺瓦不再被单纯地看作“风流浪子”,对他的传统评价也被颠覆,其及时享受生命每一刻的态度受到赞扬,他的生活方式被视为榜样,,大众视其为伟大的生活艺术家,其自传更是被不少人当作生活教科书。在这种情况下,维也纳作家对卡萨诺瓦这个形象进行反复研究与再创作也就不足为怪了,从1898年到1919年维也纳各创作团体涌现大量有关卡萨诺瓦的作品,占了两个世纪以来同类作品的三分之一。(Lehnen 60)阿图尔.施尼茨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这两部有关卡萨诺瓦的作品。
二.年迈的冒险家:卡萨诺瓦形象在《卡萨诺瓦归乡记》
《卡萨诺瓦归乡记》是施尼茨勒长期研究卡萨诺瓦回忆录后的创作成果,在创作这部小说的同时,他也在着手写自传,53岁的他认为这个年纪是他生命的转折点,可以对他的前半生做一个总结,因此其小说主角也有了相同的年龄:53岁的卡萨诺瓦不再年轻,却仍然渴望新鲜刺激的生活,于是不断回顾过去。(Gleisenstein 120)在小说中,新旧生活不断爆发激烈冲突,卡萨诺瓦处在精彩的过去和平淡的现在之间,已显得不像个冒险家,而更像个渴望落叶归根的老人——一如施尼茨勒自己。文中第一句话即定下来基调:
“卡萨诺瓦在他第53个年头上,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冒险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周游世界的不安,他渴望回到故乡威尼斯的愿望与日俱增,如同一只鸟儿奋力冲上云霄后,却被困在越来越小的圈子里。”(《卡萨诺瓦归乡记》:1)
此处可以看出,热爱远行和冒险的心已被回家的渴望所取代。卡萨诺瓦如此渴望回归威尼斯,是因为那里承载了太多他年少时的记忆,那时的他颇受欢迎。(Norbert 246)“他曾经为母亲写过一部喜剧《被监护人》,还曾孩子气地爱上过一位园丁的小女儿;他假冒‘圣.萨姆剧院的乐团小提琴手,和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穿梭在小巷里,混迹于酒馆中,出入威尼斯的各个舞会和赌场,有时乔装打扮,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卡》:93.)这些快乐的经历让卡萨诺瓦坚信:“当他再回到威尼斯,也会重获新生。”(《卡》:48)
正当卡萨诺瓦将这次回家之旅视作反抗衰老的唯一出路时,马可丽娜出现了,这使他又有了新的冒险动力。实际上,他的内心从未放弃过冒险。尽管这已与他的年龄格格不入,但他仍然试图尽力挽救其“风流浪子”的形象。于是除了回到威尼斯以外,得到马可丽娜成为了他重返青春的第二条出路。
这位19岁的女孩,是小说中塑造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才貌双全。(Gleisenstein 133)有了马可丽娜的对比,更凸显卡萨诺瓦的衰老:“我额上皱纹沟壑纵横,脖子上皮肤松弛,眼袋浮肿!”“手指像鸡爪一样,指甲上布满小黄斑”。(《卡》:26)卡萨诺瓦对自己的年龄深深地厌恶,称自己“乞丐”、“蠢材”。(《卡》:26)这还是他不愿面对的现实。为了找回自信,证明自己的魅力,他必须得到马可丽娜。他认为:“马可丽娜可以让我重获青春”,(《卡》:26)“少女的拥抱能让我健康起来”(《卡》S. 27.)。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竟不择手段: 利用马可丽娜的爱人洛伦兹的经济窘境,得到了接近马可丽娜的机会。这时的卡萨诺瓦已经不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浪子,而沦落成了强迫女性就范的唐璜式人物。
与马可丽娜度过的一夜,充满了梦与希望,卡萨诺瓦在那个瞬间确实找回了自信。(Lüthi 53)年龄似乎对于他的冒险生涯不再是障碍:“不是有神的存在吗?年轻和年老不过是人们臆造出来的神话罢了”。(《卡》:99.)他甚至构想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将来能够取代洛伦兹在马可丽娜心目中的位置。然而第二天清晨马可丽娜的反应让他迅速跌回了现实。(Rey 247)整个场景没有一句对话,当卡萨诺瓦向“马可丽娜张开双臂,她用左手挡开,同时快速用右手抓起衣服挡在胸前”。(《卡》:103)此时无聲胜有声,眼神和动作已点明一切,卡萨诺瓦在马可丽娜冰冷的眼神里读出了对他的评价:
“他从马可丽娜眼神中宁可读到:“骗子—登徒子—流氓”,然而并没有,他只读到一个词,这个词足以将他重重击倒在地,比任何指责都让他恐惧,那是对他最终的宣判:老人。”(《卡》:103)
尽管卡萨诺瓦能够与马可丽娜共度一晚, 甚至后来还在决斗中杀死了她的情人洛伦兹,但是外在的胜利却不能掩饰他内在的失败,高潮很快褪去,剩下的只有空虚与颓废。最终卡萨诺瓦意识到,衰老是冒险生活无法逾越的屏障。他曾经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经历了许多充满浪漫的冒险,但此刻这些都不得不终结。(Lüthi 51)因为这样的旅行受时间和自然规律的限制,即使能通过控制片刻时间来短暂逃避,却终将被时间的车轮无情地碾过,岁月流逝,让曾经的冒险家变成了老人——老得不能再冒险的老人。杀死洛伦兹,卡萨诺瓦在逃亡回威尼斯的路上,他的睡眠“无梦而沉闷”,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
三.年轻的冒险家:卡萨诺瓦形象在《姐妹们或者卡萨诺瓦在斯帕》
滑稽剧《姐妹们或者卡萨诺瓦在斯帕》虽然也是根据卡萨诺瓦的自传所创作,施尼茨勒却仅借用了自传中的名字、人物特性及戏剧冲突的动机(Gttsche8),实际上卡萨诺瓦32岁时并未到过斯帕。
戏剧与小说同时创作,却呈现另一种风格,与小说里压抑绝望的气氛截然不同,戏剧的基调轻松愉快。(Lehnen 217)剧中的卡萨诺瓦是纯粹的印象派,32岁的他,依然是一名颇有名气的浪子,正值他魅力的巅峰,年轻英俊,很讨女性欢心,总是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在第一幕里卡萨诺瓦并未露面,仅通过旁人的对话,便将其四处游走,浪迹天涯的形象勾勒得清清楚楚。封.古达尔先生——一位被开除的荷兰官员,在剧中这样描述他:
呐,说到这个人
人们在哪里看见他,他就属于哪里
多年前我在西班牙遇到阁下,是一位绅士;
后来去伦敦的海边,我却在贼窝里看到他和恶棍称兄道弟;
在巴黎他是和上层人士打交道的生意人
在布列塔尼的城堡里却他是牧羊人剧里的诗人;
他是警察,是百万富翁,是乞丐,亦或是平民
我都不吃惊,他经历的远比这多得多。
(《姐妹们或卡萨诺瓦在斯帕》:655-656).
第一幕中登场的是两对恋人:安德烈和安妮娜,以及弗拉米尼亚和桑提思。故事由安德烈和安妮娜的对话展开。整部剧围绕着嫉妒这一主题。戏剧冲突发展来自一个传统的动机:当事人不知道他们上一晚和谁在一起。事实上,卡萨诺瓦与弗拉米尼亚约定:在她的丈夫去和安德烈一起赌博的晚上,去与她幽会,但是卡萨诺瓦爬错了窗户,上了安妮娜的床,而他对此一无所知。
在小说展现的是年轻与衰老之间的冲突,而荒诞剧则表达了印象派与市民阶层不同的生活理念。卡萨诺瓦在剧中作为反市民阶层的形象,与安妮娜的丈夫——安德烈形成鲜明对比 (Gleinstein 126):循规蹈矩的市民阶级,寻求的是安全、稳定的生活,最好生活能够没有波澜,一直平稳地持续,家是他们的避风港;卡萨诺瓦则过着典型的印象派生活,作为一个冒险家,他总是四处漂泊,没有一点儿思乡之情,他即不想定居也不想回家。对比小说中卡萨诺瓦强烈的回归威尼斯的愿望,在滑稽剧中他只向往远方。
回家?哦,别傻了,人就应该以流浪为家
行游不能带给灵魂永恒的平静吗?
昨天已经远去
围绕我们的是今天,为何不能信任它?
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家乡?
它就像路上曾经的歇脚处,可近,可远。
家和远方——令人麻木的音调。(《姐》:733).
卡萨诺瓦对安德烈说:“你的目的是平静、秩序与规则。你旅行的目的是回家”。(《姐》:691)卡萨诺瓦的生活正好与之相反。他不在乎生活的延续性。每一次经历对他来说都是不可复制的快乐瞬间,是一次性的体验。(Lüthi 49)这部喜剧的结尾表达了自由地爱的快乐。卡萨诺瓦宣称:所有的女性都应该像姐妹们一样。“男人们能像兄弟一样正如女人们像姐妹一样。在灵魂深处都是姐妹,若果真如此,生活就轻松多了。”(《姐》:735.)就这样,似乎之前所有的烦恼都被遗忘,甚至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四.两个卡萨诺瓦形象对比
1.性格的统一性
在两部作品中,卡萨诺瓦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首先他的性格特征始终保持一致性:即无论在戏剧中,还是小说里,卡萨诺瓦都是极富魅力的人物,戏剧中,弗拉米尼亚和特瑞莎都爱上了他,甚至反过来引诱他。尽管安妮娜不爱他,但她由于与卡萨诺瓦的一夜情,竟也愿意离开她的未婚夫安德烈。小说里,虽然展示了一个失败的老年卡萨诺瓦,但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失掉魅力,他仍然对女性具有吸引力:旅馆的寡妇追随他到曼图阿,他曾经的情人阿米莉亚在过去16年里仍对他念念不忘。即使是洛伦兹的情人玛切莎,都用“含情脉脉的眼神”(《卡》:36)打量卡薩诺瓦。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冒险了,他能得到的,并不喜欢,而他想要的,却得不到,基于这样的不满足,引发了后续的故事,切入了对印象派生活方式的反思。
2.同样的主题,不同的结局
同为表现典型的“引诱者”追求女性的主题,却有着不同的结局。两个卡萨诺瓦都经历了一夜情,一次是无意的行为(《姐妹们或者卡萨诺瓦在斯帕》),而另一次是有意为之(《卡萨诺瓦归乡记》)。在幽默剧中,作者以轻松愉快的笔触,着力刻画了卡萨诺瓦错综复杂的爱情关系,凸显了他的个人魅力,他误翻安妮娜的窗户,事后也没有引起女性的强烈反感,反而安妮娜想让这种误会合法化并和他继续联系,甚至,强迫自己爱上他。印象派生活方式取得又一次胜利,同时反衬出市民生活的无聊与乏味。而小说则正好相反:卡萨诺瓦本是广受欢迎的“妇女之友”,深谙女人心事,颇得女人欢心,但其原形毕露之时,为了私欲不择手段,不负责任的性格显露无遗。这样的反差使一夜情后他和女性的关系彻底被破坏,马可丽娜无声的惊恐和沉默表明错误无法再弥补,欺骗别人的结果,最终反噬自己,卡萨诺瓦自欺欺人的迷梦也被打破。
很明显,在两部作品中,施尼茨勒对老年卡萨诺瓦着墨更多(Rey 198)。在戏剧中,既没有展示生活的艰辛,也没有对道德问题的正视,虽然剧中也有一个老引诱者,封.古达尔先生,起到镜面形象的作用,但剧中对年纪问题只是一笔带过(Lehnen 204)。年轻的卡萨诺瓦带着印象主义的特点,像个爱情和生活的天才般出现,他的生活由无尽的爱情冒险构成,而被换下的爱人,他们的生活轨迹已被打乱,矛盾冲突并未真正解决。在安格利卡. 格莱森希坦的文学研究中这样表述:“在喜剧中最后产生的和解不是理性处理矛盾的结果,而只是环境需要一个大团圆结局,戏剧结尾时未解决的问题被抛到了脑后。小说则通过对卡萨诺瓦彻底分析完成了对当时衰落的特有的市民时代的分析。”(Gleinstein 137)与青年卡萨诺瓦相比,老年卡萨诺瓦是时间的牺牲品,在小说中,围绕着欺骗与自我欺骗,呈现了这个威尼斯人的重要生活转折,他已经被“浪子”的冒险生活所抛弃。回家途中的卡萨诺瓦再不能像以前一样,进行无尽的爱情游戏了。
3.印象派生活方式的两极映射
卡萨诺瓦的成功与失败,体现了印象派生活方式的正负两极,当只聚焦某一个短暂的时间片段时,印象派的生活无疑是惊险、刺激,富有激情的,远比平淡的市民生活精彩,然而岁月不饶人,当冒险家老去,在连续的时间中,他要面对的正是他所厌弃的无聊的市民生活,此时的印象派则呈现出消极的一面。两部作品的反差感与作者的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施尼茨勒年轻时也曾有如卡萨诺瓦般的经历,但是在他创作这两部作品时,奥地利“安全的黄金期”已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奥匈帝国陷入即将分崩离析的绝境,民族矛盾重重,社会冲突不断,大战造就的“世界废墟”更是“残暴得惊人”,施尼茨勒试图从这样可怕的时期逃离(Gleinstein 120),希望能再次找寻一战前的美好时光。幽默剧正是体现了他对曾经生活的怀念。而对外在世界的危机的逃避,更促使文学作品关注内在危机,年过半百的施尼茨勒感觉自己即将步入老年,曾经的印象派生活方式,使他感觉力不从心,于是他开始反思这种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小说正是作者自我描述、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的体现,也是他试图寻找解决自我危机的出口。 虽然施尼茨勒依然向往印象派的生活,但是他也深知这种生活不可延续,因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五.结论
如文章所示,两部作品中的卡萨诺瓦形象侧重不同,冒险家的行为、性格貌似对立,实则统一,呈现的是其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表现,年迈的卡萨诺瓦和年轻的卡萨诺瓦即有共同点,比如引诱的能力,爱人的交换;也有区别,比如老年卡萨诺瓦的乡愁对比年轻卡萨诺瓦的渴望远方,以及一夜情后的不同结局。
这样的表现手法反映的是作者对自己生活的反思,在印象派盛行的二十世纪初叶,以为可以永远追求片段的欢愉,而最后在连续的时间进程里,留下的却只有无尽的落寞。
引用作品
[1]Schnitzler,Arthur:Casanovas Heimfahrt.Stuttgart 2003.
[2]Schnitzler,Arthur:Die Schwestern oder Casanova in Spa. In Gesammelte Werke: Die dramatischen Werke 2. Frankfurt am Main. 1962.
引用文献
[1]Gleisenstein,Angelika: Die Casanova-Werke Arthur Schnitzlers.“ In Hartmut Scheible, ed., Arthur Schnitzler in neuer Sicht, München, 1981: 117-141
[2]Lehnen, Carina:Casanova bei Arthur Schnitzler.“In Das Lob des Verführers. ber die Mythisierung der Casanova-Figur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zwischen 1899 und 1933. Paderborn, 1995: 179-232.
[3]Lüthi, Hans Jürg:Der Taugenichts als Abenteurer. Arthur Schnitzler und Hugo von Hofmannsthal“In Der Taugenichts. Versuche über Gestaltungen und Umgestaltungen einer poetischen Figur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Tübingen, 1933: 47-74
[4] Norbert, Oellers: Arthur Schnitzlers Novelle Casanovas Heimfahrt‘“. In Mark H. Gelber, ed., Von Franzos zu Canetti. Jüdischen Autoren aus sterreich. Tübingen, 1996: 239-252
[5]Rey, Willian H.:Schnitzlers Erzhlung Casanovas Heimfahrt‘Eine Strukturanalyse“. In Schwarz, Egon u.a.ed., Festschrift für Bernhard Blume. Gttingen, 1967: 195- 217
[6]韓瑞祥: 《赫尔曼.巴尔:维也纳现代派的奠基人》, 《外国文学》 2007年第1期: 54-61
[7] 韩瑞祥: 《自我-心灵-梦幻——论维也纳现代派的审美现代性》, 《当代外国文学》 2008年第3期: 66-73
[8]Gttsche, Dirk: Der Abenteurer als Reflexionsfigur einer anderern Sozilialitt:Arthur Schnitzlers Lustspiel Die Schwestern oder Casanova in Spa‘ im Kontext der Casanova-Figurationen der frühen Moderne“.
(作者介绍:胡麟,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对外德语专业,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教,从事德语教学,研究方向:德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