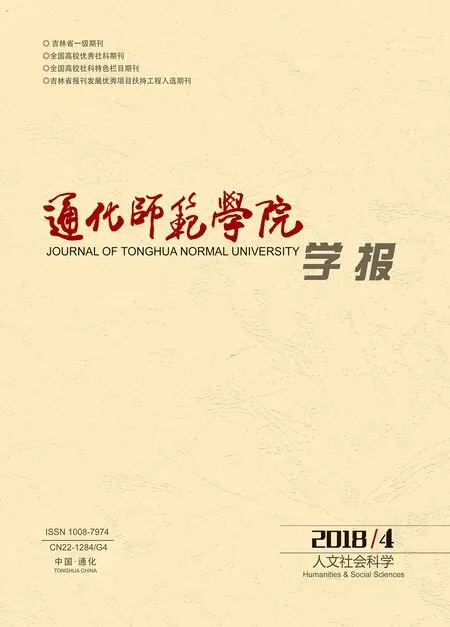先秦汉语情态动词“能”“得”的语义功能对比
余素勤
一、引言
“能”“得”是先秦汉语中常见的表“可能”的情态动词,对它们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大多是对二者语义的分别描写,对“能”“得”语义的联系和对立,少有系统的研究。已有研究中所提及的“能”“得”之间的差别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自身能力”和“客观条件许可”的差别。李佐丰[1]111指出:“‘得’主要表示客观上的可能性……‘能’大多表示主观能力。”姚振武[2]135-137、朱冠明[3]54-55和巫雪如[4]221-222也认为“能”“得”之间有这种差别。就用例来看,“能”“得”确实有这种偏向。但如果把“自身能力”和“客观条件”编码到“能”“得”的语义之中,如何解释“能”的“客观条件许可”(如下例1)和“得”的“自身能力”(如下例2)?又如何解释“得”用例中,只表述VP事件实现与否,不指明导致其实现与否的是主体还是客观条件(如下例3)?
(1)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韩非子·初见秦》)
(2)夫富之于人……至人之所不得逮,贤人之所不能及。(《庄子·盗跖》)
(3)(余)曰:“得为君之妾,甚幸。”(《韩非子·奸劫弑臣》)
第二,“能”“得”后 VP 的差别。许维静[5]指出“大部分‘能’句核心动词的发出都与施事有关,施事是可控的。而‘得’句的核心动词动作很多情况下是施事不可控的。”“可控”与否的表达并不准确,上述三例中VP事件的完全实现,对施事而言都是不可控的。“能”“得”后VP的关键差别在其施动性,“能”后VP大多施动性强,“得”后VP大多施动性弱。不过,这一点与第一点一样,也只是一种趋势。例(1)“能”后VP是非自主事件,施动性弱;例(2)“得”后VP又是施动性强的事件。
由此而言,上述两点差别仅仅是“能”“得”在表现上的差别,而没有把握住导致这两种差别的是二者的语义功能差异。对“能”“得”语义功能的系统对比,有助于更为细致全面地了解二者的语义,也有助于深化对先秦汉语情态系统的认识。本文调查《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战国策》等十部先秦文献,分析“能”“得”在语境上的交叉和对立,从而比较二者在语义功能上的异同。
二、“能”“得”的情态类型
根据 Palmer[6]35-37的分类,一共有三种情态类型。先秦汉语的情态动词“能”“得”可以表达这三种情态类型,且都以动力情态为主。
动力情态(dynamic modality):表示物质世界人或物的能力、意愿、性质、功用等。
(4)a.余不能治余县,又焉用州?(《左传·昭公3年》)
b.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道义情态(deontic modality):表示说话人基于现实社会条件对施事者表达的应允或义务的态度。
(5)a.(达子)使人请金于齐王,齐王怒曰:“若残竖子之类,恶能给若金?”(《吕氏春秋·权勋》)(译为:“你们这些残军败将,怎么能给你们赏金?”)
b.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茆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表达说话人对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必然性的观点。
(6)a.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荀子·王霸》)(译为:“智者的智慧,本来就很多,又用它来管理较少的事,怎么可能不明察呢?”)
b.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荀子·正论》)(译为:“你们和子宋子关系友好,不如去制止他的行为,(他继续如此),恐怕会伤及自己。”)
“能”“得”二者的语义功能差异主要体现在动力情态和道义情态之中,下文将分别论述。
三、“能”“得”动力情态的对比
(一)语境义的对比
动力情态“能”“得”表示VP事件实现的能性。①“能性”也就是动力情态中表示客观世界的可能。为了区别认识情态的可能,本文采用范晓蕾[7]的术语“能性”。已有研究把决定VP事件能性的因素大致分为两类:主体指向和客观条件指向②Вybee et al[8]首先把根情态(root modality)分为两类:“施事指向(agent-oriented)”和“说话人指向(speakeroriented)”,是想要区分根情态(包括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中的说话人指令和其他用法。Auwera et al[9]81将其修正为“参与者内在情态(participant-internal modality)”和“参与者外在情态(participant-external modality)”,把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中由客观条件决定的用法归为“参与者外在情态”,而表示自身能力的这类归为“参与者内在情态”。Palmer[6]83在动力情态中也区分出“主语指向(subject-oriented)”和“中性/条件(neutral/circumstantial use)”,后者仅指VP事件的能性,略等于“动力情态”中由环境决定VP事件能性这一部分。在古汉语的研究中,李明[10]6不把指向主体能力的看作情态动词,而把指向客观条件的归为“条件情态”。朱冠明[3]34参照Palmer的分类,在动力情态中区分出“主语指向”和“中性(条件)”两小类。。
主体指向中,VP事件的实现与否取决于主体,最为典型的是指向主体能力的用例,如上例(4)的“余不能治余县”,就指主体“余”在政治方面的才能。
客观条件指向中,VP事件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外在环境,如例(1)的“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决定“荆、魏独立”无法实现的是“韩亡”这一外在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情态动词的实际用例中,还存在“主体指向”和“客观条件指向”之外的第三类,即上文例(3)这类。“得为君之妾,幸矣”,只表述现在“(余)为君之妾”实现,但究竟是由于自身原因(如“余”长相姣好),或者其他外在原因(如别人引介“余”和“君”认识),语境没有说明。再如现代汉语的例子。下文例(7)也只表述了“(我)参加你的婚礼”没有实现,没有指明其未能实现的原因。
(7)杨冬儿说:“恭喜你,可惜没能参加你的婚礼。”(夏商《裸露的亡灵》)
本文把最后这一类称为单纯能性。①对“能”而言,“主体指向”“客观条件指向”和“单纯能性”与它所联系的成分直接相关。“主体指向”联系的是主语和VP事件能性;“客观条件指向”联系的是上文语境和VP事件能性;“单纯能性”联系的是对话背景和VP事件能性。
下文分别论述这三个小类,先来看“能”“得”用例都较多的“客观条件指向”一类。
(二)客观条件指向
客观条件指向,情态动词往往出现在前后文具有因果关系的语境中,典型的是复句和致使动词宾语从句。
在复句主句中出现的情态动词,VP事件的能性往往受从句所述事件影响,如:
(8)a.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国语·晋语一》)
b.“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也。(《孟子·万章上》)
(9)a.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b.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韩非子·安危》)
(10)a.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左传·襄公10年》)(此句译为:“王叔您手下各级官员都因受贿富裕得不成样子,我能不蓬门荜户吗?”)
b.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无危?(《韩非子·人主》)
例(8)a、b两句的从句事件叙述了“能”句VP事件中主体②此处主体、客体、环境等都指“能”所在句的VP事件的主体、客体和环境。如例(8)b中“能”句VP事件为“娶妻”,其主体是“舜”,从句叙述主体“告”的行为。例(9)a中VP事件为“御之”,从句叙述客体“之”的行为。之前的行为。a句中“兼翼(兼并翼地)”的实现,以主体“无亲(不顾及亲人)”的行为为前提。b句“娶”无法实现,是由于主体“告(父母)”的行为。例(9)的从句事件叙述客体的行为状态。a句“御之”无法实现,受到客体“保民而王”的阻碍。b句“臣夺主(指田氏代齐)”能实现,是因为客体“(齐)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例(10)从句事件叙述外在环境。例(10)a句“吾无筚门闺窦”无法实现是受到外界环境“官之师旅不胜其富”的影响。b句“法术之士无危”无法实现,也是前述外界环境“(主上)有术而不用”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例(8)(9)两句虽然影响VP事件的因素一致,但“能”“得”无法互换。a句中的“能”无法换成“得”,是由于“兼翼”和“御之”都是典型的及物事件,与之结合时,“能”隐含了“主体为VP事件实现提供动力,主动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得”排斥此隐含义,因而无法替换“能”。例(8)a中的“娶妻”也是一个典型及物事件,此句中之所以无法用“能”替换“得”,在于此处“娶妻”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父母的态度”,如果替换为“能”,则有暗示主体能力之嫌。例(9)b的“夺主”也是一个典型及物事件,此句“得”无法替换成“能”,一方面在于替换为“能”,有暗示主体“臣”能力之嫌;另一方面“臣夺主”是消极事件,因而无法替换成“能”。VP事件为消极事件的再如下例(11)(12)。
(11)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子·守道》)
(12)薛公以人臣之势,假人主之术也,而害不得生,况错之人主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进一步而言,之所以“得”之后的VP事件可以是消极事件,而“能”却无法与消极事件搭配,在于说话人的视角不一致。在“能”所在句中,说话人总是站在“能”主语的立场,消极事件对主体有害,主体不会主动致使它实现。在“得”所在句中,说话人可以站在从句主体的立场,“得”句VP事件是从句主体行为的结果。如例(9)b句说话人站在“齐”的立场,全句是在批评“齐”;例(11)中站在“人主”的立场(使“法分明”实现的致使者),全句是在建议“人主”去使“法分明”。
与例(8)、例(9)相对,例(10)的VP事件是典型的非自主事件,施动性弱,它的实现与否往往受到外在环境影响。与之结合时,“能”所暗示的“主体主动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不凸显,且复句语境中,VP事件能性主要由从句事件决定,因而与不暗示“主体主动致使”过程的“得”可以互换。例(11)的VP事件虽然带有施动性,但“能”“得”指向事件的起点,其实现与否与主体的施动性无关,“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不凸显,因而“能”“得”也可以互换。
致使动词宾语从句也有类似的表现,如:
(13)a.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韩非子·守道》)
b.(孔子)乃遣子贡之齐……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墨子·非儒下》)
c.有相与讼者,子产离之而无使得通辞。(《韩非子·内储说上》)
(14)a.楚王方侈,天或者……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左传·昭公4年》)
b.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故(天)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墨子·天志上》)
(15)a.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诗经·郑风·狡童》)
b.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孟子·梁惠王上》)
例(13)a句“设柙(设置笼子)”致使“胆小懦弱之人也可以制服老虎”,决定VP事件能性的是外在环境。b句外在环境“子贡教高国鲍晏”致使“(高国鲍晏)害田常之乱(妨碍田常犯上作乱)”无法实现。此两句的VP事件是典型及物事件,a句用“能”,暗示主体“怯弱”主动致使“服虎”实现的过程,换成“得”则无此暗示。b句“得”指向“害田常之乱”起点的实现,完全由外界环境决定。换成“能”则有暗示“害”无法实现是由于主体能力不足之义,因而无法替换成“能”。c句VP事件(争讼之人使言语相通以串供)也是典型及物事件,此句说话人站在从句施事“子产”的立场,VP事件是消极事件,“使”表示“允让”,无法替换成“能”。
与之相对,例(14)的VP事件是非自主事件且VP事件积极,例(15)“能”“得”指向VP所述活动起点且VP事件积极。这两类VP与“能”结合时,“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不凸显,可以与“得”互换。
(三)主体指向
主体指向又可具体分为三类:“能力”“条件”和“意愿”。
1.主体能力
指向主体能力的,大部分都只能用“能”表示,少数“能”“得”可以互换。如:
(16)邮无正御,曰:“吾两鞁将绝,吾能止之。”(《国语·晋语九》)
(17)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左传·襄公31年》)
此二例分别指向主体的体力、技能和知识,均无法替换为“得”。
再如:
(18)彼之善者我能以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斩其首,何故而不治!(《韩非子·内储说上》)
(19)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庄子·至乐》)
(20)a虽然,仲子恶能廉?(《孟子·滕文公下》)
b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论语·八佾》)
(21)a(涂之人)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荀子·性恶》)
b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羞而不为也。”(《吕氏春秋·士容》)
例(18)中“能”“得”对举,指向主体权力。权力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主体的一种抽象力量,另一方面主体又为社会所限制。着重于前一点,则可以使用“能”;着重于后一点,则可以使用“得”。例(19)指向主体的心理素质,例(20)指向主体的道德素养,例(21)指主体的综合才能。这三例虽然和(16)(17)一样,都属于主体能力,但“能”“得”可以互用。二者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后VP事件的性质。例(16)是典型的及物事件,例(17)也是认知域的及物事件,包括施动过程。例(19)~(21)指主体的状态,无施动过程。由此而言,在VP事件指向主体所达到的状态时,由于VP事件本身不带有施动过程,不凸显“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因而即使VP事件的实现由主体能力决定,“能”“得”也可以互换。在这种语境中,使用“能”的语义隐含“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使用“得”则强调主体目前处在(或不处在)这一状态,“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由常识可得。
2.主体条件
指向主体条件的,基本上“能”“得”可以互换,如:
(22)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吕氏春秋·知化》)
此例指向主体的位置、习俗,属于主体条件,前一句用“能”,后一句用“得”。
3.主体意愿①刘利[11]115-118采用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能愿式”的分类方式,把指向“主体意愿”的“能”单独列为与“能力”平行的“肯愿”一类。李明、巫雪如等把此种用法看作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或者“道德素养”。考察这一类用例,显著特征是VP事件对主体而言是完全可控的,如心理活动,它的实现不受能力、客观条件等影响,只与主体意愿相关。其中,有部分与“主体能力”类似,如“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左传·僖公8年》”,此句“让”的实现虽然取决于主体意愿,但体现了主体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能为常人之所不能,与“能力”相近。再如“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左传·僖公30年》”和“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国语·晋语一》”不要求主体具有较高道德素养,不是常人不能为之事,与“能力”相远。再如“要离曰:‘……王诚能助,臣请必能。’(《吕氏春秋·忠廉》)”,此句译为“王真的能帮助我的话,我一定能杀了他”。此句VP事件“助”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听话人“王”的意愿,可以替换为“愿意”。
此类与主体能力类似,只在少数指向主体状态的例子中,“能”“得”可以替换,如:
(23)昭神能孝。(《国语·周语下》)
(24)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墨子·非儒下》)
带有施动性的VP事件只能使用“能”,如:
(25)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26)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
(四)单纯能性
此类多使用“得”,“能”例较少,如:
(27)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28)韩索兵于魏曰:“愿得借师以伐赵。”(《战国策·魏策一》)
(29)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庄子·列御寇》)
例(27)“得”后VP指向过去已实现事件。例(28)表达说话人意愿,假定将来“借师以伐赵”实现。此二例未指明VP事件实现原因。例(27)替换成“能”则有暗示“VP事件的实现与主体能力相关”之义,“能”没有例(28)这类用法。例(29)的“得珠”也指向过去已实现事件,前文没有指明“得珠”的原因,是单纯能性。由于核心动词为“得”,只能用“能”。
再如:
(30)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31)诚得如此,臣免死罪矣。(《韩非子·内储说上》)
(32)咎犯曰:“事若得成,继文之业,定武之功,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吕氏春秋·不广》)
此三例情态动词都出现在假设从句之中。例(30)假设“见君子”实现,主体担任主语,无法替换为“能”。例(31)“诚得如此”指“现实情况真能如此的话”,此句无主体;例(32)“事若能成”的主语也不是主体。例(31)和(32)语境类似,前句用“得”,后句用“能”。由此而言,在假设从句中,如果主语非主体,则“能”“得”可以互换。如果主
本文支持李明等的做法,把指向“主体意愿”看作附属于“主体能力”的一个特殊小类。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在先秦汉语中,可以表现出主体具有较高道德素养的例子居多,这一类无法用“愿意”翻译。第二,可以翻译为“愿意”的只出现在对话语境之中,必须是对说话人而言的积极事件,因而与“意愿”并不完全相同。消极事件,如“如果你想去打游戏,就去吧”这句话,无法把“愿意”替换为“能”。语是主体,则“能”始终隐含“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无法表示“单纯能性”;“得”排斥此隐含义,表示“单纯能性”。
(五)动力情态“能”“得”的核心语义
上文比较了动力情态“能”“得”在具体语境中的语义差异。总体而言,“能”“得”均有“主体指向”“客观条件指向”和“单纯能性”三种用法。
在“主体指向”这类用法中,如果VP事件带有施动过程,则只能使用“能”,“得”无法出现在这种语境之中,如“臣则尝能斫之”;如果VP事件表示主体的状态,则“能”“得”都可以使用,如“人也孰能得无为哉”。
在“客观条件指向”这类用法中,如果表层结构有“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这一过程时(VP事件是典型及物事件且语境凸显主体的施动性时),如“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只能使用“能”。如果语境中暗含“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VP表示积极的主体状态)”这一过程,“能”“得”都可以使用,如“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如果语境无“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这一过程,则只有“得”可以出现,如“薛公以人臣之势,假人主之术也,而害不得生”。
先秦汉语的“单纯能性”多数由“得”表示①例外是“VP”的核心动词为“得”时。。“能”由于有暗示主体的作用,一般都无法出现,只有在假设从句且主语非主体时,才可以和“得”替换。其分布如下表1。

表1 动力情态“能”“得”的语境分布
由此而言,“能”所在句(主体担任主语),都有以下隐含义:主体为VP事件实现提供动力(或条件),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因而正如《马氏文通》所言,“凡动字为‘能’字所助者,概非受动,以‘能’字明有使然之意……诸引‘能’字,所助者皆外动字也。[12]184”与之相对,“得”排斥这个隐含义,它的核心用法并非如已有研究所言,表示“客观条件许可”,而是表示单纯能性。正是由于表示单纯能性,语境中致使VP事件实现的可以是客观条件,也可以是主体自身,也可以不指明原因,只表述VP事件的实现与否。这也解释了“得”后VP中核心动词的特征,它的语义中排斥“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因而VP大多是不带有施动性的非自主事件。
四、“能”“得”道义情态的对比
道义情态“能”“得”从动力情态发展而来,数量较少。此类“能”“得”的主要区别在于道义源②“道义源”,指对主体行为发出许可、命令等指令的人或抽象事、物,典型的如“法律规定、道德、社会习俗”和“说话人的命令”。。
“能”主要以“道德情理”作为道义源,如前文所提的“若残竖子之类,恶能给若金”就是从情理上来看,“我”不应该“给若金”。再如:
(33)吾兄弟之不协,焉能怨诸侯之不睦?(《左传·僖公22年》)
(34)魏虽强,犹不能责无责,又况于弱?(《吕氏春秋·应言》)
“得”主要以“礼仪法律”作为道义源,如前文所言“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茆门”就是由于“楚国法律”限制,不能乘车到“茆门”。再如:
(35)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庄子·天道》)
(36)下妾不得与郊吊。(《左传·襄公23年》)
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在于二者来源不同。以“道德情理”作为道义源的“能”来自于指向“主体意愿”的“能”,如:
(37)臣不佞,不能苟贰。(《左传·昭公20年》)
此例中,楚子命令说话人“奋扬”捉拿大子“建”,“奋扬”放纵“建”逃跑,楚子追究此事。此处“(奋扬)苟贰”(即“奋扬”从后命而捉建)是听话人(楚子)希望实现的,但此事违背说话人的道德观念,说话人不愿意实施。此句中“苟贰”从“道德情理”的角度看是消极事件,不允许它实现的是“道德”。同时,“苟贰”是听话人希望实现的,因而说话人为了尊重听话人,把它看作积极事件,“能”指向“主体意愿”。“主体意愿”类只有在VP事件为主体状态时,才可以用“得”,而主体状态和道义情态不合①道义情态指向VP事件的实施,预设主体能做到VP事件,但受到道义源的限制。因而道义情态中的VP事件大多带有施动性和自主特征,与主体状态不合。。
而“得”的道义情态多来自指向“主体权力”的“得”。尤其是当“得”出现在否定句或反问句中时,“法律、社会规约”对主体的限制凸显,容易解读为道义情态。如上例(35)的“轮人安得议乎”既可以看作“轮人没有权力、资格议论”(动力情态),也可以看作“礼法不允许轮人议论”(道义情态)。这种指向主体权力的例子,“能”也可以出现,但由于说话人总是站在主体的视角,强调主体自身的能力,因而道义情态用法不成熟。
五、小结
本文分析了先秦汉语情态动词“能”“得”的功能的交叉和对立。表示动力情态时,“能”和“得”都有“主体指向”“客观条件指向”和“单纯能性”三种用法。“能”以“主体指向”为主,总是隐含“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可以出现在复句或致使动词宾语从句之中,很难表示不指明VP事件能性原因的“单纯能性”。“得”以“单纯能性”为主,排斥“主体致使VP事件实现”的过程,无论决定VP事件能性的原因是什么,VP事件都倾向无施动性的非自主事件。另外,在使用“能”时,说话人的视角总是“能”的主体主语;而使用“得”时,说话人的视角可以变为主语之外的其他个人。因而“得”允许与消极的VP事件搭配,而“能”没有这种用法。
道义情态的“能”常常以“道德情理”作为道义源,而“得”以“法律”等社会规约作为道义源。前者主要来自于指向“主体意愿”的动力情态,因而只有“能”有用例,“得”没有用例。后者主要来自于指向“主体权力”的动力情态,“能”指向“主体权力”的例子以主体为视角,难以编码“社会规约”对主体的限制;“得”不限定于主体这一视角,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道义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