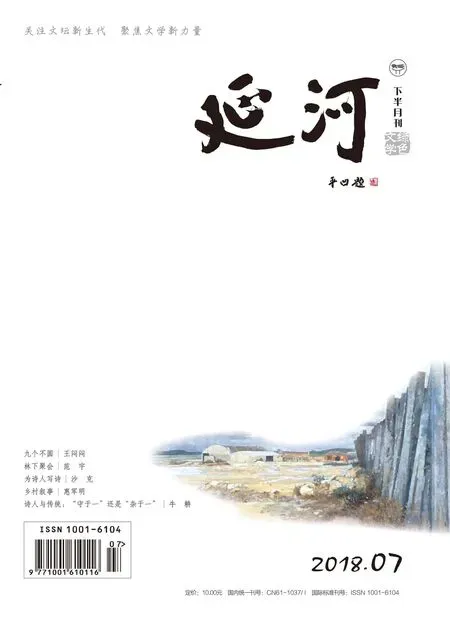搓 麦
张菊兰(彝族)
每每见到泛黄的麦子,总会想起小时候吃过的搓麦,就忍不住流口水。
记忆中,儿时的彝家山村,只要能哄嘴的东西,人们都会找来糊口,可还是撑不饱肚皮。最难熬的是青黄不接春的三四月,柜子底的苞谷或谷子少得能数清颗粒,地里的麦子和蚕豆还铁青着脸。这段时间里,米饭是不敢奢望的,除非生病实在咽不下粗糙的苞谷饭时,才有白米稀饭救救急。平常日子,苞谷饭里还得掺些野菜凑数,否则熬不到小春成熟。棠梨花、白刺花、黄花、婆婆丁、蕨菜、荠菜、水芹菜、马齿草、柳叶、榆钱等等,猪牛羊能吃的植物都找了来,洗干净拌在苞谷面里蒸熟,当饭充饥。
能下肚的花草树叶不少,但也有限,需要的人一多,就越来越难找。到最后,一木甄子饭里得掺好几种野菜,才能满足一家人饭量需求,那味道别提多难吃了!于是,人们等待庄稼成熟的心情越来越迫切,看麦子的目光越来越炽热,恨不能把绿莹莹的麦苗烧成金黄,把麦穗一束束塞进嘴里。
几场透雨过后,麦子终于在人们热辣辣的期盼中,开始泛黄,由三四成熟渐渐到半生半熟,再到六七成熟,后到八九成熟。麦子每黄一分,人们的心情也随之高涨一点,到八九熟,喜悦也到了极点!大家催促生产队长,选择几块长势较好、黄中隐青的麦子,弯月似的镰刀嚓嚓嚓一阵后,先让割倒的麦子在地里睡成一排,然后捆绑成花束般美丽的麦把,按把数分到一家一户。
麦把抱回来,全家兴高采烈地一齐动手,把一穗穗麦穗拿在手里细心搓,耐心揉,使还未熟透的绿色麦粒从麦壳里剥离开,一粒粒落到簸箕里。等所有的麦粒都进了簸箕,再轻轻簸干净后,拿木甄子蒸熟,凉到仅剩点余温,用石磨一磨,就成了爽口的搓麦。
说实话,我至今不知道这东西的汉语名称(好像叫麦圈,但又拿不准),只晓得彝话叫“硕微”(硕:彝语麦子;微:彝语搓,揉。硕微:彝语麦搓)。我根据彝语直译后,按彝汉语习惯调整语序,就叫它“搓麦”了。俗话说,世上有三苦——读书、赶马、磨豆腐。我觉得,磨豆腐苦,磨其他粮食也不轻松。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到的。
石磨由四个部分组成:木架子、木磨盘和上下两扇笨重的石磨扇。两扇磨扇都有扇形磨齿,上磨扇横面朝上那方的中央,有一个直径两寸左右的圆形磨眼,磨扇竖面还有两个相互对称的木楔。推磨时,把粮食堆在磨眼上,扁担套进八字磨绳,再套到木楔上,用胸脯推着扁担向前转圈,两扇磨盘就像人的上下牙在咀嚼蚕豆,嘎吱嘎吱一阵,粮食颗粒就成了粉末,被两扇磨扇吐到木磨盘上。
山里农家的孩子,换下开裆裤就得学干活,我也不例外。放牛、放猪、捡细柴、摞叶子、找猪草等,都是小孩儿要做的活计,有时还跟着大人出集体工,挣三分工分(全劳力挣十分工分)。如果是女孩,还得在阿妈督促、指导下辑麻、推磨、做针线。
在半大孩儿的劳动中,我最害怕推磨。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刚比磨盘高一点点儿,每晚就要跟着阿妈推磨,准备一家人第二天的食物。开始时,个头矮小,技术又不行,只能把扁担套在阿妈的扁担上,尾随她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灰暗土房里机械地旋转,转得胸闷气短、晕头转向,只想恶吐,仿佛在炼狱里煎熬一般。半年后,我就从阿妈那里“分离”出来,独自撑起一根扁担,不适现象也逐渐减轻,甚至完全消失了,但还是讨厌推磨。你想,每晚在磨房里转两三个小时,一步一步,一圈一圈,有始无终,没完没了。苦累且不说,受不了那份枯燥乏味。
可磨搓麦却不一样了。被野菜苞谷饭糙得火烧火辣的肚皮,马上能享受到美味,想想都开心,都会流口水,高兴还来不及,怎可能有厌恶之情呢?知道要磨搓麦,周身洋溢着兴奋因子,不用阿妈催促,便哼着欢快的彝族歌谣,一蹦三跳地跟着她去磨房了。
微黄的煤油灯忽闪忽闪,简陋的磨房散发出青麦子煮熟后的香味,冒着丝丝热气的绿色麦子,在磨盘上堆成一座小绿山,“山”中央插着光滑的木筷子(磨眼插筷子,目的是减少粮食下去的数量,使之磨得更细腻),磨盘随着我和阿妈沉稳的脚步,一圈圈转动。
当绿色“小山”从中间凹下去一点点,一股股麻线粗的搓麦发出诱人的清香,从磨齿间窜下来。不一会儿,下磨扇上悬挂着一道间距相等的圆形翡翠珠帘。等到虫子般蠕动而下的搓麦长到一定程度,就温顺地躺倒在木磨盘上,耐心地等着主人来收拾。
嘴馋心也馋,脚步随着磨盘转动,眼光却紧紧盯着挂在磨扇上的搓麦,吧唧吧唧直咽口水。阿妈见状,会摇头轻叹一声,微笑着轻柔地吐出我期待已久的两个字:吃吧!
得到阿妈准许,我的心一阵狂喜地跳跃,脸上绽放出山茶花般灿烂笑容,边跟着石磨转圈,边大大方方地从磨扇上拽下几条带暖气的搓麦,塞进嘴里夸张地嚼着,浓而不腻的香味裹着淡淡的甜味在唇齿间萦绕,像吃了人参果一般,每个毛孔都舒坦,每个细胞都欢愉,周身陡然充斥着无穷的力量。刚消化完野菜苞谷饭的肚子,也高兴地唱起歌,欣喜若狂地迎接着这美味的到来。
一条条搓麦进嘴,脚步也变得分外轻松,把磨盘推得飞快。在阿妈的赞赏声中,在灯光嗤嗤的笑声里,把肚子撑得像刚打完气的皮球一样圆,走一步一个饱嗝。阿妈又摇头轻叹,但从没有劝过我少吃一点,她不忍心打扰馋成这份狗样的女儿过嘴瘾。她清楚,半大孩子消化力强,加之还得使力推磨,不用担心肚子胀坏。
不管经历多长时间,整个磨搓麦的过程是愉快的,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是啊,打了牙祭,饱了肚皮,还有比这更令人舒心的呢?等磨盘上的麦子全都磨完,阿妈便从木磨盘上把一弯圈一弯圈的搓麦摞下来,摆在簸箕里晾开,等第二天用木甄子一蒸,就是全家的早晚饭。

为了让我们姊妹更开心,阿妈还会用蒸熟的搓麦捏几个饭团,放在搓麦饭上,等吃饭时,给我们姊妹三人每人分一个。全家围坐桌旁,有说有笑地吃着香甜的搓麦饭,弟弟妹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大口大口往嘴里塞饭团,大声嚷嚷“好吃”,那场面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头晚就解够馋的嘴皮和肚皮,不再那么迫切地渴求食物,可以特意在阿爹面前,表现出女孩子的文雅了。望着弟妹们狼吞虎咽的馋相,我微笑着,把像绿球样漂亮的饭团捧在手心里,转着圈,慢慢欣赏。看够看饱后,才小口小口斯斯文文地品着,骗得阿爹频频颔首微笑。
搓麦味美爽口,让人们被野菜撑大的肚皮,得到无比的舒适和满足,心情也不由随之畅快。可人们的快乐,不仅因为吃到搓麦,而是吃过两天搓麦饭后,小春就该成熟,就能暂时告别半饥半饱的日子了。
搓麦的馨香萦绕着小山村,化成一朵朵笑靥,挂在那群修理沟渠(每年队里都会在吃搓麦那两天修沟,等待割完麦子后耙田栽秧的)农人褐色的脸庞上。男人爽朗的笑声、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重叠成双声部,在山山坳坳间翻滚,连飞过头顶的鸟儿和路过的风儿,也莫名其妙地回首张望,再繁重的劳动也感觉不到劳累。
打着搓麦饱嗝,谈论小麦即将丰收,那话题是轻松的、愉快的。人人都在说,人人都在笑,那是大集体劳动时中最热烈最欢乐的场面。这样的场面千篇一律,每年一回。可有一次却有些特别,我至今历历在目。
许许多多张合不停地嘴巴里,有几张紧闭的嘴;在大家开心的笑脸中,有几张尴尬且带着苦楚的脸。在或好奇或关心的人们一再追问下,大家才晓得,桥头阿玖老表家的搓麦出问题了。没粮食可磨而闲置多日的石磨眼里,躲着一只觅食的耗子,阿玖妈没发现,就把热乎乎的青麦子堆在磨眼上,开始推磨。石磨嗡嗡转动一阵后,耗子肉掺杂在麦圈里,搓成一根根细绳出来,恶心得要死!
这事一传开,年轻人不知深浅,嘻嘻哈哈嘲笑个不停,甚至指着阿玖哥弟俩,给他们取绰号叫“搓耗子”,把他们弄得面红耳赤,哭笑不得。上点年纪的人,看着阿玖妈满脸窘态,十分同情,却又无可奈何,只能责骂拿这事打趣逗乐的年轻人。
眼巴巴盼着麦子变黄,可分得的几把麦把只换来一场笑话。村里人家有滋有味地享受着搓麦美味时,他们一家六口只能流着汩汩心泪,继续吞着难以下咽的野草。嗅着飘荡整个村庄的搓麦香味,看大家眉眼飞扬的神情,还得听人嘲笑,想想都心酸!
麦子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期盼缺了又圆,圆了又缺。日子如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当风抖动一阵后,落了一茬又一茬。几年之后,麦子该青还青,该黄还黄,可人们等待麦子成熟的心情,不再那么急迫。
如今,石磨淡出人们的生活,磨面的经历只成了老年人口中的故事。搓麦和山村许多东西一样,被掩埋在时间的土层里,再也寻它不着。只有我,每次见到泛黄的麦子,还是忍不住去刨出小时候的那段记忆,回味搓麦的味道,让口水溢出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