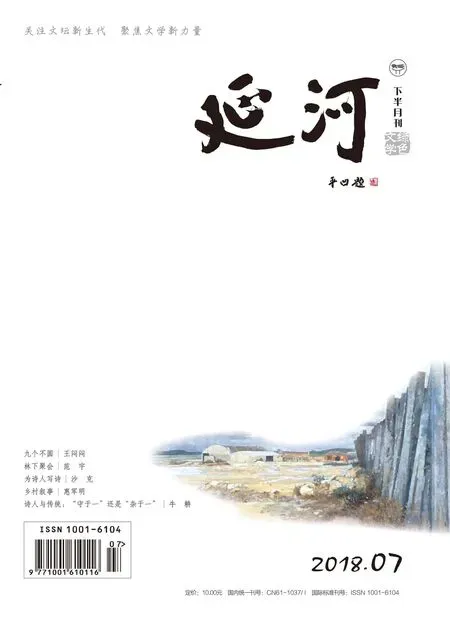父亲德云的最后时光
杨文清
一
连日阴雨直把人的骨头淋酥,太阳刚刚从云缝中探出头,父亲德云就兴奋得啧啧直叫,一双树皮似的手将黄牛的头拍得啪啪响:憋坏了吧,老伙计?黄牛看着父亲德云,眼里充满兴奋……父亲德云在前,黄牛在后,步履从容地出了村。
母亲秀梅扯了把麦秸生火,火苗忽地蹿起,红彤彤的火焰舔着锅底。母亲秀梅手起铲落,将一铲煤炭盖在火焰上,火焰熄灭的一瞬,母亲秀梅拉起了风葫芦的开关,继而燃烧成熊熊火焰。母亲秀梅的面庞被火焰映照得红扑扑的。
儿媳仙婷仓促抹了把脸,来到炕头,揭开了被子,取掉盖在面盆上的瓷盘。昨晚起的面已经发了,布满黑芝麻般的眼儿。儿媳仙婷将手伸进面盆,挖了一把面放到鼻子下闻,之后,端起面盆来到灶屋,干净利落地收拾案板,撒了干面粉,将发好的面倒在案板上,用力揉起来。
儿子明宝头发乱蓬蓬的,拿起扫帚唰啦唰啦扫院子。虽然是巴掌大的一块水泥路地面,扫过的地方却清整了许多。再远些是黄沙土,太潮湿,落不得扫帚。明宝便摸出一根纸烟点着了狠命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烟柱一直伸得极远。
炊烟伴着水汽在升腾,太阳的光芒透过来,成了紫红色的。毕竟有了阳光,庭院里亮堂堂的,暖洋洋的,柿树叶、刀豆叶、青菜一律翠生生的惹人眼。
“明宝,快点儿,你爸昏倒了!”喊声未落,几个人拉着架子车进了大门。父亲德云躺在车厢里。
明宝赶忙扑过去,见父亲面色如纸,闭着眼不说话。“爸呀,你这是咋了?”明宝急言失色。母亲秀梅、妻子仙婷听到明宝的喊声相继跑出来,面对眼前情景,先就慌了神。
大家七手八脚将父亲德云抬上炕头。母亲坐在炕头上,搂着父亲的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明宝、仙婷不知所措,爸呀,爸呀叫个不停。还不快叫大夫?有人对着明宝喊。明宝大悟,急忙转身奔向门口。父亲睁开眼,“不用叫大夫,我歇息一会儿就好了。”
父亲睁眼说了话,大伙提着的心放了下来,说了会儿闲话,相跟着散去。
二
村医来家的时候,父亲德云已经像个好人了,未等村医诊询,他便高喉咙大嗓门儿絮叨开了:“早上,雨停了,我牵着牛出去遛遛,忽然胸口难受得不行,咚咚地跳,心脏像要跳出来,后来就不省人事了。”村医给父亲德云诊了脉,开了几副中药,告诉明宝,你父亲可能患了冠心病,这号病耽误不起,最好送到医院确诊。明宝还未答话,父亲德云说:“病得在我身上,我清楚,不用费神去医院,这是老毛病了,不碍事。”
明宝和母亲还是不放心,决定拉父亲上医院治病。父亲说啥也不肯。逼急了,父亲吼道:“我老了,还能活几天,花那闲钱干啥!有那钱把咱这房拾掇拾掇。”一句话说得明宝母子心里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
是呀,房子早该翻盖了,这房子还是二十年前父亲德云翻盖的土坯房,低矮不说,房顶有些地方已经塌陷漏雨。前几年东邻的两间旧房拆除后,自家的山墙没有了依靠,与沿墙产生的裂缝有两指宽。每逢秋天的连阴雨,父亲德云、母亲秀梅的心总是攥在一起。前一向雨下个没完没了,屋内也叮咚地漏雨,父亲上房苫雨布,差一点儿失足滚下来。镇、村干部三番五次劝德云一家人暂时搬迁到安全地点去住,终因没有找到合适去处,才没有搬成。如今,雨停了,一家人悬着的心方才落了地,哪曾想,父亲德云却病倒了。
母亲秀梅说:“房是一定要翻盖的,你爸的病也耽搁不得。可怜你爸受了一辈子苦,临了连医院的门都没有进,到死也不能瞑目。”
明宝用眼睛看妻子仙婷,向她讨要主意。
仙婷明白明宝的心思,心里打着鼓,嘴上却说:“房子的事以后再说,先给爸看病要紧。”
明宝、母亲秀梅送父亲德云到医院看病,留下仙婷在家看门,给儿子维杰做饭。
在医院门诊部,大夫给父亲德云做了简单的检查,便开单要求到心脑内科住院治疗。
住院部收费处窗口内是个粉团脸,她张口要明宝预交2000元住院费。明宝只带了2000元钱,一再哀求,粉团脸答应先交1500元钱住院,以后如果不够用再补交。
刚住下,医生护士围了一大堆,测心电图、量血压、量体温,血、尿、大便化验单样样俱全。明宝上气不接下气楼上楼下地跑。等到一切就绪,回到病房,父亲的手腕上插了吊瓶,胸膛戴着动态心电仪,说是要二十四个小时监控。
安顿完父亲,已是晌午。母亲下楼买饭。不一会儿,母亲端着一碗鸡蛋炒米饭进到病房递给明宝,催促明宝赶快吃。明宝问:“你的饭呢?”母亲秀梅说:“我不饿,回家去吃饭。”明宝明白,母亲是舍不得花钱为自己买饭,便硬将米饭推给母亲,他自己下楼买了份凉皮稀饭狼吞虎咽地吃完方才上楼。
下午没事,母亲放心不下家里的鸡猪,决定回去。父亲叮咛母亲晚上别忘了给牛加料,母亲嗯了一声算是做了答应。前脚已经走出门了,母亲回头打手势叫明宝出来。明宝跟着母亲到楼梯口,在肯定父亲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声音后,母亲嘱咐明宝晚上睡苏醒些。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护办室一女士送来第一天的花费清单。明宝拿起一看是640元,心里暗暗吃了一惊。父亲德云问花了多少钱,明宝故作轻松说花了150元。父亲德云面有疑色,但没有说话。
第三天一上班,科主任带着一群医生、护士查房,主治医生介绍了13床病人(父亲德云)的情况。主任接过病历随意翻了翻,便询问病人感觉怎样。父亲德云连忙说:“我没事了,那阵儿心慌起来,胸口嘡嘡嘡跳个不停,过去了,就啥事都没有了。我住这儿闷得慌,今儿说啥你也得让我出院。”主任被父亲德云逗乐了,劝父亲德云来了就要安心治病,甭急着回去。
主任、大夫、护士走出病房。父亲德云对母亲秀梅说:“医院这是把咱的钱花不完不让咱出院,不行!今天咱必须出院。”母亲秀梅说:“还是听大夫的话再住几天。”父亲德云用手猛捶床沿,闷声道:“真把人往死里气呢!”母亲秀梅只好不吱声。
父亲德云还是找了主治大夫,要求出院。大夫被缠烦了,面带愠色说:“你的病刚刚稳定下来,还得再治疗几天。你硬要出院,今天也没有办法……主任已经开会走了,要出院得有他的签字才成。何况今天的用药已开到药房了。”父亲德云只得悻悻地离去。
下午,明宝被大夫叫到主任办公室。主任对明宝说:“想必你父亲的病你已经了解了不少,按理应再治疗一段时间,可病人总吵着要出院,你的主意是啥?”明宝幽忧地说:“我当然听大夫的,还是再治疗几天吧。”主任说:“那你回病房做做你父亲的思想工作。”
明宝背着父亲向母亲谈了大夫及主任的想法,问母亲怎么办。母亲眼眶一红,半天不言语。明宝心里也有些酸楚……要不,再做做我爸的思想工作,我再回家准备治疗的钱。母亲木然地看着明宝:“算了,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明天出院。”
父亲德云要出院了。主治大夫给明宝一家人交代说:“回家后要注意吃药,千万不能劳累,生闲气。”父亲德云鸡啄米似地连连点头。母亲秀梅和明宝心里仿佛一块石头压着,轻松不起来。一家人相跟着无话步出医院,已经到了街头,父亲还回头向医院看了一眼。

三
已放晴几天,低洼地仍是明镜一片。今年的秋玉米减产已成定数,收获期也要提前。明宝和妻子仙婷商量购买种子、化肥的事。仙婷说:“九月初,维杰上高中交了一万五千元择校费,一千元学费,住宿吃饭每月还需一百元。父亲住院花了两千多元。眼下秋收秋播到了,哪样都得用钱。”明宝说:“维杰差2分就能读县里的重点中学,那里师资力量好,前程有保证,不让娃在那里读书,进了普通高中,将来上不了好一点的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那可就惨了,娃的前程耽搁不起啊,那一万五千元钱还是要花的。”仙婷说:“谁说不是呢?现在的学校不知咋了,光知道向学生收钱,好像学生家长都开了银行。”明宝没有接茬,等了一会儿说:“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这次又得了心脏病,我看很严重,你要有思想准备。”仙婷说:“这个我知道,就是心里堵得慌。”明宝说:“看来房是一时半会盖不成了,先叫人将山墙修补修补,凑合着住几年,等维杰大学毕业咧再说。”仙婷说:“嫁给你我算倒了八辈子霉,这一辈子恐怕住不上新房了。”明宝又说:“眼看秋收到了,家里还有没有钱买种子化肥和付机耕费?”仙婷说:“还有一点钱,就是不多了。”明宝说:“家里的积蓄真是经不起折腾。”仙婷说“差点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咱爸住院期间,村上给各家各户发了通知,说是村内街道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很不符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决定在秋收后用水泥硬化村内道路。具体办法是村上成立老年人组成的村民代表小组,由他们牵头组织,村双委会具体实施。修路费用按住房间数摊派,每间房可能收500块钱,咱是三间房得交1500块钱。”明宝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说:“没钱就甭修路,犯不着用群众的钱给干部脸上贴金。”仙婷说:“话虽是这么说,钱可是硬成东西。”明宝说:“我知道。”
第二天,明宝早早起了床,将本村在外搞建筑的来旺堵在家门口。来旺招呼道:“明宝,你来了正好,这几天工地上正缺人手,走,跟我一块上工地。”明宝说:“甭忙,我给你干了八个月活,没见一分工钱,你让我的婆娘娃喝风屙屁呀!况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得病住院,我急等钱花呢。”来旺正色道:“明宝,你跟我干了几年活了,哪一回欠过你的工钱?等年底工程交付使用,钱一个子儿少不了你的。”明宝无言,只得跟着来旺去工地干活。
仙婷在明宝走后,立即爬起来将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一遍。之后给三轮车充气,又将火炉、小铁锅、面盆、小方凳搭进车厢,边往门外推车边给正在烧饭的婆婆秀梅打招呼:“妈,我走了。”婆婆秀梅嗳嗳地答应着。仙婷已经走出了院门,婆婆秀梅追了出来喊:“出门做生意全凭和气生财,油饼少卖几个钱无所谓,咱人可不能吃亏。中午你抽空儿到学校看看维杰,天冷咧,千万甭叫娃冻着饿着。”仙婷回答:“我知道了。”
四
吃过早饭,父亲德云扛着铁锨往外走。母亲秀梅见了,问:“你干啥去?”父亲德云回答:“河湾地苞谷总让水泡着不是个事,我去把水放了。”母亲秀梅说:“还是等明宝回来再放水,你的身子骨会吃不消的。”父亲德云像受了伤害似的:“我是泥捏的不成,干不得一点儿活了!”母亲秀梅没话说了。父亲德云气鼓鼓地扛锨出了门。
父亲德云走后,母亲秀梅从炕上拉下被子哧哧地扯着拆了,套子叠得见棱见线放回炕头。顺手将被面被里扔进大铁盆,撒上洗衣粉,倒水搓洗。人虽在洗被子,母亲秀梅的心里却不在洗刷上,思绪总是集中不起来,脑海里总惦记着父亲德云。洗衣粉用了多半袋,一件被面还没有洗完,有心撂下不管,又放不下家。正在为难之际,院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抬头一看,是女婿桦林进来了。母亲秀梅急忙将手在衣襟上擦了擦,站起身来,上前招呼道:“桦林来咧,我娃快进屋,叫妈给你做饭。”桦林忙阻止:“妈,不做咧,我吃过饭了,我爸呢?”母亲秀梅答道:“到河湾地给苞谷地放水去了。”桦林吃了一惊:“不是说我爸病了,咋还能干那活?”母亲秀梅叹了口气说:“你爸那犟脾气,谁能拦得住?”桦林埋怨道:“妈,你真把我当外人了,我爸病了咋不告诉我一声。”母亲秀梅说:“才说要告诉你呢,又见你爸不要紧了。再说你也上有老下有小的,够忙乱的,也就没告诉你。”桦林说:“我爸病了,我再忙也得来,钱财上帮不上忙,在医院服侍几天总是可以的。”母亲秀梅说:“难得你有这片孝心。”桦林从自行车栏里取出装有水晶饼、水果等礼物的塑料袋交给岳母秀梅,说:“我去看看我爸。”岳母秀梅说:“你先坐下喝口水再去不迟。”桦林说:“不咧,我这就去。”
河湾地在村子东边。那是一片临河的低洼地。河不宽,名字却响亮:天河。这天河自秦岭山脉逶迤北下,似彩绸迎风飘舞,注入黄河的重要支流渭河。过去,天河水总是丰盈的,潺潺地流着。现在情况不同了:枯水期,河床裸露。即使有水,也仅是细细的一条线,宛如久饿的老妇;丰水期,则河水决堤四溢,周围数百亩农田顿成泽国。又适逢秋庄稼即将成熟,造成眼看到手的希望变成泡影。有时积水达数月不退,无法播种冬小麦,来年的收成也无法保障。桦林对这片河湾地太熟悉了,过去妻子明珠活着时,经常帮助岳父家收庄稼,只是近年来来得少一些罢了。
田里的积水有半人深,耳畔不断传来青蛙和蛐蛐的叫声。桦林脱了鞋提在手里,顺着田埂东拐西绕地来到岳父家地头。
岳父德云正忙着挖渠排水,没有留意桦林的到来,直到桦林走到近前,喊了声“爸”方才抬起头,说“来咧?”桦林说:“爸,让我来挖,你到路边歇歇。”岳父德云没有说话,把铁锨递给了桦林。岳父德云头上冒着汗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直起腰,稍稍站了会儿,转身走向田头。
来到路边,父亲德云伸手抓下头上的草帽放在地上当作座垫坐下来,从腰间掏出烟锅,装满旱烟丝,刚点燃吸了一口就一连的咳嗽,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只得放下烟锅,目光茫然地向远方望去……天空湛蓝湛蓝,没有一丝浮云,深邃辽阔,透着安逸,透着静穆。这样洁净的天空已经多日不见了。父亲德云忽然想起儿时的往事来。那时候这里是一汪好干净的水呀,村子周围全都是清亮亮的。清澈的水静静地流淌,女人们蹲在石头上,伸出藕节般的手臂洗衣服。河边水草绿茸茸的,开着各色小花,蝴蝶、蜻蜓、蜜蜂飞来飞去。水里的鱼自由自在地游动,伸手就能捉到。下河捉鱼是小伙伴们久玩不衰的游戏。你在下游下了竹笼,他在上游用脚走着驱赶。竹笼提起来,鱼虾活蹦乱跳。伙伴春喜还是空手摸鱼的神手。他捉鱼不用任何工具,双手张开成喇叭状顺河边摸,一会儿就摸到吐气泡的螃蟹,还有鲫鱼、绵鱼哇(鲢鱼)、刺王拔(一种比鲇鱼个儿小,背上有刺的鱼)……德云不信自己就空手捉不到鱼,挽了衣袖下河去就往水里摸,手指却被夹拔(螃蟹)的一对钳子夹住了,疼得嗷嗷叫,手臂乱甩。捉来的鱼虾小伙伴们有的是吃法:从你家偷来菜油,从他家偷来盐巴,从我家偷来柴禾,三块石头支起小锅便开始做美味佳肴——大点儿的鱼当然是放在锅里清炖,仅需少许菜油和盐巴煮炖的鱼香得人直流口水。小鱼小虾呢?先甭急,给佐有菜油的热水里,边倒边搅拌半碗麦面糊,徐徐倒,快快搅,吃起来口舌生津。到天河里踏鳖也很有乐趣——光着脚丫,在淤泥里一脚连一脚踩踏,感觉脚板下有硬硬一块,弯腰伸手一抓一抡就有一只鳖被甩上岸。照例是清炖,鳖肉没有鱼肉香,但也吃得高兴。最有趣的事是捉黄鳝了:夏夜,提着布袋,拿着电筒到稻田去,电筒的强光射到黄鳝,它就不动了,等你去捉。这时候须敛声静气,伸出食指和无名指小心夹进袋子里,黄鳝就再也跑不了了……想到这里,父亲德云独自乐了起来。如今,过去的伙伴已有一大半埋进了土里,剩下的也都成枯藤老树,经不起风雨了。水也好像被龙王吸走了,田里没了水,种不了水稻和莲菜,改种小麦和苞谷。河里经常干涸,遇有水就泛滥成灾。井水不再甘甜,成了苦的,烧开后锅底沉淀白色渣子,真不知道这日子往后怎么个过法。
不知不觉间,桦林已排完水走了过来。婿丈两人洗了脚,抚平衣服,扛着锨往回走。岳父德云询问:“两个娃学习咋样?”桦林回答:“都还认真,知道学习。”岳父德云说:“这就好。”接着岳父德云话锋一转:“桦林,听爸一句话,明珠已经过去三年了,你一个男人家拉扯俩娃不容易,活着的人要紧,要遇到合茬的,续一个吧。”桦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还是过几年再说,一方面我的思想还转不过弯,另一方面我怕娃娃受可怜。”岳父德云说:“话是这样说,只是到那时恐怕你的岁数混大了,人不好找。”桦林说:“走着看吧。”岳父德云说:“也只有这样了。”
时已晌午,阳光无遮拦地照着两个苦难的人,他们拉着家常步入绿树环绕、炊烟飘升的村庄。
五
午饭吃的是农村人常吃的浆水(酸菜)软面。浆水是用荠荠菜窝的,连同生姜末子用菜油炝了,佐以捣得很烂的蒜泥,油泼辣子。面条自然是又宽又筋道的“裤带面”,吃起来有嚼头,香味绵长。桦林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浆水面了,因此一连吃了三大碗,直吃得满头的汗水,满嘴的辣子油。岳父岳母高兴得嘿嘿直乐。
饭吃饱了,桦林记挂着家里的活路,决计要回去。临走时,桦林从上衣口袋掏出两张一百元钱硬要给老人们留下。两位老人说啥也不肯收,推来让去,最终桦林留下一百元钱,另外一百元钱装回自己口袋。
桦林走了。父亲德云母亲秀梅围绕着桦林的处境拉开了话题:“桦林这娃多好啊!可惜咱的女儿明珠没有福气早早地走了。”父亲德云一开口,母亲秀梅就抹开了眼泪,泪水像房檐水停不下来:“咱这是前世遭了啥孽,命咋这么苦?”
父亲德云年轻时算是村里的能行人(聪明人)。他信守“家有万贯,不如薄艺在身”的道理,早早学会了木工手艺,桌椅木箱甚至盖房造屋,样样都能来。当初就是青年德云在秀梅家所在村里给人盖房时,被秀梅的父亲相中的:嗯,小伙子人勤快,心眼活,有眼色,又有手艺,是块好料子。秀梅父亲这才托人将女儿嫁给了德云。岂料秀梅自嫁给德云起就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德云的爸过世得早,德云在继父眼里就成了多余的人,左看右看不顺眼,稍有不顺非打即骂。母亲劝阻,继父非但不听,连母亲一起打。阻止不了儿子被打,母亲总是为了德云整日以泪洗面。德云成家结婚,继父非但没有分给他一星半点儿家产,反而分给他一百元钱的外债。无处安身的德云秀梅夫妇在村里老年人的帮助下住进了破庙里。那时候,仗着年轻,德云捏紧拳头,过日子的心劲十足:“我就不信日子过不到人前头去!”他起鸡起(鸡叫时分)熬半夜,白天给人家盖房造屋做木活,晚上回家熬夜做板凳、椅子、木箱拿到集市上卖。转眼间,小两口的日子滋润起来——在村人大部分住茅草屋的情况下,德云秀梅盖起了一间半瓦房,告别了破庙。这件事让乡邻羡慕。秀梅的父亲也洋洋自得地向人夸耀自己有眼光,没有看错人。
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打击接踵而至。
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加强对私营商业和个体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德云的私活做不成了,他极不情愿地加入了合作社。再下来是成立人民公社,斗私批修。德云在外做木活记工分。自己虽然混个油嘴,家里的用度愈来愈艰难。秀梅和德云吵嘴拌舌的事也频繁起来。永远忘不了的是1959年冬,严重的饥荒造成公共大食堂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供大家吃饭。生产队大铁锅里烧着开水,不蒸馍,不烧稀粥,只是不断续入野菜,象征性撒一些苞谷面粉。开饭时各家各户只能领到这样的吃食,由于大炼钢铁,各户的铁锅已被收去炼了铁,无法生火做饭。为了节约粮食,上边推广邻村一农民用苞谷芯子做稀饭的经验。就是在第二年春上,德云和秀梅的大女儿爱云被活活饿死的。女儿死时浮肿的腿脚,奇大的眼睛,如今回想起来仍让德云夫妇浑身颤栗。
刚刚摆脱饥饿的困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心为公的老支书被拉下马,反剪双手五花大绑着吊在房梁上抽打。德云家就在大队办公室隔壁。有一段时间,每天半夜都能传来皮鞭抽打声和老支书的疼痛嚎喊声,令德云全家心惊肉跳。大儿子根宝那时12岁,好奇心驱使他半夜偷爬起来窥视隔壁发生的事——只见四个手里握有用三角带钉做的皮鞭的人抽打老支书。每每“叭”的一声,老支书的身体便抽动一下,他已无力嚎喊。12岁的孩子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幕。平时和蔼可亲的老爷爷究竟干了啥事,让这几个人这样狠心抽打。孩子的神经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从此,时常发高烧说梦话,嘴里反复念叨着:“老实交代,打打打……。”几天后,人们在涝池中打捞上来根宝的尸体。
谁也不会想到儿子兆宝会做出那种蠢事。村里办了化工厂,承包给私人经营。由于效益时好时坏,厂子也就时关时开。停产一些时日,重新开产,必须将沉淀池中的气体排放掉才能进人。可就有大庆那个脑子缺少一根筋的傻货,未等气体挥发就下了池子,下去了便没能再上来。兆宝当时路经化工厂,听到喊声,奋不顾身地跑过去。跳进了沉淀池,下去了也没有活着上来,留下孤儿寡妻可怎么办呀?
明珠和桦林买了台农用拖拉机,闲时拉货农忙时收种庄稼,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那次在外村做活,回家时天晚了。桦林竟夜不观色的将拖拉机开翻车了。明珠被压在车厢下,呼喊救命,桦林一个人抬不动车厢,向过路人磕头下跪也没有人伸出援助的手,可怜明珠活活被压死了。
五个孩子,如今只剩下明宝。父亲德云母亲秀梅的泪水早已流干了,心早已空了。夜里睡不着觉,思量起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孩子相继离去,心似刀绞。上苍啊,为什么把我们两个无用的老东西留在世上,而让我们的孩子提前上了路,他们都还是花骨朵呀,正需要活人哪!上苍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六
往年大都是国庆节前后扳苞谷。今年却提前了,早在9月12日左右就有人陆续往回扳。父亲德云心里很着急:虽然说按节气种冬小麦要到10月中旬,迟扳几日无伤大碍,但父亲德云想早扳总比迟扳强,早早把地拾掇干净,施了底肥,也好种麦。因此,父亲德云托人打电话把明宝从工地上叫回来收秋,又嚷嚷着要母亲秀梅将用过的旧化肥袋清理一遍,该洗的洗,该补的补。16日傍晚明宝终于回来了,还带回800元钱工资。父亲德云自然十分高兴,立即喊仙婷明天不要出去卖油饼油条了,一块儿扳苞谷,他自己溜下炕出门找明天拉苞谷的拖拉机。
第二天早早吃了早饭,一家人刚要出门,维杰回来了。奶奶秀梅留下来给孙子准备饭菜,其他人赶到地里扳苞谷。德云家5口人,有6亩责任田。村东河湾地3亩,村西岗坡3亩地。河湾地受水浸泡,苞谷杆已经枯死,苞谷棒小不说,还大都发了霉,得尽快扳回家。父亲德云、儿子明宝、儿妻仙婷每人胸前挂一条小布袋用来装苞谷棒,布袋满了再倒进旧化肥袋,扎紧口子,等拖拉机来拉。几个人扳了十几米了,秀梅、维杰婆孙两人也来了,相挨着摊摆扳苞谷。大人只是干活,维杰的嘴闲不下,发着牢骚:“这苞谷还有啥扳头,要棒子没棒子,要颗粒没颗粒,苞谷梢梢霉烂了,抓在手里象抓了一把屎。”明宝面露不悦:“闲话少说,好好干活!”维杰只得息声。
农忙时节,人人都忙着赶活。中午饭只是草草吃了,一家人就都下了地。下午3点多,这片地扳完了。四轮拖拉机拉了不满两车,运费掏了40块钱。今天来不及扳岗坡的那片苞谷,一家人就都围坐着剥拉回来的苞谷。果然,苞谷棒剥去皮后,一个个秃了顶,包谷棒里时不时有毛毛虫爬出,让人作呕。天黑时,大家的腰都直不起来了。父亲德云呼吸像拉风箱,有出的气,没进的气,直喊脊背痛。
岗坡地情况好得多。苞谷杆粗,叶子泛绿,苞谷棒大,扳在手里沉甸甸的。一家人来了兴趣,话头也多了起来。仙婷讲起她卖油饼油条与市容工商斗智斗勇的趣事——千万不能和这些人硬碰硬地对着干,他们来了,咱就躲,他走了咱出来继续做生意。最难对付的是市场收费员,这些人都是地头蛇,见了离县城远的农民——一句话,只要是生面孔,开票收费没说的。碰见咱这离县城近的又整天泡在县城的人,只要悄悄给他手提包里塞5毛钱,他会装作没看见,好几天见你绕着走。明宝来兴趣的是工地上的事,一再夸来旺是讲义气的包工头,有钱决不欠大家的工资。干恁大的世事,还节省的很,每天来旺都要叫工人清扫落在地上的石灰,将其堆起来,明天掺进去再用。维杰说高中学习跟初中就是不一样,人人紧张得就像打仗,晚上11点多才睡觉。有的同学星期日到老师家里补课,一个小时要交20块钱补课费呢。像咱家这条件肯定是补不起的。家长们也挖空心思想办法:有的请任课老师吃饭,有的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品,有的家长还请老师出外旅游。老师投桃报李,对在他那里补课或家长有所表示的学生格外照顾,格外用心,其他同学几乎全靠自学。奶奶秀梅听了孙子的话,感慨不已:“现在的学校咋能这样呢?这不成了商场,跟做生意一个样儿。”德云只是低头扳苞谷,一句话不说,但他的耳朵和心思一会儿也没闲着。
同样是3亩地,岗坡的那片地就扳了满满三拖拉机。连同河湾地扳回来的苞谷,院子顿时成了苞谷堆起的山。剥苞谷的活不像扳苞谷那样赶人,但也要抓紧时间。不然,堆起来的湿苞谷棒很快会发热发霉,得尽早将皮剥下来,把苞谷连同粒儿一起晾晒。
母亲秀梅和仙婷婆媳俩蒸花卷,烧红苕稀饭,切萝卜丝调了做下饭菜。家里老少三个男人剥苞谷。父亲德云对明宝说:“我看咱也得找老师给维杰补补课,不然娃会吃亏的。”明宝说:“对着哩。”维杰连忙拒绝:“我不补课,一个小时20块钱,咱出不起。”爷爷德云说:“如今把牛赶到半坡了,只能上不能下,出不起也得出。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你把学上好,你看农村人生活有多艰难。”明宝一锤定音:“星期一到校就找老师补课,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翌日,维杰提早上学去了。明宝上街买化肥和拌种用的农药。剩下的苞谷父亲德云、母亲秀梅和仙婷三个人继续剥。下午明宝回家时,所有苞谷剥完了,房前屋后连同窗台上尽是黄澄澄的苞谷棒。一家人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明宝念叨化肥太贵了,买了两袋美国复合肥就花了近260元钱;听说柴油价格也在上涨,翻地、耙地、播种的费用都要提高,6亩地没有240元钱怕是种不到地里去。
父亲德云起身时可能用力猛了些,突感心慌胸闷,天旋地转的就要倒地。明宝眼尖,跑过去扶住了父亲,从父亲上衣口袋里掏出速效救心丸倒进手心,硬是塞进父亲嘴里。仙婷忙跑回屋端来半碗开水给父亲灌下肚。过了大约十分钟,父亲德云逐渐苏醒过来,这才将父亲德云扶回家休息。
明宝、仙婷又吵着要送父亲德云去医院看病,父亲这回铁了心,坚决不到医院去。母亲秀梅也不支持送医院:“你俩已经尽心了,你爸这病是劳累落下的病根,到医院也治不好,我看就不要花那闲钱了。叫村医给你爸挂两瓶吊瓶,然后再歇两天就会好的。”明宝两口没了办法,只得去叫村医。
七
父亲德云挂了三天吊瓶,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转出转进手脚不闲。但是这次犯病与上一次明显不同。父亲德云总觉浑身乏力,手指发麻,而且一直叫喊着脊背疼痛,走不了几步路就心慌气短,必须蹲下来恢复体力。明宝从当地电视广告节目中得知,一种叫强心卡的器械能治疗父亲这种病,便赶到县城专卖店掏了200元钱买了一个强心卡。父亲德云先是不肯戴,嫌器械太昂贵,硬要叫明宝退了强心卡。母亲秀梅劝说父亲德云:“娃已经买回来了,就戴上试试嘛。”父亲德云勉强戴上强心卡,加之按时服用复方丹参片等药物,几天后症状明显有所好转。父亲德云脸上多日的愁云散了,庆幸自己没有进医院花冤枉钱。他天天早上起床锻炼身体,还学会了一套什么功法,有空就练。看电视节目也有所改变,从一味看秦腔到现在连寻医问诊类节目也特别留意。明宝和仙婷再不让他做重活,他也很自觉,再不争着抢着干,见到老熟人总是说:咱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不发病,少吃药就是儿子最大的福气。”
母亲秀梅相信了一辈子神,过去是阴历初一、十五雷打不动地敬神。现在母亲秀梅是天天晚上焚香叩头,在大院门把手上拴上红布条,屋内门后放了桃木棒,炕头挂着几束柳枝,所有能想到用来避邪的法子都用上了。即便如此,明宝晚上回家晚了,母亲秀梅仍要在门口生一把火,让明宝来回跨三回才准进屋,弄得明宝晚上不敢出门,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父亲德云的身体状况成了母亲秀梅的牵挂,稍有异样,她就坐不住——取来黄裱纸在丈夫头顶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再让丈夫往黄裱纸上吐三口气,边烧黄裱纸嘴里边念念有词:“阿弥陀佛,各路神灵都听着,今日送来冥国钱,如何花费随你便,只求把大小灾祸都带走,保我丈夫身康健。”要不,母亲秀梅摇着铃铛,举着柳枝在屋内角角落落抽打。父亲德云的病情缓解了,母亲秀梅就说要感谢神,是神给我们家造福呢。霜降来临,母亲秀梅偷偷去了三十里外的道观为丈夫抽签算卦。拆签的结果是父亲德云是富贵命,还有十年阳寿。母亲秀梅怀着无限的激动和喜悦将这个喜讯告诉给父亲德云。父亲德云的心像用鸡毛掸掸了,舒服得无法说:“我说呢,咱的命大,小鬼不敢惹……看明宝仙婷一天到晚急的样子,好像我今儿死呀明儿死呀,真是没经过世事。”
太阳还有一杆子高。仙婷反常地早早地回了家。一进家门,谁的话都不问,跑进厦屋,关上房门,呜呜地哭起来。父亲德云母亲秀梅不明就理,面面相觑。等仙婷哭声有所平息,母亲秀梅才敲门询问仙婷啼哭的原委。仙婷哽咽着说:“最近县城整治市容秩序,不准沿街乱摆摊点。事前我不知道一点消息,今天早上刚到地方,还没有摆开摊位,就来了几个小伙儿,说是市容综合整治办公室的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推上我的三轮车就要没收。我当然不会让他们收走三轮车,就给他们说软话,只差下跪磕头了,他们就是不松手,我气急了,和他们吵起来。几个小伙扑上前挥拳动脚地将我乱打一气。周围群众为我气不平,纷纷谴责这伙人的野蛮行径。他们才罢了手,末了三轮车还是被收走了。我跟到办公室,向他们的领导讨要三轮车,那领导扬着头说:‘别要了,这次收回的三轮车一律销毁,不然今天罚了款,明天你还出来影响市容。’”母亲秀梅劝仙婷别难过,三轮车没有了,咱以后干别的事,天无绝人之路。父亲德云在屋内走来走去,不说话。晚上,明宝回来,得知仙婷的遭际,狂喊着就要拼命。母亲秀梅,妻子仙婷劝阻不住。父亲德云声如裂帛:“你不要命了,这两天给我好好待在家,胆敢出外惹事生非,我砸断你的腿。”明宝这才善罢甘休。
三秋忙完了,进入传统的农闲时节。过去生产队往往在冬闲时节大拆大换(火炕、山墙)积肥。如今是利用冬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渠挖沟铺设地埋线、地埋管,整修乡村道路。条件好的村子已经实现了道路水泥硬化。农村中有门路的人或到工厂上班,或做小买卖。明摆着的事实是现如今抬脚动步都要用钱,花钱的路子太多,谁也不敢闲待在家。村子留下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人不出远门,但他们改善生活环境的愿望更强烈些。明宝所在的村子已经紧锣密鼓地张罗硬化村内道路的事。这天晚上,村里几位村民代表——实际是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上下的中老年人来到明宝家。他们跨进家门,与父亲德云寒暄了几句,话题就入了正题。年岁最长的张生财老汉开口介绍村里这次打路的情况:“咱村距县城近,可是村容太差,别人不想来,很多好事也就轮不到咱,村子一直是泥路,秋夏两忙庄稼难运回来,收回来的粮食又愁肠着没处晒;村里娃娃们上学深一脚浅一脚太不方便了,一句话,必须尽快用水泥把街道硬化了。”父亲德云一家人只是听着,没有插言。张生财老汉继续介绍道:“村上经过反复协商,决定今冬先将村内南北主街和东西支街用水泥打了,出村路以后再说。按照设计方案准备将南北主街打8米宽,20公分厚;支街打6米宽,15公分厚,全村打完初步预算得一百万元。筹钱的办法是南北主街向市县申请一部分项目资金,集体预留的100亩地承包出去,再动员经济条件宽裕的人及咱村在外工作的人捐一部分钱。各条支街是路过谁家门前由谁家负责修平整,村上统一铺底子,打水泥,所需石子、沙子、水泥及工钱由各户按住房多少摊派,每间房大概需用400元钱。”张生财老汉介绍完,几位代表用目光征求明宝一家人的意见。父亲德云说:“这办法我看能行,你们大胆干,我家应出的1200元钱不成问题。”张生财老汉提高了声音说:“我们来时,支书说了,你家情况较特殊,他个人替你家出一半的钱。”父亲德云连连摆手,“修路是万古千年的大好事,我还活着,必须尽好这一份责任,不用别人替我出一分钱。”母亲秀梅了解丈夫的性子,他犟了一辈子,不愿意受人的话,可眼下这钱的来路在哪里呢?
村民代表们走后,父亲德云把明宝两口叫到面前,对他们说:“爸这一生活得很艰难,自小离了父亲,成年后又失去了四个儿女,经的困难太多了,但爸刚强了一辈子,自己再困难不向别人伸手。说起来实在对不住你们,我到老来也没有给你们把日子过上去,没给你们盖一院一砖到顶的楼房,但爸死前能看到你俩亲亲热热的过日子,维杰能争一口气考上大学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已经想好了,咱家那头黄牛已经养了七、八年,成了咱家一口人了,别看他是不会说话的牲口,可通人性呢。可是眼下我已病成这样,你们也都有各自的事要做,没有时间照看它,最好找个好主家把牛卖了,只要不卖给杀坊就成。这头牛兴许能卖两三千元,你们用这笔钱给村上交了打路钱,剩下的钱在最近找个泥瓦匠把山墙整修整修——至于维杰的补课费,咱家打下的苞谷晒干后卖了,也能抵挡一阵儿。”明宝和仙婷听了,觉得也只能如此。
第二天早起,明宝端着草料照常去替父亲喂牛。推开牛房的门,眼前的情景让明宝傻了眼……牛不见了!明宝慌了神,扔了竹筛往回跑“爸、爸、爸……咱……咱家的牛不见了!”父亲德云、母亲秀梅、妻子仙婷蜂拥着跑到后院。黄牛确实不见了,牛棚靠出村路的砖墙被人在夜里拆了豁口,黄牛是被小偷从那里拉走了。
父亲德云一句话没说出来,像座山一样倒在了地上。
- 延河(下半月)的其它文章
- 九个不圆
- 海港一号
- 谷莠子的狗(外一篇)
- 乡村叙事
- 工业之殇:傻子(外一篇)
- 搓 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