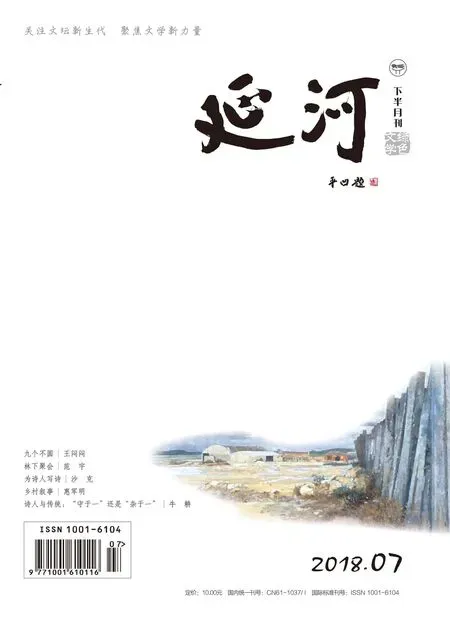工业之殇:傻子(外一篇)
刘 涛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始终会从幻觉中醒来,一睁眼,就感觉自己还住在粮油加工厂十三号楼中间,母亲还在不远处的房间里择菜,开始一天的生活。然而,转瞬间我就会明白那一切都是幻觉。此刻的我与意识中的假想的自己足足拉开了二十年的光阴,而这二十年,中间该有多少空白的记忆。
如果父亲没有在1964年来到新疆,而是仍然滞留在皖北偏僻的村庄,我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场景。但是母亲随着父亲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我而言,这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十岁以前一直没有出过粮油加工厂的大门。有一次,一个朋友怂恿我去看“金秋书市”,我才背着母亲走出了加工厂大门。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加工厂门前竟是一片幽深的树林,甚至到现在我也想不起书市是在哪里办的,只记得在初出厂门时的那种慌张和焦躁。朋友的父亲也是从安徽过来的,那时,加工厂有许多安徽人,出于怀念的缘故,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中有许多叫“皖新”的,什么陈皖新、朱皖新,这些名字寓意深刻,既有失落,也有怀念,不管身处何种境地,谁也不能扼杀人怀念的权利。
但彼时的失落与怀念恰与此时不同,一进厂门,一条大路直通沙依巴克村,这条路将近一公里长。每年盛夏,是粮油加工厂最抢眼的时节,交公粮的车辆一直排到糖厂、八棉,足有二三公里长,车多,人也多,难免闹哄哄的。路旁林带里都坐着团场来的司机,燥热,并且漫长。排在大门口的司机则时刻坐在驾驶室内,等待着车辆指挥人员的声音。正在焦急间,忽然看见一个黄军装、黄军帽样的人从大门里走出来,站在第一辆交粮车前指手划脚,驾驶员有些奇怪,明明应该进厂门,可黄军帽的手势却让他向路边开,驾驶员也是农村人,老实,一边纳闷,一边还就顺着黄军帽的手势把车开动了,一直开到了树林带边的高坡上。再开就开到树林里去了,黄军帽还在挥动着手臂让他继续开,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不知在说些啥。此时,驾驶员才明白:指挥他的是个傻子!望着刚刚空出来的车位已被后面的车挤占了,驾驶员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要打傻子,傻子不傻,调头就往厂门内的保卫科跑。
那时候,粮油加工厂有许多傻子,据说是“一·二六”事件给吓得,李雷说:那天晚上,加工厂许多对夫妻正在办事,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加工厂民兵连连夜抽调了许多民兵包围了师部大院。那一天,死伤了许多人……
傻子有着独特的面貌,从外表形容上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往往是面部扭曲,或龇牙,或歪嘴,或手折,或腿跛。曾国藩谓:“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这些上苍失手抟捏的人群依然有着饱满的精神、健康的体魄,足具活力。
傻子与傻子不尽相同,有的很木讷,有的很乖巧,伶牙俐齿,见了人,不管老少,远远就迎上去:“爷爷,爷爷,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爸我妈有情况……”每到这时,尤其是车队的司机们,一把摁住傻子的脖颈,厉声喝道:“说!你爸、你妈有什么情况?”不消一个上午,傻子爸妈的情况很快传遍了全厂,而傻子妈正撅着屁股扛面粉,傻子爸正悠闲地坐在原粮库房蘸着红墨水往墙上写毛笔字,许多人都叹着气说:“这么鬼精的父母咋能生出个傻子出来?”
世界上有许多事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正像粮油加工厂,1950年代还叫“八一联合加工厂”,再往前,刚建厂那阵儿叫“第二十二兵团面粉厂”,是正儿八经的军人选址、军人建。再往后,一提到“三八企业”,就把粮油加工厂撇到一边儿去了,老是什么“八糖”“八棉”“八毛”。1952年,加工厂建厂的时候,它们不知道还在什么地方转筋呢。
离开粮油加工厂后,确实很少能见到几个傻子,区区两千多人的企业,成天有那么多傻子在厂里闲转悠,男傻子,女傻子,而且那些傻子大多是60后,不知是中了哪门的邪。而“有情况”更是不闲着,成天在车间、办公楼上转来转去,偶尔还会干些顺手牵羊的事。“有情况”眼尖,只要在路上一看到车队的几个年轻人,调头就跑,被那几个司机一口喊住:“站住!”“有情况”立刻像被施了定身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司机走到他跟前,今天有没有情况?没有,没有……
真没有,假没有?
真没有!
然而,终于有一天,还是有情况了。气得他爹把他吊起来打,关在小黑屋里,一个多星期不许他出门。
一杭独自坐在母亲的坟前,小心地展开那份发脆的剪报,一篇题为《爸爸,我知道您会回来》的散文,勾起往事。文章是一杭读小学六年级时写的,后来在区报上发表,作家梦也由此播下。
情况是这样的:一天夜里,保卫科全副武装追赶一个窃贼,枪、电警棍、手铐,啥物件都备齐了。窃贼也是加工厂子女,一溜烟钻进了四合院,四合院蜿蜒曲折,好在保卫科的人对这块地方也熟悉。就这样,追到“有情况”家门口,突然没情况了,四下不见人影,保卫科副科长就敲开了“有情况”家的门,“有情况”的爸爸笑容满面打开了门。

刚才有人到你家吗?
没有,没有。我一直在家,没人来过。
唔,保卫科的人在他家里里外外、门前门后搜了几遍,确实没有。
一会儿要是看到窃贼,立刻向保卫科报告。临行,保卫科副科长给“有情况”的爸爸交代着,便出门去了。
这时候,“有情况”突然从家里冲了出来,大喊着:“爷爷,爷爷。我知道。”说完,兴高采烈地拉着保卫科的人进家,走到床前,用力掀开床板。一个人蜷缩在床下,头上挂满了棉絮……
“有情况”的腿脚不好,走路总是感觉一跳一跳的,像一只麻雀在蹦,在粮油加工厂所有的傻子中间,“有情况”是最灵光的,也是最爱惹事的。俗话说,傻子见面,分外眼红。好在傻子们不记仇。我们房产科早先设在加工厂职工医院内,临街,来来往往的,今天谁得病了,明天谁转院了,都看得一清二楚。隔壁是诊疗室,一群年轻护士每天早晨从煮针头开始,在隔壁叽叽喳喳,不时还要过来问问分房政策,着实令人可心。但也有闹心的时候,只要听到隔壁护士们一片尖叫,我们就知道“有情况”又钻进去了,立马过去又用掌掴,又用脚踹,把他赶了出去。卫生所里姑娘多,不光“有情况”爱往这里跑,冬冬也成天在这儿守着,只不过冬冬比较内敛,从不往诊疗室钻,黄军装,黄军帽,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我那时骑着二八加重自行车,就放在路边排水渠旁,一抬眼就能看到。冬冬站累了,通常会走到自行车旁,胳膊肘肘在自行车座包上稍事休息。在这里,冬冬和“有情况”经常会不期而遇。大抵相安无事,但也有例外。一天,我从窗口向外张望,正好看见冬冬依旧倚在高大的二八自行车旁“稍事休息”。忽然就发觉他紧张起来,随即就听到嗞嗞啦啦的脚步声——“有情况”来了。“有情况”面无表情,一跳一跳地往前走,目不斜视,连头都不抬一下,仿佛根本没看见冬冬。在与冬冬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他忽然抬起手,狠狠地推了冬冬一把,冬冬闪避不及,从二八自行车上重重地栽倒在树沟里。“有情况”撒腿就跑,跑得快,跳得也就更厉害。
冬冬从树沟里爬出来,捡起落在一旁的军帽,依旧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顺手从地上抄起两块铁石头,开始去复仇,他的身影在窗口出现了三次,铁石头依然握在手中。
父母亲经常会告诫年幼的孩子们不要去招惹傻子,不要一放学就跟在他们后面傻子傻子地叫。“傻子杀人不犯法!”父母亲甚至用这样激烈的言辞来警告我们。加工厂有温和的傻子,但也有暴力倾向的傻子,他们都是傻子。他们的父母看到他们快活的身影,不免会暗自垂泪,“如果我们死了,他该怎样生活呀?”但是这种担心纯属多余,事实证明,所有的傻子都会在他们的父母老去之前纷纷夭折。
傻子死了,没有什么讣告、追悼,一把火烧了就完了。他们是生活在你们中间的另外一支族类,仿佛是远古灵长类进化为人类后的另一支人群。“有情况”死的时候,只草草几个亲属来帮忙,该烧的烧了,该扔的都扔了。有人劝慰道: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好,省得将来吃苦受罪。可她的母亲突然嚎啕大哭:“就是家里养的小狗小猫死了,我们也要难受啊——”
黄昏以及荒原上的狗尾草
在离开炮台镇之前,我特意到小镇西边的野地里走了一趟。初秋,野燕麦黄澄澄的,一簇一丛,为视野中打上了一层金黄的底色,夹杂在草丛里的野葡萄,红彤彤像一粒粒血珠,而远处的鸟用翅膀惊动了无名的黄昏。
这是个散漫的黄昏,视野从低矮的山包上漫射出去,出奇的开阔,只有视野不能及的遥遥的地平线,而没有阻碍。我对蓓蓓说:“我喜欢这地方。”蓓蓓的脸上立刻闪现出巨大的惊叹号:“这有什么好看的?走吧!”随着蓓蓓的手,我离开了野地。据蓓蓓讲,要看荒原就到大沙包去,那里荒得连一根草都没有,能把眼睛珠都磨破。
蓓蓓是沙包窝里长大的孩子,识字不多,她从小在沙包窝里拾柴、挖大芸,如今她已不去想那些日子,而她在沙包窝里常穿的红褂子,也小得不能再穿了。蓓蓓在慌不迭地收拾衣物,一边收拾一边喊着儿子:“乐乐——乐乐——”于是门口闪现了一张黑黢黢的脸,一张黄昏的脸正在咀嚼玉米棒子。蓓蓓有些气愤了:“还在吃?还不快换衣物!”
乐乐的咀嚼漫不经心,他的手里除了玉米棒子,还有一根枯黄的狗尾巴草,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狗尾巴草把脸庞撩拨得痒痒的。见母亲板了脸,乐乐一闪身出门去了。我们都没有立即要走的意思,倒是蓓蓓显得急不可耐。
W-lan的网速慢下来了,荒原上的显示屏闪烁不定,我随手点开一个页面,竟是T·S·艾略特的《荒原》:“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干什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西比尔的预言一直吸引着我:“你来的时候,我正独自在外坐着/你注视着我的眼睛,表现出神才有的恐惧”。
“乐乐——”“乐乐——”又是蓓蓓匆匆忙忙的呼唤。
乐乐肯定又跑到长满狗尾巴草的野地里去了,他或者我好像从精神上都没有做好离去的准备,倒是蓓蓓显得烦躁不安。
不多一会儿,岳父领着乐乐进门了,乐乐的手里抓着一大束摇曳的狗尾巴草,岳父说:“明天再走吧,天黑了。非要赶末班车吗?”
蓓蓓好像没有听见,执著地翻捡着乐乐的衣服。
我是骑着三轮车走的,提包放在车斗里,岳父还从地里刨出了土豆,蓓蓓和乐乐坐在车斗里,乐乐不停地扭动着,我掌着车把的手明显地感觉到他在身后的每一个动作。
岳父骑着自行车,慢慢地跟在三轮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