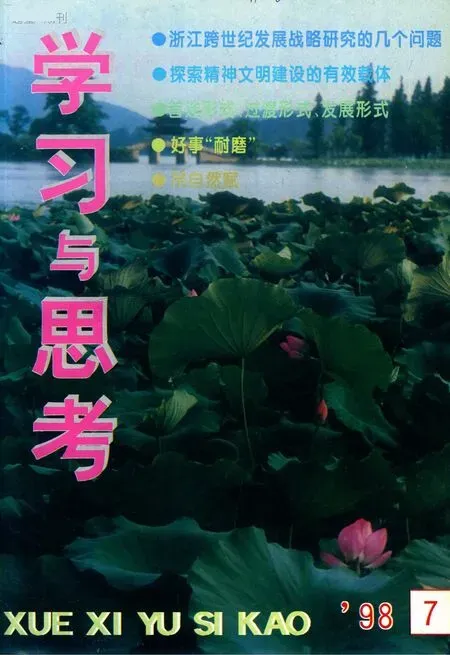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特点
冯 波
提 要: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对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进行了扼要的分析和说明,是国内最早将唯物史观视为社会学之重要进展的文献之一。以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界的社会学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传播不是纯粹的学术景观,而是作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而发挥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带有明显的中国特点。
马克思的名字最早见于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新民丛报》18号上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 。他说:“麦喀士,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此后,也有一些对《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著作的零星介绍——“中国少数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轮廓。其中,朱执信是最著名的一位,但在中国及知识界并没产生什么影响”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那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不具备充分的社会条件和理论准备。“这种情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有所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相对地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多的发展。随之而来,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就成长壮大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又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在广大知识青年中掀起了追求真理的热潮,加上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社会阶级的基础和思想理论的条件。所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欢呼十月革命的同时,就很快接受和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①杨凤麟、屠承先编:《中国现代哲学史概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第一篇真正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文,也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译著作,便足以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大理论发现之一,开辟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崭新一页,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许德珩指出:“能够解释社会最确切的理论,就是历史的唯物论,而历史的唯物论,就是正确的社会学,而社会学也就是社会科学。”③转引自闫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页。马克思当之无愧地被列为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流派也相应地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家、实践家结合中国革命的需要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做了很多工作,形成了他们的理论成果,也形成了此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特点。结合相关文献,梳理这一传播状况,可概括出一些传播特点。
一、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以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为代表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派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社会学流派之一。“中国早期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法则,在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社会学应用研究及有关社会结构的理论与实证探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就。尽管该派的观点尚不成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们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位置则是不可否认的。”④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对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进行了扼要的分析和说明,是国内最早将唯物史观视为社会学之重要进展的文献之一。李大钊认为:社会学得到唯物史观这一重要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会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⑤《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0页。。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初步传播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播的序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后续传播起到了“播种者”的作用。
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比较系统地体现在《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等著作中。瞿秋白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的全体,包括社会的发展或衰灭的根本原因、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社会现象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因此,“社会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页。。瞿秋白没有把历史唯物论划归哲学,而是划归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他认为:哲学是研究社会思想的。“瞿秋白的社会学思想是庞杂的,受着历史唯物论的深刻影响。《现代社会学》是瞿秋白撰写的讲义之一,共6万余字,主要参考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著作写成。由于瞿秋白当时担负着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使他后来没有对社会学继续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而且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使得他的社会学著作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建者。”②周建明:《瞿秋白——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建者》,《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4-5期。值得一提的是,与李大钊等人主要通过日文译著了解马克思主义不同,瞿秋白主要是通过俄文论著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比起马恩著作来,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更成为其介绍、论证的主要依据。”③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央宣传主任)之一李达从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时期起,就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1921年5月,李达翻译、出版了荷兰社会民主党领袖郭泰所著《唯物史观解说》。这是我国早期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译著之一,到1932年共出了14版,产生了很大影响。为配合中共二大宣言的基本精神,李达还撰写了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 一书。 1923年,李达与陈独秀发生思想和政治分歧、自动脱党,但他仍然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26年,李达出版了近18万字的《现代社会学》专著,到1933年,该书共印行了14版,影响很大。这是“继瞿秋白同名著作之后集大革命时期唯物史观理论之大成者,也是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理论水平”④周太山:《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受当时语境的影响,该书没有使用“唯物史观”作为书名。李达在书中指出:唯物史观社会学,即应用唯物史观说明社会的本质。他将人类相互之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二类,人与共同团体的关系;第三类,人与人、共同团体与共同团体、共同团体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所著《现代社会学》的“学术水平在当时中国学界应属领先地位,尽管现在看来书中的不少观点不是那么精确或准确,甚至错误。较之瞿秋白的讲义,《现代社会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⑤胡为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百年历史》(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27页。。1930年代中期,李达又编著了另一部影响很大、42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著作——《社会学大纲》。他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是前著《现代社会学》绝版以后的新著,内容完全不同。《社会学大纲》共分五编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其个人背景及经历各不相同。有早年曾参与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社会服务而后从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有出身贫寒、在日本留学时接触马克思论著的邓初民和李达;有曾留学欧美的许德珩与陈翰笙;有在革命实践中开展农村调查、运用‘阶级分析’制定斗争策略的毛泽东和张闻天。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同之处,是接受得了历史唯物论,对以革命推动社会进步持坚定不移的信仰。”⑥闫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二、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特点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传播不是纯粹的学术景观,它首先是作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而发挥作用的。“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理论的准备阶段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把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五次大规模的学术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由此彰显唯物史观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价值。李大钊、瞿秋白参与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李达、陈独秀参加了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瞿秋白、陈独秀介入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其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学,例如,“从瞿秋白的社会学著作来看,他的社会学研究是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他是为这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研究社会的,这一点是今天我们从事社会学研究所要根本继承和发扬的”②周建明:《瞿秋白——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建者》,《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4-5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和社会发展变迁理论同实践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不仅仅是思想理论,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观点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转化成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③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
从传播路径上看,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不是靠成建制的大学体系这条路径,而是靠报刊、出版物的传播。当时,高校社会学系的主流是传授欧美社会学的孙本文、吴文藻等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者。1922年初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是当时唯一一所传播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高校。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是1949年前唯一的一个以传授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目的的高校社会学系。上大的校长为国民党元老、同共产党关系良好的于右任。但他仅是挂名,真正掌权的是数位早期共产党领导人。总务长为邓中夏,教务长是瞿秋白,后者兼社会学系系主任”④闫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227页。。但上海大学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于1927年4月被迫关闭。这也就意味着,高校传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体制在1949年前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许德珩、邓初民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者在其他高校讲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受到学生欢迎,但都为期不长,很快即遭解聘”⑤闫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227页。。这种态势的形成和当时主流的社会学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看法有关。孙本文所著《当代中国社会学》在“凡例三”中说:“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故凡从此种史观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⑥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页。1919年5月,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发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物史观部分的摘译。他同时还在《新青年》杂志上编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的系列文章。从1920年11月起,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用唯物史观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探讨中国革命问题。这本刊物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被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列为必读资料,广为流传。1921年9月,李达和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地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马列著作,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欧美社会学传统进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共性。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主流观点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认为,他们所传播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学”,以前的社会学是“传统社会学”、“旧的社会学”、“资产阶级社会学”。这就为欧美社会学传统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一度(1952-1979)取消社会学学科埋下了伏笔。这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学术与政治关系方面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带有中国的特点,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学处境产生了影响。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在学术为政治服务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作用是作为直接的“批判的武器”。例如,《社会学大纲》1937年5月出版后,李达曾将此书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研读这本著作,做了3392个批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对李达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①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否定其他社会学的价值,用唯物史观取代和消解一切社会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流派,没有考虑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将学术根据政治立场、阶级属性分类,这种做法本身没有将学术和政治作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取消社会学提供了逻辑上的前提。这个教训是值得汲取的。正如有学者分析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所参与的三大哲学论争的成因时所说:“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过于强调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性,致使学术研究丧失了相对独立性,丧失独立性后的学术研究与宣传通常沦为政治的注脚。……理论的研究的科学性就无法得到体现。”②王红梅:《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页。
此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传播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体现了这个特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整体性的,即在传播时该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产物,尽管它吸取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思想精华,但关注当时无产阶级的苦难、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是它的使命,因此,哪里的工业获得发展,哪里就有无产阶级运动,哪里就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者,并且往往是其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在先,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有关资本家剥削无产者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论证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唯物史观也随之得到传播。”③胡为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百年历史》(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