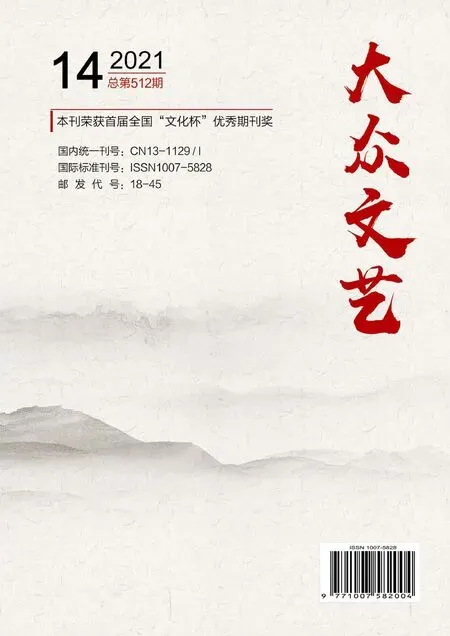网络时代的艺术衍生形式
余思宇 (四川大学 610207)
一、超越真实
2014年阿玛莉娅•乌尔曼开始了一个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创作的一整个历时四个月的网络行为艺术,2014年4月29日,乌尔曼开始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传了自己的自拍照,和众多社交媒体网络红人并无区别,只是她扮演了一个不存在的虚拟人设,刚开始上传照片时她是一个清纯可爱的普通女孩,之后她经历了“失恋”、“自杀”、“被包养”、“重新振作”一系列过程,相对应地,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同时也是这场行为艺术中的不知情观众,对之做出鼓励、失望、非议、支持等反应。当然,最后乌尔曼公开了她的艺术家身份,为这个行为艺术画下了句点。当乌尔曼宣布了她的艺术家身份之后按理说这个艺术行为已经宣告了完结,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艺术需要展出,需要一个媒介到另一个媒介的移植,当乌尔曼的艺术移植到博物馆之后,她的自拍照被打印出来,挂在博物馆空间里的展板和白墙上。
当我们在博物馆观看此艺术时,它显然没有在网络上看起来有趣,因为它只是把自拍照打印成更大幅的图片,观众在其中不自觉地活跃互动是重要的一部分,当它移植到博物馆之后,观众却无法在这一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参与的事实变成了观看的事实,互动变为了艺术家一方威权的展示。
这似乎导向了一个在场的悖论,网络事件的在场和肉身亲临的不在场,以前观看艺术品的经验在这里完全倒置了过来。网络的观看是一种透明的观看,观者通过这一隐匿而放纵的观看获得了无止境的好奇心和膨胀的窥癖欲,因为自身的现实性得以藏匿,从而给观者的注视延伸了监视、参与甚至控制的权力。“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产生的眩晕”1,观者通过“实际不存在而偏偏存在的事实”获得的眩晕感,即在超真实维度取得的参与感已经超越了现实维度能够获得的参与感,从而导致了网络上的真实在场而现实中的缺场。
从“拟像”到“图像”的位移,是一个“没有所指,没有本源”的“像”到一个指向网络行为艺术本身的“像”,使博物馆展出的自拍图片变成了对拟像的模仿,对非真实的“符号的符号”拙劣的模仿。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本身即是信息。网络创作的艺术这一符号一方面因为它指向自身的特性而无法成功脱离网络媒介这一载体,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光纤被压缩了的时空维度在被现实恢复时而膨胀的体积带来的是密度的缩小,从而导致了信息的空洞。网络媒介是一种信息点组织松散、无序、不连贯、模糊不清的媒介,也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冷媒介,当一种在网络上传播的艺术移植到另一传统的信息密度大的媒介时发生的异象就使其显得直白、浅陋甚至粗俗。
二、媒介即收藏
无论是纹身、化妆、插画、剪纸或是传统的绘画,都是上传原物的照片或者视频传播,大多数作品对观众而言实物都是无法接触到的。社交媒体大量传播的同时带来的是对实物的遮蔽,这一问题并不是网络时代到来才出现的,自印刷、摄影技术和大众媒介诞生以来,观众都只能通过报纸、电视观看到实物的复制品,本雅明将这种复制品认定为“技术复制品”,这种复制品一方面“比手工复制更独立于原作”,另一方面“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2。以摄影技术拍照上传的艺术品,展现出的形式也受了摄影技术的影响,而不能简单地指向原作本身,原作可能因为摄影的光线、构图、色彩而展现不同的样貌和质量,同时网络艺术的数码复制品能达到原作所不能达到的传播范围。
1859年,美国作家奥利弗•W•霍尔姆斯语言,摄影图像将如书籍那样充满图书馆,被艺术家、学者和爱好者广泛使用3。现在各大博物馆建立了自己的线上资料库,网友可以便利地从线上获取自己想要了解画作的高清大图。最近,谷歌与7个国家的33个博物馆合作,对弗里达•卡洛的作品进行了一次开创性的调查,其中包括了弗里达的数百件从未数字化的作品。
网络艺术对实物的数码转译,使传播行为同时也带有收藏的性质。鲍里斯•格罗伊斯认为博物馆具有不断使自己变得完整的任务,它收录的是现实中越是无价值、短暂、越是世俗的,它就越有资格在档案内展现世界普遍的无价值性。4而这种无价值事物因为对档案来说是新的,“正是由于它无价值且无关紧要”,才能获得机会在有限的档案空间中展现整个无限。那么,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博物馆为什么没有收录更广大且无意义的网络艺术创作呢?
网络会给博物馆的权威带来威胁,是我们当今的艺术家不更多地利用网络进行艺术创作的原因之一,网络不仅是一种创作材料,它在创作和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资料的储存,它的一切创作过程和创作成果已经化作数据被收录在互联网这一庞大的数据库中。一件艺术品直到被博物馆收藏之前无法被认定价值,是因为博物馆作为一个“档案”,它以往的任务是对现实生活中庞大驳杂的信息进行筛选,档案里的东西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更广大的未入选的艺术将被历史遗忘,档案的权力因素会持之以恒地对后世实施着它的权威。
三、网络为媒介的创作形式
“大众媒介所显示的,并不是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同时参与的事实”。5
是否可以回答网络的艺术衍生形式和博物馆艺术的差别呢?
先通过观察网络艺术的不同形式,试探究这类新兴艺术的特点。
1.除了以原作的数码复制品形式存在的艺术,另外一类本来以数码形式创作的艺术,是没有原作的,它本身的存在形式就是一张数位图。在网络上创作的数码绘画和影像和传统绘画、影像在内容上的区别是没有现实指涉物的区别,它创作出来不是对任何现实的模仿,是一种全新的“真实”。但近来当代艺术创作所依赖的临场感,新媒体艺术、体量巨大的装置艺术,反而是很大程度上拒绝图片转译的艺术,“拟像”挑战“图像”的存在,当代艺术做出的回应是将人类的身体纳入到场域中,制造视觉无法替代的触觉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在抵抗技术对人类的异化。
2.艺术家和所有观众的同时在场,当人们在网络上欣赏到一幅艺术作品时,虽然艺术家身份也被网络隐匿起来,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缺场。但对观众来说,这件作品是与传播这件作品的账号联系在一起被观众接受的,但人们在博物馆观看艺术作品的时候,艺术家的身份也仅仅出现在作品旁边的小卡片上,博物馆担任了传播的中介,博物馆充当了艺术家的发言人,使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而在网络上,艺术家与观众直接对话,观众与作品、与艺术家超越时空地位于同一个交流平台,观众借此产生了一种平等的错觉。罗伊•阿斯科特认为网络通信技术是一种文本新秩序,也是一种话语新秩序,网络提供的分散式权限的参与模式引发的不是‘独乐’而是‘一起来吧’的‘众乐’。
3.以图代文的图像文本体系,在网络上“内爆”式出现的另一类图像,将任何图片配上一两句简单的文字,用来交流的语言体系,在中国被叫做“表情包”,在英语国家则被命名为“memes”,这种新型的语言填补了赛博世界交流中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的空白,另一方面将复杂的语言以图片的形式进行压缩,需要用多个词语甚至句子来表达的语言可以被压缩进一张图片所暗示的时空中。比如说“当反复听到同一首流行歌曲之后我不胜其烦”,这样一个句子,指向了一个事件的前提限定,主体,个体,主客体之间的联系。而在图像文本里它们可以怎样表达呢?有这样一张“图像文本”,大街上一个男孩吹着小号向女孩走去,女孩厌烦地捂住了耳朵,而创作者则是将某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添加到图片上。这样,图像原本的所指就完全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操作几乎近似波普艺术的拼贴手法,用来表达不同的内涵。一张图片或一段影像的所指可以无限地膨胀。
四、网络为媒介的消费模式
经历过“内爆”的网络创作已经变成了“拟像”的乌托邦。
进入网络时代以来,艺术品的数码复制品得以大量、爆炸式的传播,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深感忧虑的复制品对原作的独一无二性的侵蚀,如今可能成为现实。一方面线上艺术复制品对原作光韵的侵害,网上资料库和博物馆的建立使得艺术的数码复制品可以轻易获得,而且观看者可以通过任何线上媒体将它发布传播出去。另一方面,大量的形式各异的数码图像被创作出来,它们可以是自己拍摄的影像、数码绘画、人体艺术的照片,或者是对艺术作品的拼贴、再创作,这些图像的作者将作品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与博物馆艺术家迥然不同的是,他们在进入一场展览之前就有了自己的观众,并且这不是短期内带来的关注,而是一种持续性的关注,他发布的每一件作品都受到观众的审视并留下评论。他们其中有些会引起策展人或者艺术机构的注意,并帮助这些艺术家们引入到博物馆中,或者引起时尚行业的注意,与时装品牌进行合作。或者是吸引广告商,将广告融入到自己作品中。
网络图像的大量繁殖也给它自身的定价带来困难,显然一件数码作品很难吸引人去消费,不如说它因为其无实体的特性本身就对价值判定造成了困难,它需要转变成实体性质才能产生它的商业价值,如果想对一件数码作品进行销售,它需要转变为图册、打印的装饰画、甚至服装、环保袋。
网络创作位于“价值分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价值规律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知识某种价值的流行和某种价值转换,以及价值的随意性增殖和扩散……我们已不可能衡量美与丑、真与假或善与恶”6,因为不可能对价值判定,从而也导致了价值交换的难以实现。
网络艺术只拥有生产环节而没有消费环节,赛博空间的符号无法拥有文化区隔的功能,这恰恰证明了只有在物的层面上,符号才具有阶级性,符号本身是无所谓阶级性的。所以现在有的特权阶级也试图通过建造技术壁垒来垄断信息,以实现自己牟取利益或者维护统治的目的,试图在信息上恢复古老社会的等级断裂,但这也只能通过技术手段来强制建立等级差异,反而恰恰证明了信息或者说符号本身是平等的。
而海柔尔对于网络对社会等级制度的破坏保有乐观的期望,“在当前的社会骚乱中,机构组织慢慢意识到如果他们和社会想要继续存在,他们就必须重组、重新制定目标,减少金字塔般的等级划分……在当前我们这个混乱的社会,网络是最重要、最智慧、最综合的组织方式……这可能预示着人类意识发展的革新。”7
网络艺术的盈利模式借助了从事古老的物质形式,尽管现在人们认同信息的大量浏览可以带来财富,但是信息本身却无法直接转换成价值。信息的传播带来的关注度最终会汇集在作者身上,也就是将信息产生的关注转变为作者个人的品牌价值,品牌的概念才是阶级性得以实现的标志,实际上是作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数码创作转化为实体衍生物的价格,也是他吸引广告商投入他的数码创作时他所收取的费用,也就是他的网络虚拟人格的代言费。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下来,网络艺术不是“物”,所以本身并不具有商品价值,它所属的作者才是被消费的对象。这里消费的对象不是“物”,而是“人”。
五、结语
网络时代的艺术创作是一种指向自身的“拟像”的创作,网络艺术的观看方式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超真实”观看,观者和作品、艺术家的距离在赛博平行空间得以拉近,网络媒介的传播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收藏行为。网络艺术因为其自身只具有符号和信息的特性,本身不具有价值属性,只能依靠古老的物质形式出售和消费。
注释:
1.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2.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3.巫鸿:《美术史十议》,三联书店2008年版. 第35页
4.鲍里斯•格罗伊斯:《揣测与媒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页
5.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5页
6.孔明安:《仿真与仿像,内爆与超真实》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第44页
7.罗伊•阿斯科特:《未来就是现在:艺术,技术和意识》金城出版社,2012版. 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