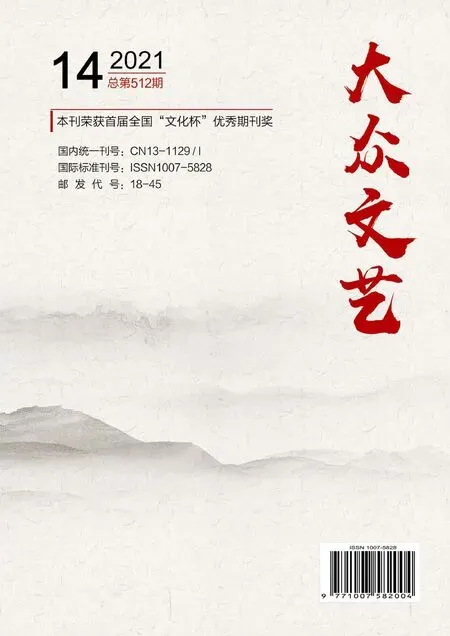毛南肥套传承人口述资料研究
刘益行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530000)
在当代的学术研究中“口述史”的纳入历史学研究已然成为一个常态和推动新史学发展的动力,无论从其学科自身日渐完善、规范的建设,还是到研究层次之深、维度之广、跨度之大,口述史凭借自身的优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为历史学发展注入鲜“活”的生命力。它对于传统史学研究而言,不仅丰富了研究内容、拓展了研究视野、弥补了研究缺失、转变了研究范式,而且对其它学科领域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广西这块生机勃勃的土地,自古便有壮族、瑶族、毛南族等多民族在此生息繁衍,孕育出具有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深深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毛南族人,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民俗活动就是肥套,汉化之意为“还愿仪式”。毛南族肥套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因此,对毛南族民俗文化的研究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毛南人用规模较大的还愿仪式来传递对神灵敬畏,许下的愿望实现了,就必须做一场还愿仪式,回报神明,才得以安然处世。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还愿”活动进而演化为固属于本民族的重要祭祀仪式。因此毛南肥套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深厚。
本次毛南口述资料收集工作开始于2017年2月26日,为期一周;本部分写作内容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访谈人物依次为:谭荣周(毛南肥套传承人、毛南肥套三元公)、谭三刚(毛南肥套传承人、毛南肥套三元)谭承松(环江县政府文化馆工作人员)。
一、采访人:刘益行,被访人:谭承松,记录、整理:刘益行。采访时间2017年3月2日,地点:环江县。口述内容:
刘:谭老师,您在小时候所接触到的毛南族这种“肥套”舞,您小时候对它有什么印象?您家里有人从事“肥套”吗?
谭承松:我小的时候,应该是76年,还是77年,在我外公家看到的。当时看的人很多,家里面全部是人。文革刚结束,但是那时候他们还挨批斗。那时不敢公开,也是偷偷摸摸的,我去的时候也是半夜去的,因为那时候我在下南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我的直系亲属没有,就是我外公和我舅他们做,我爷爷这边没有做,因为我爷爷是医师,他有几个诊所,他没有做。我小的时候也不想学,从来没有学过肥套。
刘:您舅舅他不是在搞“肥套”的吗?您舅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肥套”,开始学习的吗?
谭承松:我是13岁的时候就来县城了,来县城以后就很少跟他们接触了,他们做的时候我去到下南的时候有机会跟他去看。我就是七几年看了一场,然后到83年见了几场,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跟他们接触比较多。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帮我外公把那些东西挑到山里面收起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是查得很严吗?所以像刚才你们看的神像也就是那个时候保存下来的。那个时候是偷偷的做,偷偷的收藏这些东西,像我舅的那些经文,当时都被没收过了,他能背多少,后来回去再重新抄一遍,都在你的肚子里面,过后再回忆再抄的。现在他家里面的那些东西也还在那里,还没有人接班,虽然我表弟他已经接班了,但是他现在还不做,他现在在柳州开了一个牛肉店卖牛肉。
刘:就等于说没人接他的班了?现在“肥套”这一块保护下来的多不多?现在和以前的差别,和您小时候看到的表演形式。
谭承松:有人接,但是不是我们家的人,是他的徒弟。但是那个人也还没有成才,他会念,但是还没人请他去,他现在在学习当中,他也是把我舅的整套经书都抄完了,也是50岁的人了。从我们毛南族自治县成立之后,他们来环江参加毛南族自治县成立的那一年开始,这帮师公基本上就有一点胆量了,胆量大一点了,开始做了,学的人也逐步的有一些,在30岁的人学,但是现在学20多岁的也有。
二、采访人:韩德明,被访人:谭荣周,整理、记录:刘益行。采访时间2017年2月27日,地点:环江县。口述内容:
韩:今年有50岁没有?你做这个是祖传的吗?
谭荣周:51岁了,我是65年出生的。我做这个是祖传的,从我这里往上算有十代了,十代都做这个,我是第十代。
韩:你们叫做肥套的“师傅”三元公?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谭荣周:对,我们也不喊师公,我们喊作三元公。1989年开始跟我爸学,记得是24岁。一开始是跟他们跳,跳了以后再看书。跳的时候是结了婚有孩子了,当时也不是自己去学的,是我爸叫我去我就去了。
韩:你们要学很多东西吗?开始是学什么呢?你学跳的时候动作教你们吗?
谭荣周:就是跳舞而已,没有念经,开始就是戴面具跳,跳舞穿针。两年以后我才开始跟他们念经。开始是爸在家里头教,打锣鼓教我。
韩:他是念到锣鼓,还是打到锣鼓来教?
谭荣周:打锣鼓,他有一个小鼓。
韩:也不是做还愿,就是打着锣鼓给你学。那你学得比较正宗了。先教你怎么跳,然后就打锣鼓给你跳,让你学。在家里面学了多久?
谭荣周:在家学了两天而已。
三、采访人:韩德明,被访人:谭三刚,整理、记录:刘益行。采访时间2017年3月1日,地点:环江县。口述内容:
韩:我们想做毛南族“肥套”艺术口述史,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就想通过你们口述讲出来,把你爷爷那一辈、你爸爸那一辈以前做“肥套”当时的过程,什么时候学艺的,他们是怎么学的,怎么做的,我就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学的,他的师父又是怎么传的,然后你爸又是怎么学的?
谭三刚:我们是父子承传,我跟我爸学,我爸又跟我爷爷学,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不是师徒,我们是父子承传,我是第十四代承传人了,历史蛮久了。我就是跟我父亲学的,父亲跟祖父学,就是这样子。到我这一代,我是第十四代,我儿子是第十五代,我肯定要教我的儿子学的,他现在出去打工了,立秋之后他回来就跟我们学,他现在随便跳了,就是唱比较难一点,我们慢慢教他。他们经书还没背得,他们这一辈读得了,但是背不得,我们一代人背得很多。他们刚开始学的是跳,不会唱。跳也是我们教他的。初一到初四我们都叫这帮兄弟到我家里,到我们祖宗排位那里敲锣打鼓。
韩: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几个徒弟是在哪里的呢?
谭三刚:有五六个徒弟。包括我的儿子跟侄子。玉环屯有两个,上塘屯有一个,卢壮全(肥套三元公)也是我的徒弟。他是老徒弟了,他学得比较早,去年我带侄子,前年带我儿子。他们现在出去打工,立秋以后就回来学。学了三年了。侄子是去年学的。他们跳都跳得了,但是唱还不行,咬音不清楚。
韩:瑶王(肥套里的“神”,有专属的舞步)你教他们跳吗?
谭三刚:也教,但是我现在老了,我跳不了,又这么胖了。我们教兄弟都是不用学费的,免费学。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是我的侄儿,还有一帮朋友,都免费学。这也是应该做的,因为不教的话就没有传承人了。
韩:你是国家级传承人,你带了几个徒弟你就要告诉他们,这是你是传承任务职责。
谭三刚:我跟他们讲过了,我们不收费的,现在他们的兄弟过来我也教,其他的事情就不能告诉他了,这个是传男不传女的。外面的人过来,兄弟过来,有些是不能教的。
四、总结:
从毛南肥套传承人、文化工作者的口述资料中,了解到了他们记忆里“初识”的毛南肥套,以及他们最初接触到肥套的历史回顾。谭三刚与谭荣周是世代相传的传承人,皆是传承十代以上未曾中断,他们学习肥套更带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父传子授,谭三刚对于他的儿子教育也是如此;谭承松虽然不是肥套传承人,依然看出他对肥套非常熟悉,关于肥套的事情了解颇多。从他们口述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即使在“文革”的风暴中,民间信仰依然没有熄灭,而如今国家大力支持“非遗”工作,宽裕的环境使得毛南肥套传承人更能倾诉心中所想。
毛南肥套的传承研究,离不开供养它的土地,还需要具有奉献精神毛南传承人的付出。毛南肥套的保护传承,需要多方倾注更多心血。在此次田野考察返程的高速上,笔者看着路边飞驰而过的房屋农田,心中不免思绪万千。为期一周的时间是短暂的,所能收录的口述资料也是有限的。由然而生的内心渴望,将继续研究毛南肥套传承人口述资料,关于毛南肥套传承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