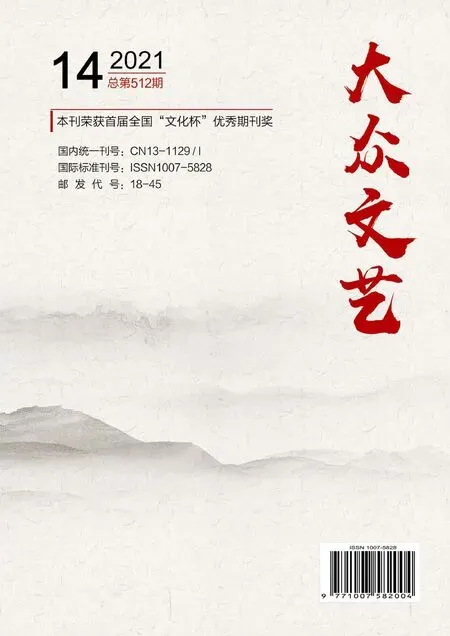存在主义的注解:读波伏娃《人都是要死的》
吴越萌 (武汉大学 430072)
在中国的神仙方志中,最不缺的就是“长生”、“延寿”这样的字眼。可是“长生不死”并不总是作为一个美好的概念被接纳的,在波伏娃《人都是要死的》一书中,它是主人公福斯卡背负的“天罚”。
福斯卡最初的身份类似于历史上常见的封建君主和野心家,他祈求获得永生,以不朽的时间征服无垠的土地,按照他的个人理性建立完美的国度。福斯卡在获得永生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世界的荒诞,卡莫纳的统治者换了又换,却在夺取权力之后无所作为,百姓被剥削压榨、城邦积贫积弱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他抓住了那个看似最为关键的问题:时间。生命是如此短促,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把一个城邦控制在手里,给它带来昌盛和光荣,君主和革命家往往没有完成夙愿便一事无成地死去。此时的福斯卡坚定地相信,无论以什么形式存在,生命始终胜过死亡,他唯一的信念就是活下去。然而等到千年之后,等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他却说:“需要很多力量,很多傲气。或者很多爱,才能相信人的行动是有价值的,相信生命胜过死亡。”1这其间贯穿了福斯卡无休无止的一生,也贯穿了波伏娃对存在的辩证和对生命的感悟。法国文艺评论者把《人都是要死的》这部著作称作对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艺术注解,波伏娃笔下的福斯卡为萨特的说理赋予了肉身,形象地阐明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分裂的个人”是书中所呈现的重要主题,与“分裂的个人”相对立的是“统一的宇宙”。福斯卡获得永生后立即踏上了建设“理想国”的征程,最初他的设想仅仅是平坦的大道、白色的宫殿、效忠于城邦的军队,紧接着他要征服瘟疫和饥荒,征服意大利的其他城邦。他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到,国家与国家、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命运是相通的,要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掌握一个统一的宇宙。在故事的第二部分,福斯卡把卡莫纳献给了疆域庞大的神圣罗马帝国,企图借皇帝之手实现世界的统一。然而现实令人沮丧,帝国在诸侯的纷争中分崩离析,基督教自身也分裂为新旧两派,殖民者给美洲大陆带去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福斯卡终于身心俱疲地明白:统一的宇宙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分裂的个人。人无法窥视他人的内心,遑论真正实现对他人的控制。福斯卡几乎把一切都给了爱子安托纳,可是安托纳却背离了他设定好的轨迹,他自以为被卡利埃所需要,却没有预料到他的朋友会以自杀的方式来捍卫生命的尊严。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在这些各不相干的心灵中无法找到真理的共同依据;相互理解并非一句空话,而是心灵之间跨越崇山峻岭的艰难跋涉。雷吉娜渴望福斯卡仅为她一人而存在,她要把福斯卡驯化成她理想中的恋人,与她共享记忆中的每一刻,使她在他不朽的生命中成为永恒。但是,“天空中是同一个月亮,但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各不相同,别人无法分享……这层坚硬的外壳使我们各人孤芳自赏。”2每个人都是一座被深水围困的孤岛,尽管在形式上处于社会群体当中,彼此却无法理解、无法进入,孤独是人的宿命和本质。
福斯卡的孤独比任何人都更为深重,因为他试图建立统一的宇宙,使他人的意志顺从自己的意志,他要用他的理智来统治世界。他的自信以永恒的生命为基础,他在历史长河中积累的经验多于史籍上记载的一切,他的理智将延续千秋万世,而不会受到个体短暂生命的限制。“任何力量都不会浪费,任何财富都不会流失。我将结束人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的对立,我将结束不正义造成的混乱。”3然而他的意志在执行过程中不断与他人的意志产生摩擦与冲突,要么在结果上大打折扣,要么带来不必要的牺牲和损伤,由于缺乏公允的评判标准,他本人的意志甚至会因为他人观点的影响而动摇。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说,他从获得长生的那一刻起就被人类社会排除在外,也把自己排除在了人类群体之外。福斯卡具有两重身份,半个他是神,半个他则是被尘世抛弃的人,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加深了他的孤独,也给他的行动增添了一分悲剧色彩。
以福斯卡与雷吉娜为主要人物的悲剧折射了三个关于“存在”的问题:如何证明自我的存在、存在是否有意义、人应该成为怎样的存在。
雷吉娜曾经苦恼地想:“我不愿意做一根草。”世界如同一片阔大的草原,由成千上万片单调的绿草构成,它们一般长短、一个模样,淹没一切个体的存在。多数人选择接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现实,但也有像雷吉娜这样不甘于平庸的人,他们渴求特殊的关注、别样的目光,证明自己的存在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矛盾的根源。福斯卡的出现于雷吉娜有两重意义:他激起了雷吉娜的欲望,成为她证明自己存在的“捷径”。一个历经百年风云、不老不死的男人,得到他的爱情即是得到了他的认可,也就意味着雷吉娜短暂的生命将通过福斯卡的记忆成为不朽,她因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爱人而证明了自己“生来就有异乎常人的命运”4。然而事实与雷吉娜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她看不透福斯卡的目光,那样的目光里仿佛没有爱情,只有对凡夫俗子的怜悯,他百年来经历的爱情显然不止一次,而她“那么引以为荣的德性”对福斯卡而言也并不新鲜,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其说是激情,不如说是相互需要和相互利用。福斯卡希望雷吉娜能让他“活过来”,不再做一个没有任何生命意图却永远不会死去的怪物,雷吉娜希望通过改变福斯卡证明自我的价值,并伴随长生的他进入永恒。曾经的福斯卡一度与雷吉娜一样处在“追逐者”的地位,他试图改变安托纳、查理五世、卡利埃和阿尔芒,他追求贝亚特丽丝的爱情却一无所得,他深爱玛利亚纳却无法让她接受真实的自己。他在追求的过程中经历了重重幻灭,由于深刻洞悉了生命与历史的本质而不再对未来抱有任何期待,他失去了存在的感觉,只有他人身上偶尔闪现的存在的激情能够触发他的生命实感。萨特说:“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他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意图上方才存在。”5福斯卡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存在。
雷吉娜的伪装在福斯卡的绝望哲学面前不堪一击,而福斯卡的绝望本身并非没有漏洞:尽管对世界和自己心灰意冷,福斯卡的内心仍然会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透入希望的光芒;尽管洞悉了生命与历史的永恒悲剧,他却无力彻底否认存在的意义,这在小说的第五部分表现得尤为突出。透过阿尔芒以及其他革命党人的奋斗,福斯卡似乎终于觉察了生命的独特性,卡利埃这些人曾经在他看来那么相似,可是他们无疑是不同的:“对每个人,生命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只有本人才能体会。这么一个生命是永远不会重现的;在每个人身上,生命没有一点一滴不是崭新的。”6福斯卡在堆积如山的死亡中固执地思考那个终极的问题:人生下来,活着,最终却总是要死去,那么这其间的挣扎和奋斗有什么用呢?他放慢了脚步,把自己沉入时间的细节,答案已经隐约浮现出来:“在人间还有希望,还有惋惜,还有恨与爱。最后,是死了;但是首先,他们是活着。不是蚂蚁,不是石头,而是人。”7人就是在这样痛苦又欢愉的矛盾中存在,在欲望的海潮中浮沉。加尼埃的死让他明白——死亡可以不是冰冷、凄惨、令人忧惧的结局,而是人的选择。这一选择之中包含的道德意义人们无从评判,但死亡完成了加尼埃作为人的命运,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通过选择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一个人从事的事业与他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区别,人有的只是选择,以及选择的可能性。而福斯卡被历史的循环淹没,看不到选择,也看不到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生命历程,但他无法否认人间将始终有爱恨,有微笑和眼泪,有理想和希望。福斯卡是一个“超人”的存在,他身上属于人的本质却无法消除:他有人的欲望。他怀疑人类事业的虚无,却一次又一次进入历史的轮回中,半是被迫,半是选择。小说中多次出现这样一句话:“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福斯卡身上有着夸父、西西弗斯式的悲剧英雄的气质,他实际上象征着人类顽强拼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人都是要死的》一书的独特之处,于绝望中孕育希望,从虚无中催生意义,在思辨的过程中传递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
注释:
1.波伏瓦著.《人都是要死的》.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57页.
2.波伏瓦著.《人都是要死的》.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78页.
3.波伏瓦著.《人都是要死的》.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09页.
4.波伏瓦著.《人都是要死的》.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37页.
5.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43页.
6.波伏瓦著.《人都是要死的》第27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版.
7.波伏瓦著.《人都是要死的》.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