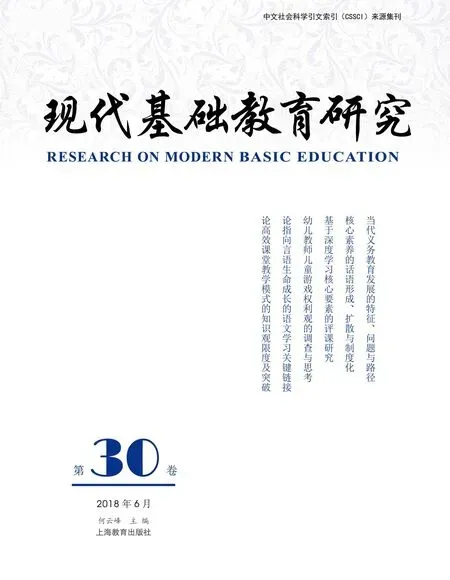绘画作品的深度解读对培养高中生历史解释能力的意义
靳技科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中学,上海 201600)
一、引言
新修订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将“历史解释”作为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一。它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和方法。“历史解释”建立在“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和“历史理解”三大核心素养基础之上,同时为形成正确的“历史价值观”这一核心素养创造了条件。因此,它能综合体现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其提升的关键在于对史料的理解和判断。[1]
随着近代新史学的产生,传统史学一元文本史料体系被打破,建立了新的多元史料体系。[2]英国新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首部《图像证史》中指出,“图像所提供的有关过去的证词有真正的价值”[3],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并且图像以其直观性和丰富性为高中历史教学提供了更为生动、更具思维力的史料,因而日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教学资源,其中尤以绘画为最。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开篇明义:“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工。”[4]绘画是社会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绘画背后隐藏的信息进行探究,对学生而言既是重回历史时空,感知美的旅途,也是重构历史,揭示真相的探索。而这一过程与高中历史核心素养的历史解释能力的要求非常吻合,“历史解释”是要求学生依据史料,理解历史,并理性分析、客观评判,不断接近历史的真相。[5]因此通过对绘画史料的充分运用,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但长期以来,高中历史教学中对绘画史料的使用仅仅局限在表面的印证和感知,缺少对绘画内涵的深入理解和挖掘,也就是缺少深度解读,更没有发挥绘画史料对学生历史理解能力提升的巨大价值。主要的原因在于绘画经过一定“美学创作”,表现的有“真实,也可能是虚构的现象,表现叙事主题,也创造完全抽象的视觉形象”。[6]这种极具艺术气息和主观性的特质,导致绘画长期以来被认为“可感而不可信,可爱而不可言”。但随着艺术史、图像学、艺术社会学等相关研究的发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探索绘画隐藏的秘密变得有迹可循。因此笔者根据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教学实践,尝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探究“绘画的深度解读对高中生历史解释能力的培养”这一论题。
二、综合绘画外部信息,把握绘画的历史“语境”
克罗齐(Bendetto Croce)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指出了历史研究必须重新回到历史事件和时代中,实现对历史的重构。对于绘画而言,也“只有重新返回到那个时代才能实现对作品的解释”。[7]例如图1的《汉代·文翁讲经图像砖拓片》所描绘的场景大量出现在汉代的壁画和墓室的画像砖中,说明当时的人们非常熟悉并推崇画作的内容,能够清楚地知道它表现的是官学的教学场景。而现在的学生则大多认为是宫廷议事或亲友聚会。因此要学生解读绘画,就首先要培养学生将绘画放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观察的意识。

图1 汉代·文翁讲经图像砖拓片
对绘画历史情境的把握重点在于关注绘画的语境,它是一幅绘画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绘画创作的时间、年代、国家、标题绘制者、定制者、用途、版本、大小尺寸等。这些语境能够提示学生绘画创作的年代、国别、主题等相关信息,帮助学生结合相关的知识背景去观察绘画的内容。仍以图1为例,如果给出了画像砖拓片的年代和标题,学生根据课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容,就会很容易理解画面表现的是汉代官学教授儒家经典的场景,进而了解师生的形象、授课的形式、使用的文具等,最终实现对这幅绘画的深度解读,挖掘出绘画的“深义”。[8]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明白,要将绘画放入特定历史中去观察,才能理解绘画表现的内容。
历史的解释以史料为依据,要求有实证意识,因此绘画史料使用的严谨性是一切探讨的基础。但这一点却常常被高中历史教学忽视,不论是教材还是课堂教学中,都充斥着大量没有任何语境的绘画。笔者教学参考的华师大版历史教材中大量的人物肖像都没有标明年代、绘制者、版本和出处。以教材中朱元璋画像为例,学生直观地认为其就是朱元璋的真实样貌,但这只是流传于民间的版本。并且绘画经常被复制,不同版本会有细节上的差异,绘画语境所提示的历史情境只有对原版绘画才有意义。忽视对绘画语境的准确说明,不仅会使学生感知错误的历史情境,进而影响对绘画的理解,也忽略了对学生史料实证意识的培养。
三、聚焦画面细节,塑造绘画理解的历史眼光
相比于文字,绘画能让学生更直接地进入历史的情景。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斯蒂芬·巴恩(Stephen Bann)所说,“我们与图像面对面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3]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并不陌生绘画的直观展示效果。例如常常会用《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像》展示拿破仑的英雄风姿,用《步辇图》呈现盛唐的多民族交流,用《耕织图》说明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景象等。有时候课堂需要这种浏览式的展示,但这仅仅是将绘画作为照片去简单呈现,印证已有结论,既没有发挥绘画的史料价值,也没有培养学生理解绘画的历史眼光。
绘画中呈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历史的证据,而这样的证据要“入乎画内”,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分析才能理解。例如图1的《汉代·文翁讲经图像砖拓片》,在没有任何引导的情况下,学生更多的是以艺术的视角去观看颜色、线条、形状、人物的形态等,而这些信息并非历史的信息。当教师让学生带着“画中反映了哪些历史信息”这样的问题去观察的时候,这幅画的史料价值才开始发挥作用。学生从画面表现的整体情境与课本太学的相关内容形成印证,并进一步通过以历史的眼光观察细节——从师生手握的竹简,学生了解到汉代主要的书写工具;从学生身材大小不一,学生推测出汉代官学无年龄限制;从师生就坐的位置,学生得出汉代官学授课的形式,进而通过推测、求证,分析出汉代尊师的风气等信息。
一幅绘画呈现的细节越多,学生从中理解的历史信息也就越多。例如从北宋的《清明上河图》、清朝的《盛世滋生图》等描绘生活场景的绘画中,学生可以获取人物的衣着、活动、从事行业、建筑、船的造型数量等历史信息;从唐朝的《步辇图》、清朝的《万国来朝图》描绘官方活动的绘画中,学生可以理解民族服饰、礼仪制度等历史文化。这些通过画面直接呈现出来的丰富内容,需要学生带着探求历史信息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才能获得。
图像学大师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将通过观察获得的浅层信息称为绘画的“自然意义”,实际上就是理解画面直接反映的历史信息。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融合了历史眼光、整体把握、细节观察和归纳、理解历史信息的能力。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绘画的审美眼光,也锻炼了想象、推测、辨析、求证等理性分析的态度、能力和方法。
四、考察绘画创作因素,培养绘画解释的多元思维
绘画的难以解读除了本身浓郁的艺术气息外,还在于仅仅通过对画面的观察无法解释绘画表达的含义。因为“图像被不同的人、因不同的原因、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和使用,而这些对于图像所承载的意义至关重要”。[9]因此学生需要“出乎画外”,全方位、多角度探究绘画的隐藏信息。绘画的创作主要受到以下三类主体的影响:
1.绘制者——绘画意蕴的缔造者
绘画的表达直接来自于绘制者的刻画,因而其中映射着画者的知识眼界、价值观、世界观等信息。学生通过对绘制者身份地位、学识经历的考察,能够加深对画面内容的理解,同时揭示绘画更深层次的信息。例如在讲述儒家文化“远播西方”这一部分内容时,可以选用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于1742年左右绘制的《中国婚礼》(图2)、《中国捕鱼图》(图3),来理解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实际情况。

图2 中国婚礼

图3 中国捕鱼图
学生深入画中,却发现布歇笔下的中国难以理解:既像中国又非中国,人物的样貌和服饰以及生活用品和场景很有中国的特点,但又有大量出错的细节。例如图2中新娘的白色礼服,图3中老百姓精致的着装,安逸、和谐氛围等。学生在觉得画面好笑又奇怪的同时,会发问:“为什么画中的中国是这个样子的呢?”教师适时补充“布歇从未到过中国”这一信息,学生综合画面、补充信息和课本知识经过猜测、分析、论证最终做出解释:这些绘画描绘的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画家布歇眼中的中国。它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中国热”,加强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喜爱,但这种交流仍然存在着局限和误解。通过布歇的作品来分析其笔下的中国,学生获得的不仅是知识上的深入理解,更重要的是从“绘制者”这一外部视角分析绘画的思维。
2.赞助人——社会风尚的传播者
1455年,佛罗伦萨的画家内里·迪·比奇(Neri Di Beech)受委托制作一件祭坛画,根据赞助人的要求:“它必须被做成这样:用三块尖形木板,木板尖端上方是一些叶饰和花饰,每两块木板之间是祭坛华盖,华盖下方是壁柱,两侧是没有人像的圆柱,底部是与祭坛画一致的附饰画。”[10]实际上在现代大众传媒和消费兴起之前,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一幅绘画的制作往往还受制于赞助人的要求。他们会参与甚至决定绘画的设计,以此来表达个人或者群体的目的和观念,体现社会风尚。

图4 大使
以“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课为例,仅仅通过文本里的赞颂,学生很难体会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形象。而当时大量出现的肖像画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以德国著名肖像画大师小荷尔拜因的《大使》(图4)为例,教师首先提问:“肖像画一般反映的是谁的意志?”接着让学生带着“两位大使要塑造的是一种怎样的形象”这一问题对画面中的细节进行观察。学生分析出画面的物品以及大使的职业映射出几乎全部的学科知识:算数、几何、音乐、天文、地理、修辞辩论等。进一步得出他们要塑造的是一种通过科学、知识的武装达成的完美形象。而赞助人是社会流行风尚的传播者,他们追求的这一完美形象正是人文主义者的普遍追求。文艺复兴研究者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将这一完美形象称为“全才”[11],印证了画中分析得出的结论。学生通过体察赞助人,深刻地体会文艺复兴时代“人”的自信和荣光。
3.受众——“时代之眼”的塑造者

图5 庄严的圣母子(局部)
艺术社会学家认为,“观众是理解艺术的核心,因为艺术所创造的意义以及它被使用的方法取决于它的消费者,而不是它的创造者。”[9]这里虽然有绝对之嫌,但提出了影响绘画的另一重要因素——受众。绘画的制作不仅要考虑到人们的认知水平、思想观念,同时绘画还会“成教化,助人伦”,对受众有一定的塑造作用。例如汉代画像砖上的《文翁讲经图》既是当时人们极易看懂的场景,同时也有宣传经学、教化百姓的目的。清代画家焦秉贞的《耕织图》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南宋至明清各类耕织图的汇总,描绘的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男耕女织社会,同时也是统治者大力提倡宣传的绘画内容。艺术史家迈克尔·巴克桑达尔(Michael· Baxandall)将每个时代独特的认知方式称为“时代之眼”,指出对绘画受众的关注是解开绘画意义的关键。[12]这也是培养学生理解、评判绘画不可忽视的视角。
“出乎画外”,即从不同视角去分析绘画,不仅是一种多元史学思维的培养,更是对学生解释能力的培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搜集、整理、辨析,以及与其他史料的相互印证,完成对绘画的理解,最终做出理性、客观的解释和评判。当然影响绘画创作的因素还有很多,解读绘画时选择哪个视角以及视角的多少,取决于教学所要达成的目标,也取决于绘画史料所体现的视角。因此,绘画史料教学需要教师对绘画进行筛选并对选用的绘画有详细、全面的了解,这对高中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探究绘画背后的时代特质,达成绘画体悟的情感共鸣
潘诺夫斯基说:“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个阶级、一种宗教信仰或者哲学信念的基本态度——所有这些都不自觉地受到一个个性的限制,并且凝结在一件作品中。”[8]对绘画解读的最高层次是要“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宗教或者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8]。历史解释不仅要求学生理解历史,还要深层次地感悟历史。只有揭示出绘画蕴含的根本精神、根本原则,与画“共忧乐”,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在达成情感共鸣的过程中,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情感都会得到提升。
第一,以时代差异凸显观念变化。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绘画风格和主题,因此通过不同时期绘画的对比,学生会更容易理解时代特征和观念变化。例如学生通过图5《庄严的圣母子》和拉斐尔《西斯廷圣母》的比较,从对差异性的理性、客观分析会发现“文艺复兴时代,神开始走下神坛,走向现实世界,而人的形象开始被关注”,进而体会文艺复兴时代人挣脱神的束缚,开始觉醒的时代精神。
第二,以时代共性归纳社会实质。同一个时代的绘画也会因为相同的孕育环境而拥有相似的特质,学生通过对一个时期大量绘画相似性的寻找、推测、求证,也能够揭示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例如通过审视汉代画像砖大量出现的讲经、孔子问礼、子女尽孝等画面,学生从中归纳出其体现的儒家思想,进而揭示出“汉代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为儒家思想”这一时代特征;学生也会从文艺复兴时代充满喜怒哀乐百态的肖像画中感受到这个时代人的一切都被赞美的时代主题,体悟挣脱束缚后找回自我的狂喜和身为“人”的无限荣耀。
第三,以真假矛盾探求核心精神。绘画是艺术创作,其中必然有虚构的成分,但这也恰恰是解释背后深义的一个突破口。不论是真实还是虚构,对于绘画来说都是“有意为之”,其中必然有原因。学生通过对一幅绘画中虚构或者矛盾之处的考察,同样可以获得时代的本质。例如乾隆年间的《万国来朝图》中:恢宏壮丽的盛世图景中存在大量虚构的朝贡国家和贡品,对这一现象的思考会让学生领悟到盛世梦境与现实余辉相互交织的康乾“盛世”;对图4《大使》中精致先进的科学仪器与角落里的耶稣像、中央摊开的赞美诗的矛盾的思考,会让学生明白文艺复兴时代人神共舞的精神内核,感悟“人”为万物中心的赞歌。
学生在深度解读中把握绘画背后的时代特征既是对绘画的体悟,也是对历史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学生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去审视绘画、解释绘画、评判绘画,与绘画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个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长期的培养。
六、结语
高中历史教学中越来越注重对学生的历史能力和素养的培养,相对于“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家国情怀”等维度,“历史解释”的落实和把握更为不易。但是兼具直观性和复杂性的绘画史料为学生提供了历史情境、历史眼光、多元思维和情感共鸣的试炼场。绘画以其展示历史情境的生动性和直观性激活课堂,在深度解读绘画的过程中,学生对绘画史料的实证意识、观察提取信息的能力、逻辑分析的理解能力、归纳表达的解释能力都可以得到锻炼。绘画是艺术的表达,给学生美的感知力,更是时空留下的痕迹,给学生提供无止境的探究源泉。
但对绘画的解读往往容易导致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诠释,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解读绘画的过程中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避免过度解读,偏离客观分析。就像乔瓦尼·莫雷利(Ciovanni Morelli)说的那样:“如果你想完全认识意大利的历史,那么,请仔细端详人物肖像……在他们的脸上总有那么一些关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东西有待解读,只要你知道如何去解读。”[3]
注释:
①“绘画”一般作动词用,但本文中的“绘画”作名词用,其所指的是“绘画作品”。
②“拓片”本不属于绘画作品,但为了更好地论证“综合绘画作品的外部信息,以把握其历史语境”的观点,本文权且使用图1的“拓片”加以诠释,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 余文伟. “历史解释”的重要性及其意识的养成[J]. 历史教学(上半月),2016,(3).
[2] 雅克·勒高夫,等. 新史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7.
[3] 彼得·伯克. 图像证史[M]. 杨豫,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6.
[4] 巨若星,曹意强. 观念、艺术家与赞助人[J]. 新美术,2013,(12).
[5]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S].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2016:4.
[6] 大英百科“paint”词条[EB/OL].https://www.britannica.com/.
[7] 易英. 图像学的模式[J]. 美术研究, 2003,(4).
[8] 欧文·潘诺夫斯基. 视觉艺术的含义[M]. 傅志强,译,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36.
[9] 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 艺术社会学[M]. 章浩,沈杨,译.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68.
[10] Anabel Thamas. The Painter’s Practice in Renaissance Tuscan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15, 109, 137-138, 140.
[11] 雅各布·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何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31.
[12] Michael· Baxandall, Paintings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taly, 2nd edi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