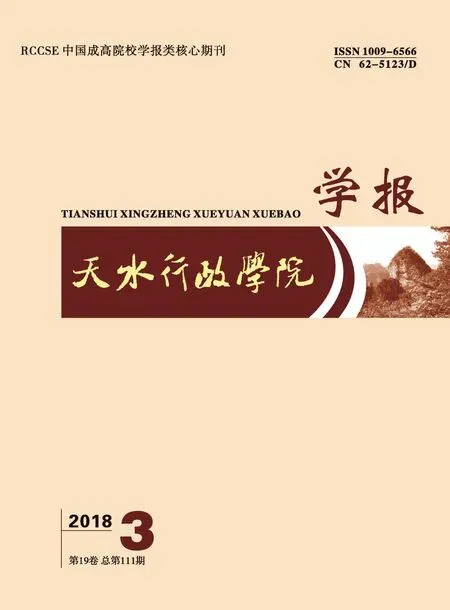基于“春秋决狱”的现代考察
蔡婷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一、“春秋决狱”概述
“春秋决狱”作为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其主要包括“原心定罪”和“亲亲尊尊”这两项司法原则。这两项司法原则不仅使得“春秋决狱”制度能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自身也成为了我国传统司法的两大特色。
(一)“原心定罪”
“原心定罪”,又称“论心定罪”、“原情定罪”,是指在运用儒家经典作为断狱标准时,着重考虑行为人主观动机对定罪量刑的影响,而将客观事实的考虑放到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原心定罪”最直接的定义来自于董仲舒的论述,其指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在董仲舒看来,“春秋决狱”是在既考虑行为的客观事实,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善恶的基础上来定罪量刑的,但在具体适用时在主观善恶的判断上有所偏重。
历史上也存在着许多具体案例来说明董仲舒所提倡的“原心定罪”这一司法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丧夫女改嫁案为例。“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逆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在这个案例中,董仲舒便是运用了主观加客观的“原心定罪”原则加以判定。按照汉律的规定,妻子在死去的丈夫未安葬之前擅自改嫁的,应认定为私为人妻罪,适用弃市的刑事处罚。然而在董仲舒看来,本案中通过考虑客观事实,即甲的丈夫死于海难,尸体无法找回,因此已失去了能够进行死后安葬的客观可能性,不能适用上述汉律私为人妻罪的相关规定。同时,依据《春秋》中夫死无男,更嫁有道的经义道德,并结合甲的主观善恶,判定甲是由于遵循其母的命令进行改嫁,自身并无淫乱之心,客观事实和主观心理均符合儒家经义,因此不构成犯罪,不应受到刑事处罚。可见,董仲舒所提倡的“原心定罪”,因具有的主观加客观的归罪模式,有助于儒家经义更为有效地应用于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在当时的司法判案中应加以广泛应用。
董仲舒所提倡的“原心定罪”的司法原则,是基于主观和客观双重考虑的基础上,并相对偏重于主观判断的入罪原则,然而,由于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及部分司法官吏对于权力的滥用,“原心定罪”中对于主观判断的重视开始走向极端化,逐步发展为仅仅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善恶来认定犯罪,完全抛开了客观归罪要求,使得“原心定罪”这一司法原则逐步成为司法腐败的工具。《盐铁论·刑德》中提到:“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二)“亲亲尊尊”
“亲亲尊尊”源于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亲亲尊尊”分别体现以“孝”及“忠”为核心的宗法秩序,“亲亲”要求维护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讲求父慈子孝、男尊女卑,“尊尊”则要求维护皇权的至高地位,讲求君臣之义,君为臣纲。在“亲亲尊尊”作为“春秋决狱”制度的基本原则加以适用的过程中,体现为“亲亲相隐不为罪”、“子不报仇,非子也”、“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等断案依据,其中最主要的为“亲亲相隐不为罪”及“君亲无将,将而诛焉”这两项原则。
“亲亲相隐”作为“亲亲”之道的核心,在“春秋决狱”的适用过程中得以广泛应用,以养父包庇养子案为例。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杜佑通典》卷六十九)按照汉律的规定,甲明知乙犯杀人罪而帮助其藏匿,应构成犯罪,然而在董仲舒看来,主观方面,甲具有将乙视为亲生儿子的意识形态;客观方面,甲也尽到了身为父亲所应尽的抚养责任,将乙抚养长大,因此养父甲与养子乙在法律上已视为等同于亲生父子的法律关系。儒家经义中的“亲亲相隐”观念适用于养父甲为养子乙隐匿犯罪的行为,因此甲的行为符合儒家经义中“父慈子孝”、“亲亲”的基本原则,不构成犯罪,不需要受到刑事处罚。
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心定罪”、“亲亲尊尊”这两项主要司法原则之外,“春秋决狱”制度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司法原则,诸如“以功覆过”、“家不藏甲”、“为亲者讳”、“继母如母”等。这些原则共同发挥着儒家经义对裁决司法疑难案件的积极作用,最大程度地推动儒法合流及法律儒家化的发展进程。
二、“春秋决狱”的利弊
“春秋决狱”开创了封建社会从真正意义上引礼入律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古至今,文人学者对其的评价可谓是褒贬不一,笔者认为,“春秋决狱”制度可谓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之精髓值得肯定,也有弊之糟粕需以批判。通过多角度对“春秋决狱”的利弊进行分析,有助于全面并深刻地从中汲取能够借鉴于现代刑事活动的精华,并明晰现代刑事活动中应注意规避的危险因素。
(一)“春秋决狱”之利
“春秋决狱”之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春秋决狱”制度确立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入罪模式。董仲舒所提倡的“原心定罪”的司法原则讲求在定罪量刑时既考虑行为的客观事实,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善恶,即既重视“事”的考察,也重视“志”的考察,这一主客观相统一的入罪模式有利于实现司法实践中定罪科刑的正确性。秦朝遵循法家的治国思想,主张人性本恶,在判案时也仅仅依靠客观归罪的司法模式,完全忽视了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判决结果不能服众,司法权威也因此遭到了削减。以秦朝法律中规定的“奴妾盗主罪”为例,秦律中对“奴妾盗主罪”规定了比一般盗窃罪更为严厉的刑罚,若行为人盗窃的是主人的亲人,秦律采用“同居者为盗主,不同居不为盗主”的方式来认定是否构成“盗主罪”,而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被盗之人为主人的同居者,导致审理结果不具有合理性[1]。因此,秦朝所遭遇的三世而亡的结果,便与其所采用的纯客观归罪的断案方式脱不了干系。纯客观的归罪模式实质上是“诛名而不察实”,即“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贤良策二》),而主客观的归罪模式则是“循名责实”,既考虑了行为的效果,即“名”,也考虑了在行为背后所体现的动机和目的,即“实”,使得由此得出的定罪量刑结果具有合理性。同时,“春秋决狱”在要求对行为人的主观善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上述主观心理有了进一步地细化,即区分主观故意和主观过失,并在共同犯罪中根据主观恶性的严重的程度区分主犯和从犯,并处以不同程度的刑法处罚。“春秋决狱”对我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
二是“春秋决狱”制度利用判例补充了制定法的不足。“春秋决狱”主张在制定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却与儒家思想大相庭径时,利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中的故事、案例作为判案的依据,从而引进了以判例作为司法审判依据的新型审判方式。除了儒家经典中的故事和案例,董仲舒将其依据儒家经典中的案例、经文、经义所决断的司法案例汇编成了长达十卷的《春秋决事比》,该《春秋决事比》在司法实践中同样被广泛引用。制定法的本质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现实落后性,在当时社会,采用引例判案的灵活司法模式,有助于对制定法的不足起到补缺和纠偏的作用,解决无法可依或无良法可依的尴尬状态。同时,“春秋决狱”所采用的这种以判例为依据的审判方式,使得以律、令、格、式等为表现形式的制定法与以各式案例为表现形式的案例法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优化司法审判的功能。该以判例为依据的审判方式类似于古罗马时期的“裁判官告令”及现代英美法系所采用的“判例法”制度,体现着我国古代的司法衡平机制,同时,该审判方式对于我国现代司法审判模式的选择也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二)“春秋决狱”之弊
“春秋决狱”之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春秋决狱”制度对于主观动机的过度强调,使得司法适用产生极大的随意性。“春秋决狱”在逐步向法律渗透的过程中,“原心定罪”的司法原则开始走向极端化,统治者及司法官吏逐步将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放在绝对的考察地位,即仅通过对行为人主观动机的判断,而不考虑行为的客观事实,便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司法审判实质上走进了绝对的主观主义陷阱。在绝对的主观主义影响下,若行为人的动机符合儒家经义的要求,则不会被定罪判刑;若行为人的动机与儒家经义的要求相冲突,则会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由于行为与动机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同一行为可以由数个截然不同的动机导致,同一动机也可以对应数种不同的行为表现形式。因此仅对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进行考察,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同时,在完全强调主观动机进行司法适用时,司法过程极易受到裁判者个人好恶及社会人情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裁判者可以以“动机不良”为由,对某些无辜之人予以刑事处罚,也可以“动机善良”为由,使得某些享有特权的人不至受到刑罚的处罚。如此,便使得思想犯罪开始泛滥,冤假错案不断发生,百姓权利遭受了极大的损害,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二是“春秋决狱”制度中适用儒家经义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司法腐败的滋生。“春秋决狱”重视运用儒家经典中的案例、经文、经义作为判案的依据,而儒家经典中的内容基本以文言文的方式进行表述,并且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精炼度,因而,司法官吏在适用儒家经典时,需对其中的内涵进行释义以运用到具体的审判当中。毋庸置疑,解释是一项极富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因此司法官吏在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时,也会产生数种基于各自理解而得到的解释结论,从而导致对同一案件的裁判由于司法官吏的不同,便产生了数种截然相对的结论,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还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对同一案件可以在儒家经典中寻找到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截然相对的内容,也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以“亲亲相隐”及“春秋之典,大义灭亲”为例,前者赋予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的权利,而后者却要求亲属之间相互揭发犯罪以维护正义的实现[2],这两条内涵完全相反的经义导致了在司法适用中,针对亲属相隐的案件,可以被认定为犯罪并需接受刑事处罚,也可以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对于上述两种犯罪结论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司法官吏主观上的取舍,使得行为人的权利遭受了极大的损害。虽然之后上述两条经义之间的矛盾,通过“亲亲得相首匿”法律制度的确立得到了解决,但在儒家经典的众多内容中仍存在许多类似的矛盾尚未解决,为司法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上述适用儒家经义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变相地赋予了司法官吏随意解释和适用儒家经义的可能性,助长了司法官吏进行罪行擅断的气焰。对此现象,《汉书·刑法志》中论述道:“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死则予死比。”
三是“春秋决狱”制度模糊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为了迎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春秋决狱”制度强调儒家经义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性,即强调道德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不断地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渗透到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中,“春秋决狱”制度把儒家伦理道德看做是一套高于法律的适用标准,却完全忽视了制定法所应发挥的功能。道德所具有的空洞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在以道德作为司法适用的标准时,赋予了司法官吏较大的主观能动性,裁判结果因而具有随意性及不公正性。此外,道德对百姓的要求要远远高于法律,若以道德作为司法适用的标准,则会强加给百姓其本不应承担的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损害百姓的基本权利,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法律与道德虽然在内容上有相似之处,但法律毕竟不是道德,道德也毕竟不是法律,“春秋决狱”制度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势必会导致司法适用的随意性,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也会因此而遭到破坏。
三、“春秋决狱”的现代借鉴价值
“春秋决狱”作为一项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特司法制度,其所蕴含的“原心定罪”、“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及自身所具有的利弊影响均对现代刑事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现代刑事活动自身的特点,以探究我国现代刑事活动中应注意的原则及尚待完善之处。
(一)主客观相一致的入罪原则
董仲舒所提倡的“原心定罪”原则,主张采用主客观相一致的方式进行定罪,有助于保证司法认定的准确性,应为现代刑事活动所采纳。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国家及我国均已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引入了主观方面的内容。虽然各国在所应采取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方面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无论是苏联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德日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还是英美的二分式犯罪构成理论,均包含了主观方面的内容。可见,主客观相一致的入罪原则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适用主客观相一致的入罪原则时,要注重平衡主观动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比重,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优化司法定罪活动的作用。以刑事立法活动为例,在进行立法活动时,如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高,则可相对降低入罪的客观标准,以实现司法定罪活动的正确性。以盗窃罪为例,刑法规定,在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情形下,盗窃罪的客观入罪标准不再需要具备数额较大的要求,即存在上述情形,便可认定为盗窃罪的成立。刑法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在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情形下,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高,此时,可以相对降低入罪的客观标准,以实现司法定罪活动的准确性,立法者便在上述情形下删除了数额较大的客观要求。当然,在司法定罪活动中更要遵循上述平衡主观动机与客观事实之间比重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发挥主客观相一致的入罪原则在司法定罪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此外,要注重发挥主客观相一致的入罪原则对于司法量刑活动的影响,在对行为人所应承受的刑罚轻重进行考量时,也应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共同加以把握,以实现公正量刑。
(二)判例法审判模式的引入
判例的引用作为“春秋决狱”制度的一大特色,应为我国现代司法审判活动所借鉴。我国目前采用的是成文法的司法审判模式,虽然最高法院有权力发布指导性案例,各地方高级法院也有权力发布参考性案例,但这些案例都不能起到类似于判例法审判模式下案例的作用,不具有强制适用性,而仅仅是对各地方下级法院的司法实践起到监督指导的作用。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曾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逻辑思维固然重要,但逻辑本身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人类逻辑的产生需基于经验的积累,可见经验较之于逻辑具有更强的重要性。尤其对于讼案的解决,人们普遍会认同某种已有的道德共识,而司法官员从以往的经验中寻找解决方法往往会比创造新模式要保险得多[3]。因此,判例作为先前司法审判活动的经验,对于之后司法案件的审理就显得极为重要。我国从建国之初至今一直以制定法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希冀在短时间将判例法这一审判模式引入我国所有的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想法较难实现。刑法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作为一部最容易对公民权利造成损害的法律,对其适用应最为严格谨慎,并应坚决杜绝司法适用不公正,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产生。因此,可以先在刑事司法领域引入判例法的审判模式,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以依据先前的裁判案例进行定罪量刑,以实现刑法适用的统一性,避免被告人的权利因定罪量刑的不恰当而遭到侵害。通过判例法审判模式在我国刑事审判领域的率先实施,深入探究该模式在我国司法领域全面实施的可行性,并最终决定是否将该模式逐步扩展适用于我国其他司法审判领域。
(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厘清
“春秋决狱”制度模糊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将道德随意凌驾于法律之上,并使之成为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标准,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的治理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缺少了其中一个,都不足以维护社会的和谐及长治久安。对此,孟子论述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在适用二者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时,要注意绝不能将二者无区别地加以混淆并适用。针对如何具体地协调二者的关系,以刑事活动为例:
一是,在刑事立法中可以适当考虑道德因素的影响,使刑法符合人情及公民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治不应当仅仅是冰冷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还应当包容人在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4]。遵循基本伦理道德和人民朴素的法感情的刑事立法才能够被称为良法,才能够得到全体公民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与遵循,此时的刑法才能称之为法。因此,应注重发挥道德因素对刑事立法的积极作用。二是,在刑事司法中,道德因素只能影响司法活动的量刑阶段,而不能影响司法活动的定罪阶段。司法活动中对于犯罪行为人该定何种犯罪及该罪名所应适用的量刑区间的判断,应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在此基础上对于刑罚轻重的具体确定,则可以适当考虑道德因素的影响,对犯罪行为人判处相对较轻或者较重的处罚。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审判中也正积极地适用上述规则,以充分发挥法律与道德对司法审判的有益作用。如“山东辱母案”足以说明道德因素不能影响法庭对被告人的定罪判断。虽然从道德的角度出发,于欢的行为是属于对他人侮辱自己母亲行为的反击,符合孝的标准,不应受到处罚。但根据刑法的规定,于欢的行为虽构成正当防卫,但属于防卫过当的一种,仍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二审法院最终依据法律认定于欢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可见,即使与道德不相符,刑事司法程序的定罪过程也应完全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广州许霆案”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道德因素对量刑阶段的影响。2006年广州青年许霆在取款时偶然发现ATM机存在机器漏洞,之后利用该程序漏洞,在此ATM机上合计取款17.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并判处无期徒刑。后该判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引发公众的质疑,大多数人认为该判决违背了社会常理,许霆的犯罪行为是由于银行机器的性能故障所引发的,却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严重的刑罚,显然违背了公平公正这一基本原则,与公民朴素的法感情不相符。对此,二审在量刑方面做了调整,即鉴于许霆是在发现ATM机出现异常后产生的犯意,与有预谋或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因此改判五年有期徒刑。该判决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了道德因素的影响,做出的判决符合民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法律效果。通过这两个案例的介绍,更充分地说明了在刑事活动中应如何更好地协调并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当然,在其他活动中,我们也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协调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充分发挥法律与道德的能动作用,使其共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四)“亲亲相隐”的现代应用
正如前述,刑事立法需适当考虑道德的影响因素,尊重人性基础,符合经公众世代相承并已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并在刑事制度中加以体现。“亲亲相隐”原则作为儒家传统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人性之本能及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应在现代社会中予以传承及弘扬。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有关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强制作证义务豁免的规定,体现了“亲亲相隐”原则在刑事立法中的运用。然而,对于《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我国刑法仍将包括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内的近亲属包含在该罪的适用主体之中。将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标准作为全国公民普遍的行为准则在刑事立法中加以规定,使得法律脱离于最基本的人性而制定并存在,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的权威性不应仅仅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加以保障,法律规则自身的合情合理性也是增强法律权威性的一大重要途径。同时,上述刑法规定也违背了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因此,建议修改我国刑法中有关窝藏、包庇罪的相关规定,即将“亲亲相隐”的儒家思想融入到该罪的刑事立法中,以实现国家利益与民众朴素情感需求的平衡,并有助于维护家庭和睦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健康。
具体而言,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将“亲亲相隐”的原则更有效地运用于现阶段的刑事立法中:第一,“亲亲相隐”的适用主体应是包括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内的被告人的直系血亲、兄弟姐妹及同居的其他亲属,而不能过度地限制该原则的适用主体,导致与对窝藏、包庇罪进行修改的初衷相违背;第二,“亲亲相隐”的原则应仅适用于提供处所、财物以帮助犯罪行为人逃匿的窝藏行为,而不能适用于包括积极地作假证明或者诬陷他人进行包庇的行为在内的其他积极行为;第三,“亲亲相隐”的原则应不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严重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犯罪及其他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以防止因为亲属的窝藏行为而导致的不可挽回的危害后果;第四,适用“亲亲相隐”原则的窝藏行为,其动机必须是出于真正的爱护亲人这一纯粹的目的,而非基于获取非法利益或者掩饰自身非法行为的邪恶动机。通过上述方式,将“亲亲相隐”的原则体现于现行刑法有关窝藏、包庇罪的规定之中,充分体现了道德因素在刑事立法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了现代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平衡,也是我国立法朝着人性化轨道发展的又一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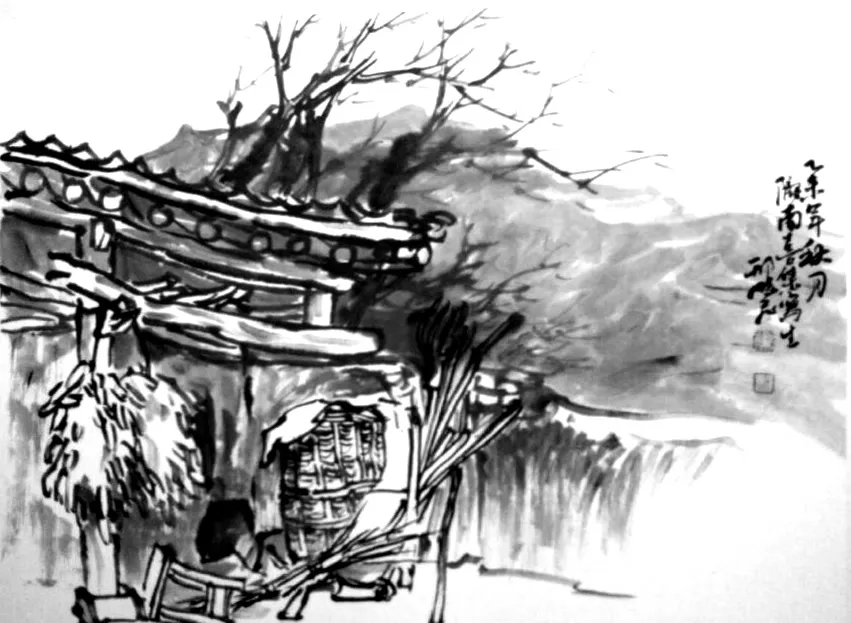
本期插图均为邢鹏飞国画作品
[1]方庆淼.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新辩[D].西南政法大学,2013.
[2]于涛.以史为鉴——对“春秋决狱”的研究[D].山东大学,2011.
[3]孙倩,赵晓耕.春秋决狱——从实践出发的审判思路[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3):71.
[4]李忠良.“亲亲得相首匿”法律价值析[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