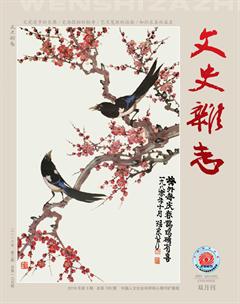关于《诗经》的作者
闻衷
《诗经》由于是通过采集汇编成书,而当时对著作权又不甚重视,以致使各篇作者一直处于云遮雾罩中,难见庐山真面目。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诗序》那里,这些似乎大多不成问题。例如《关雎》,《诗序》说:“后妃之德也”;《葛覃》,《诗序》说:“后妃之本也”;《卷耳》,《诗序》说:“后妃之志也”;《七月》,《诗序》说:“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鸱鹗》,《诗序》说:“周公救乱也”……在《诗序》看来,《诗经》的作者并不成问题,至少是可以寻得出大致身份的——其中以王公贵族大臣或后妃居多。《诗序》的这种推断或推断方式,遭到古往今来的不少学者(特别是现代学者)的猛烈批评。现代学者中,以郭沫若对《诗序》关于《诗经》作者的看法批评最力。他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里这样写道:
《诗》三百篇的时代性尤其混沌。
《诗》之汇集成书当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而各篇的时代性除极小部分能确定者外,差不多都是渺茫的。自来说《诗》的人虽然对于各诗也每有年代规定,特别如像传世的《毛诗》说,但那些说法差不多全不可靠。例如《七月流火》一诗,《毛诗》认为“周公陈王业”,研究古诗的人大都相沿为说,我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但我现在知道它实在是春秋后半叶的作品了。就这样,一悬隔也就是上下五百年。
陈子展也有相似的看法。他在《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里说:“凡诗一首,必问作者为谁?作者在何时?作者在何地?为何而作?《诗》三百中经《序》指明者大部不甚可靠。”
蒋伯潜、蒋祖怡在《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里亦对《诗序》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传统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大多数是揣度之辞,不能信以为实”。他们特别举出《关雎》与《卷耳》两首诗作为批判的靶子。二蒋认为,《关雎》明明是一首写恋爱成功而结婚的诗,“可是《诗序》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乐得贤女以配君子,以为是后妃所作;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宫中人所作,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之后‘太姒;《鲁诗》《韩诗》之说,则又谓系刺后妃失德,君王晏朝而作;余如张超《诮青衣赋》以为是毕公所作,罗泌《路史》以为是暴公所作,皆云当周康王时。王应麟《困学纪闻》又谓是周宣王时人作,而皆以为是刺诗”。只有清人崔述《崔东壁遗书》之《读风偶识》“以为是‘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比较合于情理。”
讲到《卷耳》,二蒋指出,这其实是一首很妙的思妇之诗(写丈夫远行,妻子思念之苦)。可是《诗序》却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朱熹也认为是“后妃因君子不在而思念之”。对此,二蒋说:“试问后妃为什么要去采卷耳?求贤是国君之责,何劳后妃费心?后妃居深宫之中,如何能‘求贤审官?而且后妃对于所求之贤,竟如此体贴而称之曰‘我,不更狎亵了吗?以思妇之辞而谓为后妃所作,自然不合情理了!总之,我们倘为旧说所囿,则全部《诗经》将全为捕风捉影的解说所蒙,无从廓清整理了。作《诗经》的都是些无名的诗人,时代又隔得太远了,本事如何能查考得清楚呢?”
二蒋还指出:“诗序对于《郑风》中的诗,见有‘仲字便以为是祭仲(春秋时郑大夫,‘祭读如蔡),见有‘叔字便以为是共叔段(春秋时郑武公之少子、庄公之弟,共音恭,地名,段所封之邑),余则大半都说是‘刺忽(郑庄公太子)。似乎郑国除了祭仲、共叔段、太子忽以外,更无他人;郑诗人除了美刺这几个人之外,便无别的情感,这不是很幼雅、很可笑吗?(朱子的《詩集传》比《诗序》已高明得多,可是又另有其凿空武断之处,亦不尽信。)”
尽管现代学者在《诗经》著作权问题上对《诗序》的批评从总体上看是不错的,但也应看到,就《诗经》的少数篇章而言,《诗序》的结论则并无臆断,而是言之有据,即如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所言:《诗经》作者“极小部分能确定”。这极小部分能确定或能大致推测出身份的作者可分作两种情形:一是《诗经》原诗中就已标明的;二是在《左传》《国语》《史记》及《尚书》里给有说明的。我们所说《诗序》在少数篇章上对作者或作者身份的判断乃言之有据,就是讲的这两种情形。
一、《诗经》标明的四位作者
在《诗经》原诗中得以标明作者的,一共有四位,他们是:
1.家父。《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
2.孟子。《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3.吉甫。《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4.奚斯。《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长且硕,万民是若。”
这五首诗,是《诗经》中仅有的几首标明作者的诗。其中“家父”,郑玄《毛诗传笺》认为系周大夫之字。其在鲁(申培)、齐(辕固生)、韩(韩婴)三家诗中均写作“嘉父”。《春秋·桓公八年》曾记“天王使家父来聘”。东汉何休注《公羊传》说,家为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称字,不称伯仲。还说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诗序》说:“《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于平王之末,书尹氏卒,见权臣之继世也。于景王之后,书尹氏立王子朝,见权臣之危国也。《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讥。”在早,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已提出疑问:“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岁。此诗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则八十五年矣。韦昭以为平王时作。此时不应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孔颖达又说:“古人以父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父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今人陈子展认为:孔颖达疏其实“是肯定此诗作在幽王之世。古人父子同字,求车之家父未必是作诗之家父也。”(《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我们还注意到,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嘉父则与谭大夫、寺人孟(子)同居“九等之序”中的第四等——“中上”之列。蔡邕有《朱公叔谥议》云:“周有仲山甫、伯阳父,嘉父,优老之称也。”所以叶舒宪认为:“家(嘉)父并非指父亲,而是男性长辈的美称。他作此诗的目的在于批评周幽王时把持朝政的尹氏不恤国事,用‘危言耸听的呼告劝谏他回心转意,以畜养万邦为重。诗中末章虽言‘以究王,但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控告尹氏来刺幽王的。”(《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叶氏这里所识,正合《诗序》对《节南山》的题解:“家父刺幽王也。”
至于孟子,则当然不是战国时代的儒家大思想家孟子,因为在他的前面冠有“寺人”一词,这就是《巷伯》的作者、阉人孟子。《诗序》说:“《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巷伯,奄(阉)民兮。”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认为:“《序》以巷伯为奄官,则巷伯、寺人为一人。”又有刘敞《七经小传》指出:“孟子仕人,以辟(避)嫌不审,为谗者谮之,至加宫刑为寺人,故作此诗。诗名《巷伯》者,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
吉甫是《诗经》中唯一注明作有两首诗(《崧高》《烝民》)的人,为周宣王时代(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的尹,史称尹吉甫,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辅弼大臣)。据《诗经·小雅·六月》等记载,当时狁迁居焦穫,进攻到泾水北岸。吉甫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率军反攻到大原;后又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赋。其遗物《兮甲盘》(金文)。吉甫还是当时有名的大诗人,有《诗经》所存《崧高》《蒸民》为证。这两首诗,《诗序》均作:“尹吉甫美宣王也。”对《崧高》,朱熹《诗集传》说:“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谢,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朱熹《诗序辨说》又指出:“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诗,因可以见宣王中兴之业耳,非专为美宣王而作也。”对《烝民》,朱熹《传》说:“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
关于吉甫为《崧高》《烝民》二首的作者,因为是原诗载明了的,所以历来都予以首肯,无甚争论。但《诗序》却就此生发开来,将《大雅》中的《韩奕》《江汉》的著作权也归于吉甫名下,并均以为是“美宣王”之作。由于《诗序》不能提出较为有力的证据,所以也难令后人信服。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台湾学者李辰冬(其研究《诗经》数十年,有《诗经通释》《诗经研究》《诗经研究方法论》等专著行世)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去探寻吉甫率军东征西讨的历史足迹,“发现”《诗》三百都有史实依据可征。李辰冬更为重大的“发现”还在于:“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李辰冬因此而提出,《诗经》乃吉甫在从周宣王三年至幽王七年(公元前825~公元前775年)50年间一人所作。(见阿城:《轻易绕不过去》,《读书》,1993年第8期)
李辰冬此论不啻于向《诗经》学界摔出一颗重磅炸弹。但由于其推测成分多于实证分析,这颗炸弹虽然惊世骇俗,却不至于产生会令先秦文学史与西周史推倒重写之虞。
奚斯即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时的鲁大夫公子鱼。《左传·闵公二年》记:“共仲奔莒,乃人,立之。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使公子鱼请。不许,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声也。乃缢。”文中共仲即鲁庄公之弟庆父。庄公死,子般立。庆父杀子般立闵公,后又杀闵公而奔莒。齐大夫仲孙湫去鲁吊问,回来对人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鲁庄公少子申在季友帮助下立为国君,是为鲁僖公。季友又贿赂莒国送还庆父。庆父回鲁后到达密地,自知罪孽深重,又存侥幸心理,请公子鱼(奚斯)向季友求情赦免死罪,但遭到季友拒绝。公子鱼哭着回去向庆父报告。庆父远远地就听到了,长叹道:“这是奚斯的哭声啊!”于是就上吊自杀了。此事件也见载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其中也有奔波于慶父与季友之间的奚斯。
《诗序》说:《閟宫》是奚斯“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其实,僖公复国全靠季友之功,至于僖公本人,“既无文德,亦无武功”(黄中松:《诗疑辨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实不当颂。而奚斯居然以八章之巨,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这一则属于传统社会里一般臣子的媚上尊君的表现,二则也反映出奚斯心中有病,企图将功折罪的阴暗心理。毕竟,他曾听命于鲁难的罪魁祸首——庆父,在鲁国那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大动乱的尾声中扮演了一个不很光彩的角色。
二、其他先秦文献记载的作者群
除家(嘉)父、孟子、吉甫、奚斯以外,《诗经》还有一些篇章的作者姓名或身份是可以通过其他先秦文献的记载查找出来的。
1.许穆夫人作《载驰》
《左传·闵公二年》说:“初,(卫)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许穆夫人赋《载驰》。”按《载驰》在《鄘风》。
2.公子素作《清人》
《左传·闵公二年》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按《清人》在《郑风》,“郑人”指郑文公,娶江氏所生之子公子素(或称公子士)。《左传·宣公三年》有记,作公子士。《诗序》说:“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境)。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由于《诗序》之说在《左传·闵公二年》里得以印证,所以古往今来对此无甚争议。诚如陈奂《诗毛氏传疏》云:“此诗为公子素所作。《汉书·古今人表》有公孙素,与郑文公、高克列下上(笔者按:查《汉书·古今人表》,郑文公实列中下,公孙素则与高克并列下上),当是一人。”
3.卫人作《硕人》
《左传·隐公三年》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硕人》在《卫风》。魏源《古诗微》则不仅肯定《硕人》系卫人所作,并且进而指出系庄姜之傅母(古代贵族家庭保育、辅导子女的老年男女)所作。他说:“《硕人》,庄姜之傅母所作也。姜交(交姣古通)女子,始往,操行衰情,淫佚冶容。傅母谕之乃作诗,砥厉女以高节:家世尊荣,当为民法则;子之质聪达于事,当为人表式;仪貌壮丽,不可不自修整;衣锦褧裳,饰在舆马;是不贵德也。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陈子展说,魏源之论出自《列女传·女仪篇》,属今文鲁、韩二家之说。但陈子展也认为:“《硕人》,庄姜始嫁,人见其嫁时及其嫁后短时期之幸福生活而作。作者熟谙其时奴隶主贵族剥削生活之享受,殆非民间歌手。”(《诗经直解》)
4.秦人作《黄鸟》
《左传·文公六年》说:“秦伯任好(按:即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也有类似记载:“三十九年(公元前621年),缪公(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黄鸟》(在《秦风》)之诗,既是秦人对残暴的奴隶社会之殉葬制度的谴责,亦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作为人的自尊自主意识的觉醒。它昭示着奴隶社会的行将就木,呼唤着更加进步的新时代的来临。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篇》里所写到的:
最重要的材料是《秦风·黄鸟》一篇。秦穆公死的时候使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虎殉葬,秦国的人哀悼这三良,大家都呼天哭泣,不惜以一百人来掉换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殉葬的习俗除秦以外,各国都是有的。(就是世界各国的古代也都是有的)不过到这秦穆公的时候,殉葬才成为了问题。殉葬成了问题的原因,就是人的独立性的发现。……同一是关于秦穆公的文章,《书经》最后一篇有《秦誓》。……这一篇文章不一定就是秦穆公做的。古人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有古事古言都是出于史官之手,也就像现在的文牍报告都是秘书幕僚做的一样。所以尽管《秦誓》里面把人的价值提到最高点:说到“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而穆公自己死的时候偏偏要三良从葬。这不一定是秦穆公自己的矛盾,这只是时代的矛盾的反映。秦穆公的时代应该是新旧正在转换的时代,这儿正是矛盾的冲突达到高潮的时候。像这样,《秦誓》在高调人的价值,《黄鸟》同时也在痛悼三良。所以人的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正是新来时代的主要脉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秦哀公作《无衣》
《左传·定公四年》说:“申包胥如秦乞师……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无衣》在《秦风》。《左传》的这段记载,就是著名的“申包胥哭秦庭”故事,亦见载于《史记·秦本纪》。清初王夫之《诗经稗疏》说:“《春秋》申包胥乞师,秦哀公为之赋《無衣》。刘向《新序》亦云然。……为之赋云者,与卫人为之赋《硕人》、郑人为之赋《清人》,义例正同,则此诗哀公为申胥作也。……孔子删《诗》在鲁哀公十二年以后,凡前此者皆得录焉。秦哀公有救患之义,申胥立誓死之诚,故节取之,存而不删。”
6.周公作《鸱鹗》
《尚书·金縢》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鹗》。王亦未敢诮公。”《鸱鹗》在《豳风》。对《尚书》的记载,《诗序》总结说:“《鸱鹗》,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鹗》焉。”但古人对此颇为怀疑,魏源《诗古微》说:“《七月》《鸱鹗》皆邠(豳)国旧《风》也。”《朱子语类》也说:“问《鸱鸮》诗,其词艰苦深奥,不知当时成王如何便即理会得?”但朱熹笔锋又一转:“曰:当时事变在眼前,故读其诗者便知其命意何在。自今读之,既不及见当时事,所以谓其诗难晓。然成王虽得此诗亦只是未敢诮公,其心未必能遂无疑。及至雷风之变,启《金》之书后,方始释然开悟。”陈子展则认为,即令《鸱鹗》同《七月》一样,属豳国旧《风》(因《鸱鹗》托为小鸟哀呼鸱鹗而告之,如寓言、如童话、如禽言诗,显示出民间歌谣的特征),可能系“周公述而不作,或述而加工,仍当视为周公作品;不则未必流传至今也。”(《诗经直解》)
7.周公或召穆公作《常棣》
《国语·周语中》记周襄王十三年(鲁僖公二十年,即公元前640年),周大夫富辰谏阻襄王讨伐姬姓郑国:“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务)。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郑在天子,兄弟也。”周文公即周公旦。不过,《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记与《国语》则有不同:“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即管叔、蔡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按召穆公(即召伯虎)为召公奭(即召康公)后代,名虎。周厉王暴虐,“国人”围攻王宫,他把太子靖藏匿在家,以其子替死。厉王死后,他拥立太子继位,是为周宣王。据《诗经·大雅·江汉》等记载,召穆公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并奉命经营谢邑(今河南唐河南),以封申伯。遗物有《召伯虎(敦)》(金文)。
上举《国语》与《左传》所引之诗,皆出自《小雅·常棣》,但两书一说作者为周公旦,一说为召穆公。对此,三国吴人韦昭注《国语》说:“文公之诗者,周公旦之所作《常棣》之诗是也,所以闵管、蔡而亲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御,禁也,言虽相与佷于墙室之内,犹能外御异族侮害己者。其后周衰,厉王无道,骨肉恩阙,亲亲礼废,宴兄弟之乐绝,故邵(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而合其宗族于成周,复循《常棣》之歌以亲之。郑(众)、唐(固)二君以为《常棣》穆公所作,失之,唯贾君(即贾逵)得之。穆公,邵(召)康公之后穆公虎也,去周公历九王矣。”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也支持韦昭之说,称:“郑答赵商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所云诵者,指此召穆公所作诵古之篇也,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郑辄言召穆公事,因左氏所论而引之也。”今人杨伯峻注《左传》则以《左传》之说为是,认为《常棣》乃召穆公所创作。其理由是:“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周公则诛管、蔡二叔,是非周公之所作。说参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六年《雕生》(即《召伯虎敦》)跋。成周在西周本为纠合诸侯发号施令之所。《逸周书》有《王会篇》云‘成周之会。《令彝铭》云:‘隹(唯)十月月初癸未,明公(笔者按:即鲁公伯禽,周公旦长子,鲁国始祖)朝至于成周,(出)令云云,尤可证。”
8.卫武公作《抑》
《国语·楚语上》记左史倚相语说:“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韦昭注说:“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之曰‘抑。《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儆也。”这里的卫武公,即卫僖公之子,名和,称共伯和(共是卫的别称),公元前812~公元前758年在位。魏源《古诗微》说:“《抑》,卫武公作于平王卿士之时,距幽没三十余载,距厉没八十余载。尔、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词,而刺王室在其中矣。”“《史记》言卫武公将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为公,则知诗作于为平王卿士之时,八十既髦之后,当东迁之始,‘变雅之终,不但非刺厉,并非刺幽。”陈子展《诗经直解》评论魏源之说道:“魏氏论此诗用‘韩说,肯定诗作于平王之世,自戒即以刺平王。可为定论矣乎?卫武公使人日诵是诗于其侧,时年九十有五,至平王十三年(公元前758年)卒。计其得年当在百岁左右也。”
9.周公作《时迈》
《国语·周语上》说,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周文公即周公旦。他所作《颂》诗即《时迈》(在《周颂》)。韦昭注曰:“武王既伐纣,周公为作此诗,巡守、告祭之乐歌也。”但《左传·宣公十二年》则将《时迈》的著作权归于周武王名下,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櫜弓矢。我求懿得,肆于时夏,充王保之。”不过,孔颖达《毛诗正义》则支持《国语》的说法,指出:“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周公述其事而为此歌焉。”
三、当代学者推测的作者队伍
寻找《诗经》的作者一直是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即至当代,仍有不少作者乐此不疲。他们不满足于《诗经》作者“极小部分能确定”的状况,以执著的精神进行着顽强的探索。这之中,堪以青年学者叶舒宪为代表。
1.寺人是《雅》《颂》的主要作者
宋人王安石在《字说》里曾根据《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句并结合许慎《说文解字》关于“诗”乃“言”与“寺”合成的象声字(形声字)之说提出:“诗为寺人之言。”以后,明人何楷在《诗经世本古义》里也顺着王安石的思路,把“诗”字解为会意字,即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所转述的:“‘志字是‘之‘心合成的,即‘心之所‘之,人而有‘志,志之于‘言,则为‘诗。”(孟庆文译:《中国文学思想史》[日]青木正儿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在周代宫廷中,寺人属小臣之列,由于寺人是被去势(去掉生殖器)的阉人,所以得以“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周礼·天官·寺人》)《诗经·秦风·车邻》:“未见君子,寺人之令”。讲的就是寺人握有引见君王的大权。寺人长期陪伴在君王身旁,出入于朝堂后庭之间,目睹政事兴衰、宫闱变故,一定有良多体会、良多感触。王安石、何楷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形,从而提出《诗》为寺人表心聲之作的推论。
在此基础上,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里提出,在先秦典籍中,“诗”“志”是通用的,“志”其实乃“寺”的假借,所谓“言志”也是“言寺”的假借;“寺”的本义即为“祭礼主持”,而“诗”原来是一种“具有祭政合一性质的礼仪圣辞”。从这种认识出发,叶舒宪认为:
尽管现存305篇中,明言由“寺人”所作的诗只有一首,但可以推知《诗经》中雅、颂部分的众多作品均可能出自寺人之手。他们原来是宗教典礼的主持者,王政的神圣监护者。他们在正规场合赋诗献诗,本有代神传言的性质。只因王道衰微之后,寺人的监督作用表现为歌谏诗谏,这也许就是雅诗中大量抨击王政的政治诗的发生背景吧。(《诗经的文化阐释》)
叶舒宪还认为,作为儒家思想家的孟子所叹“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之“诗”,主要指的就是寺人所作之《雅》《颂》。但是进入东周以后,寺人(阉人)“已被男性中心文化视为与妇人同列的异己者了,他们的诗作当然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公众心目中的‘有法度者。由此可知,寺人地位的跌落是随着西周王权与神权的衰微而发生的,圣诗传统也由此而濒于灭亡。我们可以补充孟子的话说:王者之迹熄而寺人衰,寺人衰而诗亡。”(《诗经的文化阐释》)
2.尹人也是《颂》和《雅》的作者群
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里还认为,除了寺人以外,“尹人也是《颂》和《雅》诗的最合乎情理的作者群”。他的理由有三:
第一,“尹”同“寺”一样,原也是祭政合一、僧官不分的原始时期所传下来的主祭司政者的职称。以后,随着教权衰微而王权兴盛,尹人集团中一部分上升为王者之师或王朝卿士,一部分则沦落为民间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在政权中地位突出,为天子股肱之臣(在《雅》中除个别篇章外多得到颂扬),又继承和发扬了先世知识特权的传统,因此,“他们的存在与诗的发生发展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大雅》中有不少诗,如《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等都描写有王在宫庙册命或赏赐臣下的场面,这些诗实际都具有仪式歌辞的性质;“而主持仪式者正是介于王与臣下之间的尹氏”,所以尹氏应“是这类仪式歌的初始作者”。
第三,《崧高》与《烝民》明白无误地标明了吉甫为二诗的创作者。“吉甫全名为尹吉甫,属尹氏一族中的知名者”。以此可以推测出:“《雅》诗部分的作者群主要为更多的不知名的尹氏。”
3.盲官是《诗经》的传诵与加工者
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里还提出,如果说寺人、尹人等是《诗经》(主要指其中的《雅》《颂》)的主要作者群,那么,作为周王朝宫廷乐队(据《周礼·春官》统计共有306人之众)的盲官们(包括瞽、师、瞍、矇)则是《诗经》的主要唱诵与传播者,这可以以《国语》和《周礼》的记载为证。《国语·周语上》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礼·春官》说:“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叶舒宪认为,周室的这支庞大的盲人乐队的工作不外乎乐器演奏、唱歌与诵诗三项。就诵诗而言,盲官们一是以诗“讽谏劝上,为统治者下察民情风俗和政教得失提供咨询依据”;二是以诗“记诵国史世表或祖宗谱系,充当神话历史的活的存储记忆库和传声筒”。
叶舒宪在其“瞽矇传诗”说的基础上,又进而认为上古盲官还是“声教”的创始人(“以有韵的或合乐的歌诗传播礼乐教化,自殷之瞽宗至汉之乐府,一千多年间不绝如缕”)与中国文学的早期奠基者。他指出,盲官们的口耳相传的方式“必然反作用于诗歌的语音形式,形成上古诗体用语简朴而音律繁复的突出特征。诸如双声、叠韵、重言等见于《诗经》的音声特色,无一不与盲诗人高度发达的听觉美感相对应,同时也为后世文学修辞技巧在语音方面的讲究开辟了道路”。叶舒宪这里不仅看到了上古盲官(主要是周代盲官)的传《诗》之功,而且也注意到盲官们对《诗》的语言加工与修辞润色。
4.瞽工是《风》的作者队伍
又有萧甫春在《〈国风〉原是祭社诗》(1997年桂林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一文里提出:先秦典籍里的瞽人、瞽工并非盲人乐师。因为“瞽”在那里面的意思即“白眼”,如同后来《晋书·阮籍传》里阮籍藐视“礼俗之士”而“以白眼对之”一样。这也就是《韩非子·八说》里的“瞽工轻君”(轻视国君)的意思。萧甫春认为,瞽工是《诗经·国风》的真正作者。他针对朱东润关于《国风》大半不出于民间,而“多为统治阶级之作品”;因为那个时代“劳苦大众”不具备“文学上必需之条件”(《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读诗四论》)的论述发表看法说:“《国风》既非出于民间,也不是‘统治阶级之作品”,而是‘瞽创作的祭社诗。”萧甫春认为,关于“瞽”为诗的观点,是有典籍记载依据的。他指出:第一,“史为书,瞽为诗”(《左传·襄公十四年》),不仅说明了“瞽”会作诗,而且还像“史为书”一样,瞽是专业的诗人;第二,“帅瞽登歌”(《周礼·春官》)“瞽,乐太师”(《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又说明“瞽”是专业的歌手;第三,“瞽献曲”(《国语·周语上》),“属瞽史,谕书名”(《周礼·秋官》),“明习文字”(章炳麟:《官制索隐》),更说明“瞽”具备着音乐上和“文学上必需之条件”。
尽管萧甫春对“瞽”的解释有些牵强,但他关于“瞽”为《风》的作者的推论,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