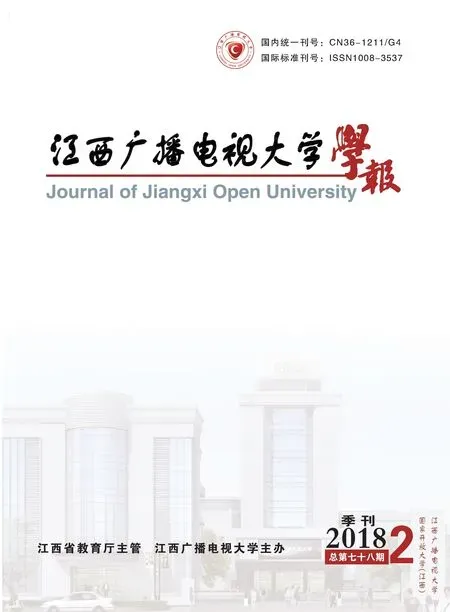卢西恩·弗洛伊德化巧为拙的形式语言探析
郑炜,王安娜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a《.职教论坛》杂志社;b.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330038)
我们知道,绘画研究的本质在于研究其形式语言,也就是常说的绘画语言,要研究形式语言就必须对美术史上曾出现过的所有造型语言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定义其造型语言的价值和难度。有的画家的语言确实在美术史上未曾有过,但难度不大,甚至小孩都能画得出,那么他的语言就创新而言意义不大。还有的画家语言难度很大,需要经过长年累月地精打细磨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但在美术史上早已存在过,那么他的语言又不具备创新价值。卢西恩·弗洛伊德之所以能成为当今时代著名的油画大师,就是因为他的造型语言同时具备了价值和难度这两个关键点,可谓是给“将死”的现代艺术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利用反传统的技法,反而给无路可走的传统语境重新开启了新的探索空间,其形成的绘画语言风格和画面风格可以概括为“化巧为拙”。
一、拙之美
弗洛伊德在长期的绘画语言的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关于是选用古典罩染法还是直接书写式的画法,弗洛伊德是经过一段时间探索的,对此他说:“我曾拥有过一幅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画。26岁那年我说服父亲为我买了这幅画,画面是一朵花,背景是漂亮的绿色颜料,但后来我就对那幅画厌倦了,我认为马克思·恩斯特不知道如何用笔去‘画’。在某种程度上说,那幅画不是那种需要以素描作为基础的作品,是‘涂’出来的。我觉得人们还是可以从作品里看出画家会不会‘画’(指用素描的方式),还是只会像印脚印那样地‘涂’。”[1]14很显然,他的绘画语言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的,而这个关键点是26岁之后在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斯特的“一朵花”作品之后。
在绘画语言的处理上,弗洛伊德不追求工整平滑的妙笔丹青,而是一反常态,逆向创新,追求一种愤怒的笔触,形成了以拙压巧、外刚内柔、粗而不俗的独特风格。他在长期探索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风格,即以粗糙的方式表现出一切的细节。作为画家,弗洛伊德的风格是独特的、不重复前人的、完全创新的。需要说明的是,弗洛伊德的此“化巧为拙”与中国画家徐悲鸿曾提出过的“宁拙勿巧”不属同一种概念。建国初期徐悲鸿针对素描基础教学曾提出过“三宁三勿”说,即“宁脏勿洁”、“宁方勿圆”与“宁拙勿巧”。“宁拙勿巧”的大致意思是:我们在学习素描的时候,不要拘谨,要放开胆子来画,要从整体把握形体出发,才不易陷入局部的细抠。事实证明在这样的观察方法之下画出来的绘画画面就会有一种粗放的效果,整体感很好。相反,如果仅仅关注局部细抠,其绘画画面效果虽然是精巧的,却失掉了整体感。所以徐悲鸿在基础素描教学中强调画面的宁可笨拙,也不要精巧,其本质意思就是宁可不管局部,也得要抓住整体。
然而,卢西恩·弗洛伊德的“化巧为拙”则完完全全不是这个概念,它与徐悲鸿的“宁拙勿巧”的区别在于:
第一,弗洛伊德的技艺已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正所谓艺高人胆大,其不拘一格、率真自然的用笔用色,证明他技法上真正达到了一种从无法到有法,再从有法回到无法的清纯境界,是对技艺法度的超越。这远远高于“宁拙勿巧”的层次,换句话说,“化巧为拙”就是从“熟能生巧”到“巧极为拙”演变过程的一种全新的提炼。
第二,弗洛伊德这种笨拙艰涩的笔触是与他苦涩的生命历程和体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名犹太人,在世界大战中目睹同胞们遭到德国军队那种灭绝人性的屠杀,使弗洛伊德幼小的内心遭到来自现实世界最沉重的打击,所以他的绘画无论从主题到形式,通通都在揭示这种真实,毫无矫饰和雕琢,甚至有意堆砌人物身上的笔触和颜料,从而强调这种真实。而追求这种苦涩的真实,才是形成他的绘画语言的核心动力。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他早期作品中带有的精巧敏感渐渐演变到晚期的“拙之美”,这个变化过程就叫做“化巧为拙”。
然而,弗洛伊德的“拙之美”和一般意义上的拙之美还不太一样。区别在于:平常笨拙的笔触,最多涂上一至两遍就结束了;而弗洛伊德的“拙”属于强迫症性质的,他常常用数个月的时间,无数遍地反复多次涂抹出他自己独特的“拙”。所以才会有种琳琅满目、浑然天成的视觉冲击力。“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绘画都比较实在,基本是地毯式轰炸一般地画。弗氏的画面不太注重虚实,他的油画像地毯式轰炸,起码轰炸两遍甚至若干遍。”[2]弗洛伊德曾说:“当一幅画与质量扯上关系时,也许一辈子的时间都会嫌不够的。”可贵者胆,所要者魂。正是在这种与画面做高强度的、反复搏击的审美观念的长期统治下,以至于弗洛伊德不得不感叹“拉斐尔笔下的圣母轻飘飘。”[3]
有经验的画家知道,灵巧的笔触一定是用笔飞快地画出来的,那么与灵巧相反,朴拙体现在用笔上就是要慢。各种不同的颜料在不断地、但又以极慢的速度被涂抹到画布上去[1]132。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画一幅画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对此弗洛伊德的纽约代理人、画商阿奎维拉在一次受访时,谈到了他给弗洛伊德当模特的情景。弗洛伊德每天作画长达十几个小时,而且这位画家习惯于同时进行三到四张画作创作,分白天与夜晚两个时间段轮流进行(各请两班模特儿),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画一拨,再一拨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画到凌晨2点,一周七天,天天如此,循环往复。有的模特需要在他面前坐(或躺)上几个月,甚至几年[4]。
不入魔,不存活。在这种反反复复地、高密度地“持久战”之后,留在“战场”上的是无数鼓起来的笨重粗暴的颗粒,与通常油画那种平整、均匀的画面截然相反——这,便是弗洛伊德反向艺术观中的“拙之美”。
当然,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完全全的原创,弗洛伊德这种“拙”的画法也不是他独创的,而是他站在前辈大师们的肩膀上探索出来的。画法“取巧”的那些画家他直言不讳地说不喜欢,哪怕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通过翻译一段弗洛伊德和记者瑟巴斯丁·斯密的对话,可以准确清楚地知道他在巧与拙之间的立场:
瑟巴斯丁·斯密:你似乎主动避开用笔的灵巧与用色的微妙,而刻意培养一种“拙”之美。
卢西恩·弗洛伊德:综观美术学院里的画作,我总感觉那些所谓技艺娴熟的好画,比起最老实笨拙的坏画,还要更加糟糕。
瑟巴斯丁·斯密:所以你讨厌拉斐尔(Rapheal)的画?
卢西恩·弗洛伊德:我一贯很少看拉斐尔的画。但不久前,我很震惊地发现了他一幅风格很华丽的画,是一幅裸体人物画,但它仅仅只是很华丽而已。我讨厌的就是拉斐尔的这个华丽。
瑟巴斯丁·斯密:你所钦佩的那些画家们,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笨拙厚重的特质,比如塞尚(Cezanne)就是。
卢西恩·弗洛伊德:塞尚绝对是,我爱极了他的作品。[5]
说明就欣赏角度而言,弗洛伊德也讨厌看到崭新而平滑的画面。还比如有次他去国家画廊看艾尔·格列柯展览,总体而言他很失望,他特别不高兴的是很多作品看上去都很平滑,有光泽,非常干净、明亮。不幸的是那幅有名的《圣马丁》也包括在内。弗洛伊德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被搞坏了的画,有时我觉得我几乎可以看出那些修复画的人所用的清洁剂和漂白剂。”他还说他已经开始在想自己的画慢慢地变旧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并希望那时的修复者会允许“修旧如旧”[1]165。
与此同时,毕加索在他看来也缺乏情感上的真实,他说毕加索只是为了“震惊世人,惊天动地,出人意料”。就连大名鼎鼎的米开朗基罗的早期作品(巴洛克式主题)都不是弗洛伊德所欣赏的风格。作为一个主张女孩不化妆,木质地板不要上漆的艺术家,镀金和大理石很难吸引他[1]144。
当然,他的“拙”不全是他主观营造的,也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弗洛伊德说:“我在帕丁顿区的邻居们常说,‘卢,你的画很有意思。从远处看,可以看出画的是什么,但是靠近它看的时候,只觉得它整个是一片乱七八糟的笔触’。我为什么这样画画呢,是因为我看不清我在画布上画得怎么样。很久以前我就决定在画油画的时候不戴老花镜,当然在画版画的时候还是要戴,因为画版画时要非常接近画面。只有在我往后退一步的时候,我才可以看到我画得怎样,所以我的油画笔在画布上画的时候更像是在瞄准一个靶子。但我敢肯定,如果我戴老花镜就会影响我的创作方式。此外,我不常使用我的左眼,我的左眼是人们所谓的弱视,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纠正不了了。我的右眼是主眼,这与大多数左撇子的人是一样的,大概也算是一种补偿吧。”[1]211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老花眼作画非常吻合他所追求的拙之魂的效果,所以他才有意不去戴眼镜。
既然弗洛伊德这种粗暴笨拙的造型语言将油画技法的难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那么,关于它在世界美术史中的价值和地位必然要重新定位。
二、拙之魂
人们已经习惯了绘画作品是展示美好事物的。而弗洛伊德画面中的模特们,不仅体态丢人现眼、姿势也毫不添彩,与浮光闪烁、精彩绝伦的杂志模特截然相反,所以人们往往觉得他是一个病态的画家,对丑陋怀着自满的兴趣,还有着对令人作呕的事物的明显偏好。
殊不知这一看法混淆了主客体:到底是弗洛伊德故意把人画成这样,还是人体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弗洛伊德只不过是冷静地将它展现了出来而已,于他而言,根本没有什么美或丑,有的只是对真实毫不留情的逼近。在弗洛伊德看来,世人所说的“美”往往就是丑,世人所说的“丑”常常就是美。这一点也可以从他和模特之间的关系看出来。曾经有一个女模特担心没穿睡衣的话,她会被画得不好看。弗洛伊德不同意这种看法,并说他总是有意将模特丑化,为的是保证绘画的逼真。为了让女模特感觉好受一些,他告诉她,自己更担心会把她画得太美丽了。这是卢西恩·了不让画作失败而惯用的奉承小伎俩[6]。
在另一方面,弗洛伊德非常鄙夷美术史上通常称之为“人体(nude)”的绘画形式,正是因为这一形式散发着矫揉造作的臭气。他每幅作品的题目便揭示了这一点。在英文“nude”和“naked”这两个指称“未着装的身体”的词汇之间,弗洛伊德只使用后者:《大笑的裸体孩童》(Naked Child Laughing)、《裸像》(Naked Portrait)、《熟睡的裸体女孩》(Naked Girl Asleep)、《床上的裸男》(Naked Man on Bed),诸如此类。他对那种学院派意义的、被净化过了的、道德上无害的人体画(the nude)毫无兴趣,而只钟情于真实性的那种裸体画(nudity)[7]。
同时,弗洛伊德对模特又非常挑剔,他几乎从未用过专业人体模特,画中模特全部是他生活中熟悉的、真实的人们。“我需要那种能一下激发画家创作冲动的模特,他们呈现出某个不一样的姿势,是为了向我提供一种私密性的服务,而不是在那儿搔首弄姿。”[2]要知道,他全方位讨厌华丽的东西,喜欢朴拙的东西。比如他讨厌猫,他说“我不喜欢它们独处时的华丽姿态,也不喜欢它们跳到你的大腿上。然后带着‘你现在可以抚摸我了’的姿态蜷缩在你腿上。”所以他喜欢养狗并画狗[1]190。
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罗丹的著名雕塑《欧米哀尔》,是用极其朴拙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极丑陋的老妓女,并且“欧米哀尔”的法文原意是“头盔制造者的美丽妻子”,呈现给人们的却是一个骨瘦嶙峋、乳房干瘪下垂、沿街乞讨的老妇人雕塑,表现的是她的暮年悲凉气氛。这使得当时的人们乍一看又惊又恐,纷纷抱怨太过丑陋和骇人。但实际上,整件作品蕴含着的却是一颗尊重生命的善心、一声对巴黎社会上层阶级的批判、一场宣示真实的视觉盛宴。
同理可证,在弗洛伊德的代表作《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里,画面中的肥裸女通体笨拙厚重、画家的造型语言也酣畅淋漓,精彩的画面使得大家可能容易忽略题目的含义:一个负责管理救济金的人,居然胖成这样?是否有点搜刮民脂民膏的讽刺意味?明显,弗洛伊德不仅在画面形式上逼近一种丑陋的真实,而且在画面内容上也毫不留情地揭示真相。

《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拍卖现场.2008年
自古素者莫能与之争美也,罗丹说天下最美的是朴素,马克思认为人类最高尚的品格就是纯朴。这也正是卢西恩·弗洛伊德“反向艺术观”之魂、“化巧为拙”之根。我们还能从他说过的一句话中可以见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我灵魂的自画像。”[8]
这样一来,就要求观者在鉴赏他的作品时,同样也需要一双淳朴无华的眼睛:弗洛伊德谨慎地拒绝人们在他祖父的心理分析学中寻找理解自己作品的钥匙,因为在他看来生命是生理学,而非心理学;是身体肌肉,而非心的召唤;是器官的物理机能,而非祖父研究的精神机能。
所以在这里,“拙”的更深一层含义不是表面的视觉冲击力,而是真实,一种萨特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真实。
弗洛伊德称自己为“生物学家”。让我们换一个词,也许更加丑陋,但同属于一个语意的范畴:他是表现物种多样性的画家。就像他的同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写,当他从科隆群岛返回之后,为当地生物的多种多样感到兴奋不已。终其一生,弗洛伊德对生命的各种形态表现出长久的、永不疲倦的激情,从卑微到神奇,从植物到人类,从生长在伦敦花园或室外的普通植物——毛绒花和贝母——到新衍生出来的人类:他们也许是最卑贱的人,那些坐在吧台上的变性人和坐在办公室里的银行家,对生物伟大的爱。在生命萎缩、凋零、枯萎的时代,在生命的多样性戏剧化地削弱的时代,当人类古老的爱心在商业利益的定律下消亡的时候,他还像过去那些伟大的画家一样,例如伦勃朗(Rembrandt)和华托(Watteau),不知疲倦并满怀热情地描绘那些活着的人[9]。
三、小结
欧洲传统古典油画的形式语言可以概括为“平涂轻抹,强光暗影,过渡柔和”,表现出巧妙和高超的技术手法。而当代英国画家卢西恩·弗洛伊德的油画语言则一反常态,他把技法中“巧”的一面去除,取而代之的是“拙”的手法,不仅笔触笨拙粗糙,颜料厚堆,坑坑洼洼,而且抛弃顶光照明的古典法则,选取平光或底光来突出人体肉感,展现了油画艺术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绘画形式语言,可谓是将“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油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不喜欢看起来太像艺术品,或者说“很协调”的画作,评论家有时会批评弗洛伊德作品不协调,其实那些“不协调”是他特意营造的。
有谁料到,当美术史进入我们这个万事万物都趋于观念化的当代,在这个众人预言古老的架上绘画即将消亡的当代,恰恰是被这个真正懂得朴拙的灵魂所解围,是卢西恩·弗洛伊德的作品为现代艺术的语言形式拨开了迷雾,从而使我们认清,他“化巧为拙”风格在美术史上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于:从此宣告古老的绘画永远不会消亡,造型的语言也永远不会被穷尽,手法和形式就像时间,没有起点也不会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