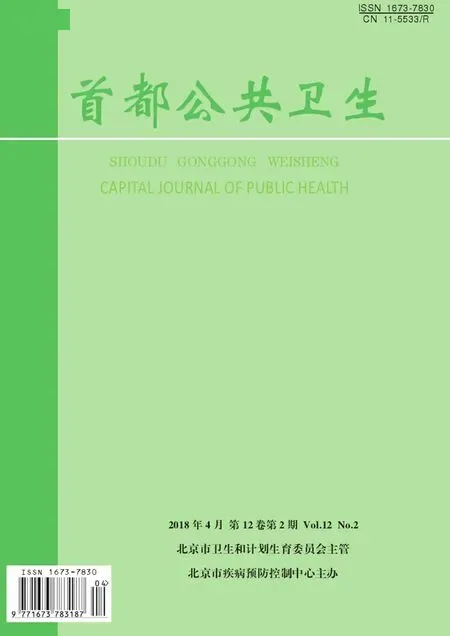北京市西城区小学生及家长营养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赵芳 刘嘉 张楠 杨春雷
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是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双重高涨[1-2],营养不良会影响孩子的认知发育、造成环境适应能力差、智力和学习能力的损伤,肥胖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是成年期慢性病的诱因[3]。由于儿童青少年是一个最具可塑性的人群[4,5],通过开展营养相关的健康教育干预活动,对学生普及营养知识、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意义。于2014年4月-2015年11月,对北京市西城区部分小学生开展了以学校为基础系列营养健康教育干预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等形式对家长也进行了营养宣教,并在干预前后对学生及其家长的营养相关知识和饮食行为进行了效果评估。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西城区抽取5所小学(3所干预学校、2所对照学校),干预学校的全体师生和学生家长均作为干预对象。问卷调查对象:学生为3~5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2个班,每班的所有学生;家长为1~5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2个班,每班的所有学生家长。
1.2方法
1.2.1问卷调查:采用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设计的调查问卷,在一年半的健康教育干预活动前后分别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采用自填的方式,问卷内容包括营养相关知识和饮食相关行为等。
1.2.2早餐营养质量评价:将早餐的食物分为“谷类”、“肉类”、“蔬菜水果类”和“大豆、奶类”4种,食用4类食物评价为早餐营养充足,食用3类食物评价为早餐营养良好,食用1~2类食物评价为早餐营养较差[6,7]。
1.2.3营养健康教育: (1)对学生:每周0.5课时的营养知识健康教育课,发放专用教材《健康校园》(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编制),学生人手一册,对学校讲课的老师提供教材的老师分册及配套课件;每周通过校园广播开展营养知识宣传;每学期开展营养专题的班级板报、自制健康小报及发放宣传折页、展板等。(2)对家长:发放营养知识宣传材料、家长信等;每学期开展一次营养健康知识讲座;采用“小手拉大手”的形式,通过学生向家长宣传营养知识。
1.3统计学方法 用EpiData 3.0进行数据录入,数据经核对和清理后,用SPSS 19.0软件进行率的计算,不同人群的营养知识和早餐行为的比较用χ2检验。
2 结果
2.1干预前后营养知识知晓率比较 干预前,干预校和对照校的男生、女生及其家长的营养知识知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Р>0.05)。干预后,干预校的男生和女生营养知识知晓率均高于自身干预前及对照校(Р<0.05),对照校学生的营养知识知晓率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Р>0.05);而家长的营养知识知晓率与自身干预前及对照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Р>0.05,表1)。
2.2干预前后学生早餐行为比较 通过干预,干预校小学生每天吃早餐行为从77.3%提高到84.2%,且高于对照校;吃早餐的学生中,四类食物的摄入均有所增多,其中谷类摄入增加的最高,早餐质量营养充足及良好(包括3~4类食物)的行为增加,营养较差的行为降低;对照校学生除早餐中的豆、奶类食物摄入与干预前比有所增加外,其他行为均无明显变化(表2)。

表1 干预前后不同人群营养知识知晓率比较
注:自身干预前后比较,*P<0.05;自身干预前后比较,**Р<0.01;干预校与对照校比较,△P<0.05;干预校与对照校比较,△△P<0.01。

表2 干预前后小学生早餐行为比较
注:自身干预前后比较,*Р<0.05;自身干预前后比较,**Р<0.01;干预校与对照校比较,△Р<0.05;干预校与对照校比较,△△Р<0.01。
2.3干预前后家长早餐行为比较 干预后,干预校的学生家长每天吃早餐行为从74.8%提高到79.2%,且高于对照校;吃早餐的家长中,蔬菜水果类食物的摄入从32.3%提高到39.0%,但其他类食物及早餐营养质量无明显改变;对照校家长早餐相关行为与干预前比均无明显差异(表3)。

表3 干预前后家长早餐行为比较
注:自身干预前后比较,*Р<0.05;自身干预前后比较,**Р<0.01;干预校与对照校比较,△Р<0.05;干预校与对照校比较,△△Р<0.01。
3 讨论
3.1通过对干预校一年半的系列营养健康教育活动,使干预校的小学生的营养知识知晓率、每天吃早餐行为、早餐食物的种类及营养质量均高于自身干预前及对照校,而对照校学生的营养知识知晓率及早餐相关行为前后比较均无明显变化。说明以学校为基础开展营养健康教育,对提高小学生营养知识水平、转变营养态度和改善饮食行为具有明显效果,这与梁健平等[8-10]的调查结果一致。因为儿童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的健康教育活动,便于组织实施和持续进行,实践证明,学校是开展健康教育效果最好、时机最佳和健康促进最理想的场所[4,5]。
3.2每天吃早餐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一种健康促进行为,不吃早餐是儿童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11]。本次研究,干预校的学生和家长每日吃早餐的行为通过干预后提高到84.2%和79.2%,高于段一凡、宋超等[7,12]的调查结果,低于张海蓉等[13,14]调查结果。此外,干预校学生早餐中的谷类、奶豆类、肉蛋类和菜果类食物在干预后虽然有所提高,但肉蛋类、菜果类食品的摄入仍然未超过半数,而且只有21.1%的学生早餐质量是营养充分的,这些与干预校家长的早餐食物结构及早餐质量类似。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小学生年龄较小,对于知识指导自身行为等方面能力不足,早餐大多数是由家长准备[6],所以提高家长的营养知识水平和意识,对于改善学生的饮食结构及习惯至关重要。
3.3研究中发现,干预校的家长每日早餐行为和早餐中蔬菜水果类食物的摄入高于干预前,但营养知识知晓率和早餐营养质量与自身干预前及对照校比均无明显提高,这与夏庆华等[15,16]的调查结果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家长作为生活方式基本定型的群体,通过“小手拉大手”的宣教形式对其固有的行为影响有限。因为小学生尚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其有重要的影响。建议通过社区、医院或就业单位等多途径开展营养健康教育,进一步提高家长的营养知识及健康素养水平。
参考文献
[1] 刘峥, 郭欣, 段佳丽,等. 北京市2009-2010年度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及健康行为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2, 33(6):656-658.
[2] 黄珍茹, 高润颖, 张雅莉,等. 上海市中小学生在校午餐与营养状况调查[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7, 37(1):106-109.
[3] 季成叶.儿童少年卫生学[M].7版.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36-159.
[4] 马骁.健康教育学[M].2 版.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210-218.
[5] 曹蕾. 对发展我国学校健康教育的思考[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 2009, 20(6):118-119.
[6] 胡小琪, 范轶欧, 郝利楠,等. 我国7城市中小学生早餐行为的调查[J]. 营养学报, 2010, 32(1):39-42.
[7] 段一凡, 刘爱玲, 张倩,等. 城市儿童1998年和2008年早餐行为比较[J]. 中国学校卫生, 2011, 32(12):1417-1419.
[8] 梁健平, 陈静仪, 林嘉玲,等. 广州市小学生膳食营养知识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16, 37(8):1170-1172.
[9] 陈晓英, 张洪斌, 张燕,等. 海南省农村黎族初中学生早餐情况调查与营养知识教育效果评价[J]. 预防医学论坛, 2008, 14(2):132-134.
[10] 张伟, 付爱民, 靳淑珍,等. 济南市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效果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 36(1):61-62.
[11] 李艳平, 胡小琪, 马文军,等. 我国4城市儿童少年食用早餐频度和肥胖率关系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05, 26(1):10-12.
[12] 宋超, 郭海军, 宫伟彦,等. 我国4城市中小学生家长饮食行为现状[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 36(7):1010-1013.
[13] 张海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小学学生早餐现状调查[J].职业与健康,2014,30(3):329-330.
[14] 王丽, 付慧英, 聂晶. 北京市门头沟区199名中小学生健康知识及行为调查[J]. 首都公共卫生, 2015, 9(2):86-88.
[15] 夏庆华, 孙建平. 中学生及其家长合理营养综合干预效果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06, 27(6):481-482.
[16] 唐咏梅, 宁鸿珍, 周瑞华,等.唐山市小学生家长营养教育效果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02, 23(1):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