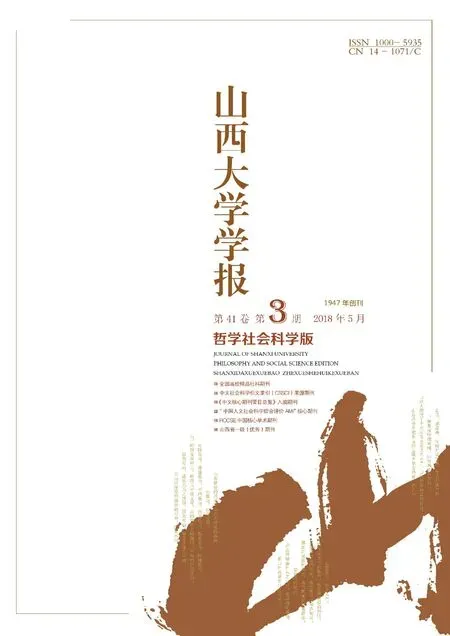唐代儿童的孝道教育
——以《孝经》为中心
金滢坤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孝经》是孔子所做的儒家伦理经典*张涛:《<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考》认为《孝经》不是孔子所做,《中国史研究》1996年1期,第122页。,以孝为中心,为“百行之本”,阐述了忠孝、孝悌的关系,以及以忠孝、孝悌来处理父子、君臣、兄弟等各种社会伦理关系,再扩展到立身、处事、事君等各种社会、政治事务。汉魏以来,《孝经》《论语》就作为童蒙教育最主要经典[1],唐五代仍将《孝经》作为童蒙教育的最主要经典,对孝道教育产生非常重要影响,也为国家培养具有忠孝品质的文武官僚队伍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 《孝经》与儿童启蒙教育
唐代童蒙教育重视《孝经》《论语》与自汉魏以来童蒙教育就重视《论语》《孝经》的传统有关,通常先《孝经》,后《论语》,有时两者同时进行。如薛鲁鲁“儒家之令子”,“五岁能诵《孝经》十八章,七岁通《论语》廿二篇”。[2]334又权顺孙,幼有敏智,“读《孝经》《论语》《尚书》”。[3]卷16又元衮,“六岁入小学,读《孝经》”,“七岁学《论语》。”[4]816
官僚士大夫更是重视子弟的《孝经》教育。唐中宗时李恕《诫子拾遗》中就记载了子弟培养方案,“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5]37也就是说儿童的《孝经》教育一般在七岁左右。如贞观元年(627),崔沉“七岁诵《孝经》《论语》,十二通《毛诗》《尚书》,皆精义贯理,默而识之”。*《唐代墓志汇编》神龙35号《大唐故文林郎崔君墓志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65页。按:崔沉,武德三年(620)年生。又鲁谦,“年七岁,好读诗书……未逾十五,《孝经》《论语》《尚书》《尔雅》《周易》皆常念,《礼记》帖尽通”[6]2354-2355,说明他最先读的是《孝经》。又萧元明,元和二年(807),“时年九岁,已诵得《孝经》《论语》《尔雅》《尚书》《李陵》《李斯》等书”[4]809,也是在七八岁左右读的《孝经》。从史料记载来看七八岁读《孝经》的事例很多,不一一而俱。
唐代皇室也十分重视子弟孝道教育,多以《孝经》为童蒙教育的启蒙读物。唐太宗就非常重视对皇子的孝道教育。高宗李治幼时,著作郎萧德言授其《孝经》,太宗问李治曰:“此书中何言为要?”对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大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7]卷4开元六年,太子侍读褚无量,以“皇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岁,尚未就学”,“缮写《论语》《孝经》各五本以献”。玄宗明白褚无量的用意之后,“遽令选经明笃行之士国子博士郄恒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为太子及郯王已下侍读。”[7]卷102
唐代儿童超前教授《孝经》的情况很常见。甚至有幼儿在襁褓中就由母亲教授《孝经》。如贞元末,姚夫人“生一子,始稚孺,坐于膝,手持《孝经》,点句以教之”。[6]2353幼儿稍大一点,就会由父亲教授《孝经》。比较突出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次子李仲宣,两岁的时候,后主就“亲授以《孝经》、杂言,虽未尽识其字,而每至发端止句之处,皆默记不忘”。[8]卷887:11117稍大点的孩子有:贞观十九年(645),郑崇道,“四岁而孤,哀号合体。叔祖沛公嘉其丧慼,爰授《孝经》。曾未浃旬,成诵于口,人斯与,众以神称。弱冠,乡以明经贡,对策高第”。[2]116一般来讲四岁为儿童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能掌握一千个字左右,而《孝经》一千九百来字,郑崇道浃旬即十天就可以背诵《孝经》,应该属于神童级的儿童。又薛鲁鲁,贞元十四年生,“五岁能诵《孝经》十八章,七岁通《论语》廿二篇”。[2]334又元衮,天宝十二载(753),“六岁入小学,读《孝经》”,七岁学《论语》。[4]816晚唐沈瑀,“六岁读《孝经》,至参不敏,略而不读。师问之故。曰:‘此大人称之,而小子曷称之?’”[9]卷918:4239从小孩子口气来看,幼儿超前教育《孝经》违背了儿童教育的规律,的确存在脱离儿童心理和实际需要的情况。此类不到六岁的幼儿读《孝经》的情况还很多,就不一一而述。
唐代教授儿童《孝经》的方法,注重背诵、默写。如梁春,大和七年十一岁卒,“训诲弘诱,小学大成,至于《孝经》《论语》,通卷背文;颜氏字类之书,问之便写”[6]2141,就是比较典型的背诵和默写。敦煌学士郎学习《孝经》的写卷[10],[11],为我们研究唐五代教授儿童《孝经》的方法提供了宝贵资料。

表1 敦煌文书《孝经》抄写表
上表8件《孝经》分别由沙州学生、学郎,敦煌灵图寺、永安寺、三界寺的学士郎曹元深、高清子等书写、抄写,寺学的学士郎教育为童蒙教育[12]104-128,足以说明敦煌寺学的童蒙教育仍以《孝经》作为启蒙教育的最基本课本。从目前来看,敦煌文献中学郎题记的儒家经典,《论语》最多,为10件[11],《孝经》其次,有8件,考虑到有些《孝经》书法稚嫩、抄写杂乱,应该就是学郎抄写的读本。从这种意义上讲,敦煌寺学童蒙教育以《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教育为主。
敦煌文献中有一首非常有趣的学郎诗,描写了学郎学习《孝经》的场景与收获。S.728《孝经》的背面有学士郎李再昌书写“学郎诗”云:“学郎大歌(哥)张富千,一下趁到孝经边。太公家教多不残,猡实乡偏。”此诗非常生动、活泼,充满了童趣,描写了儿童之间争相诵读《孝经》《太公家教》,你追我赶的场面,也反映了《孝经》是学郎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检验学郎学习好坏的标杆。
二 《孝经》对儿童道德观念、行为举止的培养和塑造
在中国古代,《孝经》常被看作“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7]卷155,对培养和确立而儿童道德品质、价值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一)儿童学习《孝经》与孝行实践
儿童在学习《孝经》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将“孝道”思想融入日常行为举止中。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解云:“《孝经》者,尊祖爱亲,劝子事父,劝臣事君,理关贵贱,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经》也。”[13]3也就是《孝经》讲的子弟敬事父祖、关爱亲人的言行,侍奉君主、劝谏长官的言行举止,以及处理君亲长幼、贵贱的关系的准则和伦理,重在指导人的行为举止。因此,《孝经》对培养儿童最基本的言行举止至为关键,有“百行之首”的说法。故玄宗一再强调:“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8]卷37:476;“道为理本,孝实天经,将阐教以化人,必深究於微旨”。[14]卷40孝是国民道德教育的根本和基础,一切社会教化始自孝。
既然《孝经》是指导士人的行为准则,“百行之首”“德之本”,通过国家、社会和家庭对儿童的《孝经》教育,儿童就会形成朴素的孝道价值观念,也会转变为行为指南。《百行章·序》云:“《孝经》始终,用之无尽。但以学而为存念,得获忠孝之名。虽读不依,徒示虚谈,何益存忠?则须尽节立孝,追远慎终。”认为学习《孝经》不是为了虚谈,而是要践行忠孝,尽节立孝,终身指导自己的言行举止。儿童幼小读《孝经》,便会耳濡目染,在生活、行为举止中,把孝道观念转化为实践。如崔歆“七岁读《孝经》《论语》《毛诗》《礼记》”,曾因玩耍时,不小心戏而伤手,其父见其面有忧色,便责怪问他。崔歆敛容对曰:“《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以忧惧。’时通人韩俭、长史丘贞观在座,对崔歆言语非常惊奇。”[6]933-934从这一事例来看,崔歆牢记《孝经》《论语》等经典所讲,在言行举止,孝事父母,对待朋友方面,将《孝经》作为“百行之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和遵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孝经》对培养儿童的行为规范,特别是塑造孝道观很有效果。又李少康,“年始孩而毕公捐馆,(永徽元年)七岁受《孝经》,至《丧亲章》,捧书孺慕,哀哽不食,邻伍长幼,为之涕泗。既冠,遭太夫人弃孝养,苴皃茹毒,血泣无声者三年。自是孝称乡党,名冠宗室”。[15]卷8:62又薛鲁鲁,五岁就能背诵《孝经》十八章,年纪少长,“言必有文,动必中礼。亲族之内,无不敬之”。[2]334又天宝六载(747),元某“五岁读《孝经》,至《丧亲章》,常恶其题,弃而不览。年十二,丁庐州府君之忧,鞠然在疚,涉旬绝浆,三年之中,曾不见齿,亲族以为难”。[6]1939无独有偶,天宝十二载,元衮“六岁入小学,读《孝经》,至哀良,弃而不览。人问其故。对曰:‘详其义所不忍闻。’”。[4]816又权顺孙,幼读《孝经》《论语》,“凡举措语言,循理谕义,出常童远甚”,就在其患大病之际,“上辞尊长,下诀幼弟妹,恬然不乱”[3]卷13,尚且不忘《孝经》所讲尊亲、孝悌观念,逐一告别,实在感人。元和中,杨行立“七岁通《孝经》《论语》,十岁明《诗》《礼》。尝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可以终身之矣’”。[4]934咸通六年王仲建卒,其子王知教,“及成童,伯仲以《孝经》授,见末章有裂骨之痛,亲属以为曾闵之匹。俾专就养,克扶竭力之仁。捧药问安,式展因心之孝。衔酸茹恨,泣血穹苍。擗地扪心,几将灭性于庐次。”[9]卷806:8475晚唐钱师宝,“童时通《孝经》、《论语》。尝语亲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圣人之至行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孔门之高节也。惟此二者,吾庶几焉。’遂高谢徵辟,覃精载籍,极事亲之道,得乡党之誉。”[16]322
以上事例多为早卒儿童,考虑到儿童年纪尚小,没有太多事迹可赞,便以读《孝经》《论语》,有孝行作为表彰的重点,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读《孝经》,有孝行,是衡量儿童品格端正、有才学的重要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墓志所言童子至孝,往往超乎寻常,不必过度在意,但通过《孝经》培养童子的忠孝观念、道德情操具有诸多益处,也为儿童树立志向高远,扬名天下的正向观念,对营造家庭和睦,维护中央集权,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二)读《孝经》与扬名天下
读《孝经》有利于从小培养儿童的正确人生观,树立远大理想,忠孝国家,立身扬名。如太宗“十八学士”之一的苏世长,周武帝时,年十余岁,上书言事。周武帝以其年小,召问:“读何书?”对曰:“读《孝经》《论语》。”武帝曰:“《孝经》《论语》何所言?”对曰:“《孝经》云:‘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论语》云:‘为政以德。’”从君臣对话来看,苏世长从小读《孝经》和《论语》后,就懂得国君治国要善事鳏寡、老幼,“为政以德”的大道理,令周武帝十分惊讶。苏世长正是接受忠孝观念的影响,在隋唐群雄逐鹿之际,苏世长对前朝君主的忠贞,颇受唐高祖、太宗敬重,被列入“十八学士”[7]卷75,获得了极高荣誉。
儿童读《孝经》,立志入仕为官,立身行德,扬名天下,光宗耀祖,有利于培养其正向的价值观念。独孤及,“七岁诵《孝经》,先秘书异其聪敏,问曰:‘汝志于何尚?”公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是所尚也。’”显然,读《孝经》可以树立儿童立志扬名的思想。独孤及十五岁的时候,父亲死后,“茹血在疚,逾时而后杖,由是乡党称孝”。独孤及不负初心,天宝十三载(754),应洞晓玄经科,对策高第,官至常州刺史,“比及三年,吏不忍欺,路不举遗;年谷屡熟,灾害不作”[9]卷522:5302-5303,并以文学名闻天下。这不能不说,与独孤及幼时读《孝经》立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有很大关系。
三 蒙书的编撰与《孝经》的关系
自汉魏以来,《孝经》就是童蒙教育的重要内容,故蒙书编撰也通常摘引和改写《孝经》内容,以便更加通俗、浅显地向儿童传授孝道思想。早在南朝梁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中,就吸收了不少《孝经》的内容。《千字文》云:“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这两句就是针对《孝经·开宗名义章》所云:“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纪孝行章》所云:“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就是对《孝经》两章相关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用通俗易懂的韵文表述,便于儿童学习和记忆。唐代新编撰的蒙书,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特点,对《孝经》大量地摘引、摘编、改写,甚至同一部蒙书中有关《孝经》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千字文》的字数。详细情况请见拙文《唐五代敦煌蒙书编撰与孝道启蒙教育——以<孝经>为中心》[17],本文仅以敦煌蒙书《文词教林》为例,加以说明这一现象。
敦煌蒙书对《孝经》进行摘编、摘引和改写的情况很常见,只是编撰形式和摘编、摘引和改写多少的区别。《文词教林》则是对《孝经》按章进行摘编、改写,或者合并两章的内容,用以训诫儿童。《文词教林》卷上云:“士有百行,古难备陈,略而言之,大数举十:孝义者,立身之本……谦恭者,立身之操;谨信者,立身之德……慎口者,立身之务。”[18]第16册:242其列举士大夫立身出身的十大要点,将《孝经》的核心内容“孝义”,视作“立身之本”。而谦恭*《孝经·三才章》:“子曰:‘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收入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页。、谨信、慎口三点也是《孝经》宣扬的重要内容*《孝经·卿大夫章》云:“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孝经注疏》,第11页。,可见《文词教林》对孝道教育十分重视。《文词教林》直接引用《孝经》的内容有三条:
1.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因情以教仁,而人乐乎。畏其刑罚,爱其得义,是以爱而畏之。(见《孝经·圣治章第九》)
2.君惠臣忠,父慈子孝,祸乱无缘得。(见《孝经·士章第五》《孝经·孝治章第八》)
3.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见《孝经·事君章第十七》)
从这三条来看,第一条是对《孝经·圣治章第九》的摘编和改写,第二条则是对《孝经》“士章第五”“孝治章第八”两篇的改写和合并,第三条是对《孝经·事君章第十七》直接引用。此外,还摘引了《真言决》《论语》《礼记》《左传》《礼记》中有关“孝义”的内容亦有7处,至于摘录和改编的情况就不再一一说明。足见《文词教林》对“孝义”的重视,也是作者把“孝义”列为第一的原因。
四 童蒙教育重视《孝经》的原因
唐五代启蒙教育最为重要的经典,非《孝经》莫属,这是由“蒙以养正”即童蒙教育的核心内容决定的。[19]39具体来讲,其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孝经》宣扬忠孝观念,符合国家统治的需求,得到帝王的高度重视;二是,《孝经》是科举考试最基本的内容,士人从事举业必须从《孝经》学起。
(一)国家统治的需要与官方推动
童年教育重在“义方”,“以明尊卑之义,正长幼之序”[9]卷39:429,因此,宣传“百行孝为先”,以“孝为本”的《孝经》,对培养和端正儿童的品性和行为举止无疑尤为重要。赵匡说:“《论语》诠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20]卷17:421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将《孝经》视作“立身治国”的儒家最重要的经典[21]卷175,北周、隋、唐等几代开国皇帝都将《孝经》作为儒家群经之首,往往亲幸国子监,延请名儒讲授《孝经》,并将《孝经》作为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最基本经典。
北周太祖尝亲临太学释奠,杨尚希时年十八,“令讲《孝经》,词旨可观”。[22]卷46开皇五年(585),隋文帝就亲自主持国子学释奠仪式,命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宣扬忠孝,意在推崇《孝经》地位,宣扬孝道,教化民风。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诏:“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22]卷3意在宣扬孝道。武德六年(623)*《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上·徐文远传》云:“武德六年,高祖幸国学,观释奠,遣文远发《春秋》题,诸儒设难蜂起,随方占对,皆莫能屈。”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4页。,“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进《老子》。诏刘德明与之辩论,于是诘难蜂起,三人皆屈。”[23]卷11:162徐文远是隋唐之际的大儒,擅长讲《孝经》,曾为隋汉王谅讲《孝经》。唐高祖将《孝经》作为儒家经典代表,并请当时名儒徐文远主讲《孝经》,与佛家、道家同台辩论,可见高祖对《孝经》的重视。
继高祖之后,太宗在贞观十四年(640)三月,幸国子学,亲观释奠,令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太宗问颖达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对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太宗又谓侍臣:“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7]卷24显然,太宗幸国子学,意在崇文,令国子祭酒专门讲《孝经》崇重儒学,提升《孝经》的地位,并借此对孝的内涵进行了发挥,将讲孝从“善事父母,自家刑国”,扩展到忠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等层面,全面阐释了孝是“百行之本”。
唐代皇帝讲筵,延请名儒给百官讲《孝经》。永徽初,“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召中书门下三品及弘文馆学士、太学儒者,并预讲筵”。赵弘智“演畅微言,略陈五孝,诸儒难问相继,酬应如响”。高宗怡然曰:“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经》之益为大也。”[7]卷188高宗延请名儒设讲筵,令三品以上宰相,以及馆学名儒参加,旨在宣传孝道,“德教加于百姓”,赵弘智所讲内容正合高宗之意,故获赐彩二百匹。
唐代皇帝对儿童《孝经》教育的推动。武德七年(624),天下初步统一,高祖就下诏奖拔史孝谦为两个幼子“讲习《孝经》,咸畅厥旨”,强调“义方之训,实堪励俗,故从优秩,赏以不次”[9]卷3:37,旨在从童蒙教育着手,加强《孝经》教育。唐太宗也说“百行之本,要道惟孝”,将孝道提高到“齐礼道德,耻格之义斯在”的高度。[9]卷5:58-59唐玄宗亲自御注《孝经》,并令弘文馆学士元澹作疏,于天宝三载(744)下制,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并奖励孝勤过人,名闻乡里的人。[9]卷310:3150
唐代科举考试的乡贡举人参加省试之前,要先赴国子监谒先师,一般由名儒先从《孝经》开讲。唐玄宗为了推崇谒先师之礼,于开元五年(717),令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入国子监谒先师,象征性为举人答疑解惑。开元七年(719)十一月十一日,以贡举人将谒先师,质问疑义,玄宗敕皇太子瑛及诸子,宜行齿胄礼。于是乙亥,“皇太子入国学,行齿胄礼,谒先圣,太子初献,其亚献、终献并以胄子充。右常侍褚无量开讲《孝经》,并《礼记·文王世子篇》,初诏侍中宋璟亚献、中书侍郎苏颋终献”。[14]卷260;[28]卷35《孝经》作为举人在国子监谒先师,首讲之经典,无疑提升了《孝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必然会影响到科举考试最基础的教育,也体现了朝廷重视童蒙教育的事实。
此外,后唐天成四年(929)十二月《请设官讲明经义疏》,以国子监诸博士讲经,“欲讲小经,以消短景”,不受重视,“今已请《尚书》博士田亩讲勘《论语》《孝经》,行莫大于事亲,道莫逾於务本”,从而引导希望“策科名而得俊”的举子重视《孝经》。[8]卷974:13287-13288
《孝经》是士人的行为准则,不仅可以用来治国理政,甚至化解民事纠纷,感化人心。景云二年(711),韦景骏为肥乡令,有母子相告者,很感慨地讲:“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痛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23]卷4:67“因泪下呜咽,仍取《孝经》与之,令其习读。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24]卷197唐初有王渐作《孝经义》五十卷,在当时很受欢迎,“凡乡里有斗讼,渐即诣门,高声诵义一卷,反为渐谢。后有病者,即请渐来诵经,寻亦得愈,其名蔼然”;其实,就《孝经义》对《孝经》内容阐释的非常接近民意,百姓对其非常崇敬和诚信[25]285-286,遇事还可以化解邻里矛盾,甚至疗治身心疾病。
(二)教育与取士合一
唐代实行了教育与科举取士相结合的制度,将《孝经》作为科举考试最基础儒家的经典,以选拔文官。《新唐书·选举志》云:明经诸科无论选习大中小经多少,都必须“《孝经》《论语》皆兼通之”。[24]卷44;[26]卷2又《唐六典·尚书吏部》吏部考功员外郎条记载:“诸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26]卷2两者记载明经类科目,兼习《孝经》《论语》的情况,大致相似,进士科试《孝经》的方法与明经大致相同。
现存科举考试的史料,可窥视科举考试,所考《孝经》策问的情况。如大足元年(701),张说试洛州进士,第二道策问:“夫子述《孝经》,裁《道德》,辅天相地,树之王化,穆乎人伦,既钩命而合谟,亦契神而尽性。历听藏书,同为代宝,永言五孝,不列六经,将设教之有旨,岂偏序之无法?”[27]卷30:1458可惜没有相关对策记载。不过,开元七年(719),制举考试文词雅丽科策问:“朕闻至道虽微,不言而化,皇天阴骘,相叶其彝。信寒暑而生成,施云雨而沐润。垂范作训,树君育人,时有浇淳,教垂繁略……悉情以对,用释余疑。”[9]卷353:3579针对此问,制举人苗晋卿对云:“陛下顷与三事大夫议于朝,以计天下有奇才异行,含光而不扬其辉,诏诸侯咸举之。臣实至愚,不通大识,循才审行,不副高求……《孝经》曰:‘王者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理;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而保大定功,勋业盖时也。”苗晋卿就用《孝经》的内容,来对策。
关于明经系诸科、进士科试《孝经》注本,开元以前以孔安国、郑玄注比较流行。贞观中,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也包括《孝经》,对《孝经》的音义作了解说。开元七年(719)三月一日,玄宗《令诸儒质定古文孝经尚书诏》,引起了群儒对《孝经》《尚书》诸家注疏的争论。同月六日,玄宗又下《孝经参用诸儒解易经兼帖子夏易传诏》云:“《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指趣,颇多踳驳……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9]卷28:316;[14]卷50显然,此前《孝经》以古文《孝经》和孔安国、郑玄注为主。敦煌文献中发现的蒙书《杂抄》中提到:“论经史何人修撰制注?”有一句:“《毛诗》《孝经》《论语》,孔子作,郑玄注。”的确说明唐代《孝经》孔安国、郑玄注很流行。在四月七日,左庶子刘子玄上《孝经注议》曰:《孝经》注,“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音发问,较其短长,愚请行孔废郑,于义为允。”[28]卷77经过中书门下的审议后,中书门下奏:“《孝经》郑义行已多时…望并付所司,令诸儒与子玄对质定[详]。”[29]卷604
玄宗最终亲自御注《孝经》,并大力推行,促进了全民对儿童孝道教育的重视。开元十年(722)六月,玄宗训注《孝经》,颁于天下;天宝三载(744)十二月,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令其精勤诵习。要求“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百姓间有孝勤过人、乡闾钦伏者,所由长官具以名荐”;并大力表彰百姓孝事父母的行为。[8]卷310:3546文宗朝修订的开成石经,名为九经,实际上包含了《孝经》和《论语》《尔雅》,与“九经”合称石刻十二经*(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109《石刻十二经》条引〈石经考〉曰:“按《旧唐书·文宗本纪》及《郑覃传》,皆言不壁九经,即黎持之记(按即〈新移石经记〉)亦然。其实九经之外,更有《孝经》、《论语》、《尔雅》,凡十二经,不止九经也。”北京:中国书店影印,第3册,第8页。,也是对《孝经》的又一次重要的修订。

唐代国家对儿童的孝道教育十分重视,开元中玄宗还一度专门设置孝悌力田科作为常举科目,通过乡贡,参加省试。[32]开元二十六年(738)五月,玄宗诏:“孝悌力田,风化之本,苟有其实,未必求名。比年将同举人考试,词策便与及第。以常为科,是开侥幸之门,殊乖敦劝之意,自今已后,不得更然。其兼著状迹殊尤者,委所由长官将以名荐,朕当别有处分,更不须随考使例申送。”[29]卷639的确孝悌力田属于德行类,很难通过考试评判,在实际操纵中往往是“开侥幸之门”,有“乖敦劝之意”,玄宗考虑到实际情况,便将令各级长官荐举,由皇帝亲自处置,实际上就变成了制举考试科目。据《唐六典·三府督护州县官吏》云:“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其人正直清修,名行孝义,旌表门闾,堪理时务,亦随宾贡为孝弟力田。”[26]卷30大概《唐六典》记载的就是开元二十六年前的一段时间,孝悌力田的确有乡贡的情况。
唐代常科中孝悌力田科的废除,给制举孝悌力田科等提供了空间。唐代制举科目,唐宋以来不断有学者将其分为德行、才能、文学三类。在德行类下又分孝悌类等若干科目。在儒家观念中,“孝为众行之根本”[33]1557,“孝为百行之首”[34]19,“孝为德之本”[35]963,是儒家道德的根本,因此,自汉代就比较重视孝廉的选拔。汉武帝元光元年,就“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36]卷6,此后孝廉科就成为两汉的取人最多的科目。[37]唐代十分重视孝悌、力田类科目,孝悌包含孝事父母,敬事兄长,力田,盖指廉吏和良官等,是儒家德行的实践。
唐代孝悌类科目包括孝弟力田素行高于州里、孝悌力田、孝弟梗直、孝悌廉让、孝行过人乡闾钦伏、孝悌力田闻於乡闾、孝通神明等七科*详见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75-480页。。孝悌力田类制举科目,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孝悌力田科。明确记载设置孝悌力田科的是开元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藉田赦书》,云:“孝悌力田,乡闾推挹者,本州长官勘实,有才堪应务者,各以名奏。”[38]卷74十月,此次制举开科,玄宗又下诏云:“文学、政事,必在考言;孝悌、力田,必须审行。顷从一概,何谓四科?其孝悌力田举人,宜各自疏,比来事迹为乡闾所委者,朕当按覆,别有处分。”[29]卷639可惜,是年有茂才异等科、文藻宏丽科及第者,但未见孝悌力田科及第者。肃代之间,屡次下诏开孝悌力田科,但未见有人及第,这大概是受到藩镇叛乱、割据的影响,忠孝观念淡薄,对中央政府极为不利,因此,肃宗和代宗利用制举因事设科的特点,力图设孝悌力田科表扬忠孝,改变社会风气,但乱世难有以孝悌力田声名卓著者,故考策官不轻易放此科举人及第。由于孝悌类科目往往名不副实,在唐代“以文取士”的大环境下,很难选拔出真正孝悌、力田之人,故此类科目一直不盛。*详见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0页。
总之,唐代进士、明经系诸科均兼习《孝经》《论语》,作为科举考试必考内容;童子科考试,更是以《孝经》《论语》为主,无疑学习《孝经》对从事举业的举子来讲,就是必读儒家经典,儿童学习《孝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应试教育需要。作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最核心经典的《孝经》,是“百行之本”、“德之本”,深受统治阶层重视。在行幸国子监、举人谒先师等重大国家崇重儒学典礼和仪式上,多开讲《孝经》,代表崇重儒学和学校教育。这无疑大大提高了童蒙教育对《孝经》的重视,在加强对《孝经》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咏孝经十八章》等辅助性童蒙读物,在编撰童蒙教材时就会把《孝经》和“孝道”观念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唐五代有关《孝经》教育内容丰富多彩,方式多种多样,充斥到社会每个角落,对培养儿童正确孝道观念,树立“百行之本”,以立身扬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杜甫说:“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39]卷222把《孝经》作为读书人不可或缺的经典,需要时时翻阅。晚唐薛逢《邻相反行》云:“家藏一卷古孝经,世世相传皆得力。”[39]卷548随着整个社会对《孝经》崇重,唐代对童蒙教育的影响在各方面都可以反映出来。
参考文献:
[1]王子今.两汉童蒙教育 [J].史学集刊,2007(3):15-25.
[2]吴 刚.全唐文补遗[M]∥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3](唐)权德舆.权德舆文集 [M].霍旭东,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宋)刘清之.戒子通录 [M].影印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后晋)刘 昫,等.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周绍良.全唐文新编 [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9](清)董 诰,等.全唐文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 [J].敦煌学辑刊,1987(1):26-40.
[11]伊藤美重子.敦煌の学郎题记にみゐ学校と学生 [J].唐代史研究, 2011(14):65-70.
[12]金滢坤.唐五代敦煌寺学与童蒙教育 [M]∥童蒙文化研究: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3](汉)公羊寿,传.何 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序 [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5](唐)独孤及. 毘陵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6](唐)罗 隐.罗隐集·杂著·钱氏大宗谱列传·师宝钱公列传 [M].雍文华,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金滢坤.童蒙文化研究: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9](魏)王 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 [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0](唐)杜 佑.通典 [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21](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 [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2](唐)魏 征,等.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23](唐)刘 肃.大唐新语 [M].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2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5](唐)柳宗元.五百家注柳先生集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7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6](唐)李林甫,等.唐六典 [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7](唐)张 说.张说集校注 [M].熊 飞,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28](宋)王 溥.唐会要 [M].北京:中华书局,1955.
[29](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0](唐)王 维.王右丞集注 [M].(清)赵殿成,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31](宋)薛居正.旧五代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2]龚延明.唐孝廉科置废及其指称演变 [J].历史研究,2012(2):174-182.
[33](汉)郑 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4](唐)李隆基,注.(宋)郉 昺,疏.孝经注疏 [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5](晋)杜 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6](汉)班 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7]劳 幹.汉代察举制度考 [J].史语所集刊,1948(17):116.
[38](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9](清)彭定求,等.全唐诗 [M].北京:中华书局,1960.
——五常市实验小学校教育剪影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