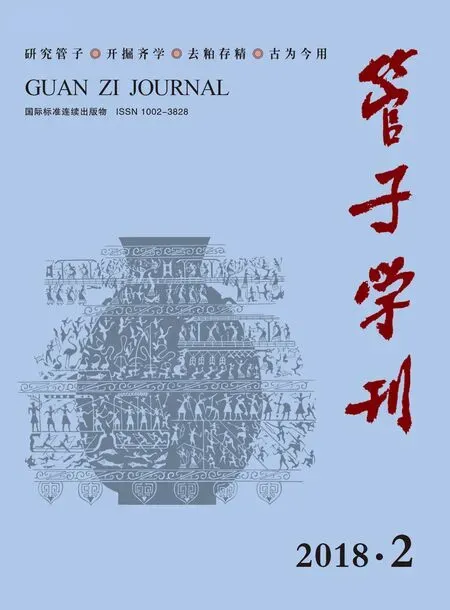章太炎《管子余义》述议
王 诚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清代中叶以后诸子学兴起,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乾嘉诸老都曾致力于先秦诸子的校议和考释,后者还专门作过《墨子间诂》,王先慎、郭庆藩、王先谦也分别对《韩非子》《庄子》《荀子》作过集解、集释。章太炎作为乾嘉学派的“殿军”,在诸子研究上既秉师承传统,又能推陈出新、多有创获。他对《管子》一书作过较为集中的研究,重视文献的考据,善于从音韵、训诂入手解读字词、考释疑难,成果以考据为主,也兼涉义理。他早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经学和小学,期间随日札录,撰成《膏兰室札记》,三卷共474条,皆为考释载籍或驳论旧注之作,范围广涉先秦两汉典籍以及中古史书、训诂专书等。其中有关《管子》的考证条目多达135条,对《管子》字词文句中的疑难多有发覆。但自谓“滞义未除”,未能手定问世,中岁以还,独选取其中部分辑为《管子余义》。1897年发表在《经世报》上的《读〈管子〉书后》则对《管子·侈靡篇》(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中的经济思想作了深入的阐释和新的解读[1]。
《管子余义》收入1933年浙江图书馆刊印的《章氏丛书》。1986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第六卷,由沈延国校点;2014年又收入新版《章太炎全集》第一辑。《管子余义》考证《管子》中的疑难字词、文句共62条(其中正编54条,补编8条),除2条外(此2条涉及纬书,当是后补)均见于《膏兰室札记》,因此可以说,《管子余义》是章太炎《管子》字词考释札记的精选和汇编。本文尝试从章太炎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新的发明、训诂考释方法的渊源和特色、考释的疏误以及训诂考据之外的其他内容等四个方面分析和论述《管子余义》的成就和不足。
一、继承前人成果并有新的发明
章太炎受业于俞樾,同时受孙诒让的影响,俞樾和孙诒让皆传习乾嘉考据之学,服膺和继承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平议》和孙诒让《札迻》中都有关于《管子》字词考释的内容,章太炎充分吸收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形势》“飞蓬之问,不在所宾”条,尹知章注:“蓬飞因风动摇不定,喻二三之声问,明主所不宾敬。”俞樾《群经平议》云:“此未达问字之义也。问犹言也。《广雅·释诂》:‘言,问也。’言为问,故问亦为言。飞蓬之问,犹飞蓬之言也。”《管子余义》云:“俞先生以问为言,是也。”[2]195又如《侈靡》“鼠应广之实,阴阳之数也;华若落之名,祭之号也”条,章太炎云:“俞先生据尹《注》应字若字为衍文,是也。”[2]210再如《心术上》“直人之言,不义不顾”条,对于下文“莫人,言至也……因也者,非吾所顾,故无顾也”一段,完整引用了俞樾的解释[2]211。同时,章太炎也注意吸收日本学者研究《管子》的最新成果,如《轻重己》“秋至而禾熟,天子祀于大惢”条,《管子余义》引日本汉学家安井衡的说法:“大惢盖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惢。”[2]221章太炎认为其说确凿①类似的观点已见于《通雅》,卷十二云:“太惢,秋祀也。……天有五帝星,心宿其一也,为天子之心,心中一星曰天王,其次舍曰大火,秋为七月流火之候,而东方宿属木,金令克木,故祀之惢乃心宿之聚象也。”。但另一方面,这种继承又是批判性的,即在辨析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如果我们拿《管子余义》与《札迻》相比对,可以发现其中有三条重合,即《幼官》“刑则交寒害釱”和“刑则绍昧断绝”以及《地员》“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但二者的考释迥异。下面着重从四个角度举例说明章太炎如何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明。
(一)发前人未发之覆,证成前人的观点。例如《七法》“故攻国救邑,不恃权与之国”条,《管子》一书共有四处用到“权与”一词,其他三处分别为《幼官》:“慎号审章,则其攻不待权与。”《事语》:“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与。”②今本“与”字作“舆”,王念孙已指出“此后人不晓文义而妄改之也”,见《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轻重甲》:“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指出“‘权与’为与国”,但“未说权字之义”。为此,章太炎提出他的观点,认为“权、圈声义相同”,并引《管子》本书内证,《幼官》:“强国为圈,弱国为属。”《立政》:“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圈属”与“群徒”对文,故“圈”“群”义同。又,“麇”和“圈”通,《左传·昭公五年》:“求诸侯而麇至。”杜注:“麇,群也。”故“圈、权、麇皆训群”。《说文》:“与,党与也。”“群、与义相同”,因此。“权与”可视为同义并列,可指与国[2]195-196。
(二)根据前人的结论作进一步推论和引申。例如《幼官》“十二小郢、十二中郢、十二小榆、十二大榆”条,王念孙《读书杂志》把《宙合》篇“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的“浧儒”读为“逞偄”,认为“皆字之误也”,“逞与盈同,偄与緛同”,引《广雅》:“緛,缩也。”又引《淮南·人间篇》:“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嬴缩、卷舒,与物推移。”认为“诎伸、嬴缩,即诎信、盈緛”。章太炎肯定了王念孙对“盈緛”的解释,但同时指出“儒之与偄,古盖同字,而非误写”,并举例证明“耎”“需”声通,“儒”可通“緛”,然后以王念孙的结论为依据,推证“郢”即逞,而“榆”即儒,“郢榆即逞儒,亦即盈緛”,引申之义为长短,从而指出“小郢”“中郢”“小榆”“大榆”是“以其日之长短言之”[2]196-197。
(三)提出不同的意见,指明前人未恰之处。例如《小匡》“举财长工,以止民用”条,王念孙认为“止”当为“足”,但章太炎引《尔雅·释诂》“止,待也”,指出“待、止声义同”。“待”有供给义,《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待邦之用”,注:“待犹给也。”“止民用”与“待邦之用”相类似。又引《说文》“偫,待也”,指出“偫”可引申为备具之义,“止民用亦即偫民用”[2]201。又如《心术上》“直人之言,不义不顾”条,王念孙认为“直人”当为“真人”,但章太炎指出,“义与顾意相近,义借为俄”,都有倾邪、偏倚的意思,“顾”《说文》训“还视”,“还视者,亦必倾邪其目以眄睨”,“凡倾邪者,必有所偏倚”,所以“直人”不误[2]211。又如《轻重丁》“溪谷报上之水,不安于藏”条,王念孙《杂志》曰:“报当为鄣,字之误也。”但章太炎认为“报、鄣形声皆不相似,无缘致误”,“报当借为赴”。[2]220再如《兵法》“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匮”条,戴望认为“疑”当为“碍(礙)”之省字,《说文》:“碍,止也。”但章太炎指出“疑本有止义,不必借为碍也”[2]222。
(四)利用前人对其他典籍的训诂成果,解释《管子》中的疑难字词。例如《内业》“遇乱正之”条,旧注曰:“遇废乱,则当正之。”王念孙则以“遇乱”与“爱欲”对文,认为“遇”为“过”之误。章太炎指出“遇即暂遇奸宄之遇”,“暂遇奸宄”出自《尚书·盘庚》,《经义述闻》引《淮南子·原道》“偶智故,曲巧伪诈”,以“偶”为奸邪之称。又《本经》:“衣无隅差之削。”高诱注:“隅,角也。差,邪也。”《吕览·勿躬》:“幽诡愚险之言。”“愚”亦即“暂遇奸宄”之“遇”,“遇”“愚”相通。王引之对《尚书》这个“遇”的分析可以移用来解释《管子》“遇乱”的“遇”,而不必从“遇误为过”之说。章太炎为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举《登徒子好色赋》“愚乱之邪臣”为佐证,指出“愚乱即遇乱”[2]213。
二、训诂考释方法的渊源和特色
章太炎继承乾嘉考据之学,在训诂考释上沿袭了清儒的传统方法。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3]1王念孙《自序》云:“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諊为病矣。”[3]2章太炎在《清代学术之系统》一文中曾总结说:“清代小学所以能成为有系统之学者,即因其能贯通文字、声音、训诂为一之故。”[4]400从《管子余义》的训诂实践来看,他的考据方法既承袭传统又有自己的特色。
(一)因声求义是最为常用的训诂方法。首先,《管子余义》中有大量据声音破假借的例子,如:《幼官》“刑则交寒害釱”条,章太炎认为“交寒”为“骹骭之借”[2]198;“形则烧交疆郊”条,指出“交借为烄,为”“郊即墝之借”[2]198;“刑则绍昧断绝”条,指出“绍借为”[2]198;《宙合》“讂充末衡”,指出“讂借为觼”“充借为统”[2]199;《侈靡》“父系而伏之”条,指出“父乃捕之省借”“伏借为偪”[2]204;“辱举其死”条,指出“死即尸之借”[2]204;“犹傶则疏之”条,认为“犹借为欲”[2]206;“聚宗以朝杀”条,指出“朝当借为昭”[2]207;“使君亲之察同”条,认为“察借为际”[2]207;“椽能踰,则椽于踰;能宫,则不守而不散”条,认为“椽当借为阝彖”“能宫之能读为而”[2]224;《四时》“则民事接劳而不谋”条,认为“接当借为 口翣”“谋者借为悔”[2]212;《七臣七主》“刑振以丰,丰振以刻”条,指出“丰借为锋”[2]214;《地员》“其立后而手实”条,认为“立借为粒”“后借为厚”[2]216;“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条,认为“穀借为録”“造借为次”[2]217;《轻重丁》“其贾中纯万泉也”条,认为“纯借为准”[2]220;“谨守泉金之谢物”条,认为“谢读为豫”[2]220;《轻重戊》“韘十七湛”条,认为“韘借为渫”[2]220;《兵法》“而无所疑匮”条,指出“匮亦止也,字借为言贵”[2]222;《君臣下》“明立宠设,不以逐子伤义”条,指出“逐借为胄”,故“逐子”即“胄子”,亦即嫡子[2]223;《山至数》“鹿台之布,散诸济阴”,指出“鹿当借为録”[2]225。其次,在破假借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指出声符的相通,如《侈靡》“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条,章太炎指出“诸书孚声、包声之字,关通者不可胜数,故可借浮为苞”[2]206。下面将章太炎所举其他声符相通的例子列表如下:再次,《管子余义》中的一些例子还说明同源通用关系。例如《幼官》“三年,名卿请事”条,章太炎认为,“名卿”的“名”并非“名臣”“名士”的“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说文》:“名,自命也。”《广雅·释诂》:“命,名也。”“名”“命”同源通用,“声义皆同”,“名卿即命卿,谓命于天子之卿也”[2]197。又如“刑则交寒害釱”条,引《汉书·扬雄传》“肆玉釱而下驰”“以釱为軑”,说明“軑”与“釱”声义相通,“軑可言辖,故釱亦可言辖”[2]198。又如《君臣下》“中民乱曰詟谆”条,引《说文》:“譶,疾言也,读若沓沓,语多沓沓也。”又引《琴赋》注:“譶,声多也。”指出“譶与沓声义皆同”[2]204。又如《侈靡》“辱知神次者”条,引《广雅·释器》:“蓐谓之菆。”《说文》:“菆,一曰蓐也。”指出“菆、蓐一声之转,音义皆同”。又引《墨子·明鬼下》:“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读书杂志》曰:“菆与丛同,位当为社。”《急就篇》“祠祀社稷丛腊奉”,“丛”一本作“菆”。据此认为“蓐、菆、丛一声之转”[2]205。再如《七臣七主》“刑振以丰,丰振以刻”条,指出“此振则训重”,并引《曲礼》“袗絺绤”、《诅楚文》“绅以昏姻,袗以齐盟”,认为“申、袗皆重也”又《释言》:“眕,重也。”《韩诗·云汉》“胡宁疹我以旱”《传》:“疹,重也。”章太炎云:“皆是重复之重,与袗声义相同者也。”[2]214

?
(二)重视《说文解字》,充分利用《说文》中的字形和训释解决疑难问题。例如《问》“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条,“诡”字前人多以常用义欺诈来解释,于文未恰,章太炎引《说文》“诡,责也”,认为“此言人有余兵,则责其陈之于行伍,不得私匿,所以慎国常也”[2]202。据《说文》则“诡”的本义是责,段玉裁注引《汉书·赵充国传》:“况自诡灭贼。”又引孔融《荐祢衡表》:“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5]100义皆训责。此义后世少见,如不熟悉《说文》,则易造成误释。
(三)利用“连文”上下二字的同义关系推求词义。例如《兵法》“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匮”条,前文已指出“疑”是止义,而“匮”旧注未恰,章太炎认为,“匮亦止也,字借为言贵,《说文》:‘言贵,中止也。’”又云:“疑言贵并言,犹《诗》‘靡所止疑’,亦以同训字并言耳”[2]222。又如《戒》“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条,尹注:“为犹与也。言妾身在深宫之中,未尝得出与人相持而接对。”章太炎认为“此望文生义也”,他引《诗纬·含神雾》:“诗者持也。”《仪礼·特牲礼》:“诗怀之。”注:“诗犹承也。”《礼记·内则》:“诗负之。”注:“诗之言承也。”指出“持、承同义,承、接意相近,承即承事君子之承,接即接见君子之接,皆谓为人婢妾也”[2]222。
(四)内证与外证相结合,即将《管子》本文中的证据和他书中的证据相结合,来考释字词意义。例如《形势》“飞蓬之问,不在所宾”条,章太炎以本书《形势解》篇“飞蓬之问,明主不听也”说明“宾当与听同义”,同时引《广雅·释诂》:“听,从也。”《尚书·尧典》:“寅宾出日。”马融注:“宾,从也。”证明“宾与听皆为从,则宾亦得为听”[2]195。又如《幼官》“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条,引《尔雅·释言》和《考工记·轮人》注说明“称”有好义,同时指出本篇上文云“求天下之精材”,《小问》篇有“选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精材”,可确证“称材”就是好材料,亦即美材[2]197。
(五)文化索义,即从语言之外的文化观念的线索出发来解释词义,揭示词句中所凝聚的文化信息和因素。例如《七法》“衡库者,天子之礼也”条,尹注:“衡者所以平轻重,库者所以臧宝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当准平天下,既知轻重审用于心,无令长耳目者所得,此则天子之礼然也。”章太炎一方面肯定了这种解释,另一方面又指出其“未明措词之由”。为此,他引《汉书·天文志》:“南宫朱鸟权衡,衡大微三光之廷。轸南众星曰天库,库有五车。”认为“衡库皆南宫之星,而又皆隶于五帝,故假天象以明帝制耳”[2]195。这是运用古代天文知识来推求名源。又如《君臣上》“下有五横,以揆其官”条,章太炎指出“五横即五潢,假天象以名官也”[2]202。又如《宙合》“物至而对形,曲均存矣”条,古注未释,章太炎指出,“曲即曲矩之曲”“均即陶钧之钧”“曲为匠人模范之器,钧为陶人模范之器”[2]199,本篇“宙合”为天地之运转,章说正是从《宙合》全篇的语境及其文化背景来推定“曲”和“均”的所指。再如《山至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条,据《释乐》“大钟谓之镛,小者谓之栈”,释“栈台”为钟台,同时指出“凡铸钱与钟皆用铜,故古者或以一官掌之”,“藏钱于钟栈同处”[2]225。
三、《管子余义》在考释方面的疏误
《管子余义》是章太炎早年课艺的结集,虽然经过筛选拣择,但还是存在一些求诸过深、穿凿附会之处,有不少误释和纰漏。近人黎翔凤《管子校注》征引各家之说,其中包括章太炎的不少观点,同时也有自己的案语。我们从《管子》原文出发并对照《校注》中的不同意见,整理出《管子余义》考释可商或疏误不足取的条目,下面试举例说明。
(一)改易文句可商。例如《君臣下》“以德弇劳,不以伤年”条,章太炎认为“当作不以年伤”,且“伤借为扬”“不以年扬者,谓不以历官积日而举之”[2]203。但是黎翔凤在《校注》中指出,“任何政府未有专重德而不顾年资者”,下文云“及年而举”,可证兼顾年资[6]596。所以太炎的改动未必确切。又如《七臣七主》“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佰其本也”条,章太炎认为,“淫当为徭之误。……调徭犹言均调,言有轻重羡不足贵贱之殊,而上不为平准、均输等法以均调之,则游商之利息,得什伯其本矣。”[2]215但黎翔凤指出,“《书·无逸》‘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郑注:‘淫者浸淫不止。’谓不调其浸淫不止者,非误字。”[6]994
(二)破读假借不确。章太炎早年受其师影响,在因声破假借上勇于立异,乃至有过滥之嫌。例如《君臣下》“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条,章太炎认为“沈借为抌。《说文》‘抌’下曰:读若告言不正曰抌。是抌有告言不正之义。……抌疑得民者,谓诈为君欲虐下之言以欺民,所以扇诱民而得其心。”[2]203此说过于迂曲,且所引《说文》读若,宋本无告字,段玉裁云:“曰抌之抌未知何字之误。”[5]60“9抌”的告言不正之义未见文献用例,较不可靠。因此,不如黎翔凤《校注》依本字解较为直截,“沈疑”即沈默而凝定[6]579。又如《势》“大文三曾,而贵义与德;大武三曾,而偃武与力”条,章太炎把“曾”读为“载”,认为“三曾”就是三年[2]212,但正如黎翔凤指出的,《管子》一书“无以年为载者”[6]892,由此可知章说不确。
(三)名物训释牵强。如《臣乘马》“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条,章太炎认为“扶盖蒲之假借”。《释名·释宫室》:“草圆屋曰蒲。蒲,敷也。总其上而敷下也。”由此推测,“此岂僭为清庙茅屋,上圆法天,复立灵台,以观天文之制,犹其欲行封禅之侈心欤?”[2]217-218这个说法较为牵强,并无足够的证据。黎翔凤认为,“‘扶台’为训练扶身之士而筑,寓兵于农。……于农忙立扶台,则春失其地,夏失其苗。”[6]225
(四)拆解联绵词。如《地员》“其人夷姤”条,尹注:“夷,平也;姤,好也。”章太炎云“此训未的”,他认为“夷”有悦义,“姤即逅”。《诗·绸缪》:“见此邂逅。”毛传:“邂逅,解说之貌。”因谓“此以解释邂,以说释逅,即悦字也”“然则夷姤皆谓悦,谓其人容颜悦畅也”[2]217。但是,“邂逅”一般视为双声联绵词,又作“解构”。胡承珙《毛诗后笺》:“邂逅,会合之意。《淮南·俶真训》:‘孰肯解构人间之事。’高注:‘解构,犹会合也。凡君臣、朋友、男女之会合皆可言之。’传云‘解悦之貌’,即因会合而心解意悦耳。”据此,将“邂逅”拆解为解和悦不确。王绍兰、张佩纶训“姤”为厚,黎翔凤认为此说较胜[6]1105。
(五)辗转为训致误。三个及以上的字辗转相训称为递训,递训本为训释的一种形式,但在此过程中容易偷换义项,特别是以字代词、以训代义,造成词义相远。如《内业》“凡道无所,善心安爱”条,章太炎认为“爱借为隐”,又云“此隐则训据”,谓此句“言凡道无常处,惟善心于是依据也”[2]213。此说不妥,“爱”即“薆”,确有隐义。如《诗经·邶风·静女》“爱而不见”,但这里所谓的“隐”指遮盖、隐藏,与“隐”的据义是两个不同的义位。由此可知章说不可信。
四、《管子余义》所涉及的其他内容
《管子余义》的主要内容是训诂考据,但与《读书杂志》《群经平议》《札迻》等一样,这些札记中也有涉及其他方面的条目,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内容。下面从句读校勘、篇章文法以及章句义理等方面略述一二。
(一)关于《管子》原文的句读和校勘。与王念孙、俞樾和孙诒让有所不同的是,章太炎在校勘上措意并不多,《管子余义》中没有专论校勘的条目,但是在训诂考释的条目中偶尔也会涉及句读和校勘的内容。例如《内业》“凡道无所,善心安爱”条,尹注:“道无他善,唯爱心安也。”章太炎认为旧注“大误”,指出“所字当断句,处也”[2]213。又如《小问》“臣使官无满其礼三强,其使者争之以死”。尹注:“不识不满之意,才激强之,则争之以死,是不智。”章太炎指出“尹读三字绝句,强字属下。……此说非也。强当属上句读”[2]214。又如《七臣七主》“臣主同则,刑振以丰,丰振以刻”条,指出“则字当断句。……与上句上下相干,文义一贯”[2]214。又如《轻重戊》“夏人之王,外凿二十,韘十七湛”条,指出“外字总举以下诸事”,“字断句”[2]220。再如《宙合》“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条,指出“行忿速遂句,没法贼发句。丁氏士涵乃欲读行忿速遂没法为句,……不知上文没法二字,实涉此处而衍,言止忿则事速成,正明所以毒而无怒之故,不容有没法二字也”[2]221。校勘方面如《君臣下》“明立宠设,不以逐子伤义”条,章太炎认为:“伤义乃后人增窜之字。知者,‘不以逐子’,与‘势不并伦’‘礼无不行’相俪。彼皆四字句,则此亦当然。”[2]223
(二)关于篇章文法方面的内容。章太炎在字词训释之外对构词、文法、篇章等层面也有所关注,这体现出他在语言学上的开阔视野和独到见解。试举例说明。《幼官》“十二小榆、十二大榆”条,在证“榆之即儒”时提到“《荀子》言偷儒,言偷懦,《方言》言儒输,皆举叠韵为连语也”[2]197。王氏父子已使用“连语”这个概念。《读书杂志·汉书十六》云:“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7]407章太炎沿用了这个术语,并进一步指出连语也可分开单用。《四时》“民事接劳而不谋”条云:“接当借为噿。……窃谓噿喋本叠韵连语,与苛事连文,当即谓烦苛之意。连语者亦可单语,故此单言噿也。”[2]212又如《轻重丁》“皆以鐻枝兰鼓”条云:“枝兰本实指物体,亦可转言物用,鐻枝兰鼓言以鐻枝兰此鼓也,犹言鐻架鼓耳。”[2]219这里提到了词性的转换问题。又“其贾中纯万泉也”条云:“湻、纯、准三通也。中万泉与准万钱同意。中准两言者,古人文法多复举也。”[2]220这是指先秦的复音结构。又如《轻重己》“天子祀于大惢”条云:“大琐与夏至所祀之大宗,秋始所祀之大祖,文法一例,而事则相异。”[2]221即这三个词的语法结构相同,但语义有别。又如《侈靡》“辱知神次者”条云:“菆社即丛社,本当言社丛,谓社神之丛位,古人文法倒耳。”[2]205《戒》“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条云:“于人承接,即承接于人,古人语多倒句,类如此也。”[2]223《侈靡》“椽能踰,则椽于踰”条云:“阝彖于踰犹踰于阝彖,亦倒句也。”以上三例是说明上古构词和语法中的倒装现象。再如“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臧”条云:“次浮、差樊、瘗臧三者平列。次浮下有也字助语词,古人立文,不必截然整齐,亦所以免平直也。”[2]206这里提到古人行文的变换。章太炎对于文法、篇章的关注,很可能是受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启发。
(三)关于章句和义理。《管子余义》虽以字词考释为主,但也间或有章句的说解,其中最典型的即《山至数》“桓公问管子曰”条,章太炎解释说:“此一章,论厚葬之非也。”随后逐句串讲,除“室犹冢圹”和“国会犹国计”两处训释字词,其余皆为章句的解说[2]218。又如《度地》“桓公曰”条,对管仲所述“扼水使高之法”作了细致的解释[2]215。此外还有一例较为详尽的章句义理的分析,《侈靡》“请问形有时而变乎?(至)图具其树物也”条,此条特别之处在于章太炎用汉代兴起的谶纬之说来解读《管子》的这段话①《管子余义》另外一处涉及谶纬的是《大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条。,认为“此管子所定之谶,托桓公问以明之也”,并将“佁美然后有煇”“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溪陵山谷之神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也”等一一对应于齐桓元年之后的若干史实、事件[2]208-209。

(谭玉伟 篆刻)
作为早年研读《管子》札记的精选和汇编,《管子余义》充分体现了章太炎学术生涯初期的治学风格,从中可见乾嘉诸老特别是师辈对他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他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独立思考和进一步开拓。一方面,《管子余义》在训诂考释和词义分析上有精彩的发明,并且在句读校勘、篇章文法以及章句义理等方面也作了有价值的探讨,这些成果为后人注解《管子》所吸收。如黎翔凤《管子校注》收录和引用了《管子余义》中大多数条目,或者对章说加以肯定,或者将其列为一说。但另一方面,《管子余义》在训释方面也存在不少疏误,求诸过深、穿凿附会之处不容讳言,对于这些疏误的条目,《管子校注》或者舍弃不引,或者征引之后加上按语,提出不同意见。从《管子》研究史的角度出发,客观地看待章太炎这一得失参半之作,特别是将其与王念孙《管子杂志》、俞樾《管子平议》以及孙诒让《管子札迻》相比较,可以看到章太炎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对前辈学者的继承,同时也不难发现他独到的观点和新的发明,在这种纵向的比较中更能明确《管子余义》在《管子》研究史中的位置。
参考文献:
[1]王学斌.晚清管子研究述论[J].管子学刊,2009,(1).
[2]章太炎.章太炎全集·齐物论释、定本、庄子解故、管子余义、广论语骈枝、体撰录、春秋左氏疑义答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王念孙.广雅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
[4]傅杰.章太炎学术史论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王念孙.读书杂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