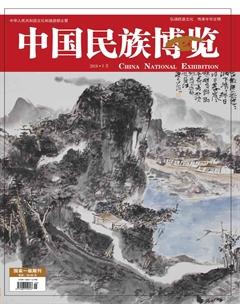从“象”“意”“法”三个要素分析来临习碑刻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书法中“象”“意”“法”的哲学渊源,并通过对《礼器碑》《开通褒斜道碑》中的这三个要素进行分析,探索临习这两个作品的正确方法,并举一反三,最终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找到临习碑刻的恰当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象;意;法;碑刻;临习方法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哲学里的“象”不同于西方哲学里的“象”是客观事物的表象,而是沟通自然与人的桥梁。“象”具备了一定的非客观性。老子最先提出了“象”的概念。老子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老子》)。老子认为,“象”是本体“道”的显现。它可以传递“道”的真意,总的来说,象既是客观之物,又是非客观之物,是“道”的外显形态。“意”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层含义是指主体的主观思想,《说文解字》中云:“意志也,从心音,察言而知意也。”第二层含义是指物象之外体现的一种意识观念;第三层含义是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意”。我认为,“意”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又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法”从中国哲学角度出发是以“道”为基础而建立的不可违背的原则法度。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哲学中的“象”“意”“法”都是以“道”为根本原则的,都是“道”在不同层次上的展现。而具体到书法上,“象”包含了书法单字的结体与造型,笔画的形态与倾仰。而中国汉字结构造型的起源本身就源自自然之物,更使汉字的“象”成为了一种掺入了人的主观思想的“道”的展现。书法中的“意”就如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解释的三层含义:“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有时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书法中的“法”包括了“笔法”“字法”“章法”等概念。
从汉代起,书法理论一经产生,历代的书法理论家的众多书势、书赋的论述都逃不出与书法相关的三个要素,这便是“象”“意”“法”。许慎的《说文解字》最早揭示了中国书法的象形意义,魏晋的众多书家更是将书法的“形”与自然之物象联系以论述书法创作过程中“象”的问题。如卫夫人《笔阵图》中就用自然物象规定了汉字的七种基本笔画的形态:“横如千里阴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山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撇如陆断犀象之角,努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钩如动弩劲节。每为一字,各像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随着书法中“象”的发展与完善,书法家及书法理论家便更加重视书法中的意蕴气息,如黄庭坚的“以禅喻书”以及米元章的“真趣论”等都是重在追求一种书法作品“象”以外的文人气息。我们创作时所追求的书卷气、金石气、庙堂气等都是超越“物象”之外的“意”的体现。“法”这一要素更是几乎贯穿于整个书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赵孟頫云:“书法以用笔为上,结字亦需工。盖结字因时而异,用笔千古不易。”由此可见,笔法的重要性。所以,想要在历代的铭刻书法中得到滋养,必定要因碑而异从“象”“意”“法”三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做出适当的取舍,把握不同的侧重点总结出一套完善的方法指导自己实践,最终才能入古出新有所得。
《礼器碑》无疑是汉代碑刻中的精品之作,从“象”的角度观之,此碑严谨之中不乏变化,波磔分明。如清代王澍在《虚齋题跋》中云:“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可见从“象”的角度,古人给予了礼器碑很高的评价,也能看出《礼器碑》是学习汉代隶书的典范之作,故临习者从“象”的角度出发,可以尽量做到尊重原帖以熟悉汉代碑刻的结体及造型规律,通过临摹的深入逐渐增加自己对作品结字造型的敏感程度,使得作品中的结字规律和造型特点逐步内化为己所用,最终通过临摹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从“意”的角度出发,由于礼器碑的纵有序、横有列、字距宽、行距窄的章法特点,使得作品展现出和谐端庄的特征,又因为单字结字严谨而不失变化,用笔精到而不趋于流俗而使得作品富有流动感,通篇自然灵动而富有生机,可谓端庄与灵动并存。所以,这要求临习者在临习的过程中应尽量表现出作品中的端庄和谐之气,又不能忽略字里行间的灵动秀美之感。另外,能够准确把握书法作品中的“意”与书家自身的文化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书家具备了较高的艺术修养之后,才能与准确感受作品带给自己的心灵震撼,才能与古人的“意”产生共鸣。这就要求书家在伏案写字的同时,还要通过读古今好的文学著作增加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
最后从“法”的角度分析,因为无论碑帖,只要是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都包含了“笔法”“字法”“章法”。而字法直接对应了书法作品中单字的结体与造型,这在“象”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讨论,在此不过多赘述。从“笔法”角度看,此碑起止提按明显,锋芒毕露,如睹墨迹。故临习者可以用“透过刀锋看笔锋”的方法揣摩笔画的起止之锐圆,行笔之提按。在临习过程中,初学者可以尽量做到尊重原碑的笔法特点,随着临习的加深,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艺术追求的需要,对此碑中波磔过分明显的特征加以分析进而做出适当的取舍,避免落入如唐人隶书的庸俗一路。从章法角度看,此碑采用了纵有序、横有列、字距宽、行距窄的章法,章法设计严谨规整,变化不明显,所以,临习者在临习的过程中需尊重原碑章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作品中和谐端庄的气息。
与《礼器碑》相比较,《开通褒斜道碑》因为摩崖刻石,则其因山而就,稍加修整,大书深刻,浑穆苍茫。临习者往往对于此碑感到无从下手,也不能正确认识学习此碑的目的。
从“象”的角度出发,此碑因做于山崖之上,字径较大,结字法度及造型规律并不严谨清晰,加之临习者在临习过程中也无法按原比例一比一临习,所以,在临习过程中不必过多纠结此碑的结字规律,以免陷入怪圈,但是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分析此碑笔画长短阔狭之随意,结字造型之大胆,从而感受工人在就崖而书时的创作状态,那一定是一种最纯真、最专注、最能体现个性的创作状态,这样的探究对于书家以后的由临转创有着积极的作用。
从“意”的角度出发,因创作条件的限制以及创作者“书无定法”的创作状态,反倒为人们带来一种天真烂漫的艺术风格,给观者带来一种最真实、毫不做作的艺术美,加之摩崖刻石长期的风吹雨蚀,加深了碑刻中的斑驳苍茫之感,给人以别具一格的艺术感染力,所以,临习者在学习此碑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感受此碑中高古天真蒼茫的气息,多临习此类作品对提高艺术家的艺术修养、了解汉代人们最真实的书写状态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最后从“法”的角度分析,从“笔法”看,由于此碑刻于山崖之上,本身的镌刻难度就较大,加之多年的风吹日晒,所以,如今呈现给我们的刀斧之痕早已与当年镌刻前的墨迹之痕有了较大出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临习者就需要通过自己临习碑刻的经验心得,找到一种符合隶书普遍的用笔规律,并能够较为准确地表现此碑结体造型的用笔方式,并且能淋漓尽致地展现此碑高古天真、苍茫气息的用笔方式,只要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即可称为真确的用笔方式。而并不是纠结于原碑用笔,对于此类摩崖如果拘泥于用笔,反而会使自己南辕北辙。从“章法”观之,此碑采用了纵有序,横无列,字距窄,行距宽的章法布局。并且单字大小不一,倾仰方向各异,千字千面,不可端倪,使得整体章法如乱石铺阶。而但从艺术的角度看,此碑章法与礼器碑相比,更能给予临习者市局冲击与艺术启示,所以,临习者在临习过程中应感悟此碑所透露出来的高古天真的气息与其章法的关系,细细揣摩,并通过实践细细摸索。
通过从“意”“象”“法”三个方面有条理、分层次对《礼器碑》和《开通褒斜道碑》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临习过程中应对《礼器碑》带给我们的“象”和“用笔”多下功夫,全面把握汉代规范隶书的结体造型特征以及用笔方式上的特点。而对于《开通褒斜道碑》,我们可以把侧重点放在“意”上。通过摩崖刻石表现给书家的高古气息指导自己创作,并通过作品揣测古人最真实、最放松的创作状态,从而指导自己的实践。
参考文献:
[1]王镇远. 中国书法理论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王镛. 中国书法简史(BZ)[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华人德.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4]杨春时,杨晨.中国古典美学意象概念的主体间性[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4):21-25.
作者简介:孙政,男,汉,山东建筑大学,研究方向:美术学(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