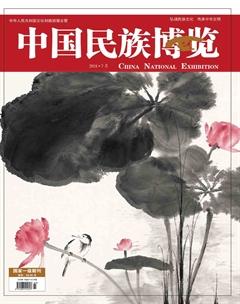浅论柳宗元诗的骚怨与淡泊
【摘要】柳宗元诗现存160余首(《柳宗元集》),絕大部分作于贬谪期间。柳诗淡泊简古、幽清冷峭,表达了内心的忧愤寂寞,揭露社会矛盾,寄托政治理想。既有“屈骚”式的怨刺讽喻,也有酷似陶渊明诗的自然恬淡。
【关键词】柳宗元诗;贬谪;骚怨;淡泊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为中唐文学家、哲学家,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公元805年因王叔文集团案遭到迫害,贬永州司马。“自此蹭蹬不振,以是益自刻苦为文章,养成了隽郁而清幽的作风。”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在更加艰苦而偏远的蛮瘴之地生活了四年,便病死于柳州,年47岁。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柳宗元少时曾负大志,并在追随王叔文期间得以施展政治才华,以挽救国家衰微、造福天下百姓为己任。然而,当时社会的黑暗势力过于强大,他们的革新措施遭到打压之后,本人也无法摆脱窜逐身死的命运。自屈原始,封建社会官员被贬至边远地区是极为常见的情况。贬谪官员的心态也由个人性情的不同而表现为乐观豁达或者消极低沉两种。前者如苏轼,后者恰如柳宗元。
柳宗元一生留有作品六百余篇,其诗歌清冷幽峻,淡泊简古,传世作品虽不多,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室中语》云:‘人生作诗不必多,只要传远。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给予柳诗极高的评价。诗人不仅有深刻的哲学思维、深厚的文学造诣,更有别人难以体会的艰辛的人生历程,使其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
一、仕途起骚怨
《旧唐书》卷一六〇《柳宗元传》云:“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故柳宗元诗中的骚怨精神,实渊于屈原。究其原因,柳宗元与屈原的相同之处甚多:同样有着美政理想,同样遭遇贬谪他乡,同样的文采飞扬。当然,两者相距千余年,自然少不了后者对前者作品的认真究读。柳宗元到永州以后,“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杨京兆凭书》)在苦闷孤寂且湘楚文化浓厚的南国,柳宗元读百家书聊以解忧,屈原与之相似的人生经历打动着他,光辉的人格精神照耀着他,自然成为他千年以前的知音,读骚、用骚、写骚,屈骚的哀怨之情与比兴之义深入其心,故“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柳宗元的忧郁和骚的哀怨有共通之处,主要是从精神上接受了屈骚文化。”缅怀屈原而及自身,终至“垂泪对清湘”。与其说此诗是拜贺同僚,不如说是顾影自怜,是对自己身世的无限感伤。“长捐楚客珮,未赐大夫环”“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对“楚臣”“楚客”的追思,无不寄托着自我的情思。总而言之,柳宗元“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将一腔愤懑寄情山水间,发言为文,以屈骚精神为伴。
“少时陈力希公候,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这四句诗可以说是柳宗元一生思想心态和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空有报国之心,却久困于南荒,诗人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无处发挥,只好寓意于诗文,且看他的这些诗句: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蜺断,霹雳掣电捎平冈。……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笼鹰词》
城上日出群乌飞,鵶鵶争赴朝阳枝。刷毛伸翼和且乐,尔独落魄今何为?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尔令尔疾?……
——《跂乌词》
飞雪断道冰成梁,侯家炽炭雕玉房。蟠龙吐耀虎喙张,熊蹲豹踯争低昂。攒峦丛崿射朱光,丹霞翠雾飘奇香。美人四向迴明珰,雪山冰谷晞太阳。……
——《行路难·其三》
诗歌充分运用山川景物、飞禽走兽、香草美人等多种多样的意象,或托物言志,或借题发挥,或以史咏怀,或借古讽今,表现出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士人孤傲高洁的品质。他自比为被困牢笼的苍鹰,期待着某一天重新展翅翱翔。但是奸佞小人的诋毁排挤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终于只能在诗文中申述不平,抒写情怀。
终唐一代,北官南贬这一惩罚制度持续被封建统治者运用着。“驰驿发遣,仍差纲领,送至彼所,勿许东西。”诏书的严词力句明确规定,流、贬者必须遵循固定的驿道前往贬地。于是,南贬的官员们大都行走着相同的路线,共同体验着跨越五岭、南溯沅湘的人生历程。“对于南贬的诗人群体来说,宽阔的驿道是如此地狭窄,因而巧合出许多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际遇。”这个作家群体处世心态和作品风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屈原及其百年后的同道贾谊,作为失意政治家与杰出文学家双重角色的个别性,却在唐代贬谪诗人中发出了‘萧条异代不同时的群体共鸣。”南贬作家的作品中蕴含着屈骚哀怨深沉的特色,以屈原贾谊为偶像,运用楚辞的象征意义,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南贬士人的普遍心态。柳宗元的“凄凄宦情”可以看作是这个诗人群体所共有的特点。
二、解忧学陶潜
对于柳宗元的诗歌,常常会看到“幽峭”“冷峭简淡”这样的评价。苏轼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自此,以“枯淡”评柳诗,谓宗元学陶者代不乏人。黄庭坚曾说:“欲知子厚如此学陶渊明,乃为能近之也。”江西诗派的韩驹也曾说:“柳诗不多,体亦备众家,惟效陶诗是其性所好,独不可及也。”
柳宗元酷似陶诗之类,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与《觉衰》: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久知老会至,不謂便见侵。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伤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时春向暮,桃李生繁阴。日照天正绿,杳杳归鸿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高歌自足快,商颂有遗音。
前首诗人描写自己晨起读佛经,汲井水漱齿,手持贝叶书,在清新幽静的禅院,沐浴着自然的气息,感悟佛理真谛。一句“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与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何其相似!《觉衰》诗中表现出一种对待衰老、对待人生的豁达与超脱,“咄此可奈何,未必伤我心”,没有忧愁,没有愤懑,只有处之泰然的安宁与恬静。“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看到的似乎正是“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的陶渊明。南宋曾季狸《艇斋诗话》评曰:“萧散简远,秾纤合度。置之陶渊明集中,不复可辨。”这类诗歌与政治无关,与仕宦生活无关,诗人仿佛已经放下了官场的失意和羁旅的孤寂,忘记了尘世的纷扰和喧嚣,在纯净的自然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在儒家入世思想的浸润中成长,热心追求理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理想屡遭打击,便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独善其身”,退出或躲避官场的种种争夺倾轧,这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贬谪之初的文士,多是心中块垒难平,故感伤自身遭际,抒发不遇之愁绪,作品也多怨愤之情;而后在时间的打磨下,用世之心逐渐淡化,在现实爱好中寻求解脱,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情趣。陶渊明归隐田园安于农家,不问世事的生活态度,以及在诗文中表现出的快乐和满足,唯美的山水自然所衬托的健康向上的情调,一度成为贬谪诗人们追寻的乐园。柳宗元在这样的境遇之下,以真挚的情感和深厚的文学底蕴为基础,深情地诉说着自己的生活与情绪,形成了他的诗歌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高文,屈光选注.柳宗元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薛天伟、朱玉麒主编.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4]吴在庆.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M].合肥:黄山书社,2006.
[5]洪迎华,尚永亮.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J].文学评论,2004(5).
[6]戴伟华.柳宗元贬谪期创作的“骚怨”精神——兼论南贬作家的创作倾向及其特点[J].文学遗产,1994(4).
作者简介:任慧敏(1987-),女,汉族,辽宁朝阳人,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