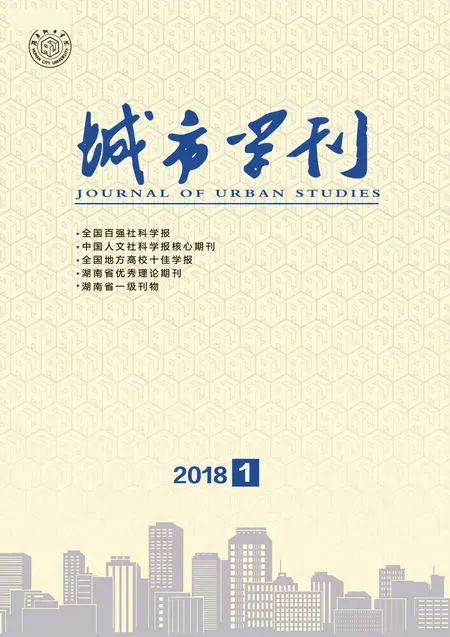财政分权对教育配置效率的影响
——以安徽省为例
王 艳,张焕明
(安徽财经大学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一直以来,教育被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习近平主席更是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水平上。李克强总理强调,办公平优质教育,有效提高教育配置效率,是实现公平优质教育的关键。随着财政分权的提出,其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尤其是教育的供给)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2015年安徽省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告》可以看到,2015年全省的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 157.85亿元,同比增长10.72%,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为856.73亿元,同比增长9.56%。纵观安徽省历年来的教育支出数据发现,教育支出的费用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种现象是否是财政分权带来的?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关注点。
一、文献回顾
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深入,龚锋等(2013)认为,我国的财政分权只是一种非规范的事实分权,下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存在着不平衡的关系,尽管地方政府拥有财政自主权,但是地方官员在决策时往往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李成宇等(2014)指出,由于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是以经济增长作为标准,为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官员的“标尺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将财政收入投入到收效快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忽视了对教育的投入。[2]最早的财政分权理论可追溯到Tiebout(1956)提出的“用脚投票”理论,他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中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模型,认为人们会在社区之间自由流动,选择公共产品供给和税收组合效用最大化的社区政府,社区政府只有提供满足条件的公共物品,否则,社区居民将流动到其他满足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地方政府。[3]然而“用脚投票”理论只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如中国,其实并不适用。乔宝云等(2005)以及刘长生等(2008)认为受到户籍的限制,在中国人口并不具有完全的充分流动性,对于进城打工的劳动力来说,他们并不作为流入城市的合法居民同等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供给。[4-5]因此,“用脚投票”理论反而限制了政府对当地居民偏好的重视程度,影响了公共服务的配置效率。
对基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有很多,但是得到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研究结论主要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财政分权程度会对公共物品——教育的供给产生负作用。如程侃(2013)年以福建省为背景研究财政分权与教育配置效率的关系发现,分权程度的提高反而会降低福建省基础教育配置的效率,应此提出适当的集权反而有利于提高教育的配置效率;[6]李成宇等(2014)运用空间模型分析全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认为,财政分权形成的政府激励会不利于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并且分权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各地的教育支出;[2]宋珏遐(2016)分析财政分权对教育配置带来的地区差异性问题时,认为财政分权对公共教育供给水平具有负面影响,且对中部地区影响最大;[7]其他学者(乔宝云等,2005;刑祖礼等,2012;周亚虹等,2013;潘健,2016)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4][8-10]另一派认为,财政分权会对公共教育的供给带来有利的影响。刘长生等(2008)以我国不同区域的义务教育供给效率为切入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义务教育的提供效率;[5]杨良松(2013)对1995-2008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认为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11]李鼎和赵文哲(2013)区分了预算内教育支出和预算外教育支出,研究认为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提高预算内和预算外的教育支出,形成这种原因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是财政支出分权更多的是体现地方政府的利他性;[12]王志平(2016)以江西省为背景研究地区财政分权,发现地方财政分权提高了教育的支出水平。[13]
从以上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研究财政分权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主要以省级层面为主,很少涉及到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分权问题的研究。并且,众多学者在公共教育的衡量指标的选取中,往往选择了单一的度量指标如乔宝云等(2005)选择“小学入学率”,[4]傅勇和张宴(2007)以“基础科教文卫支出占预算内总支出比重”作为衡量指标,[14]林江等(2011)选择“义务教育完成率”作为教育指标,[15]罗伟卿(2009)选择“小学生师比”,[16]等等。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突出以下三点:一是研究背景不同,以安徽省16地级市作为研究切入点。中国的地方政府可以分为省、地、县、乡四级地方政府,如果仅关注省级财政分权对公共教育提供的影响,显然是不够精确。根据1985年先后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义务教育法》,各级地方政府由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代理者转变为提供者,在教育的供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故应考虑到省内各地级市的财政分权对公共教育配置的影响问题。二是指标选取不同。如前所说在研究公共教育配置效率时,多数学者往往选择单一指标对其进行衡量,根本无法系统、全面地反映公共教育的配置效率。本文将基于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选取安徽省2000-2015年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投入产出指标来测量公共教育的配置效率。三是对数据进行调整。在本文分析的时间区间内发生了巢湖撤市的行政区划变动,多数文章往往很少对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受影响的经济数据进行调整。本文认为,巢湖撤市后,相关联的合肥、芜湖以及马鞍山三市的人口变动最为显著,而其中的劳动力人口显著增加是三市各经济指标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基于劳动力增长的情况对三市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
二、安徽省公共教育配置效率与财政分权指标测算
(一)指标选取
1. 教育配置效率指标
理论上,只有将所有衡量公共教育配置效率的直接指标与间接指标都纳入到DEA模型中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最为全面和精确的公共教育配置效率值。考虑到一些数据的缺失或难以获取,且全部考虑在内会使得运算量过大。本文选取的单一投入指标为各地市财政教育支出,产出指标包括各地市的幼儿园数、小学和中学学校数、小学和中学生师比(在校生数与任教老师的比值)、小学和初中升学率。
2. 财政分权指标
财政分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收入,另一个是财政支出。多数学者在选择财政分权指标时,往往仅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对另一方面则在模型分析结束后的稳健性检验中涉及到,得到的研究结论也是从两方面来说。本文认为,既然财政分权指标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在实证研究中就应当综合考虑。基于此,文章将从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支出两方面进行研究,使用Shannon-Spearman的SSM信息损失最小准则进行指标综合。
本文数据选取的时间段为2000-2015年,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安徽省统计年鉴2001-2016》。
2011年之前,安徽省下设17个地级市。2011年国家和安徽省政府新的行政区域规划出台,撤销巢湖市,将其下辖的县区划分到合肥、芜湖和马鞍山市。其中,原巢湖市市辖区由合肥代管,庐江县划归合肥,无为县、和县的沈巷镇划归芜湖,含山县、和县(不含沈巷镇)划归马鞍山。地级市的撤除、县区的并入无疑会影响相关各市的各项经济指标。为了剔除巢湖撤市对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三市的各经济指标的影响,使得文章数据具有可对比性,本文对选取的地方财政收入指标、地方财政支出指标以及地方财政教育支出进行了调整。由于其他相关指标根据其变动趋势发现,在2011年前后并无显著变化,这里不做调整。新的行政区划,首先带来的就是人口的显著变动。根据图1,在2011年之前,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三市的劳动人口均无显著变动,但是2011年实行巢湖撤市,下辖县区并入以上三市后,三市的劳动人口有了显著上升,其后基本无太大的波动。由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10-2015年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三市的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为8.74%、8.87%和15.97%。在无其他外部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本文认为合肥、芜湖和马鞍山市的经济在2011年发生显著变化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的显著增加。因此,本文对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支出以及财政教育支出按照劳动力的平均增长率进行调整。相关数据分别见表1和表2。这里只列出了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数据调整,对地方教育支出的数据调整未列出。

图1 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三市就业人数

表1 2011-2015年合肥、芜湖和马鞍山的财政收入调整对比/万元

表2 2011-2015年合肥、芜湖和马鞍山的财政支出调整对比/万元
(二)研究方法与结果
1. 教育配置效率测算
数据包络分析[17](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一种基于被评价对象间相对比较的非参数技术效率分析方法。Fare R.等人在1992年采用DEA方法计算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并将该指数分解为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被评价DMU(决策单元)在两个时期内的技术效率的变化(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EC);二是生产技术的变化(Technological Change,TC)。本文基于产出型的距离函数来进行生产效率指数测算:

其中,D(eduout,Y|C)表示以产出为导向的距离函数,F(eduout,Y|C)为效率指数,C表示规模报酬不变。eduout表示财政教育支出,是投入项。Y是产出向量,其中,chsch是幼儿园学校数,prisch是小学学校数,midsch是中学学校数,pritsrate是小学生师比,midtsrate为中学生师比,prigra和midgra分别代表小学和初中升学率。由于时期选择导致的差异性,从时期t到t+1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两个Malmquist指数的几何平均值,即:

因此,Malmquist指数、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为M=EC*TC。当M>1,表示生产率过高;当M<1,表示生产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当M=1,表示两个时期的生产率相同。本文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产出导向模型分析,得出的结果见表3。

表3 安徽省16地市2001-2015年全要素教育配置效率指数

续表3 安徽省16地市2001-2015年全要素教育配置效率指数
Malmquist指数的计算是基于两个时期(t期与t-1期)的指数进行几何平均求得的,故本文分析的时间区间范围是2001至2015年。根据上表的结果显示,安徽省16地市的全要素教育配置效率指数在(0.803, 0.857)的区间范围内,其中最高的是宣城市,为0.857,最低的是芜湖市,为0.803。整体来看,16地市的教育配置效率均处于低效率的状态,且各效率值相差不大。
2. 财政分权指标SSM分析
组合指标的方法有很多,龚锋等(2010)认为,如果仅仅是为了基于组合指标的数值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评价,采用简单的组合指标分析即可。[18]基于此,本文以4种组合指标:加权算术平均(SAW)、加权几何平均(WP)、加权重置理想法(WDI2)和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为考察对象(具体形式见表4),基于Zhou.etal(2009)提出的信息损失最小准则(SSM)进行指标组合。[19]

表4 4种组合指标法
为了方便指标含义的解释,本文将各指标采用线性的标准化(LN)处理为0~1区间的数据,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这也符合我们对财政分权指标的理解。线性化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其中,xij表示不同指标下的个体值。由于对财政分权的各指标缺少经验信息,因此采用等权重进行处理。按照SSM信息准则,选择信息损失最小的组合指标作为财政分权指标的度量。4种组合指标的信息缺失值经计算分别为:SSM(SAW)=0.004077、SSM(WDI2)=0.005763、SSM(WP)=0.001676、SSM(TOPSIS)=0.004483。当SSM越小,表明组合指标代替原始指标所造成的信息缺失越少,替代效果也就越好。因此,比较4个SSM值,最终选定WP形式的组合指标,作为财政分权指标的有效衡量。
三、财政分权与教育配置效率实证分析
结合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对其他文献的参考,在接下来的实证模型中引入了以下变量:教育配置效率指数(edu)作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的组合指标CIw(pfd)作为解释变量。人均GDP(pgdp)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该指标越高,地区经济发展越好,对该地的教育资源的投入也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教育的配置效率。人口密度(pd)是一地区的单位面积人口数,一般认为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也越高。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显示了各地市的政府竞争情况,政府之间的竞争也会对各政府间的教育配置产生影响。以上三项指标均取对数后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
一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而本身这些序列之间并没有关联。如果直接对数据进行回归,则会造成“伪回归”,即各项指标检验均显著,结果却并无意义。为了避免“伪回归”的发生,在对面板数据建模前,有必要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LLC、ADF以及PP单位根检验,发现面板数据存在共同单位根,且是一阶单整的。
在处理面板数据时,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个体差异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表明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反之,表明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但是无论假设检验的结果如何,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是一致的。并且,相关文献的实证分析也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固定效应计量模型:


表5 安徽省教育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
表5中模型1-4均采用了模型(3)的形式。为了较全面反映各变量的影响,做了以上四个回归模型。以上4个模型中的财政分权系数均为正,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为正,在10%水平下显著。但是人口密度与人均GDP系数均未通过t检验,表明二者对教育配置效率并无显著性的影响。因此从中我们可以发现:1)安徽省各地市的财政分权明显提高了基础教育配置效率。本文得出的结论与经典结论相一致。正如前文所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分为省、地、县、乡四级政府,而县、乡级政府承担着教育投入。像教育等基础公共服务的投入,如果直接由省级政府进行控制,对于基层人民的需求缺少了解很容易导致各类服务的配置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降低公共服务的配置效率。因此,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各下级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权与事权,能更好地提高基础公共服务如教育的配置效率。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基础教育的配置效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政府间竞争的直观反映。政府官员的“标尺竞争”,使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以提高政绩,往往会将财政资金用于基础建设领域,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而势必会减少教育的财政投入。3)人口密度与人均GDP对教育配置效率无显著的影响。一般认为,人口越密集的地区、人均GDP高的地区其相应的教育投入也会提高。但是,本文这里研究的是教育配置的效率问题,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高,并不代表着教育的配置效率也高。影响教育配置效率的因素可能还有工作人员对政策的执行是否到位等。
四、结论
本文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和SSM信息损失最小准则,对2000-2015年安徽省16地市的教育配置效率指标与财政分权指标进行测算,并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发现,财政分权对安徽省16地市的教育配置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适度的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基础教育配置效率,这与经验研究的结论一致。同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教育配置效率有显著的负影响,但是作为选入的另外两个控制变量:人口密度和人均GDP,二者对基础教育配置效率并无显著影响。
本文基于安徽省16地市财政分权对教育配置效率的研究对后续相关分析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本文的研究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第一,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在用DEA-Malmquist指数的投入产出分析时,选取的投入指标太少,产出指标中未考虑受教育年限、各类学校的入学率等。在基于信息损失最小下的财政分权指标测量考虑指标太少,也没有考虑到转移支付对其的影响。第二,未考虑财政分权对教育配置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传统的面板回归模型都是基于空间观测值具有相互独立性,在这种假设的影响下,根本不能深入分析区域间的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配置效率的影响。[2]后续的研究应在这两方面有所改进。
参考文献:
[1] 龚锋, 卢洪友. 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 2013(1):42-51.
[2] 李成宇, 史桂芬, 聂丽.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教育支出——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14(3): 8-15.
[3] Tiebout C.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64): 416-424.
[4] 乔宝云, 范剑勇, 冯兴元.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6): 37-46.
[5] 刘长生, 郭小东, 简玉峰.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研究——基于中国不同省份义务教育的面板数据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8(4): 61-68.
[6] 程侃. 福建省财政分权和基础教育财政支出效率——基于DEA_Malmquist指数分析法[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86-91.
[7] 宋珏遐. 财政分权对我国公共教育供给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8] 邢祖礼, 邓朝春. 财政分权与农村义务教育研究——基于财政自给度视角[J]. 中国经济问题, 2012(4): 62-68.
[9] 周亚虹, 宗庆庆, 陈曦明.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市级政府教育支出的标尺竞争[J]. 经济研究, 2013(11): 127-139.
[10] 潘健.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物品供给[D]. 杭州:浙江大学, 2016.
[11] 杨良松.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教育供给——省内分权与财政自主性的视角[J]. 公共行政评论, 2013(2): 104-134.
[12] 李鼎, 赵文哲. 财政分权与公共教育投入的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4): 207-213.
[13] 王志平. 地区财政分权与农村义务教育配置效率: 以江西为例[J]. 教育与经济, 2016(2): 19-26.
[14] 傅勇, 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 管理世界, 2007(3): 4-12.
[15] 林江, 孙辉, 黄亮雄.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地方政府义务教育供给[J]. 财贸经济, 2011(1): 34-40.
[16] 罗伟卿. 财政分权及纵向财政不平衡对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S1): 13-20.
[17] 成刚.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与MaxDEA软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18]龚锋,雷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J]. 统计研究,2010(10): 47-55.
[19] P Zhou, B WAng. Comparing MCDA Aggregation Methods in Constructing Composite Indicators Using the Shannon-Spearman Measure[J]. Social Indictors Research, 2009(94): 8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