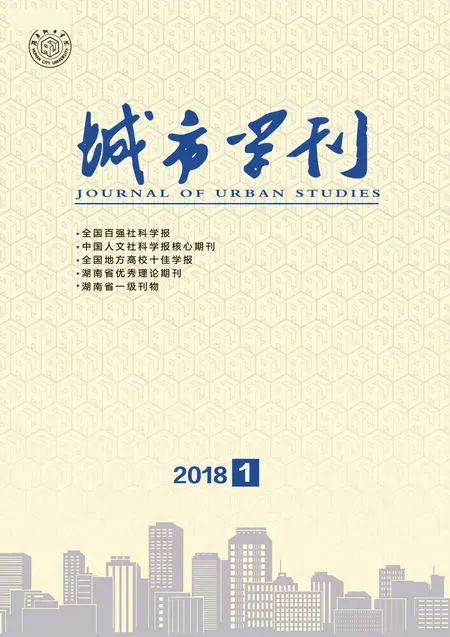遗产旅游景观建构的文化逻辑
——以四川仁寿大佛文化旅游项目为例
周延伟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一、实践中的思考
2016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公布,《纲要》第8篇名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该篇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小城镇。”为贯彻和落实《纲要》的相关要求,2016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0年,培育1 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2016年10月和2017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先后两批分别公布了127个和276个中国特色小镇的名单。从这两份名单中可以发现,大部分上榜的小镇都可以归为旅游发展型和历史文化型。也就是说,围绕遗产和历史文化建构的综合景观或将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川仁寿禅宗文化小镇的规划就是这一建设热潮中出现的典型个案。仁寿县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成为四川天府新区“两湖一山”国际旅游文化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之下,仁寿大佛文化旅游开发项目应运而生。
仁寿大佛建成于公元707年,是中国现存大佛中唯一一尊胸佛,其工程布局和人物形态与乐山大佛极为相似,加之比乐山大佛先建成6年,有文物专家认为它是乐山大佛的蓝本。同时,大佛所在地牛角寨山上分布有大量儒、道、释摩崖造像群,据统计已编号建档的有101龛。2006年5月25日,以仁寿大佛为代表的牛角寨石窟作为唐代文物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见图1)。

图1 仁寿大佛及周边场域状况(作者自绘)
令人感兴趣的是,项目虽然围绕仁寿大佛展开,但实际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大佛及其周边文化遗存的保护上,而是着力推敲附近方圆1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功能布局和设施摆位。另外,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笔者还接触了多项与文化小镇相关的规划设计项目。将其与仁寿项目比较发现,它们都或多或少涉及历史文化遗存,虽然项目位置天南地北,但似乎存在着相似的开发模式和设计流程。在项目密集和紧张的时候,设计方案的形式内容,汇报文本的图像文字等常出现相互因借的情况。
这不禁引发了笔者的些许思考:什么是我们常说的遗产或者文化遗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它在旅游规划中发挥着什么作用?如何围绕它进行景观的建构?它的背后是否蕴涵着共通的文化逻辑和运作机制?
二、遗产与发明的景观
遗产一词的原意为继承(inheritance),通常是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那些存在或可以继承的事物;二是指由前辈传给后代的环境和利益。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遗产划分标准是198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分类方法,将遗产分为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其中物质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见表1)。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基础上将遗产分类名称正式改为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但在我国出于使用上的延续和习惯,仍沿用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称谓。

表1 遗产分类
长期以来,遗产被人们等同于历史本真,但是由于特定的产生条件,其所代表的生活状态、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显然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遗产是社会通过某种价值体系筛选出来的,属于选择性的历史记忆。正如阿什沃斯(Ashworth G J)和图恩布里(Tunbridge I E)所说:“(当代社会)对历史的解释、保存至今的古建筑和文物,以及公众与个人的记忆都被用来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这其中包括个人对社会、种族和国家认同的需要,以及遗产产业商品化提供经济资源的需要。”[1]同样,休伊森(Hewison)在《遗产产业:笼罩在衰退氛围中的英国》(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1987)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真实历史与遗产绝对是两码事,……一言以蔽之,遗产可隐蔽社会不公,掩盖地方差异,把肤浅的重商主义和消费主义巧妙地遮掩起来,但有时,这反而将最应该保留下来的元素摧毁殆尽。[2]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具有资源性,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社会和群体的需要进行发掘、开发、利用和交易。如何看待围绕遗产开展的旅游开发活动呢?这里不妨引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发明的传统”这一概念。在《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1974)一书中,他写道:“‘被发明的传统’……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3]也就是说,传统是可以被人为发明和建构出来的,它的目的在于为当下的实际需要服务。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在《现代性与视觉文化中的旅游凝视》一文中基于此创造了“发明的景观”这一概念,他认为:“对当代旅游业来说,任何景观都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实在,更是一个需要不断地被‘发明’的符号,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旅游需要。”[4]因此,供人们旅游消费的遗产可以说主要是视觉美学意义上的遗产景观,这种景观是以遗产为中心建构的多种产业的复合体,是地方为了发展或者满足现代的需要所进行的对遗产本身及其周边环境的改造和再设计。
由此观之,仁寿大佛文化旅游项目实际上是人为“发明”的景观,是为了适应当下的旅游活动、文化活动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生产出的新的意义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当地以居住为主的空间模式转变为商业文化旅游空间。而仁寿大佛则脱离了原初的宗教色彩,成为了勾连时下流行的禅修养生的“由头”,这也是其得以超越周边其它遗产脱颖而出的显著原因。也就是说,供大众消费的“修禅”取代虔诚的“观佛”成为了项目的主要卖点,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其背后隐含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三、遗产旅游景观的建构
旅游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认为,旅游活动是一个“由地方生产符号、中介传播符号、游客验证符号、收集符号的符号化过程”。[5]遗产旅游景观作为一种被人为发明的景观,其建构的方式可以看作是地方生产符号的具体实践。
对本案进行SWOT分析可知,与少林寺的合作、天府新区的开发、丰富的民俗和自然资源、政府和开发商的重视是项目的优势和机遇,而相对闭塞的交通和周边开发较早的旅游区是项目的劣势和挑战。通过竞品分析发现,周边产品尤其是离此最近的三岔湖景区主要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游客,相较而言,本案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并不占明显的优势。因此,项目主打人文特色,以仁寿大佛、少林文化、民俗资源和自然资源为四个主要支柱(见图2),秉承复合型山地景区规划模式,以少林文化为核心,衍生出“禅、武、医、艺、茶”的全产业链,并且荟萃巴蜀文化,延续仁寿古城以及高家镇的各种民间文化活动,将项目定位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复合文化旅游综合体。基于此,项目的规划主题与空间结构定为“一佛一镜三世界”(见图3),“一佛”指的是仁寿大佛,“一镜”指的是佛光湖及围湖而建的僧俗交界的小镇街巷,二者组成了项目的核心区域即仁寿大佛寺景区,“三世界”分别指禅武国际传习基地、禅医养生体验区和禅修艺居体验区。

图2 项目的四大支柱(作者自绘)

图3 项目的规划主题与空间结构(作者自绘)
由此可见,经设计的禅宗文化小镇拥有双重身份,既包括国家级的文化遗产,也具有商业休闲的功能。也就是说,小镇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的体验产品,归纳起来包括实体景观、休闲活动及主题事件三类(见图4)。

图4 项目休闲体验产品构成体系
实体景观是项目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吸引游客的最基本要素。鉴于此处以大佛和摩崖等石窟类遗迹为主,辅助类建筑相对较少,因此,绝大部分实体景观需要重新建造。大佛寺力图恢复该地寺庙的历史风貌,坛神岩雕塑馆为摩崖造像提供了保护和展示的场所,禅学中心、禅武学院、禅医苑为人们提供了修禅问道、砥砺心性的空间,禅居别院营造了超凡脱俗的世外桃源。休闲活动包括餐饮、购物和相关的文化艺术活动,主要分布在佛光湖附近的佛光商业街及周边区域,这里是僧与俗、静与闹的交汇处,在这里人们既可以品尝清淡的禅斋,又可以回味地道的川蜀美食;既可以找到各种宗教法器、祈福饰品,又可以购得各种地方特产、传统手工艺品;既可以欣赏少林武僧的拳脚表演,又可以品味当地绝活的艺术魅力。主题事件指的是小镇定期开展的各种主题活动,诸如禅武节、禅音节、禅艺节、创意市集以及与传经布道、修禅养生相关的专题讲座,这些活动增加了小镇的文化气息和参与性。
法国作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在符号学的意义上得以解释。“如果把设计作品视作符号的话,设计作品的形式是一种能指,其所传递的信息和指涉的意义就成为所指”。[6]在这个意义上说,遗产旅游景观可以看作是一个由众多符号构成的综合体,这些符号是历史和文化信息的载体,人们通过其获得对场景的体验和认知。因此,禅宗文化小镇景观的建构实际上是三类符号的组织:其一是直接意旨性符号,这类符号是刻意保留的历史遗存元素,“复制了原有视觉形象全部的视觉信息”,[7]常以点缀的方式出现,体现了历史在场的证明,诸如山间小路边的茅草房、破败寺庙的老院墙、老门头、拴马石和古树等;其二是重组性符号,这类符号是对历史景观的模拟和仿真,其“运用简化和抽象变形的手法对原有信息进行提取……通过符号与原有对象间的关联性和相似性,唤起观者对于原有对象的感受和经验”,[7]51它构成了设计的主体,大佛寺依史料设计,禅学中心、禅修书院、禅文书局等也都基本按此形制,但在局部运用现代的材料和样式以增加亮点,突显新意,商业街和民俗街中设有原真生活馆,展示地方民俗,增强与游客的互动;其三是创新性符号,对这类符号的理解需要借鉴个人的文化储备,“观者依据自身的经验运用类比和联想的手段进行解读”,[7]52例如禅武表演场的设计,室外平面构图借鉴了香炉的样式,建筑造型则是取材于莲花的玻璃幕墙结构,是否具有禅意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四、遗产旅游景观的运作机制
根据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理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8]换言之,空间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环境,它还是一个社会的产物,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空间生产模式,并且生产出与之相对应的空间。基于此,遗产旅游景观也是空间生产的产物,它既包含了表面上的物质过程,也包含了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我们知道任何设计项目都不是单纯由设计者一方就可以完成的,它涉及了开发者、设计者和使用者,景观是沟通三者的媒介。开发者包括政府或开发商,他们具有景观营造的决策权。设计者指规划师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往往以“专家”的身份介入设计决策,运用自身的专业技能进行景观物质层面的营造。使用者包括游客和当地人,他们的使用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设计的优劣。
本案的投资主体是河南省万顺达集团和少林寺无形资产管理中心,政府则发挥着牵头人的作用。开发商作为主导,必然要以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少林寺的介入,一方面要借助恢复西少林继续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巨大的品牌效应也成为吸引更多潜在投资者的强有力的保证。而伴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兼具了区域经济调控主体和经济利益主体双重身份”,[1]128其在保有行政权力的同时,逐渐转型为企业型政府。政府与城市的关系也由管理阶段发展到经营阶段。至此,三者各供所长,各取所需,相互平衡,合力形成的开发团队对项目的推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接下来他们需要设计者来实现相关的建设意图,虽然设计者可以通过专业话语影响开发者的决策,但也大部分限于物质形态层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和权力相互谋和的景观生产模式。
另外,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于是城市的空间和景观呈现出品牌化的趋势,并以商品运作的方式被包装和出售,城市的形象具有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潜在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城市文化成为了突显城市之间差异的象征,因而也成为构建城市品牌和形象的关键。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任何与文化活动相关的有形或无形资产称为文化资本,当今文化与经济越来越密切的结合加速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说,文化不仅是“引诱资本之物”,更是作为一种资本具备了趋利的本能,并且为资本营利提供了掩饰。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还是“参与社会权力竞争必备的‘入场券’和‘符号’”。[1]130因此,遗产作为一种垄断性的文化资本,自然就成为社会各方利益团体和力量争相利用的对象。
由此可见,围绕仁寿大佛及其周边摩崖造像展开的景观建构是被政府及商业利润重新发现,在资本和权力的联名下,披着文化外衣进行的以利益为目的的“空间的生产”。文化从而成为了被消费的对象,将文化元素与当下的旅游休闲生活方式相融合,就生产出了以遗产景观为外显的休闲消费空间。
仁寿大佛文化旅游开发项目以展示和体验禅宗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小镇作为外在的物质呈现形式,其实质是供人们休闲娱乐的消费空间。在这里,围绕大佛所建构的物质环境“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9]这种景观是人为发明的,其所展现的图景性遮蔽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主题化是这类“发明的景观”主要的营造方式,设计方借此构建了周边景观符号与遗产的联系,游客在欣赏遗产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消费周围配套的景观。厄里认为“人们根据能表达某个特别主题的符号来划分空间——这些主题不一定与实际的历史或地理的过程有关。”[10]本案中“大佛”被“禅宗”所替换正是这一方式的显现。因此,这些人为建造的场所模糊了真实与虚拟、模拟与仿真之间的界限,它们建造的唯一目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消费欲望。推究这类景观的建构方式可以说是以历史元素为基础,利用多种符号的组合完成的。在国内,这种开发利用模式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上海新天地,此后类似的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型城市展开,并沿袭着从大型城市到中小城镇的发展路径大规模的复制,在成都就有宽窄巷子、锦里、水井坊等许多经过重构的历史街区。这些遗产旅游景观虽然外表各异,但是内核却是基本一致的。换言之,类似的开发和设计模式成为了可供模仿和复制的文本,遗产旅游景观也成为了一种“无地方性的空间”。
总而言之,在当今的消费社会,遗产和文化成为了一种符号消费的对象和社会各利益集团争夺和博弈的焦点,遗产旅游景观也变为资本和权力共谋生产出的消费空间。因此,主题化的景观营造方式日渐模糊了真实与仿真的距离,并且通过复制的手段使无地方性空间成为可能。而这似乎也构成了遗产旅游景观建构的内在文化逻辑。
参考文献:
[1] 廖卫华. 消费主义视角下城市遗产旅游景观的空间生产:成都宽窄巷子个案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25.
[2] 约翰·厄里, 乔纳斯·拉森. 游客的凝视: 第3版[M]. 黄宛瑜,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6: 161.
[3] E 霍布斯鲍姆, T 兰格. 传统的发明[M]. 顾杭, 庞冠群, 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2.
[4] 周宪. 现代性与视觉文化中的旅游凝视[J]. 天津社会科学,2008: 111-118.
[5] 胡海霞. 凝视,还是对话?——对游客凝视理论的反思[J].旅游学刊, 2010: 72-76.
[6] 胡飞. 艺术设计符号基础[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22.
[7] 周延伟. 四合院空间环境在室内设计中的符号化表达[J]. 设计艺术, 2013: 48-52.
[8]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8.
[9] 居伊·德波, 王昭风. 景观社会[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10] 约翰·尤瑞. 游客凝视[M]. 杨慧, 赵中玉, 王庆玲, 等, 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