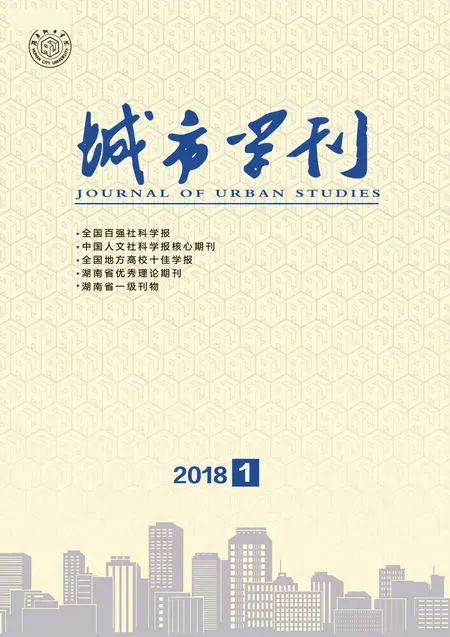基于城市韧性理论的旧城改造与更新研究
柴海龙,程 艾,余小芳
(1. 西南交通大学 建筑与设计学院,成都 611756;2. 四川农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成都 611130)
一个城市的旧城区是在岁月中经历了消亡、演变并保留下来的重要城市文化遗产,它是居民延续生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区域重要的时空特征,也是增强城市辨识度的重要名片。然而在政府现有的城市建设意识下,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1]挖掘远没有新城区建设来得立竿见影,因此,对于旧城区的改造往往浮于表面。旧城区的改造与更新,不单单是“囚笼式”的历史街区的保护,而忽略了与周边区域的互动与交流,也不是沿街风貌的重塑与业态管理,而忽略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再生;更不是粗犷式的推翻重建,而忽略了旧城区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传承,这样的旧城或者已经死亡,或者正逐渐消亡,即便改造过后也只是一具没有价值、内涵、灵魂的行尸走肉。
城市的演变是空间与时间上的动态过程,[2]其内部呈现出的是功能混合、布局混乱、管理无序、不同历史时期共存的系统特征。韧性是研究系统“扰动—恢复”的理论,作为复杂社会系统的旧城区,受到周围区域发展的扰动,人流、物流、信息流相互交织,因此,“扰动”是导致旧城区衰败消亡的重要原因,而“恢复”则是旧城改造与更新的主要目的。同时,旧城区所经历的“使用-破坏-修复-使用”的历史进程,这也与韧性“利用-保存-释放-重组”的演进过程不谋而合。结合以上论述,本文认为,旧城改造与更新的核心是在历史价值挖掘的基础上,内部空间自组织更新与外部空间功能交互的共生,从而达到旧城的复苏乃至整个城市文化灵魂的重生。
一、韧性理论基础研究
(一)韧性的起源及概念
韧性(resilience)源于语源学,词源为拉丁语中的“resilio”,意为“恢复或复原到最初状态”。19世纪,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韧性最初被西方国家运用于机械工程领域,用来描述在外力作用下金属的“变形-复原”能力,即“工程学韧性”。1973年,美国学者霍林(C. S. Holling)首次将韧性的概念引入生态学理论,总结出“生态系统韧性”,并将其定义为自然系统应对自然或人为原因引起的生态系统变化时的持久性。[3]2001年,霍林进一步将韧性概念引入人类社会系统,探索建立了用以描述“社会-生态”系统中干扰与重组相互作用及韧性变化的“适应性循环”模型,认为系统的发展包含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利用阶段(exploitation phase)、保存阶段(conservation phase)、释放阶段(release phase)以及重组阶段(reorganization phase),[4]即“演进韧性”(见图1)。
21世纪初,韧性理论开始被美国城市学者引入城市规划领域,并大量应用于研究环境适应性、自然灾害防御、城市系统等。城市韧性研究领域正在被不断拓展,城市韧性概念也在不断完善。通过总结戈德沙尔克(Godschalk)、坎帕内拉(Campanella)、杰哈(Jha)、迈纳(Miner)等学者的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城市韧性是指城市系统和组织应对内部失衡及外部扰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由基础设施韧性(infrastructural resilience)、 制度韧性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和社会韧性(social resilience)[5]四部分组成。

图1 系统适应性循环的四个阶段
(二)韧性理论与旧城区的适应性研究
1. 旧城区是特殊的社会生态系统
城市旧城区,是集商贸、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功能为一体的特殊地域空间,拥有着不平衡的人口系统、资源系统、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组成了特殊的社会生态系统。城市旧城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旧城区面对外界各种扰动冲击影响下,必须主动适应环境变化,逐渐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旧城改造与更新策略关注的重点,也是城市韧性本质的体现。
2. 旧城区面对扰动冲击的不适应现象
城市旧城区作为一个区域性围观社会生态系统,其自身内部各系统不平衡的特征使得其对外界扰动冲击具有高度敏感性,并出现一系列不适应现象。旧城区社会生态系统扰动冲击源来自于多方面,并通过其内部不同系统产生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口流动的扰动,旧城区人口的大量外迁以及外部人口的内迁,造成了管理的混乱以及社会治安的不稳定;二是城市功能整合的扰动,旧城区与其他新城区一样,都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新城区的建立,新产业的引入与新业态的整合,导致旧城区在部分城市功能上丧失;三是内外部环境的扰动,旧城区内部环境系统正逐渐被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外部交通环境对旧城区扰动也十分巨大;四是经济效益的扰动,新城区吸收了城市大量资源,造成旧城区传统业态及经济模式难以为继,经济日益萧条破败。
3. 关联性分析
1)旧城区韧性空间
旧城区韧性空间是根据旧城区所受到的外部扰动及冲击确定的。现阶段,旧城区受到扰动主要来自于城市其他区域,如城市新区、产业园区等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对旧城区各空间造成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社会资源不平等、经济效益低下、社会人口流失等。因此,旧城区韧性空间主要表现为历史文化空间、生产经营空间、生活环境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等四个韧性空间,即在面对城市其他区域扰动及冲击作用影响下,旧城区通过采取规划、管理、组织等有效策略,可以适应外界变化,在维系自身空间良好运作同时,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完善和会功能、巩固区域经济的能力。
2)旧城区空间韧性
历史文化空间主要包括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建筑、历史文化习俗传统等,在城市现代化的扰动和冲击下能够通过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保护历史文化建筑风貌,拓展历史文化街区功能和延续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来构建空间韧性。
生产经营空间主要包括生产与经营两部分,如手工作坊、工业厂房、传统市场、商业街区等,要求其在现代产业化发展背景下,主动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型产业引入、合理规划商业业态以促进市场复苏来构建空间韧性。
生活环境空间主要包括居民的居住空间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空间,如居住区、学校、医院、文化体育空间等,要求在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服务资源流失、生活环境破坏的背景下,通过合理规划、招商引资等策略,加快区域基础设施更新,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优化居住环境,营造全新的生活环境来构建空间韧性。
社会交往空间主要为城市开放空间,如公共绿地、公园广场、河流绿道、车站等,要求在有限的旧城区空间,整合各项资源,提升社会交往空间服务能力,丰富社会交往活动,从新集聚人气来构建空间韧性。
二、成都市新都区旧城改造与更新:宝光寺片区案例研究
(一)研究区概况
新都区位于成都市东北部,是“成-德-绵经济带”重要经济节点,面积497平方公里,历史悠久,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佛教禅宗寺院宝光寺和西蜀园林典范升庵桂湖两处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现以物流、制造业为主要经济产业。
宝光寺片区位于新都区中心旧城区北部,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宝光寺为核心,北至鸿运大道、南至宝光大道、西至新军路、东至规划圣谕亭北路,面积约105公顷(见图2)。

图2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二)改造与更新的历史困境
1. 城市定位与区域定位的矛盾
尽管宝光寺与桂湖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以其为核心的旅游业及相关附属产业不足以成为新都区主导经济。因此,新都区将自身定位为“城北副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新型城市,导致研究区至今无明确的功能定位,改造规划方案一再搁置。
2. 建设现状与空间整合的矛盾
研究区建设现状混乱,建筑密度高,私自搭建现象普遍,企业建房、农民自建、集体建房混搭,拆改难度大。此外,研究区用地性质多样,国有土地集体土地混杂,由商业用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文物古迹用地、医疗卫生用地、行政用地等构成,空间整合难度大。
3. 外联扰动与内联不畅的矛盾
研究区在交通区位上优势明显,但是扰动与冲击也很大。研究区北面的鸿运大道为新都区主要的过境道路,货运车辆较多,南部的宝光大道目前以货运交通为主,连接物流园区,对研究区扰动较大。研究区内联道路不畅,东部圣谕亭北路及西部的新新路均为双向两车道,是居民重要的生活性道路,静态交通设施严重缺乏;区域内部因建筑密度高,农民自建房较多,多数为机耕道及院落道路,通达度低。
4. 商业业态与历史风貌的矛盾
研究区核心宝光寺位于区域内部,辨识度不高,周边被各类商业业态环绕。宝光广场两侧是以佛教用品商店、旅游用品商店构成的商业街,周围主要有川视宾馆、川视游乐场为主的综合娱乐功能商业以及各类小型餐饮、百货、建材等业态,业态混乱且与宝光寺周边建筑风貌严重不相协调。
(三)改造与更新策略研究
1. 确定整体策略
研究区确定了以宝光寺为核心的改造策略,以禅文化内核组织区域韧性。首先明确了宝光寺的地位,即“先寺后城”营城的历史地位以及“四大佛教丛林”之一的宗教地位,其次,深入分析了区域地位与格局不相匹配的现状问题,即深藏不露、流线不畅、可达性弱的空间问题,与周边功能区干扰混乱、联系度弱的结构问题,以及自身配套不足、品质低端的业态问题。最终确定整体改造及更新策略为“扩展空间、扩展轴线、扩充业态”,对外形成地域外部扰动的壁垒,对内形成自我组织循环的能力。
2. 历史文化空间韧性的构建
历史文化空间是研究区的内核空间,其他空间均是围绕该空间进行构建与完善。该片区的历史文化空间被混乱的自建空间排挤与侵占,使得历史文化空间的弹性被挤压,因此空间韧性的构建最重要的是拓展过渡空间,把宝光寺“禅文化”进行传承、拓展与创新。
研究区在保留历史中轴线的基础上,将宝光寺北侧轴线向北延,将现状为500米的“宝光广场-宝光寺”轴线向北延伸至1.2公里,规划形成宝光寺、宝光精品馆、行禅大道、禅佛文化公园四大节点,不仅形成融合功能节点的多元禅文化轴线,同时通过开敞空间促进社会交往,将禅文化要素 “柔”性渗透至区域其他功能区(见图3)。

图3 禅文化轴线示意图
3. 生产经营空间韧性的构建
生产经营性空间应主要围绕历史文化空间进行布置,生产经营性内容主要依托历史文化要素进行整合,历史文化是生产经营的重要内涵。因此空间韧性的构建最重要的是寻求传统与新兴的生产经营内容与模式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内建筑因功能、价值、位置等要素不同进行保留、改造或拆除。
区域内保留宝光寺、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都区卫生局等大地块及功能区;改造川视宾馆、军区干休所、冯家院子等,面积约9.6万平方米;拆除质量较差、有危险隐患、严重影响节点效果的建筑,如农民自建房、私自搭建建筑、环境污染严重的小作坊等,面积约12.2万平方米。对整合用地重新进行用地布局规划,合理安排工业、商业等用地空间。合理布置商业业态,淘汰落后产业、创新业态模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区主要沿禅文化轴线布置业态,引入新兴文化产业链,如禅修讲堂与文化商业、禅修接待与展示、禅主题文化创意商业区、禅文化公园与高端居住区等,最终形成新兴禅文化产业生态圈(见图4)。

图4 禅文化轴业态布局示意图
4. 生活环境空间韧性的构建
生活环境空间是区域最重要的韧性空间,它直接关系到人口的集聚,也直接关系到生产生活空间与历史文化空间的活力。区域内环境差,生活消费水平低,导致区域低素质人口数量急增,因此空间韧性的构建以疏解区域人口为主,通过空间规划达到环境承载力与人口需求的平衡。
生活环境空间最主要的是生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生活环境空间主要规划布置在规划宝光北路西侧,对该区域进行拆迁、整合土地,疏解人口。同时,完善内部路网体系,新建南北向干道——宝光北路和东西向干道——北一街、北环路,扩宽南北向道路圣谕亭北路、东西向新光西路,新建新光西路和宝光大道下穿设计,人车分流,新增地上地下停车场各一个,供给停车位1 500个,增强交通系统韧性。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新建幼儿园、小学各一所,新建文化活动场所2处,保留区域内2处大型医院及行政办公用地。
5. 社会交往空间韧性的构建
社会交往空间是提升区域品质的重要元素,然而区域内建筑密度高、生态本底差、空间组织混乱的特征导致社会交往空间缺乏。因此韧性空间构建以整合原有“少且散”的公共开敞空间为主,通过整合、置换等手段进行空间拓展,形成新的公共开敞空间,供社会交往。
扩建宝光广场面积,向南拓展禅主题功能,打通联系古城通道;向西置换部分闲置医疗卫生用地,扩大南侧宝光广场;向东整合东部川视地块,打通开敞步行空间,将宝光广场由原有2.08公顷增加至3.4公顷。向北依托现有水系,扩展后备发展空间,规划了新型产业业态的同时,也形成了禅文化“商业区-展示区-文化创意区-主题公园”的连续性社会交往空间。
三、结论与建议
无论是建筑、街区抑或是区域,他们都同样处于“开发建设-稳态运营-破坏衰败-重组再生”的适应性循环过程中。[6]目前,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区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城市旧城区却正处在破坏衰败到重组再生的关键转折点。旧城改造与更新,既不是表面上对破旧街区的穿衣戴帽,也不是暴力地对旧城区的推倒重建,核心还是在于通过规划、调控、管理等手段,培养出旧城区空间的韧性,从根本上完善内部组织对于区域外部干扰以及自我修复的能力。
本文从城市韧性理论与城市旧城区空间适应性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成都市新都区旧城区宝光寺片区基于空间韧性培育的规划策略,提出了以优化空间组织、整合空间碎片、拓展空间弹性为原则的内外双修的旧城区韧性构建方法,建议在旧城改造中以自身文化基质为核心,由内而外地培育自身的区域韧性。
参考文献:
[1] 毕凌岚, 钟毅.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的泛社会价值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 城市规划, 2012, 36(7): 44-52.
[2] 胡晓明, 李月臣, 黄孝艳, 等. 城市空间扩展研究及进展[J].现代城市研究, 2013(6): 60-65.
[3] 李彤玥. 韧性城市研究新进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5):15-25.
[4] 邵亦文, 徐江. 城市韧性: 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J].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2): 48-54.
[5] Alexander D E. Resilience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 Etymological Journey[J]. 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2013,13(11): 2707-2716.
[6] 袁奇峰, 蔡天抒, 黄娜. 韧性视角下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以汕头小公园历史街区、佛山祖庙东华里历史街区为例[J]. 规划师, 2016, 32(10): 11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