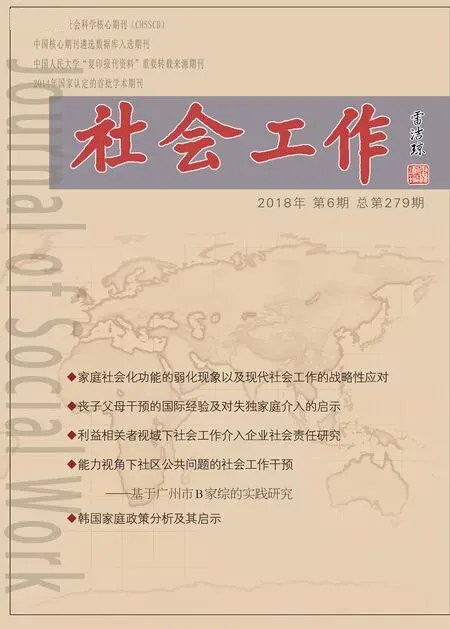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弱化现象以及现代社会工作的战略性应对
张 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通常涉及三种理解:一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形态的变迁,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三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化,即一种整体全面的结构状态变化,其中包括社会分层的变化。“社会转型”的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极端型模式(“休克疗法”或“剧烈碰撞”),例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方式;另一种是梯级性模式(“循序渐进”或“一步一步”),中国的“社会转型”属于梯级型模式。
中国的社会转型给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体带来了巨大变化。对个体和家庭而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物质资源的丰富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部分中国人已提前进入了(物质上的)小康生活状态。但是物质生活并非生活的全部,也不是决定人们幸福感的最关键因素,人们的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道德状态一样不容忽视。因此社会转型给个体和家庭带来的影响必须辩证分析。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本文所分析的“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弱化现象”是中国转型期社会变迁的一个阶段性现象,也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种体现。一方面笔者尝试分析:转型期社会变迁对中国家庭发挥其社会化功能有何影响?如何从理论层面解释这种变化和影响?另一方面,尝试分析如何改善和应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尤其体现于百姓和家庭的生活世界中,在各种应对领域中,社会工作因贴近生活世界和家庭领域,可以为应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分析背景
(一)思考的出发点:“两个结合”的“融合性观点”
社会工作既是一门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或专业,也是一种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职业。因此,无论在任何国家或地区,社会工作这一学科或职业,首先要澄清的是:社会工作需要应对的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或者说,在这个国度,最核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它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社会工作是否适合于应对它?在澄清了这些基本问题之后,下一步才是思考“社会工作如何应对它”。前者是社会工作理论的任务,即从反思层面应对社会问题;后者是社会工作实践的任务,即从行动层面应对社会问题。而培养从反思和行动层面应对社会问题的人才,是社会工作教育的任务。
中国的社会工作已走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三大领域中,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最快,社会工作实践处于摸索状态,最为薄弱的是社会工作理论。在社会工作理论中,通常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阐释社会问题形成原因和如何应对社会问题的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因其涉及上述基础性问题、是社会工作行动的基础和前提,笔者称之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张威,2012);另一种是阐述社会工作在Assessment(预估)和Intervention(介入)两个工作阶段的理论模式和理论依据,即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Engelke/Spatscheck/Borrmann,2009),因其主要涉及社会工作的行动层面(即观察—判断—行动),笔者称之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主要借用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法学和医学等,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则来自于本学科,主要形成和发展于欧洲大陆的德语国家。因中国社会工作受英美国家影响较大,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在国内并不陌生,而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在中国尚为空白。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空白的这一现状,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所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总体来说,在还没有理论澄清“社会工作所要应对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有何特征、为何形成”、“社会工作能否应对这些问题、承担什么社会功能”这些基本问题之前,过快地进入了“如何应对和操作”的这一环节。忽略方向性理论探讨、聚焦于实践过程的做法,导致中国社会工作的方法化、技术化倾向以及单一聚焦个体的做法,也因此引发了社会工作职业中的诸多乱象。
笔者提倡一种“两个结合”的“融合性观点”:一是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结合。无论是在理论层面反思社会问题,还是在行动层面应对社会问题,这两种视角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后者应对问题、解决问题;二是个体取向和结构取向的结合。个体取向是指单一面向个体工作的心理学化工作方式,即将社会问题的成因定位于个体,针对个体进行咨询性或治疗性工作(“修理个人的脑袋”);结构取向是指系统性、结构性地解释分析和应对社会问题,兼顾个体和个体以外所有层面的环境性和社会性因素,不仅面向个体提供帮助,也不忽视与个体困境相关联的宏观性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在向个体提供咨询性或治疗性工作的同时,也要改善与其困境相关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框架条件、并构建发展与其困境相关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兼顾个体与环境双重视角)。在“融合性观点”下,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是“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助人是指面向个体提供服务,协助其提高独立应对问题的能力,以确保其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监督是指社会工作机构受社会和国家的委托,监督社会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支持国家政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助人与监督”的双重功能与个体取向下单一的“助人自助”功能有着本质区别。
(二)研究对象与认识方法论
融合性观点,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与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结合、个体取向与结构取向的结合,要求中国社会工作将关注的重心转向全局,而不再只是“实践操作”和“个体治疗”。而关注全局的视角首先要求我们将思考的重点转向“社会工作所要应对的社会问题”:它们是什么、它们有何特征、如何解释它们、社会工作是否适宜于应对它们。本文的分析和阐释,便是对这一方向的一种思考,或者说,是在社会工作科学或社会工作基础理论范畴内所进行的一种尝试。
人类获得知识和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是诠释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柏林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曾用一句短语表达这两种方法:“大自然我们去解释它,精神世界我们去理解它”(Engelke&Spatscheck&Borrmann,2009:336)。按照Dilthey的观点,“解释”是一种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方法,它涉及的是一种“并非由人类自身创造的现实”。“解释”是指通过阐述某种事物比如树或火的形成、功能和使用方式,去了解该事物。而“理解”是一种人文科学的认识方法,它涉及的是一种“由人类自身创造的现实”,比如思想与感受。人们通过“熟悉某物”、设身处地的体会、感受和领会,去理解该事物。这两种途径被视为人类获得知识和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在这两种方法的两极之间,又形成很多不同的认识论与方法(同上:337)。在社会工作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诠释主义和实证主义也成为两种主要的认识途径,除此以外,现象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方法论也对社会工作科学理论的形成产生过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弱化与缺失”与“社会工作的应对功能定位”,对这一主题的思考,源于笔者与社会工作学科和职业20多年的渊源和交道,也来自2013年以来笔者在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工作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对中国式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初步尝试和思考主要基于诠释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兼顾实证主义。
(三)实践分析框架: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本文对“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弱化与缺失”与“社会工作的应对功能定位”的思考,除了基于已有的教育学和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亦基于对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华仁)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长达近6年的实践研究和分析。华仁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三类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预防性、咨询性和介入性社会工作。咨询性社会工作为重点工作,此类服务主要面向家庭和家长提供单个咨询或团体咨询。截至2018年11月华仁共为近三百个家庭提供了一对一的“家庭教育咨询”以及半开放式的“家长团体咨询”,其中“家长团体咨询”已持续了3年时间,收效巨大(因在每个星期二晚7∶00—9∶00点进行,家长们称其为“华仁星期二”)。很多家长在持续参加“家长团体咨询”一至两年后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本文的分析基于以下两类一手研究资料:一是100个一对一进行的家庭教育咨询案例(2013年1月至2015年7月)。笔者对460次咨询谈话进行了质性分析,从中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家庭关系的显著特征和家庭教育中所存在的典型问题(张威,2015a),分析了家长和咨询员在家庭教育咨询中的行为特征和互动方式以及应对策略(张威,2015b)。第二类研究资料是以团体形式进行的“家长团体咨询”(2016年3月至2018年11月)。笔者对48次“家长团体咨询”记录(每次咨询记录约3万字)进行了质性分析。此外,为了紧贴家长的日常生活、密切关注其需求和成长历程,“家长团体咨询”要求家长们每周提交总结(交作业)。笔者亦对420次“家长周总结”进行了质性分析。第一类和第二类研究资料时间维度均跨越3年,为笔者的分析和思考提供了极其详实可靠的一手资料。本文对中国家庭社会化功能现状及其成因的分析主要基于第二类研究资料。
除了对上述一手资料进行质性分析,笔者亦参与“家庭教育咨询”和“家长团体咨询”,直接面向家庭和家长提供咨询。与家庭和家长的直接接触、长期的咨询实践、持续的分析和思考,使得一个普遍存在、越来越严峻的“隐性社会问题”逐渐变得清晰化:中国当代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育严重缺失。
在分析“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与缺失”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工作的应对性战略地位”之前,本文首先从家庭研究的角度界定“家庭”、“家庭功能”、“社会化”、“家庭社会化功能”等基本概念,其次梳理、描述、分析和解释“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与缺失”这一现象所呈现的特征和现状、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这一现象所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和社会后果。目的在于,呼吁政府和社会工作领域高度重视“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与缺失”这一严峻的隐性社会问题,并将社会工作定位和提高到“应对这一社会问题、继而预防其他社会问题之职业”的战略性高度和重要地位。
二、基本概念:“家庭”、“家庭功能”、“家庭社会化功能”
(一)家庭研究中的“家庭”概念
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对“家庭”的理解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家庭概念既会受制于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或法律秩序,也会受制于基于性别之间或代际之间的社会关系秩序(Herrmann,1997)。谈到“家庭”,人们传统的理解是“一个孩子与成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地点”。但是在当今社会,“父母与孩子共同生活”的家庭早已不再是唯一的家庭模式了,“家庭”被更多地理解为“一种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派尔凑特(Petzold,1999)认为,这种“多样化生活方式”体现在四个层面:“社会框架条件”、“社会义务”、“子女”、“伴侣关系”,其中每个层面又被进一步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家庭”-“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对家庭概念的不同理解,也体现在各种不同方向的家庭研究中。家庭研究通常在教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进行,艾卡流斯(Ecarius)和科贝尔(Köbel)(2015)认为,当今对家庭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家庭之外的视角分析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家庭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二是家庭之内的视角,分析家庭内部的家庭成员行为、代际关系、教育过程等。两种研究方向互为补充。两人认为,也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对家庭研究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微观视角主要是研究家庭对家庭成员社会化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儿童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宏观视角主要是研究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及其变化)、以及家庭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微观层面“家庭对家庭成员的社会化影响”研究,主要受心理学的影响,比如精神分析(Dornes,2006)、符号互动主义①德语原文是symbolischer Interaktionalismus。和系统—生态性心理学(Schneewind,2002;Stierlin,2006)。在研究“家庭内社会化和教育”②德语原文是Sozialisation und Erziehung in der Familie。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微观层面的研究,是由鲍比(John Bowlby)进行的、由爱恩斯沃斯(Mary Ainsworth)进一步发展的纽带关系研究③德语原文是Bindungsforschung。。他们认为,一个人在童年时期与其身边最近的人④德语原文是primäre Bezugsperson。之间所获得、体验和形成的关系,对其成长和社会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研究结论显示,家庭内互动方式和关系模式体现于三种核心的纽带关系类型⑤德语原文是Bindungstypen。:安全型、不安全型、矛盾型纽带关系(Bowlby,2005;Ainsworth,1978;Hopf,2005)。此外,微观层面的社会科学性分析,也越来越受到结构理论和系统性观点的影响。此类观点所理解的家庭概念,不是绝对静态、一成不变的,它所拥有的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稳固的关系网络和沟通网络⑥德语原文是Beziehungs-und Kommunikationsnetz。,家庭被视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发展动力的系统,这一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而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的关系网络会持续不断地去尝试适应随时变化了的客观条件与现实环境(Allert,1998)。
宏观层面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以及家庭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性研究方面,即分析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之下,家庭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人们的家庭观和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哪些变化(Kaufmann,1995;Fuhs,2007)。在宏观层面观察分析家庭内互动模式时,人们所依据的理论更多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观点(Künzler&Walter,1999)。
除了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两种家庭研究,为了能从多维度观察家庭内生活方式和互动过程,融合性理论⑦德语原文是integrative Konzepte。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连接起来。例如社会生态性观点致力于分析:在家庭内互动过程中,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和集体的“自我身份认同”⑧德语原文是 personale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是如何构建起来的(Nave-Herz,2002)。又例如,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庭在社会文化结构与个人生平⑨德语原文是Biographie。之间所起到的连接性中间作用⑩德语原文是Vermittlung。,生命历程理论观点尝试,将发展心理学观点与家庭结构分析相结合(Herlth&Strohmeier,1989;Ecarius,2002)。
借助多样化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融合性理论所得出的结论认为,家庭具有以下建设性特征(Nave-Herz,2002):
家庭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因为,家庭既在生物层面承担着再生产功能,又在社会层面影响着子女成长和融入社会的决定性进程;
家庭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系统,它有着独特的合作关系、共济关系①德语原文是Kooperations-und Solidaritätsverhältnis。和角色结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样的成员称呼,只存在于这一独特的社会系统中;
家庭具有代际差异②德语原文是Generationsdifferenz。的特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差异,是界定家庭概念的决定性准则。由此,单亲家庭和育有子女的未婚夫妻也可被称为家庭。当然,代际差异既指父母-子女-单元,也包括祖父母和祖祖父母在内(同上)。
(二)“家庭功能”的变迁:当代家庭功能浓缩于“再生产和社会化”
家庭的历史变迁,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进程进行的,尤其是在“社会的(结构性)功能分化”③德语原文是strukturelle Differenzierung der Gesellschaft。背景下进行的。芬得(Fend)(2000)认为,在整个现代性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执行功能,如政治性、宗教性、经济性、家庭性功能,被越来越多地拆解和转移,它们逐渐被列为国家、社会、经济和家庭领域中独立的功能体系。也就是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逐渐出现“结构性功能分化”。不过,只要传统文化(尤其是农村地区)保持不变,这种“社会的(结构性)功能分化”所带给人们的社会性和心理性影响只是潜在和隐性④德语原文是latent。的。然而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发展为现代社会,农村地区近乎解体。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越来越明显的多样化和个体化生活进程,传统文化、安全保障、社会控制逐渐消融(Beck,1989)。“社会的(结构性)功能分化”也为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化带来了影响。
家庭结构的变迁,尤其体现在“一人独居家庭”和“未婚同居家庭”类型的增多以及离婚率的提高等方面。社会科学性研究提出以下论点,用以解释这一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迁:家庭发展成今天的现代小型家庭,是“社会分化进程”⑤德语原文是gesellschaftliche Differenzierungsprozess。所带来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原本属于家庭的一系列社会功能,转移到(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次系统中(功能外移)。由此,家庭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在亲密关系中共同生活的社会地点”(Nave-Herz,2002a)。多尔和施耐德(Doer&Schneider)这样描述家庭功能的消融和转移过程:在前工业社会中,家庭类型以大家庭为主,家庭同时承担着诸多功能:一,如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管理、宗教教育与文化教育、政治、生产、法律;在工业社会中,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为主,大多功能从家庭内部转移到家庭以外的社会次系统:二,如二级社会化功能(幼儿园、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宗教教育(教会)、文化教育(学校、协会、大众媒体)、社会保障(国家和自由机构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险和救助)、管理(官方机构)、政治(党派、利益联合会)、生产(企业)、法律(法院)(Belardi,2008)(见图1)。家庭的功能越来越浓缩或集中于“初级社会化”功能。

图1:“家庭功能”的缩减与外移
那娃-赫尔茨(Rosemarie Nave-Herz,2004)认为,当代家庭拥有五大功能:再生产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定位功能、业余生活功能、均衡矛盾和冲突的功能①德语原文分别是Reproduktionsfunktion,Sozialisationsfunktion,Soziale Platzierungsfunktion,Freizeitfunktion,Spannungsausgleichsfunktion。。其中,“再生产功能”属于生物性功能,其他四种功能均属于社会性功能。而在所有社会性功能中,社会化功能是核心。从这一角度看,当代家庭的功能主要集中于“再生产”和“社会化”两大功能。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的(结构性)功能分化”导致了家庭功能的外移和缩减(如物品生产、后代培养的功能被移至经济领域和学校),这使得当代家庭功能浓缩于“再生产和社会化”。当然“功能”一词只是针对社会,家长则将其理解为一种天然权利。
(三)社会化理论和教育学理论中的“家庭社会化功能”
人的成长与发展取决于“社会化”和“教育”,即他是否得到了成功的社会化(环境或过程)、是否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此处的教育并非单指学校教育)。因此澄清社会化和教育概念的内涵至关重要。社会化是一个立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概念,它是指:随着社会性、互动性、环境性影响,个体形成认知、语言、情感、动机的过程以及一个人的终生变化过程(Helsper,1995)。因此,社会化是一种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化过程既能推动个体的成长,亦能阻碍个体的成长。家庭社会化属于社会化的初级功能(见图2)。

图2:家庭:初级社会化机构
家庭社会化含两个层面:有意识的教育行为和无意识的教育效果。因此,与“教育”概念相比,“社会化”是一个上位概念。因此,家庭的社会化功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家长针对孩子的教育行为和教育过程”。孩子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自信的形成、能力的形成、相信自己有能力的状态,是日常沟通方式和互动过程所产出的结果。然而,日常生活无法完全理性化和目标化,因为生活的意义恰恰体现于过程之中。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既有意图性成分也有非意图性成分,其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动的非意图性成分,是其他社会化机构或场所无法替代的,学校教育也无法替代它。反过来,传递知识和培训技能,不是家庭的任务,它属于学校的职能范畴①类似于家庭和经济的关系,家庭和学校的关系几乎也是对立的。在西方国家,家庭和学校之间相互抱怨和责备。家长抱怨学校不注重孩子个性的发展,学校抱怨家长,送来的孩子不具备学校所希望的行为特征。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家长们强调孩子作为个体的发展,而学校强调集体教育、注重学习成绩。当然,两种角度对个性发展都不利。现代社会的标志是社会功能的分化,然而,这种功能分化既没有体现在家庭中也没有体现在学校中(Schütze,2007:179)。(Schütze,2007:179)。因此,第一,“家庭社会化”涵盖“家庭教育”概念,故笔者选择使用家庭社会化概念。第二,家庭社会化的核心任务在于:促进孩子个性的发展、促进孩子自信与能力的形成,而非传递知识和培训技能。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践行广义教育思想,而不是狭义教育。
(四)狭义教育与广义教育
社会化与教育概念相比是上位概念,它涵盖“教育”。但此处的教育不单单是指“传递知识、经验和价值观”的“狭义教育”。狭义教育基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在知识、经验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受教育者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因此可称为“他人教育”。与此不同的是“广义教育”概念,它不仅涵盖“传递知识、经验和价值观”的“他人教育”过程,更强调通过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和推动,使其形成一种自我教育、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因此广义教育包括“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两个层面,甚至后者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广义教育的标志是个体形成一种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反思式关系。广义教育贯穿人的一生。当广义教育发生时,个体不仅能形成自己的个性,亦能掌握生活所需的各种能力,并自主做出价值观和道德判断。本文中的教育概念更多是指广义教育。
而成功有效的“教育”的前提是,教育者必须与受教育者之间建立一种稳固的“教育关系纽带”。受教育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育者所处的客观社会文化环境是教育客体,教育者处于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的位置,他的任务是权衡以下两者:一是向受教育者传授其客观社会文化环境要求他所掌握的知识、经验、技能和价值观,二是关注受教育者的状态和需求,促进其成长和发展。若只关注前者,将摧毁个体的发展。“教育关系纽带”的建立基于两个维度:一是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权威角色的认可,二是受教育者所感受到的教育者对他的爱、温暖和尊重的态度。“教育关系纽带”存在与否,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前提(张威,2015b)。
三、理论分析:家庭社会学中的“去融合性”与“去组织性”
家庭社会化属于“家庭内部关系或内部结构状态”议题。为此,需要了解:“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家庭内部的关系是如何构建的”,为了从理论层面澄清这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引入科内希(Rene König)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两个家庭社会学基本概念:“去融合性”①德语原文是Desintegration。和“去组织性”②德语原文是Desorganisation。(König,1946;1974)。“去融合性”涉及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去组织性”涉及家庭的内部结构。König认为,家庭是一种特殊的“团体”,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上,它既是一个生育团体,也是一个亲密关系团体。
(一)家庭社会学中的“去融合性”:
“去融合性”从以下两种趋势阐释“家庭与社会的关系”:
第一种趋势对家庭造成威胁。一方面,由于以下原因,与其他社会系统相比,家庭处于“相对较弱、易受伤害”的处境,需要外部支持。首先,如上所述,社会的结构性功能分化使得家庭曾经承担的许多功能被外移出去,由其他社会次系统承担,这一过程本身便加剧了家庭对很多功能领域的不可控性。当今家庭的功能主要集中于再生产和社会化,而家庭的再生产和社会化过程,不可能像经济领域的工作过程那样,被完全地合理化、理性化和程序化,所以,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其他社会系统相比,家庭处于一种相对较弱的地位,它只能跟在其他社会系统的现代化进程之后“一瘸一拐”地蹒跚前行。家庭的这一弱点,可以从很多国家的宪法保护或基本法保护看出,正因为如此,家庭需要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其次,现代社会呈现越来越明显的个体化趋势,生活方式变得日益多样化。现代生活方式的个体化和多样化,一方面为人们构建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和自由度,但另一方面选择性和自由度的提高,也对人们“与他人构建关系的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个体化社会中,人们(与他人或环境)构建一种持续有效、相互连接的关系,成为一种自我构建、自我负责的机构化进程③德语原文是Prozess der Institutionalisierung。,家庭也因此成为一种需要自我构建和自我负责的社会系统(Tyrell,1988;Kaufmann,1995;Schneewind,2002)。再者,“体制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冲击和影响,加剧了家庭“相对较弱、易受伤害”的处境。在“体制世界”中,“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占主导,而在“生活世界”中,“价值理性”或“沟通理性”占主导,前者对后者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是控制。日益增强的经济合理化进程、交换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交换关系,迫使人们以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式、依照理性原则和效率原则思维和行动,而家庭是一个更适宜于亲密关系和情感交流的社会系统,无法按照家庭以外的原则运转,两者之间通常格格不入、无法协调一致,家庭秩序中的天然因素被体制世界视为非理性的,并受到最大程度的排挤(Theodor W.Adorno,1956),由此也加剧了家庭相对较弱的地位。
第二种趋势促进家庭的发展。另一方面,以下因素又在推动着家庭的发展,使得家庭“经久不衰”。首先,家庭的独特性,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和“自我规律”(Kaufmann,1995a:S.161)。比如,家庭会本能地抵制来自国家的任何一种干预措施,即便在专制国家,家庭也会尝试维护其独特性。因此从原则上讲,每个家庭都拥有独特的现实状况,“家庭”一词无法概括这种独特性。其次,体制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在具有巨大冲击力的体制世界与弱小的个体之间,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冲突关系或非融合关系,但这又促使个体为了保护自己缩回到家庭中。也就是说,当体制世界和生活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会选择在家庭中寻求保护。对此,König和Adorno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König和Adorno两人都没有提到:在发达工业国,一直到70年代,家庭内部所提供的这种保护,是以劳动分工的形式得以实现的。男性的任务是养家糊口,女性的任务是相夫教子、为家庭营造一种情感氛围。女性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她们必须放弃工作。不容忽视的是,男性也要付出代价:他们不允许表达情感、举手投足不能表现出女性特征,他们虽然免除了带孩子的责任,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在家庭内情感结构中起着配角作用。这一现状也清晰地体现在(西方)社会化理论中:一直到70年代,父亲在社会化理论中只起边缘作用。Bowlby(1972:13)曾这样写道:“他们(父亲们)不只是养活他们的妻子,以便妻子可以好好照顾婴儿或幼儿,他们也给与妻子爱和温暖、帮助妻子保持内心满意和安定,因为这对孩子成长很重要。我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母子关系,而关于父子关系,我们似乎无话可说。”。但是过去的40多年里,这种传统的家庭内劳动分工已发生彻底改变。女性在就业领域和公共生活中发挥着与男性一样的作用。科学研究表明,年轻女性在生育后放弃工作的趋势日益下降(Lauterbach,1992)。丈夫们总是抱怨妻子因工作原因较少时间照顾孩子(Petzold,1990)。这意味着家庭结构和家庭内劳动分工的变迁:男女双方都要养家糊口、照顾孩子。这种家庭模式与中产阶层家庭模式并不矛盾。相反,(西方)中产阶层家庭模式自形成起,就要求它不仅是一个情感港湾,而且也是一个能使每个家庭成员自由发挥能力和兴趣爱好的场所。只不过,这一家庭模式从20世纪下半叶起才变为现实。但同时,这一状况并不代表:社会与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发生改变或得以缓解①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国家、社会和家庭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也体现在出生率的下降上,孩子作为家庭的“动产抵押品”,成为家庭与社会抗衡的有利手段。。所有现代社会都如此,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②东德与西德的对比研究清晰表明这点:在东德,虽然男性和女性都拥有成家和就业的条件,但家庭在经济领域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父母和孩子能够共同度过的生活时间非常有限(Meyer&Schulze,1992)。一个东西德统一后的调查研究显示:若家庭育有3岁以下孩子,在(原)东德,32%的人希望,母亲最好不工作。54%的人希望父母中一方是非全职工作。只有9%的人希望父母双方都工作。相反,在(原)西德,63%的人认为母亲应该不工作。23%的人主张父母中一方是非全职工作。0%的人主张父母双方都工作(Dannenbeck,1992)。东西德之间相对接近的观点是∶若家庭育有幼儿,父母双方不应都去全职工作。一方面这意味着,东德已逐渐适应西德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表明,东德绝大多数父母一直以来也希望给孩子留出更多的时间。相反,在西德,母亲虽然有时间照顾孩子,但这种情况是因为缺少幼儿照管机构、缺少工作岗位不得已而导致的。而且,这种工作机会缺失的状态,当时被政府以意识形态的方式给合理化了。一直到今天,很多人在公共领域中呼吁:母亲应该放弃工作,这样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种呼吁在西德还有听众,但在东德经常被驳回。1996年,“女人应该呆在家里照顾孩子”的这种说法,西德55%的男性、47%的女性同意,相反,东德只有26%的人赞同(Schröter,1997)。。
Theodor W.Adorno(1956:117)认为,以上两种趋势,一方面对家庭造成威胁,但另一方面似乎又推动着家庭的发展。这两种发展趋势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再生产和社会化机构)变得“既易受伤害又经久不衰”(Schütze,2007:172-173)。
(二)家庭社会学中的“去组织性”
“去融合性”阐释的是“家庭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家庭内部的状况如何呢?家庭内部的关系是如何构建的?这就要谈到Rene König提出的家庭社会学的第二个基本概念:家庭的“去组织性”①德语原文是Desorganisation。,他用这一概念形容“家庭作为再生产团体和亲密关系团体的解体”。造成“去组织性”状态的原因,既可以是生理性原因如家庭成员的去世,也可以是社会性原因,如离婚和分居,或者家庭关系已经疏离(相互之间已没有情感支持)、家庭内部凝聚力(家庭内团结)②德语原文是Der innere Zusammenhalt der Familie。已经名存实亡。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家庭的“去组织性”状态通常是由家庭成员的去世导致的,当然其规模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18-19世纪的文献记载显示出:维持家庭内部凝聚力(家庭内团结)的因素大多是强制性经济原因或阶层利益,而不是情感纽带和人际互动。20世纪末,虽然造成家庭解体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死亡,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老龄阶段。在青年或中年阶段,家庭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离婚或分居(当然可以推测的是:在没有解体的家庭中,有些婚姻是勉强维持或名存实亡)。这一发展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没有了限制离婚的经济性或法律性约束,婚姻的基础即相互信任和爱慕也已消失,离婚的可能性就更大。但这并不代表:除了“爱”,就没有其他维持婚姻的原因了。比如无子女、拥有共同房产的夫妻离婚倾向较低(Wagner,1997)③比如东德自1989年的离婚率下降,一方面是因为统一后东德启用了(原西德的)新婚姻法,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变迁触及所有生活领域,间接地维持住了部分婚姻(Engstler,2001)。。
“家庭内部凝聚力”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而是一种在持续人际互动中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家庭成员之间不断地沟通交流着日常话题和其他话题,家庭内部凝聚力就是在这种沟通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生变化的。在这种沟通过程中,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能体验到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同时也能在其他家庭成员身上获得归属感(即个体能参与到家庭关系中并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和尊重)。这点尤其体现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当家庭内部凝聚力(家庭内团结)已不复存在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离婚率的高低来判断家庭凝聚力的状态。König(1974:83)这样描述“家庭凝聚力的消失”:“在家庭中,因为某些特定原因,家庭成员的自身成长和发展状态受到威胁,相互之间已没有情感支持,已经无法对亲密关系产生健康影响”④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家庭内部的沟通结构已发生改变。在发达工业国,截至60年代,家庭中是绝对家长制,孩子必须听从父母规定。实证研究表明,当今的父母-子女互动已转变为双向交流的沟通过程(Oswald/Boll,1992;Büchner/Fuhs,1996;Zinnecker/Silbereisen,1996)。1998年的《父母与子女关系法》规定,夫妻离异后孩子由父母双方共同抚养,父亲或母亲一方只能根据特殊情况提出申请单人抚养权(Schütze,2007:177)。。当然,由此引发一个问题:这些导致家庭内部凝聚力解体的“特定原因”,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有着多大程度的关联呢?
四、转型期中国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弱化现象及其解释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40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迅猛提高,但同时,人们的健康状态、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以下笔者以每个家庭最担心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为切入点、立足于人们的生活世界,尝试分析“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这一转型期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现象:转型期社会变迁对中国家庭发挥其社会化功能有何影响?如何从理论层面解释这种变化和影响?
(一)转型期中国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弱化现象及其后果
如上所述,人的成长与发展取决于:他是否得到了成功的社会化(环境和过程)以及他是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此处的教育既包括传递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狭义教育,也包括培养个体形成自我教育、自我学习能力的广义教育。社会化是个上位概念,它既包括有意识的教育行为也包括无意识的教育效果,因此本文中笔者没有使用“家庭教育”而是“家庭社会化”这一概念。换言之,家庭社会化已包含家庭教育。个体的社会化环境分微观、中观、外部、宏观等各个层面。其中对未成年人讲最直接、最重要的微观社会化环境是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如前文所述,家庭社会化的主要任务是为孩子成长提供一种环境,使其能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个性、形成自信、形成各种能力。而增加知识和掌握技能,属于学校教育的职能范畴,不是家庭社会化(包括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
那么,转型期中国家庭发挥其社会化功能的现状如何?长达六年的实践工作和实践分析表明:当代中国家庭的社会化(包括家庭教育)现状呈现出以下矛盾状态:一方面,家庭中生活“以孩子为中心”,但另一方面,家庭所应承担的社会化功能逐渐弱化甚至消失,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育严重缺失。一方面,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4∶2∶1的家庭关系结构,四个祖辈和父母双方围着一个孩子,家庭中的生活呈现出“以孩子为中心”“围着孩子转”的特点,中国父母和祖辈可以做到:为了孩子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没有自己的生活)。但另一方面,过度关注于孩子,主要体现于狭义教育方面,即最大程度地让孩子掌握知识和技能。家庭演变为学校教育的一只延长的手,家长(或家庭教育)的任务演变为:监督孩子学习、让孩子参加补习班(甚至陪同孩子补习)。而最为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和推动孩子形成自信和能力的广义教育思想严重缺失。来自体制世界的各种冲击和压力迫使家长以要求、催促、监督的方式“管理孩子学习”。从孩子开始上学起,家庭中的欢笑突然消失了,出现更多是的指责、不满、郁闷、愤怒,愉快的心情被紧张压抑的情绪和氛围所代替。这一过程中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教育关系纽带”要么完全缺失、要么被严重破坏,“教育”无从谈起,孩子形成自信和能力的空间也随之被剥夺。偏重于狭义教育、缺乏广义教育思想,使得当代中国家庭几乎丧失其应有的社会化功能,很多家庭虽然保留着家庭的外壳,但只剩下再生产的功能了,家庭的社会化功能正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笔者称这一现象为“中国当今最严峻的隐性社会问题”。“隐性社会问题”是指“尚未爆发和显现、但在特定条件下会恶化甚至影响家庭环境和家庭稳定或社会安定的各种问题”(张威,2015a)。之所以称其“严峻的隐性社会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其普遍性与严峻性双重叠加。普遍性:这一现象几乎覆盖所有阶层(高中低收入阶层)、所有家庭(高中低文化程度)、各种职业类型。严峻性:这一现象引发一系列个体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其影响辐射到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各个层面,成为各类问题的根源。
“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家庭无法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促进个性形成和发展、培养自信和能力”的社会化环境,广义教育缺失,真正意义的家庭教育缺失,由此导致个体层面的问题:一是自我价值感、自信心的缺失;二是核心能力的缺失,与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行动能力(尤其指完成生活任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负责和自我掌控生活的能力。这些能力的缺失进一步导致:个体与周围环境无法互动、无法顺利完成生活任务。这一后果体现于孩子出现的各种不同“症状问题”。比如“学习问题”:做事拖拉、丢三落四、注意力不集中、厌学甚至缀学;“人际问题”:无法与其他同学交流和玩耍、要么疏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要么抗拒、以暴力方式与人相处;“行为问题”:自卑、缺乏自信、遇事胆小、外面内向、家里外向、爱撒谎;其他问题:遇到问题承受能力差、独立能力差、无自控能力、脾气暴、易生气、冷淡冷漠、无生活兴趣等。“自信心缺失、核心能力缺失”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个体出现偏差行为(如网络/手机游戏成瘾、赌博、酗酒)或者心理问题(如自残、自杀倾向),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心理疾病(如抑郁症)甚至犯罪行为(如吸毒、诈骗)。需要强调的是,导致这一后果的因素,绝非只是“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弱化和消失”。当今,孩子的业余时间越来越多地被“做作业和参加补习班”占据和挤压,“同辈群体”这一作为个体形成自信和能力的成长空间正在被压缩和逐渐消失,同时学校教育中真正意义的广义教育思想严重缺失。也就是说,影响个体成长和发展的三大微观社会化环境(或教育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问题”,由此可以解释孩子的上述生活和学习状态。
中国家庭内关系结构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这一现象所带来的结果是辩证的: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人注重培养下一代的传统观念、将大量精力和时间倾注于子女身上;但另一方面,“夫妻关系”本应是家庭中的核心关系,但在中国家庭中,它被置于“父母与子女关系”之后,夫妻双方更多关注子女教育,而非夫妻关系的维护和经营,这为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埋下种子。当“子女教育产生偏差”,“孩子问题”又会引发“成人问题”比如夫妻之间或父辈与祖辈之间的问题。因“教育声音不一致”所引发的成人之间的冲突,反过来加剧家庭社会化环境的恶化,在这种冲突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难掌握与环境互动的能力,也很难体会到家庭和生活的乐趣,出现各种成长问题。“孩子问题”使很多父母生活在焦虑、郁闷、痛苦甚至崩溃中,这不仅严重影响着父母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夫妻之间也因“孩子问题”冲突和争执不断,家庭氛围紧张压抑。而在“孩子问题”和“成人问题”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引发各种家庭矛盾、家庭悲剧,甚至导致家庭破裂。更为严重的是,家长们并不清楚原因,针对“孩子问题”继续寻求所谓的“教育方法”,恶果越演越烈。
以上是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所导致的个体性问题和家庭性问题,而家庭稳定问题又导致社会稳定问题以及公民素质问题,因为家庭的稳定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家庭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直接决定着未来国家拥有什么样的公民。因此,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广义教育缺失这一现象,引发各种个体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这些问题产生的本质根源。那么,如何从理论层面解释“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这一现象呢?或者说,究竟是哪些因素或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
(二)转型期中国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现象的解释与分析
笔者尝试从三个层面分析和解释当代中国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的成因:一是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分析转型期社会变迁对中国家庭“去融合性”的影响;二是从“家庭内部关系状况”层面,分析转型期发展趋势对中国家庭“去组织性”的影响;三是从家长个体层面,分析个体原因对“家庭社会化”和“家庭教育”的影响。
1.转型期社会变迁加剧了中国家庭的“去融合性”
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层面看,中国转型期的以下因素或发展趋势加剧了当今中国家庭的“去融合性”。首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就业竞争与工作压力增大,父母能够与孩子共同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少。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的引入,虽然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的自由和更多机遇,但同时也将很多人置于巨大的就业、工作、晋升甚至失业的压力之下,一些中年父母甚至必须直面下岗和再就业的挑战,在陪伴子女方面常常心有余力不足。不同于西方工业国的是,中国妇女的就业率较高,“男主外、女主内”更多涉及的是子女教育,而非养家糊口的劳动分工。这种情况将女性置于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之下。与西方国家70年代前相似的是,大多男性在子女教育中承担着配角的作用。其次,社会形态的变迁: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为那些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新的生活天地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也打破了他们以往村落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家庭结构。再次,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分层的变化,使得一部分进入小康生活,但同时贫富差异和高额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开支也将一部分人置于强大的生活压力之下,他们只能疲于赚钱养家,而无力顾及生活中的其他层面。“物欲横流、物质至上”的社会氛围以及自我价值观的缺失,更加剧了人们单一追求物质表象的倾向。最后,应试制度下的学校教育:以学习成绩为中心、以考试升学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制度,对家庭和家长产生巨大影响和控制。学校教育延伸到家庭中,很多家庭甚至演变为“学校的一只伸长的手”,完全丧失了家庭应有的(社会化)功能。
因此,一方面,体制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冲击和影响体现于以上经济、社会、住房、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主导体制世界的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效率原则,也被带入家庭之中,与原本家庭中应有的沟通理性和情感理性格格不入、冲突剧烈,将家庭置于一种孤单无助、力不从心的状态。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单位体制的瓦解和改革,中国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但笔者认为,“个体人”或“家庭人”或许更适合于描述中国人目前的总体状态,因为人们在应对上述挑战和问题的过程中,基本都是以家庭为单元在“孤军奋战”的,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个体和家庭独自应对问题的压力、负担、挑战和冲击急剧增加,甚至部分家庭已出现力不从心、无力应对的状态,或者,虽然很多家庭的外壳还存在着,但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已丧失殆尽。此外,从传统角度看,在中国,长期以来,家庭被视为家事、私事,与社会和国家无关。很多家庭功能虽然从形式上被转移出去了,但从实质上并没有被国家或社会真正承担起来(比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三岁以下幼儿的机构照管、养老和护理),在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依然是家庭在独当一面。因此很多家庭更处于一种单打独斗、自生自灭的状态,应对以上挑战的压力倍增。
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传统的成家立业、传宗接代思想牢不可破,“成家生子”的观念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同时,体制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剧烈冲突,也促使人们愿意在家庭中寻求保护。这又使得家庭这种社会系统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牢不可破”“经久不衰”。
2.转型期社会变迁加剧了中国家庭的“去组织性”
从“家庭内部关系状况”层面看,以下因素或发展趋势加剧了当今中国家庭的“去组织性”。第一,城市化进程。城乡之间生活地点的转换,引发了一个转型期中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父母进城工作,年幼的孩子留在农村家中由祖辈(或亲戚)带大,上幼儿园或上小学时才被接到城里与父母一起生活①在华仁所服务的300多个家庭中,这类家庭的比例约为35%。。这一现象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纽带关系缺失或断裂,当孩子回到父母身边生活时,矛盾和冲突重重。而每当冲突发生时,父母非常无助,自责和愤怒又将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推向恶性循环。中国转型期的这一特殊现象,加剧了家庭的“去组织性”。很多家庭中,尤其是育儿初期,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处于四散分离的状态。这不仅影响着家庭内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亦引发夫妻关系和其他家庭关系问题。第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或独生子女现象:独生子女结婚成家后的特殊现象体现于,因没有经历多子女家庭的社会化过程,夫妻之间在遇到问题时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第三,隔代教育:中国人退休年龄较低、3岁以下幼儿机构照管体制缺失、年轻父母就业压力增大,几个因素共
3.家长自身能力的缺失加剧了“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
除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与“家庭内关系状态”层面的因素,家长个体性能力的缺失也是导致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的直接原因。如上所述,社会转型中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打破了人们以往村落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家庭结构。在进入城市、扎根立足的转折过程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和应对问题的能力受到极大冲击和挑战。个体化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也同样触及中国当代社会、对个体和家庭自我负责和自我构建的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而曾经的村落式社会关系网络和家庭结构,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学习和掌握这种新型能力的场所和经验,很多人被置于一种孤军作战、茫然无助的状态。更确切地说,当代的父母们生活在一个不同于其父辈的生活环境中,个体化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要求他们掌握一种全新的自我负责和自我构建的能力,这些核心能力比如是与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行动能力(尤其指完成生活任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负责和自我掌控生活的能力,然而很多家长在原生家庭中并没有掌握和获取这种能力。因自身不具备这些核心能力,当他们养儿育女时,便无法将这种能力传递给下一代,加之社会转型和时代背景带给他们的各种压力和冲击,使得他们只能茫然从众或力不从心、没有能力在家庭内为孩子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化和教育环境。同促成了中国特殊的隔代教育现象。为了相互照顾,很多年轻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与自己父母同住,三代同堂,直到孩子上幼儿园或上小学。“老人带孩子”这一现象不仅隐含和伴随着两代成人之间的教育冲突,也引发家庭关系问题以及孩子问题,很多孩子的童年(0-3岁或0-6岁)是在父母与祖辈的持续性冲突关系中度过的,其成长和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第四,应试制度下的学校教育:一方面,来自学校本身的要求和压力,被传递给家庭,家长成为教师的一只延长的手(只关注孩子的学习);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带给家长的压力以及家长自身没有实现的愿望,被传递到下一代(给孩子造成更大的压力)。而在“孩子问题”与“家庭问题”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第五,广义教育思想的缺失:中国式家庭教育或父母—子女关系的典型问题是:很多家长对“教育”的理解非常狭隘,就是“监督和确保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在放学后与同龄群体玩耍、在这一过程中获取能力的时间和空间被严重挤压,大多孩子不是被关在家里做作业就是在补习班里补习。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教育体制中,广义教育思想严重缺失,人们对教育的理解只停留在“传递知识、培训技能”的狭义教育层面。这一现象直接导致:孩子形成自信和能力的空间被压缩,由此导致各种成长问题。第六,现代生活方式的个体化和多样化:生活方式选择性和自由度的增加,也增加了家庭中成员之间建立连接和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家庭成员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将家庭“再机构化”。而这种能力,在转型期受到极大冲击。其原因与上述的家庭“去融合性”状态密切相关。
以上发展趋势,加剧了当今中国家庭的“去组织性”状态,即“家庭作为亲密关系团体的淡化或解体”。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离婚分居的增加,离婚率在不断升高,同时很多家庭迫于工作原因长期两地分居,尤其是年轻的父母,在育儿的最初阶段,父亲或母亲必须在另一个城市中工作、在两地间奔波。很多家庭处于四散分离的状态。第二是家庭关系的疏离、家庭内部凝聚力的弱化或消失,也就是说,家庭成员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相互之间的情感支持较为缺乏,家庭内的人际互动方式更多是抱怨、指责、不满、否定,较难对个体成长(孩子和成人)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明显,很多夫妻虽然没有离异,但家庭只剩下外壳,他们只是为了孩子或为了面子勉强维持婚姻。分析表明:中国家庭“去组织性”状态的增强,直接导致“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同时,家庭的“去组织性”以及“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又与其“去融合性”状态密切相关。
五、现代社会工作应对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的战略定位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文分析的“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现象”显然是中国转型期社会变迁的一个阶段性现象,也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一种体现。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尤其体现于百姓和家庭的生活世界,在各种应对领域中,社会工作因贴近生活世界和家庭领域,应该为应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现代社会工作的战略性应对功能:环境支持与能力建设
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德语国家因在一战后遭遇家庭功能弱化和缺失的社会问题,许多家庭已无力承担教育子女的社会化任务,社会教育学领域应运而生(不同于社会教育)。简而言之,社会教育学被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当家庭教育出现问题时,社会教育学作为独立的教育领域,对其进行补充和辅助,但它与家庭教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过去的100年里,通过国家的立法和官方社会教育学专业机构的设立(如青少年事务局),社会教育学已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教育领域和服务领域,今天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概念已被人们并列使用,“社会教育学/社会工作”既成为大学的一门学科,也成为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专业帮助的服务领域。中国没有“社会教育学”概念,因此笔者选择使用“社会工作”。但社会教育学作为应对“家庭社会化功能和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的专业领域,其理论思想和职业经验,对中国是极有价值的。
笔者认为,应对当今中国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或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的战略性定位在于两方面:一是结构层面,二是个体层面。现代社会工作的战略性功能定位体现于:它界于(个体的)生活世界和(结构的)体制世界两者之间。在生活世界中,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占主导。在体制世界中,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占主导。社会工作的任务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均衡,由此,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具有双重特征:社会工作具有“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以及“个体与环境”的双重视角。助人是指面向个体和家庭为其提供专业服务,使其具备独立应对问题的能力、较为顺利地完成生活任务;监督是指接受国家和社会的委托,监督和控制社会风险因素,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功能或目标,在应对问题时,社会工作的切入点必须是个体和结构两个层面。一方面,结构是指,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结构层面的应对措施是指,改善或构建影响个体和家庭生活状态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社会政策,尤其是家庭政策。家庭政策是社会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出台和制定家庭政策的目的在于:缓解或减少家庭在工作和育儿之间的冲突和压力,从物质层面给与家庭在养儿育女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个体是指个人与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应对措施是指,第一,为家长和家庭提供环境支持,为其提供和构建人为营造的专业性、支持性环境或公共空间,比如华仁为家长们提供的定期接受咨询的专业空间和环境。第二,能力建设:通过持续性工作、引入广义教育思想,教育家长,使他们逐步掌握轻松生活和教育子女所需的各种核心能力,从能力建设方面给与家长在养儿育女方面的支持。
(二)“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成功经验与工作难点
在近六年的时间里,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环境支持和能力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华仁长期持续的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过程,验证了“环境支持和能力建设”的巨大成效。很多家长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家长能力的提高,家长自身在逐渐改变,家长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改变,带来了家庭氛围和家庭环境的改变,良性健康的家庭环境又带来了孩子行为方式的改变,在“家长成长”和“孩子成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同时,推动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加入到华仁的团体咨询中,作为教师她们担负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作为母亲她们一样面临“孩子问题”带来的困扰和痛苦。很多教师在华仁第一次听到“社会教育学”,广义教育思想为她们打开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视野,她们在华仁飞速成长,并将这种改变带入学校、影响更多的孩子和家长。
华仁之所以能达到“环境支持和能力建设”的成效,关键在于以下三点成功经验:一是社会工作者具备“反思性专业性”;二是长期陪伴和持续支撑;三是在“认知学习”和“日常践行”的反复循环过程中,推动家长的能力建设。首先,现代社会工作对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专业性”提出很高的要求。社会工作者如果单单拥有知识、掌握方法,是无法胜任这一工作的。因为,“环境支持和能力建设”的工作过程是一种面向家长的“广义教育”过程,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一种能够对家长产生影响力的素质和能力,能够推动家长自身形成一种自我学习和自我成长的能力。为此,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反思性专业性”。“反思性专业性”界于专业知识和行动能力两者之间,它体现于多个层面,比如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以下能力:理性分析能力:分析和解释社会问题的能力、在社会环境框架下观察和分析具体案例的能力;“创立第三逻辑”的能力:即在学术逻辑和实践逻辑之间,在科学知识和日常经验之间创立一种适宜于具体情景的第三逻辑;与案主平等合作和对话的能力,即自己“从上面下来”并推动案主“从下面上来”的能力。
第二个成功要素在于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咨询能力,需要长期陪伴和支撑案主。首先,华仁的咨询(如家长团体咨询)是指社会工作咨询,有别于临床咨询(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其核心目的是能力建设而非家庭治疗。其次,华仁之所以能达到“促使家长改变进而改变家庭环境和孩子”的巨大效果,与其咨询工作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是分不开的。华仁的家长团体咨询目前已持续三年时间,每周星期二晚进行,很多家长风雨无阻、不间断地参加。华仁的经验表明:这种长期持续的咨询工作非常必要和重要,因为,家长们在咨询中所获的,只是一种“认知式学习”,即他们“学习”到新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而当他们回到现实环境和日常生活中,他们所获得的这种新的认知能否付诸于行动,受到太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长期的咨询工作中,家长们经常带着挫败和气馁回到咨询中,他们得到社会工作者温暖的鼓励、心理的支撑、方向的引导,获得希望和勇气后,他们返回日常生活、再次尝试。这一成功要素与第三个要素相连。
第三个成功要素在于:在“认知学习”和“日常践行”的反复循环过程中,推动家长的能力建设。实践证明:假如家长们在咨询中只是获得了“知识和信息”,这种认识式学习通常会在日常生活中“夭折”,因为他们不具备将知识与现实相连接的能力、不具备生活所需的核心能力。因此单靠“家长讲座”式的工作方式,对家长帮助不大。相反,改变家长和家庭现状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家长必须掌握完成生活任务所需的核心能力,比如与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其中包括洞察力、体会他人内心的能力)、允许差异存在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行动能力、自我掌控生活的能力。而“能力的形成”取决于现实生活中“正面经验的积累”。也就是说,家长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不断地尝试、不断地积累正面和积极的体验,慢慢地形成一种全新的能力,这是一个较为艰难和漫长的过程。发生巨大改变的家长反馈: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的,改变是从生活中的小事、“尝到甜头”开始的。很多家长表示:他们大约是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发生变化的。华仁的经验表明:家长能力建设和培养,不仅需要持续一定的时间,在“认知学习”和“日常践行”之间也需要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其中“日常践行”是最关键环节,也是社会工作者推动家长能力建设的助人艺术所在(见图3)。

图3:能力建设:“认知学习”和“日常践行”的循环过程
除了上述成功经验,华仁在工作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难点。最大的难点来自于“体制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巨大控制”,家长们在能力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反复与挫败,很大程度上源于体制世界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法抵御工具理性目的理性、效率原则、功利观念对家庭和生活世界的控制,在强大的体制世界框架下,他们的努力显得极其微弱和不堪一击。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华仁的支撑和支持变得极为重要,华仁的任务重心甚至逐渐转向:引导人们掌握一种能够在体制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均衡、重新回归生活世界、驾驭和掌控自我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显然这种工作需要很多前提条件和整体框架的改善,尤其是宏观机制方面的改革。
(三)期望与建议
本文目的在于,呼吁政府和社会工作领域高度重视“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与缺失”这一严峻的隐性社会问题,并将社会工作定位和提高到“应对这一社会问题、继而预防其他社会问题之职业”的战略性高度和重要地位。本文对“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现象”的成因分析以及华仁的实践经验表明,要应对这一现象,需要构建系统性和结构性整体机制。社会工作若要充分发挥“环境支持和能力建设”的作用,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和机制改革。从教育体制来看,政府首先需要建立全新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国教育体制急需突破狭义教育思想、消除应试制度弊端、践行广义教育思想。这不仅关系到学校教育的质量,亦直接决定着中国公民素质的培养。在学校教育中,教育思想的践行主要体现于教师,需要以广义教育思想重塑教师队伍。在家庭教育中,需要重新定义家庭教育功能、家庭社会化的任务。在同辈群体层面,需要制定政策和创造公共空间、确保孩子成长所需的同辈群体环境。此外,从社会政策角度看,政府需要制定或出台能够缓解家长工作与育儿之间压力的家庭政策,为此需要走出“家庭和育儿是家事私事”的误区,重新分配家庭、社会和国家三方在支持家庭、保护家庭方面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