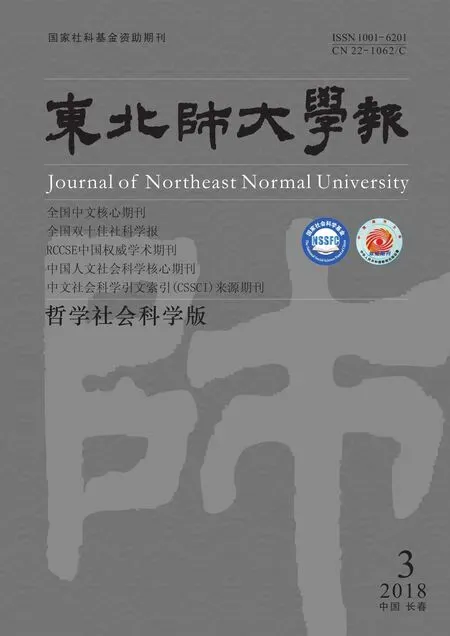默认意义及其翻译策略探究
——默认语义学视角
李家春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黑龙江大学 应用外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一、引 言
经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对一般会话含义的解释存在理论缺陷,因而导致了后格赖斯语用学者对语用学和语义学分界的争论。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般会话含义是语义的还是语用的,一般会话含义是否是默认意义,一般会话含义与推论是否有关系,一般会话含义与规约是否有关系。”[1]22对于这些理论问题,默认语义学试图提供最简解决方案。2005年,剑桥大学语言学教授K.M.Jaszczolt出版了专著《默认语义学:交际行为合成性理论的基础》,提出了默认语义学,将语用学和语义学合并到一个意义层面,认为真值条件内容包含语用因素,话语理解是一种合成性合并表征。“合成性合并表征由词语意义和句子结构、有意识的语用推理、认知默认、社会文化默认共同组成。”[2]8-9该表征是语义和语用因素等各种意义来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默认语义学仍在发展之中,尚有分析层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对于翻译过程中的意义理解和传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以该理论为基本框架,进一步探讨默认意义的界定、分类及翻译策略。
二、默认意义的界定和分类
默认语义学认为,默认意义是“无需说出话语时的特殊情景语境参与的一种突显性解释”[3]5。默认意义的产生无须有意识的语用推理,它是一种由语言使用的规约性所触发的非真值条件意义[3]5。Jaszczolt将默认分为认知默认和社会文化默认,该分类忽略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表述方式和修辞手法差异。本研究将默认分为认知默认、社会文化默认和修辞默认,目的在于通过对默认意义进行进一步划分,同时收集例证来深入探讨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处理不同类型默认意义的策略*笔者在访问剑桥大学期间,针对默认分类问题与Jaszczolt教授进行探讨,她赞同笔者的划分,即将默认分为认知默认、社会文化默认和修辞默认。同时,她对三个类别的进一步细分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一)认知默认
认知默认产生于语言交际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的意向性。认知默认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心理状态意向性的默认”[3]47-49。这种默认是最强意义上的默认,因为和人类的思维方式相关。Husserl认为,“每个行为都有合适的、意向性的客体指代。不论一个行为的构成如何,只要是行为,一定会指向某个客体对应物。”[4]114意向性也有强弱之分。最强的意向性是规约,即默认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不会受到主体知识缺乏、指称错误和其他干扰因素的阻碍。例如,The author ofOscarandLucindais a very good one.这句中the author of Oscar and Lucinda一般指Peter Carey,即该书作者,也可以指Roddy Doyle,即说话人误以为的该书作者,还可以指任何一个可能写这本书的人。其中第一种意向性最强,可以称为默认意向性。第二种和第三种意向性则逐步减弱。Jaszczolt认为,意向的工作机制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是程度原则,即意向允许有程度差别。第二个原则是首要意向原则,即交际中意向的首要作用是获取说话人话语中的所指[3]51-52。这两个原则总结了意向的工作机制和意向如何产生默认和非默认性理解。默认理解是瞬间、自动完成的,而非默认理解则是依赖于语境进行的推论。
认知默认涉及人的心智,因此错综复杂,不易识别。Jaszczolt未对认知默认深入讨论,也未将其详细分类。而进一步的划分对于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准确识别认知默认,以及正确的理解和翻译都有重要意义。认知默认可以进一步分为指称默认和级差默认。
1.指称默认
默认语义学认为,交际中有三种意向,即交际意向、嵌于交际意向的信息意向和指称意向。说话人交流某种内容,告知受话人某种内容,并且指称某个事物和事件。这种交际中的意向,与心理状态中的意向性的心理对应物一样,可以强也可以弱。因此默认理解可以用交际中的意向性的强弱来解释,理解指称意向时也是如此。
Bach区分了说话人指称和语义指称,他强调“说话人指称是一个四维的关系,关乎说话人、表达式、受众和指称对象。指称意图本质上是语用的,并不决定语义指称,但是说话人确有具体的语义意图。”[5]45我们分析交际过程中的指称时,不仅要分析其一般情况下的语义指称,还要分析特定情况下带有不同意图的说话人指称。Lyons针对指称的本质提出,“是说话人通过使用某种合适的表达式进行指称,他通过指代行为将表达式赋予指称。”[6]177这种指称的语用观与Strawson一脉相承。Strawson认为,指称不是表达式做出的,而是某人使用一个表达式做出的[7]。指称的理解方面,Brown & Yule认为,“成功的指称依赖于听话人基于使用的指称语以理解当前语言信息,进而识别说话人意欲表达的所指”[8]205。一般情况下,说话人和听话人同处于一种文化中,双方的互动通常会较为顺畅,因为听话人比较容易识别交际内容中的指称对象以及相应的交际意图。但如果二者属于不同的文化,则需要靠语境识别指称对象。例如,汉语文本中经常出现“我们”“我方”“我国”等表达,中国受众无须推理,可以直接在语境中得出所指对象,但是国外受众则容易产生误解。因此,翻译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2.级差默认
Levinson将格赖斯提出的一般会话含义解释为默认推论,“这种推论是基于话语的优先或正常解读的直觉把握”[9]11,一般遵循三个原则,即“QMI原则”。Q原则即量的原则(没说的就不是要说的),I原则即信息充量原则(所表达的仅仅是常规化的典型内容),M原则即方式原则(非正常方式说的即不是正常的)。级差含义是由Q原则引发产生的一类含义,一般是“从具有层级性的一系列词汇(量词或形容词)中得出”[9]176。例如,构成霍恩级差(Horn Scale)中的系列词项存在语义信息的强弱
(二)社会文化默认
社会文化默认是指“由文化原型和社会原型引起的默认理解”,二者的生成机制是一致的[3]55。社会文化默认一般在原语文化中能够得到迅速、自动地识别,例如,英语文化人群能够迅速将“Pablo’s painting”理解为“the painting by Pablo Picasso”,将We advised for a new nanny.中的“nanny”理解为“a female nanny”,前者属于文化默认,后者属于社会默认。这种默认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原文中的默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译文脱离了这种背景相当于植物脱离了赖以生存的沃土。如前面的“Pablo”,我们不能只音译为“巴勃罗”,而要代之以中国受众更为熟知的姓氏“毕加索”或将全名译出。因此,译者常常需要多角度思考,将默认在译语中重新进行构建。社会文化默认可以进一步分为原型默认和文化习俗默认。
1.原型默认
Lakoff曾在文章中回顾了经典范畴理论,即不同范畴之间有清晰的分界,不存在边缘和模糊地带,某一个类别共有一些特征,可以通过列清单法来确定类别从属[10]20。Wittgenstein早前则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论[11]36,论证了范畴边界的模糊性和隶属度的差异。Rosch通过实验证据提出了自然分类理论,认为范畴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原型,即人类以原型形式对世界进行划分[12]328-350。Rosch的理论催生了“原型语义学”,对生成学派理论进行了挑战。Fillmore认为,某个类别中的词汇项不能只依赖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要依靠社会文化因素充实的原型。他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范畴的塑造和充实作用[13]34。因此,本文对原型默认界定如下:原型默认是特定文化框架中对于某个范畴的原型和边界达成的一定程度的集体性默认。翻译过程中,原语文化中的某个范畴在该文化中有默认的固定原型,而在译语文化中这种原型可能会有差异甚至完全不同,翻译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解释说明。
2.文化习俗默认
文化习俗默认是某个文化群体对于所在文化中长期积淀下来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交往规范的集体性默认。文化习俗默认一般是对于规约的默认与遵守。Davis认为规约是“一种任意的社会风俗或习惯,是一个群体的自愿活动中的规则。它具有社交有用性、自我持久性和任意性的特征。”[14]133同一文化群体对社会交往和风俗习惯等规约一般具有相似的心理预期,而翻译过程中原来共享的规约系统和知识系统的默认经常有所缺失,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
中国文化中,长辈询问晚辈婚姻、家庭、收入等问题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询问对象一般不会觉得受到冒犯。而西方文化中这些话题一般是隐私和禁忌,如果询问会违反社交礼仪。因此,译者翻译时需要进行适当的处理,回避文化习俗上的冲突,以实现文本信息的有效传递。
(三)修辞默认
修辞是“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的一门实践”[15]2。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修辞系统和语言特点,这些特点一般对于本族语群体来说是习以为常或是默认的,但对于另一文化群体可能是完全陌生化的。修辞默认指的是某个文化群体在语篇架构、修辞手段和行文风格等方面达成一种基本性共识。译者在对原语文本进行跨文化阐释的过程中不仅要把握其语义结构,还要理解其修辞结构,力求在保持原文风格特色和获得译语读者接受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事实上,多种修辞手段在原文化中是默认的,本文限于篇幅,仅以隐喻和转喻这两种修辞为例进行论证说明。
1.隐喻默认
Lakoff & Johnson在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还存在于行动和思维之中。”他们通过大量的语言事实表明,“我们日常大多数的概念系统本质上具有隐喻性”。“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一种事物”[16]3-5。隐喻默认是指某一文化群体对于使用和理解一些隐喻表达式达成的基本共识。隐喻是人脑中概念系统、经验系统、语言形象系统等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同的设喻目的会使同一喻体具有不同的语用价值。隐喻可以分为常规性隐喻和创新性隐喻。常规性隐喻通常是已经石化定型的表达法,交际双方一般共享相关知识即可实现交际目标,而创新性隐喻则是说话人使用的个人化或场景化的隐喻表达法,受话人一般可以通过具体语言背景甚至宏观文化背景得出说话人意义。隐喻的跨文化理解过程中,有些隐喻具有普遍性,不同文化可以共享;而另一些隐喻则仅为某一文化群体所使用,在翻译时需要进行特殊处理。
2.转喻默认
Lakoff & Johnson认为,“转喻是用一个实体指代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实体”[16]36。转喻具有指称功能,能够让我们用一个事物代替另一个事物。Croft认为,“转喻是对认知域矩阵中某个认知域的突显”[17]335-370。“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即用某个概念实体(喻体)为处于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内的另一个概念实体(喻标)创建心理通道的过程。”[18]21转喻可分成三种类型,即符号转喻、指称转喻和概念转喻[18]22-28。我们认为,转喻默认是指某一文化群体对于使用和理解一些转喻表达式达成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可能会有所失落,因此译者需要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进行处理。
三、翻译策略
认知默认、社会文化默认和修辞默认在跨文化阐释的过程中都需要译者准确理解、合理传译。我们在收集语料和翻译实践过程中总结出四种策略,即默认保留策略、默认转化策略、默认增减策略和默认置换策略。
(一)默认保留策略
三种类型的默认都既有普遍性,又具有文化特殊性。默认保留策略主要针对具有普遍性的默认,指的是不同文化群体共享一定的“共有知识”,认知共性和语言的相通性使得译者可以保留原有的语言形式和内容直接进行传达。
例如,在王毅部长演讲中曾有“中华儿女……勒紧裤带帮助了一大批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表达。“勒紧裤带”是一种修辞默认,外交部的译文中采用了tighten our own belt的译法。为了验证这种用法在英语国家的使用情况,我们在BNC和COCA两个语料库中各找到一个类似用法,分别是“tighten the government’s belt and loosen the belt on the people”和“Feds must tighten belt”。因此,这种情况下默认可以保留,对于跨文化理解是有效而快捷的。
不管身处何种文化,我们自身和日常生活的经验知识,很多时候是有相似之处的。无论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对社会生活的体验,还是对生活经历的描述,都会有一些文化共通性,这使得我们拥有很多具有普遍性的默认,这些默认在翻译过程中无需解释,也能得到较快的识解。
(二)默认转化策略
由于历史背景、社会习俗等原因,一些默认带有明显的社会文化标记。如果采用字面译法,不能激活译语读者头脑中相似的意象图式,还有可能引发与本意相反的假设。这时我们可以采用转化的方法。默认转化策略是指,翻译具有明显社会文化标记的内容时进行语言形式或内容的转化,例如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转化,或语言形式与副语言形式的转化,还可以是不同模态之间的转化。黄友义先生曾经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则”[19]27-28。外宣翻译的译者,除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外,还要深刻了解中外风俗文化的差异,以便将中国优秀的典籍和传统文化翻译成外语[20]52。
(三)默认增减策略
“隔着文化和语言的两大鸿沟,所有经过翻译的传递不可能百分百精确,译者就像献花的使者,要把异域的花朵献给本土的读者,这是千里迢迢的艰难旅程,他必须要保证花朵的完好,而途中掉落一两片叶子,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什么样的损伤是对花朵的损伤,什么样的损伤是对枝叶的损伤,这要根据文本仔细甄别。”[21]46这是作家苏童从中国文学外译角度提出的观点,但对汉英双向翻译均有意义。作者主要意欲传递的信息即是花朵,而所用的修辞是枝叶,在无法保留的情况下损伤一些枝叶是可以接受的。默认增减策略指的是翻译过程中针对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行适当的增补和删减,在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的同时关注译文的读者接受程度。
以指称默认为例,中国领导人或发言人在国际场合的发言应通过语境来确定所指。例如,“我们”可能指中国,或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也可能指中国和受众所属国家。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7月9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讲话稿中提到“我们双方更应该审时度势,转变思路、创新思维,不断开创两国合作新局面”。其中的“我们”意指“中美双方领导人”。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原文化中的指称默认,重新赋予其真正的所指。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第一次参展方会议的会议日程上有这样的文字:“汉民副局长主持会议”“杨副市长致开幕辞”等。其中的所指对于会议参与者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无需全称,但是在对外传播中则需要称呼明确,完整译出。
再举一例。英国民众会对红色的邮筒这种原型有集体的默认,因而原文作者如果使用此类文化意象能够获得理解和共鸣。但中国文化中邮筒的原型却是绿色邮筒。因此,如果该译文的目标读者是非英语专业或无英国生活经历的中国读者,这种原型默认就会失察,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对这种失察进行适当的补充说明,以利于读者理解。
另外,汉语文本中经常有四字格形式的隐喻表达,以及各类借诗咏志的表达,既具有韵律上的美感,又能增强文字的表现力,是中国文化中默认的修辞手法,但如果直译到英语中,很难引起英语读者的共鸣,甚至会导致误解,因此应该适当删减,以传递基本语义为要义。
(四)默认置换策略
“文化障碍大于语言障碍,翻译需要进行文化置换。”[22]28文化置换是“译者在把源文本内容转移到目标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可能会采用的对字面翻译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偏离。”[22]28文化置换是一个连续体,朝向目标语语言和文化特征的选择,而非源语语言和文化特征。结果是异国特征在目标语文本中减少了,甚至是中性化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默认置换策略,该策略指的是翻译过程中采用目标语中功能或语用上对等的表达法代替原文中可能会引起歧义或误解的表达法,以适应行文和表意的需要。置换策略的前提是译者对原文语义的准确而透彻的理解,在翻译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是层级置换和意象置换。
1.层级置换
层级置换包括翻译过程中语义强弱层级的置换和上下义词之间的置换。例如,翻译级差默认时,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确定词语意义。有些情况下,如果生硬进行直译会导致译文在语境中表意不准确。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生产安全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新华网英语频道的参考译文为Serious and major industrial accidents occur frequently,该译法有待商榷。我们通过对爱词霸和海词在线词典的句库检索,发现与“时有”对应的英文19个。其中副词结构有“often,sometimes,occasionally,from time to time,now and then,still,frequently”,形容词结构有“sporadic,intermittent,common,unavoidable”,此外还有省略的情况。其中,often使用频率最高为36.8%,而frequently仅为5.3%。由于词语本身具有模糊性,人们实际使用带有语义强弱的词汇时有可能出现分歧。但上述统计表明,人们对“时有”的频率有一定程度的默认。显然,“frequently”在语义的强度上要大于“often”和“sometimes”,因此笔者建议采用后两种译法。
礼仪致辞中曾出现“欧洲陷入群雄征战”这样的隐喻默认表达,属于汉语常见的隐喻形式,说话人使用这种形式来代替“世界大战”,显然目的在于弱化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分歧,而且“群雄”也带有褒义。这种主观因素导致形、义选择组合在特殊语境中具有特殊的修辞效果。翻译时如果译为“world war”,就不能完全译出原文中默认的修辞效果。而采取修辞上具有语义层级上较为弱化的“major-power rivalry”的译法,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则达到了基本对等。
上下义词之间的置换,可以用两个译例说明。第一个是原型默认。2015年中国农历羊年到来之际,英美媒体中针对“羊”字的翻译有多则趣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5年2月19日刊发了一篇题为《绵羊年、山羊年还是公羊年?》的文章拉开讨论序幕。中国羊年中的羊到底是绵羊、山羊还是公羊?外国记者走访中国多地新年集市后发现,羊年玩偶有绵羊、山羊和公羊,甚至还有卡通形象喜羊羊。中国民俗专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山羊更为合理。但针对不同区域民众的走访,结果并不相同。这表明即使在中国文化中羊的文化原型范畴也是存在个体认知差异的,但是汉语人群通常默认“羊”这个上义词,无需进行区分。而在英语中,囿于语言所限,缺乏这样一个上义词,人们需要确定一个下义词表达这个原型范畴。我们认为,应该在“羊”的多个下义词中选择一个在英语中具有积极意义的词汇。由于scapegoat和black sheep均有贬义,因此建议选择ram一词。该词在英语中象征着领导力和权威,适合用于表示农历羊年。
第二个是转喻默认。张培基先生的《英汉翻译教程》中有如下例句:On the walk through the city they saw breadlines.原文用“breadlines”来代替“people who queue in line for the food given by the charity”,其中我们发现“breadline”经历了概念实体的两次转化,第一次是从下义词到上义词即“bread”到“food”,第二次是从食物到为领取食物而排队的人。英语受众对于这两次概念实体转化一般可以达成默认性理解。但是中国的救济方式有所不同,食物的种类也有所区别,译语读者不易理解和接受原有的默认,默认可能在任一环节中失效。认知语法中提出了详略度的概念,“人们可以使用高层次范畴的概念,以概括的方式来识解外部世界,也可以采取低层次范畴的概念来认知外部世界。”[23]120因此翻译上句时可以用高层次范畴的概念“食物”代替“面包”,之后再进行二次转化,以此弥合文化差异。参考译文为:“走过市区时,他们看见领取救济食物的人排着长队。”
2.意象置换
意象置换,即不同文化中使用不同的文化意象表达相同或相似的含义。翻译过程中,我们可以在不影响原文表意的情况下将受众不熟悉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意象替换为其更容易接受的意象。例如,“我们锐意推进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这个隐喻表达式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具有明确的默认意义,比喻完成艰难的任务。而英文中的“gnaw the hard bones”和原意并不对等。因此译者将之替换以“crack the hard nuts”,实现了功能与语用上的对等。
四、结 语
首先,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默认意义进行重新界定和分类。默认意义不仅包括认知默认和社会文化默认,还包括修辞默认。然后,对三种默认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细分:认知默认包括指称默认和级差默认;社会文化默认包括原型默认和文化习俗默认;修辞默认包括隐喻默认、转喻默认等。最后,提出默认意义的四种翻译策略,即默认保留策略、默认转化策略、默认增减策略和默认置换策略,以期促进默认意义在跨文化传译中的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1] 张绍杰,张延飞.默认理论与关联理论——解释“一般会话含义”的两种对立方法[J].当代外语研究,2012(7).
[2] Jaszczolt,K.M.Default semantics[A].K.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ition)[Z].Oxford: Elsevier,2006.
[3] Jaszczolt,K.M.Default Semantics: Foundations of a Compositional Theory of Acts of Communication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4] Husserl,E.Logische Untersuchungen (Vol.2) [M].Halle: Max Niemeyer.(trans.as Logistic Investigation.by J.N.Findlay).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0.
[5] Bach K.On referring and not referring[A].Jeanette K.Gundel & Nancy Hedberg (eds.).Reference,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6] Lyons J.Semantic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7] Strawson,P.F.On Referring[J].Mind,1950(5).
[8] Brown G. & Yule G.Discourse Analysis[M].Cambridge,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9] Levinson,S.C.Presumptive Meanings [M].Cambridge,Mass.: MIT Press,2000.
[10] Lakoff,G.Categories and Cognitive Models[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ognitive Science Report,1982(2).
[11] Wittgenstein,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Second Edition) [M].(trans.By G.E.M.Anscombe).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53.
[12] Rosch,E.Natural categories[J].Cognitive Psychology,1973(4).
[13] Fillmore,J.Frame Semantics[A].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C].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1982.
[14] Davis,W.A.Implicature: Intention,Convention,and Principle in the Failure of Gricean Theor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5] 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
[16] Lakoff,G. and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17] Croft,William.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J].Cognitive Linguistics,1993.
[18] Rudden,G. & Kovecses,Z.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Panther K.& Radden G.(ed.)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John Benjamins,BV,1999.
[19]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
[20] 张士东,彭爽.中国翻译产业发展态势及对策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21] 高方,苏童.偏见、误解与相遇的缘分——作家苏童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2).
[22] Hervey S. and I.Higgins.ThinkingTranslation:ACourseinTranslationMethod[M].London: Routledge,1992.
[23] 金胜昔,林正军.识解理论关照下的等效翻译[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