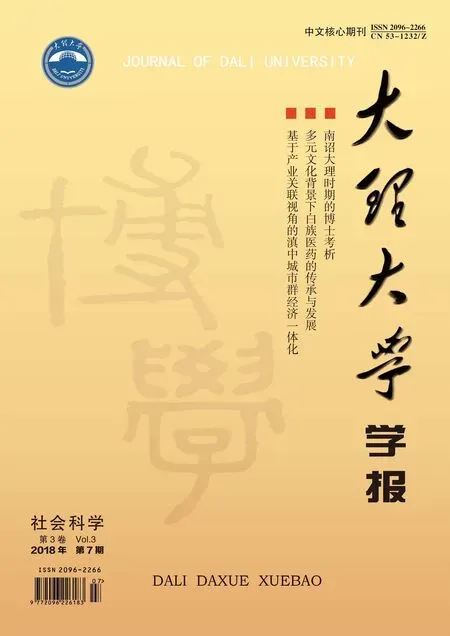大众旅游与旅游目的地人居环境变迁
潘 宝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
一、大众旅游与地方性社会人居环境
大众旅游(mass tourism)的存在意味着生活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其转变为旅游者是较容易的。便利的交通、消费社会的影响以及对远方的想象等因素激发了个体转变为旅游者的欲望。在现代性社会的影响之下,大众旅游也将更多的地方性社会转变为旅游目的地。大量的旅游者进入地方性社会,改变的不仅仅只是地方性社会的现代进程,也将地方性社会人居环境置于旅游活动的影响之中。这里所说的人居环境,指的是地方性社会的居住环境,包括水环境、声音环境、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社会交往环境等生态元素,是与旅游者原有居住环境相对的旅游目的地的人居环境。
从地方性社会的角度分析,那些远离现代性社会中心的边缘社会,特别是当现代因素影响较小时,其原有的人居环境变迁是缓慢的。而随着大众旅游的影响,特别是在旅游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刺激之下,尤其是当地方性社会将旅游作为其主要发展模式的时候,旅游目的地的人居环境就处于快速变迁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原有的人居环境,并不一定适于旅游者;而以旅游为导向对地方性社会人居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虽然能够接待更多的旅游者,但却并不一定适于生活于地方性社会的人们。
旅游目的地人居环境变迁与旅游者越来越多进入地方性社会紧密相关。以云南西部古城旅游为例,在旅游的影响之下,地方居民的饮用水由雪山水、泉水变为自来水;古城道路全部铺成石板;古城居民的居住环境被各种噪音污染;餐饮业的发展使得古城每天处理的垃圾越来越多;街道上不时出现宠物粪便等。这些变化对原来生活于古城的地方居民的直接影响是,既提高了其生活的成本,又使其日常生活存在诸多不便。由于大量旅游者进入古城,古城原来居民的房屋大部分被改造为客栈和餐馆,更多的客栈和餐馆使得古城的旅游发展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服务旅游者,而非古城地方居民。古城里面百货商店消失、菜场等生活场所消失使得居住于古城的地方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有时甚至需要步行去古城外面购买生活用品。因旅游者过多,特别是在旅游旺季,地方居民需花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才能获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旅游者过多,街道拥挤,有可能使得老人生病救护车进不去;甚至凌晨两三点旅游者还拉着行李箱在古城里走动,产生大量噪音影响居民休息;小孩与大人有时被外来宠物咬伤,地方居民与外来者发生冲突;旅游者以及客栈和餐馆产生大量垃圾,气味难闻。古城这些人居环境的变化,使得古城不再适于原住居民的居住,加之,在短期旅游经济利益刺激之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搬离古城。
单纯从旅游者的角度分析,地方性社会接待与服务旅游者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效果。地方性社会在进行旅游发展的时候,也多以旅游者的视角审视自身旅游发展的水平,这有可能忽视了地方性社会原有人居环境的变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旅游者越来越多,原住居民越来越少的情况发生。美国学者迪安·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曾指出:“现代化同时把这些东西与它们所在的民族与地域分离开来,打破了这些族群的完整性,并把这些族群从传统的依附带入现代的世界,旅游者们在现代世界里可以努力发现或重新构筑某一文化遗产或某一社会标识物。”〔1〕这就说明,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所改变的,除了人居环境,更将地方性社会的人们带入旅游影响的过程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人居环境之间,存在着旅游发展的矛盾性。一方面,地方性社会被塑造为旅游目的地的目的即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如此,地方性社会原有的各种民族文化形态有可能被再生产为旅游者感官体验的对象。另一方面,地方性社会原有较好的人居环境有可能也因为旅游的影响而朝向不利于原住居民的方向改变。地方性社会原有的社会秩序有可能被旅游重构,地方性社会人居环境的变迁有可能也单纯地以旅游为导向。这就说明,在旅游者视野中适宜居住的人居环境,在原住居民看来并不一定适宜。旅游确实能够为地方性社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地方性社会借助于旅游也能够与外部社会更好地沟通与交往,但大众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可能使得地方性社会更多关注的是旅游者、更多进行的是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而对于旅游目的地人居环境的变迁是否有利于原住居民,特别是在旅游发展的初期,则考虑得相对较少。
若旅游的发展是以人居环境的消极改变为代价的话,那么地方性社会的旅游发展对于原住居民来说,则有可能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离开旅游的中心区域,在旅游的边缘选择适于居住的地方。这样的旅游发展,既有可能造成原住居民离开现有居住地,又有可能将这些原住居民排除于旅游发展的过程,致使原住居民无法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最终,旅游目的地人居环境的变迁成为了外界旅游因素主导的一种过程,原住居民则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人居环境变迁主要涉及地方治理主体的旅游管理策略、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旅游从业者的经营活动等因素。大众旅游是现代性社会中的一种现象,其所改变的不仅仅只是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数量,也是地方性社会人居环境变迁所必然面临的一种旅游现象,与旅游行为直接相关。旅游行为所引起的人居环境的改变,应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人置于人居环境变迁过程中考虑;将旅游者、原住居民、旅游从业人员纳入人本位之中考虑,从而思考旅游行为与人居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旅游行为与旅游目的地人居环境变迁
地方治理主体的旅游管理策略是人居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即地方治理主体在面对人居环境变迁时,是制订以旅游者为导向的旅游服务策略,还是制订以原住居民为导向的旅游服务策略,导向的不同直接决定着旅游目的地的人居环境是否再次适于原住居民居住。而且地方治理主体的旅游管理策略也直接影响着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和旅游从业者的经营活动。地方治理主体是地方旅游活动的主导力量,因此,人居环境直接受到地方治理主体在旅游形象塑造等活动中的影响。而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则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地方性社会的人居环境,更有可能破坏人居环境的社会秩序。旅游从业者直接的作用对象是旅游者,两者之间的活动所带来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旅游行为所产生的餐饮垃圾以及改变旅游目的地原有的生态环境。
如古城的水资源,旅游者未大量进入古城之前,河道里的水是从雪山流下来的水,且居民日常生活可以用。但随着旅游的影响,产生了大量的河道垃圾,这些水已经无法直接使用。古城井水较多,煮饭、洗菜、洗衣服,每一眼井都有水的地方性社会秩序,但随着旅游者增多,外地居民在古城居住,自来水使用的增多,井水也受到了污染。而古城的噪音,如酒吧的声音、旅游者的嘈杂声、宠物的叫声等直接影响了原住居民的休息,尤其是有些家庭小孩还要上学、大人还要上班,这使得古城更不适于原住居民居住。旅游者选择居住在古城,但时间短暂,过短的时间体验使得旅游者反而觉得古城有特色,适宜居住;而那些世代居住于古城的居民,面对天天如此的人居环境,他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是被破坏了。若古城只适于旅游者,而不适于原有的地方居民,那么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确实改变了古城的人居环境。但旅游恰又是地方性社会发展的一条现代道路,它将处于边缘的地方性社会融入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性社会也确实通过旅游发展提高了人均收入,改善了地方性社会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这些改变并不意味着居住于旅游目的地中的居民,他们的人居环境是在朝着积极的一面改变的。
这也并不意味着,人居环境的消极变化就一定是旅游行为所导致的,或者说,并不能一味指责旅游所带来的消极因素,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协调各种利益主体,使他们能够同时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英国学者约翰·尤瑞(John Urry)曾指出:“旅游者可能会因当地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发展而受到指责。当旅游者在经济上、民族及文化上与当地的居民之间差距很大时,这种现象就更明显。当地居民在经历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时,这种现象也同样明显。”〔2〕这就说明,旅游者与地方性社会人居环境的变化虽然有着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能绝对主导人居环境的变迁。若地方居民或者地方治理主体只是被动接受旅游行为所带来的影响,那么,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就有可能绝对主导着人居环境的变迁。
因此,地方居民和地方治理主体应主动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将旅游者的旅游行为转变为地方性社会发展的动力。即使没有旅游发展,人居环境也处于变迁过程中,只不过旅游的存在加速了人居环境变迁的步伐。若旅游的发展过于关注旅游者和旅游从业者,则有可能忽视地方居民日常生活因旅游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旅游发展不可能使得所有生活于地方性社会的人都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同样的,旅游活动也不可能影响地方性社会所有区域的人居环境。而是说,在旅游活动直接影响的地方,原来居住于此的人们,他们的人居环境确实因为旅游行为而被改变了。
旅游行为的产生首先因为个体期望观看远方的景观,并想象着远方的各种文化形态,以及期望体验异域的民族文化。但在个体转变为旅游者的过程中,旅游者的视野并不一定能够与地方居民的视野相一致,或者说,两者有可能在旅游行为中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并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冲突,而有可能是一种间接的冲突。尤其是当过多的旅游者影响了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地方居民从心理上不接受旅游者及其旅游行为也就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当旅游经济行为与地方居民无关的时候,这种冲突就极易发生。英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曾指出:“经济边界创生出了一些以地域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利益共同体都具有这样一个极为本质的特征:它们很容易把所有的利益冲突都变成它们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人员构成会不断发生变化的那些群体之间的冲突;因此,它们所导致的那种冲突也就成了某个国家居民群体之间的永久性冲突,而不是位置各不相同的个人之间的那种冲突。”〔3〕这就说明,旅游行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可能将地方居民与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等相关群体相区隔,并导致其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这种利益冲突又不仅仅只局限于经济利益,有可能是人居环境的一种冲突。也就是说,旅游目的地人居环境的变迁是某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而非只是由旅游这一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
地方居民有可能在旅游经济利益的刺激之下,主动适应并参与旅游经济活动,从而由地方居民转变为旅游从业人员;也有可能无法适应已经变化的人居环境,不参与旅游活动而迁移至旅游边缘地带那些适宜地方居民居住的地方。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地方居民居住于哪里,其所处的城镇或者乡村整体的人居环境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旅游行为的影响,旅游目的地亦应制订相应的生态策略,在旅游环境中创建适于地方居民居住的人居环境。
三、旅游过程中人居环境的生态策略
随着生态观念的发展,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都意识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地方性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旅游确实为地方性社会发展提供了比较便捷的路径,但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性社会也应考虑长期居住于此的居民,制订相应的生态策略,使他们的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美国学者戴伦·蒂莫西(Dallen J.Timothy)曾指出:“可持续的旅游应该使当地居民和少数民族从产业中获益。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很多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人来说却是弊大于利。就业和社会服务是文化旅游的重要产出,属于任何当地群体参与旅游业的正常期望。而大多数情况下,旅游企业常常隶属于富裕的外国人,并用极少的薪水雇用当地人。”〔4〕这就说明,地方居民在面对旅游经济发展之时有可能处于劣势地位,而人居环境的改善,并非与某一旅游主体直接相关。或者说,并不存在单一旅游主体的力量可以绝对改变旅游目的地的人居环境。而是在旅游语境中,所有受到旅游影响的相关主体,都能够主动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并主动适应旅游交往的规则,将不利于旅游目的地人居环境改善的因素降至最低。
从地方治理主体的角度来说,人居环境的改善不应仅仅只从旅游的角度考虑,或者只将短期的旅游经济利益作为重点,而是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引导地方居民与旅游者相互沟通与交往,增进彼此的文化认同。旅游发展应当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生活于旅游目的地的人,而不仅仅只是旅游者,因为曾经的旅游者也有可能因为认同地方性社会的人居环境而转变为地方居民。因此,地方治理主体应当制定保护人居环境的规章或制度,在投入一定经济资本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应提升旅游目的地的人居环境。地方治理主体既不能从纯粹发展旅游经济的角度一味地将旅游发展置于地方性社会发展的最优级别,纯粹追求资本经济利益;亦不能从纯粹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一味地忽视那些借助于旅游提高其家庭人居环境且生活于地方性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当个体与家庭和地方性社会都在借助于旅游发展自身的时候,地方治理主体更应该在追求旅游经济利益与提升人居环境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如合理规划使用水资源、有效处理餐饮垃圾、完善旅游冲突解决机制,使得原住居民与旅游移民都能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获益。
在旅游者的层面上,因其旅游活动是短暂的,其处于旅游目的地的时间也是短暂的,但其旅游行为确实改变了地方性社会的人居环境。因此,规范并引导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提高其不打扰地方居民日常生活的意识,提升自我的旅游文明程度并规范自我的旅游行为,在旅游社会发展过程中亦显得尤为重要。旅游者旅游行为的发生不能以破坏地方性社会的人居环境为前提,更不能因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为地方性社会旅游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对其不恰当的行为听之任之,甚至纵容。另一方面,也应意识到,旅游者的行为影响的不仅仅是地方性社会的人居环境,也影响着地方性社会的旅游形象。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不应仅仅只停留于感官层面,也应主动了解并认同地方性社会的民族文化,地方性社会也应为旅游者提供直接了解地方性社会民族文化的机会,即向旅游者介绍地方性民族文化的人,应是生活于地方性社会的人们,而非仅仅只是将介绍地方性民族文化作为工作的人,以便将影响地方性社会日常生活的消极因素降至最低。
从旅游经营者的角度来说,其经营的活动不应对人居环境造成破坏,地方治理主体也应引导旅游经营者使其在获得旅游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应提高其保护人居环境的意识。尤其是当外部社会更多的旅游从业者进入地方性社会之后,这些外部社会的人们应当尊重地方性社会的民族文化,规范自我的经营活动,使其主动参与到地方性社会人居环境的保护过程中。英国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曾指出:“许多旅游业的经济组织(通过大的旅游经营商和宾馆服务)远离当地文化空间,过度沉迷于提供旅游享乐方面的商品服务,而未能认真参与当地社会。不过,当地群体已经逐渐意识到,他们也可以为观众进行自我展示。这意味着,旅游者和当地的接触总是有可能产生更有挑战性的自我与他者展示类型。”〔5〕这就说明,旅游从业人员更多关注的是其在旅游活动中能否获得经济利益,而在水资源保护、餐饮垃圾处理等方面生态意识淡薄。更突出的问题是,旅游从业人员与当地社会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现象,即地方居民不仅不接受旅游者,更不接受旅游从业人员。因此,旅游经营者应当在旅游者与地方居民之间充当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媒介,理解旅游对彼此的意义,保护地方性社会生态环境。
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说,既应理解地方治理主体发展旅游的目的,也应参与到相关旅游行为规范的制订过程中,从旅游发展的客体转变为旅游发展的主体,共享旅游发展成果。无论旅游如何发展,地方性社会人居环境的改变都应考虑地方居民现有的生活方式,即地方居民的人居环境确实因为旅游发展而受到影响,但地方居民应当参与到地方性社会旅游发展过程中,而非一味只是不认同现有的旅游发展模式,或者只是为了获得初级的旅游经济利益而一味逃离旅游中心区。美国学者罗伯特·墨菲(Robert F.Murphy)曾指出:“每一种社会习俗或社会制度背后都有一种隐藏的难以觉察的作用,紧随着每一个伟大计划的是一系列完全出乎意料、难以预见的结果。故我们必须审视表面外观和常识经验的实在背后,以便达到蛰伏于表现之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之流。我们的任务是描述和分析他种体验模式,但更为重要的是注视熟知的对象,从中发现全新之物。”〔6〕这就意味着,旅游不仅改变的是旅游目的地的人居环境,人居环境的改变亦是地方性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旅游现象所展现的各种利益与冲突,是地方性社会适应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说明,旅游生态的保护需要地方居民的参与,分析旅游生态问题也应看到地方性社会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一味适应旅游者的旅游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地方居民的不认同,而一味追求旅游经济利益的发展模式也有可能给地方性社会人居环境造成无法修复的后果。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之间,应当是良性互动的,地方居民主动参与旅游活动,不仅改变的是地方性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转变。
大众旅游使得地方性社会被纳入至旅游目的地的转变过程中,地方性社会的人居环境也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被改变了。适宜或者不适宜居住的背后,是地方性社会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过程。人居环境的破坏并非是大众旅游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有可能是人在面对旅游经济时一种功利性选择的结果。地方性社会的民族文化与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之间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表面的旅游现象所导致的人居环境变化,其深层次的原因往往也是地方性社会与外部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只不过这种结果不能因旅游的存在而纯粹评判其优劣。而随着地方性社会与地方居民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旅游所带来的消极因素正在成为地方性社会关注的焦点。旅游改变的不仅是人居环境,也改变了地方性社会的经济秩序。旅游中心与旅游边缘的存在,亦使得旅游对地方性社会的影响产生了差异。人居环境的变迁是否适于当地居民,是衡量旅游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只有在旅游过程中解决人居环境问题,才能进一步为地方性社会创造更宜居的人文环境。
〔1〕迪安·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M〕.张晓萍,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
〔2〕约翰·尤瑞.游客凝视〔M〕.杨慧,赵玉中,王庆玲,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5.
〔3〕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69.
〔4〕戴伦·蒂莫西.文化遗产与旅游〔M〕.孙业红,译.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4:314.
〔5〕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M〕.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9.
〔6〕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王卓君,吕迺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