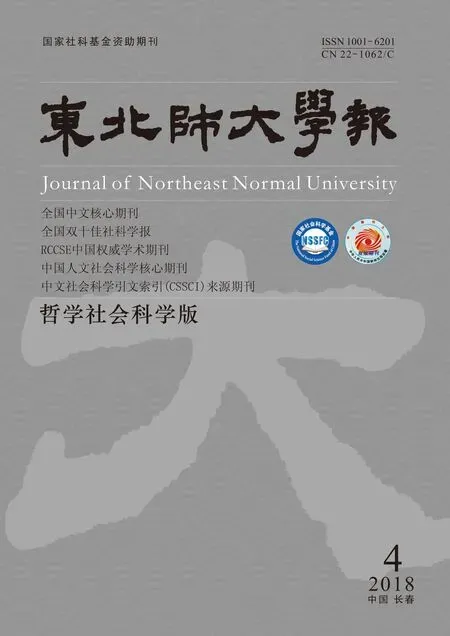从《左传》的偏正结构和句子长度看现代汉语细节意义的增强
李 青 苗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左传》这部史书的文献价值众所周知,它在文学和史学上的意义历来为人所称道,在语言学领域,也有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不断地研究探索。《左传》包含的各类信息如同海底的宝藏无法计数,每一项信息内容都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例如,书中偏正结构的内部构成与今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简洁的句式和今天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古今对比的差异便折射出了汉民族对细节意义逐渐重视的历史。
《左传》中记载的某些地名是读者们耳熟能详的,例如“城隶”“城濮”“程颍”等等,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就出现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1]458初看起来,大部分读者可能认为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地名,无特殊之处,从而忽视了它所包含的一些重要信息,因此,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城”的含义。
一、历史溯源
“城”在古文中经常以“城池”的形式并列出现,按照古代的行政区划,城池指城墙和护城河,又有“城郭”的说法,实际是内城和外城的区别,本来它们指的是古代国家的军事防御建筑,后来便泛指城市。城池依照等级的不同,又可配置不同规模的官方建筑。
周朝拥有了天下之后,周朝的势力并不能有效控制商朝的所有领土。原商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与周人相比,在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很大的差异。为了进一步稳固统治,周公于是东征,摧毁商殷及同盟的势力。东征取得胜利后,周朝便在全国新占领的东方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即分封制。周朝所分封的贵族率领他们的公社农民在进驻新占领的区域后,首先就要建立一个军事据点,以备战争的不时之需,这样的据点就被称之为“城”,也称“国”。而“国”之外的广大区域则称之为“野”。王朝的畿内和诸侯国都有这种国野之分,即乡遂之别。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的生计一般都要仰赖“野”的供给,而对“野”却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2]395。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1]94此处说的就是相互依存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立下级,等级之别分明,庶人则不再分等级而以亲疏关系作为等级之区别。由此,我们依据上面的历史记载,了解了“城”的大致含义,可以断定“城濮”“城隶”等并非是固有的地名,而是相当于“城某”,意思上等同于今天的“某城”。而今天的偏正式结构,一般而言都是“偏+正”的形式,如“北京地区”“南京市”“沙县”等等,都是小名在前,类名在后,但是在《左传》中,这些地名却是“城濮”“城隶”这样的“正+偏”的组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组合顺序变化,我们认为,这正体现了这期间人们开始对细节意义重视的变化。
二、涵括意义和细节意义
储泽祥(2004)对涵括意义和细节意义进行了精彩的阐释。“所谓涵括,即人类对世界的经验中建构和识别事物时的网络,而细节就是网络上的节点。涵括义具有整体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细节具有局部性、具体性和生动性。”[3]175无疑,对于偏正结构来说,修饰成分表达的为细节义,中心语表达的是涵括义。就一个词的词义变化来说,涵括义的变化肯定相对较慢,因为它基本上概括的是理性意义,也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细节义相比较而言,就要快得多,因为人们的认识水平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细节义是为了辅助涵括义,使其更加形象或者具体,例如“雪白”“火红”“绿草”一类,这些词语较之单用的“白”“红”或者“草”来说,一定是表义更加清晰具体,同时这些修饰成分必然会有同一聚合关系中其他的成分可以替代,从而构成更多的新词语。
当然,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的情况是偏正之“偏”有时胜过“正”的分量,在语言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偏”和“正”的关系恰如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对语法规则而言,归根结底,形式是主要的,表面上看来,形式是体现内容的,然而,很多时候,形式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否则形式语法便没什么用武之地了。朱德熙(1985)谈道:事实上,凡是形式上验证的语义分析对语法研究来说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语音形式无论负载着怎样丰富的语义,这些语义又可以获得多少认知上的理解,也都要按照线条型的原则,有先有后地以语音的方式说出来。就是形式化出来。我们的语言研究,无论在认知上取得了多少成果,解释得多么具有‘心理现实性’,如果没有跟线条型的‘说’结合起来,没有落实到形式上,就都跟语言表达的方式不相符合,其研究也都不算完结,没有落到实处。”[4]
为什么说偏正从“正+偏”变成了“偏+正”是由于细节意义的加强,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角度来理解:认知语言学中有个术语叫“完形原则”,即人们对事物有一个整体认识,例如在人们头脑中“房子”是由一些线条和形状构成的整体,而不会是墙面和门窗的多个部分组合。涵括便是人们对某事物“完形”感知的结果,我们可以视一个事物为不同细节的侧面的组合,或者说它是不同侧面的综合。细节是人们关注某事物一个或一些认知域的结果,是涵括关涉的各个方面。一个事物可以视为具有不同侧面的细节组合,可以隐喻为不同的认知域,涵括是将它们进行的综合,而细节则是人们关注了其中的某一个认知域或某一个侧面。“偏”放在了靠前的位置,也可以说将细节放在了起始的位置,表示人们的关注点放在了前面的细节;“偏”的数量的增多,则表示细节意义的增多。汉语的发展也证明了这样的变化,对比古今的工具书,我们不难发现,古今给词释义的显著变化当中,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现代汉语的细节义明显增多,《说文解字》中共收录9 353个字,《汉语大辞典》就高达5万6千多个条目。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促使人们对事物的区分越来越细致,对其表述也越来越精确,这些都是语言现象变化发展的体现。
徐通锵(1991)认为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他试图从语义角度来建构规则系统,涵括、细节范畴的建立,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试图通过这样一个平面使汉语的语义规则系统得以确立,当然同时也不能忽视句法管控的作用。虽然说,细节是用来表现涵括的,涵括成分与细节成分从表意功能看,二者却是互补的,这就如同形式语法和功能语法虽然是对立的,但是二者在很多时候也是互补的一样。二者互补是汉语句法的语义底蕴,也是支配句法组合的内在动因。涵括需要细节来描述,细节是用来表述的具体内容,细节不足会造成表述不足,语义不明,反之,细节过剩,也会造成表意繁复不能切中要害。这便是二者的辩证关系。
施春宏(2001)认为名词的语义成分可以分成关涉性语义成分和描述性语义成分两类,并认为描述性语义成分就是细节。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是恰当的,描述性、限定性的作用是修饰语的典型作用,“城濮”“城隶”和“红花”“绿草”中的修饰语都主要是发挥了这一作用。涵括与细节的互补性,是语言单位相互匹配的语义基础。涵括与细节的对立互补,是组织句法结构的基本原则[3]187。
三、《左传》后汉语句子长度的增加和范畴理论的发展体现细节意义的增强
人类认知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一定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整个人类社会,无不是沿着这样的发展轨迹向前行进的。《左传》中的每一篇或曰“每一年”,都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信息,然而,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却包含在寥寥数语当中,那时的语言表达,句子大多很短(当然,书中也有很多地方用了大量排比对仗的长句子,但是与今天的文段相比,句式简短仍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如《左传·庄公十年》:“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1]182再如《左传·僖公四年》:“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1]288了解一点春秋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两句话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然而,这里的句子却只有十几个字。而今天的句子比先秦古代汉语中的句子要复杂得多,表达的信息显然也会更加清晰和具体。
这一点,可以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理论来解释。
象似性指的是语言符号在语音、形体或者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着映照性相似的现象。象似性从不同角度又可以分为很多类型,例如数量象似性,说的是符号单位的数量与它所表示的客观现实的概念数量和复杂程度成正比,与信息可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概念量越大,越复杂,表达它们的符号成分也就越多,同时它的形式也会越复杂。语言成分的长度便象似了现实表述事件的长度。想要表述的信息量越多,强调的细节义也就越多,修饰成分越多,句子也就越长。当人们感到需要或者必须传达更多更复杂的信息时,句子的长度便在无形中增加了。今天现代汉语的句子较之《左传》的“十年春,齐师伐我”而言,无疑是更加复杂了。
符号的象似性还包括顺序象似性,体现在符号组合往往遵照认知、思维顺序来编排顺序,人们的认知习惯、思维顺序,与文化习俗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例如时间顺序的表达上,中国是按照 “年、月、日”的顺序,而西方则是按照“日、月、年”的顺序;对于地点的表达,中国按照“国家、省、市、街道、房屋”来排序,而西方则是“房屋、街道、市、省、国家”来排序;中国对人的称呼是“姓+名”,但西方却是“名+姓”,等等。这种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中西的不同认知特点。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对象的观察,在思维或认识上大体遵循两种策略,一种是由外到内,另外一种则是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策略遵照的是由小到大的语序排列顺序,由内到外的策略则是依据的由大到小的语序排列顺序。“大”与“小”或者“外”和“内”分别对应着涵括和细节。比如现代汉语,是修饰语处于核心成分左边的语言,它在操作上遵循一种由较大的外延向较小的外延逐渐过渡的排列顺序;而修饰语处于核心成分右边的语言,在操作上则会遵循一种由较小的外延向较大的外延逐渐过渡的排列顺序。现代汉语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即“偏+正”的顺序,这种由大到小的修饰语与中心语之间排列的程序,正好反映和映射了汉民族的由外到内的认知方式。
陆丙甫曾经提出了一个“向心轨层理论”,这一理论发现了语言中许多表面看起来不同甚至相反的现象背后具有的内在统一性规律。该理论认为,语言中普遍存在一种成分间的亲疏等级关系,这一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动词、方式状语、工具状语、处所状语、时段状语和时间状语中。虽然在有些语言中,某些修饰成分在语序上由大到小地排列,比如汉语的时间状语和地点状语的排列顺序,或者是某些修饰成分在语序上由大到小地排列,例如英语的时间状语和地点状语的排列顺序,然而无论是由大到小、还是由小到大地排列,总是越靠近核心的成分越小,越稳定,越远离核心的成分越大,越不稳定。陆丙甫(1986)对名词附加语作出了抽象,探讨了不同语言中的修饰语与中心语的组合顺序符合这种“轨层理论”,即无论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还是之后,它们与中心语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这一抽象反映了一些语序规则,大致如下:
时间>空间>颜色外观>质料>功能
虽然这一理论十分绝妙,然而每个成分的归属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仅就“功能”这一项就有很多成分并列,其间的顺序排列就是一个难题,于是,又得出了一个大体的原则,即按照功能出现的时间先后来安排语序。
无论什么样的语言,修饰语的叠加都是在于使核心语的意义更加形象化和精确化,即对细节意义的重视和强调,而过程就是对核心语在外延上逐步限制缩小的过程。无论是修饰语在核心成分的左边,还是修饰语在核心成分的右边,操作上虽遵循不同的逐渐过渡的方向,但是最后还是都落到了核心成分上,这种成分排列的顺序同样符合心理操作上的省力原则。
还有一个论据来证明这一点,就是关于范畴理论的发展。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的边界是清晰的,一个成员是否具有这个范畴的特征也是确定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涵括意义的高度重视;后来,认知语言学对范畴的涵义有了进一步理解,发展出了原型范畴理论,强调范畴成员之间具有属性的相似,细节意义开始被重视。沈家煊(1999)强调,追求涵括,讲究的是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的特征,而追求细节,讲究的是成员之间属性或侧面的交叉性、相似性。这两者之间本就是互补的,不必是不能兼容的。建立了涵括、细节范畴恰好又可以将理论的局限进行弥补,即范畴之间在涵括意义上是离散的,然而在细节意义上却有着各种联系,由最初经典范畴理论重视“二分”的特征,发展到后来的强调共有属性的原型范畴理论,便是细节意义被重视的证明。
“北京市”“上海市”的说法也可以简称为“北京”“上海”,这说明,在这两个语言单位中,“偏”的地位比“正”的地位更加重要,在“细节+涵括”的组合中,无疑是细节占了上风。如果说语言形式是人类认知的反映,现在这种形式体现了汉民族的认知特点,那么,《左传》中“城濮”“城颍”这种“正+偏”的组合当然也反映了当时汉民族的认知特点,何以产生了这样的变化,二者之间的转变其实就证明了从古到今细节意义的增强。
四、细节意义增强的认知基础
姚振武谈到语序问题时曾经指出:“时不我待”是我们熟知的“宾语前置”现象,这样的语序在现代汉语中几乎绝无仅有,按照“优势序列”的办法,应该只有“不待我”之类的序列,而“不我待”的序列是价值不大的,但这种语序代表了汉语过去的一个时代,在过去是一种绝对多数的现象[5]2。同样的道理,偏正结构在今天是“偏+正”,但是古代汉语却是“正+偏”的形式,今天看似微不足道的语序在古代汉语中却是一个占多数的组合顺序。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语序,任何语言事实从原则上说都有一个从少到多,又从多到少的过程,“偏正”结构的组合顺序确定下来,也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在科学研究中,以少胜多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因此少数的语言事实也很重要,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某种语序与人的“认知心理”可以直接联系起来,虽然有时候看来似乎有些牵强,然而也不失为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方法。
汉语在语序类型上有着自身的特点,有时是不规则的,而同时,又体现出自身的语序的一致性,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对汉语语序的不同理解和认识。现代汉语中偏正短语或者偏正关系的复合词通常是按照“修饰成分+中心语”的组合顺序来安排语序,而古汉语却有着大量“中心语+修饰成分”的组合实例,同样的例子在《诗经》中也是存在的,《国风·将仲子》便有“无折我树杞”“无折我树桑”“无折我树檀”,句子中的“树杞”“树桑”也就是今天的“杞树”“桑树”。刘宁生(1995)曾经分析了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即“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认知基础分别是“目的物”和“参照物”,“目的物”和“参照物”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决定了两个成分之间不能自由地充当“目的物”和“参照物”,“修饰语”常常位于“中心语”之前的原因,是因为汉语中存在着一个“参照物先于目的物”的语序原则,这就形成了汉语的“修饰语+中心语”的语序一致性[6]81。也就是开始了汉语更加重视细节意义的传统。
刘宁生认为,尚不清楚语法结构的形式是否有认知基础。但我们如果拿后来的构式研究理论来回应,无疑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构式理论认为,构式本身就存在意义,意义的产生就会有其认知基础。之后,马洪海在《中州学刊》发表文章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参照物”在前或“目的物”在前,是两种不同的感知过程,也因此,在汉语里就有两种与之相应的表达方式,人们选择哪一种,是由于不同的语境语用的需要。这是一种更加涵括的说法,事实上,“正偏”到“偏正”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不然古代汉语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宾语前置”的现象了。
参照物和目的物构成偏正关系的定心结构,它们的排列顺序当然也要受到这种由外到内的认知方式和定心式句法结构中修饰语在前的规则制约,就参照物和目的物的关系而言,目的物必是核心成分,参照物必是修饰语,而根据汉语名词性偏正结构中修饰语在前、核心成分在后这种语序规则,也就决定了偏正结构中参照物在前而目的物在后。总而言之,如果说汉语表达中存在着“参照物先于目的物”的语序原则,那它不是表现在句子的主谓句式表达中,而是表现在定心式的句法结构中。而定心结构中“参照物先于目的物”的语序规则,是由汉民族“从外到内”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和定心结构中修饰语先于中心语的语序规则以及参照物对应于修饰语的原则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语言研究中,人们对于偏正结构一直倾注了很多的研究热情,偏正关系的语言结构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左传》地名中的偏正结构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语言现象,而涵括与细节意义范畴的提出恰好可以解释其中看到的语言发展变化。《左传》中句子的长度与今天相对比差异明显,从中也可以反映人们的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规律,体现了人们对细节意义的重视,这些问题都可以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因此,传统的语言研究问题可以用现代的语言学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左传》这部文献典籍蕴涵的大量信息,是值得我们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发现和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