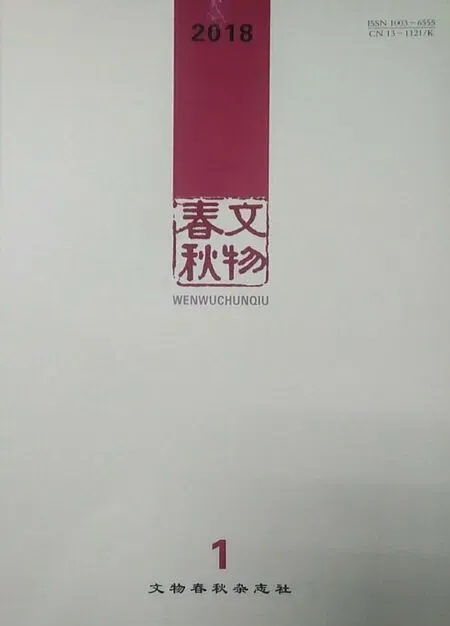北魏营州刺史高道悦墓志铭考
吕宏伟
(德州市博物馆,山东 德州 253500)
北魏《高道悦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于1969年出土于德州市二屯镇胡官营村,全称《故散骑常侍营州刺史高使君墓志铭》,现存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墓志刊刻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志石长83厘米,宽82厘米,厚10厘米。志阳刻志文28行,满行30字,共814字,每字界以方格(图一)。志阴刻志文12行,每行字数不等,共144字。字体为魏书(图二)。无志盖。此志出土后便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秦公先生《释北魏高道悦墓志》[1]一文完成了墓志的录文工作,对志文中所涉及人物进行了初步的考释,尤其是对墓志书法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赖非先生有《高道悦墓志》[2]一文对墓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赖非先生在《北魏高道悦墓地调查及其墓志补释》[3]一文中,将高道悦墓以及墓志的发现情况做了说明,成为研究高道悦墓志与高氏家族墓地的可靠资料。下面,笔者从志主的身世、历官、生平事迹及家族墓地等方面对墓志进行进一步考述,并对高道悦的死因作深入分析。
一、录 文
志阳:
君讳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安乡北里人也。世袭冠冕,著姓海右。乃祖东夷」校尉、徐无侯,声高海曲,风光前魏。曾祖尚书仆射,才辉龙部,翼范后燕。祖齐郡,清」猷孤远,名播二国。考平州璋夙树,腾声早年。君禀河山之秀气,含晷电之神」精,冲龄表岐之风,绮岁招生知之誉。渊情峻邈,器宇难窥;青襟沿庠,业光衡」塾;羁发序,童风辉茂。美清言,善赏要,好意气,重声节。孝敬醇深,机鉴英越,志」性端凝,言不流杂。气韵苕递,与白云同翻;风概昂藏,与青烟俱。年十五,除中」书学生,拜侍御史,迁主文中散,转治书侍御史。当官而行,豪右敛衽。荆扬未宾,」豹尾路,星遣飞,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阅集洛阳。而兵使褰违,稽犯军律,宪」省机要,理膺绳究。尚书仆射任城王,地戚人华,宠冠朝右。尚书右丞公孙良,才」望冲远,天心眷遇。皆负气自高,曲树私惠。君并禁劾,会赦洗咎,由此声格遐迩」敛属。虽二鲍之匡汉朝,两傅之谐晋室,无以过也。进谏议大夫,献纳风规,朝野」耸听。高祖孝文皇帝深相知体,雅见器爱,临轩称叹,形于诏牍。既而从」县洛中,更新朝典,铨品九流,革易官第,妙简才英,弼谐东贰。乃除太子中庶子。」缉正储闱,徽音独韵。但河阳失图,潜怀不轨,追纂楚商,连规宋劭,拔剑吐心,邀」同枭镜。君厉声作色,抗其凶计,既殊潘崇飨芈之谋,遂同阳原头风之祸。以魏」太和廿年秋八月十二日春秋卅五,暴丧于金墉宫。高祖闻而流涕,曰:“非但」东宫缺辅,乃丧朕社稷之臣。呜呼!枉歼良器,深可悼惜。”乃诏曰:“门下故太子」中庶子高君,资生亮,禀业忠淳,作弼储侍,匡直贞发。遂为群小所忌,危身禁」中。行路致叹,视听同悲。朕甚振悼于厥心。可赠散骑常侍、营州刺史,谥曰‘贞侯’。”」兼赐帛一千匹,并遣王人监护丧事。以其年秋九月迁葬冀州勃海郡县之」西南,以为定窀。但旧葬下湿,无可重厝,因此凶际,迁葬于王莽河东岸之平岗。」神龟二年岁次己亥,春二月辛亥朔廿日庚午,穸于崇仁乡孝义里。昔太和之」世,圹内有记无铭,今恐川垄翻移,美声湮灭,是以追述徽猷晰壤阴。其辞曰:」辽海耀精,营龙辉灵,神区蔼,世育人英。遥源昭晰,绵叶贞明,如彼芳兰,根柯」连馨。邈哉夫子,卓矣难窥,师心晓物,□洞生知。昂昂千里,汪汪万坡,清辉郁映,」芳风葳蕤。耸韵西京,翻光东国,宪阁承规,储闱仰则。二鲍著英,两傅惭德,」高皇称叹,形于简墨。比干逢辛,阳原属劭,隋庭殒光,荆门丧宝。痛贯云烟,哀惊」禽鸟,式铭泉阿,永旌风道。

图一 高道悦墓志志阳拓片

图二 高道悦墓志志阴拓片
志阴:
故散骑常侍营州刺史高使君墓志铭」
曾祖策,后燕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曾祖母辽东李氏,父超,燕太府卿。」祖育,燕大司马从事中郎,归国除建中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肥如子。」祖母昌黎孙氏,父道,后燕庭尉卿。」父起,青、冀二州治中,武邑郡督,早亡。」追赠平远将军、平州刺史。」母辽西李氏,父才,后燕给□□。」使君夫人顿丘李氏,」祖、父官宦已见于夫人」之墓志序,故不重□。
二、考 释
1.家族世系
据志文可知,志主高姓,名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魏书》载:“辽东郡秦置,后罢。正光中复。治固都城……新昌二汉、晋属,后罢。正光中复。”[4]由此可知,辽东郡最初为秦朝所置,新昌县在两汉、西晋时皆属辽东郡。另见《海城县志》载:“(汉)海城县境置新昌、辽隧、安市县,属幽州刺史部辽东郡。”西晋时“因袭汉制。海城县境置新昌、安市二县,属平州”。前燕、后燕海城县境内仍置新昌、安市二县,属辽东郡[5]。因此志文中所载“辽东新昌”应在今辽宁省海城市境内。
早在春秋时期便有高姓北迁的记载,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6]869因墓志言高道悦先祖、曾祖皆任职燕国故地,故赖非先生认为“(高道悦)大约是‘奔燕’的高止之后裔”[2]250,应该以此说为是。
志文载:“世袭冠冕,著姓海右。”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海右)泛指黄海、东海的近海地区,以在大海之右(西),故名。”[7]由此可知,“海右”实为一个泛指的地域概念,即今河北、辽宁、山东等地,而此处应理解为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更为合适。
志文对高道悦祖上有所记载,曰:“乃祖东夷校尉、徐无侯,声高海曲,风光前魏。”“东夷校尉”又称“护东夷校尉”[8],为官名。何时所设目前学术界并无定论,一般认为始设于曹魏时期,又以金毓黻先生为代表[9]。《晋书·地理志》中记载:“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而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还合为幽州。及文懿灭后,有护东夷校尉,居襄平。”[10]虽然《晋书》的此段记载明确指出东夷校尉始置于曹魏时期,但也有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其中,据陶元珍先生考证,曹魏时期并未在辽东设置平州[11],以此结论为依据,张国庆先生认为,“《晋书》云护东夷校尉与平州相伴而置,可为曹魏时不曾设置护东夷校尉之佐证”[12]。范兆飞、房奕将其划分为“魏置说”与“晋置说”[13]两大阵营,而此墓志所载“乃祖东夷校尉……风光前魏”之句则为“魏置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志文中提到了高道悦曾祖、祖父及父亲的官职,对照《魏书·高道悦传》的记载,志史互补,可将其内容进一步完善。
其一,志阴载其曾祖高策的官职为“后燕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志阳又载为“尚书仆射,才辉龙部,翼范后燕”,《魏书》载其为“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14]1399,因此可以推断,志文所谓“后燕”实指冯跋所建立的北燕,至于官职应以墓志为是。
其二,关于其祖高育,志阴载:“燕大司马从事中郎,归国除建中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肥如子。”志阳载:“祖齐郡,清猷孤远,名播二国。”《魏书》载:“祖育,冯文通建德令。值世祖东讨,率其所部五百余家归命军门,世祖授以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14]1399综合志、史所述,高育应为北燕大司马之从事中郎、建德县令,后因归顺北魏而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续用,不仅任齐郡、建德二郡太守、建忠将军(志文载为“建中将军”),而且赐子爵。
其三,关于志主父亲的名字,志史记载不同,《魏书》[14《]北史》[15]皆载曰“玄起”,志文曰“起”,应以墓志为是。
通过高道悦先祖(东夷校尉)、曾祖高策(后燕散骑常侍)以及祖高育(北燕建德令)的官职,我们可看出此支高氏世居燕国故地。通过志文可知,高道悦之父高起官至武邑太守,死后追赠平远将军、平州刺史。另据《魏书》中对高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县”[14]1399的记载可知,在高起任武邑太守后,其家方才定居勃海郡县。
2.仕宦经历
高道悦历官中书学生、侍御史、主文中散、书侍御史,后进谏议大夫兼御史中尉、太子中庶子,卒后赠散骑常侍、营州刺史,谥号“贞侯”。
高道悦任职书侍御史期间尽职尽责,对皇族高官亦以法相待。志云:“当官而行,豪右敛衽。”“豪右”即指豪门大族,“敛衽”为收敛衣冠,表示恭敬之意。此句指志主上任后豪门大族面对其正直耿介的为官作风,纷纷有所收敛。作为专职的监察官员,高道悦很快便履行了皇帝赋予的职责,志文载:“荆扬未宾,豹尾路,星遣飞,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阅集洛阳。而兵使褰违,稽犯军律,宪省机要,理膺绳究。”“荆扬”指以荆州、扬州为代表的广大南方地区,“未宾”意为未宾从于北魏,故有后来的“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阅集洛阳”之事。孝文帝曾多次南征,此次南下,征兵于“秦雍”之地,即指西安附近地区,秋季集结兵力于洛阳,而有两人并未按期执行朝廷命令,高道悦上疏奏明他们的罪过。此事在《魏书》中也有记载,曰:“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14]1400由此可知,被弹劾者为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二人一为孝文帝赏识之才,一为北魏宗室,特别是薛聪,深得皇帝信任,孝文帝曾言:“朕见薛聪,不能不惮,何况诸人也?”[16]而后,高道悦又禁劾尚书仆射、任城王元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以及尚书左丞(志文载为尚书右丞,应以《魏书》为是)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14]1400。
以上所载二事迹皆载于《魏书》《北史》之中。综上所见,高道悦所奏劾之官员或是皇亲国戚之贵,或是肱骨心腹之臣,足以表现出其耿直无私、不畏权贵的一面。此外通过上述事件也可以窥见志主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这也最终导致了高道悦悲剧的发生。
通过一系列尽职尽责的监察工作,尤其是薛聪、元澄二人的弹劾事件,高道悦深受孝文皇帝信任,并且很快擢为谏议大夫,志文中称其“献纳风规,朝野耸听”应该不为过也。
志文载:“高祖孝文皇帝深相知体,雅见器爱,临轩称叹,形于诏牍。”此句并非只是过甚其辞,而是有史料佐证。《魏书》载:“诏曰:‘道悦资性忠笃,禀操贞亮,居法树平肃之规,处谏著必犯之节,王公惮其风鲠,朕实嘉其一至,謇谔之诚,何愧黯鲍也。其以为主爵下大夫,谏议如故。’”[14]1400也就是在此诏之后不久,志主被擢为御史中尉。而志文中前一句:“虽二鲍之匡汉朝,两傅之谐晋室,无以过也”,明显也出自此诏。“二鲍”指东汉时期的鲍恢、鲍永,“两傅”指西晋傅玄、傅咸,所举四人皆为刚正不阿、直言善谏之名人。之所以志文中敢于将高道悦与此四人比肩而论,应该是源于孝文帝诏书。
《魏书·高道悦传》记载,迁都洛阳后,高祖欲走水路巡幸邺城,因此将准备在洛京建造基础设施的木材挪用来建造舟楫,高道悦闻后,慷慨陈词,指责了皇帝的行为,主要劝谏有以下三点:其一,“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其二,“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义。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其三,“又从驾群僚,听将妻累,舟楫之间,更无限隔,士女杂乱,内外不分。”而后,又以内忧外患加以鞭策,晓之以大义,最后曰:“臣禀性愚直,知而无隐,区区丹志,冒昧以闻。”[14]1401孝文帝闻后深以为然,下诏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称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于是,高祖遂从陆路。转道悦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俨然难犯,宫官上下,咸畏惮之。”[14]1401由此可知,高道悦深得皇帝信任,而且由御史中尉升为太子中庶子似乎也与直谏之事有关。此事在《魏书》《北史》中皆占有较大篇幅,而志文中却只字未提,不知是何缘故。
3.“东宫事变”考
高道悦被擢为太子中庶子后,成为东宫重臣,然而此次晋升却为其“暴丧于金墉宫”埋下了伏笔。
志文载:“但河阳失图,潜怀不轨。”“河阳”指河阳县(今属河南孟州市),“东宫事变”后太子元恂被废,囚禁于河阳县,死后亦埋葬于此地,志文中不便用其姓名,故以河阳代之。
志文又载:“追纂楚商,连规宋劭,拔剑吐心,邀同枭镜。”“楚商”应指战国时期楚国太子商臣,商臣为太子时发动兵变,其父楚成王被迫自杀,商臣继位为楚国国君,即楚穆王。“枭镜”亦做“枭獍”,传说枭为一种鸟,生而食母,獍为一种野兽,生而食父,因此常用来比喻对父母忘恩负义之人。此句对太子谋反之事只字未提,但是“楚商”“枭镜”等词语的使用,已经能够知晓其大概,而后一句的紧密承接,进一步描述了此事件,曰:“君厉声作色,抗其凶计,既殊潘崇飨芈之谋,遂同阳原头风之祸。”潘崇为春秋时期楚国大臣,曾帮助太子商臣夺得楚国王位。关于“飨芈”二字,秦公先生的《释北魏高道悦墓志》[1]、赵超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17]以及韩理洲先生的《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18]中皆将其录为“飨羊”,而赖非先生则录为“飨芋”[2]253。今有论者认为此字为“芈”[19],此种说法源自《左传》:“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问而勿敬也。’从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6]339潘崇谋划太子宴请江芈,并在宴会上故意激怒她,而得知废太子之事为实。很明显,志文中的“潘崇飨芈之谋”应与《左传》所载“享江芈问而勿敬也”为同一事件,因此我认为此字应为“芈”字无误。而后一句“阳原头风之祸”,按照文章格式,很明显是对应前一句,但遍查史书却找不到相关典故,故不知其所言。
“东宫事变”在《魏书》与《北史》[20]中皆有记载。《魏书》载:“太和二十年秋,车驾幸中岳,诏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潜谋还代,忿道悦前后规谏,遂于禁中杀之。”[14]1401《魏书·元恂传》中记载更为详细,曰:“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21]《资治通鉴》亦载:“魏太子恂不好学;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魏主赐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辽东高道悦数切谏,恂恶之。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奔平城,手刃道悦于禁中。”[22]总观《魏书》《北史》以及《资治通鉴》对与此事的记载,可以总结为两点:
其一,高道悦为太子中庶子时对太子元恂的生活、学习、思想以及日常的着装都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并对其不当之处屡次规谏,对于年仅13岁的太子来说,心存怨恨也是情理之中。
其二,元恂趁孝文帝巡幸嵩山之际,与左右密谋返回北方,而身为中庶子的高道悦定会加以阻拦,故杀高道悦。
虽然三部史书记载大体相同,但都未说明元恂为何要对高道悦痛下杀手,对于年仅13岁的太子来说,为了返回北方而亲手杀死大臣,是否值得?如想返代地,牧马轻骑回北方即可,为何要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而事实证明元恂也因此而丢掉太子之位。由此推测,史书关于此事的记载并不完全,而高道悦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其墓志内容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志文中连续使用如“潜怀不轨”“拔剑吐心”“邀同枭镜”等词语以形容元恂行为之恶劣,“潘崇飨芈之谋”一句更是一语道破了整个事件的关键,还原了元恂集团欲效仿楚穆王发动兵变杀父夺权的历史事实。高道悦作为太子中庶子则“厉声作色”“抗其凶计”,以至于惨遭杀害。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断,高道悦之死并非因劝阻元恂归代,而是因得知其意欲谋反的消息后与元恂及其左右进行了抗争,甚至可能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元恂恐事情败露才杀高氏于金墉宫。这种推测更合乎逻辑,故应以墓志为是。正是此次事件的发生,使得太子元恂被废,并于太和二十一年(497)被赐死,时年15岁。
4.高道悦及其家族墓地
高道悦死后,受到了皇帝特殊的礼遇,“赠散骑常侍,带营州刺史,赐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诏使者监护丧事,葬于旧茔,谥曰贞侯”[14]1401。志文详细记载了高道悦所葬之地,载:“以其年秋九月迁葬冀州勃海郡县之西南,以为定窀。但旧葬下湿,无可重厝,因此凶际,迁葬于王莽河东岸之平岗。神龟二年岁次己亥,春二月辛亥朔廿日庚午,穸于崇仁乡孝义里。”由此可知,高道悦死后先葬于县之西南,因地势低洼潮湿导致墓穴积水,才又迁葬于王莽河东岸的崇仁乡孝义里的平原之上。此志文明确记载了高道悦葬于王莽河东岸,而与其合葬的高道悦夫人李氏墓志则载“今山停水,改卜漳东”[23],这样看来王莽河与漳河应指同一条河流。众所周知,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后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又使用了白沟的河道。如果推测正确,今德州段运河即为古王莽河故河,后因漳河水注入,才使得高道悦夫人墓志的志文中使用“漳东”的概念。而此墓志的实际出土地正是今大运河德州段东岸,可佐证以上推论。另外,高氏一族继高道悦后满门朱紫,高氏家族其他成员墓葬应分布在高道悦墓穴周围,今后此地可能会有高氏其他成员墓葬出土。
高道悦死于太和二十年(496),而墓志刊刻于神龟二年(519),之所以相隔23年,是因为其夫人李氏于神龟元年(518)辞世,次年与高道悦合葬。时因“昔太和之世,圹内有记无铭,今恐川垄翻移,美声湮灭,是以追述徽猷,晰壤阴”,可知原高道悦墓葬中仅瘗有记载其事迹的文章,但并未勒石,此次借与李夫人合葬之机“因此动际,追立志序,即镌之于上,盖取父天母地之议,故不别造铭石耳”[23]。据此,高道悦墓志与其夫人李氏墓志并非分别放置,而是高道悦志石在上,其夫人李氏志石在下,此种两志二石为一合的情况,还未见有别例。
三、结 语
北魏孝文帝时期,有两件大事,其一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以及迁都洛阳,其二是宫廷内部围绕立储问题的勾心斗角。其中就有论者认为高道悦与北魏后族冯氏关系密切。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墓志志阴载其“祖育,燕大司马从事中郎”,可知高道悦祖上便任职于北燕冯氏政权。北魏太延二年(436)北燕被拓跋焘所灭,北燕皇族女冯氏被北魏文成帝选入后宫,并于太安二年(456)立为皇后,她便是北魏著名的冯太后,其兄冯熙在朝中身居高位,孝文帝两任皇后皆为冯熙之女,可见这一时期冯氏势力之大。高氏家族作为北燕旧臣与冯氏家族保持密切的关系是符合逻辑的。不管怎样说,元恂及其左右势力意欲谋反是高道悦死于非命的直接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保守派与改革派、元恂派与元恪派的明争暗斗,而高道悦之死也确实达到了立元恪废元恂的目的,这也许是元恪继位后“追录忠概,拜(高道悦)长子显族给事中”[14]1401的原因。在几股势力面前,正直、耿介的高道悦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最前线,成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1]秦公.释北魏高道悦墓志[J].文物,1979(9).
[2]赖非.高道悦墓志[M]//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
[3]赖非.北魏高道悦墓地调查及其墓志补释[G]//李开玲,马长军.德州考古文集.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2000:1—7.
[4]魏收.魏书:卷一百六上:地形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95.
[5]海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海城县志[M].海城:海城市印刷厂,1987:74.
[6]李梦生.左传译注:襄公二十九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213.
[8]郑天挺,等.中国历史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521.
[9]金毓黻.东北通史[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129—131.
[10]房玄龄.晋书:卷十四: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427.
[11]陶元珍.辽东公孙氏事迹杂考[EB/OL].(2006-7-18)[2017-12-5]http://www.taosl.net/tao/ys20.html.
[12]张国庆.西晋至南北朝时期“护东夷校尉”初探[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3).
[13]范兆飞,房奕.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2009(3).
[14]魏收.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李延寿.北史:卷四十:高道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67.
[16]李延寿.北史:卷三十六:薛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33.
[17]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04.
[18]韩理洲,等.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150
[19]至元书院.校碑一则:潘崇飨芈[EB/OL].(2012-1-11)[2017-6-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265f4d0100 zhvi.html.
[20]李延寿.北史:卷十九:元恂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713.
[21]魏收.魏书:卷二十二:废太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588.
[2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明帝建武三年[M].北京:中华书局,1976:4400.
[23]吕宏伟.被忽略的李夫人:北魏高道悦夫人墓志考[N].中国文物报,2017—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