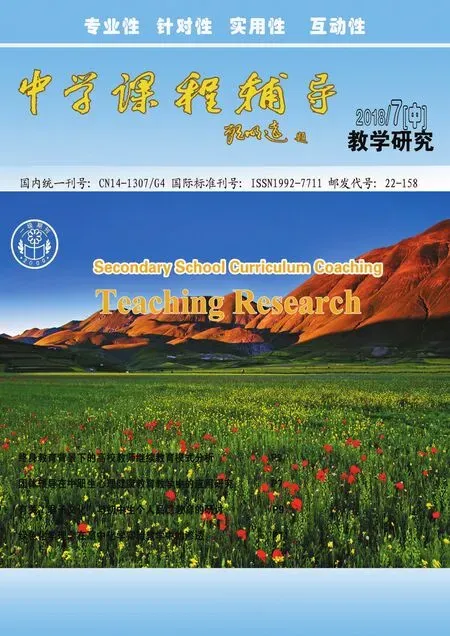论鲁迅的梦意识
◎王虹
一、导论
中国文人对梦有着情有独钟似的渊源,文人与梦文化也成为中国少有的文化现象。中国文人与“梦”文化这个话题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不管读者承认与否,至少中国文化现象一直存在着,只是需要我们细心察觉罢了。这可以追溯到庄周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梦与现实的浑然相交。说到底这其实是人性潜意识中对自由的向往,想如蝴蝶般自由而飞。因为梦境中是自由的,而真正的现实里是极其不自由。诗人、文学从业者对梦情有独钟,甚至认为“文学就是作家的白日梦"。对人生对社会越是看透看穿的人,就越有梦的意识,而后文人也要做起梦来,但梦千姿百态,苦乐掺杂。唐代飘逸的李白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在梦境中追求着非现实的美好神仙世界。就连《浮生六记》之题名,也出自于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杜牧也在梦中醒悟,“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这是他扬州梦醒之后的忏悔。宋代文人苏东坡更有着梦意识,看透人生的旷达之态,“事如春梦了无痕”,悲喜人生转瞬即逝。更喊道“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明末戏剧家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而《牡丹亭》亦为《还魂梦》,里面的“惊梦”一篇更是情之所至。清代曹雪芹之《红楼梦》,真是“一曲红楼多少梦,情天情海幻情深”,寄寓着作者之梦的生成至幻灭的过程!悲剧之源归之于不可知的命运,到头来只剩下仅有的梦幻感——“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到了近代,同样对人生有着独特看法的鲁迅,更流淌着梦意识的血,借助梦,借助诗,追求自己的灵魂自由之路,因为梦与诗是自由的最高圣地。《野草》就是两者的融合,所以在此探究鲁迅的梦意识,可以更进一步理解文人与梦的文化现象。借助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浅析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可以知道背后某些原因,而探寻鲁迅梦意识在各时期的表现,可以看到不同时期鲁迅思想的变化。以梦文本《野草》为蓝本,可以洞悉鲁迅内心不为人知的潜意识。最后在结语中,试着探究鲁迅梦意识中关于死亡、虚无意识的思想来源,可以初步了解到这与他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甚为相关,这也是他与古代文人不同的地方,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伟大也要人懂。
二、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之前要探讨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呢?与后文有什么联系吗?我在此做一个简单的解答。要想深入明白文人爱借助梦去回避清醒状态下的现实生活,不管是古代的诗人,还是现代作家(尤其是鲁迅先生),都无一例外地希望“做梦”。此时就需要明白做梦的人其实是从清醒的世界中解脱出来,这也是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的一种说法。布达赫对这两者关系,做了如下描述:“梦的目的旨在使我们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甚至当我们的整个心灵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情时,当我们悲痛欲绝或竭尽全力要解决一些问题时,梦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进入我们的心境中,以象征来再现现实。”[1]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相反的,两者关系是密切相连的。莫里用简洁的语句说:“我们的梦实为我们所见、所说、所欲和所为。”[1]。
我个人觉得两种关于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的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阐释吧。第一种解脱说,旨在从“做梦者”内心的真实思想出发,不满清醒时的痛苦,需要借助梦来暂得解脱,其实我们古代许多文人就属于此类。第二种相连说是从理论梦的来源来阐释两者关系,不管我们做梦者“梦”见什么,都从不会脱离现实世界,“梦的最崇高的和最荒谬的结构总是必定从我们目睹的感性世界或在我们清醒思想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处获取基本素材”[1],而鲁迅先生就是目睹现实,“绝望”于现实,于是就寄寓于“梦”,表达自己内心的痛感,想解脱但无法如古人出仕入仕那样来去自如。当然,梦境是虚幻的,作者只能借用梦境用一种自我矛盾的思想来继续向前“走”着,在绝望与希望,梦境与现实,虚无与实有等彷徨前进着。梦境是虚幻尚可以逃出,如果梦境竟然是现实,那将如何逃出这现实的梦境呢?其实鲁迅先生以退为进,让我们明白梦境所反映的不是更深一层反映这个世界吗?他从做梦到梦醒,经历过太多的痛,尤其是梦醒之后,有孤独、寂寞、虚无之感,但无人知晓。“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贯穿古与今。
三、早期鲁迅与梦意识
正如《呐喊·自序》中他提到自己年青时也曾做许多的过梦,而最早梦大概要数医学梦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2]。后走着弃医从文的路,梦的内涵变成“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这个梦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倾尽了所有的精力,鲁迅这一时期写下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在翻译上与其弟周作人合译汇编了《域外小说集》。并极力筹办杂志《新生》(未开始就已注定失败的命运),在《呐喊·自序》提到过“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2]。
在早期鲁迅个性主义思想形成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尼采。刘半农说鲁迅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比鲁迅更熟悉、酷爱尼采的了。他在日本早就接触到尼采的相关学说,尼采的唯意志论的超人学说深深影响到了鲁迅,它是西方较早的生命哲学,即人的生命主题。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使得人们对传统思想与文化及其现有的价值观有了怀疑。鲁迅受尼采的影响,主要就是这种反传统的个性主义思想,在早期才会有鲁迅整体性反传统的思想体系,所以鲁迅当时非常重视精神力量,重视个人,反感“群治”。正是借助尼采,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缺乏个性的现实和人的个性被文化所吞灭的悲剧。对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浪漫英雄,鲁迅心底是充满了向往(虽然愿望未如愿)。这种个性主义倾向也直接投射到了他的《野草》,他一再强调并不希望青年读他的《野草》,因为这是他的独语,也是独自面对内心及灵魂深处的个人空间。并借助“梦”的形式,似梦非梦的将他潜意识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给读者造成的一个“陌生世界”,也让许多所谓的“诠释者”云里雾里,更何况是一般性读者呢!梦本来就是难解的,不管是中国古有的周公解梦,还是近代西方学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都难以让所有人信服。“作家笔下虚构的梦也是在象征性的代替物的伪装下,再现作家们的想法”[1],鲁迅亦是。梦是有隐匿含义的,做梦是用来代替思想的某种其他过程,我们只有正确地揭示出代替物的象征意义,才能发现做梦者的思想。可是做梦者潜意识中也存在思想的矛盾性,连自己都难以把握,“所说”与“所想”的不一致性,导致梦有片段以至于破碎。鲁迅自己就有一篇杂文《听说梦》提到“说梦”的不自由,“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说梦,就难免说谎”[3]。“因为醒着做的梦,所有不免有些不真。”[3]。所以鲁迅“所说”与“所想”有时是矛盾不一致的,存有“紧张”感,在《野草》中《题辞》写到: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4]。所以我们看鲁迅的梦意识,要辩证地去分析,不能全信表面意义的绝望、希望,要结合鲁迅所有作品来诠释背后真正的含义,尤其是后文要探究的梦文本《野草》。
四、梦醒之后的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认为可惜。[2]”这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的鲁迅已不是青年时的“做梦者”了,而是梦醒之后的“看梦者”,他内心充满着痛苦与绝望,剩下的也只有自己的孤独与寂寞。孤独正如《孤独者》中典型的鲁迅意象之孤独哀伤的孤狼——“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而寂寞之感“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道出了他的人生痛感,“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3],接着又写到李贺死前对母亲的说诳—“阿妈,上帝造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2]。
鲁迅自己深知梦醒后的痛苦,所以才极力反对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叫醒他。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寓言”里,傻子要拯救奴才,则将被奴才排斥,为了不遭到排斥,为了拯救奴才,傻子除了不再当傻子而变成聪明人之外别无他法。聪明人能够拯救奴才,但这只是让奴才在主观上感到得救。就是说,不去叫醒奴才,让他做梦,换言之不予拯救才是对奴才的拯救。这或许潜意识表达了鲁迅所具有的“绝望”的意味。作为一个梦醒之后的“看梦者”,他把对现实的绝望寄寓与“梦”,在《野草》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他的“梦”意识,此后我会详细探究。
在此之前,我们先谈谈他的绝望,鲁迅的绝望,我认为更多的是自我执著的自我否定式的内省,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社会陋习的批判。《新生》的破产,给他从事文学的雄心泼了一瓢冷水,他渐渐如梦初醒,反省自己并不是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初次尝到了的失落的滋味,这为他后来绝望的构建提供了一块砖石。后来的生活阅历中,他的绝望使自己拒绝成为自己,否定自我,同时也拒绝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以至于到达虚妄。但他的绝望真正是我们所理解的绝望吗?我认为不然,这种态度其实与他笔下嵇康阮籍等人在对待“礼教”的“毁坏”异曲同工——“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用,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5]。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期间,一度绝望,他时常感到异常的寂寞与无聊,他抄古碑之“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意思”,也可以看出他的某些绝望,纵观文学史,他的这种绝望或许正真成就了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伟绩,这便是是林语堂所谓的他的第一回蛰伏时期。直到1918年,他在“绝望”之际,他应友人钱玄同之邀创作最初的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以上可以看出鲁迅的绝望是自我人生痛感的恢复和知识分子的自觉,他在自我否定中重生,他也终究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就只得归之一句“绝望之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充实的人生,固然伴有深切的满足之感,但也伴有深切的苦痛之感,人对于苦痛经验的深浅,乃表示他生命力充实的程度。纵观现代文学家与当代文学家的作品之别也存在于各自在对苦痛体验的挖掘深度之别。所以鲁迅式的现代作家也因此难以超越。鲁迅也曾将自己的苦痛寄希望于梦醒之后痛感的减弱甚至消失(但往往事与愿违,梦醒之后更痛),希望一切不幸都只是一场梦,潜意识也将这思想埋进了他作品中。在他笔下悲惨命运人物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单四嫂子不愿接受她儿子宝儿死去这个不幸的事实,所以“她心里计算:不过是梦罢了,这些事情都是梦。明天醒过来,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宝儿也好好睡在自己身边。他也醒过来,叫一声“妈”,生龙活虎似的跳去玩了”[2]。
总之鲁迅不愿意将自己为苦的寂寞,传染给也正如他年青时候似的正做梦的青年。所以他在应钱玄同之邀之前说出了一段惊人的话语——“铁屋子比喻”。正如文章中写到“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2](《呐喊·自序》),但从最后鲁迅答应写文章,可以看出这种“绝望”不同的内涵,他说“虽有自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有”。在《野草》中《希望》一篇中,鲁迅最喜欢的是裴多菲写过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但鲁迅意识中真正超越了绝望与虚无的就是一个字——“走”,在《故乡》的末段这样写到“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唯独以走的姿态告诉正如他彷徨着的青年们,也以此自慰。此外鲁迅很反感所谓“导师们”自以为的路,“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所以我想,与其找糊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3]。关于“走”的话题鲁迅在《野草》戏剧性对话《过客》中那位“过客”不是一直一直往前走吗?即使那位老人告诉“过客”前面是坟,“我还是走好罢”这就是“过客”的答语,也是鲁迅的回答[4]。这也是《野草》中鲁迅“梦”意识中的一小点。
五、梦文本之《野草》
“梦”意识是《野草》中鲁迅表达的比较明显的意识,从《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死后》连续七篇文本作者都以“梦境’’开始,加上与梦具有相同朦胧情景的《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腊叶》,梦的分量可见一斑。梦与夜紧紧相连,他喜欢夜,还特地写了一篇《夜颂》。“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人在黑暗中的本真的存在,人剥离了白日的种种面具,卸下各种身份的装点,也告别了众生喧哗,开始真实的面对自己,指向内心。大体上,鲁迅的小说(特别是《呐喊》、《彷徨》)和杂文,是“为他人”写的。而他的《野草》就是“为自己”写的。如小说的“听将令”,杂文的“让正人君子不舒服”[3]。
纵观文本可以看出,越触摸到鲁迅自己的内心,就时常可以在他文本中看到他的“梦”意识,尤其在《野草》中最为明显。而梦的内涵很复杂,不遵循现实逻辑原则,没有清晰的时空感念,没有世俗打扰的自由空间,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潜意识纯粹的精神空间”[6]。
鲁迅关于死亡的思考是他意识中常有的话题之一,在《野草》中有《墓碣文》、《立论》、《死后》集中阐释了鲁迅关于“死”的哲学思考。《立论》并非我们所看到的对中庸思想的批判那么简单,在梦文本中作者借助“我梦见”的作文课教立论的方法的故事,从一个人的出生就看到了必然的终点——“死”,但这虽是事实,但我们不能讲出真话。“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出真实,得到的就是挨打的下场,这是鲁迅不愿看到的,所以他很想“我愿意既不慌人,也不遭打“,当向“老师”提出该怎么说时,但文中的“老师”也没有给出解决之道,只是“啊呀”“哈哈”。鲁迅对于“人之死亡”的必然这一事实,大声得讲出来了,不管愿意承认与否。这正是鲁迅看清人生的一个写照,但要国人都去正视,那又是几乎不可能,这又涉及到鲁迅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论睁了眼》中谈及“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3]。此外《立论》境况中也涉及到鲁迅文本主题之一呼唤“真的人”,有真的人,才会有真的声音,才能宣示自我的存在。但梦文本却出现了不可更易的现实异己力量,不允许道出“死亡”真实人生的声音,否则要遭打。所以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道路很难,就如鲁迅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3]。这就是鲁迅悲苦人生的体味和感受。
梦文本《死后》集中体现了鲁迅关于“死”的体知和思考,文本的画面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梦境,“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而后就是“死后”的种种奇遇和异想。第一个场景就是“我”(陈尸)被路人围观,被蚂蚁青蝇舔舐。“我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找做论的材料……”,鲁迅最厌烦不堪的就是人死了还依然被人利用,被作为饭后闲谈的材料,他自己就异想自己也脱不了“死后”被人利用被人控制被人宰割的可怕命运。梦境中“死后”非人的情景不过是鲁迅对生前遭遇象征性地传递。尤其是高长虹之流对鲁迅的伤害,让鲁迅对于青年的幻想破灭。“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向来是不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7](《两地书·七九》)。文中传递出的被利用被打击被诋毁的感觉和遭遇让鲁迅对“生”与“死”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更加深了他的人生虚无之感,“先觉者”(包括鲁迅自己)的死亡变成了看客的材料。也使鲁迅对于自己“活的人生”之路有了重新的定位与调整,这也正是鲁迅梦醒之后又一写照。其实整部《野草》不过是借助梦意识,对自己身处现实中心境的解剖,并重新认识自己,抛弃“旧我”,努力去找到自己存在的现实位置,就这样一直前“走”着。
梦文本《影的告别》是鲁迅梦意识中黑暗虚无之感的写照。鲁迅曾经在与许广平通信的《两地书·四》中解剖自己:“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7]”该篇《影的告别》就是一种黑暗体验,被黑暗沉没,但又独自承担黑暗,反抗黑暗。“影”要告别“行”,首先得明白这两者的代表意义,“影”无疑代表着觉醒的自我(鲁迅内心的另一个自己),而“行”更多的是现实中自我,即觉醒前的自我。所以从题目《影的告别》,就可以看出这是鲁迅从失落、死亡到新生的自我调整,是自我的一次觉醒。而这过程是伴随着自我牺牲的,正如文本末尾提到“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同时“影“的觉醒也是逐步完成的,开始时不满拘圉于现实的“行”,所以毅然决然要告别,同时也拒绝一切既往和未来,道出了十二个“不”字,天堂、地狱、未来的黄金世界,“影”都不愿意去,正如《过客》中那位过客一样拒绝走回头路,继续向前“走”。但“影”在梦醒后依然面临着“无路可走”的困境,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这就是鲁迅“人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体知与彷徨。接着,“影”不愿这样痛苦地彷徨,所以主动承担黑暗,“我不愿意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沉没”无疑是一种“死亡”,这就是鲁迅个人主义中自我牺牲的悲剧角色的担当。但这种自我生命必将死亡中,明白了现实异己力量的强大,剩下只有一种虚无。所以“影”赠给“行”的赠品中,“我能献给你什么呢?无已,则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影”不愿意“行”在梦醒之后感到虚无黑暗的痛苦,“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这就是鲁迅两个自己的争斗,简单地说就是鲁迅自我思想的矛盾。最终,“影”决定独自承担一切痛苦,“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这就是鲁迅提倡的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路之前不要轻易叫醒“做梦的人”。
六、结语
鲁迅一生在梦之国里曾希望着,但绝望着,最终也只有孤独着。我想用一段席勒在《新世纪的开始》中的一段话来概括鲁迅一生的梦意识,“你不得不逃避人生的煎逼,遁入你心中的静寂的圣所,只有在梦之园里才有自由,只有在诗中才有美的花朵[8]”。我觉得这段对于鲁迅而言最适合不过了。在此也可以看出文人总爱在梦中或诗中寻在那片现实无法找寻的自由。而鲁迅自身对于生命死亡的思考以及常自叹的虚无绝望的意识,都是借助梦的形式展开的,而要深究其思想来源,除了外部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原因外,我认为鲁迅所受的西方所特有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明显的助推作用。我们对西方浪漫主义可以简单概括为对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即对于有限的生命到哪里去寻找现世的皈依的问题,甚至已经感受到人的虚无。这也是20世纪的浪漫精神深切关注的问题,东方伟人鲁迅做了一系列相关的思考,同时也带上的绝望虚无的时代烙印(文人郁达夫亦然)。这都是浪漫主义在东西方不断蔓延开来的必然结果。文人们从人性的角度解读人骨子里都有追求自由的天性,但这种自由是无法到达的,因为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死亡。席勒在《论崇高》中也提到:“这一例外(死亡)足以整个摧毁我们的本性的理想……人如果处于这样一种煎迫和束缚下,他引以自豪的自由也不过等于虚无[8]”。鲁迅一生中思考死亡也抱着某种虚无主义,可以看出这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消极人生观,而正是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只是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坟。[9]”。从席勒那段话中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鲁迅一直叹到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我觉得人有有限的生命,而自由需要无限来衡量,“人无法到达无限,无法猜透人由之而来的虚无和自己被湮没于其中的无限之谜。”[8]鲁迅梦意识中所有的思考都给予我们人生某种启示,无怪乎说梦文本《野草》是鲁迅一生全部的哲学思考,是其绝望中生死追问的过程,是穿越绝望的生命行动。“伟大也要人懂”这是鲁迅对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说的一句话,我想说这句话也同样适合鲁迅自己。所以无论古今中外,伟人总是孤独的,他需要灵魂间的沟通与理解,这在理性、科学之上的时代是无法达到的。最后我想说,作为青年的我们,不要一味去追求外在的东西,包括我们认为至高的外在世间的知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逐渐被证实。因为人们对外在的关注过多,那对于自己的内在,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归宿就知道的越少,这必然会造成人的空虚与无聊。一个不知道灵魂何处安放的人,再有多少外在的知识,也是枉然。鲁迅在写在《坟》后面写到:“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9]”我也才渐渐理解鲁迅要中国青年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真正内涵。
对鲁迅梦意识的种种探究,让我们懂得这样一句话——“伟大也要人懂”。在中国漫漫历史进程中,做梦者甚多,醒来的少之,醒之如庄子、东坡、曹雪芹、鲁迅者又更少之又少。幸好有他们醒着,承担着多数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才使得中国文化没有睡去。就正如王富仁称鲁迅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10]一样,必定有着守夜人的价值[10],但我更感觉到鲁迅“梦醒”之后无法言说的痛。研究鲁迅的梦意识,虽说梦的虚妄,但这恰恰是更好触摸鲁迅内心的实有。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著.梦的解析[M].国际文化出版社,2001.2,7-11.
[2]鲁迅.鲁迅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4,11-25.
[3]鲁迅.鲁迅全集杂文[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0,250-407.
[4]鲁迅.野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9,3-43.
[5]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89-95.
[6]陈立波.鲁迅散文诗《自言自语》、《野草》研究[D].2010.5.
[7]鲁迅.两地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5-49.
[8]刘小枫.诗化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9.23-39.
[9]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56-60.
[10]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