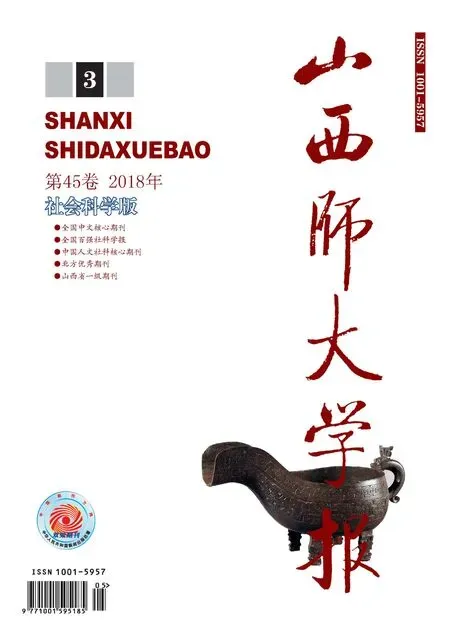王船山文质论范式下的人性建构
田 丰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武汉 430063)
不少学者指出,如果说西方思想传统的经典范式是形质论的话,中国思想则可称为文质论范式。在形质论传统中“质料总是低于形式,形质论的实质,在于以技艺制作的模式来理解一切自然的和人为的事物。文质论却并非如此。《白虎通》云:‘事莫不先有质性,后乃有文章也。’‘文’取相于质实自然上的纹理,所以不能脱离质实自然而存在。……质不是永远被动的,文也不是永远主动的。……文并不绝对地高于质,质也不是绝对地优于文”[1]197。需要注意的是,文质这对概念本身也在不断流变,有时也会在中国式的形而上学建构中呈现出某些类似西方形质论的特点。譬如,在程朱理学的讨论中,“气”与“质”常常共同使用,并与“理”(原义即是文理)相对。不过因为“气”这个概念获得了非常实在的宇宙构成本源意义,“质”的义涵也相应地退居到现实物体层面。“文”这个概念由原本事物的自然文理也获得了形而上学实体意义,成为颇具独立性的“理”。尽管如朱子人跨马的譬喻,运动与生成的力量源自“气”,但“理”却更具有优先性,这种优先性既表现在它恒常不变同时为人伦奠基,也表现在它某种程度地存在独立性——在朱子学架构中“理”是否能够独立于“气”而存在尚有争议,但其规定性与约束性必然具有超乎“气”之上的独立地位。随着明中叶以降“气学”与“实学”的复兴,“气”具有了越来越根本性的结构功能,很多特点呈现出向先秦文质论范式的回归,不过衍生出了更加精细的结构。本文试图以王船山思想为例,讨论他的“气—质—理(性)”结构对其“性日生日成”学说的意义,并以此呈现文质论范式的特点。
一、“性日生日成”说的困难
王船山“性日生日成”学说是其相当重要的原发性思想,前人研究颇多,但是对此学说的核心概念“气质中之性”的论述,则或有误解,或语焉不详。在讨论“气质中之性”之前,还需要先对其“性日生日成”思想的困难做一番检讨,才能理解“气质中之性”命题在船山性论中的结构性意义。
就宋明道学的传统性论来说,人初生之顷既有“气质之性”又有“天地之性”,学者通过后天之学能够变化的只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可能被私欲遮蔽,可以通过后天工夫去蔽让它重新呈现,却不能说它会变化。人每日新陈代谢与天地交流,只能说是气日生日成,不能说理日生日成,不变的天理落在人身上所成的“天地之性”保证了人向善的可能性基础。船山强调气先于理,理随势变,所以“性”在他这里有一个常见的用法,即合理气二者的“整全之性”。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任何个体就其自身当下而言是整全之体,同时又与其他事物不同,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包含理气二者。气因聚成形,气在一隅之流行必然呈现有文理,合理气而言有“整全之性”:“合理与气,有性之名”。*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5孟子5尽心上5四》,载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此外,对此“整全之性”的讨论可参看陈祺助的《“喜怒哀乐未发”或“仁义礼知未发”》,载鹅湖月刊第三十二卷第五期总号第三七七。此义落在心性论即为“性日生日成”之说。然而,若是没有不变的“天理”作为根基,则此说容易泛滥无归而成支离虚无之学。船山在其《尚书引义·太甲·二》中论述“习与性成”的时候,似乎尚未明确意识到这个论点可能带来的逻辑后果。一方面船山承认初生之时,天有命于人:
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日忘也。[2]300
如果没有初生所命之性,仁义礼智便没有其在人性中的内在根基;而幼少壮老的过程中天不断更有所命,以使仁义礼智之性不会被磨灭遗忘。这也即是说,船山还是承认宋明道学的基本前提,即天命于人之性包含仁义礼智,至少包含其根基或种子。
另一方面船山在论证“性日生日成”的时候,强调天始终命于人,性始终在生成变化:
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岂非天哉?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惟命之不穷也而靡常,故性屡移而异。抑惟理之本正也而无固有之疵,故善来复而无难。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侧,不受损益也哉?[2]300
人何以能够在变化中择善固执呢?这里船山将理由归于“理之本正”,这似乎是说最终还是要依凭一个先天之正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性日生日成”之说便又回到了道学传统的先天之性上去,只不过换了些概念和说法而已。不过,这显然不是船山的真正意图,所以他在两年之后的《读四书大全说·告子上·一八》中,借助于孟子“夜气”之说重新讨论了生性说同理气的关系问题:
雨露者,天不为山木而有,而山木受之以生者也;则岂不与天之有阴阳、五行,而人受之为健顺、五常之性者同哉!在天降之为雨露,在木受之为萌蘖;在天命之为健顺之气,在人受之为仁义之心。而今之雨露,非昨之雨露;则今日平旦之气,非昨者平旦之气,亦明矣。到旦昼牿亡后,便将夙昔所受之良心都丧失了。若但伏而不显,则不得谓之亡。且其复也,非有省察克念之功以寻绎其故,但因物欲稍间,而夜气之清明不知其所自生。若此者,岂非天之日命而人之日生其性乎?[3]1077
此段大义甚明,乃是说夜气滋养人如同雨露滋养山木,都是日复一日未有间断的,以此论证日生其性。但这里有个类比值得玩味,即说天降雨露木生萌蘖,这是木之生性;在人则天命为健顺之气,在人受之为仁义之心,此为人之生性。这个类比完全不同于宋明道学的一般讲法,惯常的观念会认为,健顺之气与仁义之心都属于气而不是理或性。即便说此仁义之心乃是类似于朱子思想体系下的存仁义之性统性情的心,那么无论是否有夜气滋养,于人的仁义之性并无生成助益,最多可以理解为夜气清明使得人的本然之性更加容易崭露。深谙道学的船山自然清楚这个表述会引起的批评,所以他代质疑者设问并自问自答:
乃或曰,气非性也,夜气非即仁义之心,乃仁义之所存也,则将疑日生者气耳,而性则在有生之初。乃或曰,夫性即理也,理者理乎气而为气之理也,是岂于气之外别有一理以游行于气中者乎?夫言夜气非即良心而为良心之所存,犹言气非即理,气以成形而理具也。岂气居于表以为郛郭,而良心来去以之为宅耶?故朱子说“夜气不曾耗散,所以养得那良心”,以一“养”字代“存”字。只此天所与人清明之气,健顺故清明。养成而发见到好恶上不乖戾,即是良心,而非气外别有心生,审矣。[3]1077
这个设问表明船山现在已经意识到其性日生之说与道学传统的关键分歧所在。船山在讨论大多数道学心性论问题的时候,还是尊重概念传统,在“理”的意义上使用“性”这个概念。船山说明,他所说的“理”不是一个穿梭游行于不同的气之中的外在之理,而必须是气之理。如果说夜气不等于良心,而仅仅是存放良心的场所,那么岂不是说气仅仅构成一个外在的容器,良心可以来去或盛放在此容器中么?这必然将导致张载曾经批评过的体用殊绝之论。所以船山强调“养”而非“存”,“存”即是某种现成本体的存放或者回复,“养”则是不断生生不息地成长。船山夜气之论的目的在于说明,气无不善,天地之气于平旦之时清明而与人相接,便能使其健顺之性感化于人生成仁义之性。[4]300所以船山说:
若云唯有生之初天一命人以为性,有生以后唯食天之气而无复命焉,则良心既放之后,如家世所藏之宝已为盗窃,苟不寻求,终不自获;乃胡为牿亡之人非有困心衡虑反求故物之功,而但一夜之顷,物欲不接,即此天气之为生理者,能以存夫仁义之心哉?[3]1079
这也是气论的必然推论:既然日受天之气,则必然也日受天之理,这样,仁义之性就不是人初生之际的一次性赋予者,而是始终不断化入人的生理。但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我们依然可以问,鸟兽草木都能够禀受天之日日化生,则人之性何以异于犬马之性?船山认为草木仅能承受其生长收藏之气,禽兽仅能承受知觉运动之气,唯有人才质善而可以承受清明之气以存仁义之心。[3]1078但我们若问才质之善何来,则又必然追溯回初生之际的禀受之性。所以“性日生日成”之说的关键在于,这里是否有个永远无法剔掉的先天人性设定。如果有,在何等意义上不同于传统道学要回复的心体或者性体。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更加深入分析船山气质之性学说,才能最终理解“性日生日成”理论的前提性架构。
二、气质之性说的疑难
由上所论可知,船山虽然反对将性理解为初生之际一成不变之侀,但他还是认为在初生之际人与禽兽草木之性已经有了根本差别,(整全之)性既是天地之气所凝形质之体,同时也是此形质借助于天地生气不断继善的生成,那么,物性差别的根源便在于不同天命所产生的不同形质,由此又会产生不同物继善成性的能力之不同。也是这种差别决定着不同的人、物在后天日受日生方向的不同。既然人之性与他物皆不同,船山时常以性字专指人而言:
道统天地人物,善、性则专就人而言也。[5]526
才言性即是人之性,才言道即是人之道。气外无性,亦无道也。[3]1143
性的这种用法和意义,又可以进一步分殊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船山分别在中年的《读四书大全说》与晚年《张子正蒙注》中详细讨论此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问题。尽管船山在两部著作中出于注释的需要,所使用的概念意义不同,但结构以及结构中各部分元素的意义与功能并没有根本区别,所以我们只要不执着于概念的名相变化,还是能够会通其早晚著作,获得一个统一的理解。我们先来看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气质之性的论述:
程子创说个气质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其实是由张载最先提出的,程朱继承之。船山这里程子创说的说法有误,曾昭旭猜测可能是为横渠讳,这个说法或有过度之嫌。首先,船山中年时虽然也力赞横渠,但并没有鲜明地表示归本横渠,晚年方有此论。其次,从船山晚年的《张子正蒙注》中涉及的讨论来看,他依旧认为此说是程子所创,横渠对其有所纠偏。考虑到船山颠沛流离的治学条件,此误情有可原且无关大碍,亦不必特为之讳。,殊觉崚嶒(笔者按:高耸突兀,特出不凡)。先儒于此,不尽力说与人知,或亦待人之自喻。乃缘此而初学不悟,遂疑人有两性在,今不得已而为显之。
所谓“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质是人之形质,范围著者生理在内;形质之内,则气充之。而盈天地间,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故亦无非理者。理,行乎气之中,而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故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质以函气,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气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若当其未函时,则且是天地之理气,盖未有人者是也。(船山自注:未有人,非混沌之谓。只如赵甲以甲子生,当癸亥岁未有赵甲,则赵甲一分理气,便属之天。)乃其既有质以居气,而气必有理,自人言之,则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复天之有。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3]859
首先要注意的是,船山明确表达他作此论的目的是防止对性理解的二元论倾向,“疑人有两性在”,这是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要时刻牢记的。
船山这段话的大义似乎并不费解,乃是以“气质中之性”来重新诠释“气质之性”:人出生以后,有形有质,气涵于其中,有此气其遂有此理,理即性也,则就此人整全个体而言所具有的理即是此人之性,此理人人不同,故人性亦随其气质而各有不同,此个体独特之性即为“气质中之性”。然而,这段话里又存在许多困难,从而带来诸多不同解读。我们将通过对曾昭旭与陈来两位先生不同解读的讨论来深入理解船山此篇材料。
陈来先生认为,“质以函气,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气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这段话说的是,“不同的个体形质所函的气有所不同,从而每人都有其特殊的生命体质;又由于不同个体形质所函的气有所不同,所以这些气中所函的理也有所不同,也就是气质中之性相近而不同。这个说法在朱子学里叫做‘气异而理异’。”[4]150另一方面,“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是“以反对朱子学把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区别开来的做法,而这似乎是说,气质之性不受气质的影响,与本然之性相同。这种说法在朱子学中叫做‘理同而气异’,可是,这样一来,又怎么能论证性相近之说呢?”[4]150陈来先生对这两段的解读提示我们,问题的关键仍是在于理气概念的内涵,内涵的细微变化会造成对整个结构判断的变化。
按照陈来先生《朱子哲学研究》,朱子“气异而理异”“理同而气异”的“理”字是不同的,后者指的是“天地普遍之理,在人则指性理,在性即本然之性”[6]141;前者指的是“个体人物的分理(也可称为气质之理),在性即气质之性”[6]141,“而朱熹哲学中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并不是专指气之性(如横渠所谓动静、相感、攻取之性),而是指本然之性坠入气质之中后表现出来的性……只要说到气质之性,自然包括本然之性在其中”[6]137,“本然之性作为本体即存在于气质之性之中,正如泥浆中本身即包含有水一样”[6]140。朱子晚年以人物皆有本然之性,又皆有气质之性,只是物所禀受的性偏而不全,人禀受全而又有遮蔽之不同。陈来先生进一步认为,朱子并没有完全解决此二者的矛盾,在“理同而气异”的思路下,人与物皆分有整全的本然之性,只是因蒙蔽不同而造成差别,这就会推致将理实体化的思路。而如果彻底坚持“气异而理异”的径路,最终会导致理只是气之条理的气本论。[6]143
显然,在陈来先生的思路下,“气异而理异”与“理同而气异”分属于气本论与理本论两条道路。前者能够比较好地说明不同人的性之禀赋差异,却难以充分区分人禽之辩,从而给道德伦理奠基。后者虽然能够为人伦奠基,克服相对主义或功利主义,然而又无法将自身与佛家区别开来,从而容易陷入没有分殊的平等主义中去。也是在这种思路下,陈来提出了对船山的质疑,认为“船山最后的推理也不清楚,照其最后几句所说,当形质已成之后,质以函气,气以函理,一人一生,一人一性,而那些未聚的理气仍只是天地流行之理气,并不受已聚成形的形质所影响。从这里如何推出‘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的结论?船山所用的‘本然之性’的概念与朱子学是同是异?”[4]150实际上,陈来先生认为船山的“本然之性”与朱子是相同的,所以他会在上文质疑的注脚中引用了唐凯麟的一个解释:“这就是说,气质之性即气质中所涵之理,借用朱子的话来说,就是本然之性。”[7]300并接着说:“气质中之理当然是来自天地之理,但假如气质中之理与天地之理全同,那它就不受特定气质所影响,又如何说明性是相近而不是相同呢?”
曾昭旭先生的研究认为:“表面看似与朱子所解理在气质之中不异,而实不同也。朱子乃是在理气不离不杂之纲维下解之者;而船山则是在‘理为气之理,气为理之气’,理气浑凝为一之纲维下解之者。故依船山,只可说性为‘气质中之性’(原注:实当说为‘气质中之理’,此因顺‘气质之性’之名,故尔)却不可说为‘性(理)寄在气质之中’。故实与朱子截然相异也。……其实义遂在确立人之个体性,以使此天地生化之理,有一特殊基底以发用者……是以船山每从个体性言体,而云‘乾以阴为体而起用,坤以阳为用而成体’,云‘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云‘性载神以尽用’也。此即人之个体性之存在意义。”[8]516曾昭旭先生此论点出船山与朱子之不同,若单就此段所论,陈来先生当亦无异议,惟曾昭旭先生并未从根本上说明船山是如何面对陈来先生所提出的理学与气学各自的困难,也就是说,并没有将概念自身的逻辑推演至极以明了其内部可能蕴含的困难。譬如,此处曾昭旭先生将船山“气质中之性”解释为“气质中之理”,这个说法与陈来先生上文所言的“气质之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船山反对“性(理)寄在气质之中”这个说法,至少在《读四书大全说》中也反对本然实体意义上的“天地之性”的说法*参看阳货三:“新安又云有‘天地之性’,一语乖谬。在天地直不可谓之性,故曰天道,曰天德。繇天地无未生与死,则亦无生。其化无形埒,无方体,如何得谓之性!‘天命之谓性’,亦就人物上见得。天道虽不息,天德虽无间,而无人物处则无命也,况得有性!” 《读四书大全说·论语·阳货三》,见《船山全书》第6册。,所以,曾昭旭先生所谓的“气质中之性(理)”逻辑上应当是与朱子迥异,不包含“天地之性”或“本然之性”的,那么其所谓“天地生化之理”以人之个体为基底发用又是什么意义呢?这些在曾昭旭先生论述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似有大而化之之嫌。而陈来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性论最为关键性的要害,是讨论宋明道学绝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不流于空泛之论,我们继续就船山此篇材料以及相关论述来讨论,以试图呈现船山是如何解决此困难的。
三、气、质关系
接着上文之论,船山在此篇材料中以笛来譬喻气、质、性关系:
以物喻之:质如笛之有笛身、有笛孔相似,气则所以成声者,理则吹之而合于律者也。以气吹笛,则其清浊高下,固自有律在。特笛身之非其材,而制之不中于度,又或吹之者不善,而使气过于轻重,则乖戾而不中于谱。故必得良笛而吹之抑善,然后其音律不爽。
造化无心,而其生又广,则凝合之际,质固不能以皆良。医家所传灵枢经中,言三阴三阳之人形体之别、情才之殊,虽未免泥数而不察于微,而要不为无理。抑彼经中但言质而不言气,则义犹未备。如虽不得良笛,而吹之善,则抑可中律。气之在天,合离呼吸、刚柔清浊之不同,亦乘于时与地而无定。故偶值乎其所不善,则虽以良质而不能有其善也。此理以笛譬之,自得其八九。
乃其有异于笛者,则笛全用其窍之虚,气不能行于竹内。人之为灵,其虚者成象,而其实者成形,固效灵于躯壳之所窍牖,而躯壳亦无不效焉。凡诸生气之可至,则理皆在中,不犹夫人造之死质,虚为用,而实则糟粕也。[3]860
这几段话的基本含义如下:笛譬如人,人有形质正如笛有竹身,此形质不同决定了性之差异。笛之形质不同于箫管,正如人之形质不同于犬羊,所以人性异于犬牛之性;同为笛,材料与尺寸又皆不相同,正如人与人之智愚贤不肖各不相同,所以性相近。人虽然形质贤愚不同,但都可以在自身个体基础上获得天之全理,正如笛子虽然有不同,但得善吹者亦可合于音律。“唯当知此所谓理(笔者按:指以笛音律之理譬喻人所秉承之天理),实谓天地生化之纯理至理,非一事一物形构之理也。此处以音律喻之,固比譬未妥,读者宜简别之。”[8]519此外,陈来先生指出,气在这里前后所指不同:“气丽于质”与“质以含气”所言之气指的都是构成特定形质的气,可称之为“形质之气”;未聚成形前的气可称之为“天地之气”;“气因于化”之气指的是形质形成以后在其周围时空环境中与之往来的天地之气,可称之为“形后之气”(原注:船山自己有时称之为“生气”)。[4]153“形质之气”与“形后之气”皆来自天地之气,前者是人性相近的禀赋性原因,后者指的是人生之后日日接续天地之气,而性日生日成,这是人性相近的生成性原因。
这个譬喻中尚有精微难解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以力求获得一个比较圆满的诠释。譬如:以气吹笛之气与陈来先生分殊的三种气是什么关系,在人而言有何意义?气与质又有什么关系?这里所谓的善与不善应当在何等意义上理解?笛之虚实体用与人有何异同?
曾昭旭先生对此数段论述说:“此所谓气,即指天地生化之实用,乃即与理为一者,此理气行于质中,即成乎善,善者,即此生化之用能自由表现之谓也。然而当气分凝为一一之形质,形质即可有其自成之范限与机括,当此范限机括极端僵固之时,生化之理气即难入以起用,而几若暂熄,而此形质即只能顺其一定之型以终,若然者即谓之质之不良也。……故不善之缘,毕竟在质而不在理也。……以上所论,是就一般之物而言,其形质僵固,不能有化理之自觉。”[8]518
曾昭旭先生点出船山不善之缘在质,而形质之所以不善,是因其“僵固”,使得生化之理气难以入于其中,运行于其间。不过此解读未尝切实道出僵固与生化之理气的确切含义,以及这种对善之理解带来的根本性思路变化。人与笛子不同之处在于人能够主动地生成自身,这种生成不仅是在形质层面,也是在情才与德性层面,所以,如果说笛子需要善吹者方能成就其音律,那么人则需要自身不断学习才能取纳天地之善气以变化其气质。接下来船山从气质关系角度,就初生之本与生后之用两方面说明了人何以能如此:
气丽于质,则性以之殊,故不得必于一致,而但可云“相近”。乃均之为笛,则固与箫、管殊类,人之性所以异于犬羊之性,而其情其才皆可以为善,则是概乎善不善之异致,而其固然者未尝不相近也。
气因于化,则性又以之差,亦不得必于一致,而但可云“相近”。乃均之为人之吹笛,则固非无吹之者,人之性所以异于草木之有生而无觉,而其情其才皆有所以为善者,则是概乎善不善之异致,而其能然者未尝不相近也。[3]860
船山在讨论生成关系的时候反对寄、寓、造这样的概念,认为会导致对生成理解的体用殊绝与外在化,他最常用的概念是丽、凝这样强调一贯性的概念。丽字的哲学化用法见于《易经·离卦·彖》:“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王弼注:“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孔颖达疏:“丽,谓附着也。”船山在原有“附着”之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他解释说:“丽者,依质而生文之谓也”。也即是说,初生之时,气丽于质,在此过程中会生出质中之文理,为了区别于非形质之气的文理,船山对此质中之文理专门使用了一个概念:型范。它强调的是气丽于质生文之后,反过来相对于外在流行之气的静态性与范围约束之义。范围约束之义下文有论,这里船山是要说明初生之时形质各异,是以性只能称为相近而不是相同,此之谓“固然”。“固然”指的不仅是初生之性的事实状态,也包括潜在的可能性。
船山对“已生之后”的论述与第一段相似,只是几个关键词做出了区分,“而其情其才皆可以为善……而其固然者未尝不相近也”变成了“而其情其才皆有所以为善者……而其能然者未尝不相近也”。其意图在于说明,性之固然乃是可以为善,性之能然乃是有所以为善。前者为体,后者为用,性之体用皆相近而可以为善,是以“性相近”。要注意,船山体用学说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体用二者可以交藏互用而相生[9],则固然必有能然,其能然必反过来生成新的固然,在船山接下来的讨论中,是就质与气的交互关系阐发此点的:
盖质,一成者也;气,日生者也。一成,则难乎变;日生,则乍息而乍消矣。……乃既已为之质矣,则其不正者固在质也。在质,则不必追其所自建立,而归咎夫气矣。……质能为气之累,故气虽得其理,而不能使之善。气不能为质之害,故气虽不得其理,而不能使之不善。……故知过在质而不在气也。乃其为质也,均为人之质,则既异乎草木之质、犬羊之质矣。是以其为气也,亦异乎草木之气。犬羊之气也,故曰“近”也。孟子所以即形色而言天性也。
乃人之清浊刚柔不一者,其过专在质,而于以使愚明而柔强者,其功则专在气。质,一成者也,故过不复为功。气,日生者也,则不为质分过,而能[为]功于质。且质之所建立者,固气矣。气可建立之,则亦操其张弛经纬之权矣。气日生,故性亦日生。生者气中之理。性本气之理而即存乎气,故言性必言气而始得其所藏。
乃气可与质为功,而必有其与为功者,则言气而早已与习相摄矣。是故质之良者,虽有失理之气乘化以入,而不留之以为害。然日任其质,而质之力亦穷,则逮其久而气之不能为害者且害之矣。盖气任生质,亦足以易质之型范。型范虽一成,而亦无时不有其消息。始则消息因仍其型范,逮乐与失理之气相取,而型范亦迁矣。若夫繇不善以迁于善者,则亦善养其气,至于久而质且为之改也。……乃所以养其气而使为功者何恃乎?此人之能也,则习是也。是故气随习易,而习且与性成也。
质者,性之府也;性者,气之纪也;气者,质之充而习之所能御者也。然则气效于习,以生化乎质,而与性为体,故可言气质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别有一气质之性也。[3]861
此部分材料意思比较清晰,大致有如下要点:
其一,质由气聚而成,于初生所成之后,即有较为固定的型范。气则运行不息,日日作用于质。
其二,气无论在成质之前还是之后,都是无心化成的,虽然就其全体或长久来看大公而至正,单就一时一隅而言难保时有偏至。所以并不能保证质之必正,亦不能保证形后之气作用于质之时必正。但因气总体来看为善,所以是养气向善的基本源动力。
其三,质虽由气而来,当其成形,气凝于质之后,便不再同于本然之气。不能够再毫无区分地笼统谈论气质。船山之一元论并非无差别无区分的一元论,而是以凝、继这样的字眼来体现出分化区别。
其四,有上述分化差异,质之型范遂有厚重之势,有势遂有能,即不是被动承受作用之气,随外界之气而变。而是能够通过其型范自持而立,并归纪外界相作用之气而化入自身。
其五,型范的这种势能并非绝对的,质归根结底仍是为气所构成,且船山并不认为有某种先天不变之理内在于质,所以质之文理型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气的交互作用中缓慢变化而不断生成。
其六,质之型范,或曰质中气之理,为气之纪,纪为纲领法度之义。纪又有治理主持之义。“性以纪气,而与气为体。可云气与性为体,即可云性与气为体。质受生于气,而气以理生质。”[3]863此即为性气相生之道。
归结以上要点,可以举个形象的比喻,气譬如河流,型范譬如河道。河道本是河流所至而生的自然型范,河道既成,则其势必然规定着河流的轨迹流向。河道本身却并非一成不变,河流在长年的冲刷乃至泛滥中必然会改变河道甚乃决堤而出。然而若能时时疏通维护河道,则可使河流渐趋中正清澈,灌溉良田造福万民。
四、结语
现在可以看到,船山“气质中之性”即是“本然之性”,指的是构成人的“气—质—理”这样一个统一整体,而不是蕴于人之中的某个先天本体。这个统一整体既包含气凝为质所带来的文理差异,即个体独特性,也包含源自“气”的先天生生不息之德[10],因观察与解释角度不同而有不同之名:就其初生之际便已有,并且秉承“天地之气”生生不息之德而言可称为“本然之性”;就其“气—质—理”统一不可分而言,称为“气质中之性”;二性实一而称谓指向不同,“非本然之性以外,别有一气质之性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草木,既是“本然之性”的不同,也是“气质中之性”的不同。气之理并不是独立于气的不变法则,只要有气便有其理,即便是所谓的失理之气也并不是气真的丧失了其内在本体,而只是理气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发生了变化而相应地气中之文理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中正:“气之失理,非理之失也,失亦于其理之中。”[3]863此外,在船山看来,如果说人因为纵私欲而失其本性,这说的既不是“气质中之性”中的某个先天本体不再寓于人之中;也不是这个本体被欲望遮蔽而需要以工夫磨洗后天尘垢,或观照先天本体以求复得;而指的是质与外界之气攻取过度,变得更加窒浊而不复清明,相应的“气质中之性”也更加窒浊而不再能够生生不息地化用交通天地清明之气。
所以,凝成形质之前的气固然为善,其理亦善,然因天地之气尚未成形质则不可言性。气凝为质之后,质中之性尽管依旧有不息与生成之德,但因其质必有窒碍或攻取,故并非纯善。所以“气质中之性—本然之性”,只能说是相近,而不可言善。所以船山比较孔子性相近与孟子性善论给出结论如下:
孟子惟并其相近而不一者,推其所自而见无不一,故曰“性善”。孔子则就其已分而不一者,于质见异而于理见同,同以大始而异以殊生,故曰“相近”。乃若性,则必自主持分剂夫气者而言之,亦必自夫既属之一人之身者而言之。孔子固不舍夫理以言气质,孟子亦不能裂其气质之畛域而以观理于未生之先,则岂孔子所言者一性,而孟子所言者别一性哉?[3]864
这是说孟子是就性在天之本源而论性善的,其所论其实并非性,只能说是天命天道天德。孔子说的才真正是现实中的人性。至于其论孔孟所言为一,只是个委婉的调和,究其根本,船山还是反对性善之说,而赞同孔子性相近之说。因为讲性善者都是将性一分为二,认为就本然之性来说为善,现实之性必然有不善。而船山反对有二性,反对将“本然之性”理解为一个未生之先的先天之性:“孟子亦不能裂其气质之畛域而以观理于未生之先。”所以,船山思想中的人性,既是秉承天地之善的本然之性,也是具体现实中的性,又是可以变化生成的性。由此,船山认为孟子所论其实是命,而非性,孔子“性相近”之性才是真正的“性”:
虽然,孟子之言性,近于命矣。性之善者,命之善也,命无不善也。命善故性善,则因命之善以言性之善可也。若夫性,则随质以分凝矣。一本万殊,而万殊不可复归于一。易曰“继之者善也”,言命也;命者,天人之相继者也。“成之者性也”,言质也;既成乎质,而性斯凝也。质中之命谓之性,(船山自注:此句紧切。)亦不容以言命者言性也。故惟“性相近也”之言,为大公而至正也。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船山“气质中之性”的说法必须基于其对“气”“质”的区分才能理解透彻。开篇我们提及了宋明道学传统下“气”与“质”的存在层面差别,不过在理学的一般理解中,“气”与“质”尽管可能存在清浊虚实之别,但此差别与“理”无甚关联。在船山来说,他通过“气学”回复了传统文质论的关键核心,即文质交互生成性,“理”必定是“气之理”或“质之型范”,从而始终处在与“气”的交互生成中。因此,他的人性不再是先天本体,而是作为整体的“气质中之性”。这样的性论既保证了“气”一元论的基础而无二本之虞,又具备天地之气的生成潜能,还能够保持“气—质”之间的差异性从而给出不善来源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结构下理解的善在最根本意义上依旧是个体在自身内部继承并保持气之生生不息,这样个体才能够化用外界清明之气从而使自己不会被型范所限定,并且进而通过不断地后天之“习”来改变型范,使之渐趋完备中正而合于天:“善养者,何往而不足与天地同流哉!”[3]864
参考文献:
[1] 吴飞.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M].北京:三联书店,2017.
[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2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4] 陈来.诠释与重建 [M].北京:三联书店,2010.
[5]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6]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 唐凯麟.试论王船山的人性论.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8] 曾昭旭.王船山哲学[M].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
[9] 田丰.王船山天人之辨与体用思想探微[J].汕头大学学报,2016,(10).
[10] 田丰.王船山“四德”天人之辨的人性论意义[J].船山学刊,2016,(9).
——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