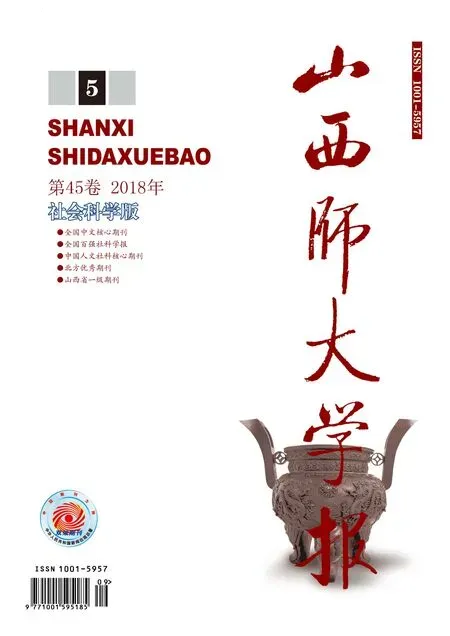吴澄的辩证诗学观
何 长 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吴澄(1249—1333)作为元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其思想兼容了朱陆之学,被称为有元一代大儒。“元诗四大家”之一揭傒斯说:“皇天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1]28册505可见其非凡的理学造诣。吴澄不仅于经学有精湛的论述,他的文学创作在元代也很有特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吴文正集》提要评价他的文风“辞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2]2211吴澄不但有着出色的创作水平,而且其诗文评论也很有特色,以至于连他本人也认为:“余非能文者,喜谈文者也”[3]206。当前关于吴澄理学思想的研究已有颇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对其文学观念的研究相对较少。*王素美《吴澄的理学思想与文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对吴澄理学与文学的契合部分作了宏观的分析。王素美《传统诗教与非传统诗教之间——论吴澄诗歌理论的特点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认为吴澄的文论尚风不尚雅,重视歌谣,并认为吴澄关于创作心理因素的研究颇近明代的“性灵”说。其余单篇论文如潘殊闲《吴澄李杜比较观述评》(《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高妍《吴澄书信价值论》(《兰台世界》2016年第16期)等也涉及吴澄的部分文论思想。吴澄的文论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其实,研究吴澄的诗学思想对于我们深入探究有元一代的诗学走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吴澄对《诗经》六义的看法及他对《诗序》的态度写起,然后深入剖析吴澄“性情”论中“重我”观念歧出的原因;并分析他为何羡慕古人尚“游”的行为,却又反对时人崇“游”的风气;最后深入阐析吴澄的“尚实”文论,揭示出于何种原因致其尊临川而贬欧苏。
一、尊《诗》与反《序》
翻检元代诗法、诗格类著作,可以发现元代大多数诗论家有着明显的宗经倾向,特别是对《诗经》极为推崇。然而,作为理学家的吴澄在尊崇《诗经》的过程中,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观点。
吴澄首先对《诗经》中的风、雅、颂重新正名。他认为风、雅、颂是“乐章之名,其音节各异,如今慢词、小令之分,虽欲以彼为此,此为彼,而不可得,非编诗者可以己意移矣”[3]130。他这一认识颇具创新意义。以乐章之名来定义《诗经》中的风、雅、颂,显然揭开了汉儒解经的神秘面纱,还原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改变了传统的看法。传统经学,尤其是汉儒将《诗经》赋予了神秘色彩,《诗经》离乐章的性质已经很远了,更多地变为体现圣贤心性、王道政治的学问。吴澄将之还原为“乐章”,无疑有着祛魅的作用,使得研究者在审视《诗经》的空间上有了开拓。
吴澄还以为,风雅颂的编撰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按照一定的意图组织成文。他指出:“《风》《雅》《颂》初无一定,由人以意安排也。”[3]130在他看来,风雅颂的排列组合是按照固有的逻辑展开。他认为:“盖祭祀之时歌之于鬼神者,《颂》诗也;受釐之时歌之于人生者,《雅》诗也。况《颂》诗与《雅》诗之体制,亦自判然有不同也哉。”[3]130吴澄对风雅颂的划分与汉儒和唐代孔颖达有所不同。他对风雅颂的划分显然是从诗歌所颂扬的对象出发的,比如《雅》所言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相关,而《颂》是向鬼神歌唱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四经叙录·诗经》中有更为详细的解说:“乡乐之歌曰《风》,其诗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王采之以入乐而被之弦歌。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歌曰《颂》。”[3]5这是从《诗经》的来源和使用场合而言的,故而认为《风》源于“男女道其情思之辞”,《雅》是用于朝廷之乐,《颂》是用于宗庙。此外,他还发现:“然则《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与乐不同,其为辞一也。”他认为,《风》是因为《诗经》的存在而成为乐歌,而《雅》和《颂》是因为配乐的需要成为《诗经》的内容,但最终它们都作为歌辞而存在。吴澄对《诗经》体裁的认识可谓极其周密,也很有创建性的。他没有沿用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所提出的“三体三用”说[4]12—13以及朱熹等人的“三经三纬”说[5]2088,这标志着他对《诗经》的新认识。
值得重视的是,吴澄延续了宋儒的疑经精神,批判了以《诗序》为准绳阐释《诗经》的合理性。事实上,在宋宝祐六年(1258),吴澄10岁时曾“大肆力于朱子诸书”[1]28册506并在至元元年(1264)16岁时曾求学于理学家程若镛,程授之以朱子之学[1]27册171,可见他受朱熹经学思想影响之深,其疑经思想不能说与朱子疑经思想没有关系。他指出:“汉儒以义说诗,既不知诗之为乐矣,而其所说之义,亦岂能知诗人命辞之本意哉?”[3]5在他看来,汉儒仅从义理上去探求诗歌的本义,在根本上违背了诗歌的乐辞本质。吴澄进一步指出:“夫其初之自为一编也,诗自诗,序自序。序之非经之本旨。”[3]5在这里,吴澄言明《诗序》并不是《诗经》的本意,而读者仍然按照《诗序》的意图去解读《诗经》,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他义正辞严地强调:“是则序之有害于诗为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诗为甚大也,今因为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乱乎诗之正文,学者因得以诗求诗,而不为诗序所惑。”[3]6于此,其大胆的批判精神清晰可见。这也显豁地表明了他对朱子疑经言论的肯定与支持,并呼吁学界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诗经》。今人胡青也指出:“元代释经疑经,以吴澄为最。”[6]133吴澄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意识,他没有沿袭汉儒以《诗序》解诗的旧说。
当然,这样说不代表吴澄仅仅把诗歌当作单纯的娱情谴兴作品来对待,相反,他对包括《诗经》在内的古诗之“兴观群怨”作用也极为重视。吴澄在《刘复翁诗序》中说:“古之诗皆有为而作,训戒存焉,非徒修饰其辞,铿锵其声而已。是以可兴、可观、可群、可怨。”[3]237在这里,他对那些绮靡藻饰之作提出了批评。将孔子所言的“兴观群怨”说再次拈出,用意一目了然。而在四者当中,他尤其重视古诗中“观”的作用。他在《秋山翁诗集序》中认为秋山翁之作品是真正的抒发性情之作,还认为:“‘诗可以观’,信夫!然则翁之诗存,诚足以为观风者之一助,而不能不动观物者之深慨云。”[3]164可见,他认为秋山翁的诗作具有存诗的作用,同时也具有观风的效果,这显然是从经学角度去考察诗歌功用的。这与其一贯认为诗歌是雕虫小技的观点颇为矛盾。但应该看到的是,吴澄如果欲求诗歌发挥温柔敦厚的诗教作用时,就会重视诗歌的价值与地位,而这种价值观的确立,往往是以《诗经》的艺术风格作为典范的。
质言之,吴澄推崇《诗经》所具有的观风与化成天下的功用,但是对《诗经》学的“六义”以及《诗序》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其贡献也正体现于他以辩证的思维发掘出了诗学中的对立因子。
二、尚“性情”与“重我”
“性情论”在元之前的诗论中早已有之,也一直是诗论家所讨论的话题。《诗大序》对诗歌中的“性情”论首发其端,唐代《毛诗正义》也有相关论述。到了宋代,理学家也常以“性情”谈诗。在元代,作为理学家的吴澄也不例外。
吴澄认为诗歌的本质就在于抒发“性情”。他在《萧养蒙诗序》中指出:“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古之为诗者如是,后之能诗者亦或能然,岂徒求其声音采色之似而已哉!”[3]208可见,在吴澄看来,诗歌最为重要的功能是要抒发真实的“性情”,还要出言“天真”,也即提倡自然为诗。但是,理学家的固有思维模式始终在限制着吴澄的抒情诗论。他紧接着又指出,作诗应该发情止礼,这是作诗基本的要求。可知,吴澄的“性情”诗论难免含有理学色彩。
其实,联系整个元代诗学理论,不难体会,几乎所有的元代诗论家,包括理学家,都认为抒发性情是诗歌的应有属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元代论诗者普遍地以《国风》作为独抒性情的典范;另一方面,这也是元人意欲打破宋代诗学范式的一种情绪反映,他们祈望重建新的诗学体系。查洪德就认为:“元代诗人和诗论家要‘祧宋归唐’,自然会以‘吟咏性情’为号召,自然会以‘性情’作为理论武器来反对宋诗并提倡唐诗。”[7]125而这一特征在元代中期的诗论中比较常见。
吴澄以“性情”说诗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极为突出的诗学观念,就是诗歌抒发感情要“重我”,在《朱元善诗序》中他指出:
诗不似诗,非诗也,诗而似诗,诗也,而非我也。诗而诗已难,诗而我尤难。奚其难?盖不可以强至也。学诗如学仙,时至气自化,元善之于诗似矣。[3]197
在这里,吴澄将学诗分成了三个阶段,“不似诗”——“诗而诗”——“诗而我”,认为能够达到“诗而诗”的状态已颇为困难,若能至于“诗而我”的境界就更为不易了。所谓“诗而我”的状态是指诗歌中能够蕴含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吴澄将“诗而我”作为写诗的最高境界,这也可以看出,在元代,即使是一贯以性情谈诗的理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诗歌应以抒发作者独特的情感为尺度。重“我”诗论在唐宋诗学中明确提出的较少,尽管魏晋是注重缘情的时代,也较少有相关的论述。此种诗论的少见并不是说以往论者忽视了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而是说他们较少将个体之“我”放于诗论中。吴澄认为创作不遵守作诗的规则自然不能成诗,但若所作之诗仅仅是为了符合普遍意义上的诗教原则,诗歌中就会无“我”之情感存在了。此种观念的出现也与元代诗坛兴起的“师心”论有关。
众所周知,江西诗派的流弊在南宋已经很明显了。而元代诗论中常谈到的“救弊”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江西诗派后期出现的模拟之风有关。元人用“师心”论来拯救江西之弊,也合乎其逻辑。当然这也与象山学派的崛起有关。南宋心学的兴起势必会向诗学渗透,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吴澄虽对朱子之学极为推崇,但对心学也颇为倾慕。《宋元学案》记载吴澄曾对学者强调:“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8]3037于此可见,吴澄也推崇“尊德性”的陆学。南宋心学强调“发明本心”,难免会出现重视个体情感体验的现象,这种重视个人体验的结果反映在诗学里,就会使得言诗者注重诗歌情感的阐扬。可以说,吴澄的“重我”诗论的出现,也正是以此为学术背景的。
但是,这也并不表明吴澄完全偏离了朱子之学的主旨。在《四书言仁录序》中他又云:“仁,人心也,然体事而无不在。专求于心而不务周于事,则无所执着,而或流于空虚。圣贤教人,使之随事用力。及其至也,无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3]179这里,吴澄虽然点明了“本心”的重要性,但是也指出“心”学出现的弊端。他认为若只专注于心性,而不务实做事,则容易流于空虚,因此他反对过分笃志于“心学”。相反,他认为士人还应在实处着力,在这过程中也是“本心之全德”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吴澄才会格外重视诗歌的“吟咏情性”作用,但是又必须坚持发情止礼的道德原则。
要之,吴澄对朱子的“道问学”和象山的“尊德性”同样予以重视,并且给以会通。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吴澄既注重以理学之“性情”论诗,又主张诗歌能够抒发“我”之真情,此种近乎矛盾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了。
三、尚“游”与反“游”
元代文人游历的风气颇为浓厚,“游”是元代一个突出的范畴,其重要性波及诗学领域。虽然这一范畴提出者较多,但是严密论证者相对较少。吴澄对“游”这一范畴作了批判性的认识,给出了具有启发性和思辨性的探索,具有很强的学理意义。
吴澄在《何养晦诗序》中提出了三种“游”。他说:“游有三,有苏相国之游,有司马太史之游,有南华真人、三闾大夫之游。相国之游,欲界之游也;太史之游,色界之游也,超乎无色界者,其惟南华真人乎?南华之游,真游也。三闾知之、言之而已,请问所安?”[3]211吴澄在这里给出了他对“游”的三种定义,分别是色界之游和欲界之游,他认为这两种“游”都算不上真正的“游”,只有“真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所谓的“真游”其实就是指庄子和屈原之游,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游”,是突破了物质与耳目之欲的“游”。吴澄对“游”的深入区分以及对精神之“游”的崇尚,与郝经所言的“内游”有相似之处[1]4册445。由此可见,元代重要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游”这一范畴的重要性,这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原因:其一,从地理范围而言,元代疆域之辽阔,为“游”这一范畴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条件。此前,由于战争的原因,南北出现了长时间的交通阻隔。而元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自然会刺激北方文人南下去体验江南水乡的欲望,致使元代后期江南滞留了大量的北方诗人。被称为“元诗之冠冕”的萨都剌就是西域人,他长期游历江南,留下了大量诗篇。[9]331同样地,南方的文人也很热衷于游览北国风光,这与以往他们一度因为战争阻隔而无法领略塞外风情有关。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元大都在北方,南方的文人由于做官的需要必须前往大都。元代延祐之后科举考试也促进了南方文人向北方的迁移。查洪德曾指出:“与南士北游不同的是,南士北上求仕,北士则是游仕南来。”[10]81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游”这一诗学范畴就极为自然了。其二,传统观念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汉代司马迁所带来的“游”文化的影响,及至宋代苏辙所论证过“游”的作用,[11]381—382而元代广阔的地域,更加有利于这种文化的孳生。另一方面,还与道家文化中的“游”范畴有关。庄子的“逍遥游”是这一文化的代表,这种思想影响了后世的思想者,尤其是到了元代,老庄思想极为盛行,这也会在某种形态上影响元代“游”范畴的义涵。其三,宋代理学思想对元人也有影响。宋人追求“性理”学说,在很大程度上都归结为对圣贤气象的学习,而这种学习不仅需要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还需要落实到体验“天理浑成”的境界,因此宋代出现了很多有开拓性意义的词汇,像“涵泳”“体验”等词汇,[12]120—131其基本内涵与元代所提出的“游”范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说,元人是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了“涵泳”的意义,而发明了“游”这一新的范畴。
对于“游”这一范畴,吴澄在《送何太虚北游序》中有较为清晰的阐发,对“游”的必要性也给予理论上的深化。他说:“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乎?”[3]359“游”这一行为,在吴澄看来是士人志向的一部分,它和六艺一样重要。吴澄还举例说孔子也曾周游列国,并认为:“夫子上智也,适周而问礼,在齐而闻韶,自卫复归于鲁,而后雅颂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齐、不卫也,则犹有未问之礼、未闻之韶、未得所之雅颂。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3]359像孔子这样的“上智”,尚且需要“游”,更何况普通的士人呢?
另外,吴澄也指出“游心”的重要性 。他在《题物初赋序诗后》中说:“‘吾游心于物’,此庄子之书述老子之言云尔。……物之初盖有所指而言,谓一物之初,非谓万物之初也;在吾身之内,非在吾身之外也。以吾生身之所从始,故曰物之初。游心物之初者,真人之守规中也。此人身要妙之境,而文士亦或拟之于天地之鸿蒙。”[3]589在这段文字中,吴澄认为“物之初”是个体自身,而非身外之物。关注自身也就是要注重个体的心灵世界,可知吴澄所提出的“游”范畴,与老庄哲学有关。他曾说:“予于道家书,自《道德》《南华》二经外,俱不喜观。”[3]594此处印证了吴澄确实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非同一般。事实上,吴澄在大德十一年(1307)就曾经校订过 《老子》《庄子》《太玄章句》等书[1]27册179,而吴澄写给何中的《送何太虚北游序》写于至大元年(1308),这正是他钻研老庄之后写的序文。可见,他在此序中提出老子之“游”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受到了《老子》的影响。
然而,吴澄在说明“游”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人们“游”之目的。他说:“方其出而游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所,伺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膀而取媚,以侥悻于寸进。”[3]360这是对当时所谓“游”士之动机的认识,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古代周游天下的意图了。吴澄一语指出了古人和今人对“游”的态度的差异,其不同之处在于古之游者是为求道,而今之游者是为了牟利。
基于这样的考虑,吴澄明确反对前文所言的“欲界之游”和“色界之游”。他指出:“游也者,仪衍妾妇之为也。不离道、不失义者肯为之哉?”[3]599在这里,吴澄十分轻视“游”,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妇人之事。为此他又指出:“欲壮其气,不必跋履齐、楚、燕、赵、关、陕、巴、蜀也;欲充其学,不必谒候寓公大人奇才隐德也。”[3]599吴澄旗帜鲜明地反对“游”,这种态度完全与苏辙之观点相悖,也与司马迁游览名山的态度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彼时社会所谓的“游”已经变质了,与古代为“道”而“游”的理想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可见,吴澄是推崇“真游”而反对物欲之游,这种主张与他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认识有关,也与他对宋末学术空疏的反思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强调了“实”学的重要性。
四、贵“实”贱“华”
翻检张健先生的《元代诗法校考》,可以看出元人有一种贵“实”的诗学倾向,[13]尽管提倡此种诗学趣味的论者并不多见,但这在元代是一忽隐忽暗的诗学线索,元代部分有识见的论家,已经将尚“实”作为一种诗学趣味加以提倡,这具有较强的诗学史意义。吴澄作为经学家,其诗学理论也比较重视诗歌中的“实学”问题。
元皇庆元年(1312),吴澄升任主管学务的司业时,提出了为学“四纲领”:“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14]4012这四条准则,虽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施行,但也能从中见出吴澄的学术观。作为重要的经学家,他将经学放在了第一位,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却没有因为尊崇儒学而放弃了具有文学色彩的“文艺”科目,这是耐人寻味的。这与宋儒二程将文学当做“闲言语”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5]188他在《刘鹗诗序》中说:“年过期颐,训其孙作诗贵实,盖知作诗作文之要领,且谓当推此实于言行,则其学识知所根柢。非但文士见趣而已。”[3]192他希望将“实”推之于言与行。
吴澄在《题得己斋叙记诗卷后》中阐释了他尚“实”的原因,他说:
窃观夫子之与人言,未尝多也。若利也,若命也,若仁也,言之亦罕。言不多矣,犹以为未,而语子贡曰:‘予欲无言。’圣人岂靳于化今传后,而欲无言,何欤?化今传后,不在乎言也。自汉以下,儒者虚言炽而实功微,流而至于宋之末,虚言之敝极矣。[3]582
这里,吴澄指出了反对“虚”言的原因。在他看来,一方面孔子并没有过多的关于“利、命、仁”的言论,且孔子教育其弟子应少言语,认为“化今传后”并非虚言能够起效。另一方面,自从汉代以后,儒者关于教化的言论日盛,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宋末。故而,吴澄认为“虚言多”而“实功微”,这是教化不得效果的原因。可以这样说,尚“实”既是吴澄作为经学家的基本观念,也是他诗学理论的重要特色。
出于崇尚事功的观念,吴澄流露出对诗歌的鄙视之情,认为诗是“小技”。他在《跋陈泰诗后》说:“吾之儒学盖不止此。文者儒之小技,诗又文之小技。有最上事业,坦若大路。”[3]601在这里,吴澄鲜明地指出古文不过儒者小技,而诗歌的地位又在文之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依然与其经学家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出于传道的需要,他自然极为重视古文的作用,而认为诗歌传道的效果相对弱一些。比起唐代韩愈自诩“因文见道”而赋予古文重要的地位[16]44,在吴澄这里,古文的地位似乎早已变为无足轻重的“小技”了。
吴澄的这种理念,也影响到了他对唐宋古文大家王安石和欧阳修、苏轼的评价态度。在《王友山诗序》中,他说:“宋三百年,文章欧、曾、二苏各名一世,而荆国王文公为之最,何也?才识学行俱优也。”[3]241其实,关于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优劣问题,后世一般都是以欧阳修和苏东坡的古文为优,但是吴澄却认为王安石的古文要远胜于欧苏的古文,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在吴澄的意识中,他不仅重视诗文自身价值的高低,还要衡量作者的功绩大小。他认为王安石的古文是有宋三百年的顶峰,乃基于王安石的政治影响要比欧阳修和二苏明显更胜一筹。可以看出,吴澄也是从理学家的角度去衡量文章的价值的。吴澄在《王学心字说》中说:“夫学亦多术矣。辞章、记诵,华学也,非实学也。政事、功业,外学也,非内学也。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实矣,内矣。”[3]94在吴澄的学术分类之中,拥有政事和功业才能算是真正的实学,而古文与诗文在他看来,并不能划为实学,它们属于“华学”,也即不实之学问。出于这样的考虑,吴澄才认为王安石的古文要胜于欧阳修和苏轼、苏辙的古文。
综上所述,吴澄作为元代第一流的理学家,他的诗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理学观念的制约,二者虽然表现出某种趋同性,但是其诗论内部的裂缝依然清晰可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他的诗论中存在很多对立的观点。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吴澄极力推崇《诗经》发情止礼的“性情论”,但是又提出写诗要重“我”的观点;他很认同孔子等先贤的尚“游”表现,但是却又激烈批判时人尚“游”的风气,进而否定了“游”的价值;他很尊崇那些具有“情性”特征的诗歌,但是出于理学家尚实的理念,又不惜将之贬为“雕虫小技”。以上种种其实恰恰体现了吴澄诗学思想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也是其兼宗朱、陆理学的反映,而这正是吴澄诗论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