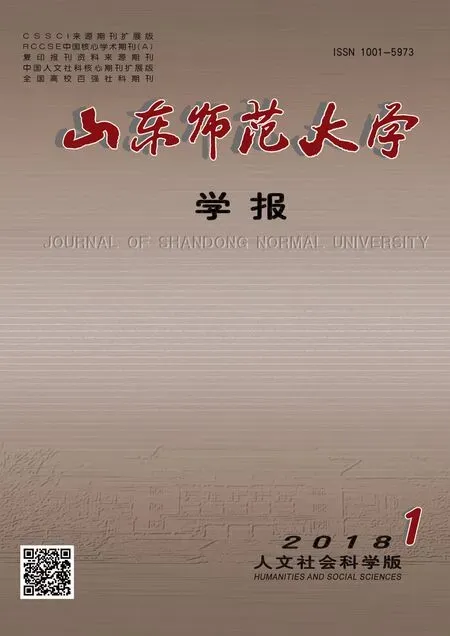从供求关系角度看科举的出路拥堵问题及近代废科举的意外后果*
苗永泉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在传统社会中后期,科举制度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一个实现社会上升的阶梯,不过这个阶梯的出口非常狭窄。大量士子中最终只有少量幸运儿能够高中。科考竞争非常激烈,以科举谋出路并不容易。宫崎市定形象地称科举为“中国的考试地狱”*Ichisada Miyazaki.China’s Examination Hell: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何怀宏则将鲤鱼跳龙门之难概括为“科举累人”和“人累科举”。*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40页。科举出路的拥堵几乎与其诱人的前景一样引人注目。本文以科举出路拥堵问题为切入点,以清末废科举事件为历史拐点,着力探讨两大问题:一是借鉴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分析框架,从供给侧、需求侧及供求之间的动态关系三方面系统分析科举出路拥堵现象的成因;二是由出路问题切入,分析近代废科举所导致的重要意外后果,并对此种意外后果的成因提供一个理论解释。
一、科举的出路拥堵问题及其成因
科举出路拥堵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相对于庞大的应考群体来说,能够获得高级功名者(具备做官资格的举人、进士)所占比例非常小;二是官职空缺有限,即使考中举人以上的功名,往往也需要排队等候官缺的出现。科举制度是一种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的考试选官制度,竞争非常激烈,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梁启超曾经估算道:“邑聚千数百童生,而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此其选之精也。”*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从后人的统计研究来看,从唐代到清代,年平均录取的进士数量(一般不超过100人)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都非常小。*具体的统计图表见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48-349页。举人数量较进士要多出一个量级,但相对于庞大的应考群体和人口基数来说其比例也非常小。*从明代的数据来看,在一些统计年份各地乡试(从生员中选拔举人)录取率多数不到5%,各开科年份会试录取率一般不到10%,见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附录部分。因此,如果说科举是一座通向功名利禄的桥梁,那么真正能够跨过这座桥的人实际上非常少,大量的士子被这道关口阻挡在外。即便如此,在很多时候官缺数量还是大大低于科举高中者的数量。比如,在咸丰元年的科举考试中,全国(广西除外)中举者1789人,上升流动为进士者249人,占13.7%,后实授官职者317人,占举人(考取进士者不计)的20.6%,候补者72人,占4.9%,两者共占25.3%,尚有74.7%仍处于“沉淀层”。*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可见在咸丰元年,绝大多数考中举人的士子都未实授官职,排队等候的现象非常突出。就科举出路拥堵现象的上述两方面表现来说,本文主要考察前一方面,因为它决定了出路拥堵问题的“基本面”。
为什么科举出路如此狭窄和拥堵?我们可以用经济学中的供求分析框架来解答此一问题。以现代人力资源市场的眼光来看,广大士子可以视为供给人力资源的一方,而选拔人才以充实官僚体系的国家则可以视为需求人力资源的一方。于是,科举出路拥堵问题就转化为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所导致的供求失衡问题,科举考试则作为一道门槛将大量的参加者限制于外。下面从供给侧、需求侧以及供求之间的动态关系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首先,从供给侧来看,科举考试的开放性和公平性特征使入口放得比较开,而获取功名利禄的诱人前景又使科举考试对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两方面结合起来使应考群体数量庞大。一方面,相对察举制,科举制度允许士子“怀牒自举”,入口放开了;另一方面,宋代以后通过严格的科场程式也基本上保证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如此一来,科举考试就具备了较强的公平性,更能吸引人才的报考。除了开放报考和公正判卷带来的吸引力之外,科举所指向的诱人前景更是吸引大量士子应考的一个关键因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以说科举就是曾经的“士子梦”。在传统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功名利禄最受社会所看重。于是,有抱负的才俊往往都将举业作为实现社会上升的第一选择。此外,科举不限应考次数的特点更使其能对士子保持着持续的吸引力,可谓“赚得英雄尽白头”。有学者称科举考试是一种“大规模高利害考试”*郑若玲:《大规模高利害考试之负面后效:以科举、高考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大规模”是因为入口放得开,“高利害”是因为前景诱人,正是这两大要素使供给侧极为庞大。
其次,从需求侧来看,科举考试的出路主要指向做官,而传统国家所能提供的官职数量比较有限,科举出路非常狭窄。在传统社会中,王朝的职官数目往往不会偏离定额太多,并不会大规模地扩张。比如明朝文官数目的法定编制是20400人,晚明涨至24683人。*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2页。清康熙年间文官定额是11951人,而道光末年,全国文官数目是11316人。*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以上是职官总数,而在这个基数上由官僚机构更新换代所产生的官缺数目是比较小的,因此相对于庞大的应考群体来说,官僚机构的纳新需求殊为有限。这种供求矛盾在科举考试开始大盛的唐代就已出现,唐代在高宗朝时已经出现“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新唐书·选举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5页。的局面。另外,异途出身者(如宋代恩荫入仕者)也会挤占大量官缺,使供求矛盾更为尖锐。官僚机构的规模受到国家财政供养能力以及国家职能的制约,传统王朝财政主要以农业税为主,在较为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官僚群体数量的膨胀最终会加重社会底层的负担,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对于现代国家而言,传统国家的职能也较为简单。因此,统治者并不允许官僚机构无限膨胀,比如明代就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增员与裁员的过程。*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6-83页。在政府规模相对稳定的常态下,官僚机构的更新换代有着自己的速率,因此科考录取人数也受到国家的“定额”安排的控制。从总体上看,科举需求侧的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而不能随着供给侧的增长而同步扩张。供求之间的不平衡是通过考试竞争来调节的,报考门槛放开而录用门槛提高使科举考试竞争极为激烈,大量士子被淘汰下来。
再者,从王朝生命周期过程来看,科举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还存在着逆向配比关系,也即随着供给侧越来越膨胀,需求侧却越来越吃紧。具体说来,一般在王朝初期,政权更替带来官僚集团的大换血,而人才则因为战乱和社会经济的凋敝而减少。这时皇帝往往求贤若渴,如明初朱元璋就要求“各行省连试三年”,以期“贤才众多而官足任使”*《明太祖实录》卷60,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181页。。但随着王朝进入承平时期,经济复苏、文教发展和人口膨胀等因素都导致人才供给大量增加。从宋代数据来看,考试大军的规模随着承平日久而不断膨胀的现象非常突出,“参加各州检定考试的考生人数在十一世纪初期约为二万至三万人,而在一个世纪后参加一零九九、一一零二、一一零五这几年考试的人数达七万九千人。到13世纪中叶,光是中国南部(即南宋帝国)的考生大概达四十万人以上”*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56页。。但相比于王朝初期,在承平时期官僚集团更新换代的速率则日益常规化,因此这时国家能够提供的官缺数量反而大为减少。清代的情况就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一问题,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人口翻了一番多,但进士及进士以下功名的录取总数却显著下降。*[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5-117页。因此,从整个王朝的生命周期来看,科举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难以匹配,这极大地加剧了出路拥堵问题。
二、传统社会缓解科举出路压力的内生调节机制及文化人的潜在过剩
由于官缺数量远远小于人才供给,大量士子被淘汰下来。这些被淘汰下来的人怎么办?既然官僚机构无法直接容纳这么多的竞取者,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自谋生路。传统社会要想维持稳定,就必须使大量落第者融入到既有秩序之中,而非游离于其外。为了缓解科举出路拥堵带来的压力,传统社会系统内部产生出一些调节机制,大量士子由此找到了生路。
竞争的残酷性使从事举业的人在一开始就要做好落第的思想准备,而科举不限应考次数的特点又总能使心有不甘者燃起对下一次考试的希冀。大量的落第者于是一边谋生,一边准备下科考试。所谓“耕读”即指读书应考与谋生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那么,士子主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谋生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科举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现代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显著的不同。现代教育着力于培养适应复杂分工体系的专业人才,而科举士子却属于“文化人”而非专业技术人才。因为他们读的书是儒家经典,通过读书更多地是获取文化教养而非专业谋生技能,这才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当然,上述说法也有些绝对化,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能够读书识字本身就是一项技能,因此文化人在社会中可以从事一些较有文化含量的工作。按照周作人的看法,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入仕是正路以外,还有几条叉路可以走。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其四是学生意,但不外钱业、典当两种。*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页。虽然经商更有可能发家,但对于读书人来说,最具吸引力的职业还是教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后期,私塾遍布城乡,做塾师的机会非常多,较容易实现就业。另一方面,在尊师重教的传统社会,做塾师也能带来较高的职业价值感。*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除了做塾师,对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士人来说,可资他们选择的就业方式则更为优渥。生员在明代以后成为一种永久性的身份,他们成为士绅群体中的一员,享有一定的特权,可以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去,并由此获取一定的收入。具体来说有两大途径:一是充当官员的幕僚(清代俗称师爷);二是经理地方社会的事务。在明清时代,大量获取科举功名的士人入幕,辅助官员处理各项政务。据学者考证,明代的幕宾身份以生员为主,举人入幕者也不少。*陈宝良:《明代幕宾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在清代,幕府制度更是大盛,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清中叶以后人口剧增而官员规模却没有相应增加,于是官员不得不聘请幕僚来协助处理日益繁多的行政事务,大量具有功名而又为谋生所累的士人得以入幕为宾。除了充当幕僚,乡居士绅也可以通过经理家乡事务而获取收入。“当一个人成为生员(绅士的下层成员)之后,他就会站出来或人们会请他出来处理他家乡的公共事务,只要他留在家乡,这就是他的‘恒事’。”*张忠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页。借经理地方事务他们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绝大多数的绅士通过经理地方事务或教授学生来谋生”*张忠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通过充当幕僚或经理地方社会事务,大量士绅可以在谋生的同时实现重要的社会价值。
士子可以一边谋生,一边备考,这使出路拥堵所带来的压力得到缓解,但这种缓解方式存在着重大的局限。首先,大量士子的谋生途径高度依赖于科举体系本身,如果科举体系终结,就会出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局面。以教书为业实际上也是在完成科举后备人才的再生产,如果举业断绝,那么社会也就不再大量需要这类塾师。同样,相比于农、工、商业者,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群体(如果不兼营他业的话)并没有自己的实业基础,其特权和生路的维系也高度依赖科举体系和传统治理架构的支撑。一旦这一体系架构瓦解,那么他们也会陷入困境。其次,科举士子都属于文化人,其生业也多非实业,从农业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属于不事生产者。如果这一群体的数量过于庞大,就会大大加重农业劳动者的负担,也会使士子群体在谋生压力下变得嗜利无耻。王韬写道:“天下之治乱,系于士与农之多寡。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亦众,而游惰者且齿甘乘肥。”*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原士》,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页。士绅享有一定的特权,这些人也总是更有能力逃避税负,所以他们的负担就会转嫁到普通百姓的头上,给底层社会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这一问题在明代中后期就比较显著,绅衿阶层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激化了社会矛盾。*伍丹戈:《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总之,以科举为业者其谋生手段也多依赖于科举,传统社会缓解出路压力的方式并未使科举士子实现大规模的结构性分流,而是仍然将大部分人都吸附在科举体系之下。一方面,这种同质性较强且不断自我再生产的体系抵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比较差,很容易因为体系的瓦解而出现剧烈的震荡。另一方面,在王朝中后期,数量巨大的科举士子使整个社会的文化人供给潜在过剩,不事生产者过多会加重整个社会的负担。在传统社会中,文化人潜在过剩的问题之所以没有显性化,是因为科举体系仍然保持着对他们的整合力,但即便如此,在王朝末年仍然常常出现“秀才造反”的现象。
三、“错位嫁接”的废科举制度设计及其意外后果
科举制度与传统社会及其治理架构较好地嵌合在一起*科举制度与传统文明在长期的互动演化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一种“结构性嵌合”状态,对此详尽分析可以参考苗永泉:《科举革废与华夏文明的近代转型》,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成为帝制时代中后期不断完成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教育陀螺仪”*谢海涛:《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但在近代西方的挑战下,儒学知识与八股人才已不足敷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致力于维新的知识分子疾呼“人才救国”。在传统社会中,教育和选才直接与科举相关,因此科举改革首当其冲。在维新变法时期,科举改革的矛头主要指向废八股。但到清末新政时期,革废科举的焦点变为科举与学堂的关系问题。袁世凯等力主废科举的大臣认为科举的存在妨碍新式学堂的兴办。“足以为学校之敌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朱寿鹏:《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袁世凯等奏,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998页。最终在1905年,由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联衔呈递的《立废科举以广学校》奏折获得清廷上谕的批准,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传统的科举体系正式宣告终结。此前出台的癸卯学制中已经包含了奖励学堂的章程,废科举后奖励学堂毕业生以功名和官职的做法全面推广开来。
废科举的直接原因在于改革者认为科举的存在影响各地兴办新式学堂的积极性,而废科举的方式则是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这实际上是将原有的科举功名和选官体系直接嫁接到新式教育体系之上了,从而使学堂教育与选官合二为一。从改革者的意图来看,这种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鼓励学堂兴办以造就大量新式人才,挽救危亡。但事后看来,直接将科举铨选体系纳入新式学堂教育体系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错位嫁接”。正如胡适所批评的那样:“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耿志云:《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8页。
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的做法产生了重要的意外后果,虽然大量旧式士子转化为新式学堂学生,但他们的出路问题并没有解决,相反却变得尖锐起来。首先,传统科举考试体系具有严格的筛汰作用,以使录用人数与官僚体系的更新换代大体维持平衡,但新式学堂却是大批量兴办的,其毕业生数量也与日俱增,它没有科举体系那样严格的筛汰作用,从而使功名授予变得泛滥,仕途出现惊人的拥挤。1911年5月,唐文治指出:“乃自今年以来,留学生之毕业回国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经学部考试而得京外实官者,综计各案,已不下千余员。毕业奖励行之未及十年,而得官之多,已浮于甲辰(1904年)会试以前之数十倍。长此不变,窃恐倍数与年俱增,而全国将有官满之患,似亦无此政体。”*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虽然清朝在灭亡之前叫停了这一做法,但这一趋势到民国仍然不减,“民初数年间,在北京和各省出现了一批数以百万计‘日费精神以谋得官’的‘高等游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毕业学生”*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可见,“合科举于学堂”的做法导致获得功名和做官资格的人在短期内剧增,原本科考用低录用率将拥堵限制在获取功名之前,现在拥堵则转化为毕业后的候官环节,并且这种转化效率非常惊人,远远超过了国家的官职供给能力,供求失衡问题在候官环节爆发开来。
其次,传统的科举体系对士子具有强有力的吸附整合作用,不限应考次数的科举考试使大量士子始终保留着中第的希望,于是他们多能安于现状。但将育士、取士合为一体的改革方式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广大的读书人发现改革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宽松得多的入仕阶梯,因为只要学堂毕业就可以获得相应功名,于是大量原本积蓄在乡村社会中的士子都被调动出来,纷纷涌入学堂。从1904到1909年,学堂总数由4222所增至52348所,使大量士子童生在短短几年内被吸收同化。*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407页。但相较于科举制度来说,学堂制度无法对学生群体发挥持续的吸附整合作用,“学堂毕业是一次性的,它不像科举制度那样,可以无限期地对所有落第者‘许诺’‘下一次机会’,正因为如此,清末的学堂制度不存在对功名追求者的挫折感的自我消解机制”*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这使学生的社会出路问题变得显性化和急迫化。
再者,由于办学仓促,资金、师资和规范都难以到位,新式学堂教育无法使人才由文化人迅速转化为专业技术人才,而当时尚不发达的现代部门也无法安置大量的学堂毕业生。其一,朝廷既以利禄之途诱导学堂兴办,学堂办学和学生自然也自觉不自觉地奔着仕途去。相对于实业学堂来说,法政学堂畸形繁荣。据统计,1912年,法政毕业生有5115人,占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8326人的61.55%。*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其二,仓促办学也难以保证教育质量,新式学堂并未能迅速造就大量可用之才。学生仅仅“会些个光线力点的新名词,别的全不会”,因此工商界“全都无法位置”。*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傅斯年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承袭科举制造游民,效能更大。学校越多,游民越多;毕业之后,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只有过其斯文的游民生活,而怨天怨地。”*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其三,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现代部门并不发达,所以社会对新式人才的吸纳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大量学堂毕业生找不到社会出路。比如,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200余人,“在军界授职任事者十不二三,而大半投闲置散”。此外,警务、师范等类别的毕业生也难以得到合理安排。可谓一开始就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危机。*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414-415页。可见,“新式人才”的供给大大超出了当时中国现代部门的吸纳能力,于是供求失衡问题在社会层面爆发出来。
最后,大量毕业生难以在城市现代部门中谋得生路,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愿甚或很难再回到乡村。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使社会上升途径多集中于城市,乡村社会对他们不再具有耕读时代曾经具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群体在接受新式教育后与乡民之间出现了文化上的隔膜,很多人不再认同于乡村。*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考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社会中的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难以在城市谋生,也难以回到乡村社会的大量知识分子沦为“边缘知识分子”,他们无法成长为带动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坚,而是纷纷涌向政治领域。无法找到满意社会出路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别不安分的群体。“尖锐的地位矛盾(教育界域高而职业界域低)强化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如不彻底改造社会,就只能自生自灭。这使学生及新知识群的破坏性功能超常发挥,而建设性功能受到抑制。”*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416页。事后看来,“常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固然成了‘鬼蜮’,而失去知识阶级的农村也变成了‘地狱’。两者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双方的结合为后来中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资源”*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社会中的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四、废科举产生重要意外后果的理论解释
废科举导致重要的意外后果,正如《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所评价的:“取消科举制度的行动破坏了2000年来通过许多步骤才得以巩固的社会统一的根基。这一行动逐渐产生的始料不及的后果,比发动它的那些士大夫在1905年公开预见的所有后果都重要得多。”*[美]吉尔伯托·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陶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9页。出路拥堵问题的显性化和爆炸性释放无疑就是这项制度变革所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后果。有意图的社会行动(包括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会导致出乎行动者意料的社会后果,这种现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政治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前者来说,社会科学需要去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行动者的目标与行动的后果之间往往并非线性的关系,而是会衍生出非常复杂甚至是失控的后果?就后者来说,社会政治实践尤其是制度改革需要去应对这一问题: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以使制度改革能够实现改革者的意图?实践问题往往涉及相应情境和约束条件,涉及实践智慧的运用和具体的技术操作,但理论研究还是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些一般性的启发。
那么,废科举这一个案对于我们理解制度改革的意外后果问题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启发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先对“制度”的内涵稍作阐释。在社会科学中,“制度”(institution)的定义颇为复杂,就本项研究来说,可以将制度定义为一系列相关规则的集合。而相关规则与相应社会实体在运作过程中则形成一种“体系”、“体制”或“系统”(system)。比如科举制度实际上包含一系列的相关规则,包括报考规则(如怀牒自举)、监考规则(如搜身以防怀挟)、阅卷规则(如糊名誊录)、录取规则(如各级考试的录取名额分配)、铨叙规则(如通过礼部掣签授官)、保障规则(如对舞弊者的重罚)等。制度改革则是对其中某些规则或整套规则的改变,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就是对相关规则作了根本性的变革。
一般来说,当制度改革并非用来确认“诱致性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是林毅夫所提出的一种制度变迁划分方式,参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美]罗纳德·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的结果,而是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推进以实现改革者的某种目标时,它就具有很强的人为设计性,会受到改革者主观因素的强烈影响。*这里所说的“改革者”是一种拟制的主体,它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具有核心决策权力的人,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制度设计都受到个体或群体认知因素(主观模型)的深刻影响。改革者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涉及理性运作的两个层面:一是其试图达到的目标,这是目的理性层面,它决定了制度设计的意图或方向;二是对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认知,这是工具理性层面,它决定了制度设计的方式或方法。制度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新的制度规则取代原有制度规则以实现改革者的意图。制度规则变了,相关的激励与约束结构也会变化,据此人们会去追逐新的获利机会或规避不利后果,因此,改革者可以通过改变制度规则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以实现其所意图的目标。
不过,制度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后果不一定会完全符合改革者的意愿。制度运作过程是嵌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它与各种结构因素网织在一起,因此相关个体的行为选择及其复杂的衍生后果并非单一地受到局部制度规则调整的影响,而是受到各种既有结构因素的制约。这些结构因素从大面上说包括配套的制度结构、权力和利益结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非正式约束、政治体与外部行为体的关系等。有些重要的制度甚至能形塑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形态,科举制度即属此类,以至有人称中国传统社会为“士绅社会”“选举社会”。就这类制度的改革来说,很多结构因素都会以复杂微妙的方式影响到个体的微观选择和制度运作的现实逻辑,这中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和非线性反馈机制往往会超出改革者的预料和控制。不仅如此,科举制度变革适逢古今中西交汇碰撞之际,要深度透视这一历史事件还需将其放到“古今”“中西”纵横两维所构建的坐标系中加以定位。古今维度反映的是科举改革背后涉及社会转型问题,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问题;中西维度反映的是科举改革涉及跨文化学习问题,即改革者致力于学习移植西方的新式教育制度的问题。在古今中西交汇碰撞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深刻地影响了科举改革,由此也为我们理解制度改革的意外后果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启发:在跨文化学习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制度改革可能会因为认知上的偏差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而引发重大的意外后果。
具体说来,废科举是一项由权力中枢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改革,这种通过顶层设计推进的“强制性变迁”受到改革设计者自身认知因素的强烈影响。而跨文化学习过程更是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认知难度,因为这时不仅仅涉及对自身(学习主体)的认知,还涉及对他者(学习对象)的认知,并面临着如何将他者的经验恰当地运用于自身这一问题。在当时改革者的话语中,学堂育才、取才既是古学校之制,又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因此,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就既是托古改制,又能收到“富强之效”。*如梁启超曾详细、明确地阐述了革废科举的上中下三策。其中上策就是“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0页。)清廷废科举的上谕也认为:“三代以前,选士皆由学校,而得人极盛,实我中国兴贤育才之隆轨,即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亦无不本于学校……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65页。)但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准确。传统的“学校”(官学)与西方的“学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方面,传统官学是为国家育才,为官僚机构提供后备人选,到明清时期官学甚至已经完全依附于科举*田建荣:《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迁》,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3页。,其办学规模非常有限;而西方的学校是为社会育才,是大众教育。另一方面,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和选官体系不同,在西方社会中学校教育与文官考试、官员选举是分开的,学生毕业后主要是进入市场分工体系择业。在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的前提下,清末改革者直接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这显然是一种“错位嫁接”的做法,并且在本质上也没有摆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如前所述,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功名授予的泛滥和仕途惊人的拥挤。因此,改革者在跨文化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认知错位是导致科举改革产生意外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认知因素之外,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要更为深刻。科举改革决不仅仅局限于时人所关注的教育转型,而且涉及深刻的社会转型,即从一元化色彩比较显著的中国传统社会转向现代多元社会。在科举体系下,社会上升渠道、人才结构都具有显著的一元化特征,社会的结构功能分化不明显。一是功名利禄这种传统社会中最优质的资源及相应的社会上升渠道垄断于国家手中,导致大量精英人才被吸引到科举一途。二是科考内容和取士标准也掌握在国家手中,考试内容和取士标准的单一性导致依附于科举体系的精英人才在知识结构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三是在传统中国政教紧密相连,科举则上系国家政教,下系士绅社会,集政治、社会、文化等功能于一体。而与传统文明碰撞的西方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多元社会。一是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优质社会资源不再被单一的中心所掌控,社会上升渠道非常多元化。二是伴随着专业化分工、科技进步和大工业生产,人才的知识结构趋于多元。三是西方现代社会在结构功能上显著分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子系统都分化开来并各自有比较自主的运作逻辑。因此,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精英人才的分化和分流是科举改革需要应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但当时中国尚不发达的现代部门根本无法消化与日俱增的“新式人才”,大量新式学堂毕业生难以融入既有社会结构之中,反而从中游离出来,最终只能通过先破而后立的方式再从边缘回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