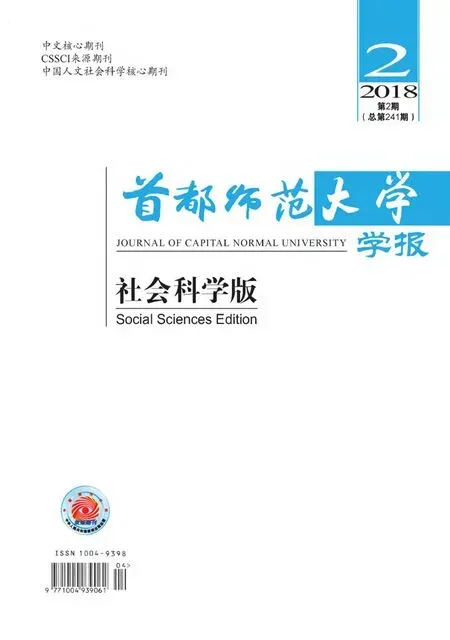成年人监护类型解析
王竹青
成年人监护是对意思能力欠缺的成年人给予保护的法律制度。从监护的发生原因来看,主要包括智力障碍和精神障碍。智力障碍既有先天性的智力不足,如唐氏综合症,也有后天因创伤或老化引起的智力衰退。精神障碍一般发生在后天的比较多,先天性精神病非常少。从监护对象来看,主要包括残疾人(主要指智力障碍者和精神障碍者)和智力衰退的老年人,这两个群体有交叉的部分,比如有些残疾人是老年人,有些老年人是残疾人。之所以强调监护对象的区别,在于现代监护制度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保护措施有所不同。针对这两个群体的不同特征,各国监护制度以不同类型、不同理念和不同原则做出了不同的规定。总体来看,无论是精神障碍还是智力障碍,影响的都是人的意思能力,即人的判断和决定能力,因此现代世界各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改革均围绕尊重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自主决定权展开。
一、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发展轨迹及新型监护模式的出现
监护制度自罗马法时期即以某种形式存在。13世纪之前的英国,监护是国王的责任。*D Surtees. How Goes the Battle? An Exploration of Guardianship Reform. Alta L aw Review,Vol.50,Issue 1(August 2012):117.监护的内容只是财产,不包括人身。监护对象仅限于痴呆者(idiots or fools)和精神错乱者(lunatics)。对于精神错乱者,法律认为其有恢复意思能力的希望,*Louise Harmon. Falling Off the Vine: Legal Fictions and the Doctrine of Substituted Judgment. Yale Law Journal,Vol. 100,Issue 1(October 1990):16.因此国王以代理人的身份管理其财产,不得获取其收益。如果精神错乱者恢复了意思能力(无论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其财产及其收益需返还给本人。对于痴呆者,法律认为其从未有过意思能力,也没有获得意思能力的可能,因此其财产由国王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基于其财产的收益归国王所有,国王只负责对其提供必须的生活条件,不得浪费或损害其财产。在其去世后,国王负责将财产交给其继承人。国王对痴呆者或精神错乱者的监护责任由上议院的大法官代为履行(后来由衡平法院的法官代为履行)。*Joseph Story. Commentaries on Equity Jurisprudence: as Administered in England and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1877∶608.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对痴呆者和精神错乱者的差别待遇逐渐消失,对痴呆者的管理标准逐渐与精神错乱者趋于一致。监护内容也从单纯的财产管理扩展到人身照顾。从14世纪开始,国家亲权的理念开始进入监护制度,对弱者的保护成为国家的权力和责任。“国家亲权”理念随后传入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大陆,成为盛极一时的监护理论。国家对心智障碍者进行保护的基本原理是对心智障碍者的保护并不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而是为了心智障碍者本人的福祉,他们必须由国家亲权给予保护。“国家亲权”最初适用于儿童,后来扩展适用于精神病人。在必要和适当的程序保护下,法庭可以决定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即使在病人拒绝接受这种治疗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法庭同样可以剥夺老年人对自己的财产和人身事务的决定权。*Peter M. Horstman. Protectiv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The Limits of Parens Patriae. Missouri Law Review,Vol.40. Issue 2(Spring 1975):231-232.此外,法庭还享有对精神障碍者的医疗决定权,包括做出结束生命的决定。*See Superintendent of Belchertown State Sch. V. Saikewicz, 370 N.E. 2d. Mass.(1977):417. (法庭在考虑是否要对一名精神障碍者做出撤掉维持生命的治疗设备时谈到:对于这个困难的、令人敬畏的问题,我们不仅仅从司法的角度进行考虑,因为它构成医学专业领域的“无端侵犯”。生命和死亡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独立、审慎的调查和决定,以达到司法应该实现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我们高级法院以及下级法院的责任,我们不能轻信其他声称代表社会道德和良知的组织,不论其动机多么高尚或者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多么深刻。)可见,“国家亲权”的管辖范围非常大,包括人身、财产和医疗健康,基本涵盖了人权的所有领域。
由法庭任命监护人替代心智障碍者做出决定是从“国家亲权”衍生出来的法律实践。在20世纪中期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之前,“替代决策”一直是成年人监护的指导思想。大陆法系国家的成年人监护制度首先对心智障碍者进行禁治产或准禁治产宣告(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宣告),然后为其指定监护人。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在宣告范围内丧失一切权利,相关事务由监护人代为做出决定。即使被监护人保留一定的意思能力,在宣告范围内其做出的决定也不具有法律效力。被监护人享有的权利仅类似于5岁儿童所拥有的权利。*Fred Bayles & Scott Mc Cartney. Guardians of the Elderly: An Ailing System Part I: Declared “Legal Dead” by a Troubled System,Associated Press,(Sep. 19,1987).
随着人权观念的提升以及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与尊重,自20世纪中期开始,对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改革成为席卷世界的一股潮流。改革针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不同特点,创造了不同的法律制度,形成了“以人为中心”、“尊重自我决定权”、“活用残存能力”、“维持生活正常化”等一系列先进的理念和价值观,使老年人、残疾人的权利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针对老年人的监护制度改革发源于美国弗吉尼亚州。1954年,弗吉尼亚州对传统代理制度进行了改革,创设了充分体现“自主决策”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根据普通法,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权利在委托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终止。委托人的无行为能力状态自动产生终止代理关系的效果,因为代理制度存在的假设前提是委托人有能力指导代理人的行为,而且委托人有权随时终止代理关系。委托人的无行为能力状态致使这两个关键要素均失去意义。针对传统代理制度的局限性,美国弗吉尼亚州法规定,如果代理协议写明代理人的权利在委托人丧失行为能力后持续有效,那么代理人的权利不因委托人丧失行为能力而终止,*1954 Va. Acts ch.486, codified at Va. Code Ann. §11-9.1(2001).由此创设了影响世界各国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其他英美法系国家也陆续建立了该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形式转变,日本和韩国的任意监护制度、德国的预先授权制度均来源于此,中国称其为意定监护制度。该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本人在有意思能力时为自己选任监护人,并将自己的人身照顾和财产管理等事宜委托给监护人,待自己丧失意思能力后,由监护人按照本人的意愿处理相关事宜。*王竹青:《意定监护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0日第6版。该制度主要适用于老年人,由完全有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在精神健康时为自己选择代理人,并对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智力衰退、老年痴呆等问题提前做出安排。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对老年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因此从其出现开始即迅速被世界很多国家所采纳。
针对残疾人的监护制度改革以支持决策(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or Assisted Decision-Making)为主要表现形式。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决策开始在加拿大的实践中出现,*A. Frank Johns. Person-Centered Guardianship and 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 An Assessment of Progress Made in Three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ging Law & Policy,Vol.9(2016):11.这被认为是监护领域针对残疾人权利保护进行改革的最早法律实践。支持决策是为响应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的要求在监护领域出现的新理念和新措施,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残疾人与正常人一样享有对自己事务做出决定的权利,亲属、朋友、社会组织等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使残疾人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偏好,并使其愿望和偏好得以实现。支持决策受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大力倡导与推行,并成为衡量缔约国残疾人权利保护水准的重要指标。很多国家基于支持决策的法律精神创建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如瑞典的“神人”(God Man)制度,加拿大的代表协议(Representation Agreement)制度,美国的支持和服务(Supports and Services)协议制度,德国照管制度中的“必要性原则”、日本的保佐制度等,均以支持和帮助残疾人自主做出决定为主要内容。中国目前尚没有与支持决策对应的法律制度,在未来《民法典》的成年人监护制度设计中,应考虑将支持决策进行本土化改造,纳入中国的监护法律体系。
随着支持决策的出现和发展,传统监护制度的指导原则替代决策受到排斥和否定,替代决策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监护领域的热点问题,下文的分析中会对此进行深入讨论。
二、意定监护与自主决策
(一)意定监护初期的立法特点及缺陷
意定监护是为应对老龄社会而产生的新的监护类型。发达国家的立法模式虽各有不同,但核心内容基本相同,即以委托代理协议为载体,以本人对自己丧失行为能力后的生活照顾及财产管理安排为主要内容,由本人选择代理人(意定监护人)执行协议内容,协议通常以本人丧失行为能力为生效要件。
意定监护发源于美国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持续性代理权针对传统监护制度的主要缺点而产生。传统监护的公示制度导致被监护人及其亲属极易遭受歧视和侮辱;经过法定程序由法庭任命监护人,导致时间长、成本高等问题。对此,《持续性代理权法》规定,持续性代理协议由当事人双方签署,无需登记与公示,协议签署后即可生效或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生效时间。由此,保护隐私、简易、低成本成为持续性代理权的显著特点。*Rebecca C. Bell. Florida’s Adoption of the Uniform Power of Attorney Act: Is It Sufficient to Protect Florida’s Vulnerable Adults? St. Thomas Law Review,Vol.24,Issue 1(Fall 2011):49.因持续性代理权完全尊重委托人的意愿,因而被认为是保护和实现委托人自主决策权的有效法律措施。
但持续性代理权的上述优点极易导致代理人滥用代理权,尤其是代理人极易侵占委托人的财产。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老年人利益倡导者开始关注持续性代理权对老年人的经济剥削,以下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一:76岁的路易斯独自生活,在教会认识了凯特琳和罗伯特夫妇。路易斯授予这对夫妇持续性代理权。后路易斯患上老年痴呆症,凯特琳和罗伯特夫妇陆续取走路易斯的存款84000多美元。*Press Release,Pa. Office of Attorney Gen.. Attorney General Corbett Announces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a Schuylkill County Couple Accused of Stealing More Than $84,000 From an Elderly Man,(Nov. 29,2007).http://www.attorneygeneral.gov/press.aspx?id=3159.
案例二:87岁的伊丽莎白授予其子持续性代理权,代为管理她的财务,后来其儿子将225000美元转到了自己的账户。*Toddi Gutner, “License to Steal” From Seniors, Bus. WK.,June 5,2006. http://www.businessweek.com/print/magazine/content/06_23/b3987113.hhn?chan=gl.
上述案例仅是冰山一角,美国2004年在19个州进行的有关老年人受骗的调查发现,有52000件关于老年人遭受经济欺诈的投诉,*Pamela Teaser et al.. The Nat’l Ctr. On Elder Abuse, The 2004 Survey of State 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 Abuse of Adults 60 Years of Age and Older,(2006):5-6.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更庞大的未上报的老年人受虐待的案例。
持续性代理权人对老年人进行经济剥削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澳大利亚的实践也证明老年人受到持续性代理权的经济剥削是一个严重且普遍存在的问题。*Paul Blunt. Financial Exploitation of the Incapacitated: Investigation and Remedies,Journal of Elder Abuse and Neglect,Vol.5(1993):19.由于任命持续性代理权人的非正式性以及缺乏监管,使老年人极易受到经济剥削。不断增长的经济剥削案例说明持续性代理权是对老年人的威胁。但是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持续性代理权对实现老年人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仍然是受老年人欢迎的法律工具。美国退休人员协会2000年做的一项调研发现,50岁以上的美国人45%都启用了持续性代理权。*Nina A. Kohn. Elder Empowerment as a Strategy for Curbing the Hidden Abuse of Durable Powers of Attorney, Rutgers Law Review,Vol.59,Issue 1(Fall 2006):7.1990年4月加拿大魁北克省开始实施预防性监护委托,截至2005年7月,魁北克共计办理了100多万份监护委托书,而魁北克的人口仅有700万。*[法]蒂芙尼·阿提亚:《意定监护制度》,上海中法公证法律交流培训中心《通讯》,2017年第61期,第21页。http://www.cnfr-notaire.org/admin/Uplmages2/2017091710072632380.pdf.澳大利亚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1年6月30日至2011年6月30日,65岁以上的人口增长了13.7%。澳大利亚统计局预测,到2056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6百万,*Se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September 2009.很大比例的老年人将失去他们的决定能力,使用持续性代理权的人数将不可避免地增长。持续性代理权的广受欢迎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各国立法者将关注重点转向弥补缺陷、完善保护措施等方面。
(二)意定监护近年来的立法完善与发展
1.英国《意思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2005年4月7日,英国《意思能力法》得到皇家批准生效。针对老年人的经济剥削问题,《意思能力法》创设了公共监护办公室,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对永久性代理权(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进行登记备案。永久性代理权必须在公共监护办公室登记后方可生效,登记可以由委托人在创设代理权时进行,也可以由代理人在任何时候进行。*Dep’t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Code of Practice,2007∶116.法律鼓励当事人提早进行登记,因为那样有助于在当事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而帮助代理人在委托人丧失行为能力后更好地为其做出决策。
根据《意思能力法》,创设一个有效的永久性代理权,委托人必须填写由公共监护办公室提供的特别表格。在登记之前,委托人必须签订一份说明以证实自己明白代理权的内容,并在自己失去行为能力时启动代理权。代理人也要签订一份说明以证实其阅读了文件并明白自己的职责。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签名必须有证人在场。委托人一旦申请登记永久性代理权则必须在文件中指定应该接到通知的人。此外,独立的第三方应该填写一份说明书,证明在他们看来,委托人明白永久性代理权的目的,没有人用欺诈或胁迫的手段哄骗或迫使委托人创设永久性代理权,也没有任何情况可以阻碍委托人创设永久性代理权。*Dep’t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Code of Practice,2007∶116.
公共监督、登记、证人、通知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老年人虐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美国最初创设的持续性代理权相比,英国《意思能力法》加强了公共权力(公共监护办公室、监护法院)及私人力量(证人、被通知的人)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保护,这些主体的介入对于丧失行为能力、处于弱势状态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必要的。
2. 法国的意定监护
法国的意定监护制度于2007年3月5日颁布,2009年1月1日生效。该法涵盖人身保护和财产保护两个方面,其中人身保护包括特殊医疗指示。意定监护以监护委托书为表现形式,委托书可以是私署文书或公证文书,但经过公证的委托书可以赋予受托人更多权利。*③④ [法]蒂芙尼·阿提亚:《意定监护制度》,上海中法公证法律交流培训中心《通讯》,2017年第61期。http:// www.cnfr-notaire.org/admin/Uplmages2/2017091710072632380.pdf.监护委托开始时,受托人必须制作财产清册,并且在委托执行过程中要不断更新这份文件。受托人每年需制作年度管理账目,在委托任务完成时需制作最终管理账目,并提交给公证人(如果监护委托是私署文书,账目需提交给监护法官)。公证人对管理账目和受托人完成的任务进行查验,如发现有任何无法解释、不符合委托书条款、违背受托人利益的行为或资金流动,则需要申请监护法官介入。③
法国的意定监护突出了法院的监督作用。监护法官在下列情形将介入意定监护关系:(1)任何一位利益相关者提出请求;(2)受托人出售、签署或终止与委托人主要住宅及其动产相关的租赁合同;(3)受托人实施无偿处分行为;(4)赠与;(5)放弃受惠继承;(6)和人寿保险相关的交易;(7)更改银行账户的户名。任何相关人员可对意定监护委托的执行提出异议,法官在接到异议申请后,如果发现委托人的财产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则可以排除委托,转而采取法定监护措施,此时意定监护自动终止。如果法官认为意定监护仍可持续,但需要就缺陷部分予以弥补,则可以附加保护措施,此时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同时存在。法官也可以指定一名受托人,对意定监护未覆盖的部分进行保护。④
法国的意定监护在监督方面与法定监护的监督手段相似,因此对限制受托人滥用权利、保护委托人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针对老年人的虐待和剥削行为。
三、辅助与支持决策
辅助主要是针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精神障碍者、智力障碍者,统称为心智障碍者)的保护措施,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该制度的名称各有不同,大陆法系的日本称为保佐,韩国称为限定监护,中国台湾地区称为辅助。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应法律形式本文第一部分有所提及,在此不赘。正如前文所述,支持决策是针对残疾人权利保护而出现的新的监护理念,通过对心智障碍者提供支持和帮助,使其对生活照顾、财产管理以及医疗健康等事务表达明确的意愿和偏好,并在他人的帮助下实现这些意愿和偏好。支持决策针对替代决策而产生,强调支持者对心智障碍者提供支持和帮助,以使心智障碍者自己做出决策而不是由支持者完全替代其做出决策,以此来保护心智障碍者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因此,支持决策是辅助制度的指导思想。
(一)支持决策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目前国际社会对心智障碍者的保护主要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2条为指导思想。《公约》的核心是尊重人的自主决策权,承认自主决策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基本保证。《公约》载明,对于残疾人而言,独立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自主做出决策的自由——残疾人应该有参与做出决策的机会。
《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在生活的各方面享有法律能力。法律能力是拥有权利和义务以及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参见《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二部分:第十二条的规范内容,第十二条第二款。即中国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意见》同时指出,心智能力是指一个人的决策技能,“心智不全”和其他歧视性标签不是剥夺法律能力的合法理由。缔约国有义务对残疾人在行使法律能力时所需要的协助提供支持,在为残疾人提供协助时,必须尊重残疾人的权利、意愿和选择,不得以协助取代决策。*参见《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二部分:第十二条的规范内容,第十二条第三款。《意见》认为,每个成年人均享有行为能力,在其因残疾而不能自主做出决策时,国家应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帮助其做出决策。该观点被凝练为“支持决策”,成为发达国家成年人监护领域的最新指导思想。
虽然《公约》强调每个成年人均享有行为能力,但事实上植物人、严重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没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适用支持决策显然是困难的。从尊重和贯彻执行《公约》的精神出发,除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以外,其他智力障碍者应均可适用支持决策,无论其残存的行为能力有多少,都应尽可能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以使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生活。
(二)辅助制度对支持决策的体现
辅助制度的重点在于如何体现支持决策。英美法系国家大多以协议的方式在心智障碍者与支持者之间建立辅助关系,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辅助协议与委托代理协议相似,由心智障碍者作为委托人将特定事项委托给支持者,支持者通过与心智障碍者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心智障碍者的真实意愿,并代表(而非代替)心智障碍者就委托事项做出决定。与委托代理的不同之处在于,辅助制度承认心智障碍者的主体地位,即便其行为能力有缺陷,其委托也是有效的。从这个层面来看,辅助具有意定监护的特点,只是意定监护的主体是完全行为能力人,而辅助的主体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主动进入辅助关系而非被动进入监护关系,是法律对心智障碍者人格的一种肯定,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
在心智障碍者非主动进入辅助关系的情况下,法庭在基于申请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进行审判时,应考虑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鼓励心智障碍者参与决策过程,尽可能使其表达自己的意愿与偏好,充分尊重当事人做出的意思表示,并在判决书中载明心智障碍者需要辅助的事项,以及辅助人应尽可能与心智障碍者沟通、帮助心智障碍者做出决定等内容。在美国的M.R. 案中,法庭认为,一个人在总体上没有能力并不意味着其在所有事情上均没有判断能力——一个总体上没有能力的人仍然可以在具体事情上做出选择。根据本案的事实,一个没有能力管理自己事务的人,仍有决定自己的住所以及与谁住在一起的能力——对住所的选择,如果是错误的,很容易被纠正,因此对住所选择权的尊重是更为重要的价值取向。我们的目标是允许发育障碍的人尽可能多地为自己做决定,同时保护他们免受因不理解而做出的错误决定的伤害。*M.R.是一名唐氏症患者,且伴有中度智力障碍。她的母亲是她的监护人。当她表示希望和父亲一起居住生活时,她的母亲予以拒绝,并认为她缺乏做出决定的能力。她的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638 A. 2d. N.J.1994∶1274-1282.
辅助制度强调“尊重”心智障碍者的意思而非“考虑”心智障碍者的意思。韩国新成年人监护制度因规定家事法院在审判时应“考虑”本人的意思而受到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批评,委员会认为“考虑”仍然是替代决策的技术手段,未能体现支持决策的法律精神。*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omm.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repor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21-22 at 4,U.N. Doc. CRPD/C/KOR/CO/1,Oct. 29,2014.委员会对这一关键词语的强调,为辅助制度的立法提供了标准。
(三)辅助制度的保障措施
辅助制度的对象是心智障碍者,尽管其保有部分行为能力,但毕竟与完全行为能力人不同,因此对辅助人的辅助行为需要外界力量的监督。在本人以协议的方式设立辅助的情况下,可参照适用意定监护的监督措施。在法院指定辅助人的情况下,可参照适用法定监护的监督措施。尽管在设立辅助关系时立法态度是宽松的,以尽可能多地给予心智障碍者自主决策的空间,但是在对辅助的监督上,立法态度必须是严谨、苛刻的,如此才能保障心智障碍者的权利不受侵害。
四、监护与替代决策
(一)监护的适用范围
从发达国家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改革成果来看,各国普遍认为监护是保护心智障碍者的最后手段,即当事人在有完全行为能力时未设立意定监护,在有部分行为能力时未建立辅助关系,在其完全丧失行为能力时,方可适用监护;对于从未有过行为能力的人,可适用监护。
尽管《公约》强调每个人均有法律能力,包括行为能力,但事实上无行为能力人是客观存在的。各国立法为适应《公约》的要求,在用词上尽量回避无行为能力的表述,如德国《民法典》第1896条表述为“成年人因精神疾病或者身体、精神或者心理障碍而不能处理其全部事务的”。日本《民法典》第7条规定监护的适用对象为“因精神上的缺陷而缺乏对事务的判断能力且处于常态的人”。韩国的表述与日本类似。各国法律对“无行为能力”词语的回避,一方面体现了对《公约》的尊重,另一方面更体现了对心智障碍者的尊重。但是,尽管各国在法律条文中成功地回避了这一词语,但在学术文献中“无行为能力”依然是频繁出现的词语,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这个词语是讨论监护制度的基础。笔者认为,对“无行为能力”词语的回避不意味着对“无行为能力制度”的回避,监护制度对行为能力补足的功能依然未改。因此,至少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理论研究,“无行为能力”与监护的关系都难以割裂。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期待未来人类的智慧在此领域有更大的发展。
(二)对替代决策的争议及其标准的转变
可以说,监护是保留传统监护特征的唯一领域。在传统监护中,替代决策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即由监护人根据被监护人能力受损之前的语言、行为等可作为判断依据的事实,揣摩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并代替当事人做出决定。这种决策机制在《意见》中受到全面否定,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认为监护人在揣摩被监护人意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加入其主观感觉和判断,因此替代决策侧重于监护人的感受而非被监护人的意愿,有可能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委员会要求各缔约国采取行动制定法律和政策,更换替代决策机制,采取支持决策机制,以尊重被监护人的自决、意愿和愿望。《意见》同时指出,在发展支持决策机制的同时,维持一个平行的替代决策机制是不足以遵守《公约》第12条的。*参见《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三部分:缔约国的义务。
除对替代决策的否定外,《意见》同时否定了与替代决策密切相关的“最大利益”原则。在《意见》出台之前,最大利益原则一直是成年人监护的重要原则。但《意见》第12条第四款彻底否定了最大利益原则的适用。《意见》要求,在做出重大努力后,仍无法确定个人意愿和选择时,必须以“对意愿和选择的最佳解释”来取代“最大利益”。《意见》认为,“最大利益”原则并不符合第12条的保障措施,“意愿和选择”范式必须取代“最大利益”范式,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法律能力。“意愿与选择”范式与“最大利益”范式的区别在于:“意愿与选择”范式强调了以“被监护人的主观意愿为中心”的现代监护理念,而“最大利益”范式是以“客观结果”为中心。这种侧重点的转移体现了法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以及对残疾人权利保护认知的进步。
尽管《意见》对替代决策机制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但缔约国并未完全采纳该观点。理论上,支持决策是对于有部分行为能力人适用的一种保护措施,对于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人难以适用。因此,尽管《意见》以高度赞成的态度推广支持决策机制,但缔约国仍保持审慎的态度。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均在《意见》出台后保留了替代决策机制,只是在适用上以“对意愿和选择的最佳解释”标准取代了“最大利益”标准。澳大利亚的学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监护人或保护人替代完全没有意思能力的老年人做出决定,例如处于植物人状态的老年人,在没有做出预先指示的情况下,则需要监护人对重要的治疗行为做出决定。*Generally Queensland Government,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to Tribunal Appointments,28 August 2014.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区分支持决策和替代决策是困难的,二者的界限是模糊的。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的意愿和其最大利益是一致的。昆士兰州的监护人有权替代被监护人做出决策,但监护人行使权利必须符合被监护人的意愿。*Guardianship and Administration Act 2000,Qld.,sch1.可以说,澳大利亚的立法态度更为客观、更加符合社会实际需要。尽管《公约》强调每个人均有法律能力,但现实生活中无行为能力人确实存在,法律在对待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态度上应有所区别,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措施,更好地保护每一个人。尊重客观事实应该是立法的基本态度。
五、中国未来成年人监护类型设计的立法重点
中国正处于《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对社会弱者的保护措施,无疑是《民法典》的立法重点之一。新近实施的《民法总则》对监护制度作了概括式规定,其中第28条和第33条分别规定了成年人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但这只是提示性条款,具体化、体系化的立法设计将由婚姻家庭编完成。对成年人监护作类型化处理是婚姻家庭法学者的共识,重点在于监护类型的设计以及指导思想的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只有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吸取立法教训,体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立法精神,才能制定出先进、科学、人文的法律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对弱者的法律保护。
(一)意定监护的立法重点
就意定监护而言,应体现自主决策的指导思想。意定监护是对传统代理制度的变革,其重点在于将代理权的效力延伸到本人丧失行为能力之后,但代理制度由委托代理协议和单方授权行为构成的特征未变,而且这一特征在意定监护中尤为重要。意定监护关系的建立需要由本人和其选定的监护人进行协商,以确保选定的监护人愿意承担监护职责,但本人授予监护人哪些权利,应由本人单方做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主决策的指导思想。在设计意定监护制度时,应充分注意到其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老年人在年老体弱时,很难不受制于人。意定监护只能是单方授权行为,才能实现本人的意思自治。*王竹青:《意定监护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0日第6版。因此,除意定监护关系的建立需要由本人和其选定的监护人协商外,监护内容的确定、监护方式的实施等,均应由本人确定。
为确保本人的意思自治得以实现,监护监督不可或缺。因意定监护通常在本人丧失行为能力后开始生效,因此对本人的保护主要依赖第三方的监督和救助。为便于第三方发挥作用,意定监护设立时的公证、登记、通知等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住所的改变、重要财产的处分、重大医疗救治行为的决定,应征得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同意。如此,通过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介入,可以有效地保障本人的自主决策得以实现。
(二)辅助的立法重点
辅助制度的设计应体现支持决策的指导思想。辅助制度的适用对象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辅助的目的是通过支持和帮助,使本人的残存能力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为自己的生活安排、财产管理等事项做出决策。因此从本质上看,支持决策只是手段,实现本人的自主决策才是目的。
从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立法来看,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协议的方式体现意定辅助的特点,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以法律规定的方式体现法定辅助的特点。中国应吸取两大法系的法律精华,辅助制度的设计可兼具意定和法定的特征,以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监护类型。
意定辅助的设计应当允许本人自己选任辅助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通常可以表达自己的喜好,特别是对自己信赖的人更容易表达情感和需求。因而由本人选任的人担任辅助人,更容易对本人提供支持和帮助,从而使本人在更大程度上做出决策。至于辅助的内容,可以采纳英美法系国家的协议形式,由本人和辅助人协商确定。需要注意的是,意定辅助与意定监护不同,意定监护中的本人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因此制度设计以单方授权的代理制度保护本人的自主决策权。而辅助中的本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有单独做出决策的能力,需要在辅助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决策行为,所以意定辅助无论是辅助关系的建立还是辅助内容,均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
法定辅助适用于本人未主动选择辅助人的情况。在相关人员向法院申请指定辅助人时,法院应首先让本人做出选择,在本人无法或不能做出选择时,法院应根据相关证据材料,选择最能理解本人、最容易与本人沟通的人作为辅助人。关于辅助的内容与方式,应尽可能尊重本人的意愿。
鉴于辅助制度的适用对象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对自身事务的保护能力存在缺陷,因此对辅助行为进行监督是必要的。在监督措施上,适用于意定监护的登记、公证、通知等程序同样可适用于意定辅助。对法定辅助的监督可适用监护监督的相关规定,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介入也是必要的。
(三)监护的立法重点
监护的适用对象是无行为能力人,其指导思想虽是替代决策,但替代决策的标准不是被监护人的“最大利益”,而是对被监护人“意愿和选择的最佳解释”。
监护作为最后的救济措施,其适用条件极为严格,仅适用于未建立意定监护关系和辅助关系的无行为能力人。对于尚有部分行为能力的人不能适用监护制度,即在以辅助制度能够实现对本人保护的情况下,不能适用监护制度。
从类型化角度考虑,笔者建议以“法定监护”作为对无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措施,从而在“监护”之下形成意定监护、辅助、法定监护等子类型,便于立法设计和学术讨论。事实上,现代监护制度倡导尽少适用司法程序,即心智障碍者在亲属、朋友的帮助下能够维持正常生活的,则无需进入监护或辅助程序。因此,只有监护候选人有争议时才需要由法院指定监护人。“法定监护”可特指由法院指定监护人的情形,以与“意定监护”相区分。基于同样的逻辑,辅助制度的法定和意定之分可找到理论依据。
除上述三种类型外,大陆法系的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还有第四种类型,即适用于暂时性(如由于住院治疗)或特殊性(如不动产买卖)保护的措施,法律允许被保护人因为重大损失而要求解除合同,或者因为法律行为的过度性而获得减价权,*[法]米歇尔·格里马蒂:《法国法上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保护:基本原则以及人身保护》,上海中法公证法律交流培训中心《通讯》,2017年第61期,第3页。http://www.cnfr-notaire.org/admin/Uplmages2/2017091710072632380.pdf.但该制度提供给当事人的保护非常有限,中国监护立法是否要吸收该种类型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六、余论
现代监护制度建立在自由、人格、决定权三个要素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其核心是保护个人的自主决定权。决定权的行使是“做出决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人自由的实现过程,也是个人独立人格的一种体现,因此,决定权是三个要素中的核心要素。法律要保护的客体是决定权的行使,而不是决定的内容,因此一项决定是否是“理智的”、“符合普遍标准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出决定的过程是否是个人自主意愿的表达,是否是个人在慎重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法律关注的是个人是否有自主决策的能力,对于因健康、年龄等原因导致的无法自主做出决策的自然人,法律该提供何种帮助,以实现其自主决策权。现代监护制度通过替代的或支持的决策过程,帮助心智障碍者做出决定,以实现其个人意愿。尽管这是一种社会建构,但它反映了法律尊重、保护心智障碍者的愿望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