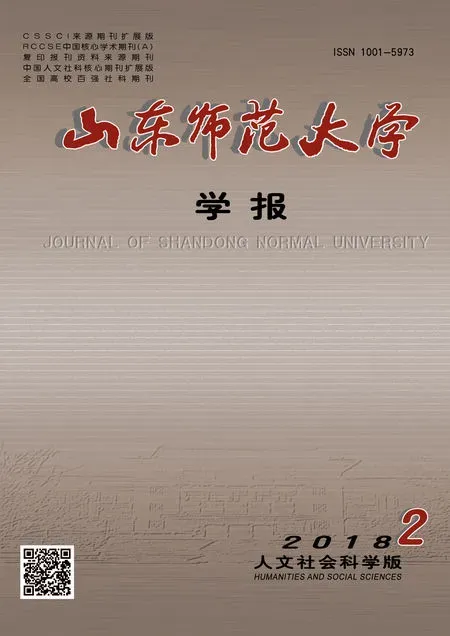女性视阈中的历史与人性书写
——以《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为例*①
刘 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
笔者在以往研究中分析过,严歌苓在像《一个女人的史诗》这样的长篇小说中,对待历史,是选取了一些特别的书写维度——女性视阈中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让她的作品溢出了以往宏大叙事所覆盖的主流历史的叙述法则。②刘艳:《女性视阈中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以王安忆〈长恨歌〉与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为例》,《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严歌苓女性视阈的历史书写,并不是将个人置于时代和历史之外,只不过是据守一方与主流历史拉开一定距离的女性生存的空间,像田苏菲的生命经历其实和历史有着撕扯不开的关系。也就是说,对待历史,严歌苓尤擅选取一些特别的书写维度,让她的作品以不同于以往主流历史宏大叙事的叙述法则,获得抵达历史的通道。
《第九个寡妇》以及其中的王葡萄,已经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③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年第5期;金理:《地窖中的历史与文学的个人——评严歌苓小说〈第九位寡妇〉》,《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等等。乡村空场上媳妇们掩护的都是八路,唯独葡萄“上前一步”“扯起”丈夫铁脑。20多年的时间里,她把公公孙怀清藏在地窖中,瞒着孙少勇把生下的孩子舍在矮庙前让来祭庙的侏儒们拣去,抚养长大。《第九个寡妇》也是从抗战写起,时间跨度几十年,这幅历经多个时期的历史画卷,是通过一个与民间地母神的形象合二为一的女性形象王葡萄来体现的,“是一部家族史、村庄史,也是一部国族史”④曹霞:《“异域”与“历史”书写:讲述“中国”的方法——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把公公在红薯窖中一藏20多年,本来“这是一个传奇式的故事坯子,严歌苓却消解了它的传奇性,把它纳入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史中,这样一种处置方式,就使得主人公王葡萄的快乐自在的民间生存哲学更加强壮”*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她基本上是以西方的价值系统来重新组织中国‘红色资源’的叙述,从而也开拓了‘红色资源’的阐释空间。”*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与其说她基本上是以西方的价值系统叙述,不如说她是在多元文化交织和错位归属的创作心态中,找到了重新进行红色叙事的方法,而如果再考虑到《寄居者》《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小说,可以说严歌苓是在摸索和寻找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她将“中国故事”在历史维度的打开和呈现,不是很多研究者所说的纯粹的“他者”叙述,“其叙述里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是可以和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叙述相兼容的”*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在历史维度打开的中国故事的叙述,是可以给中国当代文学在历史层面的叙述,提供可借鉴的价值和意义。
一、《金陵十三钗》:女性视阈中的战争历史还原
《金陵十三钗》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还原。此前,《第九个寡妇》的故事是始自抗战时期的河南农村。研究《金陵十三钗》,似乎也不能不提到《寄居者》,《寄居者》也是对抗战时期一段历史的还原。小说以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背景,美籍华裔姑娘May与奥地利的犹太青年彼得一见钟情,在获悉约瑟夫·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1941-1942年)后,她想出了一个胆大、心硬和想象力丰富的计划。她把与彼得形肖酷似的美国犹太裔青年杰克布·艾德勒从美国本土骗到上海——当然是利用杰克布对她的感情,好利用他的护照帮彼得逃出上海、前往澳门并最终转往美国。而May与艾德勒都留在了中国,却没有终成眷属。“我到现在也不能真正理解那两年我的感情是怎么回事。背叛和热恋,我在之间疲于奔命。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我。”*严歌苓:《寄居者》,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就是在这个女性形象May和她的感情故事中,呈现了抗战时期上海那一段曾经的历史,日军的残暴、日德的勾结、抗日勇士们的英勇与壮烈、犹太裔民众在上海同样遭受将被终极解决的可怕景况以及对于犹太人的拯救。所以,这部小说也被称为“沪版辛德勒名单”——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变形了的“沪版辛德勒名单”的故事,这个华裔女子要以牺牲一个爱自己的青年来救一个自己所爱的青年——这样一个有些传奇的故事。道德评判是次要的,对抗战时期上海一段历史的还原,是实实在在的。战争面前,人人无以幸免。小说中,虽然“我”在诉说着自己羡慕西摩路圣堂的诵经的声音“像是低低煮沸的声音”“熬得所有分歧都溶化”:“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溶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严歌苓:《寄居者》,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其实,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小说中无论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上海人、苏北人、客家人,在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乃至殒命的命运。小说中写到“我”10岁那年看“老中国佬”处死一条活鱼,活鱼的心脏被放到鱼的脸庞旁边,鱼扳动身体,渐渐死去,心脏却还在强有力地搏动,以此来隐喻:“整个犹太难民社区,两万多手无寸铁的肉体和心脏,在更加巨大的掌心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严歌苓:《寄居者》,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200-202页。但是,《寄居者》虽然被认为“是作者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的令人激动的尝试。同时,故事延续了严歌苓独特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严歌苓:《寄居者》,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封底)。,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第一人称“我”叙述,较少叙述视角的转换和限制性叙事策略的使用,这部小说在故事的事件和实存的话语呈现方面,不如《金陵十三钗》;在历史与人性的书写方面,也不及《金陵十三钗》那般震撼到让读者锥心的疼痛。
《金陵十三钗》运用女性的视阈,还原南京大屠杀的那段惨痛的民族历史。战后“我的姨妈”孟书娟搜集的资料浩瀚无垠,她“看到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亡城时自身的坐标,以及她和同学们藏身的威尔逊福音堂的位置”*严歌苓:《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这个教堂,是16个女孩子(小愚父亲接走小愚和她的两个同学后,剩13个女学生)和秦淮河14个窑姐(豆蔻死后剩13个),以及国民党少校戴涛和侥幸从日军秘密枪决投降的中国军人暴行下逃脱出来的几个伤兵藏身的地方。但豆蔻为了给弥留之际的小兵王浦生弹奏琵琶,外出寻找琴弦时惨遭日军轮奸并被杀害,戴涛和几个伤兵即使缴了武器,后来也被进入教堂的日军杀害。13个秦淮名妓替换13个女学生赴日军设好轮奸的暗局,不止救了13个女孩,而且完成了“窑姐”向“刺客”身份的转换。在《金陵十三钗》中,有一个“双重转述”的结构:1.“我”转述姨妈书娟的“寻找之旅”;2.书娟转述少女时代见到的玉墨、红菱、豆蔻等人的故事。两代女性的“转述”使勇敢智慧的玉墨们永存于人们的记忆与缅怀之中。*曹霞:《“异域”与“历史”书写:讲述“中国”的方法——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有研究者认为,《金陵十三钗》是通过“身体修辞”,即通过作为象征和隐喻的“女体”被强奸和轮奸,作为唤醒现代中国人集体记忆中“南京大屠杀”的核心意象。“从以往创作看,严歌苓的创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阴性书写’。我们虽不清楚《金陵十三钗》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她要将女性叙述贯彻始终,将女性身体修辞播撒文本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她坚决地选择了性别/权力这一链条的最末端——妓女的身体,来刻录、印证这段历史,使那些已被先在地书写为‘尸体’或‘死者’的见证人,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复活。”*郭洪雷、时世平:《别样的“身体修辞”——对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修辞解读》,《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严歌苓的确不是在女权主义理论影响下,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作这样的文学书写的。
一九九五年末,我的朋友史咏给我寄来了一本很大的书,他编辑并出版的一本图片册,纪念“南京大屠杀”的。这确是一本大书,其中刊出的四百多幅照片,多是从美国、德国、日本的档案中搜集的,还有小部分,则是日本军人的私人收藏。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书的沉重,它的精神和物质的分量都是我难以承受的。书的英文名叫作TheRapeofNanking——AnUndeniableHistoryinPhotographs。我立刻注意到这里的用词是“rape”(强奸),区别于中文的“大屠杀”。对这个悲惨的历史事件,国际史学家们宁可称它为“大强奸”,然而强奸仅是整个罪恶的一个支端。
却恰是这个貌似片面的称谓,引起了我的全面思考。显然,那个迄今已发生了六十年的悲剧中的一部分——强奸,是最为刺痛东西方学者和社会良知的,是更值得强调而进入永恒记载的。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八万中国女性被强暴,与三十五万遇难者的总数相比,占稍大于四分之一的比例。但“rape”却包含更深、更广意味上的残杀。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物质生命)的消灭,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那么“rape”则是以首先消灭人之尊严、凌迟人之意志为形式来残害人的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生命)。并且,这个悲惨的大事件在它发生后的六十年中,始终被否认、篡改或忽略,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它是一段继续在被凌辱、被残害的历史。那八万名被施暴的女性,则是这段历史的象征。
她们即便虎口余生,也将对她们的重创哑口,正如历史对“南京大屠杀”至今的哑口。“rape”在此便显出了它的多重的、更为痛苦的含义。因为人类历史的真实,是屡屡遭“rape”的。*严歌苓:《从“rape”一词开始的联想——The Rape of Nanking读书心得》,《波西米亚楼》,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2-293页。
严歌苓要揭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便选择了这个可能只有女性视阈的书写者才会选择和驾驭自如的—强奸和被施暴—来赋形民族的屈辱和苦难。“坦率地说,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了阅读。图片那地狱似的残酷,使我一次又一次虚弱得看不下去。”*严歌苓:《从“rape”一词开始的联想——The Rape of Nanking读书心得》,《波西米亚楼》,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3页。严歌苓看到了这让她一次又一次虚弱得看不下去的残酷,也在《金陵十三钗》里表现了这种残酷:
在一九九四年,我姨妈书娟找到了豆蔻另一张照片。这张不堪入目的照片,是从投降的日本兵笔记本里发现的。照片中的女子被捆绑在把老式木椅上,两腿被撕开,腿间私处正对镜头。女子的面孔模糊,大概是她猛烈挣扎而使镜头无法聚焦,但我姨妈认为那就是豆蔻。日本兵们对这如花少女不只是施暴和凌迟,还把她钉在永恒的耻辱柱上。
我在看到这张照片时想,这是多么阴暗下流的人干的事。他们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他们把这样的照片作为战利品,是为了深深刺伤那个被羞辱的民族的心灵。我自此之后常在想,这样深的心灵伤害,需要几个世纪来疗养?需要多少代人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最终达到淡忘?*严歌苓:《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
在《金陵十三钗》中,当然不止强奸施暴这样的暴行,违反起码的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秘密枪杀已经投降的中国官兵,肆意杀死民众,杀死在教堂避难的没有武器的伤兵,等等。教堂里没有饮用水了,阿顾到附近小池塘运水,失踪,副神甫法比运了三趟水,“扎在淤泥里的阿顾就露出了水面”,“女学生们这下知道,这两天喝的是泡阿顾的水,洗用的也是泡阿顾的水,阿顾一声不响泡在那水里,陈乔治用那水煮了一锅锅粥和面汤”*严歌苓:《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7-108页。。
《金陵十三钗》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在令人震惊得不能再震惊的可怕的战争景况下,对人性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处理。十四个(豆蔻死后是十三个)窑姐本来与十几个女学生是相处不洽的,女孩们拿世俗和憎恶的眼光和态度对待她们;她们本来是自甘堕落的,但她们最后却能主动替换下女孩们、冒充唱诗班的女学生去面对敌人,明知是个可怕的暗局,依然义无反顾从容赴辱、赴死和救下了女孩子们。有人用宗教救赎的力量来分析玉墨们的心理变化和行动,我倒觉得,是她们见证了那么多身边人的死,阿顾的死,豆蔻的惨死,小兵王浦生和伤兵李全友被日本兵残忍地杀死,而且玉墨眼瞅着与自己生了情愫的戴少校人头落地……这一切,无形中让玉墨们完成了她们内心的心理转换和人性的升华。小说实际上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传统潜结构的叙事转换,包括神甫英格曼和副神甫法比对玉墨们态度从拒绝、厌恶到救助和最后的求助,微妙的人性心理的转化和符合逻辑的转换,都是小说人性书写非常成功的明证。战争,历史,除了它残酷和让人心理恐惧与浑身冷汗的一面,严歌苓笔过留痕的那些人性的幽微与曲折之处,同样让人难以释怀。
二、《小姨多鹤》:异族女性视角与抗战后叙事
有关抗日战争叙事,近几年来,长篇频出,有宏大叙事的佳作,也有开辟抗日战争叙事新维度的作品。《疯狂的榛子》(袁劲梅)、《重庆之眼》(范稳)、《己卯年雨雪》(熊育群)、《天漏邑》(赵本夫)、《劳燕》(张翎)等作品,值得关注和研究。小说家们以勤奋的写作,践行和展示了开辟汉语文学的新的可能性。在这些长篇小说中,最宜与严歌苓的抗日战争叙事加以比较和联系的是张翎的《劳燕》。张翎的《劳燕》*张翎:《劳燕》,《收获》2017年第2期;张翎:《劳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是首部涉及中美特种技术训练营题材的长篇小说,在题材和小说叙事方面,开启了抗日战争叙事的新维度。《劳燕》描写了三个鬼魂——当年在美军月湖训练营是朋友的两个美国男人(牧师比利、美军军官伊恩)和一个中国男人(阿燕当年的未婚夫刘兆虎)在201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70年后相聚,每个人吐露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部分真相,以多声部的叙述和追述,还原和补缀出当年发生在月湖的全景历史。三个鬼魂当年都是同一个女孩的恋慕者,他们分别叫这个女孩“斯塔拉”“温德”和“阿燕”。战争将美丽茶园春和景明的生活轰炸和吞噬,年方14岁的阿燕被日本人强暴、父母被杀害,牧师比利拯救了她,教她英文和习医;伊恩因为写给“温德”的求婚信件丢失而与旧爱重燃故情,几十年后因怯懦而不敢与来美寻亲的他和温德唯一的女儿相认,抱憾死去;刘兆虎则因难解阿燕被辱的心结,多次伤害阿燕也多次被阿燕相救,两人后来终于相守一起生活,但最后刘兆虎也因肺癌而死去。小说保持作家素有的语言的细腻、美感、节制而又不失灵性,战争的阴冷敌不过人性的温情与坚韧。面对战争的灾难、苦难、伤害和恋人的背叛、村人异样目光,乃至有人心怀趁机再度糟践她的企图,阿燕以德报怨,独立,坚韧,承担,温柔与力量并存,宽容与原则共在,以一个温婉的江南小女子在战争中凤凰涅槃般的遭际,展现了战争和苦难蹂躏下的中华女性所体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毅力,是战争废墟上开出的一朵人性坚韧与温暖之花,很多的场景描写令人动容。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书写这段战争历史的角度和维度,对于长篇小说成功与否非常重要。很多研究者从女性命运和严歌苓小说的婚恋叙事等角度来解读《小姨多鹤》。小说写了抗战结束时日本在满洲的“垦荒开拓团”村民仓惶溃逃路上留下的孤女多鹤,她16岁时就被一个中国家庭(张站长家)用七块大洋买去作为借腹生子的工具,和张二孩、小环组成了二女一男的特殊家庭的故事。张二孩和小环本来与日本人有着深仇大恨,却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与多鹤生活在一起,为了隐瞒多鹤的身份,从东北一路辗转到江南——上海……小说写出了中国在抗战后几十年的历史和民众现实生活的流转变迁,辐射面从东北到江南。但是,一直为大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这部小说,其实也可以说一个部分是采用了异国女性视角(也有中国人的视角)的抗战后叙事。这个抗战后叙事,有很多对于战争给中国人和日本普通民众带来深深痛苦和创伤的体验:有张二孩、小环对于小环遭遇日本兵而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并永远失去了女性生育能力的创伤性回忆;有多鹤视角下战败时日本村民撤退的惨死和惨状的回忆;有多鹤对于当初她被装在麻袋里,被一路颠簸带到张家,麻袋打开,她与张俭(张二孩)初见时的叙事性回忆,并反复出现和呈现。
从异国视角看取日本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劳燕》中也有,但不是异国女性视角,而是两个美国男性的视角。中国作家写抗战题材小说,以日本人为主角或重要人物形象、借助日本人的视角来反思这场侵略战争,在熊育群《己卯年雨雪》中就是非常重要的叙事策略。作家在后记中写道:“这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战,我们叫抗日战争,日本叫日中战争,任何撇开对方自己写自己的行为,总是有遗憾的,很难全面,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好的小说须走出国门,也让日本人信服”,“要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寻找根本的缘由与真正的罪恶,写出和平的宝贵,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熊育群:《己卯年雨雪·后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第387页。。《己卯年雨雪》不仅详细地叙述了日本军队攻占营田的战争过程,记录日军滥杀无辜的反人类行径,而且还写出了日本民族性是如何异化人性的——借助侵华日军士兵武田修宏形象的塑造和他的妻子千鹤子的视角,来表现这一主题。*刘艳:《从〈天漏邑〉看抗日战争叙事人性书写新向度》,《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可能是男性作家采用日本女性视角的缘故,总觉得《己卯年雨雪》在日本女性形象的限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方面,还可以更加精进。能够贴近人物,写出像日本人的感觉样貌和举止言行,哪怕步态都是日本女人模样的形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却毫无疑问做到了这一点。
《小姨多鹤》这部小说“序”的部分是采用多鹤的视角,对日本战败投降后,在满洲“垦荒开拓团”六个日本村子村民撤退溃逃时的历史书写。村民几乎全是老弱妇孺,但包括多鹤所在代浪村的村长们却安排枪手射杀村民,后来因为中国游击队员与村长的遭遇并“开枪提前成全了他们”,其他村民才得以撤退。撤退路上,“一颗手榴弹在多鹤母亲旁边爆炸了,硝烟散开,多鹤已经没了母亲、弟弟和妹妹。多鹤的爸爸一年前战死在菲律宾。好在眼下的险境容不得多鹤去想她的孤儿的新身份”*严歌苓:《小姨多鹤·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2页。。第二天傍晚,所有伤员都自尽了,因为他们决定绝不拖累大家。遭遇民团,队伍里的女人们开始了“杀婴行动”。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又要杀多鹤背上生病的女儿久美,多鹤救下了久美。久美也就是几十年后日本首相的护士,她后来千辛万苦找到了多鹤并把她接到了日本。之所以说《小姨多鹤》是抗战后叙事,不止体现在小说不长的序中有对日本战败平民村民撤退时惨境的描写,还有日本的侵略战争给张俭、小环一家带来的伤害。没有小环遭遇日本兵流产而失去生育功能,也不会有七块大洋买多鹤作为生孩子工具的事情发生。战争所造成的对于民众的伤害和伤痛,几十年来一直潜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张俭内心对多鹤从拒斥、当成敌人异国女子的恨和厌恶,到深深喜欢上她;从在她生了一个女儿(曾夭折过一个儿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后曾经偷偷把她遗弃在荒郊野外,打算抛弃她,到爱她甚至曾为躲开小环而与多鹤常常到外面偷情;从多鹤把他当成胁迫自己的中国男人,到爱上这个中国男人,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张俭造成小石的死亡是为了保护自己……张俭对多鹤,乃至后来的小彭对多鹤,从作为敌人的日本人来仇恨和厌恶,到深深地自责自己对多鹤曾经的冷漠与厌恶,并为多鹤身为孤儿的遭遇和当时日本村民撤退时的惨境而心疼她,这其中的逻辑转换便是人性,是人们对于战争伤害和残酷的同样无法面对。战争的灾难和家破人亡不该由普通的平民尤其是老弱妇孺来承担。这就是严歌苓在《小姨多鹤》中作出的思考,这思考绵密细致而丝丝入扣。多鹤张俭一家共同生活的几十年,所有中国大事都在小说中隐现,是作家女性视阈下的表现和展现。比如,一炉钢出来,也不知怎么就成了“反修钢”“反帝钢”“忠字钢”,人们敲锣打鼓,吹拉弹唱,向毛主席报喜。小彭作为彭主任,多鹤曾经几天和他一起被对立派围困,对立派对彭主任这一派发动了总攻,竟然还动用了郊区的农民。张俭因为小石的死亡事件,被小彭用计重审,被判了死缓,多鹤一直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在小环的日子“凑合”着过中消失了,“多鹤在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正是为此大吃一惊:心里最后一丝自杀的火星也在凑合中不知不觉地熄灭了”*严歌苓:《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296页。。多鹤这自杀火星的完全熄灭,在1976年的初秋,其实是有着暗暗的隐喻的。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就这样潜隐和埋在了多鹤、张俭、小环的日常生活里。
《小姨多鹤》不仅在题材、主题思想等方面,是对战争反思的深度拓进,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谓之是“抗战后叙事”。小说在文体和叙述等小说的形式层面和艺术成就方面也都是上乘之作,可以视之为严歌苓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在采用多鹤这样一个异国女性视角的叙事方面,造诣颇深。写好多鹤这个日本女性形象,有两大写作难点需要克服:第一,要让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日本女人,不止外表样貌,她的内心心理活动和一言一行,都得是“日本女人”的,而不能是仅有一个日本女性的名字和身份,骨子却是个中国女性的心理活动和言行举止。第二,一个作为生孩子工具的日本女性,与几个中国家庭成员一起生活几十年,还生养了三个孩子,她与他们包括邻里和社会上的人,怎样打交道?这是很难把握和处理的。对于第一点,严歌苓很好地采用了来自多鹤和家人的尤其是多鹤本人的限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策略,贴着人物写,“我的人物比我高”(萧红语)的写作手法,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发挥和使用。对于第二点,严歌苓分寸拿捏也非常允当,充分动用了张俭、小环、孩子们、小石小彭和邻里以及所有与多鹤能打交道的人的限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策略。多鹤刚入张家不久,曾经偷偷逃走过,家人寻她不着,她却自己又回来了,遭小环一顿抢白。“小日本婆听不懂小环的话,但她的嗓音像过年一样热闹,她便停止了倔犟,由她一直把她扯进堂屋。”“一晚上谁也没从小日本婆那里掏出任何实情来。第二天晚饭桌上,小日本婆把一张纸规规矩矩铺在大家面前。纸上写着:‘竹内多鹤,十六,父母、哥、弟、妹亡。多鹤怀孕。’”*严歌苓:《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7-18页。多鹤最初基本听不懂中国话,语言从隔阂不通到粗通,严歌苓对此拿捏的分寸恰到好处。对多鹤在张家几十年里仍保持着的一些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也在不经意间,被严歌苓撒播在小说叙事的角角落落。由其他人物尤其张俭视角而对多鹤所作的限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也是令多鹤形象栩栩如生的一个重要保证。例如:
不变他对多鹤怎么会这样……看不得、碰不得?一碰浑身就点着了?他过去也碰过她啊。变化开始在两年多以前自由市场的那个偶然相遇吗?不是的。开始得更早。小环把多鹤的身世讲给他听了之后,就在第二天,他看见多鹤在小屋里给孩子们钉被子,心里就有一阵没名堂的温柔。当时她背对着他跪在床上,圆口无领的居家小衫脖子后的按扣开了,露出她后发际线下面软软的、胎毛似的头发。就那一截脖子和那点软发让他没名堂地冲动起来,想上去轻轻抱抱她。中国女孩子再年轻似乎也没有那样的后发际线和那样胎毛似的头发。也许因为她们很少有这种特殊的跪姿,所以那一截脖子得不到展露。他奇怪极了,过去只要是日本的,他就憎恶,多鹤身上曾经出现的任何一点日本仪态,都能拉大他和她的距离。而自从知道了多鹤的身世,多鹤那毛茸茸的后发际和跪姿竟变得那样令他疼爱!他在这两年时间里,和她欢爱,和她眉目传情,有一些刹那,他想到自己爱的是个日本女子,正是这样刹那的醒悟,让他感动不已,近乎流泪:她是他如此偶然得到的异国女子!他化解了那么大的敌意才真正得到了她,他穿过那样戒备、憎恶、冷漠才爱起她来!*严歌苓:《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
多鹤独有的日本女性的特点,张俭对她从戒备、憎恶、冷漠到爱起她来究竟是缘何而转变,都表现得很形象和生动。这一小说叙事,看似是张俭的内心独白,实际上是贴着张俭的感知视点和价值观视点、利益视点等所作的限制性叙事。女性视阈中的历史与人性书写,加上限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策略的纯熟运用,令《小姨多鹤》艺术性和文学性成就斐然。
三、《陆犯焉识》: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磨难史与家族史
《陆犯焉识》是通过对“我”的祖父陆焉识以及祖母冯婉喻,尤其是对陆焉识的故事的讲述,展现了20世纪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这是严歌苓作品中少见的以男性为第一主人公的小说文本,但它又与一般表现同时期知识分子的小说明显不同,小说在叙述方式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有着独树一帜的特色和价值。虽以男性形象为第一号主人公,严歌苓仍然不失她作为女性作家在面对历史和人性书写时的女性视阈,“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小说叙述背后严歌苓温情的女性目光”*丛治辰语,龚自强、丛治辰、马征、陈晓明等:《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但以陆焉识为视角的叙述眼光和叙事声音,又常常是紧贴陆焉识这个男性人物的。叙述方式的创新和细节化叙述的震撼人心,《陆犯焉识》是兼具的。鲜有作家能够将文学性、虚构性和纪实性调和得那么好,那么感人至深地来叙述那段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历史……这是该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令它在所有同类题材中显得标新立异、卓尔不群。小说带我们见识了陆焉识这个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下近乎荒诞的悲剧性命运。主人公陆焉识算得上是上海世家子弟,天资聪颖,被恩娘安排先娶了内侄女冯婉喻然后出国留学,会四国语言,20多岁当上教授,可谓才华横溢。就是因为稀里糊涂畅所欲言的几篇文章,得罪了“凌博士”和其他人,获罪发配到西北大漠,遭受了种种非正常境况和非常的生存困境乃至绝境的磨难,以犯人的身份度过了自己的盛年,归来已是垂垂老矣,年华尽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陆犯焉识》谓之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磨难史与家族史”,而从深层的意义上,或许应该更加认同和赞同小说的“归来”主题。
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因以陆焉识被平反获释后回来看望妻儿的结局为主要内容,而曾经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是对知识分子苦难史的回避。我倒是觉得电影《归来》恰恰是抓住了小说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实则把握和提取出了小说最精粹的内涵:无论现实如何变化,女性作为爱、亲情和家园的象征,始终安抚着破碎的人生和灵魂。这并非简单的‘精神胜利法’,而是潜存于家国创伤底部、历经激烈变故而依然透射出深厚救赎力量的深厚温暖”*曹霞:《“异域”与“历史”书写:讲述“中国”的方法——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所以说,像这样的概括,似乎是更贴近《陆犯焉识》深层的精神主旨:“在《陆犯焉识》中,虽然书写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的创伤,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抒情方面,在那曲绵长的爱情悲歌。在我看来,恰恰是自强觉得暧昧矛盾的历史与情感的冲撞,能够回应我的问题:严歌苓着力讲述的这段旷世之恋,才是这部小说迥异于其它此类小说的关键。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小说叙述背后严歌苓温情的女性目光。她那么缠绵浪漫地把祖父和祖母的爱情故事讲出来,真正是一场世纪之恋,一场不断错过的世纪之恋——之所以跨世纪,就是因为错过,后来的失忆也是错过的一部分:前半辈子自己错过了,后半辈子被迫错过了,最后又因为失忆再次错过了。但两个人始终矢志不渝,一个人矢志不渝了一个世纪,一个人矢志不渝了半个世纪。”所以,陈晓明才会认为:“或许你把这部小说概括为‘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丛治辰语,龚自强、丛治辰、马征、陈晓明等:《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陆焉识与冯婉喻这看起来“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无疑是小说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小说的叙述方式,是《陆犯焉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是“我”——陆焉识的孙女冯学锋,但有时候又借用别人的叙述视角。比如“老佣”这个章节,就是这样。叙述视角的自如转换,和限知视角与限制性叙事策略运用得当,不只可以贴近人物叙述,产生让人身临其境的艺术真实感和文学性,还令叙述者在这种叙述角度和距离的调换中,让陆焉识劳改的苦难史不那么残酷和过于沉重、让人透不过气来,既有现场般的真实又有距离化的叙述效果,这是严歌苓的高妙之处。而对陆焉识和冯婉喻的感情书写,又有着日常生活和人性情感等的浸润,故事性和可读性很强,也很感人,正好与西北大漠荒无人烟的那段残酷岁月和生活故事,形成一个“复调”叙事效果。就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用沉重的语调去讲一个沉重的故事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也注定不能给读者全新的审美享受。‘我’还在不时地提醒读者:‘我’是根据读祖父盲写出来的散文、笔记、回忆录等来想象他的一生。”*曾洪军:《多重话语 荒诞品质——论严歌苓新作〈陆犯焉识〉》,《名作欣赏》2012年第24期。
“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点滴日常生活的积累和情感累积成的:
婉喻的探监日子,成了焉识四季交替的临界点。春夏之交,婉喻带来笋豆、糟鱼;夏秋更迭,咸鸭蛋、腌鸭肫、烧酒醉虾;秋去冬来,椒盐猪油渣,油浸蟹黄蟹肉;来年开春,腌了一冬的猪后腿、风鸡风鹅、咸黄鱼都让婉喻装在罐子里,瓶子里,盒子里带来了……焉识拎着这些沉甸甸的食物往监号走,心里总是奇怪,来的一路几百公里,婉喻是如何三头六臂地把东西搬运过来的?那手提肩扛的,拖泥带水的长途征程怎么会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狼狈的痕迹?在会见室一坐,还是那个洁净透亮的婉喻,一脸的识相,对自己微微的寡趣乏味泰然坦荡,自知是改进不了的,但是没关系,你给她多少关注,她就要多少。*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312页。
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蜇烂了,才抠出的蟹肉,被当成了“垃圾”来处理。“婉喻亲手剥出的蟹肉蟹黄,也成了垃圾,被他们从罐子里倒出来,倒入两人合抬的大铁皮垃圾桶。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蜇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焉识的眼睛跟着垃圾桶往监号门口走。抬垃圾桶的是两个轻刑犯,他们已经走到了监号门口,就要拉开铁门出去。焉识一下子蹿起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那样蹿。他扑在铁皮桶上,伸出的双手从垃圾桶里捞起一大捧蟹油蟹黄,和着烂苹果烂柿子塞进嘴里。”“1958年10月1日,婉喻按时来看望他,似乎知道上一次带来的蟹黄蟹肉都做了垃圾,这次更加变本加厉,带了更大的一罐。他下意识就去看她的手指甲,它们都秃秃的,在剥蟹剥劈了之后给锉秃了。”“接下去,他告诉她,一批犯人很快要转监,但是转到哪里不知道。”“‘那我到哪里去看你?’婉喻突然伸出两只手,抓住他右手的小臂。”*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313页。历史与夫妻间相依难舍的人性温暖,就这样交织在陆焉识和冯婉喻的人生里。个体的生命与历史,撕扯不开,所能支撑人始终不渝坚持下去的,正是那人性温暖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