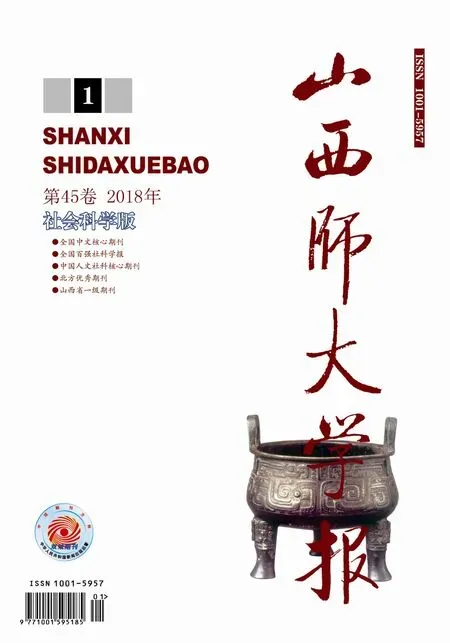齐如山戏曲观的李渔意味
郭 艳 平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齐如山作为我国近代重要的戏曲理论家与活动家,他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齐如山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与交往。在此期间,作为梅党的重要成员之一,齐如山为梅兰芳编排剧目并推动和伴随梅兰芳进行了1919年的访日演出和1930年的访美演出。其次,齐如山关于中国戏曲,特别是京剧的研究著述颇为丰富。这些著述涉及剧本创作、剧场变迁、舞台表演等戏曲领域的多个方面,由他提出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理念,集中概括了我国传统戏曲的审美精神和表演原则。齐如山亦文亦商的身份和游历欧洲的经历,使得他在自己的戏曲观构建中难以避免地混合了传统文人、务实商人和西方话剧的思维。齐如山戏曲观的多层次性不仅引导着齐如山自身的戏曲研究与实践活动,而且对梅兰芳的舞台表演美学建构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齐如山具有西方话剧理念和国际视野的戏曲观已为人们所熟知,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齐如山戏曲观中的李渔意味。解读齐如山戏曲观中的李渔意味,既可以深化和丰富齐如山的剧学研究,也可以为研究梅兰芳的舞台表演美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齐如山的祖辈可以演唱昆曲,家中也有南北曲的相关书籍,所以齐如山从幼年时代就接触戏曲。齐如山不仅家学深厚,在他的家乡河北高阳,常有昆戈班艺人奏艺,年幼的齐如山因此也有更多的机会观看戏曲演出。童年看戏的经历对齐如山影响深远。当他走入“缀玉轩”成为梅兰芳后援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后,在帮梅兰芳编排昆曲身段的时候,他的一个依据就是童年这段看戏的回忆。齐如山在少年时代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17岁时进入同文馆学习洋文。他在经营家族企业的时候有了几次游历欧洲的机会,在此期间,他观摩了西方的戏剧演出。回国后的齐如山,在一次戏界总会即当时的正乐育化会上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讲。因当时齐如山对中国传统戏曲了解不深,加之受到西方话剧观的影响,所以这次的演讲内容多是反对旧剧的言论。这次演说应该视作齐如山正式介入戏曲活动、发表自己戏曲理论的开端。齐如山将自己的戏曲活动概括为“研究国剧”。齐如山特别凸显他是以“研究”的视角来开展戏曲活动,齐如山所指的“研究”并不是一些戏界的传记轶事、观剧戏评之类的游戏之作,也不似前清文人热衷的品题优伶,而是将国剧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是一种认真治学的态度。齐如山对国剧的“研究”,既是一种探寻、归纳、整理的资料性研究,也是一项积极改编、新编和推广国剧的工作。这两类“研究”相辅相成,支撑并推动了齐如山整个“研究国剧”的活动。为了能够顺利开展自己的国剧研究活动,齐如山查阅了包括《燕兰小谱》《明僮录》《剧说》《度曲须知》《录鬼簿》《扬州画舫录》、陶九成论曲、燕南芝庵论曲及赵子昂论曲等一些相关著述。但查阅的结果却让齐如山感到失望和无助。在齐如山看来,诸如《燕兰小谱》之类的书籍只是一种文人赏色品花的指南,对于戏曲研究没有什么用处。而《剧说》《度曲须知》等书籍虽然有一些研究的性质,但偏重于南北曲和歌唱等内容,因而齐如山认为这类书籍既与当时流行的皮簧没有关系,又缺乏对戏曲整体性的研究。
虽然在齐如山查阅的书籍中并没有直接提到李渔的《闲情偶寄》,但齐如山的戏曲活动和戏曲观念中实际上包含了很多与李渔相似的经历和论调。然而,齐如山似乎没有把这本书置于很重要的位置,甚至他很苦闷地觉得前人著述无法给他的戏曲研究活动提供很多帮助。事实上,齐如山应该是查阅过李渔的《闲情偶寄》。齐如山曾在讲述一些戏曲活动和戏曲概念的时候,有意无意中提到了李渔及李渔的《闲情偶寄》。比如,齐如山在提到昆曲《游园》“袅晴丝”的文雅难唱时,说:“此曲在李笠翁的《偶寄》中有详细的解释,且最好。”[1]58可见,齐如山查阅了李渔的《闲情偶寄》,并在某一问题上赞同李渔的见解。另外,齐如山对李渔关于定场白的解说也颇为赞同,甚至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引用了李渔的一段原话来解释定场白的意思。[2]92但他也认为李渔只谈了定场白的意思,却并没有涉及定场白的来源。可见,齐如山在某一方面上提及或认可了李渔的观点。但是,齐如山认为包括李渔在内的前人研究,还有很多可以补足或者补白的地方。齐如山说道:“但是对于台上演的戏剧是怎样的来源,怎样的组织法,其原理如何等等,却是没有人来研究。不但现在没有人,就是几百年来,也没有人注意及此。李笠翁还说过一些,但亦只说其然,未说其所以然,且所谈者还不到千分之一二。”[3]7齐如山所提到的研究活动主要是指注重戏曲实际搬演的“场上之道”。但对于同样精通“场上之道”的李渔,齐如山似乎觉得李渔的研究仅仅涉及了一点皮毛而已。
二
尽管齐如山在其“研究”国剧的活动当中,并没有直接而明确地将李渔的《闲情偶寄》列入自己查阅、参考的书籍名目里。即使偶然提及了李渔或李渔的《闲情偶寄》,齐如山也没有将其放置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来讲。然而,通过对齐如山的戏曲理念和戏曲活动的分析和理解,却可以解读出其中所渗透的李渔意味。
《闲情偶寄》是李渔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集中反映了李渔主要的戏曲观。在此书中,李渔作出了对机趣、科诨、意取尖新等内容的阐述,这表明李渔十分重视在戏曲编演时的趣味性和新奇变化。李渔认为:“‘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4]24李渔的机趣说,是一种有生气的趣味。这种机趣是一种戏曲审美品格,它或为雅,或为雅俗共赏。概而言之,李渔讲的机趣就是“精神、风致、生气”,而这种机趣在李渔看来,又是制曲填词必不可少的要素。文人填词制曲之时,或为了炫耀文采,或止于案头欣赏,专注堆砌浮藻丽词,这种缺乏机趣的作品,对于戏曲的实际搬演并无多少裨益。只有那些可以“动观听”、有机趣的作品,才会使观者愉悦身心,回味无穷。李渔的机趣说被二百年后的齐如山演绎得更为通俗了。齐如山认为:“国剧绝对不可专用正面文章或专用庄重文字,因如此则不能引人入胜,亦去‘戏’字太远也。”[5]347在齐如山看来戏曲应该是要有“戏”才行,而这个“戏”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可乐”的趣味。可见,齐如山也是充分认识到了戏曲应该有“趣”,才会激发观者兴致,达到演出的理想效果。
戏曲演出中为了不让观者觉得枯燥无味,重视插科打诨的运用也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手段。而历来文人填词制曲时,多不对“插科打诨”施加笔墨,认为它是“填词末技”。但精通“场上之道”的李渔却认为“科诨”可以“养精益神,使人不倦”。所以在他所著的《闲情偶寄》里专辟章节来说明“科诨”于舞台演出的重要性。“科诨”即“插科打诨”,它在戏曲舞台上是常见的一种调节气氛、逗乐观众的方式。它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以滑稽的语言和动作等展现戏曲舞台表演的趣味。齐如山为梅兰芳所编演的多是具有文人气息的清洁高雅的剧目,但齐如山也十分重视运用科诨的诙谐来增加戏曲的“趣味”性。比如《天女散花》中两位小沙弥的对话就具有诙谐逗趣的意味。[6]233—235
另外,齐如山在编戏之时,十分注意场上的新奇变化。齐如山认为:“戏中的正场最忌讳怎么样上来,还怎么样下去,只做一件事情,场上没有变化,这是最瘟最不受欢迎的。编这种场子要用心找资料,使他情节有变化,使观众有想不到的地方,方能引逗人的兴趣。”[7]218—219齐如山对场上新奇变化的追求与李渔所主张的“脱窠臼”“意取尖新”的求新求变的戏曲观十分契合。李渔认为填词比诗赋更需要重视求新而“脱窠臼”。李渔为生计所逼游走社会,成就他亦文亦商的人格。他慨叹那些有钱财的家班主人创作不出时变时新的作品,如果自己不为生计所迫,一定能创作出令观者赞叹的“时出新奇”的作品。可见,李渔的戏曲观中就有对“时出新奇”的一种热烈追求。这也表明李渔从制曲填词到舞台搬演都十分重视戏曲的趣味性。齐如山也认为编戏应注意引人入胜、曲折变化,从而避免平铺直叙的沉闷,即要有趣可乐。这就表明李渔和齐如山二人的戏曲观都十分重视一个“趣”字。
李渔在言及自己编戏的情景时说:“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饶,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4]55“手则握笔,口却登场”说明李渔编戏时,不仅仅囿于案头欣赏,而是要以“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态度去考虑剧本实际的搬演情况,最终达到“观听咸宜”的目的。也即李渔十分重视看戏的人在观听戏曲时的感受。齐如山说:“编戏时就怕只管随意编制,不管演者,如此则势必至不能排演。当编某一句时,则必须闭目想一想,台上该脚说此一句时,他是怎样的神气?怎样的举动?甚至其他别脚色都是怎样?”[5]348齐如山所说的编戏最忌随意编制,也即李渔说的“好则直书,否则搁笔”。齐如山所说的编戏应闭目想象演员在台上表演的神气、动作等,正是李渔所说的“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饶,考其关目,试其声音”。由此可见,二人都强调编戏之时不能只是文人式的玩弄笔墨、遣兴抒怀,而应全身心地想象着登场搬演时的情景,以此来制约自己的创作。
李渔和齐如山对编戏情景的描述,实则反映出了二人都十分注意从观众欣赏的视角出发,注重剧本的实际搬演效果。李渔处处从观众的视角出发审视自己的戏曲编演创作,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对雅俗共赏的追求。李渔将戏曲观众进行分层次的划分,其中既有懂文识礼的读书之人,也有目不识丁之人,还有妇女儿童。李渔在编戏之时就考虑到了广泛的观众层次,力图做到既要雅又要俗,从而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齐如山也说:“戏中词句不可太文,亦不可太俗。太文则多数人听着不能十分明了,太俗则较文墨些的人不爱听。”[5]358齐如山同李渔一样,也是将观众进行了层次划分,兼顾了不同的观听需求,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文人编戏往往趋向于让戏曲承担更多的社会教化的职责,而忽视了戏曲的娱乐功能。齐如山就从戏曲观众赏析的视角出发,反对这种推行社会教育而不顾观听效果的戏曲编演。齐如山说道:
或谓,演戏有关社会教育,要能领导观众方算好戏,岂可自贬身份,迁就观众乎?此说亦不无理,但所谓关乎社会教育者,乃指剧本之命意而言,与技术无直接关系;况就以剧本论,亦不能专注教育一层。盖戏剧最初乃系自己娱乐之事,后乃进而为营业性质;行之既久,百余年来西洋脑思灵敏之学者,以为观众既如此欢迎,则大可借此推行社会教育,于是戏剧有关社会教育一语,乃盛行于世。然仍以观众欢迎为本,倘不管人欢迎与否,只管行其教育,有如学校之教科书,谁肯花钱来观听耶!果无人观听,则剧本虽好,亦难施展其教育矣。[8]16
可见,在齐如山看来戏曲演出是否能够受到观众欢迎,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齐如山认为,只有动人观听的剧本和舞台表演才能实现社会教育的目的。李渔和齐如山都具有文人的品性,因此编戏之时难免流露出文人尚雅避俗的旨趣精神。但另一方面,李渔和齐如山又都是精通场上之道的文人,所以二人深知腐儒晦涩的作品不利于戏曲的实际搬演效果,无法兼顾到不通文墨的观众,因此编戏也不能太雅。可以看出,二人的戏曲思想中都包含了重视观众的理念,因此无论是对编戏情景的描述还是对雅俗共赏的追求,都体现了二人戏曲观的同调性。
李渔和齐如山不仅在重视观众、注重戏曲搬演效果方面具有类似的理念,而且对戏曲演唱方法也有近乎一致的观点,这就是关于演唱之时“曲情”的认识。关于曲情,梅兰芳在《戏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盖唱曲宜知曲情,知曲情又须了解曲之节奏,因知曲之情,则可知意之所存,意既有存,即唱出口时,亦俨然剧中人矣。……所谓悲里黯然魂销,决不能面有喜色,欢者恬然自得,而不能有所悲哀,且其声音齿颊之间,各种倶有分别,此即所谓曲情是也。[9]
按照“梅兰芳”的解释,“曲情”即为“悲与欢”的“分别”,也即曲中之情感。虽然此文署名为梅兰芳,但从行文和内容来看,应该是隐匿在梅兰芳背后的文人的发声。而持有这种戏曲观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在梅兰芳的智囊团文人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齐如山。因为齐如山自己也阐释过类似的论调:“所歌之音节恒与曲文字句的意义相反。如曲意为喜而歌声近于悲,曲意为从容而音节则近于急促。种种情形尤为大病,因其违背歌唱之原理也。”[5]317齐如山所说的曲意为悲演唱为喜、曲意为从容演唱为急促,这种违背曲情的唱法就是演员的艺病。正确的演唱方法是歌唱与曲情相符,即为“声音齿颊之间,各种倶有分别”。齐如山认为戏曲表演中的演唱缘于有感而发,是要表达感情的。我国传统戏曲理论对填词制曲的案头创作与品评,较之对“场上之道”的分析更为偏重。而在有关“场上之道”的分析中,对演员表演时应重视“曲情”的观点就屡次被提及。李渔就认为:
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消而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而不见稍有瘁容,且声音齿颊之间,各种倶有分别,此所谓曲情是也。[4]98
从李渔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梅兰芳”或者应该说是齐如山对于曲情的解释显然是源于李渔的这段文字。李渔首先指出唱曲必须唱出曲情来,并进一步解释曲情就是曲中情节,演员由声音、面容传神地表现出曲中悲欢喜乐的分别,就是唱出了曲情。李渔进一步指出要唱出曲情就要做到解明曲意。而解明曲意的体现就之一就是出口之字能字字分明,不能模糊。李渔说:“字从口出,有字即有口。如出口不分明,有字若无字……”[4]101齐如山也认为演员在表演之时,“不许稍为含糊,倘一含糊,便算倒字,如此则无论歌唱多么高妙,也算是毫无价值之言”[5]317。可见,齐如山十分重视歌唱时的吐字清晰,所以他褒扬梅兰芳的念白歌唱能做到“字字动听、声声入耳”。
齐李二氏在重视艺人演唱时应唱出曲情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容易被人们轻视的戏曲宾白。李渔认为宾白并不比歌唱容易,而且善于宾白的艺人十分之稀少。李渔在提出戏曲宾白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时候,也强调艺人在念白之时应该做到高低抑扬、缓急顿挫。和李渔一样,齐如山也十分重视戏曲中的宾白,他曾对此进行了一番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在一段话白之中,某一句须拉长,某一句须提高,某一句须重念,某一句须带过,某一句应叫锣鼓,某一句应止锣鼓,某一句应呼应锣鼓,再某一字应重念,某一字应摇曳,某一字应顿住,某一字应颤声……”[7]6齐如山所说的“拉长、提高、重念、带过、摇曳、顿住”等话白的原理与情形,与李渔讲到宾白时所强调的高低抑扬、缓急顿挫的说法有异曲同工的契合之妙。
三
为了有别于文人介入戏曲之时常见的一种品花抒怀的视角,齐如山特别强调自己介入戏曲活动所采取的“研究”态度。齐如山在提及自己研究戏曲的途径时,说道:“他们所看到的无非是扬州花舫录、燕兰小谱等这些书,他们所听到的,无非是戏界人员所谈,按研究戏剧这门工作来说,也只有这两种途径,确是不错的,我所得到的这点知识,也出不了这个范围……”[10]312由此看来,齐如山一方面翻阅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哪怕在他看来这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常与戏曲相关人员进行接触、访谈等。这一点齐如山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因为无论是登台的名伶、戏班的管事,甚至后台管行头、管水锅的人,齐如山都一一询问,所得到的资料也是历来戏曲研究所或缺的“场上之道”。虽然,齐如山并没有显豁地将精通“场上之道”的李渔的著作列入其研究书目之中,但是,齐如山和李渔的戏曲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有些内容上也近乎一致,只是在语言表达上有些不同而已。很难想象,齐如山在开展自己的戏曲研究活动当中,没有查阅借鉴李渔的著作。但是,齐如山在有意无意间回避了李渔及李渔的《闲情偶寄》。正如梁燕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年代相隔久远,李渔和齐如山有着共同的创作经历和相同的戏剧观,他们在戏曲语言上的精辟见解受到后世推崇。”[6]80梁燕所说的二人持有相同的戏剧观,我们可以从二人在对待舞台搬演的趣味性、重视观众和曲情等多方面得以明了。那么,二人在很多方面有如此相似或相同的戏曲观,这表明齐如山参照了李渔的研究,而且其戏曲观是暗合了李渔的旨趣精神。
但是,为什么齐如山会在否定了很多前人著述之后,而又“接受”了李渔的一些戏曲观念呢?这可能与二人有着相似的身份和创作经历不无关系。李渔与齐如山都是亦文亦商的身份,李渔出身于商家,自己又以携“家班”演出维持生计。但李渔也是可以填词制曲的读书之人。齐如山不仅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后又进入同文馆学习洋文,而且齐如山有自己的家族企业,又有留洋的经历,所以齐如山也是亦文亦商的身份。最重要的是,李渔和齐如山都把历来受正统文人所鄙夷的“场上之道”作为研究对象。李渔带着自己的家班,穿梭于文人士绅的厅堂园林,而他的两个姬妾同时也是他家班的重要艺人。所以李渔与艺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影响了李渔戏曲观的构建。纵观齐如山“研究国剧”的活动,无论是研究的起源还是过程都与梅兰芳息息相关,齐梅二人是不可分割而谈论的。齐如山不仅是“研究”活动,也是梅兰芳智囊团的核心人物,而且参与了梅兰芳演出活动的全过程。所以,齐如山也是这样一位与艺人往还紧密、有着丰富的场上经验的编戏文人。但是齐如山比李渔幸运的是,他不受生计所困,也不必为谋生而编戏。齐如山就说道:“我一人独自无事,乃研究起戏来。”[10]64可见,齐如山完全没有生活的压力,研究戏曲只是有闲文人的一种趣味。相比之下,李渔却是一个游走江湖的卖赋文人,所编之戏有时为了迎合社会心理却不能成就己愿。
虽然,李渔和齐如山都是亦文亦商的身份,也都与艺人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二人也十分关注场上之道的研究,但齐如山也有着他自己的独特之处。齐如山有着留洋观剧的经历,因此在他的戏曲观中既有李渔意味,也杂糅了西方话剧的理念。齐如山在民国二年观看梅兰芳的《汾河湾》演出后,就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信给梅兰芳。齐如山认为梅兰芳在窑门一段的表演不合道理,原因就是在听见十八年未见的丈夫的大段倾诉中,没有运用恰当的表情和身段去呼应。所以,齐如山以话剧的“合道理、合剧情”原则,建议梅兰芳改动身段和表情。由此可见,齐如山亦文亦商的身份和其留洋观剧的经历,对其戏剧观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齐如山的戏曲观所呈现出的一种中西混合式的样态已为人所熟知,而齐如山戏曲观中所渗透包含的李渔意味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1] 梁燕.齐如山文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2] 梁燕.齐如山文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3] 梁燕.齐如山文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4]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 梁燕.齐如山文集:第六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6] 梁燕.齐如山剧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7] 梁燕.齐如山文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8] 王晓梵整理.齐如山文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9] 梅兰芳.菊花观剧话[N].戏报,1937,(21).
[10]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