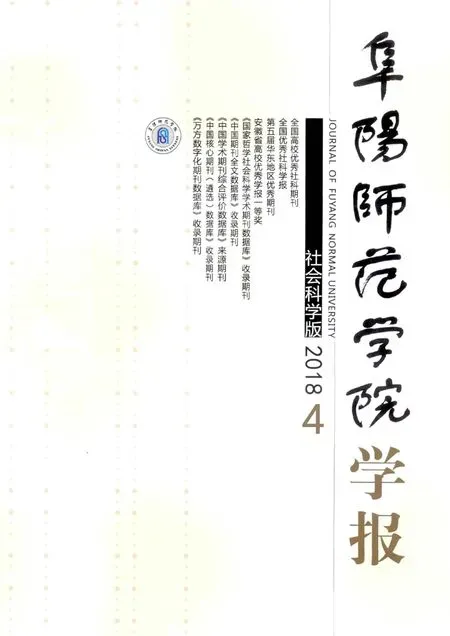文化空间中的民间乐班——以皖北民间乐班为例
张 宇
文化空间中的民间乐班——以皖北民间乐班为例
张 宇
(阜阳师范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把民间乐班植入文化空间加以研究,目的是探究其空间存在及意义,考察其在音乐非遗文化传播、传承中的地位以及在乡村音乐文化建设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研究是以皖北为例,通过田野调查、走访工作,了解在当下民俗、仪式等场合中民间乐班的文化角色和文化行为,运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民间乐班的文化活动与文化产品进行分析与解释,引发人们对民间乐班在文化空间意义上的讨论与思考。民间乐班的存在不仅占据着一定的现实物理空间,而且也具有文化上的空间意义,诸如象征空间、审美空间等,惟其如此,才能完善对民间乐班整体文化意义的考察与研究。
民间乐班;文化空间;仪式;民俗;
一、“文化空间”释义
“所谓文化空间,一是特指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在固定的时间内举行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及仪式的特定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二是泛指传统文化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的具体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文化空间。”[1]在一般文化遗产研究中,文化空间还作为一种表述遗产传承空间的特殊概念,“文化空间也称为‘文化场所’(Culture Plac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新的分类,这便是目前在各国广泛使用的五大类分类方法:(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该公约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涵盖了五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和文化场所。”[2]把皖北民间乐班置放于文化空间中加以研究,是因为乐班的行为离不开其存在的空间场所,它活动在一个公共性、文化性、民俗性、仪式性的场所里,是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相结合形成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空间。这里所指的“文化空间”应该是被赋予历史、文化、社会以及人的活动等特定的含义,是人类文化活动及行为所占据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交互集合体。民间乐班重要的职能就是要营造一种场所感和空间感,这里的场所或空间不是狭义的视觉艺术空间,而是民间乐班与特定的人和事占据的具有特定意义的场所空间,是一种与人的心理、情感、信仰、审美有密切相连的综合的文化心理空间。因此,通过田野调查和走访工作,了解皖北地区民间乐班在当下民俗、仪式等场合中的文化角色和文化行为,对民间乐班的文化活动与文化产品进行仪式性和象征性空间阐释实有必要。民间乐班不仅存在于现实物理空间中,也存在于象征空间、仪式空间、审美空间里,我们可以把空间观念看作人所编制的一张意义之网,体现着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惟其如此,才能完成对民间乐班整体文化意义的考察与研究。
二、 仪式空间中的民间乐班
民间乐班存在于现实世界里,它占据着一定的物理空间,是在现实中发生、存在并发挥着实际效用的客观事件。民间乐班的服务对象及范围基于人事、世事和时事,与人的日常生活习俗、音乐非遗及社会流行文化趋势相联系,民间礼俗文化以及各种仪式文化是乐班生存兴发的土壤和环境,因此,考察民间乐班的空间意义,离不开其所依赖的民俗场合和仪式场合。我们可以把民间乐班、民俗场合和仪式场合看作一个共时性的空间集合,民间乐班在民俗视野和仪式思想中体现了人们期许的有关社会、人伦、人道等方面的价值意义,进而实现其在空间意义上的拓展。乐班行为过程是人站在现实的端点上对其生活的世界进行空间筹划和意义塑造的过程。人和事总是作为空间事件而存在,而民间乐班的存在也必定与具体民俗仪式中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因此,对民间乐班的研究可以优先考虑使用民俗学或空间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而使得这一研究既有理论支持又有现实依据。皖北地处中原,生活习惯以及地域人文特征大体一致,体现了这一地区汉文化的一般特征。民俗活动出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里,构成了不同的民俗类型,如:0H0H0H节日节庆民俗、日常1H1H1H生活民俗、2H2H2H游艺民俗、集体性民俗、3H3H3H人生礼仪等,因此,也就造成了不同的民俗文化空间,皖北的民间乐班行为方式以及乐班用乐与当地文化风俗相互印证、相互塑造,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者。民间乐班参与并制造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也遵循和塑造了被普遍认同的大众文化惯习。
皖北地区的民俗学事件与各种社会生活及日常生活事件联系紧密,而这些事件又大都是通过一定形式的仪式行为来完成的。在以上所举的民俗事例中,集体性民俗、4H4H4H4H人生礼仪等可以说是皖北地区有代表性的民俗学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乐班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生礼仪(诞生礼、成年礼、婚礼、丧礼)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其所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做出意义阐释,它是以历史空间及社会空间为背景、以个人人生为主题的空间投影过程。人在现实空间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自身在生活、思想及权利方面的不同状况,在个人、家庭、族群、社区、世界等不同空间的承接、重叠、罔替中,确立了自身的社会存在和人生意义。人生礼仪中的各种仪式行为既是私人性的又是公共性的,但人生仪式行为从来都不是仅仅为了自身而设立或存在的,它是个体面对族群或社会对自身角色、行为所作出的仪式性论证、确认或承偌。如人生礼仪中的“婚嫁”仪式,虽然是有关于个体的,但涉及到不同的家庭背景、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及价值信仰等不同领域,是个体在一个特定的现实社会空间背景下取得两性关系合法化的重要步骤。“婚姻”是个人或个体性事件,带有个人意愿、目标、意图和动机,但个体意志的表达必须依赖于社会文化形式,才能获得公共认同,因此,作为“私人性的婚姻”就通过具有社会性的“仪式”实现两者互认。这里,仪式的功能就是“空间给予”或“空间再生”,它使两性个体空间得以“空间重组”,两性关系的合法化也就是“两性空间”的合法化。在此,音乐是一支塑造仪式感的强大力量,它使仪式正式而庄重,气氛热烈而令人心旷神怡,它给婚姻事件本身插上一面旗帜,标志着“这一天、这一刻”的非凡而特别,仪式及音乐让人在斑斓的诱惑中矗立驻足,此时此刻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者,还是处江湖之远者,一种源于生命自觉的仪式感便会油然而生,正如慧开禅师的一首《偈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我们可以把个人婚嫁仪式看作个人行为,也可以看作社会行为或民俗文化行为,因此,它发生在个人空间里,也发生在社会空间或民俗文化空间里,人类行为的纷繁复杂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多重空间结构,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现代人类”的存在有可能改变以往具有的语言、宗教、族群等文化属性而向空间属性迈进。
皖北地区汉民族居民占这一地区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民间民俗文化的宗教性质较弱,其文化的民俗性要大于宗教性,在空间文化的性质上较多地表现为以民间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各类民俗活动和人生仪式活动,民间乐班作为这些场合或空间中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深深地融入其中,它的“在场”塑造了其自身存在的现实性,同时参与、表达、创造、支持着传统本身,强调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积极性和有效性,乐班通过自身行为进入民俗叙事结构之中,在有效的现实空间内塑造自身,在民间民俗文化的空间内创造意义,在惯常的文化体系空间里定位自我。
二、文化传播空间中的民间乐班
民间乐班不仅出现在民俗礼仪场合中,同时还参与到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和音乐非遗文化等传播的场合中。因此,乐班的人员构成较为多元,有军乐队、舞蹈队,有戏曲演员、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唢呐、笙、爵士鼓等乐器演奏人员。民间乐班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的演艺团体,可以承接节日仪式、开业庆典等演出活动,可以承办政府部门“文化下乡”等形式的招标项目。
在文化传播中,民间乐班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身份而存在的,其活动一般出现在开业庆典、商业演出,乡镇的产品交易集会等场所。产品交易会是皖北地区在闲暇时节举办的大型集会,有些集会是约定俗成的,具有较长的集会历史,如利辛县芦沟集,每年有两次,分别是农历二月二十五和十月二十五,俗称“逢会”,已有近六十年的集会历史,类似的集会还有很多。这样的集会如今依然在举办,尽管形式与规模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依然能让人们感受到那一份浓浓的民俗风情。集会上的乐班文化活动也就成为了民众接受大众流行文化与非遗文化最直接的途径,传播内容多以歌舞、戏曲、相声、小品为主,但由于地方不同,传播的内容也有所差异。
民间乐班带来了音乐非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乐班表演的当地民间戏曲、民间音乐歌舞,满足了当地文化市场的需要。花鼓灯、推剧在皖北流行广泛,演出机会较多,琴书、坠子等小型剧目多用于家庭仪式喜庆宴会中,类似于堂会形式。皖北唢呐乐班更是远近闻名,灵璧的周家乐班就是一例。除此之外,皖北的界首苗集书会也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文艺大会,与会者彬彬济济,可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天南地北的艺人们或同台争辉或同场争艳,艺术形式多种多样、题材缤纷,历史的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传统的与现代的相得益彰,蔚为大观。书会每届5天,山东、江苏、湖北、河南等地的乐班及曲艺艺人相继赴会演出。“无时不说,无处不唱,无人不乐”是书会特色的重要体现,书会上演的曲目众多,鼓书、评词、坠子、琴书和民间戏曲不一而足,演唱风格真挚、朴实,特别适合农民口味,书会承载着地方曲艺和稀有曲种的传承与发展的重任,也是各地乐班发展自我、扩大影响的大好机会。
四、 象征空间中的民间乐班
仪式与音乐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家仪式到家庭仪式,其象征性是不言而喻的。思想和感情的表达依赖的是具体事物或事件的象征功能,世界各种祭神仪式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就仪式音乐而言,其象征功能尤为显著,以丧葬仪式为例,其象征功能实现了现实与虚无之间的空间转换,在仪式音乐的引领下,完成了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空间历变。人生在世的时候,以身体作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可人殁以后将在哪、去向何方?生者要给死去的人冥冥之中一个去向,才能两心相安。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仪式便是参悟,参悟人生况味、参悟向死而生的人生真谛。如何沟通阴阳相隔的不同世界,葬礼中乐班的仪式音乐提供了一个“通情达理”通道。青主说:“音乐是上界的语言。”巴赫说:“音乐是赞颂上帝的和谐声音,赞颂上帝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内容。”音乐感性材料的非语义性,赋予了音乐意义极大的阐释空间,从人类音乐产生的那一刻起,音乐的声音就被当作人神交通的媒介,当人们用语言或言语无法表达的时候,音乐开始了,绕过人的理性这一表达方式,从语言终止的地方走向一个超验的人神交互的世界,一个通过象征手段筹划出来的意义世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类思想史及文化史中从不缺乏这种“人神复调”,在人类证明神的存在并表达对其崇敬之意的诸多言说方式中,仪式及音乐对其意义的编码方式是最直接、独特和充满力量的。如何看待、理解人类这种精神现象,人类学家给出了诸多的解释,但根本一点也许是:通过仪式及仪式音乐能够表现灵魂与宇宙在时空上的连续以及灵魂在未来的延续,使神性观念得以彰显,仪式中民间乐班的乐声正是按照这一方式塑造一个特定的心理认知模式,引领世俗现实世界向“人神复调”空间的延伸与到达。
民间乐班在现实生活中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一方面,它往往是民俗文化叙事中的参与者或仪式功能上的讲述者,在现实场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仪式活动中通过仪式音乐营造出了一种象征空间,赋予仪式象征意义,引领参与者走进仪式的意义交换体系。仪式中的乐班音乐是一种物质存在,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来源于声音实体存在的场合和环境。如在仪式实践中,同一首乐曲可以用于不同的仪式环境中,如《好人一生平安》,既可用于丧葬仪式,也可用于庆典仪式,因此,仪式音乐与民间乐班一起作为一种符号具有了象征性,应是人类思想史、文化史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既是时间、空间的物理存在,又是精神存在和文化存在,根据卡西尔的观点,人不在于其物质性存在和政治性存在,本质在于人的文化性存在。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久而久之会形成习惯,习惯会成为规约,最终成为被共同遵守和履行的价值导向。人生活在一个自然物质的世界里,也生活在一个由价值、符号、观念、精神组成的世界里,从空间本身到空间观念是人的经验内化的结果,文化存在是人的最终归宿。民间乐班的仪式音声文化在一定的物理空间中发生,它有一种影响、一种指向,一种秩序,具有一种不同于现实意义的象征空间,在文化传统里,它往往被另一个具有着深广文化基础的神话空间话语方式所指代,而这也正是民间乐班的空间意义指向。
象征是人的精神构建或灵魂构建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是人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物理空间实在性与象征空间的抽象性共同塑造了人的生活空间,既有现实依据又有概括升华,普通人虽然没有高深的艺术理念,但并不能阻止他们诗意的想象和联想,因为丰富的历史人文经验和自身的生活经验足以让人们展开诗意想象的翅膀翱翔于情深意永的精神世界。
民间乐班存在的意义在于空间筹划、意义生发、情感寄托,乐班及其仪式音声在物质与精神、抽象与具体、奥义与俗理、复杂与简单中构筑一幅图景,以一种民间叙事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情境关联”的音声文化空间。
[1]滕海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特点[J].东南文化,2009(3):56
[2]张赐东,李士英.文化空间视野下客家土楼对客家武术影响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11):78
Folk Music Class in Cultural Space: Taking Folk Music Classes in Northern Anhui as an Example
ZHANG Yu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Anhui)
The research of folk music group in cultural space is to explore its space of existence and significance, study its position in music culture, inheri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exert a positive role in country music culture construction.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the research will discover the roles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behavior of folk music group in the contemporary folk custom and on ritual occasions. The paper will analyze and interpret folk music class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products by us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of art. Folk music group is not only physical space, but also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space, such as symbolic space and aesthetic space. Only in this way can people complet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olk music group.
folk music class; cultural space; ritual; folklore
2018-04-20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皖北音乐非遗文化传播与新农村乡村文明构建”(SK2015A13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皖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机制研究”(Sk2014A070)。
张宇(1968- ),男,安徽利辛人,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民间乐班的文化意义。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4.06
J607
A
1004-4310(2018)04-00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