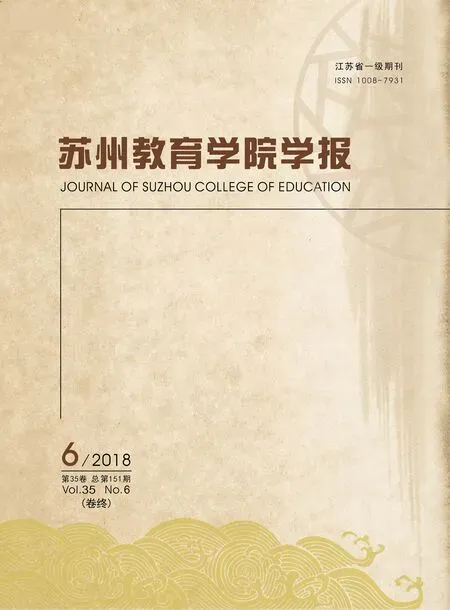混杂性:流徙空间下的香港文化身份特征—以19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为例
徐诗颖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谈到香港的“主体性”,必然与文化身份的建构有着密切关联。“文化身份”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意味着一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1]具体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作家们的身份认同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关系性、叙事性和想象性。在关系性上,混杂性的文化身份特征使作家无法追根溯源;在叙事性层面,作家对城市空间展开了多元想象,“空间隐喻”为身份认同提供了想象的载体,希望用小说的“虚构”来对抗现实的“虚无”;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作家试图建立超越中西话语支配的“第三空间”,用“边缘”和“夹缝”这两种具有想象性的视角潜在表达、突显香港文化自身的“主体性”。
一、寻找根源文化身份的虚妄
何谓“文化身份”?瑞恩·赛格斯提出:“通常人们把文化身分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分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分’(identity)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分的观念当做一种建构(construction)。”[2]由此可见,文化身份具有静态固定和动态建构的双重属性。斯图亚特·霍尔也认为“文化身份”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单向性和寻求共同性,一个是异质性和寻求变化转移。相较而言,霍尔更倾向于后者,即将身份看作“建构”的结果,可以出现充满异质的多样性。既然身份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它就需要认同的确认,孟樊认为:“从后现代来看,Identity本身变得既不确定、多样且流动,正需要有一‘认同的过程’去争取。换言之,身份(或正身)来自认同,而认同的结果也就是身份的确定或获得。”[3]
香港独特的移民文化,造就了它流徙的特征。[4]香港是一个主要由中国内地移民聚居而成的城市,且受英国殖民统治长达一百多年,流徙性成为其文化的重要特征。此外,由于英国政府实施统治意图的复杂性以及地理位置相较于内地的边缘性,香港自鸦片战争以来便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公共空间”。周毅之将香港的意识形态作了如下概括:“以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体,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殖民主义文化深刻烙印的,多元化、混合型意识形态。”[5]具体到文化领域,也斯认为香港文化的混杂性在1950年代就已经形成。城市与文化生态的演变形成了结晶化,不同文化的汇聚形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文明形态。如刘以鬯在《〈香港文学〉创刊词》中所说:“它是货物转运站,也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6]因此,“混杂性”①香港学者在使用“混杂性”这一概念时是基于本土文化特征提出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传统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历多次的碰撞与交融,民族意识与殖民主义意识此消彼长,使构成香港文化和文学的元素变得更为多样和复杂。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沿用了这一层面上的意义。便成为“香港”这一流徙空间中非常重要的文化身份特征,也得到了华文学界的认可。
“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使得多元文化同时并存于香港这个独特的空间里,但它也使香港人希冀寻找根源文化身份认同的努力显得虚妄且徒劳。这种根源文化身份的认同既不指向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更不能等同于本土文化。如洛枫所说,香港是“既不属于中国本土又不属于英国传统的产物。事实上,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历史里,透过兼收并蓄的包容性,香港已发展出一套属于她个人的、唯一的、独特的文化形态。内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亦有西方外来的冲击和养分,结合而成国际性大都市的文化模式”[7]。也斯也相信香港具备“包容性的空间”,成员的文化身份是“混杂性并非单纯的”,具体表现在“香港人相对于外国人当然是中国人,但对于中国内地的朋友,他又好像带一点外国的影响”[8]。实际上,香港社会早已摆脱了殖民政府或殖民者的计划和预期,发展为一个相对自主并拥有自我特色文化的社会。因此,阿巴斯认为拥有混杂文化的香港成为世界殖民史上的特例,因为它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竟先于“去殖民性”(decoloniality)。[9]
在香港这个混杂多元的文化语境下,都市成为包容异同的空间,像潘国灵的《我到底失去了什么》、李碧华的《霸王别姬》、颜纯钩的《关于一场与晚饭同时进行的电视直播足球比赛,以及这比赛引起的一场不很可笑的争吵,以及这争吵的可笑结局》等作品均揭示了在香港这一空间中寻找单一文化身份认同的无效性。
除此之外,茶餐厅文化以及不少港式食品都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结果。无论是来自中国内地还是来自西方的食物,在香港,都不会被原封不动地承袭,而是会进行“在地化”处理。如在香港的茶餐厅里,有一种非常著名的饮品叫“鸳鸯”,它并非隐喻中国传统诗词中的浪漫爱情之意,而是指向一种混合型饮品,奶茶和咖啡的混合—咖啡来自西方,奶茶是中国茶英式化后再经由民间转化而成为的“香港制造”—“恐怕是非常自觉彼此‘他异性’的一种结合”[10];又比如香港特产“豉油西餐”,利用中式豉油和铁板的高温弥补平价肉扒的不足,从而使西餐大众化,让普通百姓也能品尝西式风味。这些港式食物产生的过程,也见证了香港历史(尤其是香港人日常生活史)的发展。另外还有“瑞士鸡翼”“金必多浓汤”①“瑞士鸡翼”源自香港的茶餐厅。据说很久以前,香港的茶餐厅推出了这道由豉油和冰糖腌制的菜式,一位外国人品尝后觉得非常美味,不停对侍应说调味酱汁“sweet”(甜)。餐厅老板英文发音差,以广东话的发音理解为“Swiss”,即中文“瑞士的”之意。同时,在那个时候给菜式取外国名能提升档次和品味,于是这道豉油鸡翅就正式取名为“瑞士鸡翼”,甜酱汁就叫“瑞士汁”。“金必多浓汤”本身是海派西餐的名菜,在奶油汤里添加鱼翅鸡茸,是一道中西合璧的菜,颇合上海前清遗老遗少以及旧式富商巨贾的口味。1949年后,这道汤流传至各地华人聚居地的“豉油西餐”店。等,都是中西文化交汇下的名菜,而且属于在日常的误读和误解中发展出来的文化想象。
这种东西食物文化交汇的情形也反映在小说里。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11]写于后“九七”时代,用“食物”作为切入点来观察香港人的混杂性文化身份特征以及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汇中重新找寻文化归属感。也斯借食神老薛的口强调“食物是理解香港全面政局与个人心理之钥”[11]131。梁燕丽在分析也斯小说时提到:“‘食物’意象既带有生物成分又带有社会成分的双重属性呼应了后殖民文学表现的两大主题:生存环境和身份认同的转型。”[12]林沛理也谈到:“到香港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港人对食物的热情隐藏着对生活其他范畴的失望。”[13]而这些失望的产生,主要源于香港人找寻根源文化身份的虚妄。梁燕丽分析小说主人公“我”的困惑:“以食物作为隐喻,东西方融合而各自保持尊严,既不西方中心主义,也不自我东方主义,这在理论上似乎不可能,但在香港人的生存经验中似乎早已存在,这难道正是后殖民烙印?这是‘我’所不能解的问题。”[12]这种虚妄让无根的香港人时常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中,但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他们慢慢适应了这种混杂性身份,并学会了持更多的理解与包容,这从小说中他们对待食物的态度便可管窥一二。
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里,“我”的酒吧开张不久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为“我”和老何庆祝生日,并带来不同的食物:中东蘸酱、西班牙头盘、意大利面条、葡式鸭饭、日本寿司。在食评人薛公的领导下,“我们”还弄出了“热辣辣的夫妻肺片、甚至夸张地用油锅烧出了糯米酿猪肠”。[11]2可到了后来,“我”发现想在饮食问题上取得共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并发出了疑问:“这群人要再像以前那样走在一起就难了,真有一种可以适合这么多不同的人的食物和食肆吗?”[11]16然而,这不妨碍在香港寻找能令“我们”有过愉快进食经验的地方。同时,在这个具有流徙特性的空间里,“我”的朋友圈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这反而让“我们”更珍惜彼此的情谊,如同最后“我”所感慨的:“有些人离开我们到别处生活,又有些新人加入进来。这是个新的时代。事情有时不太顺遂。我们对事老是各有不同的意见,彼此争吵不休,有时也伤害对方,但结果又还是走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也会学习对彼此仁慈?”[11]19也就是说,在“混杂性”的文化空间里如何找到“自我”并且定位好自己的文化身份,是香港人在后“九七”时代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在小说的最后,“我”已经慢慢领悟到生活在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不是找寻根源文化身份,而是如何在这些混杂性身份中学会安然处之,并且获得归属感。赵稀方对此的理解切中肯綮,认为这显示出也斯独特的香港后殖民立场:“小说从香港食物的外部混杂性的角度,颠覆了香港‘本土意识’的统一性。在香港,要寻找和坚持某种本土和正宗看来是十分可疑的,有的只是多元混杂,无怪乎,‘我’最后所想念的是一种法国烹饪与泰国调味的结合,一种跨文化的‘后殖民食物’。”[14]
茶餐厅一度被视为“半唐番”“杂种”“新本土”“通俗文化”的代表[15],并深深植入香港文化的骨髓之中。陈冠中的《金都茶餐厅》[16]正是选择了香港这种独特的茶餐厅文化作为切入点来考察其混杂性的文化身份。陈冠中用“半唐番”来形容香港的“混杂性”文化身份:“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折衷主义,拿来主义,是时尚噱头,是‘刻奇’(Kitsch),甚至是无心之得。然而,当万千半唐番品种在文化浓汤里适者生存,存活下来时,就出现质的变化,得到足够的承接,开始了自己的传承,成正果的,叫‘新本土’,叫‘后现代’,叫‘文化身份’。”[17]86香港的茶餐厅文化就是适者生存的结果,是香港“半唐番”文化身份的具体表现。对此,陈冠中也不得不承认:“想不到,经过了二十年,我终得承认这是代表香港的。”[17]85于是,在小说里,当介绍金都茶餐厅的菜式时,他把蕴含在其中的“半唐番”文化展示了出来。
烧味系列、粥粉面系列、碟头饭系列、煲仔系列、煲汤系列、炒菜系列、沙薑鸡系列、肠粉系列、潮州打冷系列、公仔面系列、糖水系列、越南汤粉系列、日式拉面系列、星马印椰汁咖喱系列、意粉通粉系列;
俄罗斯系列—牛肉丝饭、鸡皇饭、罗宋汤;
西餐系列—炸鸡脾、焗猪排饭、葡国鸡饭、忌廉汤、水果沙律;
西点系列—菠萝油蛋挞法兰西多肠蛋薯条汉堡热狗三文治奶茶咖啡鸳鸯;
厨师诚意推荐新菜系列—泰式猪颈肉、美利坚童子鸡、秘制金银蛋咸鱼比萨。[16]212
“我”感慨道:“全球化在我金都,金都厨房真Can Do。”[16]212茶餐厅文化发展为香港人的“Can Do”精神,当金都茶餐厅在2003年因香港环境不好而宣布结业时,看见大家对香港前景持悲观态度的“我”发出了感慨:如果茶餐厅都死,香港真系玩完。可见,茶餐厅(半唐番)文化已经在香港拥有强劲的生命力。与其在混杂性文化空间中寻找根源认同的共识,还不如承认香港本身具有的混杂性文化身份就是最大的共识。用陈冠中的话来说,就是“半唐番是香港多元文化中最能建构本土文化身份的一元”[17]91。于是,大家在即将结业的茶餐厅里发起“救亡图存”的签名运动,并在这个公共领域发表各自的看法,齐心协力,重新确立了茶餐厅“绝不走高档,坚决发扬港式茶餐厅文化,誓死与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全球化和美式速食文化侵略,打破大财团大地产商垄断”[16]219的立场。这其实也暗示了香港人希望能够从社会危机中走出来,“陈冠中取‘茶餐厅’作为香港危机的‘底线’,以跳脱利落的粤方言俚语,将‘金都茶餐厅救亡运动’卡通化,正是以小喻大,以特殊喻普遍,慧眼独具”[18]xvii。不过到了最后,“我”还是产生了犹豫,因为作为小市民的“我”无法预测餐饮业前途的稳定性,最后陷入两难之中,小说最后留下了悬念,留下了“我”的游移不定的态度,但换个角度看,这“正暗蕴草根半唐番的生机与活力”[18]xix。
实际上,经过多年发展,香港的“半唐番”文化已自成系统,蕴含在其中的多种文化并行不悖,并渗透进人们的日常交际语之中。香港诗人崑南写过一首名叫《旗向》的著名诗歌,点出了文言、白话、粤语以及英语在香港文化语境里交汇的情形。这种草根的“半唐番”文化已经在香港人的心中获得了默许,且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也使得香港经验由本土和多种“他异”经验共同组成,并且处于不断变动调整的过程中,“香港经验”不再仅仅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理解,而是已经超出地域范围且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元素。李欧梵在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化批判领域时也承认:“香港的政治文化已经是一杂体;它结合了政治和文化,并且将文化批评与日常生活商品相融合。”[19]因此,承认混杂性的文化身份才能恰切概括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意识,任何试图寻找根源文化的努力都是一种虚妄。
二、展开城市空间叙述的多元想象
空间被不同立场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挪用,“空间隐喻为本土身份认同提供了想象媒介,其中城市更是与香港这种大都会的所谓‘本土’文化密不可分的”[20]。作为公共空间的香港,小说为这种“空间隐喻”提供了展示的载体。尤其自回归过渡期以来,不少小说家对香港的未来感到迷茫和无力,担心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会由混杂性逐渐变成单一化。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小说家需要思考“如何书写城市现实多元复杂的面貌,提防不要把它简化”[21]。小说家常常把对城市的看法通过寓言的方式表达出来,期待能形成对这个空间更多元的想象。王德威对香港文学进行考察后发现:小说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以“叙事作为行动”的总称。[22]他认为:“香港在过去的几百年来,从无到有,本身的传奇色彩其实就是小说从无到有,最具有创造性与想象力的一种实践过程,香港的未来仍然需要小说家来创造不同的说法,给予不同论述的可能……是香港这个地方,再一次让我们理解到,小说作为文类生生不息的可能性,而以小说对抗当代,可能是这一代作者和读者对于小说,对于香港的最深期望。”[23]实际上,这与香港不断创造容许自由想象的异质性书写空间有很大的关系。香港文学化不可能为可能,竟折射了香港本身开埠以来,无中生有的想象力与韧性。[24]
相较于中国文学正统的“乡土/国家”论述,现实/写实主义并未能在香港取得主导性地位,反而是在城乡交接地带形成多重可能的书写空间。小说家以“想象香港”为出发点,建构一个“存在”的香港,而不是“已然”的香港,从而进一步定位香港的文化身份。凯文·林奇对如何理解“作为文化形象的城市”曾提出如下看法:“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25]因此,关于如何“想象香港”,要视乎小说家如何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也就是他们叙述香港的策略。在“书写的方法上,城市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应该怎样写城市,要怎样认识城市?”[21]对此罗兰·巴特提出了一种答案,可以将认识城市视为一种谈话,“其实这种谈话是一门语言:城市用它和居住者对话,我们通过居住在这里、徜徉期间、观察它来使用这门语言,使用这座城市—这个我们居住的城市”[2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家对“城市”的想象与香港的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并不是完全在现代主义等理论的观照下进行书写。自从20世纪70年代西西在《快报》连载著名长篇小说《我城》[27]以后,“X城”成为小说家建构这座城市的代名词,这是因为《我城》“带出了以香港为本位,我手写我城的‘我城’意识和书写风气”[28],这源于《我城》里一段能恰切反映当时香港人身份认同困惑的经典对话:
我没有护照。他们说,如果这里的人要到别的地方去旅行,没有护照是麻烦透顶的事。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没有护照而想到别的地方去旅行,要有身份证明书。证明书是用来证明你是这个城市的人,证明书证明你在这个城市里的城籍。
你的国籍呢?
有人就问了,因为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于是说,啊,啊,这个,这个,国籍吗。你把身份证明书看了又看,你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27]156
主人公阿果在一次出游时被问及“喜欢做谁的子孙”时,很肯定地回答“当然做皇帝的子孙”[27]156,有人就善意地提醒他“做皇帝的子孙”在这个城市是没有护照的,也就是说没有国籍。这才让阿果恍然大悟,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自省。西西发明的“城籍”一词,恰好暗示出香港人身份的无所依归,于是“我城”便成为了香港人形容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家园和土地—香港—的代名词,以此确认自己的归属感。20世纪70年代,正好是香港意识高涨的时期,也是香港人建立与城市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吕大乐形容当时是香港人“建构一个自成一体的香港社会的过程”[29]。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香港回归期限的确定,香港人对香港的空间想象有了新的转变。坚固的“我城”意识不再,随之而来的是要面对一个摇摇欲坠的“浮城”。连之前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持无比自信态度的西西也开始陷入彷徨之中,并创作了“肥土镇”系列寓言和《浮城志异》,《浮城志异》中已经没有了《我城》的那种“轻逸”感,“浮城”隐喻着在《基本法》结构草案制订下前途未卜的香港命运,文字读起来“轻”,但实则蕴含着“无根”的“重”。虽然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浮城并不是指代“香港”①张系国提出:“浮城是香港吗?我肯定告诉读者它不是!……却可能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董启章:《说书人—阅读与评论合集》,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44页),但无疑用“浮城”来形容当时的香港处境,是为想象香港开辟出了新的叙述空间。
香港的前途命运如“浮城”一样充满未知数,整座城市也陷入了集体的抑郁氛围之中,“仿佛某种灾难随时要发生,但又不知是什么灾难”[11]143。当压抑气息在整座城市蔓延之际,“世纪末”的放纵狂欢心态也悄然在香港人心中“燃烧”。也斯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表达出这种心态:“大家满腹疑虑,诿过于人,但不见得就能令自己心里更加快乐。总之有得玩就玩,今朝有酒今朝醉!”[11]143因此,一种种怪现状在城市中轮番上演,使这座城市陷入了“狂城”的乱象。
心猿的《狂城乱马》[30]以嬉笑怒骂的无厘头方式描述了这些怪现状,从中也渗透着“世纪末的华丽”的凄然之美。在香港即将跨越“九七”之前,小说用“狂城”暗喻香港,“乱马”暗喻香港人。一方面,这种“狂”与“乱”将后现代的混杂性美学空间渲染得淋漓尽致。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也谈及:“我关心的是比较古怪的小问题:雌雄同体、都市空间、混杂(不是混蛋)文化,大概比较适合在这样的空间活动。”[30]246《狂城乱马》讲述了中年摄影记者老马和八卦版记者纽约水无端落入一场政治风波,并且在这个“都市迷宫”中想办法逃离,在这场冒险旅程中,老马目睹混杂文化如何融会在这座城市的多元空间里:“小贩在路旁摆了档摊、小吃店的蒸笼搁在门前、几个青年男女染了头发在戏院门前扭动身躯、几个孩子在玩溜板、菲佣坐在台阶一角野餐”,这“看来充满危险但又是各种各类活动同时和平共存”[30]244-245的情形,使脱险后的老马认出“这正是他喜爱的城市的混杂空间”[30]245。另一方面,“狂”与“乱”的混杂状态又让小说主人公不知如何摆脱受控制的阴影并重新找回自我身份,小说这样描述老马的心态:
我们从历史的噩梦中醒来,摸不到自己的头颅。
我对着一盘混杂的麻辣火锅,或我对着影像的拼盆,一曲众音纷陈的即兴爵士乐色士风的演奏。历史要作一个总结了,一双巨大的手合上了账簿。
一切都注定,一切都已太迟了,我在哪里?
我不知自己身处何方,梦里不知身是客。
太迟了,我赶不上。
总是赶不上,历史的渡船,是零余者,幸存的人?
老天,醒来吧?
我已醉了,你真的醉了?
真的,天南地北,一片旋转而晕眩的梦,你是什么呢?
你努力,努力从恶梦中醒来,带着历史血淋淋的恶梦。
你不知该怎样做,你不知你如何可以不钉死在他人的影像里,做自己的主人。[30]204-205
从“历史的噩梦”“混杂”“历史的渡船”“零余者”“他人的影像”“自己的主人”中,可以体会到老马面对过去的无力和面向未来的困惑。老马和纽约水无端卷入一场政治大阴谋,中途历经香港的过去与当下发生的种种混乱事件,最后艰难逃离并重回充满是非的人间。老马和纽约水的香港人身份使其遭到高干子弟的嘲笑和鄙视,几度落入“无家可归”和重新寻找“家”的境地。最后虽然成功脱险,但已是伤痕累累,只能在除夕夜默默等待新年的来临,做回自己家园的主人。这也暗喻了回归前夕香港人对自我身份的疑惑以及对未来的疑虑,希冀能够摆脱外在势力的干扰,重新定位作为“主体”的自我文化身份,能够在这座城市重建“精神家园”,而不再做历史的“零余者”、心灵的“流亡者”。
时间进入后“九七”时代,香港人“悬浮”乃至“狂乱”的心终于安顿下来。然而,当身体不再选择离去,不少香港人却发现精神依旧荒芜,这座城市于他们而言极其陌生。有许多隐疾会随时因外界力量的干扰乃至摧毁而发生病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断加速,使这座城市走向消亡。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香港人的心灵继续处于漂泊甚至是流亡的状态。此处的“流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萨义德对此作了解释:“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31]如同《狂城乱马》里提到的,是为了不钉死在他人的影像里,为了让心灵得以安顿。于是,在一些小说家的想象里,香港就如同一座逐渐腐化、糜烂进而消失的城市。潘国灵在《写托邦与消失咒》[32]里就把这座岌岌可危的城市称为“沙城”,将心灵处于流离失所和流亡状态的香港人喻为“消失人”。小说借写一位不安于现状的作家的消失来隐喻“沙城最终是会变成泡影的”[32]269结局,而且这结局是不能扭转与不可抵抗的。“沙城”一名是如何得来的,小说这样写道:
真正巨大的冲击还要等“时间零”的几年之后,沙城人抵受得住自己的尘埃抵挡不了外来的风暴。一场沙尘暴自北方吹来……但那种入侵浮城的粗沙粒经化验,很快证实来自极其干旱的沙漠,跟浮城的气候完全不符,确定是一种外来的异质物,经过动物或人类宿主的流动身体,而悄悄进入浮城的。为防止吸入粗沙异质物,浮城人纷纷戴上口罩如戴着一个面具似的,从此没有卸下。气候剧变,沙尘暴自此隔不久从外袭来,大大小小不同级数的,内含不断变种的毒。毒成为常态,变成悬浮粒子,变成每日生活的景致。终于再无漂浮的梦,只剩沉降,浮城告别,正式进入“沙城”时代(如今我们称“浮城”,也叫“前浮城”了)。[32]268-269
“外毒”入侵,使得防御能力极弱的城市迅速倒下,随着更多病毒的侵蚀,浮城人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已无所期盼,这座城市已失去了“造梦”的可能,只剩下活生生的残酷现实。在潘国灵的笔下,沙城“充斥过度发展的消费与浪费、政治的压抑与禁制、文化的稀薄和功利、社会的分歧和贫富不均、族群的决裂和孤绝等等积劳成疾的病变,而当这些人与城市的疾病变成绝症以后,便只有消亡的终局”[33]。但叙述者对此并没有完全绝望,而是为生存在这座无根之城的人创设了新的空间—“写托邦”。主人公兼“消失人”游幽就是因不能忍受这种失去想象力的唯一空间而遁入消失之境“写托邦”的作家,并把即将消失的沙城写入他的故事里。
这个“写托邦”类似于福柯所设想的“异托邦”(heterotopias)的混杂状态。如果说“异托邦”是作为“乌托邦”的镜像而存在,那么“写托邦”就对应着“沙城”,并照见沙城的“存而不在”。因此,“写托邦”给这群心灵的流亡者一个重新观照自我与沙城关系的空间,成为他们寻求心灵庇护与安顿的处所。游幽虽然无法返回沙城,但在“写托邦”里实现了安静写作的愿望,能够“完全从现实世界中撤走了,不再属于它自然也不再受困于它”[32]76,最后获得心灵上的解脱。“沙城”虽然是小说家对这座城市的一种想象,但或许能给当下充满“隐疾”的城市一个有意味的警醒。
从“我城”“浮城”“狂城”到“沙城”这条发展线索里①本文归纳这条线索是基于小说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下香港呈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面貌,主要表现为线性发展的顺序,但也有共时发展的形态,如“浮城”与“狂城”其实是共同呈现出回归过渡期香港人的无根感与面对未知前途的恐慌感和压抑情绪。,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家对这座城市的想象是以逐渐悲观的面貌呈现出来的—“我城”在当下的种种危机下慢慢走向消失,甚至是灭亡。出现这种想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香港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以及多元的文化空间会随着回归以及后“九七”时代的来临而逐渐消失。香港以及香港文化的前途,是否真的如小说家所想象的那样无望呢?这确实是当前“香港书写”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与香港在“混杂性”文化身份中如何定位自我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小说家们希冀通过“想象香港”的方式来保存这块独特的混杂性文化空间,为重返“我城”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三、建立超越中西话语支配的“第三空间”
既然无法有效确认单一的文化身份认同,那么在具有混杂性特征的流徙空间里寻求并建构香港文化的“主体性”身份,便成为不少作家笔下香港书写的关注点。小说这种形式天然与叙事紧密相联,文化身份的探寻多由小说叙事来承担。在“回归过渡期”以及后“九七”时代,恐慌、焦虑和无助等种种负面情绪存在于不少香港人身上,而且他们始终害怕失去主体发声的权利。不少作家同样对回归后的香港文化前景充满迷茫和担忧,到处弥漫着不安全感,而这些感受主要来源于他们将内地文化视为“他者”,害怕被作为“他者”的文化所收编,对当代中国文化也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为了能使香港文化重新拥有自主发展的空间,以逃离中英双重文化殖民力量的控制,他们期待香港文化能形成一个既包容又超越于中国内地和英国文化话语力量支配下的“第三空间”。
在试图站在“第三空间”立场来书写“香港”时,香港作家更多着眼于香港文化与中国内地文化那种既融合又冲突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探究“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内在矛盾”的命题。为了能有效抵抗分别来自中国内地文化和英国文化所形成的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使香港文化永远保持一种不受某一文化话语力量支配下的开放多元状态,“第三空间”理论在“九七回归”的现实背景下受到香港及海外学术界的青睐。受此影响,不少香港学者认知香港的文化身份亦是如此。用美籍华裔学者周蕾的话来概括,“第三空间”反映的香港是一个“既不是寻根也不是混杂”的“崛起的社会”[34]。
然而,这种视角的探讨并未能有效缓解他们对香港前途焦虑不安的态度。事实证明,“混杂性”的文化身份并未能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书写切实有效地建立起“第三空间”。不少作家以“香港”作为一个隐喻的整体,通过寓言化、陌生化、超现实以及志异想象等现代和后现代的处理手法,将“第三空间”的想象寄托于香港以及香港文化的未来。这不仅使小说中的文化身份话语有了象征性与故事性,还具有了想象性。身份的表达始终是一种和自我相关的想象[3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众声喧哗的文化场域里通过“边缘”和“夹缝”两种视角潜在表达建设自身主体性的诉求—香港回归后将作为一个有别于中国内地文化的特殊的独立文化主体而存在。
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香港的故事很难说。确实,香港是一个不容易说得清楚的城市,它的文学也一样,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道得明,因为它的文化十分多元,光谱十分宽阔,我们很难对它作出一个简单而明了的概括。[36]这其实与香港“‘身份缺失’的困惑和焦虑,‘身份认同’的迷思与寻觅”[37]有着密切关联。纵观涉及“第三空间”话题的香港书写,每一个写作个体都表现出对“香港”这一喻体想象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建立于对香港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时空发展的不同理解之中。在有关身份认同的文化批评中,不少论者一再强调,“中国性”应该是复数的、具有开放性的意符。香港学者朱耀伟曾说过:“‘中国性’应被视作‘形成过程’和‘开放的意符’。再者,当我们同意‘诸中国性’(Chinesenesses)之时,也同时要提醒自己构成‘诸中国性’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也必须同样是复数的。”[38]朱崇科也认为:“由于时空和历史因素等的影响,中国性也应当是复数的和开放的。”[39]由此可知,香港的身份是混杂的,是复数的,应被视作“成为”的过程和“开放”的意符。既然如此,那么各种“香港”的故事既是复数的,也是“开放的能指”,共同展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