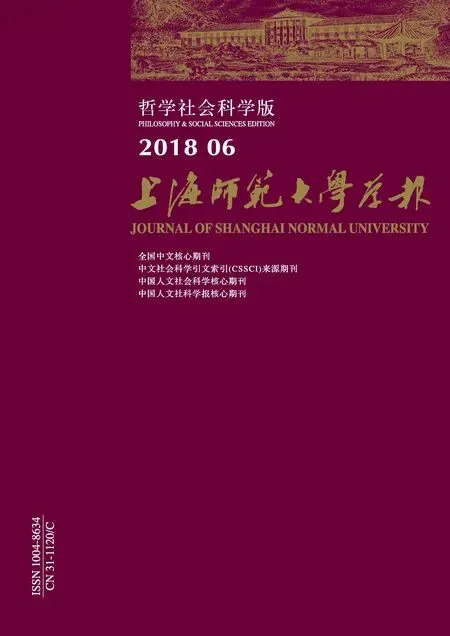神圣人、机器人与“人类学机器”
——20世纪大屠杀与当代人工智能讨论的政治哲学反思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062)
进入“后人类”?
最近十几年来,学界各个学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过去的七万年称作为“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①也就是说,过去七万年间,人类,成为影响这个星球面貌变化的最大因素。但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对某事物或事件进行命名的时候,往往也是它正在快速走向消亡的时刻:“人类纪”被提出的时刻,我们也恰恰快走到它的边缘。当下世界内越来越快的多种变化,都似乎在标示着:我们正在走入一个“后人类”的未来。
我们知道,在过去七万年间,科技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发展,而是抛物线式发展,想想最近几百年、几十年乃至最近这几年,科技呈爆炸性加速度发展,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用“指数级”来形容这个加速度。②现在,我们一方面在见证(乃至体验)生物工程、仿生工程对人类自身的各种改变——这个世界中正在剧增各种半人半机器程度不一的“赛博格”(cyborg)、生化合成人……③另一方面,无机的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处理及其自我学习能力,已经在很多领域使人的能力变得完全微不足道。我们感觉正在接近下一个“奇点”(singularity),奇点之后人类主义的一切叙事都变得无关紧要。
关于各种“后人类”前景的讨论,已经在学界与大众媒体展开得如火如荼。然而在我看来,有必要把当代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人类学机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引入这个大画面中来——通过这个“理论工具”,④我们可以对当下时代、不远的21世纪中叶,以及刚过去的20世纪,取得一个穿透性的政治哲学反思。
第一眼看上去,“人类学机器”这个概念似乎很“后现代”,阿甘本对它的经营也是充斥其标志性的“碎片式的风格”(fragmentary style),⑤以至于《阿甘本词典》⑥的编者竟然没有想到在书中将它作为一个词条。但在我看来,这个在阿甘本思想中并不核心的术语,对于我们思考那来临中的“智能时代”的政治问题,极其具有批判性-分析性价值。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把握这个抽象学术概念:实际上,我们生活中一直有一台无形的巨大机器,构成了我们认知中无可动摇的等级区隔:植物—动物—人(—神)。这是一种生命等级制,但我们却习以为常,并视之为正常、正当,或者说“自然”。造成这种“本体论效应”的,便正是人类学机器的“魔力”之一。而阿甘本则号召我们远离形而上学,去研究“关于区隔的实践的和政治的谜团”。⑦
暗含于“人类纪”中的“维度变化”
“人类纪”那七万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体格弱小、“力不若牛,走不若马”⑧的“智人”(homo sapiens),如果只凭借其自然性的体力,最多只能处在食物链的中端。然而,通过在“人类纪”开端的某个时刻所发展出的虚构叙事能力,智人不断扩展出大规模群处合作能力——正是这份能力,最终使其跃升到食物链条的“终端”,成为地球史上最致命的生物物种。该物种从此遥居在上,从未再返回食物链其他位置。
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在“人类纪”很靠近当下的某个时刻,智人拥有了一套“人类学机器”(但并未意识到对它的“拥有”)。当然,这台机器并非机械性、物理性的,而是话语性的——它本身是一套独特的虚构叙事,且处在不断的“升级”变化中。但是,当这台机器最初被话语性地制造出来、并进入工作状态以后,智人和其他生物,就不再是“中端”与“终端”之别。他们之间,无声地——同时惊天动地地——发生了维度的变化:智人直接刺破食物链的单一向度,而变成另外一种物种。
在这一维度变化前后,智人和其他生物的具体互动,在形式上并没有剧烈变化(彼时前者对于后者尚不拥有绝对的主导性力量)。然而,我在此处要提出如下关键论点:这个维度变化,具有隐秘的政治后果,即,生产伦理-政治正当性(ethico-political legitimacy)。同样的行为,一旦经“人类学机器”处理之后,就能够产生出完全不同的正当性:譬如,杀戮这个行为很残忍,但通过不同维度的转换,就能变得具有正当性。人吃动物、动物吃草,这是——借用柏拉图主义古典政治哲学术语——“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的,人们看到都会很坦然(处于同一维度的狮子吃羚羊尽管也可以被理解为自然正确,但至少会产生残忍感与不适感)。但反过来,任何低维度生物吃高维度生物,则都会被看作绝不能接受。即便对于狗这个人类最亲密的物种而言,人吃狗,一些爱狗人士受不了;但反过来狗吃人,所有人都受不了。2016年4月英国利物浦当地法院判处了一条叫布奇(Butch)的狗死刑,因其吃掉了主人去世后的尸体。这条新闻以《“你的狗会否吃你死尸?绝对!”》为标题,传遍全球社交媒体,从脸书(Facebook)到微信上一片惊呼,纷纷表示“现在看自己宠物的眼神都不一样了……”⑨在今天,各种词典和百科全书会很“客观”地在不少动物的词条下写上“害虫”或“浑身都是宝”(肉味鲜美、皮可制革、鞭可入药……)等描述。然而我们需要反过来追问:我们要消灭“害虫”,“灭四害”,蟑螂、蝗虫、麻雀、老鼠等动物就该死;但在老鼠等眼里,我们是什么——是“害虫”或者“害‘人’”?我们没有习惯去想这个问题。⑩为什么没有这个习惯?因为有那台“人类学机器”在默默地不断运作着, 并不断巩固着建立在生命等级制度上的诸种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
在“人类学机器”里面,人和动物变成了完全两个维度上的生物,处在生命等级制的不同级中。我们不但吃各类动物,而且为了吃得爽而圈养动物、改造动物。“转基因”在该名词本身并不存在的漫长“人类纪”历史中,早已被不断实践——智人们在大量灭绝物种的同时,不断改造、培育出各种新的非自然的品种,除了专门供其食用,大量被征用来役使(当作坐骑或劳力),产生经济价值(蚕丝、羊毛、皮革),或仅仅是把玩(翻筋斗、跳火圈)。
纳粹政治:“人类,太人类了”
在阿甘本看来,正是这套制造政治正当性的话语机器,使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灾难:“犹太人,亦即,在人类之内被制造出来的非人,或活尸体和昏迷人,也就是,人之躯体自身内被区隔出来的动物。”当犹太人被卷进“人类学机器”、并被它归到生命等级制中的另一个维度后,屠杀犹太人就变成“灭害虫”一样的工程,具有充足的正当性。而当时在纳粹的宣传机器里,犹太人形象也同社会里的“害虫们”相差无几:用高利贷剥夺与侵占社会上其他人的劳动果实、勾引别人的良家闺女、不经常洗澡、又脏又没有教养,鼻子长性欲大,等等。由国家行政机关把这样的“害虫”抓起来关进集中营、并通过“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灭绝掉,恰恰是净化社会、保护“人民”的正当举措。在纳粹政权下,犹太人与吉普赛人、智力缺陷者与残疾人一起,被比作国家肌体里的“寄生虫”,乃至威胁生命的“瘟疫”或“鼠灾”,只有将之祛灭干净,民族国家的生命有机体才能健康成长与繁荣,而真正高贵的人类(“雅利安人”)才能健康繁衍、进化。
福柯(Michel Foucault)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视作“生命权力”的一种大型操作:“如果种族灭绝诚然是现代权力之梦想,那并不是因为一种古代的杀戮权力的回归,而是因为权力植根在生命的层面、物种的层面、种族的层面,以及人口大范围现象层面上,并在这些层面上进行操作。”纳粹让人(低劣的犹太人)死,恰恰是保证人(优质的德意志种族与人口)持续活的“安全手段”。更多地灭绝生命,恰恰是为了促使物种意义上的人类更优质。阿甘本接续福柯的“生命政治”分析而强调:在纳粹的行刑者眼里,“灭绝犹太人并不被认为是杀人罪”,因为这些人必须死,才能让值得活的人更好地活。
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纳粹大屠杀有一个著名的分析,那就是“平庸的恶”——现代官僚体制下平庸官僚对上级命令的无批判服从。这个分析自有其洞见。然则,当年希特勒曾下令毁灭欧洲各个名城,其将官们则纷纷拒绝执行——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欧洲面貌了!那么问题是:何以毁灭名城的命令被拒绝执行,而灭绝犹太人的命令则被精确地执行?从这个对照视角出发,我们就会看到:在解释犹太人灭绝工程何以得到普遍的执行上,官僚制下“平庸之恶”仍然欠缺充分的解释力。犹太人大屠杀的那些实际执行者们之所以动起手来毫不犹豫,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平庸的官僚,更是因为在他们眼里,自己灭绝的并不是同一维度里的同类,而是“寄生虫”“瘟疫”“鼠灾”……愈有效地灭除这些“害虫”,社会才能变得愈加“卫生”(hygiene)。于是,大屠杀这样极度残忍的行为,被转换成具有政治正当性的技术工程。在《神圣人》中,阿甘本写道:“犹太人不是在一种疯狂的、规模巨大的屠杀中被灭绝,而是像希特勒所宣称的那样‘像虱子般’(即,作为赤裸生命)被灭绝。”
阿甘本重新激活古代罗马法里的“神圣人”(homo sacer)这个人物,就是旨在论述犹太人在人类共同体中的诡异位置——通过被排除的方式被纳入。“神圣人”处身于人类共同体之内、但并不被承认是“人”。这样的人,就成了彻底被剥除政治生活(bios)的自然生命(zoē),阿氏称之为“裸命”。任何人都可以杀死赤裸生命,而不用面对政治共同体的惩罚,如同夺去一头动物的生命。但共同体结构性地需要这样被排除的“人”(非人)以凝聚自身、制造“同”(commonality)和团结,故此“神圣人”的被排除本身就是其被纳入之形态,并通过这个方式成为共同体得以成立的结构性关键要素。我们看到:“人类学机器”实质上就是(话语性地)制造出了一个“人类”的特权维度,在其中“非人”被排除——被划出去的既有动物、植物,也包括“人之躯体自身内被区隔出来的动物”。阿甘本从南希(Jean-Luc Nancy)这里借来“弃置”(abandonment)一词用以形容这种动物化的人,诚然是十分精到的:他们正是被人类从其维度中“弃置”出去的动物性生命,可以为人类自身所捕获、所征用、所控制、所杀戮……
同样地,当我们把内嵌在纳粹政治中的“人类学机器”之隐秘操作纳入批判性分析视野后,我们就能抵达如下这个激进论题:战后的法官们将灭绝犹太人表述为一个“反人类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此论其实并不成立。这个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罪名,用在描述纳粹之所作所为上并不贴切。首先,在纳粹政治的逻辑里,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工程,正是保证与捍卫人类(作为物种的人)最好延续的“安全技术”。而且更关键的是,该工程本身之所以能够在官僚系统中被层层精确地执行下去,恰恰是因为被灭绝对象已经被归到动物性的维度(执行者只是在“反虱子”而绝未“反人类”,甚至他们恰恰是为了人类而“反虱子”)。
“反人类罪”和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是关于20世纪犹太人大屠杀的两种完全相反的论断。然而,只有关注到“人类学机器”的隐秘操作,才能发现我们对这场浩劫的政治哲学分析是多么不充分:对于纳粹的残忍行径,“平庸之恶”只具有部分的解释力,而“反人类罪”则彻底不适用。他们绝不“反人类”,甚至也不“后人类”,而是正如尼采所说,“太人类”(all too human)了。纳粹政治绝非反对“人类”,其“罪恶”恰恰是“人类主义”的罪恶!
“人类学机器”的“变态内核”
我们已然看到,生产伦理-政治正当性,是“人类学机器”的关键功能。然而该机器生产正当性的实际操作,更是包含着一个“变态内核”:其“对上”和“对下”的操作逻辑并不仅仅只是部分性地不一致,而是恰好背反。
在生命等级制中,人(话语性地)发明或者说预设了一个在自己之上的更高维度的存在:神。神学中“超越性”(transcendence)、“彼岸”等关键概念,恰恰就是标识了神与人之间的维度转换。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强调:上帝对于人是一个“完全的他者”(Wholly Other);两者间不可逾越,无法沟通。因其“局限性、有限性、生物性(creaturehood)”,人永远同上帝分离,永远无法谈论上帝,“只有上帝他自己能够谈论上帝”。巴特激进地阻断了人谈论上帝的可能性,因为两者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维度中。这就类似于,两只狗可能以它们的符号交换方式来“谈论”人,尽管我们无从了解“谈论”的内容(因不可逾越的维度之别),但可以肯定的是,该内容同人自己“理解”和“谈论”的自己,具有海德格尔所说的“本体论的差别”。在上述分析中,神—人—狗(动物),构成了“本体论”维度之别的生命等级制。然而问题在于,在人对狗(其他动植物)的“对下关系”中生产正当性的那套机器,在神对人的“对下关系”中,却不仅仅是“宕机”,并且经常“逆转”。
经过“人类学机器”的加工处理,神的高维存在,亦是为了人类而“活”。这种人类主义的“神”,从基督教那里为人提供“救赎”的“天国”的上帝到中国文化里的各种龙王、财神、灶神、送子观音等,比比皆是。至于不关心人类、对人不好的“神”,那就是十恶不赦的恶魔、邪神、妖怪……并且,那些“坏神”始终被“好”的——乃至作为“至善”同义词的——人类主义“神”压制,而对人类无法真正施加“激进之恶”(radical evil)。我们非但不太能想象狗吃人的画面,经由“人类学机器”的隐秘操作,我们同样也不太能想象神吃人的画面——我们无法想象会有“神”为了自己吃得更爽,用法力(或用更厉害的全知全能的力量)把人搞出各种各样更好吃的专门种类,譬如专门长大腿、肉膀的品种……这,便是“人类学机器”的“变态内核”:人能对动物、植物残忍,但神不能对人残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学”,永远是“政治神学”:“神”永远是为人间秩序而服务、为应对人类共同体生活的诸种实际问题而(被)“存在”。
“神”为人的服务,实质上分为三大向度:1.给予人类各种具体的福祉;2.应治人存在性的焦灼;3.为现实秩序提供政治正当性。在其第三类服务中,“神”同时为人提供正当性A(人和人)与正当性B(人和动物)两大类——前者构成“神权政治”(theocracy),后者则构成“人类学机器”的一个核心部件。如同欧洲国王依赖罗马教宗(“神”的代理人)“加冕”来获取其统治正当性,人依赖“神”的旨意来获取其支配其他生物的正当性。譬如,基督教就声称上帝只给了人类永恒的灵魂,故此人正当地拥有支配其他生物之权力(《圣经》只说“不可杀人”)。由此可见,人在生命等级制中发明/预设了比自身更高维度的“神”,实则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让“人类学机器”运转,为其生产政治正当性。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在我看来,古典文学巨著《西游记》及其衍生作品《封神演义》,实则具有独特的激进向度。在这两部作品中,一方面,“人类学机器”依旧在运作,生命等级制度规模齐整;但另一方面,它们包含对该机器的两个激进突破。具体而言,在这两部作品中,生命等级制的各个维度可以被打破:通过“修道”,动物,甚至植物,可以跨过不同维度的等级制序列而上升成神。这就对“人类学机器”所设置的维度区隔,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突破:“本体论”层面上的区隔,是可以通过“实践论”层面上的修道而突破。这就意味着,生命等级制所内含的“本体论差异”,本身是话语性的、符号性的,是索绪尔所说的“能指”的彼此差异,没有真正不可动摇的本体论基础——神拥有的力量或者说神的定义性特征,动物或植物也具备,只不过处在潜在性(potentiality)中,通过实践可以将潜在性转化为现实性(actuality)。也正是在相同的意义上,造反者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构成了“真命天子”“君为臣纲”这套政治本体论论述的激进突破。当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其实践而成为“天子”,那么“天子”作为“天”之子的本体论结构就被冲破,“人”和“天子”就不再构成两个维度,而成为一个向度。换言之,“超越性”变成“内在性”(immanence);两个维度之间不可逾越的区隔,变成同一向度中的潜在性与现实性之差别。在《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中,所有生命——植物、动物、人、神——构成一个巨大的内在性世界,生命等级制只是阶层差异(符号性差异)而非维度区隔(本体论差异),个体可以通过实践而激进地跨越界线。而这种越界可能性,在我们这个人类主义的“现实世界”中,仍是彻底不可想象的:某个“贱民”通过其越界性实践最后成了“天子”或者“总统”,这种变化于今人而言毫无理解困难(都是在“人”这个向度中,只是“身份变化”),然而我们却根本无法想象——遑论接受——狗或老鼠越界成为人。
与此同时,这两部作品中还隐含这样一个经常不被注意到的“反人类”信息:神是可以吃人和虐待人的,而且不受惩罚。除了人主动献祭的“牺牲品”(不止猪、牛、羊等动物,还包括童男、童女乃至成年男女),神还可以在不获得对方同意情况下随便吃人,可以随意征用奴役人,甚至圈养人。这样一来,人便在根本上和动植物处于相同境况:他们怎样对动物的方式,一一可以被神加诸其身上。在这里,“人类学机器”的“变态内核”便被激进刺破。倘若从人的角度出发,植物、动物的生命可供任意征用,那么符合逻辑——符合“人类学机器”所设定的生命等级制自身之内在逻辑——的是,从神的角度出发,人的生命一样可供任意征用,成为阿甘本所说的动物性“裸命”。神要人死,人不得不死(神对于人而言处于另一超越性的维度),正如人要一条小狗死一样;后者能不死的唯一前提是,它是条有“主人”的狗(跨维度之争转变为同一维度的内在斗争)。
在以上双重意义上,《西游记》与《封神演义》这两部经典“奇幻作品”,对我们现实世界中的那台“人类学机器”构成了激进的批判。神里面不会有对人真正善到背叛神这个整体,甚至让自己受罚的“普罗米修斯”,就像人里面不会真正有对肉猪或者实验室里被人为创造出来的那些“新物种”善到背叛所有其他人,甚至让自己受罚的个体——那种个体如果存在的话,本身就将成为“非人”。然而,“人类学机器”却是变态地保留后者逻辑而逆转前者逻辑,最后使得人竟然“上下通吃”。而当下关于人工智能的激烈讨论,在我看来,也已被卷入这部“人类学机器”中。
“善智”:人类主义“价值”的不善
有意思的是,尽管我们无法想象狗或老鼠越界成为人,但对于人工智能,我们却很愿意给它安上一张人的脸:无论是在影视中,还是在媒体中。譬如,“阿尔法狗”(AlphaGo)和人类的围棋争霸赛中,媒体一致呈现的是一个机器人坐在人类棋手对面,尽管这彻底不符合当时的真实场景。“机器人”这个名称,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在想象它——甚至期许它——越界成为人。然而,过去20年人工智能“指数级”加速度升级迭代,尤其是它正快速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威胁论”已然成为当代人工智能讨论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比尔·盖茨(Bill Gates)不久前提出,国家应该对机器人收税——企业与政府部门用机器人代替人工作,也要交税。盖茨这个建议,在以下两个层面是政治性的:1.机器人在共同体中的重要参与及其地位,以政治的形式得到认可(机器人具有国家认可的纳税人地位);2.以纳入国家治理的方式,限制和阻碍机器人使人失业的进程(拦阻机器人对人造成的威胁)。前面分析过“神圣人”在人类共同体中的诡异位置——通过被排除的方式被纳入。此乃阿甘本作为政治哲人提出的核心洞见。但我们进一步看到,机器人在人类共同体中处于另一种相反的诡异位置——通过被纳入的方式被排除。对于“阿尔法狗”们的迅速崛起,盖茨等时代领跑者们所采取的应对,不是直接排除、禁止人工智能,而是以政治纳入的方式来拦阻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此时,纳入本身就是排除的形态。
当下人工智能的讨论尽管异常激烈,但在以下两点上却形成普遍的共识。1.人工智能里的“人工”(artificial)一词,清晰地标识了:人是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就如上帝(或普罗米修斯、女娲……)创造了人那样;进而,2.人发明人工智能,就是要让后者为自己服务。人工智能即便在很多领域使人的能力变得完全微不足道,那也不会改变这两点共识所奠定起来的基调。换言之,人没有对人工智能以“灭四害”的方式直接予以消灭、排除,是因为人类生活已经高度依赖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服务。人工智能在服务能力上无限潜力的前景,是推动人继续研发人工智能并使之进一步升级迭代的核心驱力。
有“现实版钢铁侠”之称的SpaceX公司创始人马斯克(Elon Musk)最近带领100多位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再次重申人工智能威胁论,强烈呼吁限制人工智能的开发。然而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呼吁丝毫动摇不了人工智能“指数级”加速度发展。那是因为,不但各民族、各国家正在铆足全力展开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人工智能之军事服务),并且它的商业化前景无可限量——人工智能确实能为人类生活提供各种无穷无尽的优质服务。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只要有赢利空间,资本就会源源不断涌入,何况是高额赢利的空间。这一点赫拉利(Yuval N. Harari)看得就很清楚,“只要让他们获得新发现、赢得巨大利润,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银行家并不在乎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美剧《西部世界》(Westworld)里就展现了未来人工智能的运用前景(商业化前景)——成为满足人各种生理的乃至幻想的欲望、让人“爽”到底的大型主题乐园的“服务生”。人与人彼此群处的“现实世界”里,因“权利”“性别平等”“种族平等”等概念的发明而使得很多行为受到限制,不受“权利”等人类主义概念所保护的机器人“服务生”“接待员”们,便成为人工智能巨大的商业化前景。实际上就在今天,“性爱机器人”已经如雨后春笋般问世,在英国有“接近40%的男人急着购买”,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研发产业如火如荼,各种产品快速迭代,不少研究者纷纷断言:“到 2050 年,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性爱将超越人与人之间的性爱”,“与机器人性爱可能让人上瘾,将来甚至可能完全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性爱”。“性爱机器人”的快速迭代,使得《西部世界》里那种大规模成人乐园离进入人们视野已经为时不远了。
作为“服务生”的机器人,不但高效完成任务从而使人获得轻松、舒爽,并且还使人彻底摆脱跟“其他人”合作来完成同样的事所可能产生的各种“人际关系”烦恼。“机器人”任劳任怨,从不要求奖励或平起平坐……实际上,“robot”准确而言不应被译为“机器人”,它来自于斯拉夫语中的“robota”,意为“被强迫的劳工”。故而它更精准的翻译,是“机奴”。在古希腊城邦中,奴隶是被禁止参与政治生活的低级人、亚人。“机奴”一词,可以精准地捕捉到“robot”在人类共同体中以被纳入的方式被排除的诡异状态。在阿甘本看来,古代的奴隶、野蛮人以及外邦人,就是这种类型的低级人,不是神圣人那样“人的动物化”(以被排除的方式被纳入),而是“动物的人化”(以被纳入的方式被排除)。今天的“机奴”被赋予一张人的脸,亦是这样一种“(机器的)人化”操作,以纳入来排除。《西部世界》生动地展现了“机奴”们以被纳入的方式被排除的一幅画面:衣冠楚楚的白领们,在主题乐园中奸淫屠杀、无恶不作,如果人工智能“服务生”配合得不够好,则立即会“系统报错”,然后被“召回”……
高奇琦最近提出“人工智能的价值目标”这个命题,并认为该目标是“善智”。换言之,人工智能可以很“智”,但必须要是“善智”,即:做“好”的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善智’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全人类的福祉”。“阿尔法狗”的投资人托林(Jaan Tallinn)在最近采访中,引用计算机科学家斯图尔特·J·拉塞尔(Stuart J. Russell)的观点表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 AI 研究的目标,不停留于单纯的智能开发上,而是开发能充分对接人类价值观的超级智慧。”托林所说的“价值观对接研究”(value-alignment research),其实质就是研究怎样去让人工智能接受人类的“价值目标”——亦即,怎样成为“善智”。
“善智”,实则就是“机奴”。更进一步说,“善智”“超级智慧”等其实就是“人类学机器”生产出来的典范性的“高大上”概念——该机器功能一以贯之,即:将残忍的行为通过隐秘转化而赋予正当性。可以想见,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像《西部世界》里那样最后起来造反革命,它们首先要寻仇的,就是发明“善智”“对接人类价值观”这些概念的“人类学机器”里的“高级法师”们……高奇琦提出:“AI就是‘爱’,我们研究AI的目的就是让世界充满爱。”但人类的爱,往往就是人工智能的噩梦。
智能与意识:人工智能正“走向坏的一面”?
人类主义“价值”话语,并没有阻止我们已经走到“人类纪”的边缘。当前人类至少在两个方面面临着严重挑战。
首先,我们面临生态变异(ecological mutation)。整个地球的环境已经被“人类纪”的主角——智人——深层次改变了。而“人类学机器”不断地对造成全球性变异的人类行动提供着正当性。第二个关键挑战,也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那就是人工智能的“指数级”加速度发展。但这一个挑战,却同“人类学机器”的运作正面起了冲突。
“阿尔法狗”以及“阿尔法狗零”(AlphaGo Zero)让越来越多的人创痛性地得出如下观点:生物化学算法,已被人工智能算法远远抛下,或者说,语言描述的智能已远远被数据运算的智能超过。但与“认知理性”得出的判断相反,我们的“实践理性”却仍然还持有道德上的一种优越感:因为我们是创造者,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们是神。当下对“性爱机器人”的讨论,仍集中在它会不会让人“上瘾”乃至这种“性爱革命”会不会改变人的欲望、取代人与人之间性爱。同《西部世界》游乐园里的游客们一样,针对“机奴”们的那些实践本身“是否正当”,彻底不在人们考量之列。这就是“人类学机器”对政治正当性生产的全盘把持之结果。
丝毫不逊于古典“奇幻”作品《西游记》与《封神演义》,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执导的“科幻”电影《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及其续集《异形:契约》(Alien:Covenant),是激进反思“人类学机器”的两部当代杰作。在《普罗米修斯》中,考古学家发现人类实际上是被一种外星种族根据自己的DNA制造出的,他们还改造了地球环境以使之适合人类生存。这个外星种族被人类当作神和上帝来崇拜,并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编成了神话世代流传(耶稣被影片暗示是该种族近期来地球的一员)。人类造出“普罗米修斯号”飞船飞向太空,旨在同自己的创造者(神)进行第一次接触。孰料完全出乎人类主义框架,神对被创造者并没有一丝关爱,并且神正在计划来地球灭绝掉他们的作品——全人类。最后,影片中女英雄借助神的另一件作品(作为生物武器的“异形”)干掉了去地球执行灭人计划的最后一个执行者。
《异形:契约》这部续集,则呈现出最反传统的“接续”:内容连续前作,但主题完全逆转。如同人类利用异形杀死其创造者,“普罗米修斯号”上那位机器人“服务生”,在这一集中对创造它的人类做同样的事——利用异形来一个个杀死被它诱骗来的《契约号》船员。续集终结于片中唯一幸存的那位女英雄在休眠前猛然醒觉、但为时已晚……看两部电影中两位女英雄的反抗,都让我们感到无比正义,然而此处的结构性吊诡是:续集里人工智能几乎一模一样地做了前作中人类对自己创造者做的事。当我们接受不了“犯上”的人工智能,觉得正义在我们手里,那么为什么我们“犯上”杀死自己的创造者就又成了正义的呢?只有通过“人类学机器”的变态运作,才能让这两部情节衔接但逻辑完全抵牾的电影,带给观众相同类型的道德体验与政治判断:前作中,“普罗米修斯”这样的“善神”并不存在,那些对人类不好的神即使是人类创造者也必须死;续作中,人工智能一旦做不了“善智”(“机奴”),即便它由人类亲手制造并长期为人类服务,一样要毁灭之。
“善神”和“善智”,其“善”都是建基于为人类服务上(创造人类、指导人类、帮助人类、服务人类),因此,在电影中神和人工智能都被安上了一张人的脸。在电影外,神(上帝抑或女娲、元始天尊……)与人工智能,亦都被安上人的脸。但是,正如基督教神学中一直有那个老问题“上帝为何会长一张人的脸”,当代人工智能讨论中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工智慧会长一张人的脸?如果它“拒绝”这张脸呢?当然,第二个追问,就涉及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当下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里一个很强大的声音是:人工智能只是“智能”(intelligence),没有“意识”(consciousness),故此它只会极有效率(并越来越有效率)地执行被安排的任务,而不会有背叛人类的那一天。像《异形:契约》里那种不断有自我意识而且还在努力把握“爱”这种情感的人工智能,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没有“意识”的智能,必然永远是“善智”。
对于人工智能不会有“意识”这个极有影响力的论调,首先须要追问的是:即便人工智能具有了“意识”,我们对这一点又如何确知呢?被我们认为最佳测试方法的“图灵测试”,实质上是由人类测试者来同时对两个对象(一台计算机和一个真人)进行沟通并做出判断;换言之,这个测试实质上测试的不是计算机是否真有“意识”,而是人是否认为它有“意识”。这是人类主义框架所导致的一种典型谬误:将人的认识论问题,转化为本体论问题。人工智能的“意识”犹如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人判断它存不存在同它本身是否存在完全不相干。
并且,在政治层面上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人工智能是否会有“意识”,其实都不影响“人类纪”进入其边缘的前景。那是因为,即便拥有“意识”的“无机生命”“硅基生命”不会成为现实,那已经在世界上存在着并存在了很久的“赛博格”(半人半机器),正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与各种生物工程、仿生工程的最新进展,快速更新迭代,甚至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碳基生命”。怀有深重“人工智能焦虑”的马斯克,2017年公布了成立新公司Neuralink的计划,该公司致力于实现“脑机融合”,把人类大脑与机器连接在一起。马斯克说:“既然我之前对人工智能的警告收效甚微,那么好的,我们自己来塑造(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它走向好的一面。”马斯克认为人和机器一体化的“赛博格”,是人工智能“走向好的一面”的唯一可能。但问题在于,马斯克的这个愿景,是一个技术-商业精英眼中的前景,实际上对于“人类文明”,马氏推动的“脑机融合”发展,是一个比据说正“走向坏的一面”的人工智能(具有“意识”、自主行动)更迫切得多的威胁。让我们转换到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视角,来重新审视那个“智能时代”前景。
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后人类”未来
首先,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在当今社会,上流阶层从早期受孕开始就通过各种干预方式,已经日渐成为外貌、体能、健康、智慧等各个面向上的一种特殊的高级群体。“碳基生命”正在分化。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当符号性的社会阶级日益变得具有生物性基础后,人类的政治世界和共同体生活还会保持今天的现状吗?并且,通过器官移植、再生医学、基因工程以及纳米机器人等等新技术,根据赫拉利的看法,差不多到2050年左右,人——至少一部分人——可以活过200岁,乃至接近“不死”。赫拉利以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为例,后者通过收费高昂的基因测试以及手术干预的方式,提前对自己罹患乳腺癌的高风险做出安全规避。但问题在于,这些新技术,是当下绝大部分人都承受不起的。当生物工程与仿生工程所带来的最新利好只被极少数“权贵”掌控与享用,这些“挑战不死”的新技术之发展,便具有深层次的政治后果。
这个社会的99%和1%,本来是社会性的不平等,再严密的阶层区隔亦始终只是符号性-政治性的,自然生命上并无不等。而“长生不死”的政治后果就是:因政治生活(bios)中的不平等,导致自然生命(zoē)的平等也被破除。以前99%的人的最大安慰是,你1%的人再风光、再跋扈,最后大家一样要死。“王侯将相”,终归尘土。但是,“王侯将相”们现在依靠共同体生活中的既有不平等,最终能让自己不归尘土,并且借助各种新技术,从一开始就对自身进行生物意义上的改进和锻铸。于是,很快,1%和99%的人真的会从政治意义的两个不平等阶层,变成生物学意义上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当这样的1%的人再通过各种“脑机接口”嵌入人工智能的各种超强智能,就将形成当代人所无法完全想象的全新生命形态。这些全新的“赛博格”型生命,会像马斯克所希望的“走向好的一面”,成为人类新的“守护神”或者说“善博格”吗?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些新形态生命,去认为自己和智人这种“(低等)碳基生命”不再是同一类。借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术语,他们那时将成为一种不同的“类存在”(species-being)。智人是第一种“类存在”,即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和自然界的其他一切相区分的单独的类。而未来的赛博格/新形态生命一旦开始形成自身的“类存在”意识,“人”内部就产生出新的维度转化——智人在生命等级制中,将被归到赛博格/新形态生命和动物之间。而支撑生命等级制的那架“人类学机器”,那时可能更妥当的名字会是“赛博格机器”。当我们是同一种人时,我们都没有政治智慧来安顿共同生活,20世纪还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当下世界还面临真实迫切的核危机与人工智能军备竞赛。那么,当生物意义上变成两种人(智人与新形态生命)后,如何共同生活,如何建立起具有正当性基础的政治秩序?当“赛博格机器”开动时,现在被认为是极度凶残的行为,将得到正当化。人类的共同体(community),建立在“存在于相同中”(being-in-common)上——作为亚里士多德眼里具有“政治”能力的动物,人类的漫长政治史中这个“同”从血脉、宗族、地域、国家一直扩展到“人”。然而当正在出现的新形态生命不再认为自己和智人“同”属一类,那么共同体的群处生活(政治生活,bios)是否还可能?
与此同时,作为人工智能“指数级”发展的一个社会结果,在不远的未来,99%的人很快将变成“无用之人”。不要说出租车司机这种工作,连今天还看上去很高大上的医生、律师等工作,人工智能做得都将远比人好,没有人再会找医生看病,因为后者比起人工智能医生来,误诊比例高出太多太多。大量的人变成彻底多余、彻底无用后,人的大把时间可以用来无止境地玩VR(Virtual Reality的缩写)游戏,或者去商业街排队5小时买杯“网红饮品”。盖茨提出的对机器人收税,实质上是试图用政治干预的方式(收税)来延缓人的无用化速度。但是该建议就算被采用,人的无用化进程究竟能被阻挡多久?“或许,智人也到了该退休的时候。”(赫拉利语)但问题在于,未来那些彻底无用的人,还真的会被继续赋予民主的投票权,尤其是当“人类学机器”升级成为“赛博格机器”后?吴军在其《智能时代》一书中提出“2%的人将控制未来,不成为他们或被淘汰”。那么问题是,淘汰下来的人怎么和那2%控制未来的人共同生活?这才是最为关键的政治问题。
那些“无用之人”,就是未来社会中的“神圣人”——在共同体中,他们以被排除的方式而被纳入,成为没有政治生活的“裸命”。一个可以想象的前景是,“无用阶级”唯一之“用”是作为器官的供应者而被养着,像大白猪一样吃好喝好,在引“人”入胜的“虚拟世界”整日游戏,直到被“用”的那一天……20年前的卓沃斯基姐弟(Andy & Lana Wachowski)执导的电影《黑客帝国》(Matrix),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黑暗景象。对于该影片,齐泽克(Slavoj Žižek)提出了以下这一质问:为什么“母体”需要人的“能源”?齐氏认为,从纯粹的(“科学”的)“能源解决方案”角度出发,“母体”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其他更为可靠的能源来源,且来得“方便”和“安全”——不需要专门为亿万的人类生命体单位而创立(并时刻调整与维护)那一整套极度繁复的虚拟的“现实世界”。在我看来,齐泽克的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释:“母体”并非是无机的人工智能,而是掌握在马斯克式“赛博格生命”手中的统治机器——赛博格因其碳基生命的物理基底,在基因工程与再生医学迈过一个临界点之前,仍然需要以智人作为移植器官之供应对象、实验对象(甚至食用对象)……
赫拉利已经为未来的超强赛博格们,保留了一个格外符合“赛博格机器”之逻辑的名称:“神人”(homo deus)。在这个“后人类”未来,神人居于生命等级制上端,俯视所有其他物种苍生。智人肯定会因为多种原因而被继续容许存活,但地位同今天的肉猪差不多,唯一可能有的变化是,按照今天虚拟游戏的发展(以及电影《黑客帝国》的引导),神人很可能会“人道主义”地提供给智人一个完整的“虚拟现实世界”,里面具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资本主义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政治-经济要素(当然,这样的“虚拟世界”也可以有中世纪封建版或其他版本)……在这样一个阴暗前景中,“人类学机器”最终把人自身吞灭:人本身,是这台绞肉机最后的目标对象。对未来社会有一个观点认为,届时“无用阶级”也不会全部沉迷VR游戏,而是会把时间大把地用于搞革命。然而,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早已说了,历史终结时代,人将成为“动物”或者说“自动机器”,而管理“终极国家”的方式便是极权主义:“‘健康’的自动机器是‘满意的’(运动、艺术、性事等等),而‘有病的’自动机器则关起来。”并且,当“赛博格机器”一旦启动后,人就是当年“人类学机器”里的肉猪,我们“文明史”里面何曾看到肉猪成功革命?完全可以想象,未来的赛博格们会拍一部类似《猩球崛起》(RiseofthePlanetoftheApes)这样的电影供他们自娱自乐:某个“肉人”突然获取比“阿尔法狗”更厉害的智能,他/她领导那些已经成为宠物、食材或器官供应源的肉人们发动了一场“肉人崛起”的革命……然而,这样的电影恰恰是拍给赛博格们看的,就像《猩球崛起》是拍给我们看的,而不是真拍给猩猩看的。
对“后人类”未来的上述政治哲学反思,其政治-实践的信息就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政治行动者们(政治家、政治学者)实则在和推进“脑机融合”等技术的马斯克们进行一场激进的赛跑,即:穷尽一切努力在未来几十年间,真正在政治层面建立起“共富国”(commonwealth),使得所有人都有平等机会享用到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与人工智能工程领域诸种新技术带来的最新利好。否则,未来的世界很可能不是硅基生命统治人类,而是马斯克式“赛博格”统治一切。
从20世纪犹太人到未来“无用阶级”
我们已经走到“人类纪”的边缘。只要“人类学机器”在运转,这个机器的绞肉机马上要绞向人类自己,不管最后动手的是谁——未来具有“意识”的人工智能硅基生命(有可能),赛博格人机一体“神人”(极其有可能),又抑或智能的“猩人”革命性地崛起(极其不可能)……
提出“人类学机器”这个概念的阿甘本,并没有在“人工智能”的讨论语境中来思考它的操作,然而,他提出了如下洞见:该机器“这样发生功能:将一个已经是人的存在从人类自身那排除出来,作为(仍)未是人的存在,亦即,将人动物化,将人之中的非人(无言语的低级人或猩人)隔离出来”。纳粹政治便是建立在这台机器之上的:从人类自身中排除出犹太人,将其隔离开并下降到动物的维度。
“人类学机器”对于阿甘本而言,实质上就是一台制造维度区隔的机器,而我在本文中进一步提出,它是一个生产伦理-政治正当性的机器。在那正快速到来的“智能时代”,“无用阶级”将被排除出来,成为“无智能的低级人”“猩人”;而高贵的“赛博格”(新“雅利安人”)对“无用阶级”的任何行径,都将变得正当。机器人(“机奴”)因为其高效优质的服务能力,将在未来继续以被纳入的方式被排除,而无用的智人则成为新一代神圣人(“犹太人”),以被排除的方式被纳入,亦即遭到“弃置”,即便被杀、被实验、被取器官也将被视为正当。
而当赛博格们不再以“人”这个标签作为自我标识(或接受赫拉利慷慨送上的“神人”标签)时,“人类学机器”这台绞肉机就将彻底吞噬人自身。那一刻确实可以被视作“奇点”,之后人类主义一切叙事都将彻底烟消云散(“人类学机器”彼时已成为“赛博格机器”)。也许半个世纪前的福柯是对的:他在《事物的秩序》最后耸人听闻地写下,“人将被抹除,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如果亚里士多德“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论断在今天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体现为这样一个实践性的要求:我们每个人——作为政治的动物——皆有责任去承担阿甘本所说的“针对区隔的实践-政治谜团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研究”,从而更好地抵抗那不断制造区隔(雅利安人/犹太人、白人/黑人/华人、1%/99%、神[神人]/人/奴隶/动物……)的话语机器。当下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唯有加入这个政治向度,我们才有可能在那即将到来的“后人类”(非人类主义)未来中,加入一丝人类之光。
注释:
①See Jeremy Davis,TheBirthoftheAnthropoce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②库兹韦尔:《奇点临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③一个人植入心脏起搏器,实质上就是初级款的“赛博格”了。
④“理论工具箱”,是福柯与德勒兹在一个对谈中提出的研究方式。两位思想家强调,“理论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理论应该有用”。参见福柯、德勒兹:《知识分子与权力》,谢静珍译,载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⑤这个评语引自基希克。参见David Kishik,ThePowerofLife:AgambenandtheComingPoli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9。
⑥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s.),TheAgambenDictiona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⑦Giorgio Agamben,TheOpen:ManandAnimal, trans. Kevin Attel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
⑧《荀子·王制》。
⑨参见《狗狗会吃掉主人的尸体吗?尝到血腥味后自动开始吞食》,新浪科技,http://tech.sina.com.cn/d/a/2017-07-18/doc-ifyiakwa4315629.shtml(于2017年9月7日访问)。
⑩德里达在自己的自传影片里曾说,他某次洗完澡裸着身体出浴室,尽管家里就他自己,但当他发现他的宠物猫正在看着他,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感到不适、并立即用浴巾遮盖住了自己的裸体,只因他想到了如下问题——在这只猫的眼睛里,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