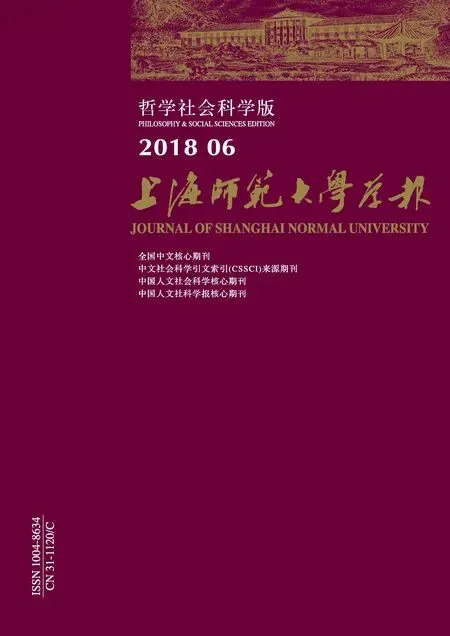自编词集与晏几道词的深隐寄寓
马里扬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北宋词人自编词集,当以晏几道的《乐府补亡》为肇始。这本是可以视为士大夫著意为歌词创作的极佳例证,但由于歌词在当日的娱乐性质,因此晏几道自编词集衍生出了所谓的“投赠”事件。以歌词来“投赠”究竟是子虚乌有,抑或别有隐情?这是首先需要有所明辨的史实。而由于后世流传的晏几道词集,往往题名为“小山集”,也就生发出第二个问题,即:今所见《小山集》与《乐府补亡》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虽然此前学者曾就文献流传的线索展开研究,但仍旧无法改变证据链条始终处在严重缺失的状态。因此,还原《乐府补亡》之面貌,应无可选择地回到作品本身的读解。文本细读能否深入,是以作品相关的时地、人事的考证为前提的。对于以歌词传世且仕宦不彰的晏几道而言,如果仅局限在文本自身提供的季节、楼台、情事等语词信息中,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只能是大胆的假设。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的突破口转移到了黄庭坚诗集中所保存下来的多达13首的、与晏几道直接相关的唱和诗,采用“以诗证词”的研究方法,为最大限度地挖掘晏几道词中的深隐寄寓提供旁证,同时为恢复其自编词集的原貌提供较为坚实的内证,并就晏几道在词史演进中的地位重新加以评判。
一、歌词“投赠”辨
晏几道《乐府补亡序》云:“七月己巳,为高平公缀辑成编。”[1](P296)最早对此进行考证的宛敏灏先生虽然未敢自信“高平公”的确指,但提出了与晏几道自编词集相关的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晏几道所编《乐府补亡》的时间在范纯仁出知颍昌府的元祐四年“七月己巳”;二是《乐府补亡》已经不是晏几道首次自编词集,而且目的都与“投赠”显贵有关 。[2](P261)在《小山词》的后续研究中,以上两个观点都得到了回应。夏承焘《二晏年谱》确定了“高平公”为范纯仁,又根据《砚北杂志》所载“不肯见政事堂中人”的“语境”推定,否认了晏几道“投赠”歌词:“词序谓‘为高平公缀辑成编’殆由范敦促。叔原不肯见政事堂中人,此时已年高,或不致以小词求贵人顾盼耶。”[2](P261)而夏先生将《乐府补亡》编撰时间下移至“建中靖国元年”“之前”(即哲宗绍圣年间),则未能顾及“七月己巳”这一准确信息。郑骞《晏叔原系年新考》有意识地弥补了前贤之未及,其由“高平公”与“七月己巳”两个信息的综合考订,确定不疑地将晏几道为范纯仁编辑《乐府补亡》置于元祐初(1086—1088)。只是就编辑之目的而言,仍旧存有“纯仁索阅或叔原自动投赠”[3](P208-209)的猜测。
考《宋史·邹浩传》云:“第进士,调扬州、颍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纯仁为守,皆礼遇之。纯仁属撰乐语,浩辞。纯仁曰:‘翰林学士亦为之。’浩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纯仁敬谢。”[4](P10955)按:《苏轼诗集》卷四十五,即“乐语”,乃为翰林学士之时所撰年节帖子词与宴会教坊词。范纯仁要邹浩撰“乐语”亦即此,属于广义的“歌词”。至于晏几道为范纯仁所编撰的《乐府补亡》,仍是出自此种用途。所谓“为高平公缀辑成编”,即范纯仁“属撰乐语”之例。因此,夏承焘先生着重强调“不致以小词求贵人顾盼”以及郑骞先生在“投赠”之前加以“自动”两字,都无例外地将“投赠”做一般意义之理解,即有所求而“投赠”歌词;而这种一般意义不但不合晏几道为人处世的惯常,也有悖于士大夫所处的历史情境。
然而,关于晏几道“投赠”歌词的认知,却早已发自宋人邵博与周煇,且将“投赠”的时间段提前至元丰,而对象成了韩维。邵博《闻见后录》成书于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月一日,[5](P151-152)周煇《清波杂志》在光宗绍熙三年(1192)六月。[6](P340)考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三月的王灼《碧鸡漫志》,有“莲、鸿、、云,皆篇中数见,而世多不知为两家歌儿”之语,[7](P85-86)是可知晏几道《乐府补亡》一编久已不存,以致连晏氏的自序也目睹者无多。因此,无论是与王灼同时的邵博还是作为后辈的周煇,他们关于晏几道歌词“投赠”韩维事件的记载,都不免是在昧于历史情境的状况下,以南渡之后士大夫对歌词的认知作为衡量标准而做出的判断。换言之,他们所谓的晏几道以歌词见示韩维一事本身确实发生过,但对这件事性质的记载,则添入自身的“当代”认知,以致后人对于这一事件的理解,往往便是将“传述者”邵博与周煇的观点转嫁给了“当事人”韩维与晏几道。
但这次为后来人所认定的歌词“投赠”事件,其呈现的状态是否又如《乐府补亡》一样为晏几道自编词集呢?这一问题的解答,要从晏几道不偏不倚地选择在元丰间“监颍州许田镇”以歌词见示韩维的深层原因说起。《宋史·韩维传》云:
韩维,字持国。以进士奏名礼部,方亿辅政,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父没后,闭门不仕。宰相荐其好古嗜学,安于静退,诏试学士院,辞不就。[4](P10305)
韩维虽出身仕宦之家,然其仕进经历中却有赖“宰相”之提携。张方平为韩维父韩亿所撰《韩公墓志铭》云:“公之先占籍常山之灵寿,考信公(引者按:韩亿父保枢)游学过河,遂不北还。公既贵,卜封树祢庙,得许昌之长社,吉,因而度竁。”[8](P675)韩亿卒葬许州,韩氏一族遂家焉而为许人。这一时期,韩维得与晏殊有较为亲密的往还。韩维《阳翟祭晏元献公文》云:“独念晩进,辱公提携。脱略尊严,降接陋卑。酬酢篇咏,从容燕嬉。”[9](P738)据夏承焘先生《二晏年谱》考订,晏殊知颍州是庆历四年至八年(1044—1048),徙知许州在皇祐元年(1049)。[2](P241-249)而韩维父韩亿卒于庆历四年汴京里第,依照他生前意愿,包括韩维在内的韩氏八子护丧归许州,此后韩维即“闭门不仕”。韩维《南阳集》卷二十八中存与晏殊唱和之作多首,如《和晏相公西湖》《和晏相公湖上遇雨》《晏相公湖上泛舟赋》等,由于颍、许两地皆有“西湖”,因此这里所谓的“西湖”“湖”,也是不出韩维许州守丧期满(约在庆历七年)后拜见晏殊于颍州,以及晏殊来知许州而韩维从游两种可能。于此可无疑问的是,《宋史》韩维本传所谓“宰相荐其好古嗜学”之“宰相”,非晏殊莫属。韩氏兄弟绛、维、缜诸人皆能词,《全宋词》辑得韩维词五首,[10](P255)其中《减字木兰花》题为“颍州西湖”,虽然文字残缺已甚,但从词题可以推断为从晏殊游时所作。
晚年晏殊与韩维结识后,始终提携他不懈。韩维怀念晏殊而云“独念晩进,辱公提携”及“酬酢篇咏,从容燕嬉”者,全无虚语。邵博记载的韩维自称“门下老吏”,也是源于曾经得到晏殊举荐并从游的这一层关系。反观晏几道在“监颍昌府许田镇”——这一官职显然和韩维一样是“受荫”得来的——来见父亲的门生韩维而“手写自作长短句”以示,显然不是邵博这样的旁观者兼后来人所理解的“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韩维在见面时所出的劝告之语,也不是周煇刻意揣测而得出的冠冕堂皇之“前哲训迪后进”的大道理,而是出于晏几道政治处境与前途的关切。与此可堪比类的是,同为“宰相”的宋庠之孙宋乔年,“用父荫监市易,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4](P11208)因此,韩维对晏几道的谆谆告诫,应是担心其行为不检而授人以柄,以致再次受到政治迫害事件的波及。
晏几道既以歌词著称于当日,就自身而言更以歌词自矜。他手写自作新词见示韩维,是同处颍昌(即许州)不免应酒筵歌席相往还之时所需。而韩维本人也非不解风情,正是在知颍昌期间,常饮酒赋诗,“情致风流,绝出时辈”。[11](P196-197)至若邵博等的记载,则证明了韩维见到晏几道时所给予之规劝,应是不期然触动了他对晏殊的怀念。总之,无论晏几道为范纯仁编辑的《乐府补亡》以及稍前见示韩维的歌词,都与“投赠”两字无丝毫关系。
二、小山词流传考
晏几道歌词究竟编撰过几次?郑骞《晏叔原系年新考》推测为三次:“第一次为元丰五年手写投赠韩维,第二次为元祐初为高平公缀辑成编,第三次则为今日通行之本。”[3](P209)这其实是扩张了上文提及的宛敏灏先生的说法。但这“第一次”仅为手写歌词以见示,显然不能认为是编集;而从“第二次”即《乐府补亡》的编集到“第三次”即所谓“今日通行之本”,也似嫌跨度太大难以弥缝。上文征引的《碧鸡漫志》的作者王灼,与晏几道晚年时代相接。从他称引《乐府补亡》时所依据仅仅来源于晏氏的自序来看,可知《乐府补亡》久已不在人间。至若他读到的“晏叔原歌词”,这本词集中有关涉“莲鸿云”的词作,又掺入作于徽宗大观、政和间的《鹧鸪天》献蔡京词,则不仅不会是《乐府补亡》,也不是后来黄庭坚作序的《小山集》,而是另一种“晏叔原词”。王灼所谓“其后目为‘小山集’,黄鲁直序之”,是想当然地牵连起《乐府补亡》与《小山集》。其实,这句话可以提供的信息仅是:晏几道歌词曾有《小山集》流传,并有黄庭坚的序。至于这个《小山集》是否出于自编,是不能确定的。
晏几道歌词,南渡之后又有一种面貌。尤袤《遂初堂书目·乐曲类》著录有“晏叔原词”一种。[12](P34)尤袤的年岁与王灼相接,其所著录仅云“晏叔原词”,或与王灼所见之本相去不远。据钱亚新先生研究,尤袤著录标目方式有五种:书名式、作者+书名式、朝代+作者+书名式、作者+著作方式+书名式、版本+书名式。[13](P31)我们以此对应“乐曲类”著录的14种,则可以判为“书名式”的有《曲选》《四英乐府》《锦屏乐章》《乐府雅词》四种;“作者+书名式”有冯延巳《阳春集》与杨元素《本事曲》两种;“朝代+作者+书名式”则无严格对应者,或者“唐《花间集》”可以归入。余下的7种即“黄鲁直词、秦淮海词、晏叔原词、晁次膺词、东坡词、王逐客词、李后主词”,无论题名还是作者的次序,明显带有随意性,甚至可以怀疑只是对诸家词集的代称,而非严格的题名。在尤袤(1127—1194)生活的时代,他所著录的7家词集中可以考知重新编撰过的有:(1)曾慥编苏轼《东坡词》;[1](P381)(2)乾道间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刻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其中卷五十《乐章》即黄山谷词;(3)乾道间高邮军学刊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至如晁元(一作端)礼(次膺)、王观(逐客)与李煜,他们词集编撰今所知皆落在尤袤之后。仅以苏轼、黄庭坚与秦观三人之词集而言,尤袤所见大体当不出传世宋刊编撰类型,即附载全集之后,或者别出冠以作者字号而单行,这或许成为他在著录时以词人的字号径直连称“词”的原因。
北宋诸名家词在南渡之后的流传,无一例外地是重编本。这种状况首先源于北宋词人自身很少会像晏几道那样去自编词集,纵然编撰了,也几乎很难在生前刊刻流播。洪迈《夷坚志补》卷二《义倡传》载有一事:
义倡者,长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讴,尤喜秦少游乐府,得一篇,辄手笔口咏不置。久之,少游坐勾党南迁,道长沙,访潭土风俗妓籍中可与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坐语间,顾见几上文一编,就视之,目曰《秦学士词》,因取竟阅,皆己平日所作者。[14](P1559-1560)
这个故事本身连洪迈后来也找出了其间的漏洞,[15](P738)但其间透露出关于北宋人词编集的一个重要讯息,即词人自身几乎不会去自编词集,歌词流传开来后一般是由他人来编撰,尤其是倡伎或者乐工,而编集目的因此也是十分明确地定格在了演唱上。当然,也不排除士大夫诵读的需要。至于它的流传形式,应是手抄本,只有像《花间集》这类已经成了“古典”的集子以及已故的词人如冯延巳、欧阳修等的词作才有可能被刊刻。
晏几道虽然例外地编撰了自己的歌词,但并未广布,只会以手抄或少量刻印的形式在友朋间传看。南渡之后,词评家所品评的题为《小山集》的晏几道歌词,与其他名公的一样,是当时人所收集整理并且刊刻的。倘后人据此考订晏几道曾自编并自序的《乐府补亡》,便不能无疑问,如余嘉锡先生云:
今本一卷二百余阕,皆有调而无题,而《花庵词选》选几道词十二首,皆往往有题。《(碧鸡)漫志》云“莲〔红〕(鸿)云,皆篇中数见”者,盖亦见于题中,为传写脱去。[16](P1600)
关于余先生所置疑的“脱去”词题,饶宗颐先生云:“不知花庵从坊本转录者,多有二字标题,以便应歌,如小山词题中之‘佳会’‘别恨’‘闺思’等字,何能信为原稿所有乎?”[17](P62)而两位先生所引据的黄昇《花庵词选》,其中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编撰时间为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或稍后,较王灼、尤袤更晚。他所收集到的唐宋诸家的词作,来源很复杂,其中北宋词当多有取于曾慥《乐府雅词》与鲖阳居士《复雅歌词》的。[18](P685)《乐府雅词》并未收录晏几道一首,黄昇反而选录了12首,并为词人撰写了小传。从传文来看,其内容并不出王灼叙述的范围;且仅云“有乐府行于世,山谷为之序”,连词集的题名也无。如果黄昇寓目过一部晏几道的词集,也应不出尤袤所著录的“晏叔原歌词”。
关于晏几道自编词集的流传,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的基本观点有三:(1)可以确定的晏几道自编词集只有《乐府补亡》,而黄庭坚作序的《小山集》则由于后来重编本多冠以此题名,反而使它距离自编性质更加遥远,以致无法判断其原貌;(2)晏几道自编的《乐府补亡》久已失传,他的歌词在南渡初期甚至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冷遇,连词中提及的“莲鸿云”都不知所云;(3)今天能够见到的《小山集》,它的词作来源中自然有晏几道自编词集《乐府补亡》,但无法通过文献学上的考证进行还原。因此,探讨晏几道自编词集的面貌,只能从歌词文本的读解来找寻答案。
三、以“山谷诗”证“小山词”
今日通行的晏几道词集,无一例外地以《临江仙》八首开卷。其中,第八首“东野亡来无丽句”既与“莲鸿云”无涉,时间上也趋近于晏几道的晚年,[2](P257-258)因此不计入。第二首“身外闲愁空满”互见晁补之词中,晁词首句作七字,虽收入《花庵词选》“晁无咎”的名下,只能是当日传唱一时的证明,因此归属难断,也应排除在外。兹先录《临江仙》首两篇如下:
斗草阶前初见,穿针楼上曾逢。罗裙香露玉钗风。靓妆眉沁绿,羞艳粉生红。 流水便随春远,行云终与谁同。酒醒长恨锦屏空。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淡水三年欢意,危弦几夜离情。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 绿酒尊前清泪,阳关叠里离声。少陵诗思旧才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10](P285-286)
首篇一起云:“斗草阶前初见,穿针楼上曾逢。”按:“斗草”为暮春,“穿针”为七夕乞巧,是指出一年之内两次相会。以下“罗裙香露玉钗风”之“玉钗风”,乃指“人胜”,亦“斗草”时节。同时,词人撰写这篇歌词之时,也正是暮春时节,观煞尾“飞雨落花中”可知。一年之内两度相会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分散呢?第二篇中给出了答案。“淡水三年欢意”中的“三年”不是虚指,而是任职三年已满。以晏几道自编词集的元祐初向前推算,则他的三年任职当指元丰五年(1082)前后“监颍昌许田镇”。据欧阳修《晏公神道碑》载,仁宗至和二年(1055)晏殊去世之时,“子八人:……几道、传正,皆太常寺太祝”。[19](P354)“太常寺太祝”是“轻裘食肉”的门荫之官,[20](P275)在熙宁七年(1074)的“郑侠上书案”出现前,他的日常生活尚称安逸。但这个牵涉甚广的案件,使他遭受了牢狱之灾,[2](P256)生活亦因此而困顿。《鹧鸪天》词云“惜无红锦为裁诗”,即困居京城的真实写照。晏几道任“监镇”一职,介于亲民、厘务官之间,虽也不能排除是“郑侠案”牵连出的贬谪,但仍旧是门荫入仕后惯常任职。[4](P3979)且“承平时,监当为美仕”[21](P1299)(查慎行注),是能对于困顿生活有所改善的。而这里所谓“淡水”之交者,是父亲的门下旧客韩维。“危弦几夜离情”之“几夜”乃“夜夜”,这里落脚在“离情”两字上,是开启下文离别;而“危弦几夜”两字承上“三年欢意”而来,是说居颍昌三年与韩维经常性地歌筵娱乐。韩维离任颍昌府,史书明确记载是在元丰六年(1083)四月甲子日,[22](P8051)而晏几道歌词所写之节候已是“晚霜红叶”,即初冬,由此可以推定词必作于韩维离任前一年,即元丰五年。韩维此际居颍昌并已获续任,[22](P7916-7919)逆推三年,晏几道应在元丰二年(1079)秋至颍昌。
也正是在元丰二年的秋天,晏几道的故交黄庭坚来到京师,他们之间有过数次会面,存留于黄庭坚诗集中与晏几道相关的唱和诗,竟多达四题十三篇之多。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系其中关涉黄庭坚、晏几道与王稚川的三题于元丰三年春,[23](P724)显然是依从黄庭坚与王稚川的交往时间所定,并不够确切。郑骞先生已经指出,如是春天,则与诗中所描写的秋冬时节不类。[3](P205)考黄庭坚与晏几道的交往,当始于治平年间山谷入京应举、新进士聚会之时。据黄庭坚《王力道墓志铭》载,他与王力道治平元年(1064)入京应举未中,滞留京城;[24](P830-831)而郑侠与黄庭坚同登治平四年进士第,则治平年间为晏几道与黄庭坚诸友人往来之始。至元丰二年秋,黄庭坚入京等待改官,①方故旧重逢。黄庭坚《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诗云:
客愁非一种,历乱如蜜房。食甘念慈母,衣绽怀孟光。我家犹北门,王子渺湖湘。寄书无雁来,衰草漫寒塘。故人哀王孙,交味耐久长。置酒相暖热,惬于冬饮汤。吾侪痴绝处,不减顾长康。得闲枯木坐,冷日下牛羊。坐有稻田衲,颇薫知见香。胜谈初亹亹,修绠汲银床。声名九鼎重,冠盖万夫望。老禅不挂眼,看蜗书屋梁。韵与境俱胜,意将言两忘。出门事衮衮,斗柄莫昂昂。月色丽双阙,雪云浮建章。苦寒无处避,唯欲酒中藏。[23](P991-992)
由于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关系,改官来京的黄庭坚心头也便笼罩上了配合调查甚至是被审查的阴云。此时他的朋友王稚川或也因改官来到京城。虽一样寄家他方,不同的是,王稚川似乎是希望仕途上有所作为,因此并不被“客愁”困扰。“寄书无雁来”是化用王稚川的诗句,但他在诗中表达的这份“愁”,毋宁说是仕进无门的感受。②“故人哀王孙”中的“故人”,便是指晏几道。“交味耐久长”的“长”,并非虚指。至此时,晏几道与黄庭坚之间的交往已逾十载。“吾侪痴绝处”,有黄庭坚后来为《小山集》作序时提及的晏几道“三痴”为证,这里亦可见有自指的成分在。“坐有稻田衲”是寂照禅房的主人:身处繁华之地,却能有这样一个孤寂的地景,貌似不可解,实则是“老禅”之外的三位皆有意避开政治上的争斗。“出门事衮衮”以下云:倘我们走出这里,则不免要深陷名利交织的苦境。黄庭坚又有《同王稚川晏叔原饭寂照房得房字》,为步上篇之原韵:
高人住宝坊,重客款斋房。市声犹在耳,虚静生白光。幽子遗淡墨,窗间见潇湘。蒹葭落凫雁,秋色媚横塘。博山沉水烟,淡与人意长。自携鹰爪牙,来试鱼眼汤。寒浴得温湢,体净心凯康。盘飡取近市,厌饫谢膻羊。裂饼羞豚脍,包鱼芰荷香。平生所怀人,忽兹共榻床。常恐风雨散,千里郁相望。斯游岂易得,渊对妙濠梁。雅人王稚川,易亲复难忘。晏子与人交,风义盛激昂。两公盛才名,宫锦丽文章。鄙夫得秀句,成诵更怀藏。[23](P993-994)
此“高人”,也就是上篇的“稻田衲”——寂照房的禅师。屋子里的墙壁上,不知是何方“幽人”留下的一幅《潇湘图》,令黄庭坚不禁想到“潇湘逢故人”来;眼前的博山香炉里吐出的袅袅轻烟,“家山鹰爪”煮沸后现出的形如鱼眼的水花,一并作用,过滤掉了现实中的烦扰与尘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云“茸割肉胡饼”,“外卖……玉板鲊肥、鲊片酱之类”。[25](P73-74)“盘飡取近市”即非入酒肆,而为此“外卖”;“裂饼羞豚脍”即“茸割肉胡饼”。“晏子与人交,风义盛激昂”,显有所指。晏几道虽“痴绝”逃世,但面对“郑侠上书案”以及黄庭坚牵连而入的“苏轼诗案”,故交的种种遭遇不免令外“痴”而里“慧”的晏几道感到愤懑。而“乌台诗案”中黄庭坚的处境会令晏几道联想到“郑侠案”中的自己:他们都是因“诗”而牵连其中。[26](P102)而晏几道当日下狱,恐也是配合调查;③且那搜查郑侠私人文字的舒亶,正是锻炼苏诗的主力。种种相似,在时代的大气候下并非偶然。
黄庭坚诗题中所见是与晏几道、王稚川三人唱和,则每人各拈一韵。黄庭坚既有“得房字”之作,余者“寂”“照”两字,必属王稚川、晏几道。而黄庭坚诗集中又有《次韵叔原会寂照房得照字》与《次韵稚川得寂字》诗,可知王稚川所作为“寂”字韵,而晏几道为“照”字韵。黄庭坚两诗云:
风雨思齐诗,草木怨楚调。本无心击排,胜日用歌啸。僧窗茶烟底,清绝对二妙。俱含万里情,雪梅开岭徼。我惭风味浅,砌莎慕松茑。中朝盛人物,谁与开颜笑。二公老谙事,似解寂寞钓。对之空叹嗟,楼阁重晩照。(《次韵叔原会寂照房得照字》)
平生万里兴,敛退著寸尺。向来类窃鈇,少日已争席。曩过招提饭,惬当易为适。食鲑如举士,名下无遗索。谈余天雨花,茶罢风生腋。谁言尘土中,有此座上客。言前倾许可,胸次开堛塞。同是蠧鱼痴,还归理编册。长安千门雪,蟹黄熊有白。更约载酒行,无为守岑寂。(《次韵稚川得寂字》)[23](P995-997)
以上两首见收于黄庭坚“平生得意之诗及尝手写者”[27](P31)之《外集》。细绎之,则深藏有待发覆之隐情。“照”字韵诗中“风雨思齐诗,草木怨楚调”,史容以“风雨”“思齐”为《诗经》名。若此,则《郑风·风雨》为“思君子”之作,尚可以有所关联;但《大雅·思齐》所谓“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却不免有落空之虞。必于此得一通贯理解,则需旁征黄庭坚与苏轼的唱和诗。进入到元丰二年,时在大名府的黄庭坚与在徐州的苏轼曾以“粲”字韵唱和数篇。
黄庭坚诗《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旧韵寄彭门》其一云:公材如洪河,灌注天下半。风日未尝撄,昼夜圣所叹。名世二十年,穷无歌舞玩。入宫又见妬,徒友飞鸟散。一饱事难谐,五车书作伴。风雨暗楼台,鸡鸣自昏旦。虽非锦绣赠,欲报青玉案。文似离骚经,诗窥关雎乱。贱生恨学晩,曾未奉巾盥。昨蒙双鲤鱼,远托郑人缓。风义薄秋天,神明还旧贯。更磨荐祢墨,推挽起疲懦。忽忽未嗣音,微阳归候炭。仁风从东来,拭目望斋馆。鸟声日日春,柳色弄晴暖。漫有酒盈樽,何因见此粲。[23](P909)
诗中“风雨暗楼台,鸡鸣自昏旦”“文似离骚经,诗窥关雎乱”,正与“风雨思齐诗,草木怨楚调”中之“风雨”“诗”“楚调”等相合,故此两句与苏轼相关当无疑问。苏轼答诗《往在东武与人往反作粲字韵诗四首今黄鲁直亦次韵见寄复和答之》云:
苻坚破荆州,止获一人半。中郎老不遇,但喜识元叹。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阴求我辈人,规作林泉伴。宁当待垂老,仓卒收一旦。不见梁伯鸾,空对孟光案。才难不其然,妇女厕周乱。世岂无作者,于我如既盥。独喜诵君诗,咸韶音节缓。夜光一已多,矧获累累贯。相思君欲瘦,不往我真懦。吾侪眷微禄,寒夜抱寸炭。何时定相过,径就我乎馆。飘然东南去,江水清且涣。相与访名山,微言师忍粲。[21](P925)
黄庭坚的诗中,意在祈望苏轼能够引荐;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个引荐直到元丰末苏轼重返京师方获实现。而在当日苏轼的答诗中,则是纵笔无拘束的姿态毕现;他借题发挥,在对黄庭坚进行褒扬之外,更谈及自己目前的归隐志愿。值得注意的是,“不见梁伯鸾,空对孟光案。才难不其然,妇女厕周乱”夹杂其间,用意何在呢?先看后两句,即“才难不其然,妇女厕周乱”,语出《论语·泰伯》篇,[28](P5402-5403)字面意义谓一老妇人侧身于周朝开国名臣之间,功绩相敌,即“风雨思齐诗”的“思齐大任”。明了这一层,只是疏通了诗句的“古典”,至于“今典”所在,即苏、黄诗中这位老妇人究竟何指呢?黄螢《山谷年谱》“元丰二年己未”云:“二月十二日,先生继室介休县君谢氏殁于官所。”[27](P111)是在元丰二年春黄庭坚寄赠苏轼的和诗之时,已然遭遇了不幸。苏轼在答诗中云:“不见梁伯鸾,空对孟光案”,这里的“空”,乃潘岳《悼亡诗》“长簟竟床空”之“空”,[29](P1091)正暗指此事。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曾质疑黄螢无据,并推算谢氏夫人卒于元丰三年或四年。[30](P94)按:郑先生所依据者,乃《黄氏二氏墓志铭》的叙述。而古人行文中曰某某年者,皆事后追记,其间或有未能严丝合缝之处。黄螢乃黄庭坚后人,去当日未远,其所记载具体到时日,并不能轻否。参证苏诗“空对孟光案”一语,亦与黄螢所载相合。又,黄庭坚早年自撰诗集曰“焦尾”者,当在元丰二年;此自有焚余之意,但亦不能无“半死桐”之感。综合多重证据,谢氏夫人之卒于元丰二年春无可更移。据此,合观苏诗四句,则上两句谓黄庭坚丧妻,而后两句“今典”所在,则谓遭逢家祸之际,太君老夫人发挥了无可替代之作用。④
黄庭坚于元丰二年秋至京城,在与晏几道、王稚川相会时,云“食甘念慈母,衣绽怀孟光”,也正谓此。“怀”与“念”都可以释为“思”,但“怀”又含有“伤”义。《邶风·终风》云:“愿言则怀。”《传》云:“怀,伤也。”陈奂《疏》云:“怀训思,此云伤者,思亦伤也。愿言则怀,言我思之则忧伤也。”[31](P14)潘岳《悼亡诗》三首中,“怀”字三见,“念”字一见。其中,“私怀难克从”“念此如昨日”者,皆为“思”;而“悲怀从中起”“悲怀感物来”者,则为“伤”。黄庭坚诗云“食甘念慈母”,“念母”两字又见元丰四年所作《赣上食莲有感》“分甘念母慈”,任渊已指出:“‘念母’字见《诗·渭阳(序)》。”[23](P61)“衣绽怀孟光”或亦兼用元稹《遣悲怀》诗“谢公最小偏怜女”“顾我无衣收荩箧”之语。也正是由于诉说离别母亲的思念以及对妻子去世的悲伤,方有所谓“客愁非一种”者。同样,在和晏几道的“照”字诗中说“风雨思齐诗,草木怨楚调”,这“思齐”两字不但有了着落,且顺带出了与苏轼交往唱和一事。黄庭坚的言外之意是告诉晏几道与王稚川说:新近结识的苏子瞻,在给我的诗中,特地问候了家母;而子瞻目前的处境,则是因为几首诗(即“怨诗楚调”)拘禁在了御史台。朋九万《乌台诗案》载:
轼在台,于九月二十三日准问目。据轼供说,其间隐晦有未尽者。比闻北京留守司取问根验,得轼元写去黄庭坚讥讽书并祭文;于六月十六日,再奉取问。轼将寄黄庭坚文字看详,轼方尽供答,其意并不系朝旨降到册子内。[32](P16)
黄庭坚诗中又云“本无心击排,胜日用歌啸”,即前次被“取问”之惊悸犹存:当日子瞻与我所唱和之诗,本无意攻击任何人事,不过是个人的吟唱罢了。《次韵稚川得寂字》诗中云“向来类窃鈇,少日已争席”,也是说被人怀疑中伤,而自己本无意与他人争斗。显然,黄庭坚此度来京,等待改官之外,尚有进一步接受“取问”的可能。故在与晏几道话旧之时,将眼下如此令人气丧之事和盘托出。其出语之晦涩曲折,本在情理之中。
在告诉晏几道目前的遭际之后,他们两人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提及了另一件发生未久的事,但同样也是刚开头却又煞了尾:“俱含万里情,雪梅开岭徼。”这里的“俱”,不仅仅指叔原、稚川“二妙”,也包括黄庭坚自己在内。此句殊突兀,既然三人相会,又无提及友朋远隔万里,如何言及此?实则,此时远在万里之遥者有一人,即“永不量移”的“英州(今广东英德)编管人”郑侠。[22](P6953)观“雪梅开岭徼”一语,是指晚秋的京城,风雨如晦、草木摇落,而万里之外的岭南,则已梅花先放。此内在一层意。但就字面意义讲,这样的“胜日”与“二妙”相会,一起歌啸吟唱,你们两位的诗中,真是得万里江山之助啊。“我惭风味浅,砌莎慕松茑。中朝盛人物,谁与开颜笑”,此四句接榫上篇,则于字面意为:我自惭阅历不多,诗篇写出亦乏风味;比之两君,无异于趴在台阶上的莎草仰望挂在松柏上的茑萝。京城人才济济,谁会对我投以青眼呢?而内在的一层意是说自己入京来无人能够伸以援手的困境。如此,则“二公老谙事,似解寂寞钓。对之空叹嗟,楼阁重晩照”四句方获一解释:叔原、稚川你们两位眼下能够离开京城的是非之地,逃脱政治攻击的网罗,诚然不易了;面对寂照房之外的峻楼重阁,我只有待命而已。黄庭坚《次韵稚川得寂字》诗,则是离开“寂照房”后入冬后的作品,观诗中有“曩过招提饭”“长安千门雪”已明。此时,晏几道已经离京西去颍昌赴任。
浅浅余寒春半,雪销蕙草初长。烟迷柳岸旧池塘。风吹梅蕊闹,雨细杏花香。 月坠枝头欢意,从前虚梦高唐。觉来何处放思量。如今不是梦,真个到伊行。
长爱碧阑干影,芙容秋水开时。脸红凝露学娇啼。霞觞熏冷艳,云髻袅纤枝。 烟雨依前时候,霜丛如旧芳菲。与谁同醉采香归。去年花下客,今似蝶分飞。
旖旎仙花解语,轻盈春柳能眠。玉楼深处绮窗前。梦回芳草夜,歌罢落梅天。 沉水浓熏绣被,流霞浅酌金船。绿娇红小正堪怜。莫如云易散,须似月频圆。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7](P285-286)
第三首是与“云鸿”诸君的“践约”之词,观词中节候已在“浅浅余寒春半,雪销蕙草初长”,与上一篇初冬离开颍昌东入“九重城”时间相接。通观前三首《临江仙》,可以就晏几道与“莲鸿云”交往的时间做一推测。晏几道在颍昌的时间已然可以确定在元丰二年秋至元丰五年初冬,则他在第一首词中所写的两度相见时间当为元丰二年的春与夏,词则作于元丰三年春天。第二首词写于元丰五年初冬,煞尾说“少陵诗思旧才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便是再明确不过之供状。第三首词是转过年的春天,即元丰六年在《乐府补亡序》中所提及的沈廉叔、陈君龙家时隔三年后的相会。
至于《临江仙》中后三首歌词据此也可以获得通贯之解释。第四首煞尾云“去年花下客”之“花”,乃照应上片的“芙容秋水开时”之荷花,亦暗含“莲”字。晏几道与“莲鸿云”们的第二度相见既然在元丰二年之七夕,正是荷花盛开之季节,故此时有对“旧景”难排之孤寂。叶嘉莹先生曾专提出此篇与晏殊词做一对读,得出的结论是:“小晏词在结尾之处所写的‘去年花下客,今似蝶分飞’,乃是一种情事的实指。”[33](P91)虽然叶先生所谓“实指”之“实”,强调的是情感的灵动与质实之“实”,但与这里实际情事之“实”正相吻合。第五首之时节乃在初春,正是第一度相见时,故下片所谓“绿娇红小正堪怜”,乃对当时之回忆。至若第六首为“小山词”名篇。观其换头处云“记得小初见”之“初见”正是春天,故有“去年春恨却来时”之语,故此词亦作于到颍昌之后的第二年,即元丰三年的春天。
综上,以“山谷诗”与“小山词”在时间、地点与人事的重合性推断,《临江仙》词表象虽为与“莲鸿云”诸位歌妓的离情别绪,但此种哀伤与无奈的情绪并非单一的,其中不免夹杂有熙宁、元丰之际士大夫间相同的悲感。而这种情感也是整个时代氛围所造成的,无论黄庭坚抑或晏几道,都无可逃避。由山谷诗的考释以还原出熙宁元丰之际士大夫的处境与心态,是目前能为晏几道歌词中深隐寄寓的掘发所提供的极佳且又是唯一的旁证,同时也能够为自编词集面貌的还原提供一些较为坚实的内证。如果我们顺延上述这一时间线索,可以较为清晰地判别出晏几道编撰《乐府补亡》所收辑的歌词创作大体不出两个时段:一为元丰二年京城短暂相会后至元丰五年在颍昌,这三年间对这一相会不断甚至是重复的回忆;二为元丰五年冬天回到京城后一两年间的“重逢”。
四、余 论
晏几道歌词的深隐寄寓的掘发,以上所做旁证只是提供一种解读的可能性,并不愿深文周纳。但此种深隐寄寓的掘发,可以为晏几道歌词体格形成的原因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宋人即有意识地将“小山词”与“花间词”相比,近人也不乏通过修辞声韵与内在感发力量的厚薄做出评判,但由于未能就其歌词之间的连属关系有一整体把握,因此对晏氏歌词体格之理悟尚有一间之未达。兹举晏几道最为名篇的《鹧鸪天》词说明: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这是一首当日便流传开来、后世更是品评不断的佳作,陈廷焯甚至推举说:“言情之作,至斯已极。”[34](P884)但是和其他的品赏者一样,对于这样一首不识字人便知好言语的歌词,惯常的做法总是不离开这首词所写的情境。较之“花间词”,“小山词”可以在固有的词境内将情感的深度极力地延伸,但同时这种延伸反成了读者读解的禁锢,因此也不免走入“狭深”。无论得失,对晏几道而言,都只是一种客观的观照,是在词学史演进背景下对其体格形成的内在动因的把握。这个“内在”是歌词自身的“内在”,而不关词人的“内在”。而我们这里的着眼点是要透过歌词“内在”与词人的“历史心理”做一联姻。
晏几道的经历没有可供研究者探讨的丰富话题,尽管可以通过黄庭坚的《小山集序》将其想象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但现实遭际总是一定的。歌词本身提供的信息虽然有限,但结合晏几道《乐府补亡》中所收歌词,则凡其所创作应是落在元丰至元祐间,《鹧鸪天》亦不例外。先看该词中的时间:“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这是对春天的描写。上文已然证明晏氏描写春天的相会无一不是对元丰二年与“莲鸿云”的“初见”,但这首词所写并非这次“初见”,而应是“重逢”。所以可知者是,初见之时,“云鸿”诸君在晏几道心中的影像是娇小可怜而略带羞涩的,观《临江仙》中之“斗草阶前初见”“旖旎仙花解语”以及“两重心字罗衣”可证。那么这里的“当年拼却醉颜红”之“当年”所指,乃是元丰六年春晏几道自颍昌归来后的重逢。更值得注意的是,换头也不是写对再度相逢的渴望,而是对已经逝去的相逢之留恋。盖自元丰六年春相见之后至元祐初即编撰《乐府补亡》之时,其间发生了变故。这场变故的起因与经过,难以考实——从晏几道现存作品来看,其中有不少言及远赴“江南”而生发的相思,以晏几道任职“监镇”衡之,当是在元丰五年冬回到京城改官,而随即再度得到了与监镇相似的官职离开京城时。⑤关于这场变故的结果,详细地载于《乐府补亡序》中:老友的死亡与病废,“云鸿”诸君的离散。由此反观这首《鹧鸪天》词,煞尾处的“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正是离散后不期然地与“云鸿”诸君中的一位重逢。
明了此间这层关系,词中将前人描写乱离之后的亲情、仕途风波的友情借来注入与歌女相逢之后的悲喜中,方不至感到意外。⑥[35](P230)就晏几道内心感触而言,“云鸿”诸君的出现,所牵动的可以远溯至元丰二年。黄庭坚与晏几道唱和的诗中,弥漫着浓重的悲苦。再上推至十余年前的京城,居住在京城故相宅子中的晏几道与他的新进士朋友,是何等欢快。而再度相见时,他们中的一位已经远谪到了岭南,生死未卜;黄庭坚因“乌台诗案”的审查郁郁难言;晏几道自身更因牢狱之灾,惊魂未定。短暂的会面后又是长期的离别,数年来晏几道辗转仕途,颍昌三年尚得父亲故人韩维的照拂,随后也不免苦闷无诉。白云苍狗,悲欢离合,映射入歌词的创作,虽然同是相思,但此时已经不同于元丰时期的陶醉,而呈现出反省与沉痛来。收入《乐府补亡》中的涉及相思的作品,当以陶醉渴望与反省沉痛为分水岭。换言之,无论词人自身是否有这样的自觉,歌词的编撰在思想史上关联起北宋一代士大夫的处境与心态,而在文学史上成了晏几道词风有所转变的标志。
歌词在宋人的生活中虽不可或缺、作者甚多,而于此擅长者或是“不经意”创作,或是在客观情势下的“被迫创作”。晏几道以“补亡”命名自己的词集,本身便是有感而发;他又将自己的感慨集中呈现在元丰年间“京城—颍昌—京城”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初见—相思—重逢”的“悲欢离合”的情事中,则正是要从这些小词中对个体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感触进行总结,正如他《鹧鸪天》词中所写:“诗篇多寄旧相逢。”由于歌词自身的娱乐性,晏几道编集歌词的用意之不能获当日理解,因而也是在情理之中。如果将晏几道的词学认知与歌词创作置于词学史的背景下,则他不同于苏轼等当日名公、士大夫之处在于,在“被迫状态”下的创作,无论词人刻意回避或者有意寄托,其歌词自身总是有意识地在承担着诗文的任务,有时不免沉重,甚至是板滞晦涩。晏几道的歌词创作中,歌词本身是独立的,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担负;他的歌词并无可以托寄之处,而他也无须在歌词中重重地打上现实遭遇的烙印。但是,还原晏几道歌词创作的历史情境,则“小山词”正蕴含有清代常州派所谓与“诗史”相补充的“词亦有史”的“史”之质素。正因为此,词学史上以“复古”面目出现的、“规模‘花间’”的贵公子晏几道,实际应是士大夫歌词时代来临之际被忽略与遗忘的一位先行者。
注释:
①按:据《寄李公择诗序》,任渊《山谷年谱》认为黄庭坚元丰三年春“在京师”(见《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目录》,第3—4页),但并未确指抵京之时日;而黄以为本年“入京”(见《黄山谷年谱》,第127页),则不足据。
②相关创作,参见《山谷诗集注》卷一《次韵王稚川客舍》《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归予戏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与之》(《黄庭坚诗集注》,第51—56页)。
③按:“郑侠案”有意排挤冯京;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正月”,第11册,第6311页。
④按:这里用“思齐大任”的典故,宋人往往用来指称辅助皇帝的皇太后,而在元丰二年即为仁宗曹后与英宗高后。但曹太后久已还政并于本年病故,高太后的听政则要迟至“元祐更化”之时,都不吻合。
⑤按:宋代的监当官如果要转为亲民官,必须经过两任;元丰二年至元祐初这一段时间,由晏几道所任“监镇”推断,他在外任职的可能性极大。
⑥关于这首词中所写的“君”,有论者甚至怀疑不应指女性,这是疑所不当疑。缪钺先生也推定是“云鸿”中的一位,由于忽略了背景的考察,因此将词人的感情理解为“惊喜”,见《缪钺说词·论晏几道〈鹧鸪天〉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这显然是不够充分的。俞平伯先生理解为“喜极而含悲”,则与本文的考证正相表里,见《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