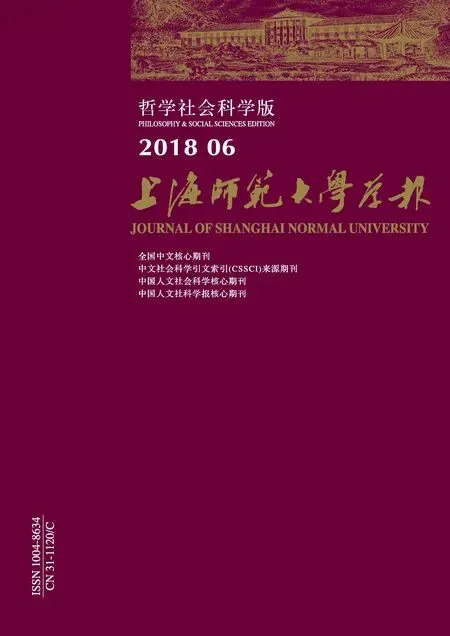美好生活的核心是劳动的幸福
陈学明,毛勒堂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2.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一、何谓“美好生活”:一个亟待阐释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题
美好生活是有理性的人的深度渴望,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他不仅有自然生命,而且具有超越自然生命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从而呈现出其特有的超越性存在特性。而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在根本上构成人的生命的本质属性,从而成为人与动物生命的本质区别。易言之,动物只有生存,而没有生活,从而是在其自然本性支配下的生命存在活动。人则不同,他不仅要生存,还要生活;不仅要生活,而且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从而社会生活和意义生活构成其生命特有的自为存在样式和彰显方式。事实上,人的生活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不甘心停滞于当下的超越性活动,从而人的生活在根本上表现为立足现实而诉求理想、身居有限却追求无限、置身必然而力求自由的永不停息的超越性存在活动,从而在理想与现实、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的内在张力中成就自由自觉的存在本质和美好生命样态。因此,追求美好生活具有深刻的人性论根据,美好生活乃是人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是其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是有理性的人的内在渴望,是人之自由本性的深度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个其不断建构美好生活理想、成就美好生活并不断提升自身生活品质的存在历史活动及其过程。
然而,由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又是人的社会历史性活动,因而“美好生活”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从而在不同的历史境遇和社会生活中,其所承载的具体内涵和价值指向是不尽相同的。譬如,在柏拉图看来,所谓美好生活就在于,在国家层面上实现各阶级各守本分、各尽其职,即统治阶级管理国家、武士阶级保卫国家、劳动阶级进行财富生产;在个人层面上则实现灵魂的和谐,即意志和情欲服从理性的支配,达到三者融洽无间。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美好生活的极致就是理性的沉思即知德,它具有自足、悠闲自适、持久不倦的属性,这是人的最高、最完满的幸福。在西方的中世纪,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则在根本上指向来世的天堂和死后灵魂的救赎。而对身处抽象资本主宰一切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来说,实现美好生活就在于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彻底废黜资本逻辑对人的无情宰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从而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53)如此可见,“美好生活”不是一个僵死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所以,对美好生活的探究,我们需要自觉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并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时空中求解和把握美好生活的本质内涵及其价值真理。
在今天的中国,经由习近平总书记多频次、广范围、多角度的阐释和宣介,“美好生活”成为一个影响日增的高频词汇,它不仅成为百姓口中相传的对更好生活的价值追求,也成为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习近平对“美好生活”及其相关问题有许多丰富而深入的阐述。譬如,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P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则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P11)并要求全党同志一定不能忘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3](P1)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新表述,以及明确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在根本上突破了现代性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狭隘视域,内在地承继并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及其要求,越来越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图景,彰显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深刻体现。同时,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时间中,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和价值指针;而且美好生活的建构不仅与民族复兴紧密相关,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具有直接关联。那么,究竟何谓“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核心和根本何在?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积极应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应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坚持和发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不断提升广大民众的美好生活和幸福度,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总之,对美好生活及其相关问题的积极应答和阐释,现实地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任务和理论课题,亟待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特别是需要哲学层面的深度介入和阐释。
二、美好生活的核心是劳动的幸福
如前文所述,如何理解和把握美好生活的概念及其价值内涵,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应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课题,并本质地关涉到如何成就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那么,何谓美好生活?其核心和根本又何在?对此,人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学科视野和理解路数,从而持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譬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一个人在生命完全自由、随心所欲的状态下,能够听任自己的整个身心选择一个生命发展的方向,一条生命走向完善的道路,并且他得以自由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走在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当人处在这样的生命过程之中时,他的人生就是美好的人生了”。[4](P283)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则从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的观点出发,主张功利乃是美好生活的根本和核心所在。边沁指出,“功利原则承认人类受苦乐的统治”,从而“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5](P211-212)由此,功利主义把实际的功利或利益作为衡量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原则和尺度,把美好生活与追求更多的功利和效用连接起来。而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则认为,美好生活是与人性的完美化紧密关联的,它是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他指出:“善的生活就是与人的存在的自然秩序相一致的生活,是由秩序良好的或健康的灵魂所流溢出来的生活。善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自然喜好能在最大程度上按恰当秩序得到满足的生活,就是人最大限度地保持头脑清醒的生活,就是人的灵魂中没有任何东西被虚掷浪费的生活。”[6](P128)事实上,对于何谓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解释,我们还可以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找出更多不同的回答。笔者认为,关于美好生活的深入解答,还是要回到马克思那里,或者说我们更赞同马克思的解答进路。
自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公开发表以来,西方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释路向。在这方面,马尔库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弗洛姆的《马克思的人的概念》可谓是代表作。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马尔库塞认为《手稿》使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即人道主义之上,而马克思正是以此为立足点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的深度异化,强烈批判资本对自由人性的野蛮宰制。弗洛姆则认为,“与许多存在主义的思想一样,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为物”,马克思的哲学“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而“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7](P15)所以,在他看来,若真有一个坚持人道主义理论的青年马克思和另一个抛弃这种理论的老年马克思的话,那么人们宁愿要青年马克思而不是相反。同样,美国道德哲学家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想是人道主义,不论就它把注意力集中于现世的人这个意义而言,还是就它最终要实现使人人都将破天荒第一次获得做人的充分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而言,都是如此。”[8](P60)这本书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论证了“人的献身的框架”,即论证了究竟什么是人、人究竟为什么去献身以及去为之而奋斗的目标。总之,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强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和焦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本性的研究,并由此出发才研究社会。所以,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好还是坏,并来判定一个人的生活是幸福还是痛苦。这就是说,一个社会能够有利于人的本性的实现,那么这个社会就是美好的,从而是值得拥护的社会;反之,就是坏的,是应当加以推翻的。同样,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是符合自我本性的生活,是自我本性的实现,那么这个人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反之则是痛苦的。
笔者认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必须基于人的本性来研究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研究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搞清楚人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构成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本质性的东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的本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手稿》中,而且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著作中。马克思一生对什么是人的本性做出过各种表述,但最核心的还是把人的本性表述为劳动。当然,最典型、最系统的表述还是体现在《手稿》之中,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明确地认定人的本性是劳动,而且围绕劳动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的要害就是“异化”,而这种“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进行了丰富而深入的论述,认为劳动作为一种自由自觉的生产生活和能动的类生活,是人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的根本方式,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人之自由本性的劳动沦落为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从而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9](P157)导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9](P156)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做了如下具体的规定和论述: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做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10](P207-208)
概括言之,马克思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他的体力和智力的表现;在劳动这一真正的活动过程中,人使自己得到了发展,便成为人自身;劳动不仅是达到目的即产品的手段,而且是目的本身,是人的本质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表现,因而劳动是享受。
把人的劳动视为人的本性,应当说不是马克思所特有的思想,不少思想家也有类似的观点。譬如,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特别推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黑格尔在其中表述了关于事物所固有的潜力及其能动的观念。再如,歌德也用诗的语言表达了人的本性是劳动的思想。他在《浮士德》中借用浮士德的口吻教诲人们:“既不是财产和权力,也不是感性的满足,能实现人对人生的意义的期望;在这一切中,人依然跟整体相分离,因此人仍然是不幸的。只有在生产性的活动中,人才能使人生有意义,虽然他在这一过程中享受人生,但他并不贪婪地想保住这人生。他戒绝了战友的贪婪欲望,他已被存在所满足;他是充实的,就因为他是空虚的;他之所以拥有许多东西,就因为他没有多少东西。”[7](P43-44)又如,弗洛姆在《寻找自我》中探究“我”究竟是什么,他最后找到自我就是劳动,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存在还是占有》一书。
由此可见,既然人的本性在于劳动,那么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潜能和本性,从而也只有在劳动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劳动是人及其社会的存在本体,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存在规定。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还不断地形塑人、成就人、提升人,从而劳动构成人基本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内容。劳动不仅为人自己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资料,而且正是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才形成了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并且劳动构成人类历史的底色。可见,正是人类的劳动活动,才能在根本上和全面地保障人的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也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实现生活的美好和社会的幸福。离开了劳动的视域,我们就难以科学地把握人的本质和真理,也难以正确地揭示人的幸福基础和美好生活的核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是生活世界的本体和根据;[11](P77)劳动是成就美好生活的基础,是奠基幸福生活的要途,从而劳动幸福本质地构成美好生活的核心和要义。那么,劳动幸福又是如何可能的?
三、劳动幸福如何可能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劳动是最基础、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从而劳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内容。所以,美好生活的核心就在于劳动的美好、劳动的幸福。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何谓劳动幸福?
要阐释劳动幸福,首先要对“幸福”做一个简要的规定和交待。然而,要对“幸福”做一个大家一致公认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困难来自幸福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捉摸的,而且幸福在某种程度是相对的,与人们所处的文化、个体心理、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生活处境等紧密相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幸福做出一些基本的思考和规定。譬如,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幸福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感受相关,它是一种主观幸福感,其实质是对自己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的问题,因而是对于满意(总体的、持久的)状态的一种认知。[12](P19)在此意义上,幸福是一种感觉良好,而不幸则是感觉糟糕。尽管幸福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自我满足状态,但是幸福的条件或基础却并非纯主观的。毋宁说幸福的基础在于客观的生活条件。在通常情况下,幸福的生活与身处其中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法律公正、风气良好、文化繁荣、教育发达、医疗充足等社会条件紧密相关。
以对幸福的前述理解为前提,所谓劳动幸福就是劳动主体对自我劳动状态的满意和满足,在劳动过程中感觉到愉悦、舒心和美好,在劳动中深刻体认到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彰显,体认到自由自觉的生命本质。事实上,从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劳动幸福意味着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种主体的自主的对象化活动,是劳动者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彰显,劳动因此是人的“第一生活需要”。如此,人们在劳动中得以享受总体而持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那么,劳动幸福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多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劳动幸福有赖于劳动必须是目的,而不能仅仅是手段。劳动幸福作为劳动主体对于自身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和劳动方式的一种愉悦的主观感受和感觉良好状态,是与把劳动本身视为目的紧密相关的。只有当劳动本身成为目的,劳动不为某种外在的目的和功利所胁迫、强制的时候,在劳动中人们才能自觉地收获劳动的美好和生活的幸福。相反,当劳动沦落为仅仅是一种达到某种外在于自身的其他目的的纯粹手段时,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是由外在的目的所施舍和认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与人的生命处在隔膜乃至疏离状态,与生命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相去甚远。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非人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仅仅把工人视为单纯的商品和微不足道的物料,把工人的劳动视为一种仅仅实现资本增值的手段,而完全无视工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生命价值维度。在把工人劳动仅仅当作实现资本增值手段的雇佣劳动中,工人根本无法以人的方式存在,也就不存在劳动幸福和生活的美好。所以,劳动幸福可能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劳动必须是目的而不能仅仅是手段。
其二,劳动幸福有赖于劳动必须是自愿的,而不能是被迫和强制的。幸福是主体自我的一种和谐状态,是对自我意愿的承认和认可,从而劳动幸福意味着劳动行为是劳动者主体在自我意愿基础上的自觉自为的活动。由于这种劳动是人的自我意愿的对象化活动,从而在劳动中人感觉到自由意志的积极发挥;是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自我自由人性的积极确证,从而劳动成为一种生命的自由自主状态,是主体的自我积极作为。在这样的劳动活动及其过程中,劳动不仅创造了幸福生活的物质前提和美好生活的基础,而且劳动本身就是幸福的体现和化身。相反,若一种劳动是被迫的、被强制性的劳动,那就意味着这种劳动是对劳动者主体意志的外在强制,是与主体的自由生命意志处于尖锐的对立和对抗之中,从而使主体意志遭遇剧烈的痛苦和打击,使得人的劳动活动乃至整个身心处于灰暗的压抑和极大的痛苦之中;而这样的劳动是与幸福绝缘的,建立在这样劳动基础上的生活是不幸和糟糕的,从而不可能体会到劳动的幸福和生活的美好。因此,劳动幸福以自觉自愿的劳动为基础,强迫性的劳动毫无幸福可言。
其三,劳动幸福有赖于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而不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正如前文所述,劳动幸福不能建立在把劳动仅仅当作手段、被迫性的强制劳动基础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劳动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劳动成为被迫劳动的情况呢?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者失去了直接的劳动生产资料,造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劳动者受制于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我们知道,现实的劳动有赖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没有了生产资料就无法进行现实的生产,也就没有了现实的生活资料,从而威胁到生命的存续。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为了维持生命,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被迫屈从于资本家的强制和淫威,遭受资本家的蹂躏和剥削,从而在资本统治下的雇佣工人是没有什么劳动幸福可言的。所以,劳动者要想拥有劳动的幸福和生活的美好,必须消灭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成为生产资料的自觉的主人。否则,劳动的幸福、美好的生活依然只是理念式的存在。
其四,劳动幸福有赖于劳动者之间形成合作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劳动关系则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从而劳动关系对于人的自由本性的形塑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这意味着,合理、合作、和谐的生产劳动关系对于人的自由劳动的形成、对于劳动幸福的获得,具有本质性的作用。试想,当人们长期处在一种极度紧张的劳动竞争关系、极度尖锐的敌对劳动关系中从事生产劳动时,他会获得美好生活和幸福吗?在一种尖锐对立的劳动关系中,“丛林法则”往往成为劳动关系中主导的原则,唯利是图成为劳动的核心价值尺度,由此会滋生出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戾气。而在这样的社会劳动关系中,难以寻求劳动幸福的踪迹。事实上,马克思从其早期的《手稿》一直到后期的《资本论》著作,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展开全面深入而又激愤的道德批判和历史批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雇佣劳动关系中充满着尖锐敌对的劳动关系,其中包括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和尖锐冲突,使得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导致了异化劳动和畸形的人际关系,人们在其中遭遇生命的无奈和灰暗。所以,劳动幸福、美好生活的可能,有赖于形成一种合作、共享以及和谐的劳动关系。
其五,劳动幸福有赖于劳动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幸福是人的自由本性的自由显现,是人的潜能得以不断实现而获得的生命的一种满足和愉悦状态。同样,劳动幸福来自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得以全面展开,在劳动的全面性和丰富性过程中,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全面展露和丰富呈现。“全面性对于人的‘本质’的要求,是一个保持开放与扩展的领域,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地有新的内涵、内容加入到人的规定性之中。”[13](P10)因此,当一个人的劳动长期在一种狭隘的劳动范围和片面的专业背景中进行时,人也就自然变得狭隘和片面,只能获得生命潜能的片面呈现。甚至在自发形成的极端的专业生产条件下,人几乎不能获得劳动的自足性和自由性,而只能是一种畸形和片面的存在。在这样的劳动境遇中,劳动主体是难以有幸福的体认和感觉的。[14]在这种狭隘畸形的劳动环境中,人们就像被限定在牢笼中的囚徒,身心会遭受强烈的被压迫感和钳制力,从而劳动与人的自由本性形成尖锐的对抗,出现像马克思所说的情况,即人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以电影艺术形式深刻而辛辣地揭示了这种片面劳动带给人们的单调、乏味、焦虑的非人道后果。所以,在片面劳动中是不可能有劳动幸福可言的,劳动幸福的实现需要以劳动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