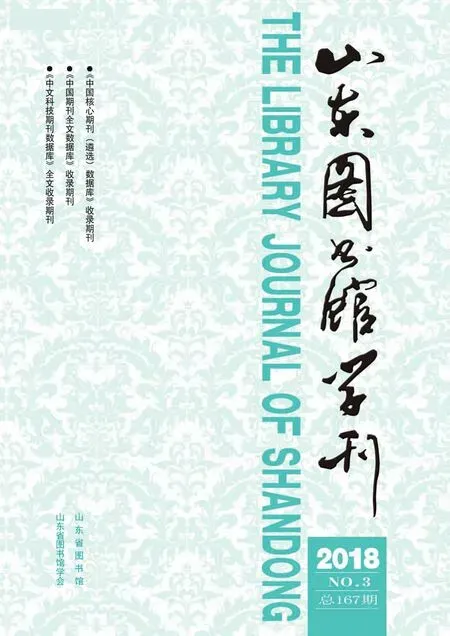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受事辨析
——读《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相关述论有感
黄俊民
(九江职业大学图书馆,江西九江 332000)
一
2017年11月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王波先生等的大著《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下文提及该书时均以《研究》简称之)面世了。这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的“国内首批与‘全民阅读’有关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之一”。(《研究》P.643—644)“书中的部分成果(笔者按:指先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该课题阶段性成果)已成为这个领域引用量可观的佳作”,(《研究》P.466)课题本身最终也以图书馆学界并不多见的“优秀”成绩结项。(参见《研究》后记P.645)因此,该书无疑具有了某种标杆意义。
该课题是一项“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调查研究”,(《研究》前言P.2)其成果十足地体现了智库式的对策研究报告的特征:既有丰富的调查材料,又有独立的建设性意见。但作者并没有止于此,而是还将触角延伸到了阅读推广活动的基础理论和理论基础上。这主要由第一章《导论》和第八章《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理论探讨》反映出来。通观全书,无论是集中研讨阅读推广理论问题的章节,还是铺陈调查材料及有关对策建议部分,我们都能从明里暗里看到或抽绎出一些构成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的范畴、命题。从我们的视角看,这当中包括阅读推广的“施事”“受事”和“与事”,阅读推广的“状语”“补语”,阅读推广的结构系统、机制等等。下面我们仅对其中涉及的阅读推广的“受事”一端作一辨析,以求得名士方家指教。
“受事”是语言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它表示语言结构中动作或行为施加的对象。如“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或她的书”(阮冈纳赞语)这个句子中,“书”即为行为“得到”的“受事”。在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语境结构中,受事无疑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书籍、读物。也许正是因为太过熟悉的缘故,许多人便熟视无睹了,对其中隐藏的玄机不大去理会,这直接导致了包括《研究》在内的不少著述屡屡在使用、表述中让人稀里糊涂,实际工作也常常出现偏离轨道的迹象。因此,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二
《研究》中述及了“中立派”阅读推广的理念——“我自备好众籍,供君自由取用”,“图书馆并不看人推送、施加影响,读者跟着感觉走,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随机而读”,“至于推广那(笔者按:疑是别字,当为‘哪’)一类的书,则不作预设。”(《研究》P.364—365)对于所谓的“中立派”阅读推广是否真的能够成立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众所周知,自封建藏书楼嬗变为近现代图书馆起,图书馆这个有机体就将面向读者、服务读者作为自己的灵魂,并逐渐建立和不断完善一套业务运行制度和服务组织体系,以适应履行职责、担当使命的要求。这包括至今仍存续和发展的广泛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科学陈列文献信息资源并为读者提供自主检索、自由披览、自愿借出的便利。这样一种机制环境比较适合充分发挥读者的能动性,满足其出于猎奇探秘、休闲养性、应对问题、系统学习的动机而主动随意翻检利用文献信息的愿望,也能在相当程度上达到目标。因此从逻辑上讲,“中立派”阅读推广与既有的图书馆服务内容和方式是完全吻合的,与“新兴业务、创新型业务”(《研究》前言P.1)似不能挂上钩。况且这种“阅读推广”的受事是全部馆藏、任意馆藏。如果拿《研究》所厘定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涵义来衡量,它因为不是“通过精心创意、策划”,聚焦“小范围的”馆藏,所以可以不认为这是一种阅读推广类型或模式,充其量只能视作在图书馆部分传统业务工作的头上加戴了一顶时髦的新帽子而已。
《研究》中着墨比较多的是图书馆“教育派”阅读推广中“经典文献”“实用文献”与“有吸引力”的图书三种不同的受事。不难发现,它们是按照不同的标准所作的划分,并不处在同一平面上。“经典文献”定义的是书籍内在的品质价值,“实用文献”强调读物的功能,“有吸引力”则直指刺激读者感官而形成的形式上的某种诱惑力(如封面颜色相同、书型尺寸一致、均为零借阅、都破烂不堪等)。一方面,在该书作者看来,援引教育学原理中的“永恒主义教育观”和“进步主义教育观”,可以将阅读推广中的“教育派”归结为“经典文献阅读推广”和“实用文献阅读推广”两种类型;(参见《研究》P.275)不仅如此,二者之间似乎还泾渭分明。另一方面,又强调图书馆阅读推广就是“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海量馆藏引导到小范围的有吸引力的馆藏”上来的活动,(参见《研究》P.9)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有吸引力的文献阅读推广”概念(书中举了很多属于此性质的案例)并将它作为一种模式,但实际上是肯定这种做法的。我们认为,将阅读推广的受事如是分别和界定,无论从阅读推广的宗旨还是书籍读物本身的意义看,困难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图书馆服务的主题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服务读者求知和服务读者求索。求知主要是分享别人所创造的知识成果和智慧结晶,求索则是在对已有知识的吸收、消化的基础上批判、创新与发展,形成新的认知。图书馆各种组织和工作无不围绕这两个主题,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协同作业。阅读推广作为一种新兴活动,“是为了推动人人阅读”,“旨在培养民众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提高民众的阅读质量、阅读能力、阅读效果”。(《研究》P.4)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图书馆的诸多活动,如图书馆宣传、图书馆营销、图书馆书目推荐、图书馆展览等活动盘根错节”。(《研究》P.6)从一定意义上讲,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是图书宣传、阅读指导等传统读者服务内容的拓展、深化与提高。它与图书馆情报资料工作主要是服务读者求索不同,其要义和核心在于为读者求知服务。放眼大尺度和长时段,馆藏的任何一种图书或许都能成为读者求知求索的阶梯。但是因为实际上,在特定的、具体的阅读推广(策划)活动中,聚焦的只能是“小范围”,而且着眼点主要是对于求知有所裨益的读物。因此谁能入闱并成为真正的受事而不是“影子受事”,则基本上取决于站在这个立场上遴选出来的图书当前所具有或被挖掘出的价值及其与本次阅读推广活动选定的“抓手”(如有关作者或书籍的整十整百纪念时间、时政热点等)的关联度,有较大价值且关联度高者即可入列。
那么,所谓的“有较大价值”又当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认为,通常情况下,一个普通图书馆的共时馆藏书籍,按照其时下读者和社会的认识水准所能判断出的品质高低和意义大小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区分为经典、要籍与名著、力作、僵书、盲肠书、劣书等六大板块。这六大板块构成分析和确定图书馆阅读推广受事的“基本标准面”,前三者就是这里所说的“有较大价值”的图书,也可称为“好书”或“有意义的书”(这与日常话语体系中的“好书”等涵义基本吻合),它们才是有资格成为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受事的图书。
三
关于”经典”,这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什么是“经典”,为什么要读“经典”,怎样读“经典”等等,大家、普通学者乃至一般的读书人不仅说了很多,而且说法也很多。《研究》虽也反复述及但对其概念、范围却未曾明确宣示,倒是其将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教育派”分为“经典文献阅读推广”和“实用文献阅读推广”的逻辑很是容易把读者带入“大凡文献非经典即实用、非实用即经典”的文献二元构成的认知阴沟。这显然是危险的。这里,我们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角度对经典(当然是指法律所能包容的那一部分,像法西斯主义文本《我的奋斗》那样的必须禁止和遭到唾弃的臭名昭著的思想浊流、逆流断然不在其列)作三点分析,以利于正确辨别、认识、选取和促进阅读。
首先,堪称经典的当是在人类精神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至高地位,已渗入各色人等思想层面,持续深刻影响着人们精神世界的那些重要著作。它是经过时间淘洗,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学术发展过程中被反复过滤、筛选而沉淀下来的书之精华。它凭藉所蕴含的永不消退、历久弥新的精神能量、思想光芒和智慧魅力,跨越时空保持着对人们的强大吸引力,并令人们萌生崇敬之情。强调这一点,是希望图书馆阅读推广永远不要忘记经典的教化意义,要努力使希望受到良好教育(大概没有人不“希望”如此。这个“良好”是”更好”而不是“最好”。这个“教育”是终身的)的所有公民知经典、爱经典、读经典。朱自清先生指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二版,P.4)那种“质疑对经典文献的阅读推广,强调要针对读者的文化程度、职业特点、生存需要以及地方主流产业的特点,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很强的读物的阅读推广”,“不盲目攀附精英教育、经典阅读”(《研究》P.274)的认识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来它把学习经典与学习实用技术完全对立了起来,把学习经典当作只是象牙塔里的事,专属精英教育。其实包括大众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都需要给受教育者“精神补钙”,也就是人人都需要也希望得到经典的滋补,这是成为有教养的公民所要求的。二来它片面甚至错误地理解了经典的概念和学习经典的涵义,以为经典等同于晦涩艰深,以为经典就是虚幻的哲学,以为学习经典完全就是逐字逐页通读、读透。其实,有些经典平实而易懂,实用技术领域也有经典,了解经典、感受经典和熟悉经典的生成史、流传史也是学习经典的一个方面。即便是阅读经典,也不能一开始就出现畏难情绪。胡适先生说得好,“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我们要打倒难读,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胡适,为什么读书,现代学生,1930年12月至1931年2月第1卷第3、5期)为什么要读“读不懂”的书?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如果一味只看那些一看就懂的书,获取感官愉悦,而美其名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则无论读多少书,也是低水平的重复,至多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很难有知识水平的进步提高。”所以应当“努力读懂自己原来读不懂的书,使得读懂的书越来越多,读不懂的越来越少。”(桑兵,读懂那些“读不懂”的书,北京日报,2015年7月13日理论周刊·读书版)三来它把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与图书馆其他服务工作混为一谈了。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室)、职业院校图书馆大量备存实用技术方面的图书报刊并提供阅览、外借、复制等服务,甚至建置专题阅览厅室,开坛宣讲传授实用技术,这些都不成问题。但必须注意,这些服务并非就是阅读推广,它们与阅读推广活动各有其趣,各有其责,相得益彰,而决不是你即我、我即你。四来无视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促读和助读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图书馆阅读推广正是为促成读者“乐读”和解决读者“读不懂”的问题而设置的活动项目,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消除某些隔阂。
其次,经典不仅在所属领域独领风骚,而且成为不同领域所能共同享用的极为宝贵的资源。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它提出的生物进化学说,“使生物界的种种现象都得到一个统一的解释”,“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也产生极大影响;它猛烈冲击了当时支配思想领域的神学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物种起源》”条)恩格斯将其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再如《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他以辩证的眼光提出来的几套术语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索绪尔”条)这一点提醒我们阅读推广工作者注意,凡是经典,都值得了解,值得学习,不要受学科藩篱的限制。但不同的人学习经典,学习不同的经典,方法及目标取向可以不求一律。比如,叶圣陶先生认为,对于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中学阶段只能间接接触,就是说阅读《经典常谈》这样的书就可以了。”“在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文史哲的学生就必须有计划地直接跟经典接触,阅读某些经典的全部和另外一些经典的一部分。那一定要认认真真地读,得到比较深入的理解。”(叶圣陶,重印《经典常谈》序,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二版,P.2)又如,对于自然科学经典,除少数研究家通过阅读来研究其中的专门问题外,大多数读者无须通过它来学习诸如物理学定律那样的专门的科学知识,而主要是通过了解、翻阅来追摩、感受文字后面的传奇故事、大师的思维与创造过程和科学精神。(参见:任定成,科学元典的精神价值,光明日报,2016-03-29第010版)
再次,经典是建构的,不仅时读时新,而且范围也处于变动之中。毫无疑问,作为典籍文献,它们与数量上汗牛充栋的其他文献书籍在形态上并无二致,为什么只有它们才称得起经典之名?这固然是由它们自身的价值意义所决定的。然而,它们的价值只有通过发现、挖掘才能被认识或重新认识,所以说经典是建构起来的,是经历了经典化过程的。这当口,经典包括哪些文献,某一具体文献算不算经典,不同的人往往也会出现理解上的分歧。如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儒家学者以儒家经典为正宗,朱自清先生早年在《经典常谈》一书中给出的范围则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以及《说文解字》等书籍。葛兆光先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完成的《中国经典十种》按照其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理解确定的经典主要是《周易》《论语》《老子》三《礼》《淮南子》《史记》《说文解字》《黄庭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坛经》。而正在进行当中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更是以“当代意识和世界眼光,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历史作用和现代化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因此,这套书不仅选入了‘五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也选入了《老子》《庄子》《太平经》《坛经》《金刚经》等其他学派的经典;既选入了众多名家的诗文集,也选入了大量小说、戏曲的经典之作;既选入了大量思想经典,也选入了《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历代名画记》《茶经》等科学类、生活类、艺术类经典著作。这个选目既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历史面貌,又具有时代特色。”(廖可斌,《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打造解读经典的经典之作,国图出版社微公号,2017-12-19推送)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等经典化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小说一向不受重视。自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就被认为不是‘可观’的一家。有些作者也自视为‘君子弗为’的‘小道’,不敢或不愿留下自己的姓名,用了各种笔名或托名。”(程毅中,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文献,2004年第2期,P.199)后经王国维、胡适等一大批先哲后贤殚精竭虑,将中国小说研究学术化,小说的地位才有了根本改观,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也得以开启,小说不仅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经典小说对人们思想行为性情的影响程度也早已不输其他经典了。古代戏曲也是类似情形。正因为经典的这个特点,图书馆工作者必须善于学习和掌握学术界关于经典著作研究的历史性成就和最新成果,并运用于阅读推广活动;同时要积极投身文献研究,积蓄力量,争取参与到文献经典化建构的过程当中来。
四
如果说里程碑式的贡献、划时代的意义、思想的种子、强磁场般的辐射力是经典的“标配外衣”,那么,在“好书”或“有较大价值”的图书阵营里,还有两类扮相不同的成员:一是要籍与名著,二是力作。
要籍就是重要的材料。它是了解、研究相关问题的入口或是进一步深入认识和探索的管道。集编的工具性图书、纪实的档案性文献、原创的认知性著作里都有众多要籍。例如教授给学生开具的专业与课程学习阅读书目当中的必读应读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少条目后附列的“参考文献”和“推荐书目”,许多目录学著作(像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陈高华、陈智超等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著录和介绍的书籍。要籍之于专业技术人员的意义比较突出。名著是知名度比较高、流传比较广、影响比较大并且有着较强生命力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红旗谱》(梁斌)、《创业史》(柳青)、历史学专著《国史大纲》(钱穆)、数学教育图书《数学分析习题集》(吉米多维奇)。
要籍、名著之间有不少交叉,有的虽是要籍但知名度却不一定很高。要籍与名著同经典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典基本上都是由要籍与名著升华而成,因而更加超然,“气度”和“格局”自然也更胜于一般的要籍与名著。但是反过来,要籍名著则不一定都能够成为经典。如《史记》被尊为公认的经典,而《清史稿》(清史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史料)却未必能够与之比肩。
力作主要是针对新书而言的。新书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要聚焦点。新书由于是新生的,尚没有经过时间考验,其影响力和价值几何势必难以充分显露,所以对其选择并进行阅读推广有一定的特殊性,故而我们把它单独列出来考察。阅读推广人员首先需要对什么是新书、新书里面的力作又该怎样判断和遴选这样两个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关于新书的划界,我们认为可以参考严肃、权威的专业和学术评奖活动对参评成果问世时间设限的做法。比如,“陈省身数学奖”奖励近五年内发表的最佳数学研究成果的作者;“王力语言学奖”评奖规则规定,推荐论著必须是在规定的评选日期前一年至五年之内公开发表的;“茅盾文学奖”主要授予评选年度内(现每四年评选一次)公开发表与出版的长篇小说;“鲁迅文学奖”各单项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大奖每四年评选一次,选出该评奖年度里某一文学体裁中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据此,我们不妨把新书设定为近五年内首次出版(不含重印)的图书。这与文献计量学中著名的普赖斯指数将五年内的新文献作为一个文献区域的方法也是吻合的。认识新书里的力作,除馆员靠自己修成的火眼金睛外,比较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学术书评、文学批评、出版社感言、编辑手记、名家序言、评奖结果等获得相关信息。
在图书馆现实馆藏中还有一批这样的书籍:出版以后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甚至一度成为热门书。然而,由于社会的快节奏变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的急速更新换代,它们在长江后浪的推送下成为前浪并很快湮灭。高等学校教科书、专科辞典、技术与管理类著作等等很多都难逃厄运。我们姑且称之为僵书,如谭浩强的《BASIC语言》。
盲肠书指的是图书馆收藏的那些品质平平、含金量较低、可有可无的图书。它之于读者就像人体的器官盲肠一样,一方面确实存在,另一方面确实没什么用处。盲肠书的出现与图书的生产端——出版社把关不严甚至买卖书号等劣行有关,也与图书馆采访工作不力或失误有关。
更为需要警惕的是图书馆的书架上兴许还摆放着劣书,也就是粗制滥造、学术不端、硬伤累累、甚至有致命问题的品质低劣的图书。比较突出的如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少儿身边的不良读物、低水平多讹谬的古籍整理出版物、质量较差的保健养生类图书和贻害无穷的劣质辞书。这当中,王同亿现象即为典型案例(参见:①袁汝婷等,青少年身边的“问题读物”为何挥之不去,半月谈,2016年第20期;②杜羽,古籍整理出版:繁荣难掩隐忧,行业亟须规范,光明日报,2015年3月18日;③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整治养生类和教辅类书出版乱象,人民网,2011年07月27日;④北京市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王同亿等被告彻底败诉,辞书研究,1998年第1期)
五
为什么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受事应当主要锁定在经典、要籍与名著以及力作,也就是有较大价值的“好书”上,而不宜不分菁芜、唯书是举?因为这符合读者一般的求知审美需要,符合图书馆服务的要求和工作规律。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1808~1970)在人的需要七个层次理论中指出,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都是较高层次的需要。认知需要包括求知、理解、探索和好奇,审美需要表现为人们追求对称、秩序与和谐。这些都是人性的基本方面。(参见:孟昭兰,普通心理学,1994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P.370—371)满足这些需要,毫无疑问必须通过读书,特别是阅读有价值的书来实现。
中国学者历来重视读好书、读有价值的书。清代考据学家王鸣盛(1722~1798)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指示读书门径的目录之学最切要之处莫过于通过揭示最有意义的书籍而使读者得其门而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先生曾应清华学校学生讨教治国学之法的请求开列了一个阅读书目,名曰《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该书目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和激烈批评,成为非常有趣的一桩学术公案,直到今天仍然聚讼纷纭。当时发出批评言论的清华同学声称:“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胡适先生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帮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梁启超先生批评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资治通鉴》,岂非笑话?”然而,据李隆国先生考证分析,胡适先生的书目自有其理路,在他看来,凡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都在收录之列,而那些最能够代表时代进步的实为首选,这些书籍是理解历史线索的凭借和工具。(参见:李隆国,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北大史学,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135—15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批评者意见如何,至少有一点不容否定,那就是胡适先生是站在推荐有价值的要籍的立场上开具这个书目的,所列之书也的确不一般。
现代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经说过,读书须“知道一位有地位的著者,常是经历着一般人所未曾经历过的艰辛,及到达了一般人所未曾到达的境界:不仅因此可免于信口雌黄的愚妄,并且能以无我的精神状态,遍历著者的经历,同时即受到由著者经历所给与读者的训练,而将自己向前推进一步,向上提高一层。”(徐复观,应当如何读书?,东风,1959年1月第一卷第六期)徐先生在这里实际上也是倡导读重要著者的书,以发展自己,提升自己。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十分强调读好书、读重要的书。他在1897年5月25日的一封信中要求,“以后,请你把最重要的一些新书直接寄给我,让我尽快地收到,这样才不致于太落后了。”(周文骏,列宁论图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P.9)1920年9月1日他在向鲁勉采夫博物院图书馆提出的借书请求中,指定希望借到的图书包括:“两部最好、最全的希腊语词典”,“几部最好的哲学辞典,哲学名词辞典”,“完全的和最新的版本”的希腊哲学史等。(同上,P.120)他还对劣书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1919年10月24日在“看完了‘1919年3月6-7日的第三国际’这本小册子”后批评道,“这本小册子编得糟透了。完全是粗制滥造。”并宣布“对这一类出版物给以严重警告”。(同上,P.108)
《研究》中提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时,应该吸收教育理论史和图书馆学史上那些具有权威性、说服力的前贤之论,选择正确的令读者信服的理论路线”。(《研究》P.13)这是高明之论。遗憾的是,《研究》在第八章中设专节对教育理论史上有借鉴意义的观念进行了一番介绍,而对图书馆学史上的理论观点却没有系统梳理和呈现。这里,我们不妨列举一些图书馆学史上有代表性的论述来简要阐明优秀图书作为阅读推广活动受事的依据。
刘国钧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指出:“图书馆的一切工作组织都以实现宣传图书、指导阅读和供应资料,也就是图书利用为其目的,”“采购工作者选择最适合本馆读者之用的优秀图书,就是在进行着图书宣传和阅读指导。”编目工作者、书目参考部门、借书处人员“都是为读者服务,因而都担负着宣传图书、指导阅读、供应资料的责任。”他还转述了苏联图书馆学家捷尼西叶夫的一段话:“我们认为图书馆事业是这样一种职业,这种职业需要具有足够的政治修养,具备马列主义的理论、广阔的文化视野以及关于藏书补充和组织问题,关于图书宣传和读者指导方法的专门知识。尤其必要的是使图书馆员能够好好地懂得一切知识部门中优良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书籍,并善于在读者中间宣传它们”。刘先生表示,“这就是图书馆事业向图书馆员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P.104、106-107)
苏联杰出的图书馆学家O.C.丘巴梁(1908~1976)在1960年出版的《普通图书馆学》一书中概括的阅读指导“这个过程的内容为:在了解读者的爱好和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地宣传图书和推荐图书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影响读者阅读的内容和性质,影响他们对书籍的选择和领会。”(转引自:张树华等,图书馆读者工作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P.6)1980年代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科书认为:“阅读指导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要有目的地向读者推荐适用的优秀书籍,有针对性地满足读者对文献的需求”。(出处同上)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中外图书馆学史上的理论遗产的精神和原则并没有过时,仍然有其重大指导意义;不仅对传统的图书宣传工作有效,而且显然更切合于后起的比普通图书宣传更加专门化、指向更明确也更有深度的阅读推广活动。
按照《研究》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内涵的分析,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图书馆的这项新兴活动与别的业务工作交相辉映却又不相互取代。传统业务部门的做法可以解决许多阅读利用文献和信息知识交流问题,唯有在“促读”和“助读”方面显得力不从心,需要阅读推广活动强力介入,全力担当。这实际上表征了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诞生和存在的理由。所以,作为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它自有独特的核心功能和核心价值。一般性的图书宣传和阅读指导工作尚且再三强调面向好书,图书馆阅读推广如果不比其他业务部门更加看重好书、有价值的图书并致力于它们的阅读促进和阅读帮助,而是单纯追逐活动表面的热闹、形式的新奇和质量不高的流通量以致罔顾推广对象中是否混杂着品位堪忧的书籍,读者将会因为不能获得所期待的应有的收益和浪费了时间与精力而失望,图书馆及其馆员费尽心机、消耗物力财力也必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