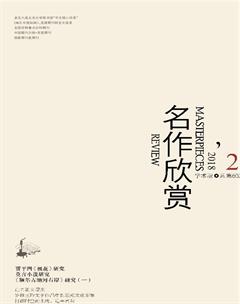解读艾丽丝·门罗《逃离》中的“替罪羊”形象
郝丹
摘 要: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其小说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有着较高的评价。《逃离》是门罗的代表作,在《逃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形象——弗洛拉。本文将从“弗洛拉”着手,对弗洛拉进行“替罪羊”式的解读,为理解门罗思想提供另一个角度,也为门罗作品的多样解读提供一个思路。
关键词:《逃离》 卡拉 弗洛拉 替罪羊
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最为著名的女作家之一,2013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學界一直对门罗有很高的评价。她的作品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小说,而是形成一种独特的门罗风格。《逃离》作为门罗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门罗主要风格的凝聚。在《逃离》中,门罗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女主人公卡拉面对苍白的感情生活和家庭冷暴力萌生出逃离的想法,并在邻居西尔维娅的帮助下进行逃离又中途折返的故事。小说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氛围中,让读者不得不注意伴随着这种神秘氛围的形象——弗洛拉。弗洛拉对马匹的安抚与卡拉对克拉克的依赖、弗洛拉的失踪与卡拉的逃离、弗洛拉的返回与卡拉的回归,自然而然使读者将这两者视为一致的存在。故事的最后,门罗以委婉的方式向读者传达了克拉克将弗洛拉杀死的事实,弗洛拉的死很容易让人想起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①,那就是“替罪羊”形象。替罪羊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文化原因,门罗借助弗洛拉这一替罪羊形象,来向读者展示弗洛拉的悲哀、卡拉的悲哀及女性的悲哀,来探讨自身欲望与他者压力、不自由与逃离、男性主导与女性反抗的矛盾,以寻找解决这些矛盾的突破口。
一、《逃离》中的“替罪羊”形象
“替罪羊”是一个一直存在于社会和西方文学中的形象,最早出现在《旧约》中,在门罗的作品《逃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或明或暗的替罪羊形象。弗洛拉是《逃离》中的一只山羊,它本身是没有“罪”的,但由于它与女主人公卡拉的关系密切,在男主人公克拉克的眼里,它就是有罪的。它的“罪”是外在权威强加的,弗洛拉便成了“替罪羊”一般的存在。弗洛拉最后因欲加之罪死去,它的死带走了卡拉逃离的“罪”。
“替罪羊”形象的形成有几个最基本的要素,即暗示、确认、仪式、罪。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要成为“替罪羊”,那么这四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正是由于这四个要素,才决定了“替罪羊”的指向与命运。
所谓的“暗示”,就是指一个有权威的、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神或人对“替罪羊”所在的群体或个人进行暗示,从而引导群体和个体对“替罪羊”进行心理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处罚。这种“暗示”有三种方法:神谕、权威、个体。《逃离》中对“替罪羊”的暗示是通过个体的权威性来展现的。在男权社会下,占据这种权威性的是男性,也就是克拉克。在克拉克的冷暴力下,卡拉萌生出了逃离的想法,并在邻居的帮助下逃离。在克拉克看来,卡拉的逃离与返回都与弗洛拉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弗洛拉的失踪才使卡拉有了逃离的想法,于是,克拉克就将卡拉逃离的“罪”归于弗洛拉的身上,并用“你这外层空间来的山羊”此类话语向他者暗示弗洛拉的异类与罪恶。
所谓的“确认”,就是将罪固定在某物或者某人的身上,在暗示的基础上使“替罪羊”的身份落实,也就是说使“替罪羊”成为“替罪羊”。“替罪羊”的“确认”方式有四种:神示确认、集体确认、个体确认、自我确认,每一种方式背后有不同的暗示者。在此,重点讨论的是“个体确认”。“个体”由于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不具有权威性。可是当集体的范围缩小时,处于权威中心的个体就有确认的能力,而此时这个个体的权威往往是集体赋予的。在《逃离》中,在家庭这个小集体中,丈夫克拉克自然就有了确认的能力,他认为谁是有罪的谁就具有罪,谁可以赎罪就可以赎罪。克拉克在家庭中的权威是由整个男权社会中男性地位的权威性决定的,因而在权威下弗洛拉一步步地成为“替罪羊”。
所谓“仪式”,在完成了“确认”后,就要对“替罪羊”进行仪式的考验。“仪式”主要有命名仪式、控诉仪式、惩罚仪式,在经历了这三种仪式后,“替罪羊”的命运就被固定了。弗洛拉从一只山羊到“蠢东西”“外层空间的存在”再到最后的死去展示了仪式的三个过程。
当这三个要素都具备时,“替罪羊”就和最后一个要素——罪结合在了一起。弗洛拉的“罪”是男主人公克拉克认为的,是权威强加的,它的罪是通过卡拉的两个梦境来表现的。
第一个梦境:“弗洛拉径直走到床前,嘴里叼着一只红苹果”②,这里的“红苹果”很容易让人想起《圣经》中伊甸园里的禁果。弗洛拉嘴里的红苹果是自由的象征,卡拉开始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无力并产生逃离的想法。第二个梦境:弗洛拉“引导卡拉来到一道铁丝网栅栏的跟前,也就是某些战场上用的那一种,接下来它,也就是弗洛拉,从那底下钻过去了,受伤的脚以及整个身子,就像白鳗鱼似的扭着身子钻了过去,然后就不见了”③,在这个梦里,“铁丝网栅栏”是一种界限,限制女性的自由与权利。女性只能在栅栏内活动,一旦她们想要跃出这个界限,就会面临恐惧与毁灭。弗洛拉像白鳗鱼似的最终钻出栅栏,表明卡拉走出栅栏,走向自我自由与权利。
“红苹果”“栅栏”“白鳗鱼”都是常见的《圣经》符号。这也正好与《圣经》中的原罪相呼应。伊甸园中的“红苹果”本意是人可为上帝所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人类思想的转变和对自由的追寻,上帝因此降罪于人类以及诱惑者——蛇。在“替罪羊”形象中,上帝就是权威存在,具有掌控力,有权确认谁“有罪”,和谁去“赎罪”。在日后的文本中,这种权力会被下放到集体或者某个人的手中。实际上,在这个文化范畴中,“罪”的本身无所谓有无,而重点在于权威是如何认知的。《逃离》中如白鳗鱼一般的弗洛拉最后被克拉克杀死,克拉克要杀死的并不是弗洛拉作为山羊主体的存在,而是克拉克认为的“有罪”者。克拉克认为弗洛拉是卡拉逃离的根本原因,是罪恶的。
二、“替罪羊”形象的成因
“替罪羊”作为一种典型的形象,从本质上是人类内在心理的产物,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结合的结果。“集体无意识”对于“替罪羊”本身形成有强大的范型作用,“个体无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替罪羊”形成与发展。
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看,世界不过是一种内在精神世界的显现,是一个意象的世界,它同时作为外在的诱惑和内在的驱力,推动着人们的日常行为。④这种集体无意识其实是造就“替罪羊”的主要原因。“替罪羊”形象源于人类本身对“罪”的恐惧和抵触。无论“罪”是如何产生的,都意味着不幸与灾难。而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之一,因而就产生了避罪。“避罪”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罪感文化”,而是因为我们对“罪”之后的“惩罚”感到恐惧。⑤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推动下就需要“替罪羊”去“替罪”。在《逃离》中,弗洛拉实际上是双重替罪羊。从文本表层来说,弗洛拉的死带走了卡拉逃离的“罪”,弗洛拉是替卡拉逃离的行为受罪。但实际上,弗洛拉替的是克拉克的罪或者說是“集体无意识”的罪。弗洛拉之所以成为“替罪羊”是因为这个家庭小群体的权威者认为其有罪,认为它引诱了卡拉进行出逃,这背后隐藏的是男权社会下男性的权力问题。在男权社会下,“集体无意识”认为男性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主体,女性必须生活在男性的周围,不能脱离这个范围,一旦女性有脱离、反抗的迹象就会被视为系统之外的异类,所以克拉克也称卡拉的另一面弗洛拉为“外层空间来的山羊”。男权社会下的这种集体无意识便使弗洛拉成为“替罪羊”。
个体无意识中存在着与情感、记忆、思维等相互关联的许多种族丛,荣格称之为“情结”。情结在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对荣格而言,自我构成了意识领域的核心,是个体意识行为的主体。可见,“个体无意识”更多的是在个体的角度对事件进行阐释,对人的意识和经验加以观照。“个体无意识”对于“替罪羊”的塑造作用多是通过对“替罪羊”的罪名指向决定的。《逃离》中弗洛拉的“罪”就是克拉克“个体无意识”确定的。在文本中,弗洛拉作为一只山羊,其本身是没有罪的,在卡拉的眼里,弗洛拉是自己关系密切的朋友,是自己受到丈夫冷暴力时的倾诉,是自己无聊时的慰藉;而在西尔维亚眼中,弗洛拉是像卡拉一样天使般的存在,是可爱的代名词。就是这样一个在其他众人眼中活泼温柔的存在,在克拉克看来却是罪恶的、引诱性的。在“个体无意识”下,克拉克把弗洛拉定性为有罪者,又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弗洛拉替罪而死。
三、“替罪羊”形象的意义
“替罪羊”形象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复现,它不仅凝结在艺术作品中,而且已经把个人命运纳入人类整体命运之中,成为整个人类的心理凝结物,它凝结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共同因素。⑥门罗借助这个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的载体——“替罪羊”形象,向我们展示男权社会压力下女性对独立与幸福的追求,揭示人对自己的阴暗面、欲望、原罪的正视以及对女性不自由与逃离之间契合点的寻求。这些从一定程度而言,既是“替罪羊”本身救赎功能的体现,也是“替罪羊”对于社会的巨大意义。
替罪羊机制是在社会各力量不均衡,个人或群体处于危机状态时,迫害者为了自身利益、关系稳定,将罪恶归结于被害者身上。这是一种来自外界的权威对于弱者的压力。《逃离》中的丈夫克拉克完全属于关系中的强者、权威,卡拉属于关系中的次弱者,弗洛拉属于关系中的弱者。在这种完全权威的统治下,弱者自然而然地有种不适感,这就使她们开始思考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社会的附属,开始思考女性的地位与权利。于是,她们产生了逃离的想法,但她们的逃离并不是一种懦弱的逃离,而是一种强烈的抗争,想要在男权社会中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但是这种想法与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不相符的,她们就被作为异类而对待,也就造成了弗洛拉作为“替罪羊”的死。但无论外在的压力有多大,面对自身的自由与幸福,女性应该有敢于追求的意识,哪怕像卡拉一样只有一小步。
那些阴暗、隐秘的欲望、原罪,是不会因为我们的否认或者忽视而不存在的。卡拉实际上可能对女性主义的自由和权利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但她清楚的是要为自己内在的欲望找到出口与方向。虽然作为替罪羊的弗洛拉之死带走了她这种欲望的“罪”,但这种原欲却一直存在,不能被否认。“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卡拉这一次的逃离虽然不是完全成功的,但勇于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对自己内在欲望的一种释放,是对自己内心的正视。克拉克作为作品中的权威,他并没有意识到潜藏在自己体内的欲望与原罪,他想逃避卡拉离开的罪,也有继续压制卡拉的欲望,因而他把弗洛拉作为“替罪羊”杀害。在这里,门罗借卡拉的逃离以及克拉克的反应来告诉人们,每个人应该用一直适合的方式去释放自己的阴暗面和欲望,去救赎自身,这样才不会以一种破坏的方式给自身与他人造成伤害。
在吉拉尔的《替罪羊》中,“替罪羊的死并无法真正治愈社会危机,但它的死能够肃清人际关系恶化的后遗症,它只对因危机搞乱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作用”。因而,门罗利用“卡拉的逃离而返、弗洛拉的神秘死亡”来暗示逃离并不能从实际上解决女性的不自由,相反带来的却是空虚与恐惧,逃离并不是女性追求自由的最佳方式,家庭和丈夫是可以成为女性个性发展的情感支点和心灵归宿的。正如故事的最后,克拉克对逃离返回的卡拉有了更多的温情和关爱,卡拉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只懂得屈服和顺从的羔羊。门罗认为女性应该在不自由与逃离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女性的自由并不是简单的逃离、盲目的追求,而是应该在原有家庭中、男权社会下找到适合自己的自由,要学会去平衡不自由与逃离之间的矛盾。
四、结语
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男性占据社会生活的主导,在性别意识较强的社会氛围中,女性权利与女性意识、男性行为与男性心理便成了许多作者关注的重点。门罗作为一名女性小说家,她从平凡的生活着手,对人性内在欲望、女性身体不自由与追求自由、男性社会压迫与女性独立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在《逃离》中,作者创造了一个象征女主人公卡拉的特殊形象——弗洛拉,将弗洛拉的失踪与重现和卡拉的逃离与返回密切相连,并利用家庭权威克拉克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将弗洛拉确认为“替罪羊”一般的存在。通过这种特殊的形象,作者使读者在感叹“替罪羊”悲惨命运的同时,对女性与男性、权力与欲望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告诉人们要正视自己的欲望与原罪,女性在争取自身自由时要选择平衡点。
{1} 〔加〕弗莱:《作为原型的象征》,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1987年版,第151页。
{2}{3} 〔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4} 荣格:《本能与无意识》,选自《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5} 王鑫:《西方文学中“替罪羊”形象的文化原型解读》,《齐齐哈尔大学》硕士论文,2012.
⑥ 陈玉涓:《论“替罪羊”原型在〈抽彩〉中的意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31页。
参考文献:
[1]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 卡尔·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 尼采.悲剧的诞生[M].李长俊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4] 李涛.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的“替罪羊”形象研究[J].外国语文,2012(1).
[5] 徐颖.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替罪羊”原型研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
[6] 李亚莉.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逃离》中的隐喻解读[J].长春大学学报,2015(5).
[7] 刘文婷.试析《逃离》中弗洛拉的神话隐喻[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5(1).
[8] 赵慧珍.加拿大英语女作家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9] 周庭华.逃离抑或回归——门罗的《逃离》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反思[J].国外文学,2014(3).
作 者:郝 丹,陕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